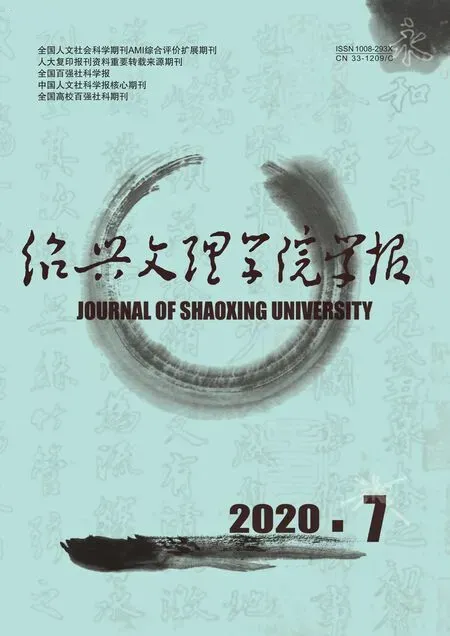上梁文“六诗”文体刍议
2020-02-24王志钢
王志钢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 党委宣传部,辽宁 沈阳 110023)
上梁文与我国古代上梁仪式有关。中国自古注重宫室屋宇的营造。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1]宫室中的明堂等建筑到了上梁阶段则意味着整栋建筑即将落成。
“天路牵骐骥,云台引栋梁。”古建筑使用梁架与斗栱,梁在建筑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七檁硬山构架为例,从顶向下依次为三架梁、五架梁、随梁等。梁上架檁,檁上承檐,梁下施柱——三架梁下施以瓜柱与五架梁相连,五架梁与随梁下承者为金柱,抬梁式构架槛柱同金柱间以抱头梁架构。高广宇殿,巍峨重顶,其构架更为复杂。如始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木结构建筑之一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梁架,平梁用大叉手,令拱承托替木与脊搏等。虫蛀中空之木,无益峻宇久安;细枝拳曲之式,岂堪尺雪迅重。梁承担着托举屋顶、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此,古人选梁极为谨慎,而上梁醮诸神灵、讨个吉利就成为一种民间习俗,与上梁仪式相关的上梁辞也应运而生。
我国早在商代就形成了卜宅、奠基、安宅等礼仪文化。《礼记·檀弓》记载了晋国大夫祝贺晋文子赵武府邸落成的“美哉轮焉,美哉奂焉”等祝词[2]。上梁辞的形成与这种祝词一脉相承,且随着时代发展和文学思想的变化而改变。就研究现状而言,近年,探讨上梁文文体的文章颇为丰富,如《上梁文文体考源》等[3],但对“中陈六诗”中“六诗”的文学思想起源等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较为有限,仅《论“上梁文”与辞赋之关系》等几篇文章进行了理论探讨[4]。本文试从上梁文“六诗”的文学思想起源及其与佛教文学、佛经俗讲的关系等角度进行探究。
一、研究范畴的界定
至宋代定型的上梁文“中陈六诗”的一般结构是以“儿郎伟”开头,后续以抛梁/上梁+东、南、西、北(或东、西、南、北)、上、下六个方位词,再于每方后分别缀以三句七言诗。此外,也有省略“儿郎伟”,也有改七言诗作五言者,但大体保留了“抛梁”或“上梁”(可省刻)+代表上下十方的方位词+每个方位词后面缀以三句诗的体制。
关于“儿郎伟”究竟何意,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从音乐演唱功能角度分析,有曲调名说、文体名说、唱诵的提示语说、呼辞说等观点。从语言学角度看,一种观点认为,“伟”是词缀,“儿郎伟”意即“儿郎们”,如吕叔湘先生(1985)认为,从词义角度看,在唐代文献中,“伟”有“们”意;从语音角度看,“伟”字喻母,“们”字明母,但“伟”或为明母字分化出的微母字,如周绍良先生(1985)认为“儿郎伟”意即儿郎懑(们)的探源。一种观点认为,“伟”是没有意义的衬词,且从音乐角度、歌唱功能看,“儿郎”也是和声用的助词,季羡林先生(1993)持此观点。还有研究者认为,“儿郎伟”与《悉昙颂》中的和声在语音结构及用法上均不同[5]。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日本学者小川阳等学者认为“儿郎伟”的内容类如祆祈福咒文[6],故应与祝祷有关。
本文不探讨“儿郎伟”的含义为何或是否有确切含义,本文主要研究唐末五代至宋,“六诗”受到何种文化话语影响,六个方位词最终定型为东、西、南、北、上、下而不可以出现其他方位词(如内、外、中);为何定型后的“六诗”中每句的组合形式多为“3/3/7/7/7”式或省略为“3/7/7/7”“1/7/7/7”结构。
二、影响因素分析
(一)“六诗”方位词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宋以前,题为上梁文的文献仅敦煌文献《□□唐天复元年辛酉岁一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囗窟上梁文》(斯3905)及《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月二十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龛一所上梁文》(伯3302)两篇。从文体来看,前者以六言韵文为主,后者为六言韵文夹杂骈体。此外,还有杨挺拟题《护军修造上梁文》(伯3757)一篇,也为六言韵文。可见,至唐末,流行于宋代的上梁文“六诗”体式尚未存在。唐末至宋定型的上梁文抛梁辞多使用方位词,且方位词多为东、南、西、北或东、西、南、北及上、下,并无其他常见方位词(如内、外、中)。在佛教话语中,东、南、西、北、上、下合称“十方”,与“十方有佛”观念密不可分。上梁文“六诗”方位词的选用或受到佛教文化与文学传播的影响。
1.学界关于上梁文方位词来源的考辨
关于上梁文方位词的来源,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为《两都赋》影响说,一为敦煌文献《儿郎伟》影响说。两说均有一定的合理性。
(1)《两都赋》影响说
有研究者认为,上梁文“六诗”的文体形式和方位词的使用应受到东汉班固《两都赋》中“五篇之诗”的影响,如班固《子虚赋》描写楚国的云梦泽使用了“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其上……其下……”的结构写法[4]。此说有一定合理性。但宋距汉未远,迄今未见宋、辽、金学者以及大体同一时期日本、朝鲜汉学者有此方面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的札记。上梁文“六方”与《两都赋》方位词可能存在关联,但也可能这种关联仅为巧合,姑存一说。
(2)敦煌文献《儿郎伟》影响说
有研究者认为,敦煌文献“东方有一鬼,不许春时出;南方有一鬼,两眼赤如日;西方有一鬼,便使秋天卒;北方有一鬼,浑身黑如漆。四门皆有鬼,擒之不遗一……”(伯2569)可为上梁文中六方抛梁驱邪求吉的参照[7]。此文体现了道教驱傩思想。道教驱傩思想的源头在《尚书·尧典》“宾于四门”“流四凶族”“四门磔禳”和《礼记·月令》“九门磔禳”可以找到[8]。从文化史角度考量,此文还明显受到中国五行思想影响。五行观念中,五方对应五季、五色:东方对应春季;西方对应秋季;南方对应夏季,其色为赤,故云“眼赤如日”;北方对应冬季,其色为黑,故云“身似黑漆”。这种道教驱傩思想与上梁文祈福禳灾的民俗文化思想是一致的。上梁文文体的形成与“儿郎伟”存在一定的关联,如敦煌文献《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月二十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龛一所上梁文》有三章便以“儿郎伟”领起。因此,可以认为,上梁文“六诗”方位词的确立过程或受到驱傩“儿郎伟”及道教文化影响,但现存驱傩“儿郎伟”中并未言及与上、下两方相关的民俗宗教活动。
2.佛教文化影响可能说
笔者认为,或还有一种可能,即“六诗”方位词的选用和最终定型受到了佛教文化中“十方有佛”观念的影响。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传播,到唐代更是名家辈出,宗派林立,信众遍及士、农、工、商。唐末,随着俗讲活动的普及,普通民众对佛教文化和观念更为熟悉。汉译佛经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世,以东、南、西、北、上、下为界(合称“十方世界”)。据唐代流传甚广的净土宗经典《佛说阿弥陀经》记载,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均有佛:“东方亦有阿閦鞞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名闻光佛、大焰肩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北方世界有焰肩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下方世界有师子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上方世界有梵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9]不仅如此,十方之佛均说法赞叹阿弥陀佛无量功德,度化众生。此经记载,“佛”尤其告诉“六道众生”,当信赞佛之功德,必有“诸佛”之护佑。不止民间文学,上流社会的文化精英们也在诗、文中表现出“十方世界”的观念。上梁文这一文艺新样式或受到来自佛教话语的影响。
唐代俗讲和变文绘画的传播促进了“十方有佛”护佑信众观念的传播,或影响到五代至宋初上梁庆典仪式祝祷时有意识地选择东、南、西、北、上、下。以敦煌上梁文《维大唐长兴元年癸巳月二十四日河西都僧统和尚依宕泉灵迹之地建龛一所上梁文》为例,祈愿文字直言:“愿我十方诸佛,亲来端□金莲;荐我和尚景祐,福祚而(如)海长延;……自此上梁之后,高贵千万年。”文中祈求“十方诸佛”护佑的心情溢于言表。
上梁文与驱傩“儿郎伟”有密切关系。敦煌文献《儿郎伟》末二句云“谨请上方八部,护卫龙沙四方”(伯4976),体现了佛教在唐五代民间腊月驱傩祈福活动中的影响。其中,“四方”即东、西、南、北。上方区别于下界,乃天龙八部所居之所。文中虽未出现“下”,但民众繁衍生息之处即为与天龙八部所处时空不同的“下界”,“护卫四方”体现了佛教护法神对人间四方的保护。
据学者考证,北宋王禹偁作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的《单州行宫上梁文》是今见宋代最早的上梁文[10],“六诗”方位词已由敦煌文献模糊的“十方”方位词遽然改为定型模式。此后,杨亿、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上梁文均与这一体制一致。《宋史》及其他文献未有一篇认为王禹偁为上梁文文体的开创者或奠基者。在唐末五代至宋初,佛教或许与道教驱傩活动共同助力了上梁祝文“六诗”中六个方位词的确立。有研究者认为,宋代盛行的上梁文体中的“六诗”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民俗文化浸润下的产物[3]。
(二)“六诗”方位词东西南北连用形式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
宋以来,“六诗”方位词中的“四方”有作东、南、西、北顺序的,如辛弃疾《新居上梁文》等;也有作东、西、南、北顺序的,如王禹偁《单州行宫上梁文》、苏轼《白鹤新居上梁文》等。佛典中,四方顺序一般作东、南、西、北,这受到中国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诗歌创作中,东、西、南、北的语言顺序与我国诗歌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宋以前,中国诗歌中方位词东、西、南、北入诗的一般形式大体有:
1.以“自……自……”句式组成四言诗句
《诗经》《楚辞》开以东西南北方位词入诗的先河。如《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11]即以“自……自……”句式构成诗句。
2.东西南北四字连用
四言诗中,屈原《天问》“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东西南北,其修孰多?”[12]中,“东西南北”四字连用,组成四言诗的一句诗句。文人七言诗中,如唐代白居易《寄题杨万州四望楼》“江上新楼名四望,东西南北水茫茫”[13]1186等的写法是对屈原《天问》东西南北四字连用诗法的继承和发展。
3.以“东西”与“南北”各领起一句组成一联
三国时期,文人五言诗中,诗人开始以四个方位词中两两组成一组起头并置于句首,后三字缀以物色描写,如曹植《吁嗟篇》:“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14]423到了南北朝时期,诗人们创造了更为生动、丰富的表现形式,如王褒《别王都官》“东西御沟木,南北会稽云”[14]2340,“东西”与“南北”对言,组成一联。文人七言诗中,一些诗人将“东西南北”四字分用于两句诗中,或置于句末,或置于句中,分咏不同景物,如唐代元稹的《青云驿》“大帝直南北,群仙侍东西”[15],白居易《岁暮寄微之三首》(其二)“紫垣南北厅曾对,沧海东西郡又邻”[13]1650,这种写法或是对王褒《别王都官》等方位词入诗语的文学表现形式的继承和创新。
4.民歌中“东西南北”各领起一字,组成四个诗句的诗歌结构
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文学中出现了东西南北四字分嵌入四句诗的文学表现形式,如汉乐府《江南》:“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16]384;再如,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辞》中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16]374。
(三)“3/3/7/7/7”结构与隋唐五代燕乐、敦煌歌辞等的关系
1.隋唐燕乐及敦煌歌辞等民间文学的影响
从音乐史、文学史角度梳理,有研究者探讨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中的谣歌“3/3/7/7/7”体,认为唐五代出现了此体杂言歌辞,其中既有文人之作,也有教坊歌曲舞曲、民间歌谣及佛教赞颂;到了中唐,元、白诗作中“3/3/7/7/7”体杂言歌辞数量较多,在当时此体已经常见[17]。敦煌歌辞等民间俗文学对上梁文“六诗”文体的定型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敦煌歌辞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以三言词领起,构成“3/7/7/7”型诗法。《敦煌歌辞总编》收录了以一天的十二时辰入诗的作品,如《十二时·天下传孝》[18]1297-1298,每章四句,以时间词领起,如“平旦寅”“日出卯”“食时辰”“隅中巳”等;时辰之语后面三句引用民间传说、佛教思想讲人生哲理,语言浅近易懂。十二章的章首均为三字,每章四句且均为“3/7/7/7”节奏类型。《十二时·佛性成就》[18]1361-1362《十二时·法体》[18]1389-1390《十二时·学道》[18]1406-1407等作品与之结构型一致,且每章首句三字均一致。此外,敦煌歌辞中还有每十年为一段、分十章写人生各阶段箴言类的作品——《百岁篇·丈夫》[18]1306-1307。从结构来看,其与《十二时》相似,均为每章四句,每章二句至四句的节奏型均为“7/7/7”。所不同处仅在于每章首句的字数:《百岁篇·丈夫》每章首句与二、三、四句均为七言;《百岁篇·垅上苗》[18]1324-1325和《百岁篇·池上荷》[18]1331-1332结构上则与《十二时·天下传孝》《十二时·法体》等相同,均为“3/7/7/7”节奏类型。
以三言时间词为句首,结构也为“3/7/7/7”型的歌辞还有以“五更转”命名的系列歌辞,如《五更转·无相》[18]1455。歌辞共五章,每章首句均为更名,次第为“一更浅”“二更深”“三更半”“四更迁”“五更催”。《五更转·太子成佛》[18]1473与之结构型相同,每章首句依次为“一更初”“二更深”“三更满”“四更长”“五更晓”。此外,《五更转·顿见境》[18]1424《五更转·南宗赞》[18]1429《五更转·南宗定邪正》[18]1443-1445等句首均为三言。
从短语结构型来看,《十二时·天下传孝》《十二时·佛性成就》《十二时·法体》《十二时·学道》首句的结构可概括为“XX”+时辰名,构成同位短语;《五更转·无相》《五更转·太子成佛》等的句首均为一至五之间的序数词(依次写入)+更字+一个汉字,构成主谓句式。
上梁文抛梁辞“XX”+方位词名(东、西、南、北、上、下)的语言结构中“XX”虽为V+O模式,但与之有相似之处。十二时、五更、百岁与“东南西北上下”十方在思维结构上有近似之处。前者表示时间的有序更迭,后者表示空间上的次第变化。上梁文抛梁辞“7/7/7”部分的内容也可找到与十二时、五更转、百岁篇等相似的模式。此部分与方位词之间的区别一样,每一章或分别描绘某一季节的景色,或阐述某一方面的哲理。《敦煌歌辞总编》收录了大量的“十二时”“百岁篇”“五更转”为题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民间传播过程中,其结构上的“3/7/7/7”文学形式或影响到了上梁文抛梁歌的文体结构。
2.敦煌变文押座文的影响因素
敦煌变文中还出现了俗讲讲话前用作开场白的押座文。我国古代戏曲的开场诗、《西游记》等明章回体小说置于每章章首的律诗均受到俗讲押座文的影响。《敦煌变文集》中收录的《八相压座文》[19]823-826《三身压座文》[19]827-828《维摩经压座文》[19]829-832《温室讲经压座文》[19]829-832等均为七言诗形式。在俗讲唱词中,也有“3/3/7/7/7”体式[17]。
“六诗”是宋代定型的上梁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梁文是《礼记·檀弓》以来建筑落成典礼上重要的祝颂辞。庆典上,念诵祝辞后还有其他相关庆祝活动。上梁文“六诗”地位类如佛教俗讲讲经前的押座文。
(四)“六诗”重章叠唱的艺术手法源自《诗经》
定型后的上梁文“六诗”每诗首句均以“抛梁”领起,这种重章叠唱的艺术手法其文学源头可追溯到《诗经》。《诗经》中广泛存在重章叠唱的艺术形式,如《秦风·蒹葭》中每章首句的咏唱——“蒹葭苍苍、蒹葭萋萋、蒹葭采采”及每章次句展示的与各章首句对应的物象变化之辞——“白露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等就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这种影响或为文学影响中的“远因”。这种文学表现样式已普遍渗透到后世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题材作品的文化因子中,对上梁文的影响应该是潜默的,不易发现。从音乐角度看,重章叠唱营造的回环往复、余音绕梁之美有助于文艺审美价值的提升和传唱,其音乐特点类如西洋音乐的二部曲式、三部曲式的表现形式[20]。
三、结语
从文学文献学角度看,“儿郎伟”+抛梁+方位词的结构不是上梁文最早的文学形态,譬如唐末的上梁文就没有这种形式。《全唐文》卷847收录了五代李琪的《长芦崇福禅寺僧堂上梁文》,此文“六诗”体例完备,与宋代流行的上梁文体大体一致。一些学者认为此文约作于唐天祐三年(906)[21],也有学者认为此文为宋人所作[22-23]。从文学发展史角度考量,若此文确为唐末文坛名气一般的李琪所作,则唐代文人尤其是与其大体为同一时代的上梁文作品或应非只此一篇,然传于今者只此孤证;即以李琪论,若其以上梁文名世,则史传或有所记载,其所作存世上梁文也应非只此一篇,即唐五代地位远高于长芦崇福禅寺的梵宇或重要道观、儒学、诸王显贵的宫室府邸落成似也应邀请其撰文,而其名下此类作品并未另有一篇传于今。此文与宋代文体定型的上梁文的文体相同,且“六诗”省略了六个“抛梁”(与宋代中叶以后“六诗”中省略六个“抛梁”字样的印刷时节约成本的方式高度一致),而宋初并无这种省略用法。因此,暂且存疑。
上梁文“中陈六诗”的结构是到宋代才定型的。这提示我们,上梁辞自南北朝时期出现雏形后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发展出宋代流行的文体。也即是说,从流行的领域、阶层来看,官方和士大夫阶层并未过多关注并有意识地对之加以雅化,上梁文的文体定型化进程更多是在民间的不断摸索中完成的。到了宋代,上梁文“中陈六诗”结构初具规模,才有了如苏轼等士大夫阶层的雅化创作。在探索过程中,佛教变文、俗讲、敦煌歌辞等或起到了助推作用。
上梁文文体形成后,特别是文人有意识地进行“骈文+诗歌”模式的创作后,其文学价值超越了民俗价值,文学性超越了实用性。这对我国周边国家如日本[24]、朝鲜[7]的上梁文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当今,深度研究中国以及国外汉学古籍中的上梁文,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性传播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