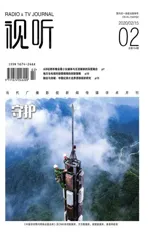记忆·公信力·自由:数字化时代被遗忘权与新闻传播的冲突
2020-02-24□杨艳
□ 杨 艳
我们每天浏览、下载海量数据,同时是数据的生产和上传者。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媒介记忆功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革新。海量的数据丰富了媒介“记忆库”,使其保留信息的能力得以提升;数字化的存储方式实现了海量信息快速检索,以简单的技术操作取代繁琐的人工资料调取;复杂的信息根据内容、性质等属性被分类,再以数据链接的形式建立起关联性,为媒介记忆的精准提取提供线索和指南。然而,这种便捷的方法背后,逐渐凸显出新闻生产方式和被遗忘权的激烈冲突。
一、被遗忘权溯源
1995年,欧盟在相关数据保护法律中率先提出“被遗忘权”概念,强调任何公民均有权要求相关部门在其个人信息不再需要时予以删除。2011年的“冈萨雷斯案”可以说是被遗忘权的开端。2012年起,欧盟委员会着手制定保护公民被遗忘权的相关法律。直到2014年,欧盟最高法院要求谷歌将关于它的公告链接从搜索引擎中删除。同年,欧洲法院做出裁决,规定普通公民享有个人隐私信息的“被遗忘权”。“谷歌西班牙公司案”作为被遗忘权接受欧盟司法检验的标志性事件,以谷歌败诉尘埃落定,随后,谷歌出台了在线申请程序,正式接受欧盟用户的被遗忘权申请①。
被遗忘权自确立以来被不断发展,在世界上呈扩大的趋势②。随着这一热潮的发展,诸多学者建议将其引入我国法律及其他学术领域研究范围。2015年,任甲玉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成为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当事人在进行以自己姓名为关键词的搜索时,发现其中有她详细的从业经历,并对其现在的工作造成困扰。任甲玉认为百度公司侵害了其名誉权、隐私权,遂起诉百度公司,请求其删除相关链接。与“冈萨雷斯案”不同,北京市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
截至目前,法律界对被遗忘权依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界定。吴飞教授将其归纳在个人隐私权范畴,将被遗忘权视为隐私权在互联网时代延伸出来的一种新的权利类型③;彭支援先生认为被遗忘权属于隐私权的范畴,是隐私权的延伸④。杨立新教授提出了比较实用的做法:在理论上,他同意将被遗忘权归入个人信息权的范畴;在司法实务上,他认为目前将被遗忘权作为隐私权的内容比较合适,这样可以依据现有的保护隐私权的法律规定对其进行保护,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⑤。
笔者认为,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是一种特殊的网络表现形式。为使受众更好地理解其含义和实践,应将其归入个人信息删除这一浅显易懂的层面。目前只有欧盟及日本、俄罗斯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和地区承认被遗忘权。中国在引入这一概念时也遭遇诸多困难,如与新闻传播的冲突就是一个鲜明例子。
二、数字化时代传播新像
互联网的普及开创了全新的人类认知、传播新范式,同时带来了储存、运行、记忆的新方式,云断储存让数据变得日益庞大,信息就像刺青一样被刻在皮肤上,数字记忆可以得到无限延伸⑥。这种全新的记忆功能被称为“媒介的数字化记忆功能”。伴随着媒介记忆功能的革新,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也迎来了新的发展。
(一)传播新模式:多维度牵连报道
传统媒体时代,记者主要靠线人提供素材,信源稀少,媒介保留信息主要是不计其数的报纸,同时受版面、刊发时间限制,多维度素材不能同时见报。因而,记者或编辑在写作时只能就事论事,不能对事件进行延伸性处理。随着新媒体的到来,较大的信息存储空间和海量的用户自产内容仍碍于“信息壁垒”的限制,很多信息无法接触。媒介记忆的提取依赖并不发达的数据链接和低效率的人工检索,信息之间建立的关联性不够精准,因此也很难在传播中实现真正的多事件牵连报道。
随着媒介记忆功能的发展和革新,事件报道就变得不再单一和固定。一方面,数据库建立起来,国内较著名的有人民网和新华社的新闻大数据库。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能从海量数据堆里迅速抓取到所需素材,具备了多事件联合报道的技术基础。同时,数据已经渗透进生活日常,媒介更容易获取信息。另一方面,媒介技术、大数据运用技术日益成熟,数据挖掘功能异常强大。如搜索“郭美美事件”,就会呈现出相应的“深圳四胞胎”“罗尔事件”等相关链接。互联网精准的链接和数据技术找到了各类素材的相关契合点,只要记者善加利用,便可以在此基础上完成多维度牵连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报道模式丰富了媒介内容。
(二)传播新效果:信息刻板印象被改变
瑞士心里学家皮亚杰认为,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认知模式,叫做“认知基模”。这是一种先入为主、自上而下的过程,当我们接触到一个新信息或新事物、遇到一个新事件或者进入一个新的场所的时候,我们过去的相关经验和知识会引导我们迅速地对新的状况做出认识、推理和判断,并及时地做出态度或行为反应⑦。这一理论后来被引入传播学领域,并广泛应用。
大数据被熟练操纵之前,经由媒介报道出来的形式大都是单一、固定的,受众在极短时间内接触到同类事件的概率较低,因而对事件的深刻印象与认知往往是印象深刻的。当媒介具备了强大的数字化记忆功能之后,这一局面大大扭转。人们在浏览了一个事件的相关信息之后,往往会在数据推送的情况下阅读相关事件的延伸性、深度报道,甚至是同类事件的信息,“捆绑传播”成为常态。通过大量、频繁接收这类信息,受众在阅读这些报道时的感触会多于单独接受某一类消息时的印象,之前对事件的固定认识受到冲击,印象被改变,形成新的认知和意见。
大数据时代,借助媒介的数字化记忆功能,无论从频度还是深度而言,信息刻板印象逐渐被减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
三、被遗忘权对新闻传播的冲突
数字化记忆功能强调对个人数据信息的深入挖掘,其内涵与被遗忘权背道而驰。因而,被遗忘权与新闻传播的冲突必定存在。
(一)媒介公信力遭遇挑战
媒介具有自动遗忘的功能,当新的事件发生并被频繁报道的时候,旧事件逐渐被掩盖和遗忘,被遗忘权所倡导的内涵正是对这一现象的自然补充。
大数据技术使得数据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证据和信息支撑。随着报道模式的日新月异,数据新闻活跃在各大媒体,成为一种重要的新闻传播模式,对新闻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被遗忘权的实行,很多有着关键作用的数据信息被删除,于信息采集者是不利的。记者或者编辑容易陷入信息空虚状态,信息透明度降低甚至消失。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新闻文本一旦缺失,相关数据和说明性文字、图文将显得毫无说服力。这会给新闻价值和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引起舆论哗然。另一方面,被遗忘权允许信息主体删除一些与自身不恰当的、不再具有价值的图文信息。这些信息单独来看或许并不具备一定的价值,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事后的舆论,那些之前被认定不再具有价值的图文或许会有重新启用的可能。这时候,信源的缺失就容易对新闻采集者造成极大不便,甚至被怀疑信息来源的可信度。这些被删除的信息会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从业者信息,不利于个人业绩和传播主体的发展。
(二)新闻自由现状堪忧
有人说新闻是赤裸裸的,毫不留情地披露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恰好是对诸多人信息的良好保护。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存在令人担忧的冲突。
“谷歌诉西班牙信息保护局”一案中,谷歌公司按照法律要求,在删除当事人相关链接的同时也删除了大量相关的新闻报道、微博信息。但事后英国多家媒体反映未能在谷歌上搜索到与关键词相关的报道文章,随即对谷歌进行舆论申诉。谷歌最后禁不住舆论压力着手恢复相关链接和新闻报道。这个环节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大量的数据、信息并非人力所能整理的,而计算机的排查是根据人所设定的程序进行的,有强大的机械性,并未能精确恢复所有数据信息。这无疑让大家看到了被遗忘权造成的实际操作难度。
同时,作为当事人,当知晓自己曾经申请删除的数据并未被删除,被遗忘权并未保护好自身权益,谷歌公司这种敷衍态度并不能被真正接受。信息控制者仅仅删除链接、图片等内容而保留了元数据,这都将是执行被遗忘权的灰色地带。灰色地带隐含了诸多可能性,被保护在“使用例外”的新闻自由很难全身而退。
(三)新闻传播中特殊人群的艰难抉择
新闻传播的目的是广而告之,但同时要兼顾特殊人群的权益、隐私。大数据时代,个人隐私像是被放在玻璃罩里,透明得像是一览无余。但在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的规范下,传播者始终要铭记保护特殊人群隐私不被恶意泄露。被遗忘权更是对特殊人群的隐私、权益保护提供了保障。
比较有显著性的特殊人群有三类:未成年人、公众人物、犯罪分子。无论是传统媒体或是互联网时代,还是如今的数字媒介记忆时代,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益始终被放在首位,他们享有特殊法律法规保护。新闻传播实践中,既要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避免曝光敏感信息,又要保证新闻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传播消息和知识并引起社会重视。因此在报道未成年人犯罪的过程中,“度”的把握至关重要,这也是对新闻把关人的严格考验。在被遗忘权提出之前,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会因公众知情权而被披露无遗。有人在公众人物行使被遗忘权时产生疑问,认为公众人物很多时候是某些社会大众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他们的言谈举止影响甚广。鉴于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行使该权利时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那些有不良影响、恶性事件的公众人物,不应该被删除不光彩的历史。同样,在新闻传播中,新闻应该对此类信息斟酌考虑。此外,针对犯罪分子,新闻传播应该减少对其的舆论中伤,公正客观报道。但有人担忧信息控制者无法全面掌握此类群体的全部事件,在行使被遗忘权过程中容易造成犯罪历史被刻意删除、洗白,这样就不利于大众人身安全和社会安定的维护。
对于特殊群体是否应该享有被遗忘权、怎么行使这一权利,新闻传播领域目前还未有明确定论,作为信息传播者,还应斟酌后再定夺是否报道,如何合理报道。
四、数字化时代如何化解被遗忘权与新闻传播的冲突
(一)司法给予参考模板
法律具有强大的效力,被遗忘权实际操作的方方面面还有望司法程序给予参考蓝本。目前已有的被遗忘权法规中,新闻传播排除在外,但并不代表过往的、已被报道的新闻信息不具有新闻价值。任何信息传播者都无法准确预测数据信息的未来价值。为了保证大众的知情权和避免这种冲突,司法应该介入“审判”甚至是删除程序。作为个体的被遗忘权信息操作者,容易因各种客观、主观性因素对信息产生误判、错判,甚至是故意删除。司法在这一方面能够发挥强制性作用。
(二)在实际操作中避免冲突
中国当前的新闻实践活动中,维护受众知情权的可行办法有“匿名处理”和“模糊处理”。部分学者对“匿名处理”有所质疑:从法律程序上来讲,“匿名处理”极易陷于丧失消息源信任或者承担法律后果的两难境地。在实际新闻报道中,有意隐去敏感性信息,既保护了信源安全和真实性,也能够把合理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还给公众。模糊表达使新闻传播者在阐明观点、表明立场时避开因关联被删除的危险,既可以保留报道信息,又可以表明立场、传达立意。
(三)人性角度减少冲突
很多学者表示,被遗忘权在现实情况下的操作应与公众知情权、新闻自由相契合,要视情况而定,采取措施。新闻传播终究还是要站在保护人权隐私的立场上从事传播活动。从人性化角度出发,数据存储应当“按周期遗忘”,而不是让用户随意搜索,如新闻报道中的弱势群体一定程度上需要被受众遗忘。中国拥有庞大的数据群体,这些群体应遵从申请人意愿,按计划删除相关数据。如此,被遗忘权同新闻传播的冲突便可得到弱化。
五、结语
媒介的记忆功能是新闻传播活动的信息、技术基础,数字化时代强大、精准的数据挖掘、分析、捕捉能力,给新闻传播带来了新的景象。但我们也应看到被遗忘权产生的新问题,看到其与新闻公信力、新闻自由和新闻传播中的特殊人群的冲突。被遗忘权的提出是对个体隐私的保护,是新闻人文关怀的体现,为了化解二者冲突,还应从司法、技术、人文关怀等角度多加思考,既做好新闻传播,又让被遗忘权在这一领域发挥恰当的作用。
注释:
①郑志峰.网络社会的被遗忘权研究[J].法商研究,2015(06):50-60.
②张里安,韩旭至.“被遗忘权”:大数据时代下的新问题[J].河北法学,2017(03):35-51.
③吴飞.名词定义试拟: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07):13-16.
④彭支援.被遗忘权初探[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36-40.
⑤杨立新,韩煦.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J].法律适用,2015(02):24-34.
⑥[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M].袁杰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3-6.
⑦https://www.360kuai.com/pc/97a3f3d2cb9607f0a?cota=4&kuai_so=1&tj_url=so_rec&sign=360_57c3bbd1&r efer_scene=so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