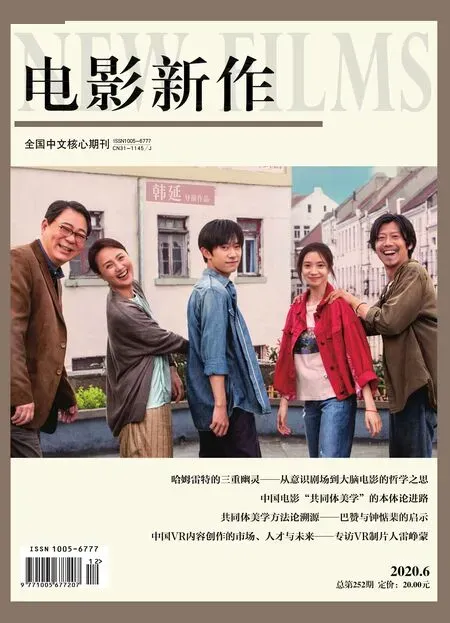共同体美学方法论溯源
——巴赞与钟惦棐的启示
2020-02-24饶曙光兰健华
饶曙光 兰健华
当前,疫情的冲击使中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剧烈复杂的变化。而作为文化产业新龙头的电影产业,同样也处于一个矛盾叠加期、利益分化期和发展模式的更新换代期。从当下的角度看,这无疑会给产业发展带来一定的阵痛,但若以共同体美学进行长远的方向性指引,或许能顺利地解决当前中国电影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痼疾,并为中国电影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不可否认,共同体美学这一理论提出的时间不长,理论内涵亟待完善和扩充,但学术和业界的影响力已经开始逐渐显现,成长空间无限广阔。共同体美学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安德烈·巴赞和钟惦棐两位电影理论家的启示和影响。不难发现,二者在理论建构层面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理论生发、植根且作用于本民族的电影实践。因此,通过对他们思维体系和理论内涵的再度发掘和爬梳,或可寻找到适用于共同体美学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和路径,助力理论体系进一步系统化和应用化,进而为中国电影由大国走向强国贡献理论智慧。
一、“未竟的启蒙”:共同体美学的理论生发逻辑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不断突破禁区、充满探索精神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热情、勇气、希望和憧憬的年代。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启蒙的时期”。众数知识分子带着“睁眼看世界”和“革新旧文化”的期望开启了自我个体价值的漫长追索。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思想解放的大旗徐徐升起,“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解读和阐释的热潮,延及哲学社会科学、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等多个领域,形成1980年代蔚为壮观的‘文化热’”。
在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经历过十年浩劫桎梏的中国电影,在与各类文化思潮的激烈碰撞下,一方面通过历史反思逐渐摒弃了“政治论”和“工具论”等传统创作观念,倡导回归艺术本体,尊重艺术的生产规律与创作规律,并“有意识地把人从‘阶级斗争链条上的一环’还原成具有独立个性的人,它反映了电影艺术家对人的价值、尊严的热烈追求与对人的本质力量实现的全面憧憬”。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汲取西方各种电影理论和经验,希冀通过“西学东渐”的方式来丰腴自身理论体系,推动电影题材、风格和样式的多元化创作实践,打破极“左”思潮设置的艺术和创作禁区。
正是在“文化热”的时代洪流下,中国电影迎来了一个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黄金年代。诚如罗艺军先生所言,“八十年代的论争与电影创作上的创新浪潮紧密切合,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进而使中国电影得以快速发展,并以崭新自信的姿态一次又一次地登上国际舞台,发出响彻时代的“中国之声”。
历史地看,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良性互动格局的形成是以1979年白景晟的《丢掉戏剧的拐杖》、钟惦棐的《戏剧与电影“离婚”》、李陀和张暖忻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三篇文章的发表所引发的电影观念大讨论为肇始的。《丢掉戏剧的拐杖》和《戏剧与电影“离婚”》两篇文章从本体论的角度角度出发,主张电影要脱离“戏剧化”和“舞台化”,认为只有摆脱传统戏剧思维和模式的束缚,挖掘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自身的潜力,才能推动中国电影“放开脚步,在电影创造的道路上大踏步地走”。而《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则从电影艺术表现形式的角度出发,观照了中国电影落后于世界电影的原因,强调电影语言要持续更新,要“形成一种局面,一种风气,就要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大讲电影的艺术性,大讲电影的表现技巧,大讲电影美学,大讲电影语言”。如果说,前者通过经验反思宣告了新时期电影意识的最初觉醒,那么后者则立足于现代化语境对未来中国电影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格局提出了构想。
随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上升为第四代导演的艺术宣言和美学旗帜,《邻居》《沙鸥》《都市里的村庄》等一批“纪实美学”电影相继出现,从创作实践层面向传统戏剧化的电影创作模式发起了挑战,“有意识地实践着对于探究影像本原的本土化努力”,同时也从理论建设层面进行了回应与追问。但迫于改革初期历史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模式的局限性,作为纲领性宣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在理论表述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同时作为倡导者和践行者的“第四代”导演在理论解读上也可能失于片面,进而导致电影语言现代化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偏差,即完全否定电影的戏剧性,强调电影镜头的本真性和时空的表现性与再现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种偏差导致部分创作实践走向了另一种远离通俗性的极端,却是电影语言螺旋式创新和进化过程中的必由路径,因为它为本就模式化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模式打开了另一扇窗,找到了另一种可能性。
如今回看,《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对巴赞理论的挪用,或许是一种刻意的“误读”。不难发现,文中并无意还原巴赞理论的本真内涵,而是意在借助巴赞理论反对传统戏剧化的电影创作模式和戏剧化所造成的“虚假”创作。这种“借他人的火,煮自己的肉”的理论引介方式,虽然在表述上有失偏颇,但却开阔了电影界的理论视野,为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奠定了基础。
80年代初期,巴赞的电影理论尚未被真正消化,电影界又通过《世界电影》《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电影新作》《影视艺术》和《世界艺术与美学》等期刊、刊丛以及《外国电影理论文选》《电影理论史评》《电影美学》等著作将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意识形态、女权主义、叙事学、文化研究等西方现代电影理论和批评方法密集译介到中国。同时,中国学者还邀请尼克·布朗和罗伯特·罗森等西方学者多次赴中国讲学。西方现代电影理论随之被广泛应用于中国电影的批评实践。在胡克先生看来,“中国学者应用现代理论的基本特征是:解读电影,理解社会,即:以中国电影与社会为研究对象,以西方现代电影理论为武器,把电影理论与批评结合起来,把电影批评和社会批评结合起来。”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现代电影理论“雁行式”地传入中国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和批评视野,但由于其本身具有“鱼贯式”的发展特征且中西文化本身具有差异性,不免导致西方电影理论与本土语境存在龃龉,进而在具体阐释和批评实践中出现“误读”或“错用”。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电影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的现代转型,使其跃出了传统创作与实用的层面,指向了更为独立的文本表意研究,进而得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大学教育体系,“并逐渐与以报纸、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电影批评分道扬镳”。
然而,80年电影理论批评“西学东渐”风潮越演越烈时,阐释本身又出现了另一种问题,即过于注重理论,忽视实践,使理论批评丧失了及物性。众所周知,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传统是以具体创作实践为对象,同时又以改善、执导和推进电影创作实践为目的。诚如钟大丰先生所言:“在中国电影的传统里,对于电影理论的认识和对电影创作规律的认识是等同的。”这种研究和批评方式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却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是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实现互动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西方现代电影理论虽然可以使研究和理论批评超越经验事实不再依附于创作实践,但却容易陷入“宏大理论”的陷阱。
所谓“宏大理论”,在美国学者大卫·波德维尔看来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体,“最著名的化身是由各种学说规则构成的聚合体,这些清规戒律来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以及各种变异了的阿尔都塞式马斯克主义。”在宏大理论的统摄下,研究者和批评家致力于将每一种电影现象都归于他所熟悉的正统理论所认定的法则和类型中去,进而使理论和批评趋于同质化和空泛化,阻碍了电影理论自身的发展。对此,大卫·波德维尔提出了“中间层面的研究”方法。即通过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将电影研究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诚然,大卫·波德维尔以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认知心理学的“中间层面研究”取代“宏大理论”的构想也因无法缓解西方理论与第三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遭受质疑,但其所强调的经验性和实用性是使理论批评走出学术“高阁”与实践建立关联和互动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能上升为“第四代”导演的艺术宣言和美学旗帜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入9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使电影业遭遇了转型阵痛。电影创作渐入谷底,批评对象的匮乏使理论批评由众声喧哗转入了“衰微”的状态。同时,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也使“以‘艺术、审美’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及其观念也发生了‘位移’”。电影意识的启蒙和对于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追求被更为尖锐的市场处境和生存需求所压倒,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鸿沟进一步扩大。这种状况至今仍旧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诚如陈山先生所言:“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电影产业的出现早已将‘无根的游谈’远远地抛在了后边。”但日趋复杂的中国电影实践,以及在多元博弈中所遗留下来的棘手问题,却亟待通过新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批评体系去给予指引和解决。不过,前人的经验已经证明单纯依靠西方理论显然是不可行的,必须通过植根于本土的理论批评体系去对本土电影实践所存在的特有问题给出针对性解决方案。需要承认的是,我们本土的理论批评体系尚处于苍白失语的境地,但共同体美学理论构想的提出正是走出这种境地的有效途径,因而必须通过恰当方法论的寻找去对其内涵进行补充和完善,才能使其发挥出理论批评的强大力量,重建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重启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黄金年代,进而助推中国电影顺利地向电影强国目标迈进。
二、“电影是什么?”:对巴赞理论及其传播的再认识
大卫·波德维尔曾在其《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大理论终结的构想。但显然,这只是一种未竟的想象。毕竟经过时间的沉淀他自己也发现“诸如文化理论、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分析和酷儿等理论的研究还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不认为它们会走向消亡。”显而易见,我们无法预测电影研究和理论的最终走向,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本身“没有独一无二的理论系统”,因为电影理论的演进、发展和嬗变与电影创作相同,从来都不是以取代、否定和颠覆传统为前提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大理论’只是学术研究方法的一种取向”,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也不可否认其独特性。
毫无疑问,电影理论体系的建构必须具备一种宏大的跨学科视野,而这也是共同体美学理论建构的一种方法取径,即对传统和现有的理论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有机生成,然后化为新的创造。但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出乎其外,也须入乎其内。电影理论体系的建构始终不能脱离对电影本体的关注和认知。尤其是当下,媒介融合的语境以及不同学科领域理论的汇集,使电影的身份和理论划分变得模糊和摇摆,合法性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因而必须追根溯源回到电影理论的历史传统,重新确立电影理论体系的生成路径。
众所周知,电影理论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一个关键人物——安德烈·巴赞,他对电影艺术和电影理论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巴赞并不符合理论家的身份的特征。因为他从来没有一部系统的、严谨的、有自身逻辑、概念演绎的电影理论专著,而只有乱杂分散在各种杂志、报刊和小册子中的鲜活、充满爱心、充满思想的影评,他更喜欢通过这种方式去与电影创作者和评论家进行含蓄的理论对话,这也是他的理论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不同于让·米特里、爱因汉姆、麦茨和德勒兹等颇具“学院”气质的电影理论家,巴赞被称为“放映机前的蒙田”,即他的电影思想表达是一种蒙田式的散文表达,一种典型的法国传统思想表述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既是电影思考者,更是放映员。他右手放着电影,左手握着力透纸背的羽毛笔”。巴赞始终“坚持在银幕面前讨论电影的理念”,并以平实的语言书写着最具理论深度和高度的文章,但文中从来没有先入为主的理论堆砌,只有对眼前影像世界的深入洞察。“在他的帮助下,电影理论第一次不再是宣告或处方,而是描述、分析和演绎。”
在许多人看来,巴赞是“法国迷影精神之父”。所谓“迷影精神”,即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偏见和自我喜好偏见的“电影至上精神”。正是这种“迷影精神”让巴赞放下凡尔赛高等师范学生的优越身段,带着扎实的理论储备和非凡的美学修养,深入民间传播电影文化、创建迷影俱乐部和对世界电影产生重大影响的《电影手册》杂志。因而巴赞教会我们的首先是热爱电影,不仅仅是口头上,而是深入骨子里,终身须臾不可离开电影。毫无疑问,“迷影精神”是巴赞电影理论得以滋生的源泉,但与德吕克、卡努杜等受艺术思潮影响,缺乏深厚理论储备的迷影派影评人不同,巴赞的电影思想深受萨特和柏格森等哲学家的影响,进而让他在评析电影时具备了哲学和美学的视野高度。正是这种以哲学思考为基础的辩证逻辑,让巴赞在短短13年的写作生涯中主要关心的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不是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而是问“艺术是什么?”和“电影是什么?”。
如今,通过对巴赞文章的梳理,后人逐渐得以洞悉“电影是什么?”这一问题背后巴赞尝试建立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但随着数字时代的莅临,又使作为其理论体系基石的“影像本体论”备受质疑和冲击。在巴赞看来,摄影的本质意义在于揭示真实,因为在所有艺术中唯有摄影“具有不让人介入的特权”,而电影依赖于摄影,所以“只有在作为真实的艺术时,才能达到圆满”,亦即“影像与客观现实被摄物的统一”;但电影又是超越摄影的,因为电影能够即时记录事件,形成“物体持续时间的印记”。这一理论之所以能够长期占据理论的统治地位并近乎上升为电影制作的“真理”,根本原因在于“它把真实作为电影美学的最高范畴加以阐释,并赋予真实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数字时代的来临,让许多学者看到了巴赞“影像本体论”被颠覆的可能性。因为当电影和摄影的介质载体由胶片转化为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代码时,电影再现现实的索引性(Indexicality)关系或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电影已经可以不是对客观影像的记录,而是纯粹人造的拟像物。因而当电影不再如巴赞所言“像指纹一样逼真地反映现实”时,影像本体论就可能走向解体。
1996年,美国学者列夫·马诺维奇发表的《什么是数字电影?》率先对巴赞影像本体论发起了挑战。他认为,“巴赞理论的时代早已结束”,因为数字电影的影像建构方式代表了对19世纪前电影实践的回归,那时候的影像是通过手绘动画得以呈现的。虽然20世纪初,胶片摄影将电影与动画区分开来,并将自身定义为一种记录媒介;但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动画手绘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又再次变得司空见惯。因此,“数字电影不再是一种索引性的媒体技术,而是绘画的一种亚类型。”英国学者肖恩·库比特也持有相同观点,“所有的电影在根本上都是动画的一个版本,反之却是不成立的。”而在国内学界,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影像本体论的解体作出了回应,如游飞和蔡卫在其《电影新技术与后电影时代》中指出“新技术不但综合了原有媒介的特性,将它们统一到数字媒介的大旗下,而更重要的是将巴赞影像本体论引向解体。”陈犀禾也在其《虚拟现实主义和电影理论》中指出,数字技术让“影像不再是一个摹本而是在一个交互关系中有了自己的生命和动力,和具体拍摄场景、气候条件以及其他限制没有关系。”进而“导致了巴赞影像本体论的解体”。近期陈旭光在其《论数字技术与新媒体艺术的美学变革与理论扩容》中也明确指出,“数字虚拟技术运用日益普遍,作为原本摄影机之拍摄对象的物与现实似乎越来越不重要了,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似乎越来越远,甚至毫无关系了。这对电影影像本体论构成了冲击。”
事实上,如果仅以媒介的物质性来指认巴赞影像本体论的消解显然是粗暴的,这不仅大大简化了影像本体论的内涵,也遮蔽了数字电影自身的复杂性和可能性。正如汤姆·甘宁所言:“我们对影像是否准确的评价(即从视觉上反映出它的主体)不仅取决于它的索引基础(化学过程)。而且取决于我们对它看起来像它的主体认识。大量的心理和知觉过程介入其中,不能被简化为索引过程。”而“索引性”也如丹尼尔·摩根所言,“并未抓住影像本体论的主要论点。”因为巴赞认为摄影像一种自然现象影响着我们,“这是一种更强大、更有力量的东西,而且从深层次上说,是一种更陌生的东西。”所以他采用了“转移”(transfer)的概念来阐述摄影“现实从事物到复制品的转移”过程。而“转移”的修辞表明,影像与它的客体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而不仅仅是“索引性”。由此可见,巴赞的立场与索引性观点根本不相容。
其实,在影像本体论中,巴赞反复表示,他是从心理的角度思考摄影的。因为巴赞已经意识到摄影的表现方式可能会随着文明和艺术的发展而改变,但始终不变的是一种深层、原始的为现实事物寻找复制品的心理需求,即“通过持久的形式在与死亡的争论中拥有最后的话语权”。因此,巴赞写道:“如果说造型艺术史不仅是它的美学史,而首先是它的心理学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基本上就是追求形似的历史,或者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史。”从这一命题我们可以看出,影像本体论的核心实际上是一种包含影像与心理的真实观,而并非达到真实目的手段或真实存在的事物。它既强调表现对象、时间、空间和叙事结构的真实,但也反映了社会心理情感上的真实。可见,影像本体论关注的实际上是影像与观众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巴赞实际上也无意将影像本体论塑造成为一个丧失延展性和讨论性的封闭理论体系,而是希冀它能具有开放、持续的动态视角。在《“完整电影”的神话》中,巴赞认为,电影技术的发明和实现总是落后于发明者的设想。这是因为,电影发展的根本动力源自于人类对描绘现实的艺术的心理和真实的伦理痴迷的反映。显而易见,巴赞是否定传统技术决定论的。毕竟在《电影语言的演进》中,他也指出要从“主题的改变和因主题改变所引起的表现主题所必需的手法和变化中去寻找电影语言演进的标志和原则”。因而以媒介物质性的改变去指摘影像本体论的消解无疑是片面的。但巴赞也并不排斥在电影中使用特技,没有把特技排除在他的真实理论范畴之外,“正是利用了一些特技,幻想的事物既可以与现实融为一体,又可以替代现实,特技是一种花招,但是它对叙述的逻辑来说是必要的”。正如汤姆·甘宁所言,“完整电影”的关键点并不是“电影”,而是“完整性”,即各种特定的技术手段被不断融合入一个整体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无非是使电影接近它的起源”。巴赞以此提醒我们不断地重返电影的“过去”,重审电影与观众的关系,进而重新思考影像之中观看和体验世界的方式。而这,也正是共同体美学的立论基础。
三、现代与传统:对钟惦棐美学思想的再发掘
对电影与观众关系的重视,也是我国“电影美学大厦奠基者”钟惦棐先生美学思想的一个核心理念。在他看来,“电影——这一群众性最广泛的艺术……最主要是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丢掉这一个,便丢掉了一切。”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电影创作受政治话语驱使还普遍沉浸在“工具论”的观念中时,钟惦棐先生就一反其道地“敲响”了《电影的锣鼓》,他前瞻性地提出了电影要加强与观众的联系,强调票房价值等问题,认为“绝对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对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对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然而,正是这部被冠以“离经叛道”之论的美学提纲使其陷于厄运而陆沉失语。不过在长达22年的沉寂期里,钟惦棐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对电影与观众的关系和构建中国电影美学体系的思考。因而到了1979年,历经劫后余生重新命笔时,钟惦棐先生便马上组织学生编写《电影美学》,以开拓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与电影美学。
在钟惦棐先生看来,“我们的电影美学一刻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广大观众。这是我们的电影美学意识中最根本的意识。”因而在《电影美学》筹备之初,就专门撰写了《电影美学撰写说明》和《电影美学提纲》两篇文章来阐明“观众在电影中居于权威地位”的核心思想。在“说明”中,钟老明确指出,“本书在体制上将把观众置于首位,着重阐明电影与观众在电影艺术中的特殊意义”;而在“提纲”中,则专门列出市场观一章,要求将“电影的商品品格,观众学”作为这一章的重要内容。后来,尽管这一尝试出于各种因素未能得以实现,但显而易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关系”在钟惦棐电影美学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重要问题。

图1.《钟惦棐纪念集》(左)、《电影的锣鼓》(右)
作为电影观众研究的开拓者,钟惦棐先生早在1956年就在《“票房价值”》一文中指出不少作家、演出者、制片者“不懂观众的心理”,不在乎影片的“票房价值”。随后又在《电影的锣鼓》中宣称了类似的观点。而正是出于对“票房价值”的强调,使其在当时遭受了严厉的批判。然而,从本质上来看,钟惦棐先生所说的票房价值实际上与电影市场、经济和票房收入并无多大关系,其重点在于对观众观影喜好的分析。正如钟惦棐先生所言:“电影对观众而言,可以说服观众,却不能强迫观众。……‘票房价值’不是我们的术语,而是电影制片商的术语,从本质上说,这是和我们格格不入的,我们只是在以上的意义上,借用了这个术语,而要说明的是电影和观众的关系。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克服主观主义的制片方针,克服艺术上的平庸、粗糙。”所以“票房价值”对钟惦棐先生而言,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对电影“喜闻乐见”的标尺或温度计。
事实上,钟惦棐先生“票房价值”的提法蕴含着其构建“电影观众学”的构想。在1981年发表的《话说电影观众学》一文中,他就指出,“‘票房价值’的提法,可以促使我们把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来一个统一的考虑。”不过他认为,观众学的内容其实要比“票房价值”广泛得多,因为观众学包含电影票房价值研究,但不归结为票房价值,“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电影要为之服务的实际”。虽然文中钟惦棐先生并未对“电影观众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作出具体界定,但他主张要从观众的观影反应入手,毕竟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的任何反应都是直观的,有一定道理的,从中我们能一窥电影和观众是怎样发生联系的。同时,他也注意到电影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票房价值有时候不一定完全一致,因而他认为要系统地对“观众中的社会阶层、教养、职业、文化程度、年龄等”不同因素构成的审美趣味加以细致分析。不过,文中最具价值的论点在于,“电影观众学不只是在影片的流转中发生作用,当它进入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入电影心理学的时候,它就和电影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溶合起来了”,而“观众学一旦表现为观众心理学、观众审美学和观众社会学的时候,它就不能不左右某些电影创作家和电影评论家的艺术思想了,而更直接的是影响制片”。不难发现,钟惦棐先生所倡导的电影观众学研究是包含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而这与巴赞“影像本体论”的内核是不谋而合的,二者都十分强调电影与观众的双向互动关系,而非单向的影像、文本和观众分析。
钟惦棐先生和巴赞之所以会在理论构想层面发生跨时空的共鸣,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二者的理论发生都是以观众作为中心的,是一种从观影机制中引发的电影理论。而钟惦棐先生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之所以能够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也是由于“实践性”在其美学思想体系中始终居于枢纽性位置。在钟惦棐先生看来,“电影的内容和影评的内容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都是社会实践包括艺术实践的结果。”所以他反复强调“实践在前,理论在后,而理论一旦符合现实的需要,符合实践中人的志趣,也就在在更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实践。”除开影评,以钟惦棐先生为核心和旗帜的电影美学小组活动在80年代也是广为人知的。因为这是一项完全不同于纯书斋研究的学术活动,也是钟惦棐电影美学不同于中国当代任何一位电影美学家的美学之所在。彼时,围绕在钟惦棐先生身边的不仅有谢飞、黄健中、张暖忻、郑洞天等导演,也有倪震、李陀、罗艺军、周传基等电影理论家,还有仲呈祥、陈犀禾、张卫等年轻一辈的电影研究者,所以钟惦棐的美学思想在没有完全成书的情况下,就已经通过不断交流在电影界散播开来,与电影创作思潮和发展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而这,实际上也给予了共同体美学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即要以实践性为立足点、生长点和发展点;产生于电影实践,也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且随着电影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唯有这样,共同体美学才有可能对中国电影实践产生积极的推动性、引领性和指导性作用,同时解决中国电影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性问题。
除了对电影与观众的关系以及实践性的重视之外,钟惦棐美学思想还有一个核心理念,即重视对本民族电影传统的继承,旗帜鲜明的反对盲目崇洋,反对洋教条。在钟惦棐先生看来:“为了了解西方电影发展的历史和某些趋势,借鉴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需的,搞‘罐头电影’是绝对愚蠢的。”因而,他大力鼓励电影语言与形式的创新。譬如,他认为从《沙鸥》和《邻居》等体现了巴赞纪实美学的影片中“可以看见中国电影的未来,而未来是可喜的”。但同时他也强调,“一个国家的电影如果不是植根在自己的土壤上,而是削足适履地使自己就范于他人,这肯定是不足取的。”他曾在《论电影指导思想中的几个问题》中,专门批评电影界不重视电影传统和民族风格的问题,认为这是导致我国电影理论建设空如白纸的重要原因。他痛心地指出,“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研究整理工作,几年来无人过问。对中国电影艺术家们在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未予认真地总结。”并强调“用传统虚无主义的观点,把现在和过去隔绝起来”是新中国初期中国电影缺乏民族风格的重要原因。因而在80年代国家“开发大西北”的政策号召下,钟惦棐立足西影厂,因地制宜地提出了“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西部片’”的理论倡导,这不仅助推西影厂迅速走出低谷、中国电影迅速走向世界,也为中国电影发掘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和新境遇。所以,共同体美学的建立也需以此为方法,要在汲取优秀文化传统、艺术传统和美学传统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创作实践,推动电影观念的革新,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
众所周知,“电影创作应该获得电影美学理论的支持和滋养,离开理论的滋养,一个民族的电影艺术和电影工业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如今,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亟须相应的、植根于本土的电影美学和理论批评体系来给予方向性的指导。不可否认,目前中国电影的美学和理论批评体系仍处于不稳定、不全面、不成熟的状态,但共同体美学理论构想的提出正是走出这种境地的有效途径,其立足于观众和中国电影实践,在借鉴西方电影理论的同时,又从中国文化传统、美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和智慧,无疑会成为一个内涵深刻、内容丰富、开放包容,面向实践、面向银幕、面向观众、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美学理论。而其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不仅能为日趋复杂的中国电影实践寻求发展路径和方法论,产生积极的引领性作用,也能深化和促进中国电影理论、美学建设具有民族性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必将为中国电影由大国走向强国贡献理论智慧。
【注释】
1 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36.
2 孙丹.回眸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C].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十五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当代中国研究所,2015:308-316.
3 刘浩东.论思想解放与电影中的“人性和人情”[J].电影创作,1999(01):3-5.
4 罗艺军.中国电影理论研究──20世纪回眸[J].文艺研究,1999(03):200-206.
5 白景晟.丢掉戏剧的拐杖[A].丁亚平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3.
6 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J].电影艺术,1979(03):40-52.
7 陈晓云.旧文重读:“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与电影本体的再认识[J].当代电影,2019(01):19-23.
8 胡克.现代电影理论在中国[J].当代电影,1995(02):65-74.
9 孙绍谊.二十一世纪西方电影思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4-5.
10 戴锦华、李奕明、钟大丰.电影:雅努斯时代[J].电影艺术,1988(09):3-14.
11 [美]大卫·鲍德韦尔、诺埃尔·卡罗尔主编.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M].麦永雄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
12 饶曙光、张卫、李彬、孟琪.构建“共同体美学”——关于电影语言、电影理论现代化与再现代化[J].当代电影,2019(01):4-18.
13 陈山.回望与反思:30年中国电影理论主潮及其变迁[J].当代电影,2008(11):32-37.
14 大卫·鲍德韦尔.从新的视野看不同的理论——戴维·波德威尔访谈录[J].世界电影,2004(05):4-10.
15 张英进.华语电影跨学科研究的实践[J].中国比较文学,2015(01):1-8.
16 陈旭光.“电影工业美学”与“中层理论”的观念及方法论——“电影工业美学”的理论资源与方法论阐述之一[J].民族艺术研究,2020(05):6-14.
17 李洋.安德烈·巴赞的遗产[J].作家,2007(05):10-14.
18 Bert Cardullo.André Bazin on Film Technique:Two
Seminal
Essays
[J].Film Criticism,Winter,2000-01,Vol.25,No.2(Winter,2000-01),40-62.19 肖永亮、许飘、张义华.数字技术语境中电影的真实性美学——从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谈起[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149-154.
20 Marc Furstenau.Film
Theory Reader
:Debates&Arguments
[M].London:Routledge,2010:14.21 LevManovich.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M].Cambridge:TheMITPress,2001:295.22 Sean Cubitt.The
Cinema Effect
[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97.23 游飞、蔡卫.电影新技术与后电影时代[J].当代电影,2000(04):65-69.
24 陈犀禾.虚拟现实主义和后电影理论——数字时代的电影制作和电影观念[J].当代电影,2001(02):84-88.
25 陈旭光.论数字技术与新媒体艺术的美学变革与理论扩容[A].上海戏剧学院编.电影的过去与未来:数字技术,视听叙事与影像文化——大型学术会议论文集[C]上海:上海戏剧学院.2020:9.
26 Tom Gunning.W
h
a
t’s the
Point
of
an
Index
?or
,Faking
Photographs
[M].Digital Aestethics,2004:39-49.27 Morgan Daniel.Rethinking Bazin
:Ontology
and
Realist Aesthetics
[J].Critical Inquiry Vol.32, No.3 (Spring 2006).28 André Bazin and Hugh Gray.The
Ontology
of
the
Photographic Image
[J].Film Quarterly Vol.13,No.4 (Summer, 1960).29 [法]安德烈·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A]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C].崔君衍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5.
30 同29,58.
31 [法]安德烈·巴赞.被禁用的蒙太奇——评《白鬃野马》、《红气球》《异鸟》[A]崔君衍译.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54.
32 Tom Gunning.Moving
Away
from the
Index
:Cinema
and
the
Impression of
Reality
[J].differences (2007) (1):29–52.33 钟惦棐.电影的锣鼓[A].钟惦棐.钟惦棐文集上[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348.
34 同33.
35 钟惦棐.《电影美学:1982》后记[A].钟惦棐.钟惦棐文集下[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261.
36 参见俞虹.四十年的探求——纪念钟惦棐先生逝世6周年[J].当代电影,1993(03):78-84.
37 钟惦棐.电影民主[A].钟惦棐.钟惦棐文集上[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507.
38 钟惦棐.话说电影观众学[A].钟惦棐.钟惦棐文集下[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27.
39 钟惦棐.起搏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310.
40 钟惦棐.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J].文艺研究,1981(04):42-46.
41 钟惦棐.电影评论有愧于电影创作[A].钟惦棐.钟惦棐文集下[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181.
42 钟惦棐.论电影指导思想中的几个问题[A].钟惦棐.钟惦棐文集上[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396.
43 倪震.银幕上的中国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