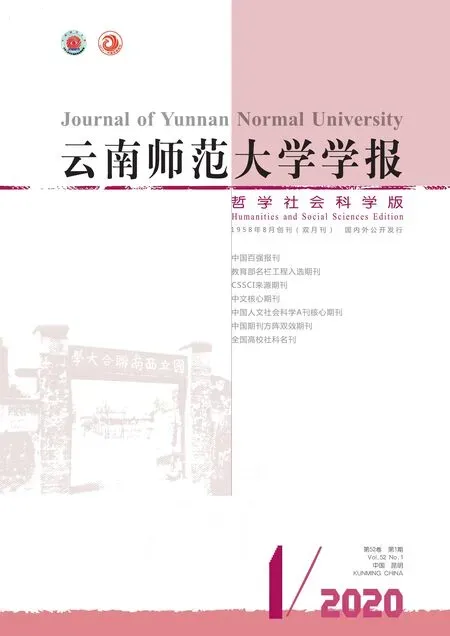官祀滥觞与民祀在场:白族段赤城信仰的仪式表征与社会整合*
2020-02-23杨跃雄杨德爱
杨跃雄, 杨德爱
(1.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2. 大理大学 民族文化研究所,云南 大理 671003)
一、前 言
民间信仰作为整合地方社会的重要工具,历来都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维度之一。就民间信仰的社会整合模式而言,根据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心权力的不同,一般可划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对此,最早对中国民间信仰问题有所涉猎的欧洲汉学家德格鲁特(de Groot)与葛兰言(Marcel Grant)就曾分别采用精英和民间之间异向流动的研究方法进行论证。(1)张原.整体性或关联性——缘起于弗里德曼与费孝通先生的一些思考[A].王铭铭.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辑)[C].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194.此后,武雅士(Arthur P.Wolf)和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等人延伸了前辈的观点。武氏认为民间信仰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反映,信仰世界中的神、祖先和鬼,分别对应了现实中的帝国官僚、族内长辈和外乡陌生人;(2)Arthur P.Wolf.Gods,Ghosts,and Ancestors[A].Arthur P.wolf,eds.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130~182.王氏则认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可通过其日常的宗教信仰来展现,他们对官僚体系的附庸借由对特定神灵的崇信得以隐晦表达。(3)Stephan Feuchtwang.Domestic and communal worship in Taiwan[A].Arthur P.wolf,eds.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105~130.其实,宗教对地方社会不同向度的整合方式,实际上就是“国家信仰”之结构化与“民间信仰”之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表征差异。这种差异使两种表征面临过渡分裂化的危险,落到仪式层面,也就是“官祀”和“民祀”的矛盾统一关系。由此,为了弥合这种分裂,一些学者开始强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力图在多样性的民间信仰和实践的表象下找到某种秩序,即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谓的“一个中国宗教体系”。
其中,桑高仁(Steven Sangren)将中国的神灵体系划分为两个等级,上者直接承载了国家对地方民众的控制,象征了严格的官僚结构。下者则将神灵视为地方的保护者,代表了地区权力的运作方式;(4)SangrenP.Steven.Dialectics of alienation:individual and collectivities in Chinese religion[J].Man(N.S.),1991,(1).韩明士(Robert Hymes)认为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是并列共存的,它们之间还有竞争关系,处于边缘地位的民众会运用个人模式,将中心权力体系整合入地方的宗教信仰之中,而不是简单地受控于中心模式;(5)韩士民.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M].皮庆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沃森(James L. Watson)则通过对华南地区妈祖信仰问题的研究,提出了“神的标准化”概念:一是国家力量会“允准”一些地方神逐渐排除并取代其他的地方神灵,一是不同的信仰主体会在仪式过程中对该信仰产生相异的理解和行为反应。(6)詹姆斯·沃森.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650~1960)[A].韦思谛.中国大众宗教[C].陈仲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7~92.中国民间信仰贯穿于整个社会的等级,在国家权力染指之下,既能仪式性地呈现出不同神祇之间的阶序关系,同时又允许人们依据历史和需要增加相应的信仰内容。也即,地方社会会依据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治理需求,对国家的宗教整合做出回应,并最终形成一种新的“地方性”机制。结构化和灵活性是共同存在的,且并行不悖。
囿于高原盆地的地理结构外耸内陷、河川汇集、排水困难等特点,大理地区自古便饱受洪涝灾害之苦。历史上每隔数十年因西洱河排水不力,位于坝子中心的洱海便会涨水上行,淹没湖滨的村落和田亩,清代刘慰三撰《滇南志略》有记:“水之利害,系于海口、河尾,即下关,例以三年一浚,过期不浚,则滨河之田必致淹没。”(7)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13)[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79.苍山十九峰所爆发的泥石流和滑坡灾害更是不胜枚举。由此,白族宇宙观之形成也大致基于其先民同自然灾害作长久斗争积淀起来的集体记忆。在被称之为“白族心史”(8)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357.的白族古书《白古通记》中,记载有《观音伏罗刹》之故事:大理原为泽国,洱海水淹至苍山麓,为罗刹一部统治,但罗刹喜啖人眼、人肉。观音怜其民,乃化为梵僧,先后用袈裟、白犬之术赢得罗刹国土,伏罗刹于石室。并最终凿河尾,泄水之半,人得平土以居。(9)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53~55.但观音开化大理以后,西洱河又遭巨蟒堵塞至洱海水涨,所以需要一个本土英雄出来解厄,于是段赤城便适时出现了。段之功绩,在白族人看来,甚至可以同观音比肩。也因如此,段赤城作为大理白族重要的地方性神祇,向来被洱海流域的广大居民崇奉为可排沥除涝、施雨驱旱的水神和龙王。段之信仰,在白族的民族文化和乡土社会中影响颇深。
可惜的是,目前学界关于段赤城的研究,大多仅限于对其传说故事的整理摘录和道德教化方面的分析,尚无针对段赤城信仰的独立研究,更何谈成体系的详尽解释。如王晓莉将白族本主神话中与水有关的本主分为“抗洪水型”和“得水型”两类,而段赤城属于前者;张向东、邹红认为,段赤城传说体现了“古代白族人把舍己为人,牺牲个人、保全集体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10)张向东,邹红.从民间故事看古代白族的伦理思想[J].道德与文明,1989,(1).张海超则关注皇权认证在段赤城故事中的结构性意义,认为“它至少非常符合士大夫们为国尽忠的政治理想”(11)张海超.白族民间忠义故事的历史人类学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2010,(1).;连瑞枝在讨论大理坝子的龙王信仰时,虽然将段赤城与李宓(12)李宓是唐朝天宝年间,带兵征伐南诏的唐将,兵败后投洱海殉国。死后因为其忠义,受到当地白族人的崇拜,被奉为利济将军,成为当地著名的本主之一,立庙祭祀。并置,认为二者都是本土化的佛教守护神,(13)连瑞枝.神灵、龙王与官祀:以云南大理龙关社会为核心的讨论[A].赵敏、廖迪生.云贵高原的“坝子社会”: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边疆[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158.但她对段赤城龙王身份历史构建的讨论较为深入。要之,前述的一些研究者虽然对段赤城信仰问题有所涉猎,但多数重史料传说而轻田野调查,故缺少对民间信仰流变痕迹的觉察,而对民间信仰当下样态的忽视,也使得以当下的视野对历史的解释缺少说服力。本文对史料和传说的运用则基于笔者详细的田野调查,因而文本内容虽多以历史为主,却不失对现实的启发。
二、段赤城的传说、分布和敕封
段赤城是大理白族特色最为鲜明的一位英雄人物,他出生贫苦却舍生取义,后被敕封为神,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大理地区被立庙奉祀最多的本主之一。段赤城在与自然殊死搏斗中体现出的英勇果敢、不畏牺牲的品质,被白族人视为其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如今地位最高的洱海之神,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官方敕封的本土水神。
段赤城据信是南诏时期的真实人物,他因杀蟒而死,此后其传说开始广泛流传于洱海流域。关于段赤城的传说版本多变,但故事梗概大体一致,历史上被固定为两个主要文本,即“段赤城斩蟒”与“小黄龙大战大黑龙”。明景泰《寰宇通志·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是最早记录段赤城故事的官方文献:
段赤城,太和人。胆略过人,勇于为义。蒙氏时,龙尾关外津梁寺西有一大蟒,吞咽人畜,往来患之。赤城乃披铁甲,持双剑,欲杀蟒。为蟒所吞,剑锋自蟒腹出,蟒亦死。土人为建灵塔寺,以赤城葬塔下。(14)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7)[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142.
“小黄龙大战大黑龙”的故事则多为民间传说,且是由前者演化而来:
南诏初,崇圣寺绿桃村有一贫女,上山砍柴,见绿桃,吞之,遂有孕。生子,弃之山间,有巨蛇衔去哺养,遂长大,其母乃携归,取名段赤城。一日儿随母入山劳作,治愈潭中龙王。后应邀至龙宫游玩,试穿黄龙衣,乃化身为龙。龙王盛怒,便命赤城驱逐腾越黑龙,解除洱海水患,以将功补过。赤城胜,仍化为小蛇,欲回绿桃。天刚亮,即止于龙凤村。百姓遂奉为洱海神,建庙祀奉。神遂长居于此,其母乃为龙母。(15)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8:202~204.
经笔者实地考察统计,洱海流域现有11处庙祠既祀段赤城为神,又定期举行相应的祭祀习俗(如图1)。这些庙宇散布于洱海西岸,自北向南依次为:洱源县茈碧湖河头龙王庙、青索村小黄龙庙,大理市下沙坪村龙王庙(扼龙首关)、喜洲镇“九坛神庙”、河矣城村“洱河神祠”、古生村龙王庙、龙凤村“洱水神祠”、洱滨村本主庙、荷花村宝林寺、石坪村应海庙、天生桥江风寺(扼龙尾关)。其中除古生村龙王庙和天生桥江风寺外,剩余庙宇皆奉段赤城为本主。段赤城的封号也有多种形式,如“大圣妙感玄机洱河灵帝”(洱河神祠)、“翊连阖辟乾坤裔慈圣帝洱海龙王大圣”(洱水神祠)、“阖辟乾坤霱慈圣帝”(应海庙)等。此外,因段赤城为绿桃村人,该村“龙母祠”中也塑有其立像,而阳平村赵氏族人因仰慕段之功德,从南诏伊始便一直定居于蛇骨塔(灵塔)下。
至于段赤城被敕封为水神的时间,有人说是“元代敕封洱水龙王,世俗遂以龙王称”(16)参见《唐义士赤城段公传》碑,现存于大理市龙凤村“洱水神祠”,笔者田野调查收集(2017年)。,有人说是南诏时“诏王劝利晟亲往祭奠,礼封为龙王”,(17)参见《重修洱河祠碑记》碑,现存于大理市河矣城村“洱河神祠”,笔者田野调查收集(2017年)。但都未见具体证据。而在段赤城之前,洱海中的主位水神已几经嬗变,即从南诏早期的巫教水神金鱼、金螺,(18)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48.变为南诏中后期的道教水神“三官之水官”,(19)赵吕甫.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30.再到大理国及蒙元时期以白那陀龙王(Upananda)和莎竭海龙王(Sagara)为代表的佛教“八大龙王”。
明以降,为厘正宗教祀典,朝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淫祠”运动。但是明政府对待庙祠的态度也并非只破不立,在“抑异教”的同时,“自洪武初,诏天下,每令百户立一社,为民间祈报之所”(20)参见清宣统元年(1909年)立《南经庄重建本主祠碑记》,“大理市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大理古碑存文录[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660、661.,这使得一些散落于村寨中的庙祠得以幸存。那些符合乡里整治需求的地方人、神便有可能通过官方的认证被列入祀典。正德《云南志》载,彼时大理府有两处水神庙:“一为海神祠,在洱海北,南诏异牟寻复归唐时立此,示不复叛之意;一为洱水龙神庙,在洱海西滨……邓川、浪穹俱有”(21)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6)[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141.。又据万历《云南通志》载,位于洱海西滨的龙神庙为“国初建”,可见段赤城早在明初便已是控水的神祇。而后,正德九年(1514年)龙神庙因地震颓陷,大理知府梁珠主持了重建。到了嘉靖四年(1525年),适值大理久旱,向来以捣毁“淫祠”闻名的兵宪副使姜龙听说此庙灵验,便前往祷雨,结果立即大雨倾盆,因此他又对庙貌进行了修缮,并“建堂阁于祠前”。(22)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地方志道教和民族民间宗教资料琐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55.于此,因为官方祈雨见效,段赤城的龙王身份便产生了新的合法性,他被列为“洱海水神”,而“洱水神祠”也被认定为官方举行祈雨止涝祀典之所。
此外,嘉靖年间,明朝廷在各地推行了一套官祀与群祀的仪式正统,“一系列仪式的规范下,大理世族与佛教化龙王地位开始受到另一股外来政治势力与仪式政策的冲击”(23)连瑞枝.神灵、龙王与官祀:以云南大理龙关社会为核心的讨论[A].赵敏,廖迪生.云贵高原的“坝子社会”: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边疆[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170.。以宝林寺为例,因靠近阳南溪,寺中原本供奉的是阳南溪之龙神,即佛教白那陀龙王。明初,大理卫都指挥使周能奉每百户立社神之令,将龙神祠改设为宝林香社,“为民间水旱祷告之所,岁时祭告之坛”(24)参见《新改重修宝林香社碑记》,现存于大理市宝林寺,笔者田野调查收集(2017年)。,这使得原来的佛教龙王降级为乡里仪式之社神。而同样为宝林寺本主佑下的清平村所经历则刚好相反。该村原有居民以段姓为主,万历以前,段赤城曾被族人视为祖先供奉于本主庙内,到了万历年间,“受到外来移居此地的汉族的影响,段氏先祖遂将本主段赤城从清平村移到了宝林寺”(25)大关邑村委会.大关邑村志[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5:82.。由此,在清平村被整合到乡里社会之时,原本作为祖先神和村落守护神的段赤城也被搬进了乡里仪典之场所,成为多村的共同本主,神格与原祀于此的白那陀龙王并列。不难看出,在官方政治权威的关照下,段赤城得以上升为乡里社神,乃至洱海水神,对他的祭拜也逐渐由民祀升级为官祀。同时,诸多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也将段赤城记述为舍生为民的高节义士,这又使得他的水神地位不断被合法化和强调。最终,段赤城虽“生不获封侯,死则庙食千古,观彼生灵如在。保庇生民,魁载祀典,节经钦奉列朝诏旨,修葺维新,日久而不忘”(26)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61.。国家力量借由对段赤城的敕封,实现了对地方社会的整治,段赤城也成了其中的受益者。
三、捞尸会的背景、形式和表征
有明一代,官府为举行段赤城的敕封仪式而设立捞尸会,“捞尸”即打捞段赤城尸体之意,表达的是人们对英雄之死的惋惜。一系列程式化的官祀活动是捞尸会的重点,但民祀活动也未被排除在外,因会期常有划花船、放荷灯等活动,故该会也被称为“海灯会”“花船会”或“耍海会”。明万历《滇略》对彼时捞尸会盛况有过描述:
七月二十三日,西洱河滨有赛龙神之会。至日则百里之中,大小游艇咸集,祷于洱河神祠。灯烛星列,椒兰雾横。尸祝既毕,容与波间。郡人无贵贱、贫富、老幼、男女,倾都出游,载酒肴笙歌。扬帆竞渡,不得舟者,列坐水次,藉草酣歌。而酒脯瓜果之肆,沿堤布列,亘十余里。禁鼓发后,踉跄争驱而归,遗簪堕舄,香尘如雾,有类京师高梁桥风景。(27)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6)[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687、688.
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捞尸会已然是洱海流域最为隆重的水神祭祀节会,沿湖各地皆有举办,尤以洱海“四大名阁”(天镜阁、珠海阁、浩然阁、水月阁)为盛。捞尸会滥觞于农历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和中元节,杂糅了儒释道巫等多种文化元素。明政府为了在地方社会营造自身的权威,遂将原本广为流行,且佛教色彩浓厚的“放生节”重整塑造,划农历七月二十三日为段赤城的官祀日。正因如此,脱胎于白族原有节日文化的捞尸会才保留了诸多民祀活动的内容。清代以后,官祀日渐式微,沿湖各村的放生集会便开始复兴,且频繁程度渐盖于捞尸会,如今则以古生村的放生会最为热闹。农历七月二十三日也是古生村的本主节,这天村民不仅要迎神请客,还要谢水放生,举行仪式的地点便设在该村龙王庙,而白语称古生为“Gouzherl”,即有放生之意。此外,捞尸会在不同村寨的举办,日期也出现变动。以龙凤村为代表,该村于清末将会期延后至农历八月初八,目的是可以同日对段赤城和“张姑太婆”进行祭祀,后者作为白族的原始农神,被认为与段赤城都有“司水之能”。
而针对段赤城的官祀仪轨,现有文献中只有清咸丰《邓川州志》中有介绍:“东龙庙在州八里灵源泽畔,每秋七月念(廿)三日礼,书备羊豕品物,请官诣祭,行二跪六叩礼。”(28)侯允钦.(咸丰)邓川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65.华生将正统的仪式实践视作保持中国文化整体性结构的主要途径,而他通过对民族志的考察发现有两类正统仪式的普遍存在:一类是婚/丧礼,另一类便是国家权威借以控制地方的标准化的寺庙祭仪。(29)James L.Watson.Rites or Belief?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A].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Kim eds.in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C].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80~103.白语称龙凤村为“Dvfsidmel”,意为“东方海神居住之地”。明初政府推段赤城为洱海龙神,遂在原有的唐诏会盟之“海神祠”边修建了“洱水神祠”,后此庙虽有萧败,但在几轮“神之标准化”的挑选淘汰之后,段赤城终于站稳脚跟,“洱水神祠”也成为最初的官祀场所。1980代,洱海水位下降,人们还在“洱水神祠”附近的沙滩上挖掘出大批明代卫所官印。这些官印不论是明、清易代之际,官员因迫于政治压力,借祀水神之典礼抛入水中,(30)杨益清.云南大理发现一批明代官印[A].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7)[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3499、3500.抑或是明政府将“洱水神祠”列为消弃作废官印的特定场所,都直接证明了当时的官祀之盛。
“洱水神祠”建成后,地方政府开始借助官祀的仪式化展演,以“崇神树礼”的名义将象征帝国等级结构的宇宙观植入到民众心中。由此,上行下效,各地纷纷在自家村寨修建段赤城的庙宇,或将其神像置于原有的龙王庙中,践行官方的意愿。一些本土神灵于是不得不让位于新兴的神祇,如今“海神祠”已被“洱水神祠”取代,金鱼、金螺二神也沦为了段赤城的侍神。“洱水神祠”因而成了整个段赤城信仰体系的仪式中心,即为各地段赤城庙宇的“大庙”(祖庙),而这些分散的庙宇便是它的“小庙”(根庙)。小庙建成要到大庙中“分神”,每到捞尸会,信众还要到大庙朝圣,这使得官祀礼仪可以周期性被公开呈现。而在建“洱水神祠”以后,由于两坝相隔,洱源地区也逐渐形成了以河头龙王庙为中心的独立朝圣体系,该庙正是前面提到的“东龙庙”。
四、段赤城信仰的社会整合功能
梳理段赤城官祀之滥觞,我们发现,似乎任何被官方权力“提携”过的地方神祇都逃不开与前者互为拥趸的命运,等级化政治投射下的官祀活动,其结构总是千篇一律,但地方文化背景下的民祀在场及其多元表征却不能被复刻。地方社会中,社会阶层分化的客观事实,使得相同的文化体系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也会出现相异的解释。正如魏乐博(Robert P.Weller)所分:社区祭仪是地方政治的一种操演;祭祖是家庭伦理的再现;“普渡”(鬼的祭祀)则是社区对外人的界定。(31)王铭铭.神灵、象征与仪式:民间宗教的文化理解[A].王铭铭,潘忠党.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07.而在捞尸会中,这些意义不同的仪式甚至交错出现在同一个场域内。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文化和民祀活动的独特性并不以隔绝官方权力和仪式的影响为存在条件,实际上二者只能以一种交融的状态同时存在。段赤城信仰的诞生既植根于大理原有的文化土壤,又成为此后一系列仪式的渊薮。而正是国家权力的参与,使得仪式框架内的社会秩序逐步建立,并影响至今。
(一)溯祖:“九隆神话”文本中的集体想象
“九隆神话”是西南地区诸多民族共有的祖源神话,也是大理白族各类感生神话的源头。目前所知最早记载该神话的是东晋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
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言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元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3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424.
南北朝范晔所撰的《后汉书》将前文中的“沙壶”改为“沙壹”,“元隆”改为“九隆”。唐代的史籍中也有对“沙壶”的记载,如樊绰在《云南志》卷三中记“贞元中(异牟寻)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33)木芹.云南志补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37.此文最早将大理地区与哀牢神话相勾连。到段氏大理时,“九隆神话”已演变为段氏先祖由来之感生神话。据刻立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的喜洲《三灵庙碑》载:该庙供奉有3位神祇,分别为南诏偏妃之子、唐军之大将、吐蕃之酋长。蒙偏妃生子时,因所生无物,便以猴尸佯装亡婴埋于王城道旁。后墓冢上长出一株芦苇,被一母牛所食,兵士于是宰牛剖出戎装男子,此人正是首灵。此后三灵四处征战,所向披靡,却在海西赤佛堂前不幸殒命。附近老翁在梦中受三灵所托,为其建庙塑像,此地便得到了三灵的佑护。多年后,有一耆老求子于三灵庙,其屋旁李树遂长出巨果,果熟落地蹦出一女娃,取名为“白姐阿妹”。后南诏宰相段宝隆娶之为妻,却未有子嗣。某天白姐阿妹戏水于苍山霞移溪,沈木触其足,致其感而怀孕,不久生下段思平和段思胄,此木便是由三灵变化的龙,而段思平长大后就成了大理国的开国君主。(34)段金录,张锡禄.大理历代名碑[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234.
该碑文中一共有三个感生神话:母牛食茔草生蒙王偏妃之子、李树应神谕生白姐阿妹、三灵感孕白姐阿妹生段思平兄弟,内容一脉相传。整篇传说也从侧面展示出段氏先祖在立国之初,被蒙氏、中原、吐蕃等各方势力掣肘时,对多边政治的斡旋能力,并借神话中应天命而降的血统合法性,来佐证段氏君权神授的政治合法性。而其中白姐阿妹触木感生段王的情节显然复述自哀牢沙壹母传说,在三灵故事中沙壹母的地位被白姐阿妹所取代。
在段赤城信仰体系中,段母母凭子贵,她被大理百姓奉为“九龙(隆)圣母”,管理苍洱群龙。“洱水神祠”版段赤城故事将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合而为一,说赤城出生后得白虎、凤凰之庇佑,年幼时又得南诏宰相之救济,所以当有黑龙来洱海中作恶时,他便愤然揭榜,做了一名屠龙勇士。(35)龙凤村邑人请画师誊写于“洱水神祠”外墙,并配有国画彩绘。笔者于田野调查中收集(2017年)。而“洱河神祠”版段赤城故事直接就是哀牢沙壹母传说和绿桃龙母故事的杂糅版本,仅将上述文本中的绿桃换成了“宝珠”,龙神换成了“东海龙王”。因此,在村民看来段赤城即为“九隆”,而九隆圣母便是“沙壹母”。(36)河矣城村邑人请画师誊写于“洱河神祠”大殿内壁,配有国画彩绘。笔者于田野调查中收集(2017年)。赵玉中在田野调查中也曾被河矣城村民告知,村后龙湖原称“九龙池”,是传说中沙壹母的居所。而“洱河神祠”中九龙圣母的塑像即为沙壹母,因为她能感生九子,所以村民常于其神像前求子求孙。(37)赵玉中.祖先历史的变奏:大理洱海地区一个村落的身份操演[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200.在洱源县的传说文本中,少年英气的段赤城变成了一位已经成家立业的果敢老父,他去斩蟒的时候还有九个子女相助,他们牺牲后被洱源各村奉为本主。此处,段赤城不再是龙之幼子,而是“九隆之父”,其子女便是“九龙”。(38)李一夫.白族的本主及神话传说[A].李家瑞.大理白族自治州历史文物调查资料[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81.
此外,有明一代,随着白族民族意识的加强,大理本地的豪门巨族除了溯祖为南诏时期的教权人物“阿吒力”外,开始以“九隆族裔”自称。如成化十三年《故善人里长段公墓铭》载:“五峰弘圭赤土江里长段公,乃是名家九隆之旺族”;成化十九年《故善人杨公墓志铭》载:“公讳永,字有年,姓杨氏。九隆族之裔,代不乏贤,世居弘圭之市户。”(39)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卷4)[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06、211.《哀牢传》中九隆十子与山下十女相结合,组建了十个小家庭,各支“后渐相滋长”,衍生为“九隆族裔”。九隆姓氏并无固定,其中段、杨、李、赵、董、洪、施、何、张、王各姓,则被《南诏野史》列为最常用之十姓,这些氏族也是白族历史上相对先进的名门望族,至今还有人家在照壁上题写“九隆后裔”几字,自恃为名家。笔者以为,白族溯祖“九隆”热潮的兴起,其实是明代以来“夷夏之辨”在其宗教文化上的矛盾体现,而正如梅根·布瑞森(Megan Bryson)对同为大理官祀之神的白洁夫人(40)传说在蒙氏统一六诏的战争中,身为邓赕诏王妃的白洁夫人忠贞不屈,投洱海自尽,被后人奉为“圣妃”,一说捞尸会所纪念的便是白洁夫人。的研究所感,当地的儒生一方面因段之义举受到官府的肯定而暗喜攀附,另一方面又力证段之品德早于朱明“教化”之前,以谋求平等。(41)Megan Bryson.Baijie and the Bai:Gender and Ethnic Religion in Dali,Yunnan[J].Asian Ethnology,2013,(1).但若落归仪式本身,两者依然绕不出在历史情境中官民实践互为因果的宗教范式——段之神权来源于官祀祭仪,却又嵌合于民祀过程。
(二)渡魂:作为祖灵之地的洱海
在历史上的民间信仰实践中,官祀的仪式化认证不仅成为段赤城神力的关键来源,在捞尸会的仪式流变中,官祀的出现和神之敕封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就民间信仰的社会整合而言,“渡魂”无疑是捞尸会中最为外显的表征。
《滇略》描述捞尸会时有“尸祝既毕”一词,“尸祝”即是对尸体祷念祈祥纳福的祝语,同时也可传达鬼神对人的诉求。在古代的祭祀活动中,“尸祝”也被引申为对神主掌祝的主祭者。(42)叶大兵,乌丙安.中国风俗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247.而祭祖(鬼),并为逝者引渡灵魂恰恰正是捞尸会中民祀活动的主要内容。所谓渡魂即是以各村莲慈会的老斋奶为执事者,对亡灵进行仪式性的超度。以龙凤村捞尸会为例,步骤大约如下:
(1) 拜神:早到后先到神祠内磕头拜神,并点燃高香。
(2)念经:寻一处空地取出香烛贡品整齐地摆成一方祭坛。以木鱼伴奏,围成一圈或两列相对开始念经。所念以《放生经》和《七月经》为主。
(3)做饭:近午,于神祠前宰杀活鱼和活鸡,视为献祭,但女性不能杀鸡,要请专人操作,饭是现焖的罗锅饭。
(4)敬神/鬼:敬神所用以荤腥熟食为主,通常为整鸡、整肉、双鱼、双蛋,配上满饭一碗,茶酒各一杯。敬者先将祭盘摆于龙王座前稍做停留,然后再端至院内分别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屈膝祭拜;敬鬼则只需从各种食物中取出一小部分放在黄纸上便可,地点在洱海边。神鬼吃后再轮到人吃。
(5)焚表:有“神表”和“祖先表”两种,神表封面上书“龙王座前,某村某社某某合家人呈请”,需在神庙内焚化;祖先表封面上书“三代祖先前,某村信士/莲慈会某某合家人上表”,需在洱海边焚化。一些有亲人于新近离世的家庭,还要焚烧一把竹制小楼梯。化表时持表者需虔诚下跪,双手握表,口中默念请神降福或请鬼(祖先)恕罪的祷词。
(6)放生:下午,各村莲慈会于湖边站成两列,由一人(通常是“经母”)立于中间提桶放生,其余人则手敲木鱼,口中颂念《七月经》:“公泥鳅、母泥鳅/为因前世你有功/我们把你超生去/把你放在清水沟/摇头甩尾游回去/摇摇摆摆在海中。”
(7)送花船:送花船是整个民祀活动的最高潮。“花船”是一艘用竹篾和彩纸扎裱制作的小船,由龙凤村莲慈会提供,也须由她们放流。待花船在阵阵诵经声中被放归洱海后,属于龙凤村的最后一桶泥鳅也被放生。至此,捞尸会中的集体活动才算完结。
不难发现,以上这些仪式的内容有浓厚的祖先崇拜情结,白族祭祖时常称的“三代始祖,四代近祖”(sal deit doufbalf,xi dei xilngv),便有类于《盂兰盆经》“木莲救母”故事中提到的“七世父母”,而“渡魂”仪式也与福建等地的“普渡”仪式相似。放流莲花灯是这类仪式的共有特点,流动的灯火象征将逝者的灵魂引渡出苦海,带往极乐世界。
20世纪30年代曾在大理做田野调查的澳洲人类学家费子智(C.P.Fitzgerald)就曾对渡魂仪式做过描述。彼时的“洱水神祠”被孤立在一座小岛上,仅由一座石板桥与岸连通。老旧的庙宇经地震破坏后,已塌毁大半,但依然抵挡不住人们朝圣的热情。每到游花船的日子,人们热衷于手捧点燃的莲花灯拥挤着渡过石板桥,然后推灯入水,期望它能从桥下漂过,以此象征亡灵已渡过奈何桥,投生转世。那些放生泥鳅的信徒则希望通过挽救临死的生命的形式来积攒功德。(43)C.P.费茨杰拉德.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M].刘晓峰,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03.此外,费子智还发现人们朝水中抛撒大量谷物,他将此理解为是农民在向龙王求雨。笔者在捞尸会和放生会的现场也发现,在香炉旁边摆放有若干个谷物环,每环以五小堆谷物为一个单位,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摆放,再用玉米粉或面粉围成一圈。在白族文化里,只有在叫魂和出殡时才会使用谷粒,而环为结界,区隔五方之鬼与人类世界,因此这明显就有“祭鬼”之意。
如今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洱海封湖禁渔,龙凤村之捞尸会已无船可耍,人们只好把做好的莲花灯临水焚化。而洱源茈碧湖却保留了此项传统,夜幕降临,人们先是提着海灯去庙里祭拜龙王段赤城,然后才徐徐划船至湖心,将点燃的海灯放入水中。同样位于洱海上游的青索村,其海灯会的会期则尚未与中元节分离。是夜,天衢桥两头聚集了数千名来自上关及洱源各地的信众,上万盏莲花灯被流放入永安江和弥苴河,一眼望去,疑是银河落九天,场面蔚为壮观。年内有老人去世或小孩诞生的家庭,则需请人定制一艘稍大些的花船用来流放,家人试图用更大的愿力祈求往生者安息,降世者健康。青索村小黄龙庙始建于1929年,本为护航镇洪祈祷之用,此后却逐渐成了海灯会的祀庙。所有莲花灯在被投放入河流前,都需带至庙内祭拜黄龙神,村民们在莲慈会朗朗的念经声中,小心地往灯内添加祭神用剩下的香油,目的是使莲花灯得到龙王的加持,并由俗物转变为圣物,具备引渡灵魂的宗教功能。被流放的莲花灯会穿天衢桥而过,最终漂入洱海。年轻人则乐此不疲地站在桥头向两岸投掷点燃的鞭炮,以驱赶滞留的游魂。
在白族人的空间观中,洱海是逝者灵魂的归属地,亡灵只有通过洱海才能去往阴间。(44)杨跃雄,王笛.《南诏图传·洱海图》与白族的“祖先蛇”崇拜[J].昆明学院学报,2018,(4).老人们说,每位祖先的灵魂都须由一盏莲花灯来引渡,一个家庭若想引渡更多的亡灵,就需要投放更多的莲花灯。而段赤城作为洱海之神,管理着河流和洱海,并能通行于阴阳两界,因此只要对他虔诚祭拜,这些星星灯火自然会受到他的引领,回归到他们应在之处。捞尸会的仪式意义也是如此,在民祀中,这种公开且集中的祭祖(鬼)的方式与中元节中以自家庭院为仪式空间,私密且分散的方式形成对比,人们朝圣海神的重要目的便是希望能借海神之力将亡魂送归洱海。由此,受到官方敕封的海神段赤城,被白族人整合到了民间的鬼神信仰体系中,兼具了佛道二教中地藏和城隍的某些功能。段赤城也成为大理祖先(鬼)信仰阶序中的执权者,对他的祭祀是维系“人-鬼”宗教空间秩序的关键。
(三)分水:水利社会中的朝圣逻辑
水在农业社会中至关重要,一切水神的塑造和敕封,以及围绕其开展的一系列仪式活动,无不与对水的社会化或文化化控制有关。水不论作为国家攫取权力的工具,还是社区之间争夺的资源,其象征意义都是这一切得以发生的前提与根本。(45)张亚辉.人类学中的水研究——读几本书[J].西北民族研究,2006,(3).因而,虽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将形成水利社会的原因武断地以“环境决定论”来总结,但他也指出,对水的分配正是地方政府整合基层社会,乃至一些东方国家形成某种政治专制传统的关键。(46)卡尔·A·魏特夫.地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M].徐式谷,奚瑞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有明一代,中央政府施行了大规模的屯兵屯田运动“以实西南”,开始在云南各坝区以卫所为单位划田而治,此举遂导致了洱海流域人口的大量增长,而军家和民家之间也常因争夺灌溉用水发生激烈械斗。为此,明清政府一方面兴修水利,制定分水规则。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水神周期性的祭拜,以期在宗教层面对人们进行慰藉和疏导。如明宣德年间刻立的《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文》就相对系统地记录了当时洱海流域军民对各条河流的用水分配情况。(47)段金录,张锡禄.大理历代名碑[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127~129.而每遇灾年,地方官也多行咒龙求雨之事,李元阳撰《赵州甘雨祠记》载:嘉靖年间,大理久旱不雨,郡邑官员“多躬亲祈祷,或以巫觋至虵”,竟都无雨。后州守潘嗣冕听从本地耆老的话,去湫龙潭求雨,祭拜了神龙以后郡内才大雨如注。而其他未得龙神佑护的地方,则“焦土如故”。(48)张树芳,赵润琴,田怀清.大理丛书·金石篇(卷2)[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677.
喜洲附近的众神代表各自佑下,聚于“九坛神庙”商讨求雨降水之事,实际上便是白族村民在宗教层面对地方政府祈雨分水仪式的模仿。“九坛神庙”中的九位本主原本分属不同的村庄,传说中百姓受干旱之苦,他们向各自本主求情,不是让其及时布云行雨,因为在这里本主都没有降雨的能力,他们在“中央本主”段宗榜的号召下相聚于九坛神庙,目的是一起去向龙王求雨。九位本主一齐去了龙王庙见到了龙王,说明了来意,龙王见如此阵势只能勉强“借雨”。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因为分水不公发生了争斗,大家互不饶让,一直吵到鸡鸣,本主们不得回家,只好一同在喜洲本主庙里做起了“九坛神”。
在洱源坝子的分水体系中,段赤城身为“龙父”坐镇茈碧湖,茈碧湖是洱海流域诸多河流的源头,他的子女被分配在水系各端的村庄中做本主,所用之水便是到段赤城处祈求得来。因而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洱源各地的百姓都要齐聚河头龙王庙,为龙王庆生求雨。在该地区的传说中,河头龙王有一个女儿,巡检司下山口的黑龙大王曾来求亲,这姑娘不愿意,后来就嫁给了云南驿(今祥云县)龙王。云南驿缺水,庄稼不好,因此龙王很穷。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与七月二十三日,河头老龙王做会,这位龙女姑娘就回家做客,向龙王哭诉自己的困厄。因此每当这两天,茈碧湖附近总是恶风暴雨。后来,老龙王可怜她,就多分给她一股水,这股水可以灌溉她领辖的所有土地。从此,云南驿五谷丰登,人们都感激她,所以她庙子里的香火常年不绝。(49)罗杨.中国民间故事丛书:云南大理·洱源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95.
龙凤村则依据村落间的疏远程度,将祈雨仪式分为两天,“每岁秋七月二十三日,恭隆段公诞辰,龙、才、凤鸣、鸟冈四村绅耆士庶,读经颂诰,祷于祠”。(50)参见《唐义士赤城段公传》碑,现存于大理市龙凤村“洱水神祠”,笔者田野调查收集(2017年)。段赤城诞辰这天,龙凤村耆老邀约临近村落的洞泾乐队至“洱水神祠”弹经颂诰,没有莲慈会的参与,延续了官祀的传统。“又八月八日,四方士女,云集于此”,直到农历八月初八,段赤城作为洱海水神的地位才被突显出来,而作为该村本主的职责则被隐藏。但是不同于向山神庙中的龙王爷求雨,前往龙凤村或茈碧湖的参会队伍皆以各村莲慈会为主,即便是家庭主妇独自要去一般也要依附于莲慈会。莲慈会实际上是代表了所在村寨的宗教利益,如果龙王会期该村不来朝拜,龙王便有可能不给予他们雨水和溪水,所以她们前来就有分水之意。“洱水神祠”走廊中央有一口古井,名曰“钵井”,据上面刻的《重修钵井序》介绍,古人初建“洱水神祠”时,所用木料皆为龙王由钵井从海底送出,该井可直通龙宫,因此所出之水也具有神效。龙凤村莲慈会的老人向笔者介绍,这水不仅可以保健治病,用来浇花灌田更可以保证苗木粮食丰产。正因如此,每年捞尸会祭祀活动结束后,人们要先进庙内奉上一些功德钱,之后才有资格聚拢于钵井边“讨神水”,龙凤村还安排专人用一个小桶伸入狭小的井中打水。讨神水的人都是先在井边痛饮一番,然后再装上一瓶尽兴而归。而所谓的“讨神水”,分明就是对分水的隐喻。
五、结 语
雷德菲尔德(Red field)提出的“大、小传统”的概念术语,曾一度成为社会科学理解和研究复杂农业文明的重要进路。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大/小传统,及由其引申出来的国家/地方、精英/农民之间的二元划分过于简单和对立。(51)王妮丽.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在白族的段赤城信仰现象中,代表“国家信仰”的官祀活动虽出于地方政府治理社会的政治需求,但它也不得不脱胎于原有的地域文化。而代表“民间信仰”的民祀活动虽不被列入地方祀典,但它也逃不开官方权力对地方神祇及其意义的仪式性再生产。在现实的宗教实践中,这种官民互动的情况依旧存在。如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始建于明清两代的古生村龙王庙,曾香火旺盛,后来于“文革破四旧”时遭到损毁。到了1996年,生活日渐富裕的村民决定划地重建,却因砍伐了湖滨的几株绿化树而遭到阻挠。待段赤城神像塑成,该村莲慈会组织村民到“洱水神祠”进行分神仪式时,还蒙受非议,被戏称为“迷信”“文盲”。然而,在环保主义兴起的今天,因传统宗教信仰被建构为人与环境友好共处的文化保障,地方开始主动将祭祀龙王与环境保护关联起来,并发明地方性知识,使得原本以促渔求安为目的的龙王崇拜,有了象征自然和谐的权威认证。
由此可见,宗教的象征体系也并非如一些人类学权威所说的那样持恒不变,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受不同的群体解释和再解释;在有国家的社会中,宗教既可以是支配者用以创造社会秩序的手段,也可以是人们想象人生与来世的解释体系。(52)王铭铭.神灵、象征与仪式:民间宗教的文化理解[A].王铭铭,潘忠党.象征与社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23.于地方社会中裹挟并行的“国家信仰”和“民间信仰”,正是宗教之权力结构和仪式实践在社会整合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样,大、小传统在历史维度上也是彼此连接的,并且可以相互转换,地区的小传统不应被视为大传统的组成部分,其文化传统可以自成体系。也就是说,大、小传统可以共存于地区的文化传统当中。(53)舒俞.从弗里德曼到桑高仁[A].王铭铭.中国人类学评论(第2辑)[C].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216.从白族特有的本主信仰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看,本主文化或萌芽于氐羌系之原始宗教,形成于蒙氏南诏,而发展于段氏大理,但最终的推广和体系建立,大略也受到了明代官方对段赤城信仰体系构建的催化影响,或两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互构互促的。官方通过对段赤城的敕封将本土英雄神圣化,并建立起一套官祀仪轨,使得大理原有的本主元素被纳入国家宗教结构化的大传统。而与此同时,白族群体也仿构并强化了以段宗榜为首的民间本主信仰体系,还通过将外来的陌生神(人)本土化(内化)的方式,重建了自己的小传统。故而,由点及面,正是各地方社会中这种既有区别,又能融合的互动过程促进了“一个中国宗教体系”的形成,进而对维护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体性”发挥整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