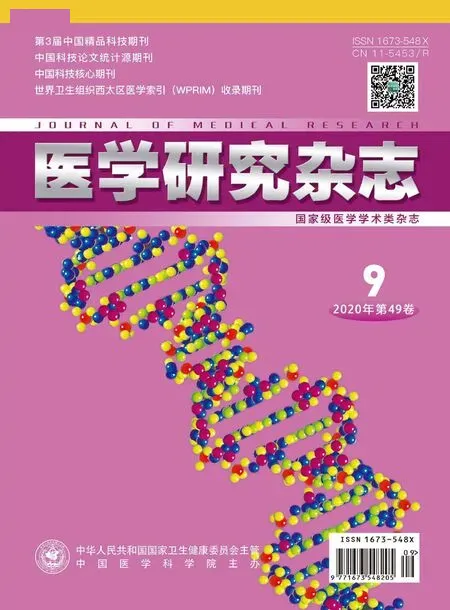肿瘤微环境在三阴性乳腺癌中的调控作用及其治疗进展
2020-02-22赵佳琳王学晶
赵佳琳 王学晶 李 炎 孙 强
根据2020年全球癌症研究最新数据[1],女性恶性肿瘤中乳腺癌的发生率位于第1位,病死率在癌症相关死亡中为第2位;与其他亚型比较,三阴性乳腺癌(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 缺乏特异性治疗靶点、预后差。肿瘤细胞与其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功能性整体,肿瘤细胞与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互相影响,共同促进肿瘤的发生及发展。既往对肿瘤治疗的思路多局限于肿瘤细胞本身,通过相应药物杀伤肿瘤细胞,近年来开始研究TME的潜在治疗价值,旨在通过TME改变肿瘤细胞的“土壤”环境。靶向TME同样为TNBC的诊疗提供新思路。
一、TME的概念及组成
1.TME的概念:TME由肿瘤细胞、周围的间质细胞(如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及脂肪细胞)、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c, ECM) 和信号分子(如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组成。早在1889年,近代病理学之父Paget[2]提出“种子与土壤理论”,即肿瘤转移需要肿瘤细胞传播即“种子”,和靶器官理想的环境即“土壤”,但之后在阐述其机制方面没有重大进展。2015年,Hoshino等[3]发表于《Nature》的论文证实了这一理论,研究发现肿瘤在转移过程中释放数百万携带蛋白质和遗传内容物的囊泡即外泌体,确保靶器官提供适宜的TME,外泌体触发靶器官的反应如炎症及血管形成等,便于肿瘤细胞到达靶器官时进行增殖。
2.TME的组成:TME中的免疫细胞由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on lymphocytes, TILs)、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s)及发挥抗原递呈作用的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 DC)等组成。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的表型依赖于TME的信号表达,其表型包括抑制肿瘤的M1型和促进肿瘤的M2型;健康组织中巨噬细胞在M1和M2之间处于平衡状态,而癌组织中该表型向M2方向移动[4]。MDSCs包括多形核MDSCs及单核MDSCs,分别反映其与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的相似性,目前研究表明二者均有明显的促肿瘤作用[5]。
除免疫细胞外,TME中还有成纤维细胞及血管内皮细胞等基质细胞浸润,构成肿瘤的非免疫微环境。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associated fibroblasts, CAFs)释放基质细胞衍生因子及促血管生成因子等,促进肿瘤细胞生长和新生血管生成;血管内皮细胞主要介导血管的生成,共同为肿瘤转移助力。ECM是由胶原蛋白、层粘连蛋白、纤维连接蛋白、透明质酸和硫酸软骨素等组成的三维网络,含多种肿瘤代谢产生的酸性物质,维持肿瘤的弱酸性环境及诱导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是肿瘤转移过程的重要屏障。除了ECM外,信号分子在诱导肿瘤发展和免疫反应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TME中的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白细胞介素-1、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0等,能共同发挥免疫抑制作用,阻止机体杀伤肿瘤细胞,并促进肿瘤的血管生成和转移等[6]。
二、TNBC的异质性
TNBC是具有强侵袭性及转移性的乳腺癌亚型,目前化疗是其主要治疗选择;但部分患者经标准治疗后仍在短期内出现复发及转移,因此研究者试图对TNBC进一步分型并探索个体化治疗。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团队通过分析465例中国TNBC患者的临床病理、基因组及转录组数据,将TNBC分为腔内雄激素受体型(luminal androgen receptor, LAR)、免疫调节型(immunomodulatory, IM)、基底样免疫抑制型(basal like immune suppressed, BLIS)及间充质样型4种亚型,并在每个亚型中鉴定出相应的生物学标志物或潜在治疗靶点[7]。中国TNBC患者以LAR型多见,主要特点为对靶向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 AR)治疗敏感。刘娟等[8]对TNBC的临床病理分析也显示,AR阳性患者有较好的预后。TNBC亚型的多样性侧面证明其肿瘤间异质性,并可能指导进一步分型治疗。
同时,TNBC的不良预后可能也与肿瘤内异质性相关。既往研究证实,肿瘤内异质性是肿瘤耐药和治疗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转移性患者的治疗难点之一。同时,同一肿瘤可能由具有不同性质和耐药表型的肿瘤细胞组成,肿瘤内异质性决定肿瘤适应新的TME的能力[9]。随着对肿瘤细胞与TME相互作用认识的加深,TME可能成为开发新型药物以改善TNBC预后的有用工具。
三、TME在TNBC中的调控作用
1.免疫细胞及因子的作用:既往研究中,恶性肿瘤的侵袭性、转移性、耐药性及不良预后,既取决于肿瘤本身的表观遗传学特征,也取决于TME中的相关因素;机体可以诱导多种免疫细胞及因子以杀伤肿瘤细胞,肿瘤细胞同样能通过释放免疫抑制因子等策略逃避免疫攻击。TNBC具有独特的肿瘤免疫微环境(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TIME)。Gruosso等[10]对TNBC的TIME进行分析发现,具有免疫反应的TIME表现为能分泌颗粒酶B的CD8+TILs浸润,并有多种免疫抑制分子如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 IDO)和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 PD-L1)的表达增加,为预后良好类型;无肿瘤CD8+TILs浸润的“冷环境”的特点是负性免疫分子B7-H4的高表达,为预后不良类型。同时,TME在PD-L1表达的调控中也有重要作用[11]。TME中多种细胞因子可调控PD-L1的表达而引起免疫抑制,其中大多数为炎性因子,而TME中炎性因子的高表达可能是导致免疫治疗效果差的原因,因此联用抗炎药物和PD-L1抑制剂可能使TNBC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此外,免疫治疗效果也取决于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的代谢,两者需要类似的代谢物、并在TME内竞争葡萄糖和氨基酸等共同营养资源;肿瘤细胞通过减少免疫细胞的关键营养物质,同时释放免疫抑制分子获得缺氧和酸性环境,免疫细胞则在TME内进行剧烈的代谢重塑以适应新环境,联合免疫治疗和限制肿瘤细胞代谢的治疗策略能增加TILs的浸润以促进抗肿瘤反应。
TAMs通过释放抑制性细胞因子、降低TILs功能及调节TME中PD-L1的表达来促进TNBC的进展;浸润性TAMs的存在往往提示预后不佳。促TNBC转移的基质细胞及信号因子,主要通过使TME内血管生成因子和MSDCs的增加来影响TNBC的侵袭和迁移能力。赖氨酸特异性组蛋白脱甲基酶(lysine-specific histone demethylase, LSD) 抑制剂可增加M1样信号表达,促进巨噬细胞极化;同时,LSD1特异性抑制剂可减少TNBC细胞迁移及MSDCs浸润,并减少肺转移灶[12]。MDSCs可控制癌细胞的生长和转移,肿瘤免疫逃逸机制的研究认为,MDSCs是治疗TNBC的重要靶点,而某些植物中萃取的化学物质可能作为MDSCs的有效抑制剂。
2.CAFs的作用: CAFs是肿瘤基质的主要成分,可重塑ECM及分泌细胞因子来促进肿瘤进展,CAFs分泌的细胞因子使肿瘤细胞增殖,促进免疫抑制,并诱导表观遗传学改变及EMT过程;同时,TME中的CAFs可能与TNBC的化疗耐药相关。CAFs同样具有异质性,肿瘤细胞与CAFs的相互作用及CAFs异质性都能导致TNBC对标准化疗耐药及后续疾病进展。Liubomirski等[13]研究发现,加入细胞因子后能刺激与MSCs或CAFs共培养的TNBC细胞表达更高水平的趋化因子CXCL8;而TNF-α能诱导与MSCs共培养的TNBC细胞增强在小鼠模型的侵袭性和肺转移能力。Costa等[14]在研究中确定了与乳腺癌相关的4个不同性质及激活水平的CAF亚群,与TNBC相关的是CAF-S1及CAF-S4,其中CAF-S1可通过复杂机制促进免疫抑制微环境形成,其特点是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fibroblast activation protein,FAP)阳性;因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CAFs相关抑制剂联用可能增加TNBC对免疫治疗的反应,从而改善TNBC患者的预后。
3.血管内皮细胞的作用:血管内皮细胞位于血管的腔面,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TME的新生血管是肿瘤细胞对氧和营养的需求增加的表现,细胞主要通过分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 FGF-2)来刺激血管生成,新生成的血管向快速增殖的肿瘤输送氧和营养物质,同时肿瘤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使血管功能失调、管腔不规则及通透性增加,导致TME内的流体压力增加、血流不均匀及异型血管生成。TME中VEGF过量影响血管通透性、并使血管结构紊乱,增加TME的缺氧,有助于肿瘤的进展;而位于血管的基部、稳定血管结构的周细胞,在新生血管中数量明显减少,造成血管通透性增加,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血管内扩张[15]。
4.脂肪细胞的作用:脂肪组织是乳腺组织周围最丰富的细胞成分之一,能通过分泌肿瘤生长相关的激素和细胞因子等,引起肿瘤细胞表型的改变。脂肪细胞通常先在TME内富集,通过TME中其他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转化为具有成纤维细胞样的表型、有小而分散的脂滴、低表达的脂联素和其他脂肪因子的肿瘤相关脂肪细胞(cancer-associated adiposes, CAAs);完成转化后,CAAs能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和脂肪因子,并释放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s, FFAs)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促使免疫细胞进入TME,形成类似慢性炎症的环境,促进EMT过程及侵袭性肿瘤表型形成。CAAs除能分泌趋化因子、白细胞介素、瘦素、TNF-α及VEGF等加速乳腺癌侵袭和转移,还能使TME产生代谢重塑来促进肿瘤进展。肿瘤细胞可通过与CAAs的相互作用,诱导脂肪细胞调控包含碳水化合物、脂质和氨基酸在内几乎所有高分子营养物质的代谢,从而适应新的代谢过程进行增殖[16]。
5.ECM的作用:ECM除能提供TME中细胞附着、增殖及迁移所需的三维网状环境,在支持肿瘤进展和转移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ECM可向肿瘤细胞提供持续的增殖信号、抵抗细胞凋亡及诱导新生血管,从而促进肿瘤的侵袭和转移。整合素介导细胞粘附于ECM上,上皮细胞与Ⅰ型胶原结合可诱导EMT,导致ECM调节 MMPs分泌,而MMPs负责从ECM中分解肿瘤细胞,最终导致肿瘤细胞的间质侵袭,并诱导肿瘤干细胞(cancer stem cells, CSCs)的形成和转移,靶向MMPs抑制剂目前也被批准用于晚期癌症治疗的临床试验[17]。此外,ECM作为物理屏障,还影响免疫细胞、抗体和相关药物渗透进肿瘤部位。
四、靶向TME治疗TNBC的潜在价值
如前所述,肿瘤细胞与TME之间的双向作用可能在多个途径上促进肿瘤的进展,肿瘤细胞通过改变TME以产生适宜的生存环境,TME又能反过来调控肿瘤细胞以影响肿瘤细胞的行为,因此,以TME为靶点可以为癌症治疗提供新思路。Li等[18]发表在《Cancer Research》的论文指出,抗癌基因突变能诱导TME改变并产生促肿瘤的分子机制,靶向TME的治疗策略有其自身优势,如间质细胞具有稳定的遗传背景、不易出现突变及产生耐药,与肿瘤细胞比较,TME的异质性更小、疗效相对稳定,并有可能预测肿瘤组织对治疗的反应性。TME是当前癌症研究的热点,TNBC中靶向TME治疗主要包括以下进展:
1.靶向免疫治疗:靶向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PD-1)/ PD-L1的免疫疗法主要通过阻断PD-1/PD-L1通路,诱导肿瘤凋亡及破坏免疫逃逸系统,以达到杀伤肿瘤的目的;在乳腺癌领域,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已加速批准首个针对TNBC的免疫治疗方案,即阿特珠单抗(atezolizumab)联合紫杉醇(abraxane)用于一线治疗无法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PD-L1 阳性的TNBC,为TNBC的临床治疗提供新选择。如前所述,TNBC的IM型主要表现为免疫治疗靶点的高表达,而BLIS型则表现为免疫抑制型TME,明确PD-1/PD-L1等靶点在TME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充分发挥其抑制剂的作用,在IM型中优先评估相关免疫指标的表达可能增加免疫治疗获益,从而实现精准医疗的目标。此外,免疫治疗同样正经历着认识上的转变,即从传统“增强免疫原性”的观念,转向“免疫正常化”以实现治疗更有效且毒性更小的目标[19]。由于TNBC中TME的复杂性,除了PD-1/PD-L1通路外,靶向TAMs的LSD抑制剂、其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机制研究及其与PD-1/PD-L1通路相关药物联用的可行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对TME进行个体化分析将有助于探索TNBC的靶向免疫方案。
2.靶向其他成分及联合治疗:虽然免疫治疗为TNBC治疗提供了新方向,由于TNBC中TME的异质性,仍有患者对免疫治疗存在耐药性,靶向TME中其他成分的治疗同样值得重视。TNBC细胞可通过新型精胺氧化酶(spermine oxidase, SMO)作用于CAFs来维持肿瘤细胞的干性,靶向SMO的小分子抑制剂联合化疗已在晚期TNBC患者中开展Ⅰ期临床试验;靶向VEGF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多项临床试验结果也证实其在晚期TNBC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0]。此外,联合治疗同样能通过影响免疫治疗提高疗效,除上述的抗炎药物、限制肿瘤细胞代谢及CAFs相关抑制剂与免疫治疗联用方案外,ECM中的透明质酸也可能影响肿瘤细胞对免疫治疗的敏感性[21],而选择性布鲁顿酪氨酸激酶依鲁替尼(ibrutinib)能同时调节免疫抑制分子IDO的信使RNA的表达并调节MDSCs的功能[22]。
3.植物化学物质:植物化学物质可抑制炎性因子、转录因子、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分泌,影响肿瘤细胞相关的干细胞信号通路和基因表达,并与TME中的细胞产生作用;因此,单用植物化学物质或与化疗及免疫疗法联用,可能是治疗TNBC的另一种思路。近年来研究表明,从姜黄中分离出的姜黄素化合物,可使TNBC细胞抗凋亡蛋白的下调因子表达升高;柑橘果实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可下调促肿瘤蛋白的表达并上调抑癌因子的表达。甘草素是异黄酮类化合物的衍生物,可改变TNBC细胞系的蛋白质组学和RNA表达谱而产生抗癌作用;硫磺素是一种富含硫的膳食化合物,能通过调控表观基因沉默机制来发挥治疗效果[23]。
4.离体模型与工程技术:体内模型可提供由免疫系统、血管系统及其他TME成分组成的动态环境,但构建体内模型耗时、费力且价格高昂;异种移植模型缺乏正常的免疫系统,而免疫系统又是肿瘤发展过程的重要部分,因此同基因小鼠模型不能完全反映人体对肿瘤的反应。相较而言,离体模型的构建更简单,更容易分析动态变化过程,并能通过调节变量更好地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工程三维模型使用如水凝胶等生物材料和多种细胞的共培养模型,使这些细胞维持其固有形态,并实现细胞与细胞和细胞与ECM的相互作用。离体模型可模拟与TME相似的环境,对其中的肿瘤细胞、成纤维细胞、脂肪细胞、免疫细胞、血管及其他基质成分进行空间层面的设计。Truffi等[24]研究指出纳米医学在构建TME模型中的作用,并重点研究纳米药物靶向CAFs的机制,虽然纳米药物可在原理上实现精准定位,复杂的TME环境同样影响纳米药物到达肿瘤部位的能力,从而降低药物的抗癌效果。但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优化离体模型将有望提高靶向TME策略的临床可行性。
五、展 望
TME在TNBC的侵袭和转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TME为肿瘤细胞与周围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等细胞的定植及细胞间的相互作用提供适宜的条件,而肿瘤细胞与TME中其他细胞相互作用又能引起TME的改变,促进肿瘤侵袭性生长、新生血管生成及靶器官的转移。由于乳腺癌的异质性,需要了解肿瘤细胞与TME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肿瘤细胞与TME的相互作用来探索肿瘤的发展机制并指导后续治疗。TNBC具有独特的TME,同时TME的异质性也与TNBC的亚型相关,分子分型基础上的靶向TME治疗将有助于实现“精准医疗”。
关于TIME的研究前景广阔,针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及其他新型免疫治疗靶点的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探索理想的用药剂量、持续时间及联合用药的可能方案,努力改变TNBC的免疫抑制微环境并诱导持久的抗肿瘤活性,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免疫治疗的疗效。TME中其他细胞及成分的靶向治疗、联合治疗及植物化学成分等相关研究,也为TNBC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此外,评估TNBC中靶向TME治疗的临床前研究同样值得重视。构建合适的肿瘤模型及药物载体,动态观察药物对TME的影响,并通过转化研究在临床试验中进行验证,都有助于提高靶向TME治疗的临床效果。相信通过进一步研究,未来TNBC的治疗将取得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