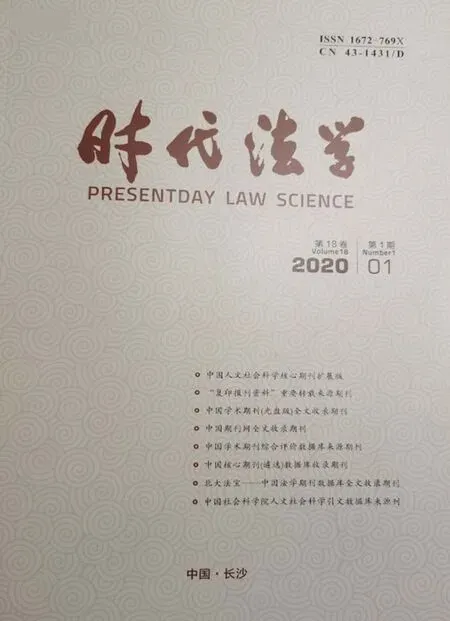我国“或裁或审”条款的反思与突破
——兼评《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
2020-02-22张炳南
杜 涛,张炳南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一、问题的提出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高度发展不仅体现在当事人可以对实体性权利进行一定的处分以满足彼此之间的利益,更表现在可以对争议方式进行选择以满足他们的诉求(1)M. Solimine, Forum-Selection Clause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Procedure, 25 Cornell Int’lL.J. 52 (1992).。显然,仲裁和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主要方式都有其不同优势,但是倘若当事人同时选择了仲裁和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无疑会对争议的解决造成巨大的障碍。这不仅会导致平行程序的发生,产生不一致的裁判结果,也会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延长争议解决的时间。
在我国,这类条款一般被统称为“或裁或审”条款。比较典型的“或裁或审”条款表述为:可以向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某人民法院起诉。在国际实践中,这类条款通常被称为相矛盾或相冲突的管辖条款(inconsistent or competing jurisdiction clause)(2)Richard Garnett, coexisting and conflicting jurisdiction and arbitration clauses,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Vol.9 No.3.。事实上,这种表述的外延更为广泛,不仅可以涵盖同一条款中同时规定这两种争议解决方式的情形,还可以囊括不同条款分别对这两种争议解决方式进行选择的情形。
虽然各国立法与实践对于这类条款的效力认定各有不同,但其本质均是为了明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确认应适用何种争议解决方式,而通常并不会直接规定任一种方式为无效。相比之下,我国对于“或裁或审”条款的态度显得十分强硬。《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协议无效。”尽管有此规定,但考虑到这类条款所具有的多样与灵活性,当事人在商业交往中依然对这类条款趋之若鹜(3)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的“或裁或审”条款,较为简单的规定有“如发生争议,双方均可提交仲裁或到人民法院起诉”;复杂一点的规定,“如发生本合同项下之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协商解决;协商或者调解不成的,提交合同签订地仲裁委员会仲裁,或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或裁或审”条款的范畴进行界定,因此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对“或裁或审”条款的把握出现认定模糊、性质混淆、法律适用不当的乱象。例如,上述第7条中所规定的仲裁协议无效,应当是整体无效还是部分无效?对于“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条款,是否属于“或裁或审”条款?对于多份协议分别规定仲裁和诉讼作为争议解决方式的情形,可否直接适用《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此外,更重要的是,在“有利于仲裁”原则为背景的大环境下,我国近年来仲裁发展的成绩斐然,而《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对于仲裁协议无效的认定是否符合我国政策倾向值得商榷。
因此,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拟从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或裁或审”条款效力认定不一致、类型识别不一致和区分适用不一致三方面着手,通过对其性质、特征和法理的梳理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我国目前鼓励与支持仲裁发展的大背景来谈谈对于《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几点思考,以期为“或裁或审”问题的梳理与探讨提供新的视角。
二、“或裁或审”条款的效力认定不一致
(一)“整体无效”与“部分无效”的相悖论断
一直以来,我国对于“或裁或审”条款的态度就十分坚决,对于这类条款的效力也一向以无效论定,最早可以溯源至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的复函中。复函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合同中解决争议的条款既约定涉外仲裁机构仲裁又约定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该仲裁约定无效”(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圳联昌印染有限公司诉香港益锋行纺织有限公司承包合同纠纷案拟立案受理的报告的复函,法经[1996]110号。。这与《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如出一辙,因此,我国司法实践大多都遵循这样的裁判要旨。例如,面对当事人约定“合同发生纠纷,当事人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乙方所在地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的情形。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审查协议的公正性原则,判定协议内容效力的尺度应当是统一的,在当事人既选择仲裁又选择诉讼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实际上是达成了两个合意,一个是关于仲裁的合意,一个是关于诉讼的合意。当两个合意发生冲突时,既然关于仲裁的合意由于约定不明而无效,那么双方关于诉讼管辖合意的效力也应同样无效。就诉讼而言,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管辖条款,应具有单一性,排他性,“或审或裁”的约定,属当事人约定了两个互相排斥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该条款整体无效,应根据法定管辖原则来确定管辖法院。”(5)(2014)淮中民辖终字第0008号。
然而,在“久益环球一案”(6)(2016)最高法民辖终第39号。中,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涉及“或裁或审”的条款却进行了分割解读。在该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33份销售合同均约定:“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也可以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提交签订地仲裁委员会仲裁,或者向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院则认为,因上述合同约定了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按照《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该争议解决方式中对仲裁的约定,应当认定无效。其后法院又审查了条款中约定法院管辖的部分,认为当事人对于“向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中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因此认定该诉讼管辖条款有效。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随后肯定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或裁或审”条款的分割分析,认可了《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中“仲裁协议无效”并不否定诉讼管辖的观点,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裁定。
可以见得,各级人民法院对于《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在实践中对于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态度也不尽一致。考虑到《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明确规定,以及我国长期司法实践对于“或裁或审”条款的否定性态度,持“整体无效”论观点的法院居多数。那么,“久益环球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肯定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割解读“或裁或审”条款的做法,能否看作是对于1996年复函一定程度上的突破,以及是否意味着我国深受诟病的“严格的有效仲裁协议”问题得以缓解?
(二)“或裁或审”条款的性质梳理
对于“或裁或审”条款性质的梳理,是明确其效力认定的前提。不同于传统的仲裁条款,“或裁或审”条款在形式上既包含了对于约定仲裁的意思表示,又包含了约定诉讼的意思表示。因此,这类条款在性质上属于仲裁条款还是仲裁与诉讼的混合条款,是一个需要首先予以定性的问题。
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通常将“或裁或审”条款认定为有瑕疵的仲裁协议(8)参见侯登华.有缺陷的仲裁协议及其补救[J].法学杂志,2012,(1);齐湘泉,马斌.瑕疵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J],仲裁研究,2011,(2);白钢.论瑕疵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J],河北法学,2014,(7).,认为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仲裁协议,只是在条款的约定上不符合传统仲裁协议的形式。因此,其表述具有瑕疵性,其效力具有不确定性。从法律效果上来看,将“或裁或审”条款视为仲裁协议的观点可以更好地支持“整体无效”论的司法实践。理由有二:其一,《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中“仲裁协议无效”的表述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类条款属于仲裁协议的属性以及隐含着“整体无效”的裁判倾向。其二,实践中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或是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案件中,法院通常在审查这类条款时并不会对条款的性质进行分析,而是直接视其为仲裁协议并援引第7条之规定认定无效。例如,在“泰州市欧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案”(9)(2014)泰中民仲审字第00087号;类似裁判逻辑参见(2017)苏04民辖终324号;(2017)苏04民辖终538号。中,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被申请人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了三种争议解决方式,双方在第(2)项约定采取第2种方式解决的同时,又在第(3)项再次约定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并未排除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因此该约定属于或裁或审的约定。所以,根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仲裁协议无效。
另有观点认为,不能把这种“或裁或审”条款直接等同于仲裁条款(10)宋连斌,黄保持.违反一裁终局原则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实践的实证分析[J].国际法研究,2017,(1):118.。无论是协议仲裁还是协议诉讼,实质上都是当事人将所涉案件管辖权交托给中立第三方的一种管辖约定。笔者认为,同时约定仲裁和诉讼的“或裁或审”条款可以看作是一种混合管辖条款。这种管辖条款中所包含的仲裁条款和诉讼条款彼此独立。从法律效果上来看,这种观点可以更好地支持“或裁或审”条款应当“部分无效”的司法实践。具体而言,法院在审查这类条款时应将其分割为仲裁条款和诉讼条款,首先援引《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认定仲裁条款无效,继而再审查剩余部分的诉讼条款是否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协议管辖的有关规定。例如,在“温州市洞头华凯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一案”(11)(2017)浙民辖终144号。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认为,根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涉及仲裁部分的条款无效,但诉讼管辖部分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有效,并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认为该案合同签订地为上海,故而双方约定上海法院管辖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从而认定该条款有效。
笔者认为,将“或裁或审”条款视为一种混合管辖条款更方便法院适用分割解读的方法,可以有效地缓解我国目前立法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蚕食。最高人民法院在“久益环球一案”中对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或裁或审”条款分割认定的解释方法的认可是十分可取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方法可以被看作是对传统“整体无效”论的一种“突破”。“部分无效”论对当事人选择诉讼的部分留有了一线生机,极大地缓和了《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一刀切”式地适用。
三、“或裁或审”条款的特征识别不一致
(一)“一裁终局”条款与“或裁或审”条款的错位适用
传统而言,“一裁终局”是指“裁决作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即使当事人对裁决不服也不能就同一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时也不能再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1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3.。“一裁终局”条款通常是指当事人在约定诉诸仲裁之后,又约定对仲裁有任何异议的,可以向法院起诉。但在司法实践当中,由于“一裁终局”条款在形式上包含了两种争议选择方式,所以各级人民法院在面对此类条款时经常误认为属于“或裁或审”的情形,从而造成适用法律的错误。
例如,对于当事人约定“凡因执行本补充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补充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结果存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的情形(13)(2014)三中民特字第06308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述条款对仲裁和诉讼进行了顺序式的约定。双方约定了在不能协商解决时,提交仲裁机构通过仲裁程序解决;又约定了如对仲裁机构所作仲裁结果存有异议的,可以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以看出,上述“纠纷解决”条款的约定,既约定了仲裁,又约定了诉讼,违反了《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有关规定,因此认定上述补充协议中所涉仲裁条款无效。同样地,在“内蒙古吉祥煤业有限公司一案”(14)(2013)民二终字第81号。中,当事人之间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为:“若因合同产生纠纷,合同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协议签订地所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任意一方对仲裁结果提出异议的,可向合同签订地法院提出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我国仲裁法对“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要求严格,如果当事人约定同时可以拥有仲裁或诉讼的选择权,等同于同时约定仲裁或者诉讼,属于缺乏请求仲裁的有效意思表示,应依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认定无效。
不过,也有少数法院并不认为“一裁终局”条款等同于“或裁或审”条款。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在“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一案”(15)(2016)京03民特289号。中对两种条款作出了区分。在该案中,中船公司认为双方约定的“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意一方均可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若双方不服仲裁裁决,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条款属于“或裁或审”条款,应当被认定无效。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则仅认定该条款违反了《仲裁法》第9条关于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的规定,并未支持中船公司的主张。此外,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北京庄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一案”(16)(2017)京02民特85号。中,也认为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一裁终局”条款并不属于《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的“或裁或审”情形。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对于“或裁或审”条款与“一裁终局”条款的界定与区分方面存在混乱。那么,是否条款中只要存在两种争议解决方式就一定属于“或裁或审”条款的范畴?仲裁与诉讼两种争议解决方式在条款中的逻辑关系(平行亦或递进)是否影响对于“或裁或审”情形的认定?
(二)“或裁或审”条款的特征明晰
比较典型的“或裁或审”条款表述为:“凡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17)沈德咏,万鄂湘.最高人民法院仲裁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74.根据上述表述,“或裁或审”条款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条款内容上同时涉及诉诸仲裁和诉讼两种意思表示;第二,两种意思表示之间为平行关系;第三,两种意思表示的效力各自独立,需分别判断。事实上,独立分析的司法裁判并不多见,“江苏富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一案”(18)(2017)苏04民辖终621号。算是其中一例。该案中争议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进行仲裁或向需方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仲裁法》第18条(19)《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18条的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的规定,认为当事人并未约定明确的仲裁机构,因此仲裁协议无效。另外还认为,不能因为当事人选择了相互排斥的纠纷解决方式而认定其约定无效,因此没有适用《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又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于约定法院管辖是明确的,所以,法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双方的约定来确定管辖并无不当。法院根本无需依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就可以依据双方约定仲裁机构不明而认定其无效。
不同于“或裁或审”条款,典型的“一裁终局”条款中诉讼与仲裁的关系是递进关系。例如:“争议由××仲裁机构仲裁,仲裁不成的,可向××法院起诉。”(20)(2017)沪01民特130号。“争议由××仲裁机构仲裁,如仲裁仍不能解决的,可向××法院起诉。”(21)(2014)绵民仲字第26号。“争议由××仲裁机构仲裁,不服裁决,可向××法院起诉。”(22)(2009)昆民一初字第48号。“争议由××仲裁机构仲裁,对仲裁结果有异议,可向××法院起诉”(23)(2013)民二终字第81号。等。这种逻辑关系的不同才是“一裁终局”条款与“或裁或审”条款相区别的关键所在。
虽然“一裁终局”条款与“或裁或审”条款均包含两种意思表示,但“一裁终局”条款应当与传统“或裁或审”条款中“A或者B”或“可以A也可以B”的表述相区分,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准确把握“或裁或审”条款的特征不仅是认定条款性质的关键,更是法院准确适用法律的重要前提。具体而言,即便法院认为这类仲裁与诉讼相冲突的条款为无效,也应视其类别区分对待,因为认定“一裁终局”条款无效系因违反“一裁终局”原则,而认定“或裁或审”条款无效系因违反《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所以,对于个别法院不加区别地直接援引《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将所有类型的“或裁或审”条款均认定无效的做法,笔者不予苟同(24)(2017)辽01民辖终15号;(2017)苏04民辖终386号。。
四、“或裁或审”条款的区分适用不一致
(一)多份协议与单一协议中“或裁或审”条款的混淆处理
在如今的商事交往中,当事人对于复杂的大宗交易,通常会在同一时间或先后时间内签订多份协议,以保障交易的各方面权利义务得以明确。在多份协议之中,当事人可能在先签订的合同中选择了仲裁,而在后签订的合同当中选择诉讼作为争议解决的方式。这时候也会形成既选择仲裁又选择诉讼的“或裁或审”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在同一条款中同时选择仲裁和诉讼的情况大有不同,考虑到后签订合同可能导致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变更,也可能是对不同事项的争议解决做出的不同规定,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机械地适用《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关于“或裁或审”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多份协议中涉及不同争议解决条款的考量不当也会造成法院对于裁判结果的极大偏差。首先,在涉及不同事项而约定不同争议解决方式问题上,从“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案”(25)(2017)京02民特375号。中就能体现。该案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出租人、承租人双方应根据本合同约定的内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时,任何一方均可将该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遂后双方又签订了《飞机委托管理协议》,其中约定:“有关本合同的一切争议,双方应根据本合同约定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北京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朗业湾乙公司辩称,两份协议无论是从签订主体还是从签订的内容来看,都是两份独立协议,一是调整融资租赁的事宜,一是调整委托管理事宜,所签订的争议解决方式也是分别调整不同的事项,并不违反《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然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两份协议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认为两者分别约定了仲裁和诉讼,显然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构成了《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或裁或审”情形而无效。
反观之,在同样涉及多份协议的“陕西盈德气体有限公司一案”(26)(2013)民二终字第11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投资建厂供气合同》(约定仲裁)在合同性质上与《设备转让合同》(约定诉讼)并不一致。因此,法院认为所约定的诉讼管辖是对转让设备发生纠纷解决的方式,并非双方将此前供气法律关系解决争议方式由仲裁变更为诉讼,或在已约定仲裁方式的情况下同时又约定了诉讼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因此并未支持上诉人依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认定“或裁或审”条款归于无效的请求。同时,多份协议往往涉及签订的时间先后问题,面对这种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合同纠纷时,不能简单地适用“或裁或审”条款的一般规定。“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一案”(27)(2018)京04民特61号。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在该案中,双方当事人自2011年9月至2017年2月之间共签订七份合同(合同主体并不相同)。其中主合同《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协议签署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在最后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各方在此确认,各方因各方已签署协议以及本补充协议的解释、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双方发生争议后,申请人华普公司认为根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补充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属于“或裁或审”情形,应当认定无效。被申请人则认为《补充协议》是双方达成的最新合意,在先签署的协议中有与《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之处,应以《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首先肯定了当事人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对争议解决的方式进行约定、补充和变更,并确定《补充协议》是七份协议中签订时间最晚的一份。所以认为《补充协议》可以对之前六份协议的相关内容进行确认、补充或者变更,这其中包括了争议解决的方式。因此,法院并未以《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认定存在“或裁或审”的情形。
我们不难发现,多份协议中的“或裁或审”条款与单一协议中的“或裁或审”条款在司法处理上并不相同,因为其中涉及对合同事项进行修改以及对不同事项进行分别约定的情形。因此,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如何把握“或裁或审”条款的特性就显得至关重要。需要明确以下事项:以不同事项分别约定仲裁和诉讼与同一事项约定仲裁与诉讼是否都属于“或裁或审”条款的范畴?是否同一时间约定的“或裁或审”条款与先后时间约定的“或裁或审”条款都适用《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
(二)多份协议中“或裁或审”条款的区分认定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通常意义上的“或裁或审”条款,仅指在特定的一个协议或者特定协议的仲裁条款中既约定仲裁又约定诉讼的情形,而不包括多个协议中部分协议约定仲裁又部分协议约定诉讼的情形(28)(2018)京04民特62号。。多份协议中的“或裁或审”条款往往是在一份协议中约定仲裁作为争议解决的方式,在另一份协议中约定诉讼作为争议解决的方式。这一般会涉及两种情形:一是针对同一事项先后分别约定了仲裁和诉讼的情形;二是针对不同事项先后分别约定了仲裁和诉讼的情形。
如果针对的是同一事项,则往往会涉及合同变更的问题。我国《合同法》第77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笔者认为,“协商一致”的表述意味着当事人对约定事项形成合意。实践中,如果当事人对同一事项的争议解决条款达成新的合意,而且又不存在《合同法》中规定的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则应当视为当事人对合同进行了变更。也就是说,如果先签订合同约定了诉讼,而后签订合同约定了仲裁的话,则意味着当事人的争议解决方式从诉讼变更为仲裁。对于这一情形,国际司法实践采取了十分一致的做法。例如在LembagaPelabuhan Kelang v Kuala DimensiSdnBhd(29)LembagaPelabuhan Kelang v Kuala DimensiSdnBhd [2010] 9 Current Law Journal 532.案中,马来西亚上诉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后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对他们重要协议的一种重新确认,其中对于诉讼的约定有效地排除了之前对于仲裁的约定,将诉讼认可为彼此之间明示的争议解决方式。不仅如此,澳大利亚(30)The Golden Glory [1991] FCA 235 (Fed Ct Aust).、新西兰(31)Ishimaru Ltd v Page [2007] NZHC 571.、加拿大(32)The Kinugawa [1998] 2 FC 583 (Fed Ct Can).和美国(33)Applied Energetics Inc v NewOak Capital Markets LLC 645 F 3d 522 (2nd Cir 2011).等国的司法实践也都支持这样的观点。
此外,如果针对的是合同中的不同事项,当事人对于仲裁和诉讼的约定不冲突,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认为只要约定的事项不超出《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认定约定有效。正如上文讨论的“陕西盈德气体有限公司一案”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仲裁是供气法律关系的争议解决方式,而诉讼是对于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并不构成“或裁或审”条款的情形。可以见得,我们不仅要区分多份协议与单一协议对于“或裁或审”条款认定的不同,更要注意对于多份协议中针对同一事项的“或裁或审”情形与针对不同事项的“或裁或审”情形的区分。
五、对我国“或裁或审”条款的思考与建议
(一)“有利仲裁原则”下的政策隐喻
纵观各国实践,对于“或裁或审”条款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对于仲裁的政策倾向。英国一直以来以对仲裁的友好态度而世界闻名,Paul Smith Ltd v H&S InternationalHolding Inc.(34)Paul Smith Ltd v H & S International Holding Inc [1991] 2 Lloyd’s Rep 127.一案便已透露出有利于仲裁的司法偏好。该案涉及了两个相互冲突的争议解决条款,当事人在合同的第13条中约定了ICC仲裁,而在第14条中则约定英国法院具有管辖权。法官认为原告主张这两个条款因为矛盾而无效的观点是十分严厉且不被人所青睐的,而且会导致当事人对于仲裁的合意完全归于失败。在法官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并不复杂,第13条应当被认为是对争议解决机制的选择,而第14条应当解释为当事人对于仲裁程序准据法的选择。或许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处理结果有些“出乎意料”,但是法官在最大程度上调和了这两个冲突争议解决方式之间的矛盾,使之有效并利于当事人的争议解决。英国之后的一些判例也都遵循了Paul Smith案的精神,将仲裁放置于优先于诉讼的地位(35)SeeThe Nerano [1994] 2 Lloyd’s Rep 50;Shell Petroleum Co Ltd v Coral Oil Ltd [1999] 1 Lloyd’s Rep 72.但是,如果当事人在“既选择仲裁又选择诉讼”情形中同时选择的仲裁地与法院地不在同一国家时,情况则会不同,因为法院并不愿意对于一国仲裁地适用另一国的程序法。See Indian Oil Corp v VanolInc[1991] 2 Lloyd’s Rep 634.。
事实上,只要不是当事人在条款中都同意选择诉讼或者明确了诉讼优先的话,在仲裁与诉讼条款相冲突时,英国的司法实践往往都是有利于仲裁的。而这种对于仲裁的偏好源于一些仲裁程序所具有的天生优越性(36)See Richard Garnett: Coexisting And Conflicting Jurisdiction And Arbitration Clauses, Journal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Vol. 9 No. 3.。另外,克拉克法官在Ace Capital Ltd v CMS Energy Corp案中,对仲裁和诉讼之间关系的梳理发现,美国对此类情形的处理与英国的做法相一致,认为“最高法院确认的联邦仲裁法中体现了十分鲜明的有利仲裁的政策倾向”(37)Moses H Cone Memorial Hospital v Mercury Construction Corp 460 US 1 (1983); Patten Securities CorpInc v Diamond Greyhound & Genetics Inc 819 F 2d 400 at 407 (3rd Cir 1987).。美国也在众多判例中确认,除非当事人明示排除了仲裁作为其争议解决方式,否则仲裁与诉讼相冲突时,仲裁应当优先使用(38)Personal Security and Safety Systems v Motorola 297 F 3d 388 at 395-96 (5th Cir 2002); Bank Julius Baer & Co Ltd v Waxfield Ltd 424 F 3d 278 at 284 (2nd Cir 2005).。由此看出,在鼓励仲裁的政策倾向下,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对于“或裁或审”条款的处理上更偏好于仲裁。
反观我国对“或裁或审”条款的态度显得极为“矛盾”。一方面,我国对仲裁事业的支持与推进达到了空前高度。随着我国自贸区改革的深入,上海自贸区入驻多家国际仲裁机构(39)2015年11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代表处,成为落户区内的首家境外仲裁机构。此后,2016年国际商会、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也相继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代表处。,并且已构建了自贸区仲裁院、自贸区仲裁规则、涉自贸区仲裁规则的司法审查及执行意见的“三位一体”自贸区仲裁机制。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从2017年至2018年初相继公布了《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归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文件和司法解释,以支持仲裁事业的健康发展。而另一方面,在如此鼓励仲裁的背景下,我国在“或裁或审”问题上对于仲裁协议却过于保守。虽然《仲裁法》第7条后半句规定“但一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另一方未在仲裁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期间内提出异议的除外。”但这样的例外规定仅认可了仲裁庭可以根据默示合意具有管辖权,并没有改变立法上对于仲裁协议归于无效的认定。此外,这一问题不仅影响国内仲裁当事人对于争议解决的约定,更会影响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执行。具体而言,如果一份涉及“或裁或审”情形的仲裁裁决在我国申请承认与执行,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之规定,法院在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前,依据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审查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如果当事人选择中国法,那么我国法院很可能会依据《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而认定仲裁协议无效。
当然,《仲裁法司法解释》制定于12年前,那时的仲裁发展远不及今日。但是,相比于普遍适用的仲裁优先政策(Arbitration Preference Policy)而言,我国的处理方式值得深思。尤其是在目前我国发展仲裁事业的大背景下,《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中所体现的仲裁与诉讼的地位并不妥当。退一步讲,即便我国不把仲裁置于优先位置,但将其直接认定为无效的做法也有失偏颇。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或裁或审”条款无效的理由主要包括:一是仲裁与诉讼在性质上彼此排斥,不能并存;二是对两者的同时选择,意味着意思表示不确定;三是会造成管辖冲突和实践混乱,浪费仲裁与司法资源(40)沈德咏,万鄂湘. 最高人民法院仲裁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76.。上述理由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却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很多法院在认定“或裁或审”协议无效时以两者相互排斥,但如若说仲裁与诉讼彼此排斥,那为何在法律效果上是诉讼排斥了仲裁,而不是仲裁排斥了诉讼?提交仲裁与申请诉讼不同,仲裁是需要当事人特别约定才可以提起,因此,在当事人既选择了仲裁又选择了诉讼的情况下,即使不赋予仲裁以优先,但至少能够推断出当事人具有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无论是“或裁或审”应当“整体无效”还是“部分无效”,这种诉讼优先仲裁的观点确实不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其次,有效的仲裁协议可以排除法院的管辖,这属于有效仲裁协议的法律后果,但并非是有效仲裁协议的生效要件(41)杨玲.论“或裁或审”条款中仲裁条款的效力——以海峡两岸司法实践为视角[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4):142.。香港法院在William Company v. Chu Kong Agency案中认为只要当事人对“中国大陆法院解决或中国大陆仲裁解决”的条款作出选择就可以解决问题,并不会产生管辖冲突。同样的,对于“或裁或审”情形,当事人的行为可以确定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不会产生意思表示不确定的情形。
最后,退一步讲,仲裁与诉讼作为具有终局性的争议解决方式,应当具有相同的地位,并不存在谁优先于谁的问题。如果当事人同时约定了采用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又并未明确谁应当优先时,就表明当事人将两种选择放置于同等地位,因此,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层面都应当平等考量仲裁与诉讼,并综合推定出最能合乎当事人意图的一种解决方式。
(二)过渡性考量与进路
宁愿使其有效也不认定无效(ut res magisvaleatquampereat)是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同时也是各国对待当事人之间约定协议的态度。因此相冲突的管辖协议不会全部归于无效,因为当事人如此约定就意味着他们彼此明确了一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无非是哪一种争议方式的问题。然而,我国的《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规定无疑不符合这样的精神。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或裁或审”条款认定“部分有效”的突破,虽不能在实质上与我国现在鼓励仲裁的背景相呼应,但是起码可以缓解《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对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蚕食,值得推崇。
尽管如此,由于我国成文法的制度属性,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也不具有拘束力,所以这样的“突破”并不能被各级法院所遵从。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或裁或审”条款分割处理并认定条款“部分有效”后,黑龙江农垦中院在“北京完美时代国际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一案”(42)(2017)黑81民辖终14号。中并未遵循最高院的做法。该案中当事人在《拍摄协议书》中约定:“本协议及未尽事宜,三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通过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或向北京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黑龙江农垦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条款的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应当是指多个条款的情形,一个条款很难划分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双方在合同的一个条款中约定了两个相互排斥的纠纷解决方式,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
基于此,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考虑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于“或裁或审”条款的性质、特征以及效力认定予以明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也可以将涉及“或裁或审”条款“部分有效”的案件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予以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意义对我国司法实践的意义重大,虽然其性质不能等同于普通法系的判例,但也是具有弱规范拘束力的裁判依据(43)雷磊.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J].中国法学,2015,(1):28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44)法发〔2010〕51号。第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不难看出,指导性案例对于各级法院的裁判具有明确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所以,对于“或裁或审”条款的突破当以具有拘束力的形式予以明确,这不仅可以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对于“或裁或审”条款性质与类型的把握,还可以规范各级人民法院对于《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的解读,以肃清当前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混乱的现象。
(三)前瞻性突破与选择
毫无疑问,“或裁或审”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摒弃过去两裁两审、一裁两审等旧制度以与国际接轨的标志(45)叶青.中国仲裁制度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58-59. 参见《仲裁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但是《仲裁法司法解释》第7条在处理“或裁或审”条款的问题上确实不合乎主流国际的司法实践。上述的过渡性考量与进路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并不能完整保全仲裁协议部分的效力。所以,这种“突破”的局限性仍然很大,依旧不能与我国目前提出将上海打造成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的目标(46)国发〔2015〕21号。相匹配。因此,只有寻求真正的切实可行的制度突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从本质上说,“或裁或审”条款的关键在于究竟应该如何认定当事人的意图,或者说,如果不能有效推定当事人意图时,一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以确定一种争议解决方式。相比大多数采取仲裁优先主义的国家而言,我国立法上采用的仲裁无效主义与目前的政策倾向严重不符。换言之,即便我国不采取仲裁优先主义的做法以迎合鼓励仲裁的政策环境,也起码给予两种争议解决方式以平等地考量。在面对“或裁或审”条款时,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同时允许当事人选择诉讼和仲裁,这应当是“最不可能的当事人意图的内容”。(47)See Cooke J: “a most unlikely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ies’ intentions”, Sulamerica Cia Nacional de Seguros Sa v Zurich Brasil Seguros SA[2012] EWHC 42.不论是仲裁管辖亦或是诉讼管辖,解决“或裁或审”问题的根本目的终究还是为避免管辖冲突的发生,所以此类情形完全可以借鉴针对平行诉讼问题的处理方法。
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平行诉讼的问题普遍适用先受理法院规则,即指同一案件在其他法院已经被受理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又到另一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则后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停止或中止该法院的诉讼,让先受理案件的法院优先审理(48)杜涛.先受理法院规则与国际平行诉讼问题的解决[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5,(2):51-52.。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5条也有类似规定,即“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事实上,我国台湾地区对于“或裁或审”条款就借鉴了这种做法,对于当事人约定“本契约如有任何纠纷,得提请仲裁或诉讼”的情形,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各采取仲裁程序或诉讼程序并产生竞合时,其诉讼标的如为同一,则应视其系属之先后,定其处理程序。”(49)中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台上字第1062 号。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认为,此类规定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当事人任一方均有权选择以其中任一方式解决争议,如若一方选择仲裁或诉讼时,先受理的一方具有管辖权,而另一方当事人即受该选择的约束(50)更多中国台湾地区司法实践,参见中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246号裁定、95年度台抗字第390号裁定、96年度台上字第1491号判決、96年度台抗字第300号裁定。。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或裁或审”问题,我国也应采取先受理先管辖的原则。这不仅在一方面尊重了当事人的选择,在另一方面也给予两种争端解决方式以平等地位,由当事人的实际行为决定管辖权的归属。详言之,当事人在管辖协议中选择了仲裁和诉讼,意味着彼此之间已经对于将要选择的争议方式达成了合意,因此,无论在争议发生后,一方当事人先选择哪一个解决方式,都在当事人的合理预期之内,并没有超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另外,一国不以立法或司法层面直接对仲裁与诉讼的地位关系予以评价可以中立地平衡两者的关系,同时也不减损当事人对于管辖协议的约定自治。
当然,先受理先管辖原则适用前提是当事人对于仲裁和诉讼的意思表示应当符合其各自的生效条件。具体而言,对于仲裁部分的约定,应当满足我国《仲裁法》中对于仲裁协议要件的要求,而对于诉讼部分的约定,应当满足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协议管辖的要求,不得选择与争议没有联系的法院管辖,也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总之,如若要从实质上解决“或裁或审”问题对仲裁协议的否定判定,应当摒弃目前仲裁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推行新的制度。先受理先管辖原则既不同于普遍的仲裁优先主义,又不同于我国的仲裁无效主义,其优越性在于:既可以中立地平衡仲裁与诉讼的地位,也符合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将“或裁或审”条款的管辖权归属交由当事人自己的手中,同时也合乎我国当下鼓励仲裁的态度与政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