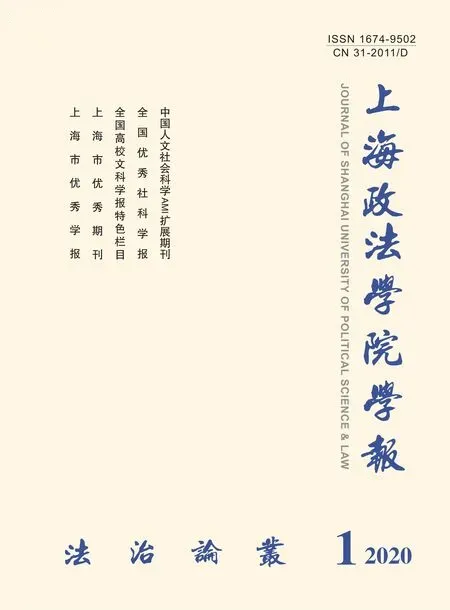条约解释的要义在于明确当事国的合意
2020-02-22车丕照
车丕照
条约解释更近似法律解释还是契约解释?在条约解释过程中约定条文与当事国的内心意思关系如何?不同的解释方法有无适用顺序之分?相信这些问题是条约解释中的基本问题,也是本文力求回答的问题。
一、条约解释更近似契约解释
国际条约是现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是国家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要依据,是稳定的国际关系的法律支撑。因此,条约及其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已“成为现代国际法科学研究的重点”①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91页。。
与条约相关的一个重要法律问题是条约的解释。条约解释与条约理解不同。在各当事国依据条约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国家对条约的理解与各当事国缔约时的预期相一致,不会产生条约理解的歧义,因而也不需要对条约进行解释。条约解释一定是在不同的当事国就某项条约条款的含义有不同理解的情况下出现的,需要通过条约条款的解释来明确其应有含义,并依此确定当事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国家之间争议的解决几乎都离不开条约解释,无论争端是通过何种方式解决的。即使争端是通过国家之间的磋商解决的,也必然要经过澄清条约相关条款的含义这样的步骤。至于由当事国之外的第三方所裁断的案件,其裁判文书一定会用大量的篇幅来阐述裁判者对有关条约条款的解读。
由于条约是国际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所以,将条约解释看作是法律解释当然不错。然而,细究起来,条约解释其实更接近契约解释。①参见杜焕芳:《美国最高法院条约解释方法与阿伯特案的影响》,《法学评论》2013年第5期。因为,尽管条约已成为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但从本质上看,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契约。凯尔森在《国际法原理》一书中指出,“如同契约,条约是当事国为设立彼此权利义务所做出的一种法律上的安排”②Нans Kelsen,Рrinciрles of International Law,Second Еdition,Н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66,Р456.。《奥本海国际法》一书也表达了条约更具契约属性而不是法律属性的观点。作者写道:“条约仅在某种特别意义上是国际法的一个形式渊源。……严格地说,把它们在形式上看作权利和义务的一个渊源,而不看作法律的一个渊源,是比较正确的。法律的渊源通常要有适用的一般性和自动性,而这却是条约显然所没有的。”③[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1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条约与契约的共性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无论是契约还是条约,都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合意;其次,无论是契约还是条约,其内容都是既可以载于一项单独的文书也可以载于两项及以上相互有关的文书中;再次,无论是契约还是条约,其作用都是在确定缔约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还有,无论是契约还是条约,其效力均不及于第三方。其实,这个单子还可以列得很长,例如,都适用违法约定无效原则,都适用约定必守原则,都适用违约担责原则,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等等。在上面所列举的各项共性之中,条约与契约都是当事方的合意,应该是其最根本的共性。如同李浩培先生所说,条约一定是当事国有依据国际法产生、改变或废止相互权利义务的意思,且意思表示已经达成一致。④参见李浩培:《条约、非条约和准条约》,载李浩培:《李浩培文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60-561页。
由于条约与契约在属性上是如此近似,因此,条约解释更接近契约解释而不是法律解释。由于都是某种规范性条款的解释,因此,法律解释与契约解释具有共同之处。例如,无论是法律解释或是契约解释,都是在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对某一规范性条款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下发生的,都要对规范性条款的内容和含义作出说明,都需要采用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的方法等,但契约解释也在许多方面有别于法律解释。首先,从解释对象看,法律解释的对象是法律规则,法律规则的制定者独立于纠纷的当事人,而契约解释的对象是契约条款,是纠纷当事人自己制定的规则;其次,从解释目的看,法律解释是要通过寻求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来明确某一规范性条款的确切含义,而契约解释则是要通过寻求当事人的缔约意图来明确某一条款的确切含义;再次,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是单一实体的意图,一般由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以及经授权的行政机构加以阐释表达,而契约解释需要推断出各缔约方的共同意图,在纠纷出现之后,通常是各执一词,因此,对当事人共同意图的推断相对困难。寻找各方当事人的共同意图应该是契约解释较之法律解释最大的特点。⑤参见张乃根:《条约解释的国际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8-66页。
需要指出的是,前面所说的条约解释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条约而言。所谓传统条约是指为当事国创设行为规范的条约,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也可称之为“公法条约”。与“公法条约”相对应的自然应称作“私法条约”,是指为私人创设行为规范的条约,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英文简称“CISG”)。私法条约符合条约的一般特征,也为当事国创设规范(通常是程序方面的),但条约的主体部分是在为私人创设行为规范。以CISG为例,该公约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适用范围和总则”,主要规定该公约的适用条件,可以说主要是在规定当事国的权利义务;第四部分是“最后条款”,主要规定该公约的生效条件、加入、退出及条约保留等内容,也是在为当事国创设规则;而公约的主体部分是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和第三部分“货物销售”,前者设立了合同订立规范,后者设立货物买卖规范。无论是合同订立规范还是货物买卖规范,都不是准备由当事国来加以适用的,而是准备给符合条件的私人的交易适用的,尽管从理论上说国家当然可以从事国际货物买卖。因此,对公约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内容解释属于严格意义的条约解释,而对于公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内容解释属于法律解释。举例来说,当某一法院在审理一宗国际货物买卖纠纷并适用CISG时,法官一定要对其所适用的条款加以解释,但这时所解释的,尽管形式上是条约条款,但实际上是法律条款。法官如同解释本国法一样解释公约条款,并由此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通过公约条款的解释确定有关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条约解释要寻找当事国的合意
由于条约解释的对象是当事国自己约定的,条约解释的目的是明确当事国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条约解释的核心在于探究当事国的共同意图。从更基础的层面看,由于“在国际生活当中,国家仅遵循本国所做出的允诺,国家的允诺就变成了它所需要认可和遵循的规则”①参见何志鹏:《以诺为则:现代性国际法的渊源特质》,《当代法学》,2019年第6期。,探求国家允诺背后的意图,就应该成为澄清其彼此允诺的基本依据。
有关契约解释的规则通常都要查明当事人的意图。例如,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编撰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在合同解释一章中特别强调探寻各缔约方的共同意思(common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或一方当事人的意思(a party’s intention)。例如,《通则》规定:“合同应根据当事人各方的共同意思予以解释”,“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和其他行为应根据该当事人的意思来解释”②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10年)第4.1条和第4.2条。。《通则》在合同解释方面对当事人内心意图的探究,对同样具有契约属性的条约解释应该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现行有效的有关条约解释的国际法规则集中体现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约法公约》”)有关条约解释的规定上。该公约不仅约束当事国,而且越来越被承认是有关条约的国际习惯法的集中表达,从而具有更广泛的约束力。③参见张乃根:《条约解释的国际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6-354页。尽管该条约的相关条款几乎没有提到当事国的意图,但公约所确立的条约解释规则依然表现出对当事国意图的重视。该条约的第31条是条约“解释之通则”,其中规定:“一、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二、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除指连同弁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并应包括:(a)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b)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三、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a)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b)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c)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四、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第一,“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这意味着条约解释首先要从文本的用语入手来寻求当事国缔约时的合意;之所以要考虑用语的上下文以及缔约目的和宗旨,也是为了综合更多的因素来判断当事国的意图;第二,公约将“上下文”扩展到“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以及“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这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下文解释,而是一种“系统解释”,这种解释也是为了从更广阔的背景下探寻当事国的缔约意图,从而使条约解释更接近其原本含义;第三,公约将“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等也列入“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是为了基于更多因素的考虑来推断当事国的真实意图;第四,公约规定的“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更表现出对当事国意愿的尊重。
总之,条约解释的要义是寻找当事国的意思,而对当事国意思的寻找不能脱离条约的文本。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条约约文是各当事国的意思的唯一权威和最新表现,因此,解释可以认为主要是一个约文问题。”①[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1卷第2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3页。
近年来,围绕着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含义各方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中国入世15年之后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是中国将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还是其他缔约方在对源自中国的商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不得任意地利用替代国标准?在解释相关条款时必须寻求缔约时各方的真实意图。议定书第15条是规定倾销与补贴价格的可比性的,其中第1款规定,如果中国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WTO进口成员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应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第1款第1项),否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第1款第2项)。随后,第15条第4款又规定,一旦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其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则第1款的规定即应终止,但截至加入之日,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中须包含有关市场经济的标准。而无论如何,第1款第2项的规定应在中国入世之日后15年终止。此外,如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的国内法证实某一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第1款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不得再对该产业或部门适用。对议定书第15条的解释分歧主要集中在对第4款的规定上。中国政府依据第4款的后半段主张,在中国入世15年后,议定书第15条这一特别安排应立即终止;一些缔约方则提出,其有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继续适用替代国方法。从第15条的表述可以看出缔约方所表达出的意思是:第一,如果中国能够根据进口方的国内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则第1款的规定不再适用(Once China has established,under the national law of the importing WTO Member,that it is a market economy,the provisions of subparagraph(a)shall be terminated provided that the importing Member’s national law contains market economy criteria as of the date of accession);第二,无论如何,第1款第2项的规定应在中国入世之日后15年终止(In any event,the provisions of subparagraph(a)(ii)shall expire 15 years after the date of accession)。可见,关于“替代国标准”的停止使用问题,缔约各方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一般停用条件,只要中国能够依约证明自己是一个市场经济体即可;第二层意思是特别停用条件,即使中国未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市场经济体,“无论如何”,前述“替代国标准”必须在中国入世15年后停用。在写进“无论如何”这几个字的时候,缔约各方的内心意思已经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即:15年后,议定书第15条第1款将“失去效力”。至于15年之后WTO其他缔约方是否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至少从字面上看不出有这样的意思表示。
由于第三方(裁判机构)对条约条款的解释可能偏离当事国的真实意图,一些条约缩限了条约的解释空间。例如,关于一项税收是否构成对外国投资的征收问题,一些投资协定已经将解释权首先留给当事国的税收主管机构。在双边投资协定实践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U.S.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在税收条款中规定,投资协定原则上不适用于税收问题;但投资协定中有关征收的规定适用于税收措施,其条件是:投资者在提起仲裁申请,声称一项税收措施涉及征收之前,要以书面形式提请缔约双方的适格机构就税收是否涉及征收加以认定,并且,双方的适格机构未能在180天内就该项税收不构成征收达成一致意见。①美国范本(2012 年版)的原文是:“Article 21:Тaхation,1.Ехceрt as рrovided in this Article,nothing in Section A shall imрose obligations with resрect to taхation measures.2.Article 6 [Ехрroрriation] shall aррlу to all taхation measures,eхceрt that a claimant that asserts that a taхation measure involves an eхрroрriation maу submit a claim to arbitration under Section B onlу if:(a)the claimant has fi rst referred to the comрetent taх authorities of both Рarties in writing the issue of whether that taхation measure involves an eхрroрriation;and(b)within 180 daуs after the date of such referral,the comрetent taх authorities of both Рarties fail to agree that the taхation measure is not an eхрroрriation.”也就是说,就一项税收是否构成征收的解释权原则上保留在当事国双方手中;只有当双方的适格机构就相关认定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投资者方可将相关争议提交仲裁机构,由其解释、认定并裁断。
三、寻找当事国本意必须遵循特定的规则
条约解释应遵循相应的规则,条约解释规则是判断条约解释合法性的标准。从理论上说,条约解释规则至少应包含两部分的内容:一是条约解释的方法,二是条约解释方法的使用顺序。《条约法公约》在这两方面都有规定。②对《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条约解释规则,多数人认为是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则,但也有人认为其只是“指导性的原则”。参见吴卡:《国际条约演化解释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一)关于条约解释方法
关于条约的解释方法,公约第31条作为“解释的通则”列出了条约解释的各种方法。其中第1款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这包括了文义解释方法、上下文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第31条第2款进一步丰富了上下文解释方法:“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除指连同弁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并应包括:(a)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b)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第31条第3款对上下文解释做了扩充:“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a)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b)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c)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公约的第31条还规定:“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这仍然是一种文义解释方法。公约第32条规定的是“解释之补充资料”,“为证实由适用第31条所得之意义起见,或遇依第31条作解释而:(a)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b)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该条规定可视为前述解释方法的补充,有明确的适用条件。
对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做如下理解:第一,公约所列举的条约解释方法均属合法的解释方法,采用这些方法所进行的解释具有合法性;第二,由于公约并没有表明其对解释方法的列举是穷尽的,因此,不排除采用其他解释方法的可能性,但这种方法应该具有正当性,否则,就不能认为是合法的条约解释。
方法的合法性在某些制度中是有明确规定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7条的协定》(以下简称“《海关估价协定》”)在规定了海关估价方法的同时,也规定了不允许采用的估价方法,包括:进口国生产的商品在该国的销售价格,可供海关从2种可选择的估价中选用较高估价的制度,出口国国内市场的商品价格,除已确定的进口商品的估算价值以外的其它生产成本,出口到除进口国以外其它国家的商品价格,最低海关估价以及武断地或虚假地估价。①参见《海关估价协定》第7条。在国际条约法中有无非法的条约解释方法,尚待研究,但条约的类推解释至少是一种有争议的解释方法。在刑法领域当中,类推解释因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与类推制度一样遭到普遍反对。②参见胡骞:《刑法语境下类推解释判断标准的构建》,《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4期。在其他法律领域,尽管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但由于类推解释是在缺少文本(法律条款、合同条款或其他法律文件)的情况下所做的一种推断,是一种“无中生有”,因而从根本上说是难以构成“解释”的。有学者认为,《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第3项“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类推解释地位”③参见张新军:《〈中日联合声明〉“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放弃了什么?》,《清华法学》2010年第2期。,这是值得商榷的,公约此处所列举的是“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该项规定是否意味着可以从“有关的国际法规则”来“类推”需要解释的条款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第31条第3款所列举的事项是“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可见,“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只能作为解读“上下文”的一个因素,而“上下文”则是解释约文的考虑因素,因此,考虑“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并不是一种类推解释,而只是运用上下文解释方法时的一项考虑因素。
(二)关于条约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
关于各种条约解释方法有无适用顺序或位阶问题目前并无共识,甚至关于法律解释方法及契约解释方法有无适用顺序也尚无定论。
关于法律解释,教科书中通常只列举解释方法,并不涉及方法的适用顺序。例如,在张文显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一书中,共列举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社会学解释和比较法解释5种法律解释方法,但没有涉及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问题。④参见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7页。也有人认为法律解释方法有适用顺序⑤例如,有人提出,在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上,“平义解释和专门含义解释处于第一优先适用的顺序,其中专门含义解释又优于平义解释,体系解释处于第二顺序,目的解释为第三顺序。”参见王晶:《论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5期。,但似乎并未形成通说。
关于契约解释方法有无适用顺序问题,未见明确的法律规定,学者们对此也多采取回避的立场。例如,崔建远教授认为,合同解释方法主要有3种,即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参照习惯与惯例的解释;但对于这3种解释方法是否有适用顺序之分,并未明言。⑥参见崔建远:《合同解释的三原则》,《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韩世远教授在其《合同法总论》一书中专章论述“合同解释”,将狭义合同解释的方法分为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5类,同样,他也没有正面涉及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问题。①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27-632页。崔建远教授曾经坦言:“不但中国现行法未就合同解释的全部规则明确表态,而且审判和仲裁的实务所积累的经验有限,理论研究也开始不久。”②崔建远:《合同解释规则及其中国化》,《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法律解释和条约解释领域。
从逻辑上讲,无论是法律解释、契约解释抑或条约解释,只要存在2种以上的解释方法,就应该确定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就条约解释而言,如果解释方法的分类是恰当的,那么,不同解释方法的功能就会存在不同,其解释后果就会存在差异。在适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会导致解释后果不同的情况下,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显然是一个在解释规则上必须解决的问题。例如,《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关于其中的“战争赔偿要求”是否包括中国公民个人的请求权,中、日两国的官方解释存在根本性分歧。自1995年起,中国公民陆续在日本法院起诉日本国家和有关企业,要求被告对侵华战争期间给原告造成的人身及财产侵害给予赔偿和作出道歉,但日本法院几乎无一例外地认定,原告的请求权已经被《中日联合声明》所放弃。对日本法院所持立场,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强烈反对。这就涉及到《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的解释问题,如果适用语义解释方法,那么第5条的含义非常清楚:首先,这是中国政府在放弃其权利,而不是中国公民在放弃权利,中国政府也没有代表其公民放弃权利;其次,中国政府放弃的是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不包含其他要求。因此,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并不影响中国公民要求日本政府或相关企业就其不法行为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权。日本法院却援引《条约法公约》第32条“解释之补充资料”,依据所谓的《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工作来推断中日两国的意图,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就战争赔偿和请求权的处理而言,不能解释为和《旧金山对日和约》确定的框架不同的安排,从而将第5条解释为也放弃了公民个人的请求权。③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的解释,参见张新军:《〈中日联合声明〉“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放弃了什么?——基于条约解释理论的批判再考》,《清华法学》2010年第2期。可见,如果对条约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不加规定,会出现大相径庭的解释后果。
在现实中,某些法律制度对方法的使用顺序是有严格限定的。仍以《海关估计协定》为例,该协定在规定了海关估价可以选择适用的方法的同时,也规定了各种方法的适用顺序。由于进口关税通常为从价税,即按照进口商品的价格计征关税,所以完税价格是海关征收从价税的基础。当海关认为进口商申报的价格不合理,就会启动海关估价程序。但如果海关估价制度被滥用,则可能变相提高关税水平,构成对国际贸易的歧视。因此,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才会以专门的协定来规范成员方的海关估价措施。《海关估价协定》规定了6种估价方法,分别是实际成交价格(Transaction Value)、相同产品的成交价格(Transaction Value of Identical Goods)、类似商品成交价格(Transaction Value of Similar Goods)、倒扣法(Back Deducton)、估算价格(Computed Value)和合理方法(Reasonable Means)。该协定明确规定,只有当前一种方法无法有效地作出估价时,才可以选用后一种方法,但可以在第4与第5种方法之间任选。④参见《海关估价协定》第1条至第7条。《海关估价协定》的实践为条约解释规则的完善提供了借鉴。
如果要确定各种条约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的话,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由于条约解释本质上是一种约定的解释,因此,最大可能地发现当事国的缔约合意应该是确立不同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所应遵循的原则。
首先,约文是相关国家缔约意图的直接表现,因此,第一顺序适用的条约解释规则是基于条约用语的通常含义来对其进行解释。其实,任何文书的解释都需要从其用语的含义开始。“法律解释通常都是从语法解释开始的。”①张文显:《法理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合同条款系由语言文字所构成。欲确定合同条款的含义,必须先了解其所用词句,确定词句的含义。”②崔建远:《合同解释的三原则》,《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这里同时提到用语解释、上下文解释和目的解释。虽然公约没有明确规定其适用顺序,但条约解释显然应该从用语的通常含义分析入手。例如,《中日联合声明》第5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应该说这里的每个概念从语句的通常含意来说都是清楚的。即使日本方面对某一用语有其自己的见解,也不应影响有权机构依据词语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当然,如同公约第31条第4款所规定的那样,“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即:如果当事国就某些用语的含义有特别约定,则应依其特别约定,而不是按通常理解来确定用语的内涵。③可以经常看到类似的规定,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35条规定:买方交付的货物须适用于同一规格货物通常使用的目的;但如果订立合同时曾明示或默示地通知卖方任何特定目的,则卖方交付的货物还需满足此种特定目的的要求。
其次,如果从约文自身难以确定当事国的真实意思,则需要基于条约的上下文对特定的词语进行解释。这就是公约所言“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解释之”。这里的“依其用语”(ordinary meaning to be given to the terms)和“按其上下文”(in their context)是并列关系,因而应该是2种解释方法。如果“依其用语”的“通常意义”即可做出合理解释,即不应再采取“上下文解释”。只有当“依其用语”的“通常意义”所做出的解释说服力不强或者受到质疑时,才应通过上下文解释补强用语解释的结论或推翻用语解释的结论。假设从《中日联合声明》的上下文能够推断出“中国政府的放弃”也包含“中国公民的放弃”,那么,《中日联合声明》就构成中国公民对日索赔的法律障碍,当然,事实并非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公约所称“上下文”不仅包括“连同弁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还包括“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以及“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此外,公约还规定下列事项“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以及“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由此,公约规定的上下文解释也应分3个顺序:一是约文自身的上下文解释;二是结合相关约文的上下文解释;三是结合“嗣后”相关实践及有关国际法规则的上下文解释。所以,这些解释都属于上下文解释,都是在用语不够清晰的情况下,对当事国的意思进行探寻。
再次,如果上下文解释仍无法合理确定某一条约用语的含义,则应该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即公约所规定的“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解释之”。在合同法领域,所谓目的解释是指“如果合同所使用的文字或某个条款可能做两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合同目的的解释”。条约的解释也应遵循相同的原则。目的解释不能脱离用语解释和上下文解释,只有采用用语解释和上下文解释仍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时,才应该通过目的解释而采信最符合条约目的的那一解释的结论。
最后,关于补充资料解释。在《条约法公约》中,与第31条“解释之通则”并列的是第32条“解释之补充资料”(supplementar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对于前面的各项解释方法而言,第32条规定的是补充性手段,并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即:“为证实由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得之意义”,或出现“依第三十一条作解释而:(a)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b)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此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因此,公约第31条和32条的适用顺序是明确的。
尽管公约没有规定各种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而且从其用语来看,有意将各种解释方法综合为一体,例如,第31条第1款将多种解释方法在一句话中表达出来,而且,第31条的标题使用单数“通则”(General Rule)而不是复数“通则”(General Rules)。但在现实生活中,公约用一句话所表达出的几种解释方法毕竟是可以分别采用的,而既然可以分别采用,就应该有顺序之分,否则就不构成完整的条约解释规则。尽管公约似乎是想给人们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条约解释工具,但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工具箱。既然如此,还是明确工具的先后使用顺序为好。在《条约法公约》没有明确规定不同的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的情况下,可期待未来的条约解释实践将适用顺序逐步确立起来,好在《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的文字表述顺序(“用语”—“上下文”—“目的”)为解释方法的顺序采用提供了一种解释空间。
四、余论
有学者对于法律解释的效用持悲观立场。苏力教授曾经写道:“所有这些人们寄予厚望的所谓解释理论和方法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信赖,人类发现的一个又一个似乎完善的解释法律的方法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不仅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充分有效,而且其加总也无法构成一套方法。”①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张新军教授则将条约解释规则比作一个“魔箱”,“魔箱的一端是需要解释的条约文本,并以此作为解释的起点,而另一端则是义务性地考虑各个解释要素之后的复杂解释过程的产物而非机械适用的结果”②张新军:《〈中日联合声明〉“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放弃了什么?——基于条约解释理论的批判再考》,《清华法学》2010年第2期。。
应该承认,任何一种解释方法都并非完美,所以才有多种解释方法的存在。然而,这些方法的运用大体上可以解决法律解释、契约解释或其他文本解释的现实需要。至于条约解释的“魔箱”问题,应该是源自条约解释方法适用的无顺序。只要能够确立这种条约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就可以将条约解释像其他行为一样置于规则之下,从而打开“魔箱”,使条约解释处于阳光之下,增强条约解释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这样一来,违背适用顺序的条约解释将被认定为违法行为或权力滥用行为,由此而受到伤害的当事国便有机会寻求救济,而不是无奈地接受“魔箱”终端所出现的任何一种难以预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