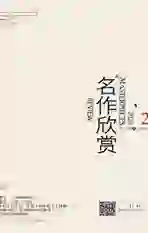大自然的神圣安排
2020-02-21邱冬梅
摘 要: 华兹华斯《丁登寺》一诗的地理意象和地理景观恬适优美,创造了幽深而光明的象征性境界,以对照映衬和逐层发展的塔式结构建构诗歌地理空间。其或隐或显的地理书写,是诗人抨击机械文明对自然文明的戕害,虔敬礼赞自然,实现个人灵魂、纯粹生命,以及上帝神恩合而为一的理想追求。
关键词:《丁登寺》 地理形态 空间结构 理想空间 地理书写
在19世纪英国诗人中,对自然虔诚的歌颂莫过于华兹华斯了。其抒情诗的杰作《丁登寺》 (又译《廷腾寺》)便是代表。1798年7月,华兹华斯重游瓦伊河(Wye River,又译怀河、崴河) 河谷,再次倾听丁登寺的天籁,纵览其优美风景:溪流的柔声低语,高峻峥嵘的山崖,静穆的天空,村舍密布的田野,葱郁的树篱,袅绕的炊烟……对大自然的神圣安排,诗人浮想联翩,浅吟低唱间使自然界最平凡、最卑微之物都有了生命,有了灵魂,宇宙万物融为一体,宇宙众生灵一同虔敬自然。
充满灵性的自然万物构成华兹华斯的诗意空间、人文空间,也形成他诗歌独树一帜的地理空间。通过文本细读由表及里分析《丁登寺》 的地理书写,透过地理物象、意象和地理景观为基础的空间形态解读诗中地理空间的呈现,分析地理空间在文本的结构及功能,理解文本地理空间的内涵,解读其地理书写的情感表达与精神追求,从而理解华兹华斯的诗学特征,阐释其诗歌的人性主题,感受领悟其诗歌的抒情艺术。
一、地理空间的呈现
文学地理空间(即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可以分为现实空间、想象空间与心理空间,简称为文学地理的三重空间。《丁登寺》 的地理景观既有眼前的现实地理空间,纵横驰骋的想象空间,还有沉潜内心后营造的心灵空间,三者合一,和谐统一地构成诗歌的地理空间。
现实空间的自然地理形态与华兹华斯生活的客观实景没有很大变形。华兹华斯出生于英国坎伯兰郡的考克茅斯,当地以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恬静秀丽的山色而闻名。这里是他温暖的出生地,是他现实的幸福居所,更是他的精神原乡。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这一带湖区度过,其诗歌很大一部分也是直观地描绘那里的自然风貌。湖光山色,乡野村落,便是华兹华斯最为熟悉的地理空间,这个空间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均熔铸于他的精神血脉之中。
于是《丁登寺》 一开头,便描述了诗人五年后重见瓦伊河两岸的景色:“这里的清流,以内河的喁喁低语∕从山泉奔注而下。我再次看到∕两岸高峻峥嵘的危崖峭壁”, “这棵苍黯的青枫树下,眺望着∕一处处村舍场院,果木山丘,∕季节还早,果子未熟的树木∕一色青绿,隐没在丛林灌莽里”,“一片片牧场,一直绿到了门前;∕树叢中悄然升起了袅绕的烟缕” …… 潺潺的溪流,清澈的湖水,村舍院落,安静的炊烟,清新的花草树木,乡村的淳朴温馨,这就是瓦伊河谷的地理空间。重游旧地,诗人欢喜不已,所见之景皆有人之情态:清澈的河流喁喁低语,几行杂树活泼欢快、野性难驯。诗人描绘的河谷空间灵动俏皮,活泼恣肆,生机盎然。无疑,阔别多年之后重游的地理景观是诗人衷心喜爱,湖区故地是诗人理想的栖居地。昔日漫游、伦敦暂居、法国旅居,这些地理空间转换带来的惆怅失望远不及眼前美景的心灵冲击,因而诗人的描摹和渲染注入了对此地理空间的太多眷恋与热爱,才有了地理景象的勃勃生机和兴发感动的力量。诗人仿若一位丹青高手,面对眼前熟悉的美景,随意着笔,简单勾勒,从容点染,境界即出。艺术评论家罗斯金曾称华兹华斯为那个时代英国诗坛上的风景画家,确是恰当准确。
笔锋一转,诗人由眼前美景联想曾短暂客居的异乡,进入记忆的现实空间:“当我孤栖于斗室,∕困于城市的喧嚣,倦怠的时刻”,“人生之谜的重负,∕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磐重压” ……城镇的喧嚣,孤独的挣扎,神秘的重负,乏味烦闷的压力,便是工业化之后的城市空间,诗中虽无细致具体的地理意象来呈现,只是以“喧嚣”“倦怠”“郁郁不欢”“焦躁烦忧”等带着鲜明个人情绪的语词概括勾勒,但对都市空间简省而相对隐性的绘写,反而鲜明地呈现了诗人的道德判断和情感倾向。
华兹华斯认为写诗必须具有“想象和幻想,也就是改变、创造和联想的能力”。所以诗中的地理景观既有眼前的自然地理空间,又有在此基础上展开创造和联想的想象空间。譬如:“这难以捉摸的信息,也许是来自∕林子里没有屋宇栖身的过客,∕要么,是来自隐士的岩穴,那隐士∕正守着火堆独坐。”诗人驰骋想象,村落的炊烟仿若漂泊者的游荡,高人逸士冥想的洞穴。诗人的想象空间幽深玄妙,意境高远,与诗歌开头的活泼灵动的景观大异其趣。地理形态的转换,是诗人从眼前的欢喜之境开始回忆与反思,从单纯的欣悦雀跃转向内心的沉潜自省,因而这一想象空间也可说是诗人的心理空间,是渗透诗人主观情态的,由感觉甚至错觉和联想介入的世界——虚拟的地理空间。在想象的地理空间中,诗人想象邂逅过客或隐士,应和或暗示着对现实的逃遁与隐逸。因而,地理形态的转换实是诗人情思流淌与现实世界的观照,是诗人以心托物后形成的心理空间,是诗人渴望重回心灵净土的真实感受。
于是,诗歌的地理形态不断在现实、想象、心理,以及现在、过去、将来三个空间维度交替闪现。譬如,诗人在林中游览时过去的经历与眼前的景色交替在他眼前闪烁,也想象着自己日后远去,妹妹所见所感之景。而诗歌的后半部分,诗人在风光旖旎的地理景观面前神与物游,童年时代、青年时代和今日的地理空间已脱离眼前的实景,再次进入到想象的空间,也可以说是诗人的心灵空间,因为诗人最终联想到“仿佛有灵物,以崇高肃穆的欢欣∕把我惊动;我还庄严的感到∕仿佛有某种流贯深远的素质,∕寓于落日的光辉,浑圆的碧海,∕蓝天,大气,也寓于人类的心灵,∕仿佛是一种动力,一种精神,∕在宇宙万物中运行不息,推动着∕一起思维的主体、思维的对象∕和谐的运转”。诗人精神升华后的意念空间或心灵空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在的一个整体,虽然是想象的产物,却与现实的地理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诗歌的现实空间、想象空间与心理空间三重空间交汇融合,使诗歌增添了审美张力和延伸潜质。
河谷空间与工业化的城市空间,诗人今日游览之地理空间与昔时生活之地理空间,想象空间、现实空间,以及心理空间,或显豁,或隐蔽,构成这首诗歌的地理空间。
二、地理空间的建构
按文学地理学解读,文学地理空间“从本质上讲乃是一种艺术空间,是作家艺术创造的产物,但也不是凭空虚构,而是与客观存在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空间有重要的关系。……特有的地理空间建构对文学作品的主题表达、人物塑造等,往往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可见,文学地理空间建构与现实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空间紧密联系,并艺术性地表达诗歌的主题。《丁登寺》 一诗中构筑了现实空间、想象空间和心理空间三重地理空间,与诗人呈现的社会现实空间相互渗透,互为映衬,关联密切。这三个空间有异质因素,也有同质因素,既是时间的历时性存在,也是空间的共时性存在,并作为有机的整体统一于“丁登寺”这一精神的保护地。
现实的河谷空间宁静美好,远离纷扰,万物和谐,是心灵憩息之所。回忆空间是城市空间,沮丧灰暗,倦怠焦躁,则是机械文明社会的折射。想象空间则由眼前实景,进入冥想世界,感受自然,感怀亲情,礼赞自然。河谷空间和想象空间是同质的,是“微贱的田园生活”的体现,“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这是返回自然,回归自由的理想理空间,是宗法制社会田园生活的情态,是诗人心之向往的理想生活。回忆空间则是异质的,诗人对法国革命的失望,对都市文明的厌倦和人生坎坷的感怀,因而对暂时寄身的城市文明空间充满厌烦鄙弃,对这一空间的描绘也寥寥数语,不愿置喙多言。
诗歌地理空间的建构若从空间形态分析,可解读为两种形态,一是对照映衬的建构,二是逐层渐进的塔式建构。前者即上面所述的河谷空间与城市空间,今日游览空间与昔日空间,冥想空间与眼前现实空间的映衬对比。而后者却是诗人成长过程中对大自然体验的变化,即经历的各个阶段的地理空间建构。为何称为塔式建构?因为塔式结构是下端固定、上端自由,以自重及水平荷载为结构依据的结构。丁登寺可视为固定的下端,是诗人思索寻绎自然地理空间奥义的基础。诗人极目远眺,思想纵横驰骋建构的空间便是塔层上端的自由空间、理想空间,或者说,渐进的塔式结构是华兹华斯对地理空间体验性的不断升华。
从对照映衬的空间形态来看,诗人以构建的河谷空间为起点,入眼是山泉奔注、危崖峭壁、静穆的天穹,然后视线转向静谧怡然的田野村落美景,然后进入回忆的空间,即孤寂却也喧嚣的城市空间。这一层面的地理空间建构是地理实景空间与回忆空间的对照。眼前鲜明的景象使诗人得到安恬的康复,唤回业已淡忘的欢愉,在此心灵空间诗人逐渐忘却了人生的重负,摈弃尘俗的焦躁烦忧以及尘世的昏沉热病。这一层面的地理空间建构是诗人的心灵空间与现实文明空间对照。接着,诗人沉醉在自然的沉思中,从地理实境描绘转化到个体生命体验的地理空间,构建人生三个阶段的自然地理空间。童年时代是“粗野乐趣,蠢动戏耍,都成了往事”。青年时代则是一种“强烈的嗜欲,那种爱,那种感情,本身已令人餍足” ,是“痛切的欢乐,眩目销魂的狂喜”。而现在这个阶段,则是“我已学会了如何观察,不再像∕粗心的少年那样;我也听惯了∕这低沉而又悲伤的人生乐曲,∕不粗粝,也不刺耳,却浑厚深沉∕,能净化、驯化我们的心性”。三个阶段的空间形态迥然不同,在比照中发现美丽恬然的地理景观已从最初的嬉戏玩乐之所,狂喜大悲之地,到今日的“纯真信念的牢固依托” ,对地理空间的体验已内化为个体生命历程与所处地理环境间不断累积的互动。
从渐进的塔式结构来看,诗人以丁登寺为基点,即塔的固定的下端,那么,眼前美景和想象空间便是上端自由空间。从地理实境描述转到理想空间的构建,便是从固定的一端累积堆砌,然后向上飞升到自由空间。塔底是坚实牢固,全心依赖的地理实景,向上的壘砌便是对理想空间的追求。在丁登寺废墟上建构的这一空间,使诗人从“从社会组织和历史时刻中逃离出来” ,进入澄明清澈的世界。重游故地,诗人聆听自然天籁,纵览湖光山色,沉醉其间,神交自然,时而欣喜于眼前美景,时而感怀于城市喧嚣浮躁,时而回忆沉浮往事,时而联想未来岁月……眼前,过去,未来三个维度的空间在地理实景空间和冥想空间来回穿梭游弋,层层发展 ,不断上升,如塔层堆积垒砌,最终建成其理想空间。
三、地理书写的蕴涵
诗歌原题为《丁登寺上游几英里处的诗行——记重游瓦伊河河岸》,诗题谈及的丁登寺是一座业已倾圮的中世纪寺院,这是诗人年轻时去过的地方,这一地理空间改变了他的生活,是他的建筑空间记忆,但丁登寺的实际形态并没有出现在诗行中。从地理空间形态而言,诗人以一著名的废墟为纵情游吟的基磐,开始精神世界的追索游历,却对此废墟景观未着一笔,颇让人费解。这一地理空间在诗行的缺席意味着什么?以此地理意象为基点的地理书写的蕴涵是什么?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是互相生发的,因此,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以地理空间元素的发展变化分析,是解读文本思想内涵,诠释诗人内心世界的一个突破点。
诗人在丁登寺这一空间基点上,开始了其天真烂漫的地理书写,并在与自然景物的对话中呈现心灵成长过程。阔别五年之后,面对无比熟悉、魂牵梦萦的旧地,诗人徜徉其间,沉醉其间,感受其美,情不自禁对其深情礼赞。于是,诗中的溪流、山崖、天空、田野、村舍、炊烟……这些地理意象无不润泽灵动、恬静美好,拼接而成一幅幅浮现在眼前的美丽风景画。诗人对美丽的地理实景深切细致的描绘,更侧重其主观情感的抒发:“我站在这里,不仅感到∕眼前的欢愉,还深为欣幸地知悉:∕此时此刻,已经收藏了、储备了∕未来岁月的活力和滋养。”漫游异乡,浸淫世俗的诗人终于在此地理空间找到精神的慰藉,心灵的依托和生命的原动力,这一地理空间是诗人的精神原乡。
接着,诗人追忆往昔,“小鹿”“奔跃”这些意象符号生动地描绘出一位单纯活泼的少年,“峰岭之间 ”“深涧之旁” “荒溪之侧”“轰鸣的瀑布”这些意象符号则准确地描摹出这位热情却又粗心的少年纵情嬉戏于山水田野,耽溺其中的汹涌激情的情状:“像是出于爱慕而追寻,∕更像是出于畏惧而奔逸。”诗人在天真无邪的少年时期只会根据肉体感受,“听凭自然来引导”,与自然发生共鸣联想。诗人幼稚阶段体验和感受的大自然令人迷狂欣喜,充满野性张力,这一地理空间是诗人少时的欢乐天地。
“高山”“巨石”“幽深昏暗的丛林”这些意象符号气象恢宏,雄伟壮丽,是诗人对自然景观强烈的嗜欲、爱和情感。也是诗人青年时代感受到的“痛切的欢乐”,“眩目销魂的狂喜”, 诗人这种大悲大喜延续了少年时期对自然万物的感受,对自然空间感官上的欢愉,粗浅却又天真炽烈。而尘俗百态的焦躁忧烦,尘世的昏沉热病,让诗人的甜蜜欢愉在现实世界的困扰中一去无踪。最后,痛苦绝望后的思想微光转向自然。这一地理空间是诗人由现实世俗的浸染转向自我找寻的哲思之路。
然后,诗人的感官欢愉和情趣相谐相合,“落日的余晖”“浑圆的大海”“蓝天” “大气”这些意象符号呈现的是诗人从迷惘痛苦的思索之后豁然开朗的襟怀。最后,在丁登寺这一神圣之所,诗人发现自然空间不仅净化、驯化我们的心性,而且给人的心灵带来良善和纯净的精神力量。“草原、森林和崇山峻岭”, “这绿色世界的百态千姿”, “耳目所及的森罗万象”,这些意象符号恢宏广阔,既有眼前的地理意象,又有臆造加工的地理幻象,诗人俯仰天地,驰骋现实与幻想世界,在说明凡此种种都能让诗人找到“心灵的乳母、导师、家长,我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 。并且这种信仰使诗人即便不在自然之中,也能够通过回忆此刻的景象而从自然空间中重获力量,因而与妹妹多蘿西并肩而立领受大自然的抚慰,并再次深情抒发对自然的虔敬,“多年来,我敬奉自然”,“自然决不会亏负爱她的心灵”。不止于此,诗人将自然空间的神奇力量升华为普照万物,抚慰一切的上帝之爱:“宇宙万物,无一不仰慕天恩” ,上帝神恩与人之天性、自然万物熔铸在一起。而这些诗行皆是诗人对生命本体、自然世界、上帝神恩深切感受后,终于醍醐灌顶。这一地理空间是诗人转向内心深入思索后的精神升华空间。
因此,诗人的地理书写不仅仅是生动描绘田园山水,怀念旧时美好时光。他笔下地理意象的制造和安排都有一定的托喻之意,在一派旖旎迷人、光明灿烂的境界中渗透强烈情感和对现实的深层思考:美丽的河谷景观展示了19世纪英国西北湖区生动有机的地域文化,但这乡野景观和乡野生活方式行将消逝,因为,城市的喧嚣浮躁已随着英国工业化的蓬勃发展进入这片净土。只是,诗人一直在极力回避这一进程的蛮横粗野,极力遮蔽随之带来的污秽肮脏。
丁登寺在诗行的缺席,恰恰表明这一地理空间是诗人避世退隐,寄寓情思的澄明清澈、纯净无染之地。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列文森认为,这一片断壁残垣的废墟是“一个神圣的场所”,一个“从社会组织和历史时刻中逃离出来并退居于其间的场所” ,也就是说,丁登寺作为昔日的宗教场所,是诗人退隐田园、进入冥想的保护地,是他的灵魂安放之所,精神的依归。
华兹华斯在1799年的一则日记中也写道:“丁登寺和丁登村:一个理想的归隐之地,一个经过慎重选择的……可做宗教冥想和退隐的地方……这座大教堂……有着神秘而崇高的气势。”因而在诗歌中,不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想象世界,华兹华斯渴望回到自然纯净的淳朴生活环境,渴望人类能重新释放天性,回归和谐的自然之地。因此,诗歌的地理书写深刻诠释了文本主题——不满与厌弃污浊肮脏的社会风尚,抨击机械文明对自然文明的戕害,渴望回归自然与人类、上帝神恩和谐共处的天堂。
综上,华兹华斯在《丁登寺》 一诗中地理空间的建构,从眼前实景到回忆空间,从地理实境到冥想世界再到理想空间,抒发对法国大革命失望幻灭之感,对英国走向工业化社会后巨大变化的深刻忧思,以及对机器文明践踏自然、摧残扼杀人性的厌恶与批判。诗中的地理书写呈现了华兹华斯对自然的顶礼膜拜,并于自然的神圣安排中思索个人灵魂、纯粹生命,以及同上帝合而为一的理想本相。诗人虔诚信仰自然的神性,并得到永恒的救赎。因此,华兹华斯在《丁登寺》诗中地理景观的表现、地理空间的体验,以及地理意象的建构,皆是诗人彼时对生命本体生存境遇的审美表达。
参考文献:
[1] 邹建军.周建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J].安徽大学学报,2010 (3).
[2] 华兹华斯(Wordsworth,W.).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M].杨德豫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3] 刘若瑞.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 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Marjorie Levinson.Wordsworth Great Period Poe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华兹华斯诗歌的地理书写研究”(17BWW063)
作 者: 邱冬梅,文学硕士,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文学教育。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