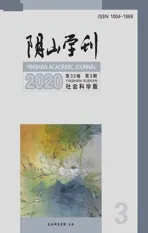《蒙古台卡志序》蒙古译语点校失误指正
2020-02-20胡云晖
胡 云 晖
(包头市政府办公室,内蒙古 包头 014060)
清代学者龚自珍曾撰《蒙古台卡志》,“志邮,志新邮,志喀尔喀自备邮,志鄂博,志察哈尔牧厂鄂博,志卡伦,志围场卡伦,志柳子边”[1]213,志成,复撰《蒙古台卡志序》。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王佩诤点校之《龚自珍全集》,全文收录该序。
在《蒙古台卡志序》中,涉及众多蒙古语地名。由于著者、刻写者、点校者不甚熟悉蒙古语,遂致一篇短序,竟出现数处失误,而且迄今未见纠正。现笔者仅就其明显者,检出数则,予以考证,以求有所裨益于古籍整理。
“喀尔喀自备邮:东路首站曰尼尔得尼拖罗海,曰他尔衮柴木达;后路首站曰肯特山;西路首站曰哈拉尼敦。”[1]214
上述蒙古语站名,有两处错误,一为“尼尔得尼拖罗海”,一为“他尔衮柴木达”,分别考证如下:
尼尔得尼拖罗海
清代的喀尔喀蒙古,共有四部落,即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赛音诺颜部。其中车臣汗部相邻内蒙古,以厄尔得尼拖罗海为东界,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如《大清一统志》卷五百四十四:“(车臣汗)东路,驻克鲁伦翁都尔多博,东至厄尔得尼拖罗海,西至插汉齐老台,南至他尔衮柴达木,北至翁都尔罕。”[2]8喀尔喀自备邮路驿站数处,在厄尔得尼拖罗海者,因为从中国内地的角度来看即为首站,所以上述所谓尼尔得尼拖罗海,当是厄尔得尼拖罗海之误,尼、厄因字形相近而误刻、失校。
厄尔得尼拖罗海,也译写作额尔德尼陀罗海。如《清史稿》卷七十八载:“车臣汗部:驻克鲁伦翁都尔多博,直古北口边外漠北,至京师三千五百里。格埒森札之孙谟罗贝玛号车臣汗,东界额尔德尼陀罗海,南界塔尔滚柴达木,西界察罕齐老图,北界温都尔罕。”[3]2432
对照《大清一统志》记载,明白可证额尔德尼陀罗海与厄尔得尼拖罗海所指是同一个地方,额、厄同音,足证写作尼字之误。
厄尔得尼或额尔德尼,是蒙古语,其义为宝或宝贝。
《华夷译语·珍宝门》:“宝,额儿的泥,erdeni。”[4]41〔明〕王鸣鹤《登坛必究》卷二十二所载(蒙古)《译语·珍宝门》:“宝,额儿迪你四。”[5]136〔清〕高赓恩《绥远旗志·方言·宝货类》:“额尔德尼,宝贝。”[6]470《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宝石,厄而得尼。”[7]
上述额儿的泥、额儿迪你四、额尔德尼、厄而得尼,均与厄尔得尼音近义同,译音用字不同而已。而尼尔得尼,在蒙古语中并不成词。
又拖罗海或陀罗海,也是蒙古语,义为头、脑盖。又译写作陀罗谷、讨罗亥、托罗海等。如﹝明﹞姚旅《露书·风篇下》:“陀罗谷,头。”[8]《登坛必究·身体门》:“脑盖,讨罗亥。”[5]144《钦定金史语解》卷十二:“托罗海,头也。卷一百二十四作脱鲁灰。”[9]239
蒙古语中,多用拖罗海等作山名,其义为山头、山顶。蒙古地区,诸如察罕拖罗海、巴颜陀罗海、库克托罗海等名,随处可见,均是以山色、形状等命名。至于厄尔得尼拖罗海,合而言之,可译为宝贝山。
他尔衮柴木达
按:他尔衮柴木达,是他尔衮柴达木之讹。原本误刻,点校者失校。
他尔衮柴达木,又译写作塔尔滚柴达木、塔尔衮柴达木、他尔浑柴达木等,如以上《大清一统志》《清史稿》所述,所指是同一地名。
他尔衮是蒙古语,其义为肥。《至元译语·身体门》:“肥,搭剌浑。”[10]7《华夷译语·身体门》:“肥,塔鲁浑,taruqun。”[4]55《鞑靼译语·身体门》:“肥,塔儿温。”[11]112﹝明﹞郭造卿《卢龙塞略》:“肥曰塔鲁浑。”[12]175其搭剌浑、塔儿温、塔鲁浑等,均与他尔衮音近义同,译音用字不同而已。
或又作塔尔古等。如《钦定元史语解》卷十三:“塔尔古岱,塔尔古,肥也;岱,有也。卷十六作塔鲁忽带,卷十八作答尔忽带,卷十九作塔剌忽带,卷二十九作塔鲁忽带。”[13]418
柴达木,也是蒙古语,其义为宽广。
﹝清﹞傅恒等《钦定西域同文志》卷十四:“伊克柴达木,蒙古语,柴达木,平敞之谓,境复宽大,故名。”[14]
又译写作柴达穆。如﹝清﹞纪昀《钦定河源纪略》卷十一:“河水伏流,又东南有察罕托辉水。察罕托辉水……东源出巴哈柴达穆(蒙古语巴哈,小也;柴达穆,平敞之谓,地小而平敞,故名)。”[15]95
蒙古语中,多用柴达木指称宽阔之地,以柴达木命名的地名屡见不鲜,如伊克柴达木、柴达木河、柴达木盆地等;也多用塔尔浑等命名地名,如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旗境内就有著名的塔尔浑河,汉语义为宽阔的河流。所以他尔衮柴达木之“肥宽”,是指其地特别辽阔,写作柴木达,于蒙古语并不成词。
至于《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一中断句为“塔尔衮、柴达木”,将一个地名无端割裂,不仅点校失误,也与卷七十八中“塔尔滚柴达木”断句不相统一,属于明显的错误。
上述序文中所谓柳,是指种柳,涉及一种特殊的边防设施。在古代,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分界线上,往往要设置一些标志性的东西,以示区别。可以取土者,即筑长城、起烽燧;能够垒石者,则建鄂博,立封堆;最简便的,就是栽榆种柳,形成一定的屏障。栽榆树的,多在西北干旱地区,称为榆边、榆塞或榆关,甚至榆林;种柳树的,则集中在东部或辽东一带,谓之柳边、柳条边或条子边。据﹝清﹞杨宾《柳边纪略》卷一记载:“自古边塞种榆,故曰榆塞。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16]可见这样的低矮柳边,只能起到象征性的隔断作用,以禁止两侧人民越境。《蒙古台卡志序》所谓“柳子边”,则是木兰围场周围类似的柳树边界,清代分设卡伦,由满洲八旗官兵负责守卫。〔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六:“国语谓围场日辉罕,称木兰者,国语哨鹿之谓。围场为哨鹿所,故云尔。久则视若地名,且有称上兰者。地本喀尔沁、敖罕、翁牛特诸部所属。康熙间,王公等以地献为围场,周一千三百余里。四面立界,曰柳条边。插柳成列如墙,以区内外。凡口外所谓边门皆如是,亦曰鹿柴门。”[17]
上引《蒙古台卡志序》中的蒙古语地名,在〔清〕和珅、梁国治纂修《钦定热河志》卷四十六中有明确记载:“木兰四面树栅,界则内外,按八旗以一营房统五卡伦……卡伦,八旗各五,镶黄旗曰赛堪达巴汉色钦,曰阿鲁色哷,曰阿鲁呼鲁苏台,曰英格,曰拜牲图;正白旗曰巴伦昆得伊,曰乌拉台,曰锡喇诺海,曰纳林锡尔哈,曰格尔齐老;镶白旗曰噶海图,曰卓索,曰什巴尔台,曰麻尼图,曰博多克;正蓝旗曰木垒喀喇沁,曰古都古尔,曰察罕扎巴,曰汗特穆尔,曰纳喇苏图扎巴;正黄旗曰库尔图陀罗海,曰纳喇苏图和硕,曰沙勒当,曰锡喇扎巴,曰锡拉托巴色钦;正红旗曰察罕布尔噶苏台,曰阿尔撤朗鄂博,曰麻尼图布拉克,曰齐呼拉台,曰布哈浑尔;镶红旗曰海拉苏台,曰姜家营,曰西燕子窝,曰郭拜,曰和罗博尔奇;镶蓝旗曰珠尔噶岱,曰苏克苏尔台,曰卜克,曰东燕子窝,曰卓索沟,八旗官兵分守焉。”[18]770明白显示所记述的是相同地域,则可证《蒙古台卡志序》中地名记述失误甚多,分别考证如下:
阿鲁色呼
证之以上引《钦定热河志》之“卡伦,八旗各五,镶黄旗曰赛堪达巴汉色钦,曰阿鲁色哷,曰阿鲁呼鲁苏台,曰英格,曰拜牲图”,可证阿鲁色呼,是阿鲁色哷之讹。
蒙古语谓后背为阿鲁。《华夷译语·身体门》:“背,阿鲁,aru。”[4]54《卢龙塞略》:“背曰阿鲁。”[12]174
其引申义,亦指山阴为阿鲁。《绥远旗志·方言·地舆类》:“哈波尔,山阳;阿鲁,山阴。”[6]443
又译作阿噜。《钦定日下旧闻考·译语总目》:“阿噜岱,蒙古语,山阴也。旧作阿鲁带。”[19]
至于色哷,因其记音的不确定性,一时难以确指为何义。如果从地名角度来考察,可能是蒙古语指称桌子、床几之词,而转义指山梁。《至元译语·车器门》:“桌子,十剌。”[10]5《华夷译语·器用门》:“卓子,石里额,sirihe。”[4]38《鞑靼译语·器用门》:“卓,失列。”[11]103《卢龙塞略》:“桌曰石里额,亦曰舍列。”[12]185十剌、石里额、失列、舍列,均与色哷音近,其义相同。
蒙古语以山形似桌而称地名者甚夥,如席勒山、可可西里、昔连脑包等,其席勒、西里、昔连等,均可译为山梁。则上述阿鲁色哷,是后面山梁之义。阿鲁色呼,于蒙古语并不成词。
川端康成一直信奉着“生——死——生”的生死轮回观念,一如《雪国》中的陈述“死并不是生命的终结”,“死亡应该是内在生命的一种转变,将其转换成另一种东西”。《睡美人》中江口认为可以在妙龄少女身边“猝死,也是老人的极乐”。
阿鲁呼鲁
证之以上引《钦定热河志》,可证阿鲁呼鲁,是阿鲁呼鲁苏台之讹。
阿鲁之义,已如上考,呼鲁苏台,则是蒙古语有芦苇之义。《钦定热河志》卷九十四:“芦,山庄湖中多有之,塞外凡遇沮洳处,亦多产。芦苇,蒙古谓之呼鲁苏,今围场中地及建昌县境内有称呼鲁苏台,皆以有芦苇处得名。”[18]485
蒙古语称芦苇为呼鲁苏,由于译音无定字,或译为忽鲁速、胡芦素、忽洛素、葫芦苏、葫芦素、葫芦斯等,而蒙古地区地名称为葫芦苏台、葫芦斯太、呼鲁斯台者,更是不胜枚举。台或太,是蒙古语有的意思,经常所见,毋烦注解。
库尔陀罗海
证之以上引《钦定热河志》之“正黄旗曰库尔图陀罗海,曰纳喇苏图和硕,曰沙勒当,曰锡喇扎巴,曰锡拉托巴色钦”,可证库尔陀罗海,是库尔图陀罗海之讹。
库尔图陀罗海,又译作库尔都托罗海。如〔清〕张廷玉等撰《皇朝文献通考·木兰》:“本朝康熙年间,各蒙古献其牧地为圣祖仁皇帝行围讲武之所。今皇上御极后,亦岁举秋狝之典于此。周遭树栅为界,设营房八,八旗各一……设卡伦四十,镶黄旗五曰赛堪达巴安色钦,曰阿鲁色勒,曰阿鲁呼鲁苏台,曰英额,曰拜甡图;正白旗五曰巴伦昆堆,曰乌拉岱,曰锡喇诺海,曰纳琳锡尔哈,曰格尔齐老;镶白旗五曰噶海雅图,曰卓索,曰什巴里台,曰玛尼图,曰博多克;正蓝旗五曰穆垒喀尔沁,曰古都尔呼,曰察罕扎布,曰汗特穆尔,曰纳喇苏图扎布;正黄旗五曰库尔都托罗海,曰纳喇苏图和硕,曰沙尔当,曰锡喇扎布,曰锡喇扎布色钦;正红旗五曰察罕布尔噶苏台,曰阿尔萨朗鄂博,曰玛尼图布鲁克,曰扎库拉台,曰布哈诺尔;镶红旗五曰海拉苏台,曰姜家营,曰西燕子窝,曰噶拜,曰和尔博尔吉;镶蓝旗五曰珠尔噶岱,曰苏克苏尔台,曰布克,曰东燕子窝,曰卓苏沟,以八旗官兵守之,统之以围场总管。”[20]此中所记,与《蒙古台卡志序》及《钦定热河志》所记并是一事,恰可互相印证。
陀罗海之义,已如上考,唯库尔图或库尔都之义,因为没有现成的史料可以作证,所以颇费参详。如果认为库尔都是库尔图之异译,而库尔图是由库尔和图两部分组成,则有如下资料可供参考。《钦定辽史语解》卷二:“库尔都哩,蒙古语,库尔,冻雪漫草上也;都哩,形像也。卷三十一作奎剌土邻。”[21]24解释库尔之义为冻雪漫于草上;而《钦定元史语解》卷十四:“库尔巴雅尔,库尔,闹热也;巴雅尔,喜也。卷二十二作阔尔伯牙里。”[13]432及卷十九:“库尔汗,库尔,热闹也;汗,君长之称。卷一百二十作阔儿罕。”[13]500解释库尔之义为热闹。究竟库尔图之库尔,属于何义,颇难抉择。两相对照,将库尔图陀罗海,解释为草上有冻雪的山头,似乎更符合蒙古语的命名习惯,但也只是猜测,谨书此以待识者。
麻巴图
证之以上引《钦定热河志》之“镶白旗曰噶海图,曰卓索,曰什巴尔台,曰麻尼图,曰博多克”,可证麻巴图是麻尼图之误。尼与巴因字形相近而误刻,点校者失校。
麻尼图,又作玛尼图。如上引《皇朝文献通考》所谓“镶白旗五曰噶海雅图,曰卓索,曰什巴里台,曰玛尼图,曰博多克;”噶海雅图即噶海图,什巴里台即什巴尔台,玛尼图即麻尼图,译音用字稍有差异而已。
而麻尼或玛尼(也译作玛呢、嘛呢、马尼等),与藏传佛教或蒙古喇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经常所说的玛尼堆、玛尼石、玛尼杆等。关于其意义,古籍中有一些解释。如《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服物·攻战之具》:“玛呢,即旗也。以布为幅,杂色俱有,长几一丈,宽如其长十之八。书喇嘛经咒于其幅,遇风展动,与讽诵等,宰桑以下建之。图克玛呢,即大纛旗也。长尺余,宽亦如之。旗幅用绿色缎,书喇嘛经咒于其上,台吉建之。”[22]536又《钦定河源纪略》卷十二:“马尼图山,蒙古语,马尼,咒文也,如意之谓,旧刻咒文于石上,故名。”[15]101又《钦定辽史语解》卷八:“玛尼,梵语,宝也,卷三十作麻湼。”[21]101
由上所引资料可知,麻尼或玛尼等,可能最初来源于梵语,有宝、如意之义。在藏传佛教中,则指将经咒书写在旗幡、镌刻于岩石等上面,相当于讽诵经文,以求吉祥如意。所以各地所见者,或是高树经幡的石堆,或是大书梵文、浮雕造像的摩崖石刻,总其名,即统称为麻尼图或玛尼图,以蒙古语翻译之,即有麻尼石或有玛尼杆。
博多克遂
证之以上引《钦定热河志》及《皇朝文献通考》,可证“博多克遂”应作博多克,遂字应归入下文,标点为“又柳于博多克,遂西,柳于珠尔噶岱”。
蒙古地区,有以博多克为名者,如博多克图山、博多克图泉等,关于博多克之义,无明确书证,唯《大清一统志》曰:“密柳坡,在旗西南二百里,蒙古名博多克布尔哈苏。”[2]2
蒙古语指丛柳为布尔哈苏。如《清史稿》卷七十七:“西:兔毛河,蒙名陶赖昆兑,源出敖柴达木,柳河,蒙名布尔哈苏台,源出插汉拖罗海冈。”[3]2419又译作布尔噶苏或补儿阿速等。如《钦定金史语解》卷十二:“布尔噶苏,蒙古语,丛柳也,卷八十一作不剌速。”[9]227《卢龙塞略》卷二十:“柳曰希扯孙,一曰补儿阿速。”[12]179由此推断,博多克或许是茂密之义。因而上述诸书所说之博多克地名,应该是一种简称。
察罕布尔台
证之以上引《钦定热河志》及《皇朝文献通考》,可证察罕布尔台,应是察罕布尔噶苏台之误,序中漏刻。察罕,蒙古语义为白;布尔噶苏台,已如上考,是有丛柳之义,合而言之,察罕布尔噶苏台,是有白色丛柳之地。
布哈浑尔
证之以上引《皇朝文献通考》之“布哈诺尔”,可知布哈浑尔是布哈淖尔之讹,《钦定热河志》并误。蒙古语谓牤牛为布哈,元代多译作不花。如《钦定元史语解》卷十八:“库库布哈,库库,青色也;布哈,牤牛也。卷九十五作阔阔不花。”[13]481
蒙古语称湖泊为淖尔,亦译作诺尔等。如《钦定元史语解》卷四:“察汗诺尔,察汗,白色也;诺尔,池也。卷十一作察罕脑儿。”[13]303《华夷译语·地理门》:“湖,纳兀儿,naqur。”[4]26《登坛必究·地理门》:“湖,恼兀儿。”[5]132《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水一·安西南路》:“哈喇淖尔,淖尔,蒙古语谓池。”[22]356淖尔、诺尔、纳兀儿、恼兀儿等,音相近。淖、浑字形相近,《蒙古台卡志序》与《钦定热河志》误刻,点校者失校。
除上述错误之外,比较《蒙古台卡志序》《钦定热河志》及《皇朝文献通考》,还可以发现上述古籍中一些其他蒙古语地名记写错误。如《皇朝文献通考》之“古都尔呼”,是古都古尔之讹;《钦定热河志》之“锡拉托巴色钦”和“阿尔撤朗鄂博”,分别是锡拉扎巴色钦和阿尔撒朗鄂博之讹。其中阿尔撒朗,《皇朝文献通考》作阿尔萨朗,《蒙古台卡志序》作阿尔散朗,音极相近,是蒙古语狮子之义,而阿尔撤朗于蒙古语并不成词。
此外,在《龚自珍全集》所收《蒙古像教志序》中,亦发现一处错误。即“黄教之祖曰宗喀巴……自称文殊师利之瑚必勒罕,生于额纳特珂克地,而唐古特、库车淖尔四卫拉特之地遍相宗祖……噶玛巴之后,近世有林沁班珠尔者,称沙布咙于库车淖尔,为库车淖尔察罕诺门之属僧,则并不敢号呼图克图矣。”[1]211-212其中所谓库车淖尔,是库库淖尔之讹。
库库淖尔,是蒙古语,义为青海。《钦定河源纪略》:“按库库淖尔即古青海,一名西海,一名卑禾羌海,一名零海,一名鲜水,《元史》名呼呼脑儿。《一统志》载青海在西宁府西五百余里,其水周回七百五十余里,水色青绿,中有山名奎逊托罗海、察罕哈达,东西对峙,即古所称龙驹岛,应龙城故址也。河水东流,淖尔在其北,众山围绕,与大河相望,支流交错,为河流环带中众川旁蓄之区。”[15]278
又译为库克淖尔等。《清稗类钞》第一册:“青海,古曰西海……青海之名,则见于西魏,时凉州刺史史宁与突厥分道袭吐谷浑还会于青海是也。蒙古语称库可诺尔,又曰库克淖尔,诺尔、淖尔,状音字之异,总之言海也。”[23]
蒙古语称湖泊为淖尔,称青色为库库等,均如上考,王佩诤《龚自珍全集》点校本在上面几处库车淖尔后,均注:“一本‘库车淖尔’作‘青海’。”既云是青海,则必然是库库淖尔,作库车淖尔者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