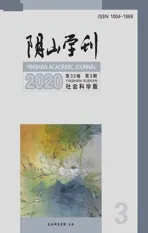《西游记· 女儿国》:大众文化时代的喜剧生产与美学
2020-02-20周红兵
周 红 兵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一
《西游记·女儿国》中有一个有趣的情节,电影第60分钟,唐僧对孙悟空说:“悟空,为师有个重要决定要告诉你,为师决定,把这孩子生下来!”唐僧、猪八戒与沙和尚三人因误饮子母河水受孕,孙悟空到如意真仙处取得落胎泉水之后,唐僧等人却对是否落胎起了争议,争议迅速形成两派,一派以唐僧、女王等为主要成员,他们不愿意落胎,因为每一个胎儿都是一条生命,众生平等,我佛慈悲,唐僧师徒三人不能落胎,否则便是违背了取经的基本信念,即便取到了真经,但也因违背了真经的基本精神而无济于事;另一派则是孙悟空,孙悟空主张应当落胎,因为唐僧等人如果生产则会贻误西天取经的事业,唐僧曾经发下的宏愿就无法完成,天下因此就无法得救。最终的结果是孙悟空施展定身法术,强行将落胎泉水灌入唐僧等三人口中,于是便引发了唐僧与女王随地写经忏悔的情节,并进而推动了唐僧与女王之间朦胧情愫的发展。这是一个有趣的改编。《西游记·女儿国》是根据小说《西游记》改编的,电影中唐僧师徒三个受孕、落胎的情节在原著中主要是在第五十三回《禅主吞餐怀鬼孕,黄婆运水解邪胎》中。唐僧师徒四人离开金兜洞后餐风宿水继续西行,行到一条小河,因水清口渴,所以唐僧令八戒取钵盂舀水给他喝,八戒“舀了一钵,递与师父。师父吃了一少半,还剩了多半,呆子接来,一气饮干,却伏侍三藏上马”[1]695。这河是子母河,这河水正是让西梁女国受孕产子的子母河水,因此,子母河水是在唐僧等人进入女儿国之前饮下的,喝水只是为了解渴,因人生地不熟误打误撞饮了子母河水的唐僧、八戒二人因此受孕。但受孕后,唐僧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三藏哼着道:‘婆婆啊,你这里可有医家?教我徒弟去买一贴堕胎产吃了,打下胎来罢。’”[1]697可见,原著中的唐僧态度是坚决的,就是买堕胎药打下胎来,并不存在“把这孩子生下来”的“决定”,因此,原著中并未出现随之而来的争议、写经、忏悔等情节。
可见,围绕着受孕这一事件,电影从饮水地点、饮水原因、饮水人员等几个方面对这一情节进行了改编:饮水地点,原著中子母河是在女儿国都之外,而在电影中则设置成封闭的女儿国之内;饮水原因,原著是唐僧见河水清洁,且自身口渴,主动饮水,而猪八戒则是出于贪吃本性主动饮水的,电影中则改成了或因跌入子母河、或因子母河水溅起而误饮受孕,同样是意外事件,但导致意外的原因并不相同;饮水人员,原著中只有唐僧与猪八戒两人喝了子母河水受孕,沙僧并未饮水因此并未受孕,沙僧在后来孙悟空前往解阳山破儿洞武力夺取落胎泉过程中,大大地助了孙悟空一臂之力,从而从如意真仙那里得到了落胎泉水,而在电影中,受孕的则是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落胎泉水是孙悟空独自前往破儿洞,用自己的真情感化了如意真仙之后取得的。因此,电影中取落胎泉水是一出“文”戏;而在原著中,则是孙悟空经过几个回合的斗力斗智,才在沙僧的配合下,以调虎离山之计取得落胎泉水,实际是一场“武”戏,电影中沙僧因水受孕,所以取得落胎泉水完全是孙悟空一人独立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原著中的如意真仙是牛魔王的兄弟、红孩儿的叔父和铁扇公主的小叔,是一位以武力阻挠孙悟空取得落胎泉水的男仙,是“牛魔王家族”[2]成员中的一员,他阻挠孙悟空取得落胎泉水的重要原因是要为自己的家族成员复仇,而在电影中,则成为无背景、无来历、以“情”配药的“女”仙,她不愿意将落胎泉水授予孙悟空的原因是每个落了胎的孩子也是众生一员的“众生平等”观念。当然,最重要也最有趣的改编,并非受孕原因、受孕人物及人数以及获取“解药”过程的改编,而是唐僧等人对于落胎一事的态度。
生,还是不生?这是摆在电影当中师徒诸人面前的难题。小说中唐僧态度鲜明,直接声明要买堕胎产打胎,而在电影中较为暧昧,但从其行动举止来看,则是选择了生,电影和小说于是便在“生还是不生”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差异。
二
生还是不生的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从生理上来说,唐僧、八戒和沙僧均为男性,即便真的意外受孕,但是否能够生产,如何生产?其二,从结果上来说,唐僧、八戒和沙僧所怀胎儿是否应当生产?
对于第一个问题,原著中,孙悟空得知唐僧、八戒二人怀孕后很是轻松愉悦,就地打趣起唐僧与八戒,他笑道:“古人云:‘瓜熟蒂落。’若到那个时节,一定从肋下裂个窟窿,钻出来也。”[1]696而在电影中,孙悟空得知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怀孕后则是一脸苦恼,压力山大,“怎么办啦?我们要出去,门都没找到,你们三个又怀孕了,为什么那么不小心呐!怎么办呀?”如果说在原著中,孙悟空是以打趣的方式,戏说了唐僧、猪八戒二人可以从“肋下”生产的话,那么,在电影中则根本没有提及如何生产的问题,似乎默认为“他们”可以自然生产。
对于第二个问题,实际只在电影当中存在,因为在小说中,无论是唐僧或者是其他人,并未意识到所谓“众生平等”的问题,并未对取泉水落胎有什么心理上的困扰或者精神上的负担,因此,这个问题只存在于被改编的电影当中。而电影当中以唐僧—女王为代表的生派和以孙悟空为代表的不生派,其分歧在于胎儿是否为众生、是否可以枉顾胎儿性命落胎,以及孙悟空是否可以代替他人做落胎决定的问题。具体来说,这个情节的设置当中实际包含了这样几个问题:胎儿亦众生的“众生平等”问题,替他人决定的问题,是否落胎还关系到目标正义与程序正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落胎这个焦点上。电影中的处理是胎儿亦众生,既然已经饮水受孕形成胎儿这个既定事实,那么必须让这个既定事实顺势发展下去;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应当生产,选择落胎就是人为杀生,有违众生平等的佛教理念。这样的改编实际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如果从佛教的观念来看,这样的改编的确是符合佛教理念的。佛教中当然认为胎儿感孕而生,因果循环,生命不息,前世今生,皆有命定。因此,胎儿一旦感孕而生,即是生命,即为众生,人为堕胎当然为佛理不容。因此,电影的改编是符合佛法的。但在小说中,唐僧实际是毫不犹豫地要“落胎”的,作为得道高僧,毫不犹豫地要落胎,这实在是有违佛理,难道说唐僧不懂得众生平等,胎儿亦是众生的道理吗?
在《西游记》到底是一部佛教著作还是道教著作的问题上,历来纠缠不清。鲁迅先生曾经说《西游记》作者“尤未学佛”,郑振铎也曾经说过:“我们观于吴氏《西游记》第九十八回中所开列的不伦不类的三藏目录,便知他于佛学实在是所知甚浅的”[3]。据一些学者考证,《西游记》中很多经唐僧之口或者其他人物之口说出来的“佛理”,实际是源自道教经典,比如第五十八回真假猴王打到西天,正遇到佛祖讲经,讲道:“不有中有,不无中无。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为有,非无为无……”看上去同《心经》讲空、无关系非常相似:“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4]但实际上“这段经主并非佛经,而是道教经典《太上洞玄灵宝升玄消灾护命妙经》”。另外,第二十回卷首偈语“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尽管有人据此研究《西游记》的“禅宗思想”,但这首偈子实出自元全真派道士何道全(号松溪道人、无垢子)《般若心经注解》,终《西游记》一书,佛教经典被正经八百提到并加以参详的,只有《心经》一卷,此外就是一些用作经忏的《孔雀经》《梁皇忏》,甚至《劝修功卷》等宝卷、《受生经》等伪经也被唐僧堂而皇之地宣说起来,凡此等等,都“实在不能说作者对佛学有多高的造诣。相反,作者对道教经典却相对熟悉一些。”(1)本段中佛、道与《西游记》关系的理解均来自:吴承恩.西游记[M].李天飞,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5-6.以上分析表明,姑且不论《西游记》作者是谁,但相对来说对宗教的熟悉程度是道教甚于佛教。不过,这依然无法说明唐僧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落胎”问题,因为,道教同样反对落胎。据《太上三生解冤妙经》记载,女子怀孕,不知保胎,或主动堕胎,或不慎流产,打落亲生骨肉,使孩儿未出世便夭折、变化为冤魂(即所谓的婴灵)、缠绕父母、伺机报复,或令其短命,或令其生身恶疾、家庭不顺、事业不遂等等,堕胎女子又因经血污秽,触犯天地日月三光,死后要堕入血湖地狱,受极大苦。总之,堕胎是一种杀人损己的行为,应当尽量避免,或做好防护措施。[5]
无论是从佛教还是从道教来看,唐僧落胎实属非法行为。因此,小说中对“不生”即落胎的处置有违佛道两家观念,电影中对“生”的坚持是符合宗教理念的。
三
那么,已经意外受孕的唐僧等人能够生产吗?这当然不可能,毕竟“怀孕”的唐僧等人均是男性,这当中实际包含了几个方面的不可能:一是男性不可能怀孕,二是男性不可能生产,因此,男性也就不可能落胎了。如果说,电影中对落胎与否的争论符合佛教、道教观点,这个改编合理的话,那么也只是貌似合理而已。因为这个合理实际是将一个有理的观点建立在一个不合理的前提之上的,因此,实际是被抽空了基础的结论,这当然是无效的立论。一本正经地以宗教观念来读解唐僧受孕、落胎乃至争论这一情节,将会陷入毫无生活经验和科学根据的无畏无知的笑话当中。那么,为什么小说、电影均在生或不生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呢?
胡适曾经说过:“《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观念的解读,必然会陷入小说仅仅为某种观念演绎的困境当中去;因此,无论是从佛教还是道教甚至是儒家观念来对《西游记》进行解读,都会陷入观念的窠臼当中去。在胡适看来,《西游记》“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他的滑稽意味”,其中的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而在这诙谐中,实际含有一种“尖刻的玩世主义”。因此,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正是《西游记》文学价值所在。历来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各自试图从道、释、儒家立场出发解读《西游记》,实际是遮蔽了《西游记》的本来面目。事实上,《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6]鲁迅将《西游记》列入“讲神魔之争”的“明之神魔小说”,但在他看来,《西游记》这部作品实际只是出于“游戏”而已:“至于说到本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淛所说的‘《西游记》……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这几句话,已经很足以说尽了。”[7]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直接的创作目的,还是为了提供娱乐,给读者以阅读的快感,而作者的思想又是相当自由活泼,所以小说中一本正经的教训甚少,戏谑嘲弄的成分却十分深厚。”[8]
所以,当我们质问《西游记》中唐僧作为一代圣僧为什么就连佛家最基本的众生平等、胎儿亦众生不可以落胎的基本道理都不懂的时候,实际上是走错了路,是落入了胡适、鲁迅先生所批评的数百年来无数道士、和尚和秀才以观念解读《西游记》的窠臼当中去了。因此,从宗教观念来批评唐僧落胎甚至要求唐僧等应当生产胎儿,实在是《西游记》解读的“大仇敌”。我们不应当陷入宗教的观念当中,被小说、电影表层的宗教说法带入节奏当中,而忽略了这本小说的另外一面,即滑稽、玩世、游戏或者戏谑嘲弄的一面。
四
所谓滑稽、玩世、游戏或者戏谑嘲弄,实际是从《西游记》美学风格上来定位的。《西游记》中处处充满了喜剧性元素,处处充满了滑稽、玩世、游戏或者戏谑嘲弄,这些喜剧性元素,在李贽的《〈西游记〉评》中,用“趣”“妙”“奇”“猴”“顽皮”“好谑”等加以评点。[9]如果说,喜剧性是由喜剧人物、喜剧事件、喜剧矛盾和喜剧效果四个方面的基础要素构成的话,那么,《西游记》中处处可见喜剧性元素。
唐僧师徒四人无疑是书中主角,就喜剧性来说,孙悟空、猪八戒无疑是最成功的。孙悟空就是“一派猴模猴样、猴腔猴性,浑身散发着令人开心一笑的喜剧气味”[3]175,无论何时何地,孙悟空身上都洋溢着一派乐观主义的气氛,对自由的向往是他的天性,这种天性使得孙悟空对于权威采取了一种平视甚至是蔑视的态度。这种内在的天性与态度,便常常外放为对一切高高在上权威的调侃、戏谑、嘲弄甚至是不留情面的斥责:对佛教的西天佛祖、观音菩萨或者是诸天神佛,他随时随地都会与之开开玩笑。他敢腹诽如来“好呆”[1]98,并且在他的手掌心里尿上一泡;他会调侃如来是“妖精的外甥”[1]993、观音菩萨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1]255;会怒斥阿傩、迦叶“掯财作弊”[1]1232;对道教正儿八经的神仙,他都是与之称兄道弟,他在玉皇大帝面前自称“老孙”,称太白金星为“老儿”,称太上老君为“老倌”;对妖魔鬼怪动不动就戏称他们为“我的儿”“外甥”,自己为他们的“外公”或“爷爷”。在与妖魔鬼怪斗智斗力的过程中,总是奇招迭出,让妖怪防不胜防:或者利用法术变成苍蝇、蚊子或其他虫子深入敌后侦察敌情;或是巧设妙计,让敌人不知不觉地陷入智计的陷阱当中;或是闪转腾挪,变化万端,与对手天上地下周旋。最令人叫绝的是,孙悟空总能在没有办法的地方想到一个奇招,即钻到敌人的肚子里去,逼迫对方就范。他至少进过黑熊精(第十七回)、铁扇公主(第五十九回)、黄眉妖(第六十六回)、蟒蛇精(第六十七回)、大鹏金翅雕(第七十五回)、老鼠精(第八十二回)的肚子,每次钻肚子的原因、效果以及在肚子里的语言、动作并不雷同,极尽诙谐之能事,让轻松愉悦甚至是捧腹大笑一路伴随人们的阅读。猪八戒更是一个令人捧腹大笑、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喜剧性元素的角色。猪八戒前世为天蓬元帅,因得罪了嫦娥被贬下凡,但是错投了猪胎,便生得一副丑陋的猪样,又以相貌为姓,官名叫作猪刚鬣。因此,猪八戒实际是神、人、猪的混合体。他既有过显赫的简历,又有着难堪的过往,这些往往成为他自夸的资本,又成为别人嘲弄他的事实。猪八戒憨厚的外表中往往隐藏着小小的诡计,一旦取经受挫就准备分行李散伙回高老庄再续前缘,这经常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猪八戒与孙悟空之间的斗嘴斗智成为《西游记》整本小说中最具有喜剧色彩的场景,无论孙悟空做何事,猪八戒总会在中间拌上一嘴,或者在唐僧面前告上一状,让本来艰苦、艰险、枯燥、乏味的取经行程充满了乐趣。
作为一部神魔小说,《西游记》当中的人物实际是由神、人、妖魔三个不同类别构成,但每个层次都充满了谐趣。从神方面来说,既有佛教系统的神仙,也有道教系统的神仙,比如“四圣试禅心”一节中的观音菩萨、黎山老母、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就化身母女四人巧试唐僧,戏弄八戒,充满了趣味。第六十六回《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一章中,弥勒佛的面相是:“大耳横颐方面相,肩查腹满身躯胖。一腔春意喜盈盈,两眼秋波光荡荡。敞袖飘然福气多,芒鞋洒落精神壮。极乐场中第一尊,南无弥勒笑和尚。”[1]852整天笑嘻嘻的面容中,完全看不出任何佛性的尊严,俨然是一位爱笑的知心朋友。即便是弥勒佛祖来收服黄风怪,也竟然是变作一个瓜农,完全脱离了神仙的形象。就道教系统来说,第四十五回《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一章中,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与唐僧师徒四人斗法,行云布雨、云梯坐禅、隔板猜枚实际更像是一场游戏。即便是妖魔鬼怪,他们“皆通人情,随事随时发隽语。其真价殆尤在于此种插科打诨处。”[3]121就连小妖的名称也起得相当诙谐有趣,比如说平顶山莲花洞中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手下的“精细鬼”“伶俐虫”(第三十三回《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和“巴山虎”“倚海龙”(第三十四回《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枯松涧火云洞洞主红孩儿手下的六个小妖:“云里雾”“雾里云”“急如火”“快如风”“兴烘掀”“掀烘兴”(第四十一回《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第六十二回《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下乃修身》)、“有来有去”(第七十回《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小钻风”(第七十四回《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刁钻古怪”与“古怪刁钻”(第八十九回《黄狮精虚设钉耙宴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等。
黑格尔认为喜剧是“形象压倒观念”,喜剧是对那些“本来不值什么的、虚伪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归于自毁灭,例如把一阵奇怪的念头,一点怎么的表现,一种任性使气的态度,拿来与一阵热烈的情绪相对照,甚至把一条像是可靠而实在不可靠的原则,或是一句貌似精确而实空洞的格言显现为空洞无聊,那才是喜剧的”[10]。因此喜剧表现了理性内容的空虚,喜剧引发的喜剧效果即笑,因此包含着人类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真与善的肯定,这是喜剧的审美价值。美国学者奥森曾说:“悲剧赋予价值,喜剧却取消价值……我们就可以把喜剧定义为是对一种无价值的动作的模仿。”[11]这与鲁迅先生所说的“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2]实际异曲同工。作为喜剧的主人公或者表现对象,实际是“无价值”的,而喜剧在表现喜剧主人公时,也就是将所谓的“虚伪的声望和虚假的伟大”撕破,从而暴露其“无价值”的实质,正因为假象和伪装被撕破之后的暴露,喜剧对象显得更加渺小可怜、毫无价值,虚伪可笑。因而,所有的喜剧必定包含着“笑”,这样的笑实际是用深刻的理性内容和犀利的讽刺,在笑声中激起人们最后埋葬旧事物的信心和勇气。所以马克思说,喜剧使“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喜剧也因此具有了现实针对性、批判性和建设性。
考察《西游记》,人们发现,实际上《西游记》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本。尽管《西游记》中处处充满了滑稽、游戏、戏谑嘲弄,但是,在这些喜剧的背后,却自有其暴露性、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也就是胡适所说的一点点“尖刻的玩世主义”。这点尖刻的玩世主义和《西游记》喜剧的暴露性、批判性和现实针对性,在书中随处可见。比如说孙悟空要把玉皇大帝拉下马来,皇帝轮流做的豪迈,实际体现了人们对既定秩序的不满;孙悟空在大闹蟠桃会后,被天兵天将捉拿,与二郎神杨戬斗法酣战时,却被太上老君从天而降的“金刚琢”偷袭,从而被二郎神的细犬咬伤跌倒被梅山七圣所擒,想要偷袭孙悟空的不仅是太上老君而且还有观音菩萨,这实际暴露了统治者对公平正义的漠视;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却是顶着一个“恶贯满盈”的罪名,暴露了统治者对孙悟空在民间“美猴王”美誉的污蔑;一路征程中,原先五百年前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个个不是对手的天兵天将的坐骑、门生或者僮儿,纷纷下界为妖却法力无边,孙悟空处处对他们束手无策,最终只能依靠天上的力量才能收拾这些妖怪,这些与上层社会有着盘根错节关系的妖魔,实际正是官方的社会基础;甚至在取经最后,当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十四年的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大雷音寺后,却被传经的阿傩、伽叶索要“人事”,索取不得之后,竟然传予了无字假经,师徒四人上雷音寺与如来佛祖理论,反遭到如来的一顿数落,最后唐僧无奈,只得将唐王赐予的紫金钵盂奉上,才取得了真经,这正是暴露、批判了统治者及其统治秩序的虚伪、腐败与丑恶,凡此等等。人们可以发现,尽管《西游记》一书中处处充满了滑稽、戏谑、游戏,但是这种滑稽、戏谑、游戏正是喜剧精神的体现,正是作者“尖刻的玩世主义”通过小说的形式对现实进行了暴露和批判。因此,这个喜剧,正是最高意义上的悲剧。
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当中也处处充满了滑稽、戏谑、游戏和戏谑嘲弄:瘦、耍光棍、凶残、别闹、师父你一点本事都没有,你才壮;“孤本,有借有还”“当娘了,怎么那么不小心啦”“好可怕呀!”……但与原著《西游记》相比,不难发现:原著中的这些喜剧元素,体现在语言、情节等多个方面,而在电影中,则主要是借助语言完成喜剧元素的构建。这里的喜剧性语言,很多是在网络上流行的网络语言,比如“凶残”“别闹”“好可怕呀”等,这些网络语言已经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被大众接受并被广泛使用,因而在电影中具有相当的喜感。不过仔细看这些语言,可以发现:实际上,一部分语言与其语境并无直接关系,只是在插入语的意义上使用。因而,这些语言在喜剧气氛的营造上,并非整个情节的有机构成,它们是游离于语境之外的,在利用人们熟悉的网络用语创造喜剧性效果的同时,实际上也将语言抽离出了语境,阉割了语言与情节之间的关系。
从这点来说,小说和电影分道扬镳了。
五
这样看来,在原著中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的“落胎”,在电影中,实际上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唐僧、女王为代表的一方,坚持要生产,孙悟空坚持要落胎,这便构成了一个矛盾与冲突。黑格尔曾经指出,矛盾冲突是戏剧的核心,电影在这个矛盾冲突中前进。那么在电影中,被落胎之后的唐僧及其他众徒是怎样的呢?电影中安排了一段争论,争论主要发生在女王与孙悟空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唐僧落胎一事。女王指责孙悟空“怎么能够替唐僧做决定”,孙悟空则一力承担了为唐僧落胎的事实,并且自认为,唐僧背负西天取经的重大职责,不可能为了受孕而耽误了西天取经的行程。由此,唐僧在落胎之后,为减轻自己内心深处的负罪感,以棍棒为笔,以大地为书,默写经文,超度亡胎;女王则在唐僧身边共同进退,默默写经,超度亡胎。这是原著中所没有的情节,是电影新增加的叙事。文学名著是电影想象资源的重要来源之一,从文学名著到电影,实际是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转换,正如美国学者约翰·M·德斯蒙德、彼得·霍克斯所说:“如果电影是基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那么两者之间的对比是不可避免的。”[13]但比较的目的何在?是要比较的天平探测出原著与改编之间的忠实度问题吗?尽管“忠实度”问题在改编研究中是有意义的,但是“小说与电影之间进行比较的关系不在于对‘忠实’于原作做美学上的确认。毋宁说,是将小说和电影看作是它们在其中起作用的文化中同样地体现出来的东西,比较有助于详细说明其中的每一个通过各自叙述学的构建如何向它们的观众进行讲述。”[14]一个完整的情节,可以包含若干个单独的事件。从电影《西游记·女儿国》来看,唐僧等人从受孕到写经构成一个因果链,因此是一个完整的情节,这个完整的情节中包含着受孕、取水、落胎、争议、写经等事件。电影的改编,实际是将叙事的重心放在“应当”生产的问题上。电影叙事者关注的问题是落胎(堕胎)与生命的关系问题,支持他们展开论辩的是每一个胎儿都是生命个体的观念,而在原著中根本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任何思考。从这个改编来看,电影是对原著的真正“重写”。
如果仅从“落胎”问题来看,中国古代佛家、道家和儒家实际对落胎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只是小说文本中没有反映出这种态度而已。我们可以说,《西游记》文本正如鲁迅、胡适等人所说,并非佛、道、儒三家观念的演绎,事实上,只是利用传说与历史进行加工的“游戏”之作而已,因此,很多细节的处理,往往会让人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电影中煞有介事地对原著中轻松带过的落胎一事进行浓墨重彩地处理,貌似是对原著的纠偏,事实上这种纠缠只是一本正经地在谈论一个毫无根基的事件,因此,仍然只是一种戏仿。但这种戏仿利用了道德的制高点,因此让人难以察觉其中的吊诡之处;又因为这个戏仿又披上了一层爱情的浪漫外衣,因此让人主动忽略了其中的吊诡之处。只是穿透道德制高点和爱情的浪漫外衣之后,人们依然容易发现,电影的处理,仍然停留在逗乐的阶段,尽管在票房上赚了个盆满钵满,收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资本,但仍未能有效突破原著,形成更高的新时代喜剧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