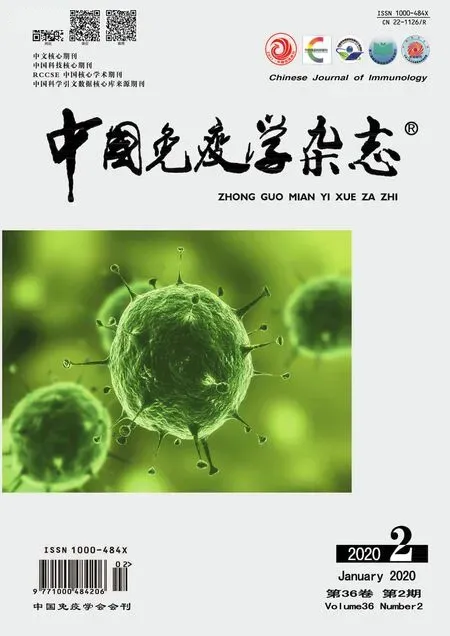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研究进展①
2020-02-20杨黎张毅
杨 黎 张 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物细胞治疗中心和肿瘤中心,郑州 450052)

杨 黎,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国际留学生导师,河南省卫生科技创新型人才,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生物治疗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与微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代谢专业委员会免疫代谢学组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细胞生物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青委会委员等学术兼职。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1项及省部级项目6项。共发表相关论文7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在Mol Cancer、J Hematol Oncol、J Immunother Cancer、Cancer Lett、Oncoimmunology等杂志发表SCI文章19篇。主要从事肿瘤微环境及肿瘤固有信号通路对肿瘤免疫的调控机制研究。

张 毅,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特聘教授,郑州大学一附院生物细胞治疗中心主任,河南省肿瘤免疫和生物治疗重点实验室主任,曾在欧美留学和工作10余年。担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生物治疗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细胞治疗质量控制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学术兼职。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项。在Nat Cell Biol、J Clin Invest、Mol Cancer、Cancer Res、Oncogene、Oncoimmunology、Nat Commun、Cancer Immunol Res等杂志发表SCI论文152篇。从事肿瘤免疫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三十余年,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微环境调控免疫抑制作用的相关机制、影响T细胞分化和功能的分子机制、肿瘤免疫治疗新策略(靶向实体瘤的 CAR-T、TCR-T细胞和新抗原临床应用)的临床试验研究等。
肿瘤微环境是肿瘤发生发展所依赖的土壤,由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等共同组成,其中免疫细胞是主要成分,因此炎症是肿瘤微环境的一个重要标志[1]。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相互作用,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移[2]。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是肿瘤微环境中重要的免疫细胞,其通过调控肿瘤微环境介导肿瘤进展[3,4]。
一般来讲,单核/巨噬细胞可极化为M1型或M2型巨噬细胞。M1型巨噬细胞也称为经典激活的巨噬细胞,由IFN-γ等促炎性细胞因子和免疫刺激性细胞因子(如IL-12、IL-23)诱导而成,这些细胞因子参与Ⅰ型辅助性T(T helper 1,Th1)细胞反应。而TAMs被认为更类似于M2型巨噬细胞[5],亦被称为替代激活的巨噬细胞,由Th2细胞因子(如IL-4、IL-10和IL-13)激活。TAMs在炎症和癌症的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随着TAMs与恶性肿瘤之间的关系不断被揭示,TAMs被认为是肿瘤潜在的治疗靶点。因此,本文总结了TAMs的来源、极化、如何参与肿瘤进展,以及其作为肿瘤治疗靶点的研究进展。
1 TAMs的来源
组织中的巨噬细胞最初被认为是来源于骨髓,然而,来自于原始卵黄囊前体的局部自我维持的肺泡和腹腔巨噬细胞、库普弗细胞、表皮朗格汉斯细胞和脑小胶质细胞被称为组织驻留巨噬细胞。虽然有证据表明各类巨噬细胞可以在肿瘤中共存,但招募的巨噬细胞占TAMs的大多数。目前,还无法评估这些巨噬细胞在不同肿瘤不同进展阶段中的各自作用,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骨髓来源的外周血单核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基质细胞和肿瘤细胞分泌的趋化因子的作用下,被招募至肿瘤局部并进一步分化为TAMs。无论巨噬细胞来自卵黄囊还是骨髓,CSF1均是大多数巨噬细胞的主要调节因子和趋化因子[6]。CCL2与其受体CCR2的结合直接介导了单核细胞招募至原发和转移瘤中[7]。在异种移植瘤模型中发现,VEGFA可以趋化单核细胞,并在IL-4作用下极化为TAMs。在人乳腺癌动物模型中发现,CCL18与其受体PITPNM3结合,协同CSF2介导了巨噬细胞的招募[8]。在结肠癌模型中发现,巨噬细胞的招募是通过CCL20结合其受体CCR6介导的,该趋化因子的缺失导致了单核细胞和/或TAMs的下调及肿瘤的消退[9]。CXCL12/CXCR4轴介导了TAMs的累积,并与B16恶性黑色素瘤的进展相关[10]。
2 TAMs的极化
在肿瘤微环境中TAMs一般表现为M2型巨噬细胞的特征,表达抗炎性细胞因子、清除受体、血管生成因子和蛋白酶的水平高于M1型巨噬细胞。这些抗炎性细胞因子可以重塑肿瘤免疫抑制微环境,进而促进肿瘤进展。TAMs的极化不受其所在部位本身影响,而是受到其所在特定微环境的信号作用所致。影响TAMs极化的因素包括肿瘤细胞来源的因子、肿瘤微环境、巨噬细胞自分泌因子及稳态失衡因素。
2.1肿瘤细胞来源的因子 肿瘤细胞产生的多种因子可以促进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研究发现,结肠癌细胞来源的CSF1可促进巨噬细胞的招募和极化[11]。趋化因子CCL2、CCL3和CCL14刺激多发性骨髓瘤中巨噬细胞的增殖和极化[12]。IL-10抑制了巨噬细胞中促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产生,导致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13]。IL-4与CSF1协同作用,诱导M2型巨噬细胞极化[14]。最近的研究表明,肿瘤细胞来源的微颗粒介导了TAMs的极化,促进了肿瘤进展[15]。此外,前列腺癌细胞来源的Cathelicidin相关抗菌肽再教育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16]。可溶性MHCⅠ类链相关分子通过激活STAT3信号通路诱导巨噬细胞向免疫抑制表型转变[17]。
2.2肿瘤微环境 一旦外周血单核细胞被招募至肿瘤部位,肿瘤微环境则迅速促进其分化成TAMs。肿瘤微环境中的多种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调节巨噬细胞极化,包括CD4+细胞分泌的Th2型细胞因子IL-4[18],调节性T细胞分泌的IL-10[19],及B细胞分泌的免疫球蛋白[20]。Th2细胞来源的IL-13亦可能对TAMs极化发挥促进作用,因为IL-13和IL-4信号级联重叠可导致STAT6激活,尽管体内实验尚未证实[21]。此外,间充质基质细胞来源的MFG-E8已被证实可增强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22]。
2.3巨噬细胞自分泌因子 最近报道称,巨噬细胞自身来源的MIF是黑色素瘤小鼠中TAMs极化的重要决定因素[23]。MIF缺失或应用MIF拮抗剂可以明显减弱TAMs极化,并降低TAMs中促血管生成基因的表达。另外,肿瘤浸润的巨噬细胞可产生IL-10促进自我极化[24]。另一项研究发现,巨噬细胞自分泌CXCL12调节自身向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方向分化[25]。
2.4稳态失衡 低氧可以促进肿瘤进展及转移,主要通过HIF介导,HIF亦可调节巨噬细胞的功能[26]。HMGB1、细胞外ATP等与巨噬细胞表面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结合,导致巨噬细胞功能改变。研究还发现,TLR2和TLR6信号通路均能通过诱导巨噬细胞TNF-α的产生促进肺癌进展[27]。肿瘤细胞来源的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包括二聚糖和透明质酸,可以通过TLR2和TLR4信号通路促进TAMs极化[28]。至关重要的是,这些ECM成分在非炎症组织中并不与TLRs结合,而是在蛋白酶裂解或与活性氧或氮相互作用后成为TLRs配体,从而形成检测炎症和组织破坏的感应通路。此外,在白血病干细胞微环境中TAMs亦可由骨髓来源的其他抑制细胞分化而来[29]。
3 TAMs调控肿瘤进展
TAMs在促进肿瘤进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促进肿瘤发生和进展、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促进转移及建立癌前转移微环境、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图1)。
3.1促进肿瘤发生和进展 TAMs联系着炎症和癌症。2009年,癌症相关的炎症首次被定义为癌症的标志之一。有证据表明,炎症微环境促进了肿瘤上皮细胞和浸润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的基因不稳定性。最近,TAMs来源的炎性细胞因子IL-23和IL-17被证明与癌症进展密切相关[30]。Kupffer细胞可以通过分泌有丝分裂原促进肝细胞癌进展,该机制依赖于NF-κB信号通路[31]。另有数据表明,TAMs来源的IL-6通过STAT3信号通路促进肝癌的发生发展[32],TAMs来源的IL-10通过STAT1信号通路促进非小细胞肺癌的发生发展[33]。这些结果揭示,肿瘤浸润的巨噬细胞在癌症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图1 TAMs促进肿瘤进展的机制及其作为肿瘤治疗靶点的策略Fig.1 TAMs promote tumor progress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AMs as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ancer
3.2形成免疫抑制微环境 TAMs是肿瘤微环境中主要的免疫调节细胞,参与抑制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的抗肿瘤效应。恶性胸腔积液中TAMs分泌TGF-β增多,导致T细胞抗肿瘤效应降低[34,35]。在小鼠肿瘤模型中,TAMs抑制CD8+T细胞的增殖,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诱导iNOS或Arginase I产生ROS,导致免疫抑制作用[36]。TAMs产生的IL-10可诱导共刺激分子PD-L1在单核细胞中的表达,从而抑制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肿瘤效应[37]。此外,TAMs来源的PGE2、IL-10、吲哚胺2,3-双加氧酶在调节性T细胞(T regulatory cells,Tregs)的诱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TAMs来源的CCL17、CCL18、CCL22是Tregs的重要趋化因子,Tregs进一步抑制肿瘤微环境中T细胞的免疫效应作用[38]。
3.3促进转移及建立癌前转移微环境 TAMs促进肿瘤进展的机制还包括增强肿瘤转移和建立转移前微环境[39]。在人移植瘤模型中研究发现,TAMs来源的CCL18促进肿瘤细胞侵袭和转移[40]。肿瘤细胞通过ECM迁移是肿瘤转移所必需的,而TAMs被认为可以通过ECM促进肿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41]。TAMs可以产生蛋白酶,包括组织蛋白酶B、MMP2、MMP7和MMP9,并可裂解ECM,为肿瘤细胞的转移提供通道和途径。
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在肿瘤进展和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阐明EMT的调控机制将大大提高我们对肿瘤迁移和侵袭的认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EMT是TAMs与肿瘤细胞相互作用之后肿瘤变化的重要特征,TAMs来源的相关因子在EMT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42]。
根据动物模型的研究结果发现,TAMs在肿瘤形成转移前微环境中起着关键作用。肿瘤组织中TAMs分泌的TNF-α、VEGF和TGF-β可以通过血流运输到靶器官,诱导局部巨噬细胞产生S100A8和血清淀粉样蛋白A3,这些因子进一步招募巨噬细胞和肿瘤细胞进入靶器官中,促进转移灶的形成[43]。因此,TAMs被认为不仅可以影响局部微环境,还会影响全身的巨噬细胞,从而导致肿瘤的进展。
3.4促进肿瘤血管生成 一些研究表明,TAMs水平与肿瘤中血管数量密切相关。低氧是肿瘤血管生成的主要驱动因素。肿瘤低氧区域,特别是坏死组织发现巨噬细胞大量聚集。巨噬细胞上HIF-1的表达调控多种基因的转录,如调控VEGF在肿瘤缺氧部位的血管生成。基因分析结果显示,TAMs可以产生VEGF、TNF-α、IL-1β、IL-8 (CXCL8)、PDGF、bFGF、胸苷醛糖、MMPs和其他分子,参与肿瘤血管生成,为肿瘤的生长提供营养[44]。在原位和转基因肿瘤模型中发现,Tie2+TAMs与肿瘤血管系统密切相关,促进血管生成,且依赖于内皮细胞产生的血管生成素-2和沿血管系统分布的TAMs上Tie2受体的表达[45]。
4 TAMs作为肿瘤治疗的靶点
如上所述,在不同的癌症模型中TAMs促进肿瘤生长,TAMs数量的增加与多种肿瘤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因此,靶向TAMs是一种新的癌症治疗策略,包括限制单核细胞招募、靶向TAMs活化、重编程TAMs为抗肿瘤活性及靶向TAMs与标准治疗联合应用四个方面(图1)。
4.1限制单核细胞招募 靶向TAMs的策略之一是阻断单核细胞向肿瘤组织趋化。由于CCL2/CCR2轴在单核细胞招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靶向该通路是非常有效的肿瘤治疗方法。CCL2阻断剂(carlumab,CNTO88)在动物模型中已被证明可以抑制多种肿瘤的生长。一项针对转移性去势难治性前列腺癌的Ⅱ期临床试验研究显示,虽然carlumab抗体耐受性良好,但是单一应用该抗体既无法阻断CCL2/CCR2轴,也没有显示抗肿瘤活性(NCT00992186)[46]。Brana等人的研究结果与之类似,carlumab联合四种化疗方案治疗实体瘤,患者耐受性良好,但未观察到血清中CCL2的下调及明显的肿瘤消退反应(NCT01204996)。然而,其他研究结果表明,应用carlumab抗体患者耐受性良好,并出现短暂的CCL2抑制及初步的抗肿瘤活性反应(NCT00537368)[47]。
Sanford等人研究发现,CCR2拮抗剂(PF-04136309)可阻断CCR2+单核细胞从骨髓向肿瘤部位募集,抑制胰腺癌生长和远处转移[48]。一项Ⅰb期临床试验研究应用PF-04136309联合FOLFIRINOX化疗方案治疗肿瘤(NCT01413022),结果显示该疗法安全且耐受性强,并具有一定的肿瘤客观反应率[49]。此外,CCR2特异性人源化抗体(MLN1202)的有效性在临床试验研究中得到了证实(NCT01015560)。
CD11b中和单克隆抗体已被证明可以有效防止髓系细胞向肿瘤部位募集。已有研究表明,应用Mac-1(CD11b/CD18)抗体可以改善小鼠鳞状细胞癌异种移植瘤的放疗反应,并可减少表达MMP-9和S100A8髓系细胞的瘤内浸润[50]。
4.2靶向TAMs活化 使用不同策略靶向TAMs活化亦是有效的肿瘤治疗方法。CSF1/CSF1R信号通路在骨髓单核细胞的产生和肿瘤组织中TAMs极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此,CSF1/CSF1R信号通路是一种具有广阔前景的癌症治疗靶点。动物模型研究发现,CSF1基因缺失可显著降低乳腺癌和神经内分泌瘤的转移及延缓肿瘤进展[51]。基于以上结果,多项应用CSF1/CSF1R抑制剂的临床试验研究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
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可作为有效的治疗靶点。甘露糖受体CD206可看作巨噬细胞特异性靶点。与CD206受体结合的单链肽被连接到纳米载体上,选择性靶向CD206+TAMs[52]。Legumain是一种应激蛋白,属于天冬酰胺内肽酶家族成员,其在TAMs中过表达,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靶点[53]。利用免疫毒素结合的单克隆抗体靶向巨噬细胞表面标志物清道夫受体A和CD52,已在卵巢癌中进行了研究[54]。此外,alemtuzumab(抗CD52抗体)治疗肿瘤的研究正在进行临床试验(NCT00637390,NCT00073879)。
Trabectedin(ET743,Yondelis)通过诱导单核巨噬细胞的凋亡来减少肿瘤组织中TAMs的数量[55,56]。目前,trabectedin已获得欧盟委员会的上市批准,用于治疗卵巢癌和软组织肉瘤,并在2015年获FDA批准用于治疗不可切除的转移性脂肪肉瘤或平滑肌肉瘤[57]。
4.3重编程TAMs为抗肿瘤活性 如前所述,巨噬细胞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具有可塑性,这使得其能够根据肿瘤微环境的不同改变表型。因此,将TAMs重编程为抗肿瘤表型是一种非常具有潜力的肿瘤治疗策略。抗肿瘤巨噬细胞(M1型)具有良好的清除和破坏肿瘤细胞的能力[58]。我们前期研究结果显示,铜绿假单胞菌在治疗恶性胸腔积液过程中,可以将CD163+TAMs极化为M1型巨噬细胞,提示重编程CD163+TAMs可作为恶性胸腔积液潜在的治疗策略[59]。
目前,纳米颗粒逐渐被应用于极化TAMs为抗肿瘤表型的方法。Zanganeh等[60]发现纳米氧化铁(ferumoxytol)能显著抑制小鼠皮下腺癌的生长,并伴有肿瘤组织中M1型巨噬细胞的增加。二氧化锰纳米颗粒通过诱导TAMs极化为M1型巨噬细胞,从而增强化疗反应[61]。负载IL-12的纳米颗粒可以逆转巨噬细胞具备抗肿瘤功能[62]。
CD40是巨噬细胞表面标记物,CD40激动剂与吉西他滨联合应用治疗不可切除的胰腺癌,结果发现该方法通过增强抗肿瘤巨噬细胞的功能,促使肿瘤消退[63]。ChiLob7/4是嵌合CD40单克隆抗体,能够诱导巨噬细胞促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一项针对常规治疗耐药的表达CD40实体瘤和弥漫大B淋巴瘤的Ⅰ期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该疗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64](NCT01561911)。靶向CD40分子的其他临床试验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NCT01103635)。
应用TLR激动剂、抗CD40抗体和IL-10抗体通过激活NF-κB信号通路,极化TAMs为抗肿瘤表型[65]。一种STAT3小分子抑制剂(WP1066)可以逆转恶性脑胶质瘤患者的免疫耐受,选择性诱导共刺激分子CD80、CD86和IL-12在外周血和肿瘤浸润的巨噬细胞上的表达,诱导巨噬细胞向抗肿瘤表型极化[66]。目前一项临床试验正在研究这种药物治疗复发性恶性脑胶质瘤及转移(NCT01904123)。
Thymosin-α是一种免疫调节激素,可以再教育TAMs为树突状细胞,产生高水平的促炎性细胞因子,参与抗肿瘤免疫反应。此外,一些临床试验研究已证实,Thymosin-α可以延长转移性黑色素瘤和进展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期[67]。
β-glucan是一种酵母来源的多聚糖,可以极化TAMs为M1型巨噬细胞,是一种强有力的抗肿瘤免疫调节剂[68]。在一项Ⅱ期临床试验研究中,应用β-glucan聚合物(PGG)显示出适当的抗肿瘤活性[69](NCT00912327)。
4.4靶向TAMs与标准治疗联合应用 放疗和化疗是许多癌症的有效治疗方法。研究表明放疗后肿瘤组织中髓系细胞浸润增加。然而,放化疗后肿瘤细胞和基质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仍不明确。在动物模型中发现,放疗后肿瘤DNA受损、细胞凋亡及缺氧增加,可导致巨噬细胞的招募及促进肿瘤进展[70]。更引人注目的是,阻断CSF1R信号通路增强了其他几种标准疗法的疗效,CSF1R的阻断已被证明可提高化疗对胰腺癌的疗效[71]。因此,认为靶向TAMs治疗与标准治疗相结合是肿瘤有效的治疗手段。
5 结语
本文就TAMs的起源、极化、功能及临床应用方面进行了阐述。TAMs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更好地了解TAMs在临床上的应用,尤其是作为肿瘤治疗的靶点将是至关重要的。靶向TAMs是一种很有前途的肿瘤治疗策略。近期正在进行的关于TAMs的体内外实验、临床前和临床试验研究均显示了令人鼓舞的结果。我们相信,未来靶向TAMs将会应用于肿瘤患者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