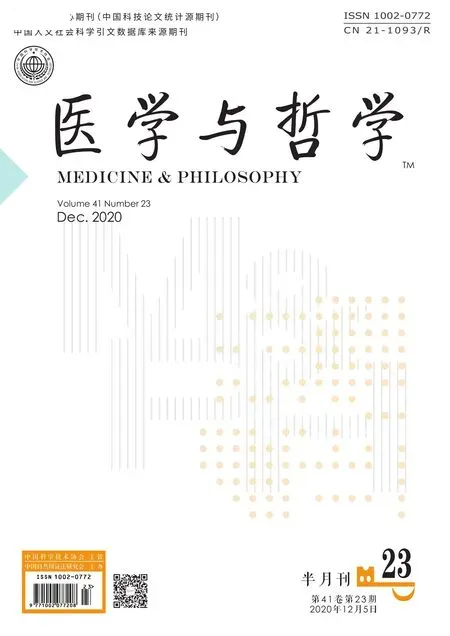生命健康视野下的叙事闭锁*
2020-02-16杨晓霖张广清
杨晓霖 田 峰 张广清
利科(Paul Ricoeur)[1]162在《自我宛若他者》(OneselfasAnother)中断言:叙事在“手把手地教会我们如何认识和面对死亡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叙事能够将我们从未知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而莫伦诺和索勒(Marta Moreno & Nieves Soler)[2]在合编的《追踪老龄化:当代叙事中的老年与记忆》(TracesofAging:OldAgeandMemoryinContemporaryNarrative)一书中提出,我们应该说叙事在手把手地教会我们如何认识和面对衰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将我们从那些对于我们不愿知道,如周围人的逝去和我们自己的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在生命健康叙事语境中,叙事在手把手地教会我们“如何在生命进程的不同阶段认识和面对未知的、恐惧的、伤痛的经历上”发挥重要作用。生命和叙事具有内在关联性,人的生命在叙事中被诠释。作为近年来在国内兴起的一种医学人文落地模式,叙事医学更加侧重于通过不同主体视角的叙事交流提升医护人员的叙事素养,而生命健康叙事则在“大健康”语境下,更关注以广大民众作为出发点的全人健康。
生命健康语境下的“叙事闭锁”是生命叙事中的一种失常状态,但并不一定是一种精神疾病,因为在当代医疗体系中处于灰色地带,需要引起更多关注。“叙事闭锁”(narrative foreclosure)由心理学家弗里曼(Mark Freeman)于2000年提出。弗里曼的概念常被用于叙事老年学的研究和实践当中。本杰明·富兰克林说,“有些人25岁就死了,只不过75岁才埋葬”,这句话描述的正是叙事闭锁者的人生。25岁就有可能成为叙事闭锁状态的人,也就是说,叙事闭锁不一定见于老年人,也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本文在弗里曼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叙事闭锁概念的适用范围,提出人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都可能被闭锁在不和谐、缺乏开放性的生命故事里。对于叙事闭锁者而言,应以叙事身份的可塑性为出发点,运用叙事生命健康理念进行叙事介入,帮助叙事闭锁者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叙事停滞状态,通过推介叙事性阅读和进行生命叙事分享,为其生命进程赋能,开启重新体验生命和阐释生命意义的按钮。当叙事闭锁者走出闭锁状态,重新获得生命叙事的稳定性和开放性之间的平衡时,主体就再次进入健康和谐的生命进程之中。
1 生命健康语境下的叙事闭锁
弗里曼[3]83认为叙事闭锁是生命故事被提前判决,进入终结或者缺乏生命力的状态,是一种认定人生不可能再有意义的不可动摇的宣判[4],弗里曼也将其称作“预先写好的脚本中的终结”。叙事闭锁者在终结感影响下,出现想象力枯竭和“阐释危机”[3]83,也就是说,生命还未真正终结,但是故事结局已被设定。
加利·默森[5]190在《叙事与自由》(NarrativeandFreedom)一书中提到的“生命叙事的尾声阶段”与弗里曼的叙事闭锁概念接近。在叙事老年学语境下,对于叙事闭锁者而言,生命的主体叙事进程已经结束,不再向前演进。叙事老年学在某种意义上强调的是叙事对老年人心身全人健康的重要性,避免老年人进入“叙事闭锁”状态[3]81。欧文-肯扬认为,叙事闭锁也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如果用一本书作为隐喻的话,“叙事闭锁”指的是一个人不再处于自己人生故事的书写过程之中,他认定人生故事不可能更新,也不愿意再去感受、重写和编辑前面的章节[6]。亦即,一个人的内化叙事不再体验为一个有丰富意义等待着在生命进程中的“开放式文本”,而是体验为“已经收尾的作品”[7]。
在生命健康叙事语境中,笔者认为叙事闭锁不必然体验为“已经收尾的作品”或“生命脚本的提前终结”,叙事闭锁可以说闭锁在前一阶段的人生故事所制造出来的叙事结节中,就像突然血脉流通不畅通所导致淤结状态,失去了进入生命叙事进程的情节筹划力。也就是说,我们将一直把自己禁锢在自己错误地认定的故事空间里,无法走出来,无法吸纳人生故事中出现的推动叙事进程向前发展的新的故事情节,这样的状态称作“叙事闭锁”。
叙事闭锁导致人生意义的退化。在正常生命叙事进程中,人们在行动中不断反思、辨识,看见多元的自己,逐渐成长出新的自我。但闭锁状态的生命主体处于相对静止的叙事状态。生命叙事是人格最有特性的层次[8],是一个与自己对话的工具。生命叙事是生命历程的隐喻。一个人在生命过程中,内化发展出的、为生命提供意义感和统合感的自我生命叙事是生命健康的基础。
按照丹麦著名作家迪内森(Isak Dinesen)的说法,“缺乏故事”会妨碍人的“生存”。利科强调叙事对于自我之构成的重要性,主张“个人身份认同的叙事化”[9]。叙事化过程贯穿整个人的一生,在我们形成对自我、对他人和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理解非常重要,但当生命叙事失去弹性,叙事化机制就无法在生命新阶段正常启动。当生命叙事的发展进程出现问题,人的生命健康也就相应地受到影响和损害。
利科[1]116将“个人身份认同”区分为“固定身份认同”和“自身身份认同”两个面向。“固定身份认同”是自我在既定的文化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的认定身份,藉由镜映式心理投射赋予自我定位,这种身份认同基本为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另一种则是与自身性对应的“自身身份认同”,自身身份认同不具备僵化的实体性,而是考虑个体的身份认同会因他人介入而改变或更新。
固定性或自身性很少偏向单一极端,两种始终保持辩证关系,协调两者之间平衡状态的正是叙事身份认同[9]。据此,利科提出“个人身份认同的叙事化”——我们的身份认同是在固定性和自身性、在恒定与变化之间求取弹性,并构成自我,此过程需要叙事赋予能量。叙事是对自身的解释与理解,它影响“我”的观念、价值、视野,也决定“我”对于他人和世界的开放程度。个人身份认同因而已然偏向于叙事身份认同,“我”等于我的故事里的“角色”。
叙事身份除了可能面临分裂危机之外,也可能面临闭锁危机。一般而言,生命不同阶段有其对应的叙事发展与身份认同,如果主体不能顺利地从一个叙事成长阶段顺利过渡到另一个叙事成长阶段,保持叙事身份发展的连续性和生命展延的连续性与秩序,很可能就陷入闭锁状态。也就是说,本应该只是必经阶段和成长阶段的生命叙事变成走不出去的“死胡同”,“无法认同将来的不确定性”[9]。
正常的生命叙事是处于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不断在新的阶段吐出旧的不利于心身健康的污浊故事,吸入有利于健康成长和健康老去的新故事的过程,正如张仲景在《类经图翼》中所言:“吸之则满,呼之则虚。一呼一吸,消息自然,司清浊之运化。”也就是说,吐故纳新原指:人呼吸时,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吐气连系着死亡;吸气连系着生命。吐和纳是一种生命气息的导引,是有节奏的生命活动,缺一不可。叙事闭锁意味着主体总体而言处于“只吐不纳”或者“不吐不纳”的状态。
叙事闭锁不只是由自己对人生故事的个人阐释造成的,因为人总是在一定的“叙事环境”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在这个语境中形成人生故事[10]。叙事成长语境中存在的重要人物是人生故事的共同作者,“非老年叙事闭锁者”,尤其是儿童叙事闭锁者大多在自己的生命叙事构建中处于劣势和被动状态。他们的生命故事被所处的叙事语境中的“他人叙事”主导,失去“自我生命叙事的构建能力”。对于这样的闭锁者而言,需要叙事介入的不只是闭锁者本人,还有在他的叙事生态中对其生命叙事建构起到影响作用的其他人。
在《共同作者的自我》中,麦克连[11]讨论了叙事生态这一概念。从本质上而言,“叙事生态由主体成长过程中所涉及的故事组成,这些故事组成不同主体独特的叙事风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身份并非简单地被自我内化的故事过程所形塑,而是由一个很多故事构成的生态体系构成,这个叙事生态里,有我们讲述的故事,有我们被告知的故事,也有关于我们的故事。
生命叙事是由似真性与可能性两者构成。似真性对应的是固定身份认同或接近心理学家德威克(Carol S.Dweck)所谓的“固定思维模式”,而“可能性”对应的是利科所谓的叙事身份认同,它让人理解任何故事均有多种可能发展情节。叙事闭锁将生命叙事的可能性忽视了,陷入固定思维模式。生命反思和意义赋予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性活动,它们只有在“可能性叙事”中才能实现。当生命主体陷入叙事闭锁状态,直接的后果是主体的想象力被限制,主体失去反思和意义赋予能力,继而失去成长和发展的动力。
正常的、良性的自我发展叙事包含对过去的回顾和对将来的想象和预期两者的融合。陷入叙事闭锁的主体往往失去了对生命故事的流动性把握,必须通过重新认知过去的生命故事和未来可能的生命故事才能成为自己生命故事的主动把握者。叙事闭锁状态则是生活在过去和当下,无法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因而,叙事闭锁是生命叙事中的一种失常状态,是对“生命叙事进程的破坏”。
生命叙事本身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自我修复的文本,然而,长期处于叙事闭锁状态的主体被一层层生命枷锁禁锢,已经体验不到动态和进步,只有停滞与腐溃。当人陷入生命叙事的闭锁状态,主体的心身健康也就会陷入失谐状态。例如,完全将自己锁定在职业身份中,无法感受和进入生命中其他的重要关系故事中;又如,儿童应该逐渐建立独立身份意识,却因创伤经历而无法实现成长等。生命叙事的失谐状态需要叙事干预来提升主体的叙事复元力。
叙事复元力中的“元”指心身元气。叙事复元力可以定义为主体面对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重大压力等非预期事件时,作为进程的生命叙事在可能遇到闭锁或已进入闭锁状态的情况下,自我修正叙事进程中的阻力,逐步恢复生命流动性,重回正常生命进程的一种能力。叙事复元力可以避免主体长时间陷于停滞或倒退的思维模式中。一般而言,暂时的叙事闭锁者可以仰赖自己的叙事素养方面的特质恢复此内源力,而大多数叙事闭锁者需要通过家庭朋友中或相关生命健康机构中叙事素养非常高的人进行正向干预,激发其内源力。
在对叙事闭锁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和梳理之后,本文将叙事闭锁进一步分为职业型、创伤型、疑虑型和老年型四种类型。对叙事闭锁者开展叙事介入,专注聆听他们的人生故事,帮助他们分析致使他们陷入闭锁状态的前阶段故事中,帮助他们提升对自我故事和身份状态的认知,重启再次体验和阐释人生的按钮,赋予其由内而外突破闭锁状态的能量。只有当主体处于叙事稳定性和叙事开放性的平衡状态时,主体经历的才是一种健康和谐的生命进程。
2 叙事闭锁的四种类型
2.1 职业型叙事闭锁
在职业型叙事闭锁中,一个人将生命叙事局限在职业身份中,不愿将叙事向除职业之外的生活、亲情、爱情等方面发展,也就是生命叙事将“面向职业之外的叙事身份”关闭,将身份闭锁在单一职业叙事中。这样一来,“主体-我”在被动的职业身份中逐步客体化,他/她越来越无法主动融入与至亲和爱人的关系中。将自己隔绝在单一职业身份中的“我”,久而久之陷入关系性孤独中。他们往往长期处于单身或离婚的孤独状态,即使有婚姻也无法真正融入家庭生活。职业型叙事闭锁使人不再有时间、精力和情绪去感受生活中其他的美好事物。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的代表作《长日将尽》、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星期六》和埃德森(Margaret Edson)的《心灵病房》等叙事作品中都有一个陷入职业型叙事闭锁的主人公,分别是维多利亚式的管家史蒂文斯,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和卵巢癌晚期患者、文学教授贝尔宁。这些叙事作品所描述的正是当代语境下,许多“事业有成者”共同的一种职业失常状态。在没有叙事介入的情况下,叙事闭锁者往往到年老回顾自己的人生或在罹患重症的情况下才意识到当时的自己被闭锁在职业叙事身份中。
人本身由多个身份组成,在不同叙事语境下承担不同的身份,如父子身份、爱人身份、管家身份、作家身份等,但是职业型叙事闭锁就只单一地承认职业身份,否认了其他身份。职业型叙事闭锁者具有两面性,在职业上登峰造极,让人崇敬;在生活上和情感上冷漠无情,让人心寒,最终走向存在性孤独和关系性孤独的人生状态。尽管他们没有经历过重大的心理创伤,但逃避亲情,不懂爱情,疏远家人,除了职业之外,对未来和其他生命关系皆无长远期待[12]。
这种状况必然引起关系性危机和存在性危机。加拿大一项为期12年的研究显示,职业型叙事闭锁使闭锁者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提高,而女性则罹患恶性肿瘤的几率也会升高。《心灵病房》中的贝尔宁教授受职业型叙事身份闭锁困扰,40多岁罹患卵巢癌晚期。临近生命尽头,贝尔宁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被闭锁在不健康的状态下,她想起导师曾告诫她,“生命的真谛在于走出内心世界,与人互动”。
笔者所在叙事分享中心2019年接触过多例职业型叙事闭锁者。其中一位53岁早年留学澳洲,曾在澳洲与伙伴组建乐队并走遍澳洲,为当地老百姓带来听觉盛宴,受到热捧。他每日沉浸在音乐世界中,想到的只是鲜花和掌声。年轻时经历一段婚姻,不欢而散。此后他认为婚姻只会限制音乐事业发展和个人自由。他对父母也毫无责任感,一直没有孩子,认为孩子是累赘。音乐家除摆弄自己的乐器和参加乐队演出外,基本不与其他人社交。可见,这位音乐家是典型的职业型叙事闭锁。笔者通过推荐他阅读《长日将尽》等叙事作品,逐渐帮助他从闭锁状态中走出。
职业型叙事闭锁的重要特点是沉浸于正在履行的责任和身份结构无法自拔,无法完成自我更新,无法接受可能潜在改变自己人生故事的新体验、新阐释和新责任。他们在职业发展上是积极的,但在职业之外的其他方面却是消极的。与职业型叙事闭锁相近的是目标型叙事闭锁。人生目标性太强,当到达目的之后,很容易不自觉地陷入叙事闭锁状态。较早获得人生所谓的巨大成功的主体更易于被目标型叙事闭锁捕获。
可以看到,对于职业型叙事闭锁、目标型叙事闭锁而言,也许前一阶段的人生故事不一定是完全消极的,但由于缺乏想象力和自我更新能力,生命进程受到严重阻碍。而接下来要探讨的创伤型和疑虑型叙事闭锁却是在生命的前一阶段遭遇过消极事件。
2.2 创伤型叙事闭锁
创伤型叙事闭锁指的是主体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创伤,在没有得到充分的创伤心理辅导和关怀的情况下,创伤事件变成一个阻碍个体成长的症结,形成叙事闭锁,无法更新融入到新的生命故事情节中,如果不调动内在资源对叙事身份进行调整或者不经他人进行叙事干预赋予能量很难走出闭锁的一种心理状态。在创伤型叙事闭锁中,一个人将内化的生命叙事局限在之前发生的某个重大的创伤事件中,“再现难关”[13]让创伤经历者一直停留在创伤事件的持续影响之中,无法跳出这个事件来实现创伤后成长。
笔者有位美国朋友,由于对军人的极度崇拜,嫁给一位美国大兵。美国大兵幽默风趣也睿智,早年曾在部队服役,后被派往非洲参加索马里摩加迪沙巷战,但是历尽艰难万险侥幸活着回到美国后,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不能工作,罹患严重的抑郁症和妄想症,对周围一切异常敏感,进入典型的创伤型叙事闭锁状态。朋友希望笔者能给予帮助和建议。笔者仔细地分析了她丈夫的经历,并在交谈时发现他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市区参加巷战时有过不小心将两位平民小孩误杀的经历。正因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而陷入创伤性叙事闭锁状态中,自己不愿与妻子讲,但内心里一直认定是自己亲手杀死两位手无寸铁的无辜孩童的凶手,不能原谅自己的犯罪行为。笔者鼓励朋友丈夫将自己的经历反复讲述出来,细节越多越好,有针对性地推荐了几本疗愈战争创伤的书籍给他阅读。几个月后,朋友打来越洋电话,说丈夫已经好多了,现在找到了一份银行安保工作,生活也回到正常状态。事实上,他讲述生命故事的过程是他将过去“杀人犯”经历划上句号的过程。其最终从创伤闭锁中走出来。
“创设新的故事空间”对于叙事闭锁者突破闭锁状态非常重要。在叙事生命健康学语境下,朋友丈夫正是将过去陈旧的故事——索马里的战争创伤“倾吐倾诉”出去(有话要讲,有故事要诉说,有眼泪要流),然后接纳了孩童已经死亡的事实,创设出新的人生故事情节——为索马里人民的自由与民主而战,积极投入眼前生活,为夫妇双方以后有稳定的居所和体面的生活而努力打拼,最终从创伤型叙事闭锁的状态中走出来。
我们常说,创伤在哪里,叙事就要在哪里。创伤是不可理解的,但却是可传递的,叙事仍要承担“传递的行动”[14]。通过聆听创伤型闭锁者的故事并予以关注和回应,能帮助主体化解“还没化解的情绪冲突”,同时能让主体将自己的创伤与他人的创伤连接起来,融入一个更大的故事里。创伤叙事变成文学创造的行动。叙事的重点并不在于内容,而是这个传递的动作本身。叙事素养高的人比较容易通过反思与想象将个人叙事与更大的叙事连接起来,顺利走出闭锁,而叙事素养低的则需要其他人的叙事干预给予走出闭锁所需要的能量。
2.3 疑虑型叙事闭锁
疑虑型叙事闭锁指的是主体在成长过程中突然因某个事件而变得疑心重重,陷入对自己健康状态或安全状态等的深深忧虑当中,失去安全感,导致心身严重受损的状态。突发的疑虑感纠缠不断,变成阻碍日常生活和个体成长的笼子,无法摆脱疑虑,推动生命叙事进程正常向前发展。如果不调动内在资源对叙事身份进行调整或者不经他人进行叙事干预,疑虑型叙事主体一般很难主动走出闭锁。
据说,明朝有一位脾膈病患者,四处求医,均未见效。后来求诊名医吴球。吴球详细问病情及患者最近忧心疑虑的事情之后,断定他的病是因疑心累及身体导致的。原来患者到女婿家做客,喝得酩酊大醉。半夜口渴难忍,朦胧中看见一个盛满水的石槽,便扒在水槽边,喝了一碗多积水。天明起床一看,石槽中全是红色小虫,心中甚感惊惧,从此感觉肚子里有小虫蠕动。
吴球找来红线,剪成小段,弯弯曲曲就像小红虫,又用巴豆同米饭一齐捣烂,掺入红线,混和均匀,制成小药丸,嘱咐患者在暗屋里服下。同时准备好便盆,里面放上清水。不大一会,患者腹泻,红线就像小红虫,在便盆里飘荡。患者亲眼看到红虫已死,疑虑顿时消除,名医吴球巧妙地治好了患者由疑虑而生的脾膈病,也使患者从疑虑型叙事闭锁状态中走出来。
成语“杯弓蛇影”的故事也很好地诠释了疑虑型叙事闭锁这个概念。对于疑虑型叙事闭锁者而言,调动内心资源主动脱离叙事闭锁状态不容易,因而,针对在对其新近发展出来的疑虑事件进行深入了解,并进行积极的叙事干预变得非常重要。
2.4 老年型叙事闭锁
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生的必经路程,每一阶段充满挣扎与努力。老年型叙事闭锁是指老年生命叙事者自认为已进入“生命叙事的尾声阶段”或人生戏剧帷幕落下的阶段,所有重要的人生事件已经发生,不再期待有新的叙事进程出现,即使有一些变化也只是之前的叙事进程旁枝末节的衍生[5]190。从这句话中,笔者注意到的是,老年型叙事闭锁者并非生命进程真的停滞,真的不再有活力和意义,而是自我设定处于这个状态,这种设定影响了他/她对人生意义的阐释。叙事闭锁直接导致构成人类存在意义的基础出现断裂。
人生到了老年期或生命末期,也就进入了艾利克森(Erik Erikson)提出的,以统合连贯生命和接受死亡为生活核心的人生第八阶段。老年是最佳的叙事时机,老年人是最佳叙事者[15],如果在这一阶段没有人聆听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的人生得不到统合,会让老年人陷入极大的孤独与恐惧中。
老年型叙事闭锁也一样,叙事老年学也可以帮助闭锁者在真正到达人生终点前活出更精彩的人生。也就是说,无论是处在老年阶段还是处在临终阶段,主体仍然有机会实现成长。
3 叙事闭锁与叙事赋能
叙事闭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叙事素养的缺失,这种缺失可能导致成长性思维的缺失。德韦克在《终身成长》里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成长性思维。成长性思维与固定性思维的最大区别是,成长性思维知道每个人的局限性,所以追求不断成长,面对挑战,突破思维定式,而挑战可以帮助不断成长,倾听和讲述是帮助成长的最好方式,因为不同视角的位置变化思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他人,也更好地理解自己。而固定性思维不愿意倾听不同视角的故事,拒绝变化。
叙事闭锁并不等于绝对的疾病状态,也不是一种疾病诊断,因而本文倡导对叙事闭锁的非病理学理解和去医学化理解。叙事闭锁者可能是暂时的,在自己的内在资源得到调动时,可以依靠自己的叙事赋能摆脱闭锁状态,重新实现生命故事的和谐进程。叙事闭锁者也可能无法主动挣脱叙事闭锁状态,这时,叙事介入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提前的叙事介入也能缩短闭锁期,尽早走出闭锁,重新开放生命进程。一个开放的人生故事能够想象出未来行动的许多不同发展路径,不断驱使个体向未来迈进[16]。
3.1 叙事闭锁与叙事介入
麦克亚当斯在《生命叙事心理学》中提出,透过生命叙事是了解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因为主体在叙说生命故事过程中,很自然地会描述个人生命的成长历程、对生命境遇的认知与反应及其结果。要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帮助主体实现成长或改变,我们不能只借助标准化工具与假设来研究,而是要直接进到他人的经验世界和叙事世界[17]。从新近发生的事件和痼疾式的创伤事件出发建构和重新阐释过去事件这一过程对于发展叙事复元力非常必要。
叙事医学的首倡者卡伦[18]在《叙事医学:尊重患者的故事》中提到一位89岁的非裔美国女性。老人患有高血压、乳腺癌、腰椎管狭窄症等疾病,还伴有失眠和焦虑等症状,是一位看卡伦门诊20年的老患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卡伦引导其讲出一个她保守了近80年的秘密。原来,老妪之前讲述的故事是不可靠的,小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经历是捏造的,真实的故事是她当时被一个白人男性强奸。也就是说,老妪闭锁在这个创伤叙事中近80年,从刚开始的应激性自我保护引发的身体疾病逐渐变成困扰一生的慢性疾病。
当她将故事讲出来,她的焦虑、失眠和心悸等症状完全消失。诉说痛苦,本身似乎就带有疗效,虽然由疾病和心理创伤产生的心身疼痛都带有孤绝、内在的特质,但人们仍然有表达的欲望。卡伦通过让老妪重复讲述幼年时的创伤经验,帮助老妪区分了过去与当下,当人们把创伤的经验化成言语讲述出来时,可以帮助大脑将创伤的经验重新定义为“过去的事”,而不会每次都引发创伤时的感受,将创伤经验言语化,能帮助人们感觉自己“活在当下”。因而,聆听患者描述疼痛和创伤经历,释放这个经验,让这个经验“完成”,确实是一种减轻与疗愈创痛的方法。
最近,笔者所在生命健康叙事分享中心先后来了几位八九岁还尿床的孩子。尿床在现代医疗语境下往往被医学化成为一种疾病,被认为是通过检查、开药、打针能解决的问题。然而,家长带孩子去许多医院,做各种检查,并没查出什么问题。这让家长更加焦虑,更加频繁地去医院,仍然希望能开些药或做些检查来找到问题的源头并解决这个问题。殊不知,这些由非生理性因素引起的尿床往往是在孩子的叙事生态中,孩子与大人之间的叙事关系出了问题,导致在尿床这件事情上家长与孩子都出现叙事闭锁。
在生命健康叙事分享中心,笔者跟孩子和家长进行了交流,听他们讲故事,发现这几个孩子有的生长在单亲家庭,有的与母亲长期分离,或者突然搬到陌生的地方居住,三个孩子都因三四岁后还尿床被父母、爷爷、奶奶打骂过。父母的吵闹或离异、亲人的突然死亡或受伤、母子长时间分离、搬到陌生地方居住、黑夜受到惊吓、家长常对尿床的孩子进行处罚和羞辱,都是造成和加重叙事闭锁状态的原因。孩子的尿床不是生理原因,而是成长中的问题没有被正确面对和接纳,也并非精神疾病,需要进行的就是叙事介入。
笔者根据孩子的不同情况推荐其阅读相关的故事书,也向家长推荐阅读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个关于童年尿床的短篇回忆叙事《如此这般地快乐》(Such,SuchWeretheJoys)。奥威尔在故事中谈道,他刚住校没多久,就频频尿床。后来,校长夫人让人用短鞭打他屁股以示惩罚。奥威尔低声啜泣,瘫软在椅子上。奥威尔说,之后他每次尿床不再因挨揍而落泪,因为“惊骇和羞耻麻醉了我”,直到成人还受到困扰。七八岁还尿床的奥威尔的初始肇因是搬到陌生环境,持续原因是被责罚。
说故事是疗伤止痛的良方。要让旧的故事和让主体处于闭锁状态的故事结束,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故事,在聆听和回应中接纳对方。当孩子处于被接纳的关系中,就可以在自身中找到成长、改变与进行个人发展的能力。对于叙事闭锁者而言,讲述和聆听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在这种主体互相认可、互相回应的生命共同体关系状态下,生命叙事会产生新的方向与动力,突破闭锁,于是生命叙事开始被“重写”。也就是说,在对话与反思中,旧思维被“解构”,新价值被“内化”。
3.2 叙事闭锁与叙事素养
19世纪中期,奥地利的塞麦尔维斯和美国的霍尔姆斯都是著名的病理学家。他们走在时代前列,指出产褥热的接触传染性,并提倡医生进产房前必须要先洗手,不幸的是未被广泛认可和应用。虽然一个多世纪之后,两位医生都被尊崇为“产妇的救星”和“母亲的保护者”,但各自的命运令人唏嘘。两位医生都因提出洗手而受到同时代医学权威的攻击和羞辱。处在职业型叙事闭锁状态中的塞麦尔维斯猛烈回击批评者,称反对者为“杀人犯”,结果被当作精神病打死,终年47岁。
与塞麦尔维斯形成对比的是,在疯狂的抨击和诽谤之下,霍尔姆斯一边潜心临床与医学科研工作,一边进行文学阅读与创作。霍尔姆斯的生命则处于更开放的状态。除了医生职业之外,良好的叙事素养让他充满想象力和阐释力。他提倡文学与医学的结合,诸多文学作品流传于世。他创作的“早餐桌系列”被现代医学教育之父奥斯勒列为年轻医生必读的睡前人文“床头书”。事实证明,霍尔姆斯良好的叙事素养拯救了自己。
在大健康语境下,叙事素养已逐渐成为评价健康领域从业者的一项重要指标[19]。除了进行故事的倾听、讲述、阅读和写作之外,医护人员学会为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创设故事,为他们的人生故事进行叙事干预与赋能,为他们寻找生命意义也非常重要。叙事素养高的人能够和患者一起引出向前、向上的且更厚实的故事。在新故事中,人会活出新的自我形象、新关系的可能性和新的未来。
4 结语
无论是哪种叙事闭锁类型,主体的共同障碍是主体无法掌握自身的生命叙事,尤其是无法形成健康的、动态的叙事身份。叙事身份认同是指主体在自我内化、成长及整合过程中形成的故事,是人们发展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也是个体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具有一定叙事素养的人首先能够处理好主体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继而将这种良好的自我关系投射到其他关系中去。生命叙事是健康人际关系(包括主体与自我的关系、主体与他人的关系、主体与社会的关系等)的“荷尔蒙”,新的生命叙事进程的缺失会导致人际关系进入一种内分泌失调的病态。
本文通过对叙事闭锁进行重新定义和分类,倡导将生命进程看作一个过程而非一成不变的、已经有设定结局的故事。根据护理理论学家华生(Jean Watson)的人文关怀理论,关怀指的是医护人员用心灵去影响患者受创的灵魂,并协助患者自创伤中复原。要用自己的健康生命叙事去影响患者闭锁或受伤的生命叙事,首先就必须聆听患者故事,然后协助其改变对生命叙事的观念。
故事是生命的“展现”,当一个人开始说故事,他的生命就产生流动。当一个人真正智慧地将生命视为一个发展的故事,并且可以从多重观点反映出自我与故事的差距……有智慧的人观看他们自己述说生命的故事、从他人的故事中学习,并且介入、改变他们自己的叙事过程,以便容许新的故事,并将其转译成他们的作品[20],就可以避免叙事闭锁,即使短暂陷入闭锁之中,也能够很快运用自己的叙事素养突围。
叙事稳定性是主体成长的基础,但是叙事开放性是主体成长的动力来源。两者对于和谐健康的生命进程都意义重大。当人处于一种叙事稳定性和叙事开放性的平衡状态之中时,人所经历的就是一种有意义的向前推进的过程。一个人如果将生命看作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则不容易陷入叙事闭锁之中。作为全国第一个生命健康叙事分享中心,笔者希望培养大众的叙事素养,对叙事闭锁者进行叙事干预,为大家创造健康和谐的叙事生态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