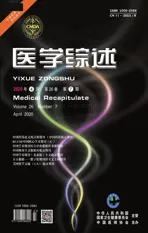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治疗出现分化综合征的诊疗进展
2020-02-16钟琳刘琳周泽平
钟琳,刘琳,周泽平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科,昆明 650101)
分化综合征(differentiation syndrome,DS)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APL)患者经全反式维A酸(all-trans retinoic acid,ATRA)或三氧化二砷(arsenic trioxide,ATO)诱导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危及生命的并发症。DS发病率为2%~31%,不同研究中差异较大[1-2]。导致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有两种,一是无统一DS定义;二是治疗APL时诱导缓解与支持性治疗不同。DS通常发生在APL初始治疗的第10~12天(范围为2~46 d),发病高峰期为ATRA使用后第1周及第3周[1]。DS的主要症状有白细胞增加、发热、肌肉骨骼疼痛、呼吸窘迫、肺间质浸润、胸腔积液、心包积液、头痛、体重增加、低血压、急性肾衰竭、肝毒性等。发热和呼吸窘迫一般在80%以上的患者中出现,而肺部浸润、胸膜或心包浸润及肾衰竭则分别约占50%、30%和10%[1]。DS相关病死率高,Montesinos等[3]报道,轻度DS对APL患者病死率影响较小,而重度DS,尤其是早期重度DS,病死率较高,DS患者易进展为严重出血导致死亡,其中重度DS较轻度DS出血所致病死率更高。DS的血栓发生率、凝血功能障碍、出血风险、血浆、血小板和红细胞输注率、3~4级肝毒性损害均增加[3-4]。由于DS发展迅速、影响生存质量、危及生命、增加病死率,因此早期预测、及时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尤为重要。现就APL出现DS的诊疗进展予以综述。
1 发病机制
研究DS发病机制可为DS治疗方向提供指导。DS发生机制较复杂,目前尚不明确,比较明确的是DS发生与过度炎症反应有关。ATRA能激活炎症瀑布机制,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上皮损伤致毛细血管渗漏[5-6]、微循环障碍及组织器官浸润[7],主要与趋化因子、黏附分子、细胞因子分泌增多密切相关。ATRA可显著增加肺泡上皮细胞分泌趋化因子,包括CC趋化因子配体[chemokine(C-C motif) ligand,CCL]2和CXC趋化因子配体[chemokine(C-X-C motif) ligand,CXCL]8,增加APL分化细胞肺部浸润能力;此外,ATRA可增加APL细胞分泌趋化因子,包括CCL1(I-309)、CCL2、CCL3、CCl4、CCL7、CCL20、CCL22、CCL24及CXCL8,促进白血病细胞从血液移行至组织中,加重组织炎症反应[2]。ATRA或ATO分泌的黏附分子整合素(CD11a/CD18)及细胞间黏附分子(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ICAM)-1(CD54)能介导白血病细胞黏附于肺毛细血管,使大量表达黏附分子的白血病细胞滞留在肺循环中,导致严重的通气功能障碍甚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8-9]。ATRA还可上调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IL-β、IL-6以及IL-8,上述细胞因子可使白细胞从血液中渗出,迁移至器官组织,进一步加重炎症反应[8]。
2 预测因素
探究DS发生预测因素有利于及早发现DS。对于DS发生的因素,多项研究对年龄、性别、发热、血小板等指标进行分析[3-4,10-11],但尚无明确预测因素。有研究称,白细胞增加是DS发生的高危因素,使DS的患病率增加,但白细胞增加界值定义尚不明确[3,10-12]。有研究报道,高体质指数患者患DS风险更高[13]。瘦素由骨髓中脂肪细胞分泌,瘦素受体由APL细胞表达,不表达于正常中性粒细胞,高体质指数的APL患者脂肪组织分泌瘦素及APL细胞分泌瘦素受体较体质指数正常者增加,瘦素受体可在ATRA作用下分泌产生更多细胞因子,细胞因子作用于白血病细胞,导致白血病细胞增多,浸润肺部[11]。东部合作肿瘤组通过多元分析指出,白蛋白<3.5 mg/dL(350 g/L)被认为是DS病死率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4]。Montesinos等[3]报道,重度DS的预测因素包括白细胞计数> 50×109/L、血肌酐异常、Fms样酪氨酸激酶3-内部串联重复序列突变、S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维A酸受体α,其中白细胞计数> 50×109/L、血肌酐异常可作为预测重度DS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轻度DS预测因素包括白细胞计数>10×109/L,乳酸脱氢酶高于正常值上限,外周血原始细胞>70%,其中白细胞计数>10×109/L可作为预测轻度DS的独立危险因素。Elemam和Abdelmoety[14]研究显示,DS的发生与CD11b、CD11c、CD13、CD14、CD33、CD34及CD45无明显关系。有学者称,经典型APL较微晶体型APL(M3V)DS发病率更高[15];而Tallman等[16]在大样本数据中观察到APL分型对DS发病率的影响无明显差别。Dore等[17]报道,ICAM-1上第469号密码子为AA基因型患者,DS发病率高,考虑与黏附分子基因突变使DS易感性增加有关。
3 DS的诊断
目前DS尚缺乏统一诊断标准,多根据Frankel等[18]对DS的定义,即出现以下症状与体征:呼吸窘迫、不明原因发热、体重增加>5 kg,胸腔积液、心包积液、低血压及急性肾衰竭等诊断为DS,若能用临床并发症来解释的肺出血、感染性休克、肺炎、心力衰竭症状,不能归为DS。有学者根据出现的上述症状与体征,又进一步将DS分为轻度和重度,若出现4种及以上症状或体征归为重度DS,若出现2~3种症状或体征归为轻度DS[3]。由于DS发展迅速,病死率高,早期症状不典型,故早期发现尤为重要。DS的症状与体征很难与菌血症、败血症、肺出血、充血性心力衰竭、高白细胞性AML引起的肺损害、ATRA诱导缓解APL期间出现的高白细胞综合征相鉴别,因此,DS极易误诊、漏诊。为早期发现DS,需同时结合发病时间、临床特征、影像学等表现进行综合性分析。
DS发病时间存在2个高峰,多数患者出现在ATRA使用第1周及第3周,极少部分为第1周及第4周,早期重度DS(使用ATRA少于3周)主要表现为肺部浸润、体重增加、高机械通气率及高诱导缓解率;晚期重度DS(使用ATRA大于3周)主要表现为低血压、不明原因发热、肾衰竭[7]。而菌血症、败血症、肺出血、充血性心力衰竭、高白细胞性AML引起的肺损害、APL诱导出现高白细胞综合征等发病时间及临床特点与DS不同。
有学者称,胸部X线、胸部CT、肺部超声可第一时间发现DS,对早期发现DS有较大意义[19]。胸部X线、胸部CT对发现DS的敏感性欠佳,而肺部超声敏感性及阴性预测值较高,胸部X线片可表现为心胸比增大、血管径增宽、间质水肿伴支气管周围迂曲、Kerley线;胸部CT可表现为肺间质病变、心包积液、胸腔积液、肺部感染[20]。肺部超声可见肺水肿中含液腔隙与含气肺泡所形成的彗星尾征[21]。
侵袭性操作(如支气管镜检、肺活检)虽可用于DS诊断,但一般不建议使用,因有加重患者病情的风险。侵袭性操作仅用于临床治疗不满意、需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支气管肺泡灌洗的患者,使用支气管镜检查,可用于排除肺出血、肺部感染等情况,以协助DS的诊疗[19]。
诊断DS时需与其他疾病相鉴别。使用超声心动图、微生物学检查有助于鉴别感染、左心衰竭、肺出血等疾病。然而,由于临床的复杂性,可出现上述疾病同时合并DS的可能性。因此,经验性及预防性治疗时,需警惕此种情况的发生,用药以能覆盖包括DS在内为佳。
4 DS的预防及治疗
4.1预防 是否预防性使用类固醇激素防止DS,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项研究,但目前仍存较大争议,尚无确切证据表明预防性使用类固醇激素可防止DS发生[22-23]。预防性用药主要包括泼尼松及地塞米松,于整个治疗过程中使用或在一定时间内使用5~15 d[22]。De la Serna等[4]对LPA96组与LPA99组患者进行分析,LPA96组中白细胞计数>5×109/L APL患者预防性使用地塞米松(10 mg,每12小时一次,连续7 d);LPA99组中所有APL患者预防性使用泼尼松[0.5 mg/(kg· d),连续15 d],结果显示,两组轻度DS病死率相近,而LPA99组重度DS发生率更低。Sanz等[22]对LPA2005组进行研究,白细胞计数>5×109/L的APL患者,在ATRA使用前或使用中预防性使用小剂量地塞米松[2.5 mg/(m2·12 h),连续15 d],进行中期分析发现,可减少约1%的DS相关病死率。De la Serna等[4]回顾性研究发现,在诱导治疗的前15 d内使用泼尼松虽无法降低DS相关病死率,但可显著降低重度DS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除激素可用于预防DS外,Kojima等[24]对14例伴凝血功能异常的APL患者使用重组人可溶性血栓调节素,结果显示无一例发生DS,重组人可溶性血栓调节素能够抑制维A酸诱导的p38和钙黏蛋白磷酸化,降低EA.hy926细胞中ICAM-1表达及血管通透性,有效预防DS的发生。
4.2治疗 DS临床表现不典型,发病迅速,因此,当出现容量负荷过重、肺功能或肾功能降低、白细胞增加、发热等情况时,需进行严密监测,警惕DS的发生。若诊断为DS,应立即予积极治疗,降低APL患者病死率。目前使用类固醇激素已被认为是治疗DS的标准方案。研究表明,首次出现DS相关症状及体征时,早期使用大剂量地塞米松可使DS相关病死率从30%降低至5%,甚至更低[3,22]。类固醇激素可以减少肺泡上皮细胞产生趋化因子,减少APL细胞移行至肺部,降低视黄醇结合蛋白Ⅰ和视黄酸受体信使RNA的浓度,以及炎症细胞因子(IL-6、IL-8、C反应蛋白)、中性粒细胞及ICAM-1(CD54)水平,从而有效抑制DS的炎症反应过程;同时,类固醇激素可增加全身血管阻力及平均动脉压,减小肾小球渗透压,稳定血流动力学,从而减少低血压、肾衰竭的发生[25]。推荐尽早静脉滴注地塞米松(每次10 mg,每日2次),直至症状体征完全缓解。短期使用激素存在一定不良反应,包括暂时性血糖升高、高血压、消化性溃疡、感染风险增高等[19]。因此,在使用激素治疗时,需针对上述不良反应予以预防性治疗。停止使用激素后,一部分患者有出现DS复发的可能[15]。当DS复发时,可再次使用地塞米松直至第二次缓解。有报道称,地塞米松对早期DS有治疗效果,而DS发展至全盛期时,治疗效果欠佳,DS发展至全盛期时,APL细胞侵犯靶器官,APL分化细胞产生大量趋化因子,导致组织器官进行性炎症反应,地塞米松虽然可以阻止肺泡上皮细胞产生趋化因子,但无法阻断APL分化细胞产生趋化因子,因此,地塞米松无法逆转全盛期DS的发展[2]。对于全盛期DS,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早期发现,及时治疗,避免DS发展至全盛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4.3是否停用ATRA或ATO 发生DS时是否停用ATRA或ATO目前仍存在争议。目前普遍认为,对于轻度DS患者,静脉给予地塞米松治疗DS时,继续使用ATRA或ATO仍然安全;当DS迅速进展或出现全身症状、严重器官功能衰竭(如急进性肾衰竭、重度呼吸循环衰竭),则需立即暂停使用ATRA或ATO,直至DS症状、体征完全缓解,此后可再次使用ATRA或ATO[26]。而重新使用ATRA或ATO时,是继续原剂量还是原剂量基础上减量尚不明确[7]。
4.4使用化疗药物 ATRA联合化疗可有效降低DS发生率及严重程度[27-28]。近半数APL患者在接受ATO单用方案时,可出现白细胞增多症,发生于初始治疗20 d左右,白细胞增多可加重APL疾病进展,加大DS患病风险[7]。基于此现象,需及时加用化疗药物降低白细胞治疗,药物包括羟基脲、蒽环类等。然而,ATO治疗中加用化疗药降低白细胞对DS相关病死率的影响仍不确切。相较之下,高白细胞APL使用ATRA治疗,如若联合化疗药物治疗,能够在改善凝血功能障碍的同时降低DS患病风险[7]。有学者对初治低白细胞(白细胞计数<5×109/L)APL患者单独应用ATRA治疗与ATRA联合化疗进行比较,发现两者DS的发生率及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7]。因此,为避免DS的发生,对低白细胞及高白细胞APL患者的早期治疗,建议联合化疗药物。
4.5支持性治疗 支持性治疗在DS的治疗中同样重要。PETHEMA(Programa Espaol de Tratamientos en Hematología)研究组指出,APL出现体液潴留时,需使用呋塞米利尿缓解症状[7]。一些难治性肾衰竭及体液潴留需肾脏替代治疗,诱导缓解中常出现凝血功能障碍,因此需输注较多冷沉淀、纤维蛋白原、凝血因子等血液制品改善凝血功能障碍。一些对高流量吸氧无效患者往往需机械通气治疗。除此之外,很多患者在血管渗漏综合征的基础上可发展为肾前性肾衰竭及低血压甚至休克,需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稳定血流动力学。上述支持治疗在重度DS患者中常较轻度DS需求性更高。大多数患者出现DS症状及体征时,及时使用地塞米松及支持性治疗可使DS得到有效控制。
4.6新型药物 结合DS发病机制,国内外学者对DS新型药物的研究主要致力于阻断趋化因子、细胞因子、黏附因子,减轻炎症反应,改善微循环障碍及组织器官浸润。雷公藤红素可有效抑制ICAM-1、肿瘤坏死因子-α及IL-1β,从而减轻炎症因子造成肺部浸润,且对白血病细胞分化无明显影响,其过程与减少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1/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活化有关[29]。西维来司钠是一种中性粒细胞蛋白酶抑制剂,已被证实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动物模型的有效抑制剂,可通过抑制中性粒细胞蛋白酶,减轻肺部浸润及肺泡上皮细胞损伤,同时部分改善出血倾向[30]。高迁移率族蛋白B1是一种DNA结合蛋白,可作为细胞因子参与炎症反应。在DS发展中,高迁移率族蛋白B1可增加ICAM-1表达,增加白细胞从血液移行至组织过程中内皮细胞与细胞外基质的相互作用,从而促进DS发生;而高迁移率族蛋白B1抗体能减少小鼠体内ICAM-1表达,降低DS相关病死率,因此,未来高迁移率族蛋白B1靶向药或可有效抑制DS的发生[31]。然而,上述药物目前由于临床研究缺乏大量样本,其安全性及有效性需进一步研究。
5 小 结
随着ATRA和ATO的运用,APL的治疗理念有了根本性变化。但是这一治疗带来了另一个新的问题——DS。DS发病率高、诊断困难,同时进展迅速、危及生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至关重要。目前DS尚无明确预测因子,诊断DS需综合发病时间、临床特征及影像学检查。一旦诊断为DS,需尽快使用类固醇激素治疗。类固醇激素治疗时,轻度DS可继续使用ATRA,重度DS需停用ATRA,直至DS症状体征缓解后方可再次使用ATRA。治疗期间支持性治疗需贯穿其中。新型药物或可降低DS病死率及严重程度,但目前安全性及有效性仍在研究中。未来仍需进一步探讨如何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有效干预,从而降低APL患者发病率及病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