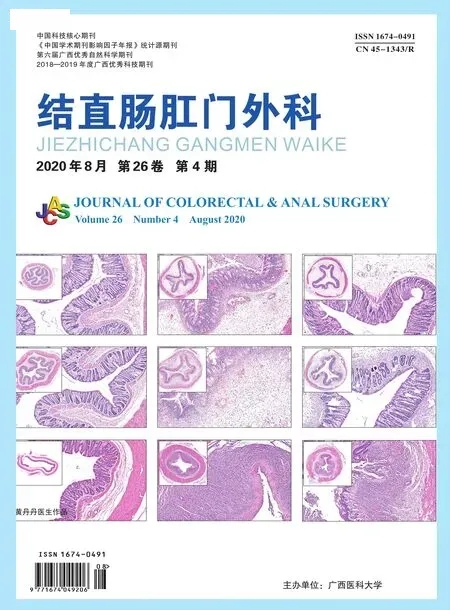肠道菌群与常见慢性肝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2020-02-13陈晖娟龚慧高江苓刘忠于
陈晖娟,龚慧,高江苓,刘忠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科研部/全军肛肠外科研究所/全军重点实验室 河南洛阳471000
1 概述
肠道菌群是维持人体生命健康所必需的重要环境因素。人体肠道内携带约1.5公斤的共生细菌,超过数千种不同的菌群,主要包括细菌、古细菌、病毒和真菌[1-2]。肠道菌群可为宿主健康提供多种益处,包括维持肠道黏膜屏障完整性、胆汁酸代谢、营养获取和防止病原体入侵[3]。由于肠道微生物种群是动态变化的,所以在不同的营养、免疫和环境条件下,其组成和分布也会发生变化。肠道菌群失调可能会对宿主的生理活动产生显著的影响,甚至导致一系列疾病的发生[4]。本文仅针对肠道菌群与常见慢性肝病的关系展开简要论述。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实质性器官,和肠道属于胚胎同源,在解剖学和功能上均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由门静脉和肝动脉共同进行血液供应。肝门静脉主要负责将肠道血液汇合并供应至肝脏,这使得肠道与肝脏之间形成紧密联系,进而形成肠—肝轴[5-6]。肠—肝轴是胃肠道与肝脏之间在解剖学和功能上相互作用的体现,肠道菌群和肝脏之间的共生关系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网络来调节和稳定,这些相互作用网络包括它们之间的代谢、免疫和神经内分泌干扰[7]。诸多证据显示各类肝病患者大多存在肠道菌群失调问题,并且菌群失调程度与肝病严重程度呈密切相关性[8-9]。近些年对肠道菌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肝病学、胃肠病学、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以及其他相关的生命科学领域,其中,在肝病学领域的研究排名第一,由此说明肠道菌群与肝病密切相关,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4]。
2 肠道菌群与常见慢性肝病的关系
2.1 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
ALD是全球与肝有关的死亡病例的常见原因,其发病初期的临床症状并不明显,肝功能生化指标基本正常或轻度异常,影像学仅显示为简单的脂肪变性,但可进一步发展为纤维化、肝硬化或者急性酒精性脂肪性肝炎,死亡率很高[8,10]。尽管近些年对ALD发病机制的认识有所提高,但治疗方法仍然很少。
ALD的发病过程是多层面的,涉及酒精对肝细胞的直接毒性作用(例如,活性氧的出现),也包括通过病原体相关分子(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PAMPs)如脂多糖间接引发肠道产生炎症信号因子。这些PAMPs能有效激活肝巨噬细胞(Kupffer细胞),并促进由白介素1β(interleukin-1beta,IL-1β),白介素8(IL-8)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驱动的炎症反应,从而导致肝脏功能异常,造成肝损伤[11-12]。另有实验证实了类似情况,ALD患者内毒素血症与肝损伤程度之间密切相关[13]。特别是当人体长期摄入酒精后,酒精和相关代谢产物造成肠道菌群失调,诱导肝脏细胞产生促炎症因子,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肠道内毒素进入血液,并启动细胞下游免疫反应,进一步加重炎症反应,导致病情的恶化[10,14]。
随着ALD的进一步发展,肠道微生物多样性随之降低,菌群相似性发生改变。有研究者通过实验证实ALD患者肠道内存在菌群失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益生菌含量减少,而肠球菌、粪肠球菌和大肠埃希杆菌等有害菌含量增加。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肠道内脆弱拟杆菌和双歧杆菌减少最显著[11]。研究者发现ALD患者普遍存在肝脏部分功能降低,血液中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及总胆红素含量升高;而患者肠道中双歧杆菌数量与血液中ALT和AST的含量呈负相关性[8]。另有类似报道发现ALD患者粪便中双歧杆菌和乳酸菌数量明显减少,口服益生菌后能改善肠道菌群数量,维持菌群平衡并可以降低肝酶水平,改善肝功能[15]。Grander等[10]研究发现酒精性脂肪肝患者中肠道阿克曼菌的丰度降低,并且与肝病的严重程度间接相关。在实验环境中,通过口服阿克曼菌能恢复因酒精而耗竭的阿克曼菌的肠道丰度,改善肠道渗透性,增加黏液厚度,显著减轻ALD患者肝脏损伤、肝脂肪变性等症状。有研究者[16]采用粪便菌群移植法将酒精抗性小鼠(耐药供体)的粪便移植到酒精敏感但不耐酒精的敏感受体小鼠体内,证实移植后敏感受体小鼠菌群与耐药供体小鼠肠道菌群非常接近,移植后敏感受体小鼠肝脏病变情况得到改善,并能逐步恢复肠道内稳态。
总之,ALD患者普遍存在肠道菌群紊乱、有益菌数量减少的现象,及时调节肠道菌群,如补充益生菌、进行粪便菌群移植等能有效预防和缓解酒精诱导的脂肪变性和肝脏炎症等。
2.2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
NAFLD是脂肪和葡萄糖代谢紊乱的肝脏表现,常与肥胖、血脂异常和胰岛素抵抗有关,可以从单纯脂肪变性发展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甚至肝硬化等肝脏疾病[4,12]。近些年,NAFLD已发展为全世界最常见的肝脏疾病,据估计全球患病率为25%~45%[17]。值得注意的是,NASH现在是肝脏移植的第二大病因,并且一定比例的NAFLD患者可能会发展为肝细胞癌[18]。
NAFLD是一种由遗传倾向、代谢功能、炎症、肠道微生物群和环境等多因素引起的综合症[12]。肠道菌群在NAFLD发生中的可能作用如下[4]:(1)微生物失调导致肠道产生对肝脏有毒的乙醇量增加,通过破坏肠道紧密连接致使通透性增加。(2)肠源性病原体相关分子可以与肝脏中特定的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s)结合,激活促炎信号通路,进一步引发肝脏炎症和纤维化。(3)肠道菌群可水解胆碱,但胆碱代谢增加可能会导致胆碱缺乏,从而阻止极低密度脂蛋白(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VLDL)的排泄并引发甘油三酸酯在肝脏中积累。(4)肠道菌群的改变可能会使血管生成素样蛋白 4(angiopoietin-like protein 4,ANGPTL4)的分泌减少,从而抑制脂质B氧化并增加肝脏甘油三酯的储存。ANGPTL4是一种内源性脂蛋白脂肪酶的特异性抑制剂,此酶可将VLDL颗粒中的甘油三酯释放到肝脏。(5)过量的短链脂肪酸是肝脏糖异生和脂肪合成的底物,通过抑制单磷酸腺苷激活的蛋白激酶的活性来促进肝游离脂肪酸的积累。
由于NAFLD的高发病率和高致病风险,现在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但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有研究报道[19],奥贝胆酸治疗可明显改善高脂饮食所致的肥胖、循环代谢紊乱、肝脏炎症和纤维化、肠屏障损害。去除正常共生菌可减弱奥贝胆酸的作用。用奥贝胆酸处理后,肠道微生物结构发生改变,布劳特氏菌属的丰度显著增加。奥贝胆酸治疗后,高脂饮食引起的肝内牛磺酸结合的胆汁酸浓度降低。总之,实验数据表明,奥贝胆酸通过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特别是增加布劳特氏菌属的丰度,对NAFLD具有保护作用。肠道菌群分析结果表明[20],新型益生菌副干酪乳杆菌Jlus66可以通过增加革兰氏阳性菌群(如厚壁菌)的数量和减少革兰氏阴性菌群(如拟杆菌,变形杆菌和梭菌)的含量来改善肠道菌群结构,然后降低血清中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的浓度。因此研究者认为,Jlus66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并随后减轻氧化应激和炎症来改善NAFLD。Eslamparast等[21]发现在NAFLD治疗中,补充合生元加生活方式改变优于单纯生活方式改变。Mofidi等[22]也报道了相似的成果,实验证据表明,补充含7种益生菌和低聚果糖的合生元可降低炎症指数,改善正常和低体重指数NAFLD患者的主要症状。诸多证据表明,靶向肠—肝轴可能是预防或治疗NAFLD的新途径,包括使用益生菌、益生元和合生元治疗,针对胆汁酸相关信号通路治疗,利用吸附剂和粪便菌群移植治疗。
2.3 胆汁淤积性肝病(primary biliary c holangitis,PBC)
PBC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胆汁形成、分泌以及排泄障碍,导致胆汁在肝脏过度淤积的一类慢性自身免疫性肝病[23]。肠道菌群通过调节新陈代谢、免疫反应和胆汁酸的代谢,在PBC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同时,PBC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丰度及功能,间接影响胆汁酸的合成和代谢[24]。有报道[25]称在PBC患者中,肠道内微生物多样性显著降低,其中有4个菌属(萨特氏菌、拟杆菌、粪杆菌、颤螺旋菌)丰度减少,8个菌属(韦永氏球菌、克雷伯氏菌、链球菌、假单胞菌、嗜血杆菌、梭状芽孢杆菌、乳酸菌、肠杆菌科)丰度增加,这些与PBC密切相关。有趣的是发现PBC患者肠道中上皮细胞的细菌侵袭能力增加,与肠杆菌科细菌的丰度高度相关。
另有研究者[26]发现PBC患儿粪便中大肠杆菌丰度明显上升,而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丰度显著下降。针对婴儿PBC患者采用益生菌辅助治疗,能够调节患儿肠道菌群紊乱,改善机体血氨水平,抑制炎症反应,并降低TNF-α含量,显著提高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27]。Tang等[25]研究发现用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 acid,UDCA)治疗PBC患者6个月后,与PBC相关的6个菌属的丰度发生了逆转,病情得以部分缓解,证实UDCA可以逆转胆管细胞衰老,改善患者肝功能的生化指标,抑制病情进展,提高生存率。诸多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在引发PBC和影响PBC进程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对胆管及肝脏损伤有保护作用,提示及时改善或调整肠道菌群可能有助于控制PBC的进程[23,27]。
2.4 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
成年人在经历急性感染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后发病,一般而言,大多数人都能通过自身免疫系统清除病毒。但也有部分患者感染HBV后转为慢性肝炎,这种情况更常见于婴幼儿时期[28]。有研究证实[29],慢性HBV感染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与病毒数量、毒性等相关,还与患者肠道菌群失调密切相关,肠道菌群通过影响肝脏的免疫反应,释放各类细胞因子,进一步加重肝细胞损伤。有报道[30]称CHB患者粪便中菌群种类和丰度与正常健康人相比均有变化,存在不同程度的肠道菌群失调现象,包括肠杆菌、梭菌属、普雷沃氏菌等在内的5种菌群丰度明显增加,而拟杆菌属、瘤胃球菌属和乳酸杆菌的丰度则明显减少。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还证实CHB患者肠道内9种细菌中只有肠球菌与白细胞介素17A(interleukin-17A,IL-17A,一种新型促炎性细胞因子,可促进多种炎症因子的表达)的水平呈正相关性。由此认为CHB的发病原因可能为过量的肠球菌与IL-17A协同作用,加重肝脏炎症反应和受损程度,呈“恶性循环”状态[31]。
目前研究认为[32],人类HBV感染的特点是病毒清除与感染年龄强相关,其具体原因还不明确,可能是由于婴幼儿免疫系统不成熟和肠道菌群不稳定。Chou等[32]通过小鼠模型证实,具有TLR4突变的幼鼠具有快速清除HBV的能力,提示幼鼠在肠道菌群建立前,存在一条TLR4依赖的HBV免疫耐受途径;而成年小鼠成熟的肠道菌群会刺激肝脏细胞免疫,导致HBV快速清除。由此指出,肠道菌群可能影响HBV的急性或慢性进程。总之,肠道菌群变化对CHB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作用,肠道菌群异常还可导致HBV感染由急性转变成慢性。
2.5 肝硬化
肝硬化是常见的由各种病因引起的慢性、进行性肝病,本质是弥漫性肝损害,多发生于肝炎之后。早期表现为肝纤维化,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导致肝硬化或终末期肝病,最终导致肝脏丧失代谢功能[8,33]。肝硬化患者免疫功能下降、肠蠕动减弱,胆汁分泌量明显减少,以及各种原因导致肠壁充血、水肿,使得肠道菌群生存环境受损,导致肠道菌群紊乱[34]。
有研究者证实,相比健康人群,肝硬化患者的亚基因组分析显示肠道菌群中类杆菌和硬壁菌水平降低,韦荣球菌属和链球菌属水平升高。而韦荣球菌属和链球菌属是口腔中的常见菌,这意味着肠道菌群中口腔菌群数量的增加可能与肝硬化的发生和进展有关[35-36]。有研究团队[35]收集181个肝硬化患者肠道微生物样本,建立了世界上首个肝硬化患者肠道微生物基因集,结合定量宏基因组学方法,揭示了肝硬化患者肠道菌群的重大变化,主要是由于口腔细菌对肠道的大量侵袭。肝硬化的严重程度与入侵菌种的丰富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表明,它们可能在病理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
Chen等[37]应用16S rDNA测序等方法证实,肝硬化患者肠道菌群紊乱明显,其中肠球菌属与链球菌属丰度显著升高;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特定的菌群变化与TNF-α、白介素-6等炎性细胞因子相关,提示肠道菌群变化可能对肝硬化患者的预后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唐源淋等[38]证实肠杆菌丰度与肝硬化分级及不良预后呈正相关性,而梭菌和乳酸杆菌丰度与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呈负相关性。进一步研究肠道菌群失调与肝硬化并发症的关系,结果显示常见并发症中自发性腹膜炎与肠道微生物的相关性最高,其发生率与肠杆菌丰度呈正相关,与梭菌和乳酸杆菌丰度呈负相关;而乳酸杆菌与腹膜炎、腹水、肝性脑病和肝癌等肝硬化并发症的发生率均呈负相关性[38]。由于大肠杆菌是自发性腹膜炎的主要病原菌,分析肠道细菌是该并发症的主要感染源,其发生机制可能为肠道细菌移位[39-40]。诸多研究结果表明,粪便、结肠黏膜和唾液中微生物的相对丰度和功能变化等对肝硬化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和预后有不同程度的影响[9,41]。
3 展望
随着微生物宏基因组和代谢组学的不断发展,肠道菌群种类和功能的研究也随之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了肠道微生物在人类健康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肠道菌群有望成为预防和治疗慢性肝脏疾病的新靶点,靶向肠—肝轴的微生态治疗不仅可以作为治疗慢性肝病患者肠道症状的一种辅助手段,也可以通过纠正肠道菌群失调成为有效预防慢性肝病发生和进展的一种预防措施。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未来会有更好地靶向肠道菌群无创治疗肝脏疾病的新疗法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