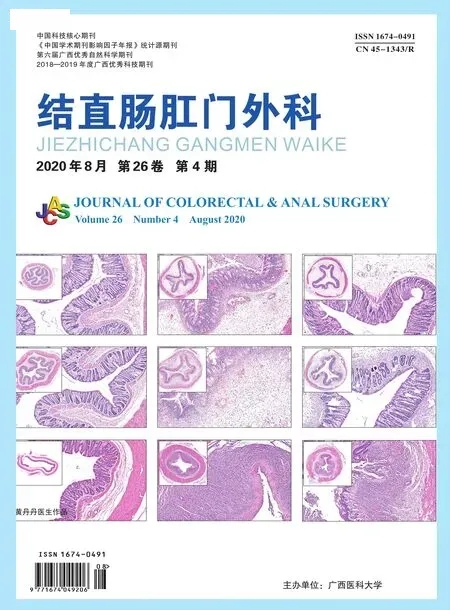肠道菌群与结直肠癌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2020-02-13王晓娜楚治良陈晖娟刘忠于
王晓娜,楚治良,陈晖娟,刘忠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九医院科研部/全军肛肠外科研究所/全军重点实验室 河南洛阳471000
人类微生物群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由细菌、病毒和真菌组成,寄生在皮肤、口腔、肺部、肠道和阴道内。在成年人的结肠和大肠的其他部分中大约藏有1 013多种细菌,微生物群主要包括严格的厌氧菌,如拟杆菌、真细菌、双歧杆菌、融合杆菌、肽链球菌等,同时也包括小部分兼性厌氧菌,如肠球菌、乳酸杆菌、肠杆菌科和链球菌等[1]。肠道菌群在促进食物吸收、宿主抵抗感染、增强肠道免疫系统、调节宿主代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
结直肠癌(CRC)是发达国家的主要健康威胁之一。西方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可能通过代谢和炎症机制参与了结直肠癌的产生与发展。同样,作为关键的代谢和免疫调节剂,肠道菌群也被认为在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和功能改变会导致宿主基因表达、代谢调节以及局部和全身免疫反应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癌症的发展[3]。
1 肠道菌群与大肠癌
肿瘤微环境是一个低氧环境,可促进厌氧和兼性厌氧细菌(如梭菌)的生长。癌组织的血管渗漏可允许细菌进入,而免疫细胞的缺失或低丰度可允许细菌生长[4]。黏膜肿瘤与细菌直接接触,易受微生物的影响。结直肠癌(CRC)因为暴露于肠道大量的细菌之中,其微生物群落被广泛关注并研究。与正常结肠组织相比,肿瘤组织中的梭杆菌门和厚壁菌门有所增加[5],而梭杆菌门、普罗威登斯菌属和放线菌门的分类单元在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之间的丰度发生了变化[6]。尽管尚不清楚核梭状芽胞杆菌是否在肿瘤发展过程中起作用,但有研究发现,其在结肠肿瘤组织中大量富集[7-8]。CRC患者肠道中发现的具核梭杆菌可能起源于口腔,在匹配的肿瘤组织和唾液中发现的细菌株相同[9]。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微卫星不稳定(MSI)状态不同的肿瘤之间,具核梭杆菌的作用有所不同,可能在MSI高表达的肿瘤中发挥免疫抑制作用,而在MSI正常的肿瘤中有促炎作用[10-12]。此外,另一项研究显示,移植了结直肠癌患者新鲜粪便的小鼠体内出现大量的高甲基化基因,而这些基因与结肠黏膜中异常隐窝灶发生率升高显著相关[13]。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肠道微生物与CRC的发生或发展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2 肠道菌群对结直肠癌治疗效果的影响
近年来,几种类型的癌症临床前和少数临床研究显示,肠道细菌在调节宿主对抗肿瘤药物,特别是化疗和免疫治疗反应中起关键作用。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通过调节药物疗效、削弱抗癌作用等方式在肿瘤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14]。
2.1 肠道菌群对化疗效果的影响
肠道菌群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化疗疗效,包括异种代谢、免疫相互作用和改变群落结构[15]。肠道微生物群可以直接改变或代谢某些外来生物,如抗癌药物。这种微生物介导的异种代谢可能与化疗药物毒性增加有关。当药物毒性增加,使用者需减小剂量或者中止用药,导致治疗效果下降。曾有日本学者报道结直肠癌患者发生了因化疗引起的可导致死亡的潜在毒性反应,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涉及拟杆菌属与5-氟尿嘧啶(5-FU)—索利夫定联合疗法[16]。拟杆菌属作为肠道菌群的主要成员,具有高活性、使索利夫定转化为中间体溴乙烯尿嘧啶,从而抑制5-FU的降解并导致其在血液中的积蓄、毒性升高。最近的研究也表明,通过补充营养或益生菌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可以降低小鼠和人类的化疗毒性和副作用[17-19]。还有研究表明,给予肠道菌群失衡的小鼠口服含双歧杆菌的益生菌,可增加PD-L1阻断的抗肿瘤效果,几乎抑制了肿瘤的生长[20]。
2.2 肠道菌群对免疫治疗效果的影响
肠道菌群对免疫治疗的重要作用首先在两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这两项研究揭示了细菌与宿主免疫反应和抗肿瘤活性的关系[21-22]。Paulos等[22]的研究表明,在黑色素瘤小鼠模型中,对小鼠全身放疗后,抗肿瘤CD8+T细胞过继转移的功能显著增强,辐射诱导释放的微生物脂多糖(LPS)通过TLR4通路刺激,激活先天性免疫应答,进而促进抗肿瘤CD8+T细胞释放,而抗生素治疗或LPS(用多粘菌素B处理)则导致抗肿瘤应答降低。Iida等[21]的研究表明在MC38结肠癌和B16黑色素瘤皮下癌鼠模型中,抗生素治疗削弱了IL-10、CpG寡聚脱氧核苷酸(ODN)免疫疗法的功能。抗生素诱导的免疫治疗反应失败是由于肠道菌群负荷减少,导致肿瘤中促炎性细胞因子产生单核细胞减少所致。这些结果表明可以在抗肿瘤免疫治疗策略中加入微生物靶向制剂,以增强疗效。然而,关于其潜在分子机制的更深入研究,可能需要在人源化动物模型或自发肿瘤发生模型中进一步验证。
2.3 肠道菌群对放疗的影响
放射治疗可诱发局部免疫原性效应,如免疫原性肿瘤细胞死亡、激活局部和全身炎症[23]。然而,放疗后的肿瘤反应仍然存在很大的异质性,不同患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肿瘤预后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异质性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最近的数据表明,肿瘤反应可能受到肠道菌群的影响。Cui等[24]研究了小鼠模型昼夜节律对放疗(全身照射)的影响,并将其体内微生物群的组成进行了比较,发现与保持在正常光周期(12 h暗/12 h光)的小鼠相比,以其他光周期(8 h暗/16 h光或16 h光/8 h暗)饲养的小鼠肠道细菌种类和组成发生变化,最终导致宿主的抗辐射性降低。该团队还用经过抗生素处理的小鼠模型研究了肠道菌群与辐射敏感性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MT)可提高辐照动物的存活率[25]。此外,肠道微生物群还可能影响放射毒性。Ferreira等[26]在一项临床研究中发现,在以放疗为主要治疗手段的盆腔癌患者中,肠道菌群组成与放射性肠病密切相关。另一项临床研究表明,盆腔放疗后腹泻患者的厚壁菌门与拟杆菌比值发生显著变化[27]。因此,我们认为肠道菌群可能是通过改变辐射敏感性和辐射毒性调节全身免疫应答。然而,肠道菌群对放疗疗效的直接影响尚未真正得到证实,需要进一步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来证明。
2.4 肠道菌群对手术的影响
减少结直肠手术后并发症的预防策略制定仍是一个挑战。20世纪50年代,Cohn等[28]首次报道了微生物群对吻合口漏发生率的影响,在无血管的结肠吻合动物模型中,肠腔内使用抗生素(特别是在吻合部位)降低了吻合口漏的发生率。此后,有研究调查了口服抗生素制剂在择期结直肠癌手术中的作用,认为口服抗生素制剂在预防大肠直肠癌术后并发症中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29]。最近,Van Praagh等[30]对结直肠吻合口组织样本使用16S MiSeq测序,结果显示,吻合口漏的发展与微生物多样性低、类杆菌科和鞭毛纲科的高丰度以及普氏杆菌和链球菌的低丰度有关。上皮屏障完整性的恢复是结直肠术后吻合口愈合的首要机制,当上皮屏障受损,肠黏膜下层组织层可能由于过度暴露在有害的肠腔内因素中(如细菌)而影响吻合口愈合,导致吻合口漏的发生[31]。上述研究表明,有必要对结直肠术后尤其是在吻合口愈合过程中宿主—微生物菌群相互作用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以鉴定具有术后并发症风险的微生物特征,并针对肠道菌群改变制定有效预防策略。
3 肠道菌群对结直肠癌发展的影响
3.1 肠道菌群产物诱导CRC细胞的抗增殖和凋亡反应
细胞凋亡是CRC肿瘤细胞死亡的基本途径之一。然而,癌细胞的特殊机制之一是对细胞凋亡过程的负调控或抵抗。在肿瘤中,大多数细胞的凋亡控制和生存途径都发生变化。细胞凋亡途径不受控制和死亡抗性是癌细胞的一个标志属性。肠道菌群的特殊群体可生产短链脂肪酸(SCFAs),如醋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除了作为能量来源的主要功能外,SCFAs还被证明是免疫系统、细胞死亡和增殖以及肠道激素生成和脂肪生成的信号分子,在维持上皮组织完整性中起关键作用[32]。丙酸杆菌产生SCFAs,通过诱导细胞死亡来抑制细胞生长[33]。CRC细胞利用糖酵解途径产生能量,该途径在肠道环境中产生大量乳酸,这个过程被称为好氧糖酵解或Warburg效应,它利用增加细胞外的乳酸,导致丙酸杆菌产生高浓度SCFAs,从而在G1期阻断CRC细胞生长。双歧杆菌通过在G0/G1期终止细胞周期和增加碱性磷酸酶活性来抑制CRC癌细胞的生长,影响结直肠癌发展。
3.2 肠道菌群产物保护肠黏膜屏障
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上皮与正常菌群相互协作,阻止致病菌、外来抗原和其他有害物质从肠腔进入体内。黏膜通透性的改变和损伤引起微生物和病原体入侵,是导致消化系统疾病的主要原因[34]。肠黏膜屏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覆盖上皮细胞的黏液层,包括黏液蛋白、糖蛋白和三叶因子。黏液中含有多种黏液素,其中上皮黏液素2(MUC2)由MUC2基因编码,在健康和炎症性肠道中起重要作用。作为肠道菌群的产物,SCFAs不仅可以增加MUC2的表达,还可以增加MUC1、MUC3、MUC4等其他黏液蛋白的表达。一些体外研究表明,SCFAs增强了肠道保护屏障作用[35]。此外,SCFAs也增加了细胞膜的组装和黏膜细胞的迁移,增加健康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对肿瘤侵袭、细胞迁移、转移和炎症有很强的屏障作用。
3.3 肠道菌群抑制致病菌的酶活性
葡萄糖醛酸苷偶联过程对激素的代谢、毒素和致癌物的清除至关重要。肠内的净化阶段,是由细菌酶完成的。肠道菌群失衡导致丰富的β葡萄糖醛酸酶、β葡糖苷酶、偶氮还原酶、硝基还原酶和致癌剂的产生。这些酶会产生有毒代谢物,如芳香胺、转化的次生胆盐、硫化氢、致癌化合物的苷元、乙醛和自由基。在CRC患者中,肠道中的胆固醇和胆汁酸迅速转化为细菌产物,导致正常菌群酶功能受损,产生有害物质。因此,益生菌可通过各种机制降低这些酶的活性,例如乳酸杆菌通过降低β-葡萄糖醛酸酶的活性来抑制细菌酶、降低原代胆汁酸和鼠李糖乳杆菌GG脱氢的能力[36]。口服嗜酸乳杆菌和双歧杆菌3周可以降低粪便中硝基还原酶的活性,保持肠道健康。
4 展望
本文介绍了肠道菌群与结直肠癌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但是目前与此相关的大多数研究还是停留在动物实验方面,临床及人体实验较少,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来验证这些发现从而推动临床制定可行的治疗及预防CRC的策略,同时减轻CRC放疗、化疗等治疗的不良反应,提升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