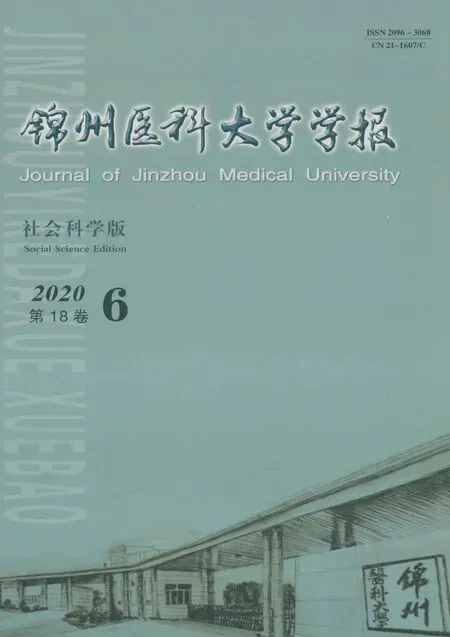汉字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原始密码
2020-02-12葛昭缨
葛昭缨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中华民族在共同生活和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出属于本民族的汉语言文字。汉字作为唯一存留的表意方块字,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象形汉字是对现实的一种简约,一种省略,是一种人的视觉选择表现。”[1]汉字是中华人民通过对世界进行图像性把握而将世界可视化的一种文字符号,是通过直观世界并悬置,过滤无关物后对世界的浓缩的表达。这种视觉选择从深层次来讲是一种价值的选择,汉字对世界的重组与整合的方式也暗含了中华民族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因此,汉字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密码。然而这种民族精神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自古就开始孕育、形成。精神往往需要通过物质载体来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这种刻在中华民族骨子中的基因在自殷商时期前便出现的汉字中得以体现。因此,笔者在孟华创立的汉字符号学基础上,结合现象学的方法分析汉字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将在汉字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称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原始密码,并将其归结为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创造精神以及和谐精神。
一、务实精神
务实精神,即致力于实在的、具体的事物,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孕育出来的。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而在汉字上,体现在与西方文字相比,汉字具有“直面事情本身”的特点。
1.西方文字的特点——“不直面事情本身”。汉字与西方文字分属两种不同的体系。传统的西方哲学具有逻辑化的特点,而西方文字正是这种逻辑化思维下的产物,“不直面事物本身”。一方面,西方文字体系“预设了一个一成不变的本源”[2],它在记录世界的时候,并非直面事物本身,而是用高度逻辑化,抽象化的拉丁字母代替事物。西方文字遵循的是任意性的原则,其能指和其所指没有直接的理据性联系,而只是形状各异的记音符号。并且,西方文字的意义产生于系统的分配,在于每个字母之间形态的差别而非自身形态的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字是该民族看待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是该民族眼中的世界的缩影。因此,西方人用文字再现世界的时候不是以“直面事情本身”的方式,而是将世界化身为一种能指与所指毫无理据性、高度抽象化的符号。另一方面,西方文字在文字形体与意义表达中间有语音作为中介物,这与西方传统哲学偏向于寻找一个“中间物”内在相通,也符合“言本位”的西方传统观念。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影响下,西方人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而文字是第二性的,西方的拼音文字是一种代替性的文字,是言本位的文字。文字只不过是语言的附属物,是对语音链条的摹写,而无自身存在的意义。“字母是音位的替代形式,是对语音的书写,让文字最大限度地体现听觉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1]。在“文字—语音—含义”这一链条上,文字不直接面向所指,而需要通过语音这一中介才能表达意义。因此,西方人用文字表达意义的时候不是以“直面事情本身”的方式,而是将语音作为中介物,并且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言观与传统西方哲学中将思想对象看得比感官对象更重要的观念具有内在契合性。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毕达哥拉斯强调的数是本原为形式普遍和本质真实论建立了原初范式,从这以后,在西方的传统中便有了本质重于现象的观念。
2.汉字的特点——“直面事情本身”。而汉字带有“直面事物本身”的特点。中国人具有很强的“象思维”,而汉字正是这种“象思维”下的产物。一方面,汉字以直观的、形象化的方式记录世界。汉字是通过“六书”构造的,即通过象形、会意、指示、转注、假借、形声的方式将世界压缩为一个个文字符号,而象形是其他构字方式的基础,单体的象形字是所有字的字元,会意字、指示字、转注字、假借字、形声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是通过对物体的大体轮廓的刻画来表现其物,见“日”之形可知其是太阳,见“月”之形可知其是月亮,这是一种通过直观,并记录直观的方式创造文字符号,与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因此,中华民族用文字再现世界的时候采取的是“直面事情本身”的方式,将世界化身为一种形象化,具有肉身理据性的符号。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小学早期仅为文字之学,而将音韵排除在外,可见,中国以字为本位的文化倾向由来已久。而在字本位的中华文化中,汉字形体与意义表达之间不需要中介物,它自身就携带了意义。汉字与汉语不具有同构性,它不是汉语的附属物,不是对汉语语音的摹写,并且在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中,汉字是第一性的,它以自身形体的出场推迟语音的出场,即汉字遵循理据性的原则,能指通过与所指搭建的肉身理据性联系使所指直接出场,对于汉字而言,观其形可明其义,每个字的形态和含义有着不可切断的联系,所以,汉字与含义的关系不需语音这个中介。尽管随着汉字的演变和简化,我们难以在当今使用的简化字中直接看出这种联系,但肉身理据性仍然潜藏在汉字的形体中。因此,中华民族人民用文字表达意义的时候是以“直面事情本身”的方式,这种字本位的文化与中国将视觉感官看得比听觉感官更重要的观念内在契合,体现出中华民族致力于实在的或具体事情的务实精神。
综上所述,汉字这种“直面事情本身”的特点是在与西方文字的对比中彰显的,并且这种“直面事情本身”特点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汉字的形象化,再现世界的直观性以及其直接表意的特点就是一种致力于实在的或具体事情的务实精神的体现。这种在汉字中得以体现的务实精神是中华民族血脉中的基因,它促使中国人更多地思考人伦和“在世间”的哲学,也促使中国人在实用技术发明上自古领先。
二、创造精神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孕育出创造精神,而此处的创造并非指西方思辨式、逻辑式,或是科学范畴下的创造,并非是基于一个观念或原理下的创造,而指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是从源头生发出的生生不息的涌动[3]。在汉字这种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符号中,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可见一斑。
1.删繁就简创设意境的汉字。从汉字的造字角度看,早期汉字是通过立象的方式构成的,这种立象意味着通过删繁就简而创设意境。立象不是指对物象的精准描摹,而是指对物象的简约化和创造性表达,在省略部分内容的同时有所创造,而达到一种非临摹性的象征性,这是一种“对现实的创造性把握”[1]。也就是说,中国的汉字是人们站在人的立场对物象的再现,在这个再现的过程中,汉字并不还原物象的全貌,而是呈现其大致轮廓或者部分一角。“衣”字这个字甲骨文写为:,纳西文写为,相比之下,纳西文是具有临摹性的符号,而甲骨文具有简约性的特征,这种简约性可称为意象性,而正是这种意象性,才显现出汉字构造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以及人在其中对物象加以创造的过程,这就像把写实画与写意画进行对比,从意境和创造性上来说,写意画更胜一筹。
2.运用毛笔书写韵味的汉字。从汉字的构字角度看,汉字的能指中的形式与实体构成了一种张力关系,尤其是毛笔这种特殊的书写工具使其书写出的汉字意蕴无穷,体现出于有限中生无限的创造精神。
符号的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构成内容面,叶尔姆斯夫将每一个面都分为两个层次,即形式与内质。[4]孟华在《文字论》中称其为形式与实体。汉字能指的形式指汉字的形体结构,是汉字的软件系统,包括形体单位、形体结构规则和书体,汉字能指的实体由汉字的书写工具、书写表面决定,是汉字的硬件系统。[1]汉字能指的形式和实体之间具有一种张力关系,用不同的书写工具能够书写出不同的书体,产生不同的书写效果。而使用毛笔可以“让其形体具有‘中性’或类文字性质:它既是笔画又是线条,作为笔画,它构成字形,作为线条,意味线条构成汉字书法,摹状线条构成美术字或文字画。而笔画的自由化就是线条,线条的习语化、程式化、规范化就是笔画。”[5]用毛笔书写出的汉字是笔画与线条的统一体,兼具自由化和规范化的特征。因此,用毛笔书写的汉字能够在汉字书写的规范内充分展现线条的自由,或舒展,或紧收,或上扬,或下抑,即便同一笔画内也有粗细变化而非均质化。人们能在实体与形式的张力中,在笔画与线条的融合中,在笔画与笔画间的舒展变化中品味到一幅字的韵味,能在汉字营造的氛围中流连忘返,汉字的创造性与独特魅力由此而生。
3.具有当场构成性的汉字审美形式。从汉字的审美体现——书法中看,书法具有当场构成性,书法不预设一个不变的本原,而是书写者在不同人生阶段以及不同情景下对主体内在的表达,它的本原不是一种固定不动的对象,而是一种变动不居的,从生活源头生发的,如同溪水一般源源流动的“源泉”。笔者认为,书法的书写是一种胡塞尔意义上的“还原”,很多“过去的东西”被悬置起来,当下的书写即是当下所感,比如颜真卿在早年和晚年的书体中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早年的书法较为秀气柔和,但是晚年的书法却变得浑圆。创作《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时,颜真卿是在一种从容不破的状态下书写,因而笔画醇厚舒缓。而《祭侄文稿》,颜真卿是在家国破灭,痛失亲人的状态下书写,因而全文多次涂抹,枯笔较多,墨色浓重枯涩。正是因为书法的创作具有当场构成的特点,不同派别、不同笔体、不同作品才会异彩纷呈,源源不断的书法作品才能涌现,这是一种原生的创造,是一种于生活源头处的创造。
综上所述,汉字在造字、构字以及审美中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劳动人民用立象的方式创设意境,用毛笔这种汉字能指的代表性实体书写韵味,用当下流露的书法墨迹创造新作,这种创造不预设任何东西,只在生活本源中不断生发意义。因此,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以某一逻辑为基点向外衍生的创造,而是一种更本源处的创造,也是一种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精神。
三、尚和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观念,即便在存有矛盾体的阴阳模式中,中华民族也强调的是阴与阳的相伴相生,强调二者的融合统一而非斗争对立。在汉字中,这种和谐精神体现在以下方面。
1.整体构义的汉字。从汉字的造字角度看,汉字体现了一种注重从宏观上把握整体的和谐精神。上文提及:象形字是汉字的字元。我们通常把汉字称为象形文字,汉字这种象形文字“本于图画”[6],并且演变至今,仍然带有图画的意味,与其他文字相比,具有较强的图像感,比如观察“暮”的古字“莫”,仿佛能看到太阳落到草丛的场景;观察“森”,仿佛能看到树木林立的状态,而这种图像感是从汉字的宏观整体上把握的,单看“莫”或者“森”中的某一个部件,无法领会字的含义,从整体上把握汉字,直观从整体构成的“图像”才能领会其义。汉字的前身是图画,每一幅图、每一个画面都是一个整体,演变为汉字之后仍保留了这种整体性,尽管后人将汉字拆解为偏旁部首,但这些偏旁部首在一个汉字中具有互文性,它们在彼此参照,互相牵连中才能使汉字显现其义。汉字这种从宏观上把握整体的特征强调部件之间的相生相谐,而非原子式个人间的分散,这是一种从宏观上把握整体的和谐精神。
2.穿插避让的汉字。从汉字的构字角度看,汉字强调穿插避让,这种包含了谦让意蕴的穿插避让是一种尚和的体现。上文提到:汉字能指的形式指汉字的形体结构,是汉字的软件系统,包括形体单位、形体结构规则和书体。其中形体结构规则包括笔画与笔顺,部件与部件组合,整字与行款,[1]在汉字的形体结构规则中笔画及部件间的组合方面,穿插避让是一个重要的构字原则。穿插避让是指通过对笔画,部首间的缩短、伸长,穿插、位移等技巧的妥善处理,使汉字各部分之间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它包括避让和穿插两个部分,避让是指笔画的适当缩短,使笔画之间互不相犯,比如,左右结构的汉字,左边部件要适当缩短,为右边部件留出位置。然而,这种避让是有底线的避让,否则,笔画或部件各部分之间相隔过远而无法构成完整统一的汉字,而穿插就是这种有底线的避让的体现。穿插是指一部分笔画插入另一部分笔画的缝隙之中,使汉字的结构连接紧密。比如“教”字右面部件的上撇的收尾处穿插在左面部件“子”的横折与短提中间;“诸”字右面部件的长撇穿插在左面部件的空隙处。穿插避让使汉字的笔画与部件在相互避让的基础上达到统一,既互不相争,又相互依存,使笔画与笔画之间,部件与部件之间获得一种依存感和整体性,是一种达到整体和谐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尚和精神的体现。
3.和而不同的汉字。从汉字的审美体现——书法中看,书法中包含着和而不同的审美意蕴,体现了中华民族包容、尚和的价值取向。从书法角度看,和而不同是指在书法作品中,如果一个字中有相同的笔画或部件,那么这些笔画或部件的写法不尽相同,须在起笔、走势以及长短等方面体现出各自的不同;同样,如果一幅作品中出现两个相同的汉字,那么它们也须书写出不同的形态。比如,“品”字中有三“口”,若这三“口”的写法,大小、形状完全一致,就会有僵硬、呆板之感,而书法中的“品”,三“口”各不相同,左边的“口”面积最小,其次是上面的“口”,而右边的“口”面积最大。并且这三个“口”虽然都是由“竖—横折—横”构成,但是它们的写法都有所不同,或长,或短,或粗钝,或纤细,或化横为点,使汉字生动而活泼。这是书法中笔画,部件书写追求多样性,和而不同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包容多样,海纳百川的尚和价值追求在书法艺术审美中的表达。
综上所述,汉字在造字、构字以及审美上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尚和精神。汉字的整体表意,穿插迎让以及书法中和而不同的审美体现都是中华民族追求整体和谐的尚和精神在汉字中的表达。笔者认为汉字与中华民族之间是“符号与主体间性”的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在共同生活中创造了汉字符号,汉字符号不仅仅是语言的凝固,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中华民族在创造其的过程中,将本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意蕴也融入在其中。另一方面,汉字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原始密码,这种蕴含了中华民族精神密码的汉字具有一种“模塑功能”[7],即具有形象化、意境化和整体性特征的汉字不断诱导,固定着使用这套文字系统的中华民族感知世界的独特方式,并强化中华民族的形象化、象征性和整体性思维模式,进而不断强化中华民族血脉基因中的务实精神、创造精神以及尚和精神。蕴含在汉字中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原始密码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追求,在与“生于斯,死于斯”[8]的稳固社会相去甚远的不断变动的现代社会中,汉字符号以及蕴含在其中的价值追求不断强化我们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并为中华民族找到精神稳固的核心。因此,汉字需要被传承,被书写,要在汉字的传承与书写中挖掘并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原始密码,带着中华文明的底色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