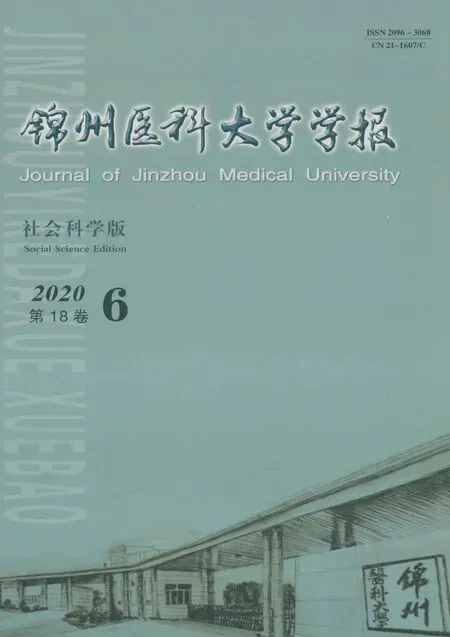翻译史书写视野下的鲁迅研究
2020-02-12班柏
班 柏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418)
由于鲁迅“译著有五百万字之多,单是翻译就占二百九十万字,而且包括苏联、日、奥、匈、西、荷、芬等国文艺理论、小说、童话多方面的作品”[1],且留下了大量翻译研究性质的文章,为此,翻译史上的鲁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依据翻译史自身编撰的目的与体例,不同的翻译史上对鲁迅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多有不同的切入,从是否断代的角度看,可分两类:一是翻译通史类,如《中国翻译通史》;二是断代史,如《20世纪中国翻译史》 (2005)、《中国近代翻译史》(2006)、《中国近代翻译史·晚清卷》 (2011)。从翻译史的内容侧重点来看,大致有两类:一是翻译思想史,如《翻译论集》 (1984/2009)、《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992)、《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2004);二是翻译文学史,如《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2001)、《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2004)、《中国20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2007)、《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 近代卷》(2009) 及《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2009)。从翻译的媒介来看,可区分口笔译史,口译方面,比较典型的是黎难秋主编的《中国口译史》(2002);从翻译的输入、输出来看,一般以输入史为主,输出史以《汉籍外译史》(1997) 为典型。就翻译史而言,鲁迅不但是其关注的不可或缺的一环,且呈现的形态有较大差异。
一、翻译史书写视野下的鲁迅研究现状与特色
以收集翻译研究史料著称而广为学界引用的《翻译论集》(1984),在“第四辑现代部分”收录了鲁迅的代表性译论9 篇。刘靖之之前出版的《翻译论集》(1981),仅收录《鲁迅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3 则),罗新璋版收录数目大为增多。如果从追本溯源的角度看,另一本更早的《翻译论集》(1940),既选中了周作人的《陀螺序》(节录):“周作人在《陀螺序》中举例阐明直译方法,言简意赅,切中时弊。”又选中了鲁迅的《关于翻译的通信回信(节录)》,在序中言明:“鲁迅答J K 同志的信,由直译谈到增加新字眼和新语法,别有一种见地。”[2]可见选编亦有历史之传承。
1984 版论集,从选编的范畴来看,《域外小说集》传播与接受的失败教训给周氏兄弟以探索的动力,促其“积极参与新文学运动中现代翻译诗学的建构。……人们将对鲁迅政治和思想上的评价延伸于翻译研究,致使《翻译小说集》超越其他相对成功的译作而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不能不说是翻译研究的一种尴尬。”[3]可见,《域外小说集》是以其理论影响与现实接受的巨大反差而引起译学界的广泛关注的。以《〈域外小说集〉序言》来引领鲁迅翻译思想研究是恰当的。另外,《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论述了鲁迅借由翻译“输入新的内容和表现法”的主张、“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方法、翻译实践的先行性等。《卢氏〈艺术论〉小序》涉及了“重译”(即转译) 问题、译者素养问题。另有对许霞(许广平) 所译《小彼得》做的序,可能是因为涉及童话翻译的问题才收录进来。《关于翻译》则表明了鲁迅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立场。
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1992) 也是翻译学界广为引用的参考书籍,虽然不乏《鲁迅论翻译》 (1977) 的影子,该书史论结合的编写体例以及总结归纳的鲁迅翻译思想五个代表性方面是较为合理的。这五个方面包含:关于翻译的目的与宗旨,关于“直译”与“硬译”;关于翻译的言语、句法问题;关于重译(转译) 和复译问题;关于翻译批评。选取内容深挖史料,论述不避难涩。对颇有争议的梁实秋同鲁迅有关“硬译”的论争、鲁迅同赵景深有关“信”与“顺”的论辩、鲁迅同穆木天有关重译的论辩之来龙去脉清楚、论述把握精当,实为翻译史编撰之楷模。
黎难秋主编的《中国科学翻译史料》 (1996)整理了鲁迅的科学翻译思想,节选了《关于翻译的通信》辑录为《鲁迅言严复的翻译(1931)》。这同瞿秋白来信提及的1930 年前后重新排印《天演论》等八部汉译名著有关。也同赵景深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鲁迅语) 有关。黎氏选编的部分开头便提及“现在严复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功夫,却从中可以查考。”选录部分似乎给人的印象是鲁迅对严复的评价不高。他一反康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中对严复的高度评价,甚至给“错译很多”的林纾的古文翻译也做出了“文章确实很好”的评价,何以对严复如此苛刻?其实,鲁迅同瞿秋白的通信的要点在于翻译语言的文白之争与对硬译的翻译方法的定性上,至于严译本的社会价值,两者都不大关注的。鲁迅对待严复社会科学书籍的译介也应从这个角度考量。
《翻译通史》在“现当代第4 卷”中设“国内现当代研究翻译理论的概况篇”。其中第2 章“关于直译与意译”第二节“鲁迅、瞿秋白等人论直译”。就直译的话题,还探讨了茅盾、焦菊隐等人的看法。
收录者限于篇幅,剔选抉择自然有其裁量,但可收录的鲁迅译论却颇不止这些。依《鲁迅全集》收录,除日记以外,至少有《不懂的音译》 (01卷417-422)、《风马牛》(04 卷354-357)、《再来一条“顺”的翻译》(04 卷358-360)、《“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04 卷199-227)、《几条“顺”的翻译》(04 卷350-353)、《为翻译辩护》(05 卷274-277)、《论重译》(05 卷531-533)、《再论重译》(05 卷534-534)、《通讯(复张逢汉)》(07 卷131) 等可收录。一些译本序跋也有收录价值,以全集第04 卷为例,就包含《〈进化和退化〉小 引》(255-258)、《〈艺 术 论〉 译 本 序》(259-274)、《〈野草〉英文译本序》(365-366) 等理论价值颇高的序跋。
《中国翻译文学史》对鲁迅的评价仍留有1989年陈玉刚等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的影子,作为第一部翻译文学专著,该史明确阐明了“鲁迅与未名社”的关系,并设专章四节来论述“鲁迅的翻译活动与贡献”。该史对鲁迅的定位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一位开拓者和杰出的翻译家”[4],可谓给后来撰史者定下了基调。这本翻译史对鲁迅翻译活动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为后来者沿袭。鲁迅对于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的批判性继承,乃至苏曼殊、陈冷血译作对鲁迅的影响也有提及。四小节分别探讨了“鲁迅的生平和翻译活动”、“鲁迅的翻译理论”、“鲁迅的主要译作: 《域外小说集》、《毁灭》、《死魂灵》”、“鲁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贡献》”。体例安排上理论与实践结合,评、述、议结合,是翻译文学史个案处理的典范。
《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对鲁迅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森鸥外的作品、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有岛五郎作品、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菊池宽作品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有关鲁迅对苏联文学的译介,《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相对详细。该文学史的近代卷还对鲁迅、周作人的早期翻译活动加以考察(291-318)。
《中国20 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 (2007) 对鲁迅有专节介绍,但无论翻译分期还是理论总括方面并无新意。《20 世纪中国翻译史》的一个特色是将鲁迅译作的原作者、译文及其评价、影响结合起来,为翻译史同翻译实践的结合做出了榜样。《中国口译史》则给出了鲁迅1909 年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铃木圭寿教授植物学课上担任翻译的情节,且鲁迅在口译中灵活应变,改正错误,为其规避了学生的尴尬提问。
《20 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2004) “以翻译思想为‘经’,以人物为‘纬’”,将鲁迅的‘信顺说’视作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的十大学说之一。而且将“移情、益智”双功能说同“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并置,这一点较有新意,少为其它翻译史提及。关于鲁迅的翻译批评,挑选了“挖烂苹果”思想,选材可谓精当。尚有一些翻译史,如王晓丹的《翻译史话》,臧仲伦的《中国翻译史话》(1991) 均有对鲁迅的提及,但无甚特色。倒是一本“另类”的翻译史《翻译史另写》对鲁迅译论的误读做了综述,如将林语堂“忠实、通顺、美”的译论加到鲁迅头上,将鲁迅的译论“易解与丰姿”误引做“风姿”,“削鼻剜眼”译论中有“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字样,误引者却使用了“割低”,“挖掉”这样的字眼。引文的不严谨,也可谓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有趣话题。另一本《中外翻译简史》对鲁迅的翻译评述虽然简短,却指出了鲁迅和梁实秋所谓的“硬译”一为“直译”的替代说法,一为“针对某些字法词法”的硬译这一本质性区别。《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中提到鲁迅劝说林语堂放弃“幽默文学”,凸显了鲁迅的名作翻译意识。
从鲁迅作品的世界传播来看,引起巨大影响的仍是鲁迅的经典作品,此外,鲁迅的创作技巧也为多国作家所折服和模仿,鲁迅在现当代作家作品外译中的分量也可见一斑。
二、鲁迅研究在翻译史书写中的不足
有一个很基本的一点,各大翻译史常常忽略讲明,那就是鲁迅的语言能力。日语和德语是鲁迅的主要外语,德语是在19、20 世纪之交,南京阶段学习来的。日语则在1902-1909 年在日期间习得。鲁迅也懂得一些英语和俄语,但不足以达到翻译的程度。另一个基本问题在于鲁迅翻译的分期。《鲁迅翻译研究》将之分为前期、中期、后期。基本上是从翻译的内容与鲁迅思想的发展方面来谈的。鲁迅的翻译方法也可分期,其转变历程经历了从“最初的编译到稍后的对科幻小说进行的意译直至在翻译《域外小说集》中采用直译。”[5]所用语言也在早期经历了从文言到言文参半再到纯用白话。如文言编译的《斯巴达之魂》就有“豪杰译”的意味,连鲁迅后来“也不免耳朵发热”。[6]这些都是翻译史在书写鲁迅时应当注意的。从目前的翻译史料来看,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被忽略了。
在评价“硬译”的问题上,一方面要分期看待,另一方面也要看待鲁迅译文的独到之处,如李芒核对了鲁迅先生翻译的有岛五郎作品《阿末之死》,“发现鲁迅先生翻译得非常严谨、准确。尽量把原文的句法、词的结构等等反映出来。”[7]而其翻译的《小约翰》至今仍受到读者的喜爱。另外,鲁迅还是译介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的第一人。
一方面鲁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值得重视与发掘,另一方面,对鲁迅作品的对外翻译是否应当在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答案显而易见是肯定的,如果说国内的翻译文学史重点在域外文学的输入,我国的文学翻译史则应看做输入输出并行的双向活动,尤其是鉴于国内国际鲁迅研究的显学性质而言,这一话题更是不能回避。文学翻译史编纂过程中,应注重吸纳相关鲁迅作品外译史料。
《翻译论集》 (1984) 中收集了瞿秋白同鲁迅关于翻译的论争,而梁实秋同鲁迅的翻译论争则未涉及,不能排除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而新版中对此亦无选录,则未免失察。加之论争牵涉的人物与思想纷杂,但就“硬译”话题的争辩,至少梁实秋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鲁迅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是颇可收录的。其中梁氏对鲁迅“欧化文”的批判也少有翻译史提及,梁氏主张“不能为了翻译的便利而改变中国文法,无论哪一国文字,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8]
鲁迅的翻译思想还有许多未发之覆,如鲁迅很早就有了明确的读者意识,而这些思想并不比西方翻译研究的读者反应理论或是读者期待视野研究逊色。如《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9]对于不同类别,鲁迅制定了不同的方略。而其著名的“宁信而不顺”是针对甲类读者专门制定的。相反赵景深的相反主张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鲁迅所谓的“乙”型读者,两者不存在所谓交集的,如果鲁迅的拨乱反正是针对学界的普遍主张,赵更多是普及的意义上谈论“信顺”问题的。
涉及到赵景深同鲁迅的“牛奶路”之争,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翻译史上对此争论或未加收录或论之不详。鲁迅在《风马牛》中狠批了赵将“Milky Way”译成“牛奶路”,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指出:“赵景深把Milky Way 翻译成‘牛奶路’基本上是正确的”[10],传达了原作的文化意象。冯世则的《奶路、面包屑,以及巨鳗里伊基的肚皮》一文也坚持“奶路”是正确的。而《论“牛奶路”乃the Milky Way 之乱译——与曹、赵易林先生等先生商榷》一文尽管就“牛”奶说、聊备一格说、赵景深本人表态、“雪擦洗”判据及“路”文化意象及“牛”论均予以了驳斥,然而牛奶路公案却未就此告一段落。刘麟《七十四年“牛奶路”》一文又提及赵景深1930 年改“牛乳路”为“天河”一事。于是张过大卫又撰《读刘麟“七十四年‘牛奶路’”有感》一文反驳。尽管如此,纷纷攘攘的论争还在继续,徐铁猊的《“牛奶路”》承袭了刘麟说法,进而得出“鲁迅写文章则是在1931 年,并不以赵先生的改动为动,这可能是鲁迅功用性选择的结果”[11]。“牛奶路”公案业已演变成为一个巨大的“阐释漩涡”,涉及的人、事越来越多,阐释的范畴从“硬译”与“宁错而务顺”、鲁迅与赵景深“结怨”说(参见《七十四年“牛奶路”》)、发展到意象的保存与回译问题(参见《奶路、面包屑,以及巨鳗里伊基的肚皮》一文第3 节),研究视角也从译介学、翻译思想研究到翻译史研究等跨越纷呈。“牛奶路”无形地见证了翻译史上一段思想认知的巨大转变过程,这一公案也许至今尚未完结(这本不应成为理由),却少有译史提及,使鲁迅翻译研究有避重就轻之嫌。
鲁迅的翻译实践与思想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起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之前的“归化”转而投向“异化”。《翻译文化史论》提及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 时“借借他人的酒杯”,未意识到“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的过渡阶段,这种过渡形态的体察是翻译史在编写鲁迅时应当注意的。
鲁迅的翻译影响源也是翻译史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如梁启超的“豪杰译”风格就曾对鲁迅译作选择与实践产生过重大影响。梁启超号召“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主”,“借故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对鲁迅翻译实践中的“拿来主义”不无启示。鲁迅对林译痴迷到“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12]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时译出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同年翻译了雨果作品《哀尘》。前者之壮烈,后者之悲情都有林译作品遴选标杆的影子。其选题中科学小说的翻译则是受小说界革命“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之影响。[13]
三、如何在翻译史编纂视野下书写鲁迅
有关翻译史编撰中如何处理鲁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由于编写目的不同和编写体例不一,自然无法强求一致,但以下几方面是值得编撰者在动笔之际应认真思考的:
体例编排方面,《翻译论集》 (1984) 对鲁迅的处理是比较独特的,“‘五四’以来的文章,除鲁迅、郭沫若、茅盾三家集中排列外,悉以写作或发表年月先后编次,以见译事研究之进展。”[14]编排时既包含鲁迅本人的翻译思想,也包含了同鲁迅论辩的瞿秋白的翻译思想。另外,在鲁迅一节末尾还设有“研究与资料”专栏,附有李季的《鲁迅对于翻译工作的贡献》、许广平《鲁迅与翻译》以及相关文章——冯维静的《瞿秋白论翻译》。而且“研究与资料”是穿插在相关翻译思想、研究文章之后的,布局比较灵活。在新版(2009) 中,这种体例得以保存,遗憾之处在于未见对鲁迅研究的跟进,所选“研究与资料”依旧如前。
思想内容方面,首先要注重鲁迅形象的完整性。鲁迅的翻译思想同他本人的思想,包括创作思想一样,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对鲁迅的翻译思想与实践也应动态来看。包括鲁迅的翻译目的,也不应简单地一刀切,应看到翻译作品之前,鲁迅作为翻译活动发起人的目的在于“输入新的内容和表现法”,在动笔翻译之际,秉持“宁信而不顺”的信条达到其“文本目的”,而在译文完成进入流通传播领域,则怀有其针对不同读者而预想达到的目的:甲,受了教育的(宁信而不顺);乙,略能识字的(改作和创作);丙,识字无几的(排除)。
还要注重翻译史的担当。一些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题不能回避,如鲁迅在何种情况下称翻译为“有妇之夫”和“洋鬼子”?史论结合方面,鲁迅指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但并不曾走到傅斯年“惟有从他,惟有欧化”[15]的道路上去,“一面尽量地输入,一面尽量地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的思想基本上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以20 世纪40 年代的白话文为例,其欧化现实至少包含复音词,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延长,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联结成分的欧化,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文学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这一点,《中西翻译简史》有所提及,只可惜缺少了鲁迅这浓重的一笔。
重视翻译史上鲁迅研究的两面性。一方面要研究鲁迅翻译实践与思想,如《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第4 卷》就援引了罗书肆的《鲁迅论翻译批评》(1951) (347) 并对鲁迅的翻译批评思想做了归纳与总结;另一方面,鲁迅作品的外译研究也应列入翻译史。《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部分第4 卷》提及杨宪益曾翻译《鲁迅四卷选集》。而鲁迅诗歌的外译在翻译史上体现不足,黄新渠、陈颖、吴钧的鲁迅诗歌英译工作大都未能收录在研究范围之内。
重视副文本的研究。鲁迅为本人和他人的翻译作品做了大量序跋,这些副文本具有一定的翻译理论价值,至今未能得到重视。《鲁迅全集》的“序跋集”包含大量翻译副文本,再加上《鲁迅译文集》的相关副文本,相关史料颇多可以发掘。尚有《〈铁流〉图特价告白》 (08 卷507)、《死魂灵百图》 (08 卷522-523)、《〈海上述林〉 上卷插图正误》等副文本相关资料。
还应关注鲁迅翻译思想的演进体系,如鲁迅对日本文学的兴趣最初是不大浓厚的,受梁启超翻译功利观的影响,他对“摩罗”诗人的浪漫及对林纾一派笔受改写风的涤荡更为渴望。此时的鲁迅目光在弱小民族的东欧,而日语则成为他们译介东欧的手段。直到后来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 (1919) 与有岛五郎的《与幼小者》 也是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引进进来,而不是对日本文学的专门关注。从这一点来看,鲁迅的翻译思想是颇为契合西方“食人主义”的翻译思想。
“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始。他的第一步运动是办杂志。……办杂志不成功,第二步的计划是来译书。”[16]可见,鲁迅的文学道路是从翻译起步的。“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鲁迅精神始终是鲁迅译文遴选贯穿始终的标杆。其儿童文学译介以及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等译介均解释了鲁迅貌似零散、条块分割的翻译题材选择。
1 000 多万字的作品一半为翻译,译介14 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200 多种作品,鲁迅的翻译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目前,收集整理鲁迅译论的专著已有《鲁迅论翻译》,专门鲁迅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专著也颇为不少,如顾钧的《鲁迅翻译研究》 (2009)、吴钧的《鲁迅翻译文学研究》 (2009)、Lennart Lundberg 的Lu Xun as a Translator(1989),鲁迅翻译的比较研究专著有陶丽霞的《文化观与翻译观——鲁迅、林语堂文化翻译对比研究》 (2012)等,也有鲁迅作品的对外翻译及相关研究,如吴钧的《鲁迅诗歌翻译传播研究》 (2012)。从翻译史的角度研究鲁迅的译作译论目前尚少有涉及,有必要深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