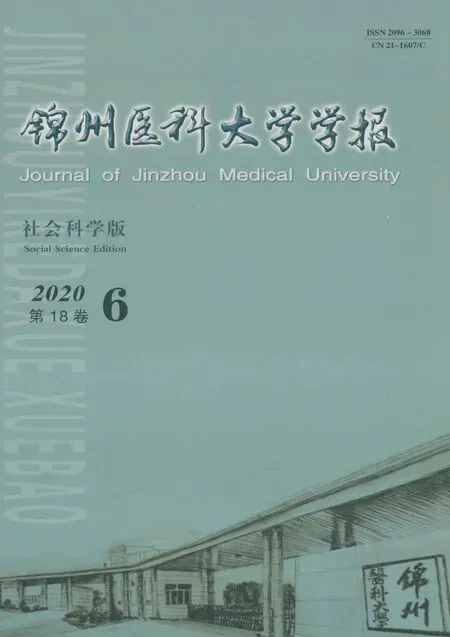闽西苏区时期的药业
2020-02-12华碧春黄颖
华碧春,黄颖
(1 福建中医药大学 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2 福建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1929~1934 年,国民党政府对闽西苏区进行武装“围剿”和经济封锁,严禁苏区产品外销,破坏了革命根据地的商业和对外贸易;频繁的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苏区军民经济生活的困难,药物的供应尤其紧张,有时连最基本的止痛、止血、消炎、退热药物都十分匮乏,严重影响了苏区医疗工作的开展。在那“黄金有价药无价”的非常时期,为了冲破国民党政府的封锁,解决根据地药物的军需民用问题,红军部队、苏维埃政府和根据地人民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千方百计地保障药物的供应和使用。
一、冲破封锁 向外购药
闽西苏区的药物供应主要依赖外地输入,因此冲破封锁、向外购药就成为主要的药物来源途径。
1.建立地下交通线。1930 年9 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加强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的联系,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拟建立长江、北方、南方三条交通线。为此,成立了以周恩来、李立三、吴德峰等为成员的中央交通局,吴德峰任局长。在此之前,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闽西红军、朱毛红军的联系,中央请福建省委选派人员到上海商议组建南方线和闽西交通大站。1930年6 月,时任中共闽南特委军委书记的卢肇西,受毛泽东和福建省委派遣,前往上海接受这一特殊任务;广东方面也派遣时任省委发行科长的李沛群前往上海。卢肇西等人到上海后,立即和吴德峰局长开始商讨建立闽西等地交通线站点的问题,决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在汕头建立交通局直属站(此为绝密站,规定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在龙岩设立闽西交通大站(当时对外称工农通讯社,各县设立通讯社分支机构)。不久,因革命斗争形势转变,闽西交通大站于1930 年12月转迁永定虎岗,之后再迁往永定县城秋云楼,最后设在金砂的永昌楼(对外称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自此,一条从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进入永定,而后到长汀、瑞金长达数千公里的红色交通线终于建成了。这条贯通苏区(即苏维埃政府统治地区) 与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地区) 的交通线,下面分设大站、中站、小站。其中香港、永定、虎岗为大站,永定大站管辖的青溪、会溪、古木督为中站,多宝坑、桃坑等地为小站[1]。
除此之外,长汀福音医院也积极帮助红军购买药物。起初,医院从上海购买药物后,通过邮局寄回长汀,然后再设法运给红军。1931 年下半年,长汀成了巩固的苏区,国民党政府开始对长汀实行经济上的严密封锁,因此通过邮局只能邮寄小包药物,这样的邮寄方式所获取的药物远不能满足红军的需要。于是,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派他的学生曹国煌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华英药房购买药物。
曹国煌从长汀出发往南走,先到上杭、峰市、汕头,再往北去上海购药。第一次购买的药械一共有20 多箱,每箱有一二百斤重,包括内科用药奎宁及各种注射用药,外科用药碘片、漂白粉、硼酸、硼酸绒布、纱布等;医疗用具主要是手术器械,这些都是红军伤病员急需的。傅连马上和红军领导取得联系,部队先后派杨志成和杨立三来运药,带了两大批药到红军中去。后来,曹国煌又去上海买了一批药。
当时,峰市、上杭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到那里去安据点是很危险的。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傅连约了一个在长汀开批发商行的姓邱的大商人合股开药房。邱姓商人找了铺保,在峰市、上杭租了房子,开了两个药房。曹国煌在峰市的药房中当医生兼经理,一面卖药,一面看病。但卖的药都是一般的药,重要的药都偷偷运往长汀。因此,红军的药物有了经常性的保证。1932 年秋天,曹国煌在峰市药房工作时不幸被捕牺牲于上杭城[2]。
2.发展对外贸易。苏区时期的对外贸易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贸易方式,是指当时的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商品交易。
1933 年4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分为五科,其中一科是“对外贸易处”,把发展对外贸易作为当时工作的重心[3]。5 月,临时中央政府将“国民经济委员会”升格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并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在纲要中,“对外贸易处”改称为“对外贸易局”,并明确其掌管的事务包括:“管理苏区对外贸易事宜,设法打破封锁,保证苏区境内的生产品与境外的商品得以经常的交换,消灭农业生产品与工业生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现象。”[4]此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长汀设立了省对外贸易局,在县或重要市镇设立分局,并在重要口岸、圩镇设立办事处,组织对外贸易网;通过实行灵活机动的贸易政策,开展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活动,出口土特产,购入中西药。
1933 年初,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成立了中华贸易公司,收购根据地出产的茶叶、烟叶、香菇、木材、樟脑油、农副产品等土特产,运到白区销售,又从白区购回大量的西药、医疗器械、布匹、煤油、食盐、印刷材料、手电筒等紧缺物资,销往根据地各县,供军需民用[5]。1934 年初,中华商业公司长汀分公司成立,政府投资全部资本,约10 万余元。公司业务以采购为主,派员工到白区购买布匹、食盐、火柴、煤油、西药等,购买的西药包括金鸡纳霜、阿司匹林、奎宁、碘酒等。
除了公营商业,长汀的私营商业也很兴旺。革命前,长汀的商业基础就已经比较雄厚,商品流通全靠私营商业。但在扰乱的政局下,私营商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有些商人闭店出逃。因此,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断出台政策,以稳定私营商业。1929 年3 月,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长汀后,颁发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通告,指出:“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6]237 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规定“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 ……对城乡小商人绝对不要没收商店、焚烧账簿和废除账目。”[6]881930 年3 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商人条例》也明确规定:“商人遵照政府决议案及一切法令、照章缴纳所得税者,政府予以保护,不准任何人侵害。商人自由贸易,政府不予限制其价格。商家来往账目,政府不予取消,维持商家账簿。”[7]262-263在这一系列政策的感召下,部分关闭的私营商店又开业了。同时,还新开业了一些私人商店。从1933 年冬的有关资料统计,长汀共有367 家私营商店,其中有药店17 家[5]。
此外,闽西苏维埃政府还制定政策,保护优待白区的商人,采取减税、预先支款等办法,吸引白区的商人到苏区进行药物贸易。如: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经济政策决议案》规定:“保护外来客商,不准向他筹款,以免外商裸(裹) 足不前。”[7]227即指示各级政府不许向白区商人筹款,不许没收其商品。由于制定了正确的政策,白区的商人在商品交易中赚取了利润,他们积极寻找商业渠道、设法开辟通商途径,把药物运到苏区进行交易。
二、创办药材合作社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导致苏区出现工业品因为物资紧缺从而价格迅速上涨,而农产品价格猛跌的不良现象。为了解决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问题,避免出现商场冷落、工业缩小、工人失业,以致整个社会经济衰落的局面,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号召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包括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解决工农群众的生活问题,以保证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从而稳固新政权的基础。[7]97-102于是,闽西苏区掀起了大办合作社商业的高潮。
1930 年起,闽西苏区不少区乡成立了药材合作社(或称公共药铺)。其形式有一乡或几乡联办,或以区为单位;资金由政府投资,或群众自愿入股集资、合股经营。有的专门售药,群众到公共看病所看病后,凭医生处方到药材合作社购药;有的聘请医生坐堂,既看病又售药。合作社职工由各乡推荐责任心强、有业务经验的老药工参加。
上杭才溪区消费合作社运动开展得比较好,该区办了5 个药材合作社,受到了《红色中华》的表扬[8]。其中,才溪区通贤乡办得最好。通贤乡药材合作社由8 个村的群众自愿认股140 元(大洋) 为基金,社里设主任、药剂生、采购员和医生。采购员每周到上杭城或连城新泉药店进药,做到常用药不缺,还备有人参、鹿茸等补品,并自制丹、膏、丸、散等成药。药品售价为进货价加20%;医生诊病或出诊不收诊费;对红军家属(发红属优待证)、合作社社员(发社员优待证) 和贫困户,收费优待,或可赊药;还免费为过路红军伤病员诊病送药。合作社每年农历五月节、中秋节、春节各结账一次,交社员审查公布,乡苏维埃政府派员参加,从纯利中提取15%分红,余额作为基金,顾及到群众、社员和合作社三者的利益。当时苏维埃政府虽然财政困难,但仍对药材合作社免纳税金,以扶持苏区医药事业的发展。
闽西苏区药材合作社的建立,对于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政策,缓和苏区严重缺医少药状况起过一定作用。1934 年底,苏区药材合作社遭国民党军队洗劫一空。
三、建立红色制药厂
为了解决苏区药物供应问题,福建军区在各地因陋就简办起了制药厂。
1932 年初,福建军区在上杭白砂洋子里(今中洋村) 创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制药厂,同年下半年迁至上杭南阳乡茶树下。该厂归福建军区后方留守处领导,曾由红十二军派一特务连护厂。厂房寄于民家,仅有一些镐头、斧子、筛子、铁锅、药碾等简单工具。药厂设厂长、共产党支部书记、司务长、文书等职务,加上药剂员、药品管理员、工人等,共30 余人。工人分为采药班、加工班和制药班。采药班的任务是按制药需要到深山密林或崖头岸边采集各种中草药;加工班则将采回的鲜药材晾晒、炒干,加工成粉末;然后由制药班在药剂员的指导下,按配方制成各种成药。药厂主要产品有止痛片、麻黄素、鸦片酊等七、八种。工人将制好的药品分装成小包,然后送往前线和各红军医院。该制药厂于1933 年底转移到长汀河田,后又迁至长汀四都。原中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阙森华同志在该制药厂工作近1 年。
1933 年2 月,福建军区卫生部在四都渔溪村创办了卫生材料厂,由王叔恒担任厂长,附属于四都红十二军后方医院。卫生材料厂设于廖氏长森公宗祠内,下分采药组(负责药材的购买和采集中草药)、制药组(负责药材加工)、包装组(负责药品包装)、总务组、文书组、会计组等,共40 余人。制药组的技术人员是由中央卫生部派来的。卫生材料厂主要采集当地出产的草药,能够生产清凉油、仁丹、八卦丹、济众水、希山丸、骨灰末、猫肠线、奎宁、大王粉、汽水、消毒棉等,成为当时重要的药品生产厂。生产的药品专门供应各军区后方医院及前方战地医院。1934 年冬,国民党军队迫近四都,卫生材料厂停止制药,合并到四都红军医院[9]。
四、采集中草药
闽西苏区还大力发展中医药。1933 年11 月下旬,毛泽东深入才溪乡做社会调查,指示区苏维埃工作人员要广泛发动群众,利用闽西山区中草药资源丰富的优势,组织群众上山采集中草药。苏区红军医院的医生和群众采集杜鹃花、车前草、六月雪、苦莱、冬泡刺、南瓜心,加工成药膏或药粉,用于祛暑解毒,退热止血;并用蜂蜡或猪油拌苦莱、杜鹃花、冬泡刺加工的药粉医治伤口。
由于药物来之不易,故药物的使用必须本着尽可能节省及中西医药结合的原则,就地取材,最大限度地使用廉、便、验的中草药。红军医院的医务人员虚心向当地中医、草药医请教,哪怕一、二味民间偏方验方,只要能解决痢疾、疟疾、下腿溃烂、疥疮等多发病,就当做灵丹妙药,传授给连队卫生员及战士,就地采集使用,在防病治病中充分发挥中草药的作用。蛟洋红军医院的医生用鲜马齿苋治痢疾、白芨粉治刀枪外伤,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四都红军医院的医生常自制生理盐水,用猪油代替凡士林。才溪后方临时中医院的伤科医生用自制的伤科药散治刀枪外伤,包括伤口方和驳骨方。两种伤科药散的药物组成如下:一是伤口方:石膏二两、洋血结(竭) 一两、轻粉一两、生乳香一两、正二拔二(冰片)、珍珠三钱;共研末撒伤口一日二次,外用生烟开水浸贴伤口上。方中石膏、冰片清热泻火,血竭、乳香活血消肿心痛,轻粉、珍珠去腐生肌,生烟开水清热解毒。该方对枪、刀等外伤有较好的疗效。二是驳骨方(“驳”为客家方言,意为“接”):田七六钱、苏木二钱、元汉(进口轻粉) 二钱、小草角(皂角) 二钱、碎粉(骨碎补) 二钱、什兰(泽兰) 二钱、胡芷(白芷)二钱、陈香(沉香) 二钱、广木(香) 二钱、庄黄(大黄) 五钱、小茴(香) 二钱、木通钱半、细辛钱半、桃仁钱半、丹香(参) 钱半、茂术二钱、山林(三棱) 二钱、赤夕(芍) 二钱、肉桂钱半、草乌钱半、生乳香二钱、末(没) 药二钱、红花二钱、血结(竭) 二钱、土别(土鳖虫) 钱半、淮七(淮牛膝) 三钱,以上共研末视病情轻重,重病一次二两外敷,轻病一两至一两半,须用粘米糊配帖。用法:以粘米糊煮好,药末贴断骨处,并用两个木板夹住[10]。方中田七活血止血,为伤科圣药;牛膝、苏木、赤芍、乳没、红花、血竭、丹参、大黄等活血消肿止痛;细辛、肉桂、沉香、木香、茴香等辛香温通血脉;草乌、土鳖虫拔毒去腐;白芷、骨碎补生肌补骨。全方配伍得当,粘米糊为调料,简便易得。上述二方至今仍由其后代伤科医生有效地应用于临床。
除以上四项主要措施之外,红军部队还在打扫战场时注意收缴药品,如第二次反“围剿”时期,红军攻克建宁城时缴获药物20 余担;还通过没收土豪军阀的财物等途径缴获药品,集中后有计划地分发到各红军医院。
苏区政府还广泛发动群众,发挥集体智慧,通过各种巧妙办法通过国民党政府设置的层层关卡,把药品运回苏区。如:群众把挑柴、扛猪的竹杠节打通,装入药品;妇女用双层粪桶(上层装粪便,下层装药品等) 运药,或把药品绑在腹部以化装成孕妇;码头工人用铁箱装药捆在船底等。有的群众在冒险运药的过程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0 世纪30 年代的闽西苏区,药物匮乏困扰着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红军部队、苏维埃政府和根据地人民采取了建立地下交通线、发展对外贸易、创办药材合作社、自办制药厂、采集中草药等一系列有效措施,解决药物供应困难的问题,为闽西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