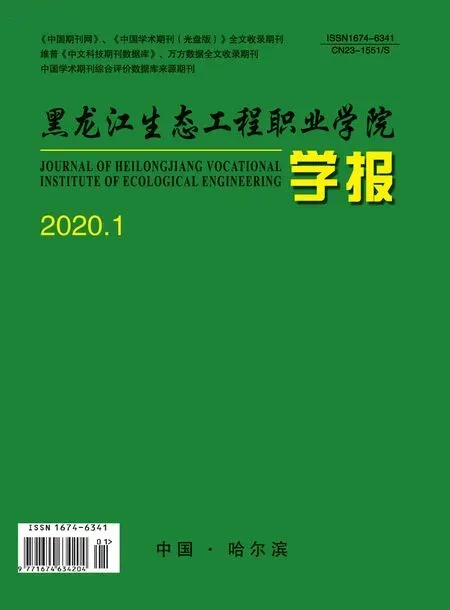我国少数民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空间分布研究
2020-02-12余聿莹
余聿莹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006)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文化基因库,代表着民族普遍的心理认同和基因传承,代表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1]。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下称“非遗传承人”)是传承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推动者,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研究已成为近几年学界研究的热点和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点。吴晓亮,郝云华,陈炜等人从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培养模式问题入手进行探讨[2-3];李虎,宋智梁等人深入研究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问题[4-5];黄小娟,王苏野等从权利保障角度进行剖析[6-7]。以上研究成果表明: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在空间分布的研究领域中,关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这一代表性群体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展示了不同地域生活风貌、民间习俗,对因地制宜、分类保护的落实具有重大促进意义。因此探究其空间分布,分析影响分布的理论依据,为非遗保护与传承发展提供一点思路。
1 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情况
文中涉及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自2007年以来,国家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单,共计3 068名,其中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占有相当的比重(见表1)。
从表1可以观察到,在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单中,各个行政区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数目不一。其中西藏为96人,占该地区传承人总数的100%,表明西藏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均为少数民族,其中藏族95人,珞巴族1人;新疆112人,占地区传承人总数的98%;贵州84人,占地区传承人总数的87.5%;内蒙古、云南、青海均占地区传承人总数的80%以上;广西、宁夏、黑龙江、吉林、海南均占地区传承人总数的50%以上;其余地区均不到地区传承人总数的50%。其中安徽、江西、香港、澳门没有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

表1 不同地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民族构成统计表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在我国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多集中在我国的西南、西北、东北等少数民族地区;东部、中部等汉族人口集中,汉化程度高的地区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较少。
2 影响空间分布的理论
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被应用于企业的组织管理当中,理论研究始见于1984年弗里曼出版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8]。如今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广泛,在文化产业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领域同样适用,本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来分析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空间分布成因,将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利益相关者界定为“任何能够影响我国国家级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或者受地域空间影响的群体或者个人” 。其中主要的三个利益相关者是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非遗传承人是非遗的载体和核心参与者,中央政府是统治和管理主体,地方政府是组织和执行主体。
在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性的保护下,少数民族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新疆目前已拥有3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是新疆木卡姆艺术、《玛纳斯》史诗、麦西热甫,对应的传承人分别有12人、5人、3人。正是由于我国政府申请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成功,调动了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新疆地方政府积极制定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政策和相关措施:2005年出台两部地方法规,2008年颁发非遗保护条例,2010年推出单项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通过举行非遗文化交流活动、设立传承机构及专项资金等措施,为保护非遗传承人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空间和场域。新疆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在此基础上获得了物质和精神支持,通过研修、传习、宣传等途径提升自身素养,传播非遗文化,培养后继传承人,全身心投入到文化传承事业中,使地方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正是由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了共赢的局面,国家在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认定上会愈加重视,因此其占比会更大,分布的地区会更广。
2.2 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理论
2009年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政府白皮书中提到:我国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数据显示:2002—2009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达3.86亿元,约有四分之一用于民族地区[9]。政府设立的《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专门工作机构,从事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目前《格萨尔》传承人为14人,其中10人为藏族,集中在西藏、青海;3人为蒙古族,分布在内蒙古、新疆;1人为土族,位于甘肃。《江格尔》传承人为4人,均为蒙古族,位于新疆。《玛纳斯》传承人为5人,均为柯尔克孜族,位于新疆。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是民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延续民族非遗的传承和发展,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及文化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民族平等原则为例,由于少数民族在文化发展方面与汉族相比有一定差距,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不仅能享受民族发展权、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等基本权利,还依法享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权益保障,在政策上会得到优先补偿或重点保护,以达到各民族共同发展、平等发展的目的。
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基本点中有一方面是公平,而公平发展包含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空间纬度上的公平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10]。因此国家在传承人的认定上,不能忽视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重要性,不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而是通过认定的方式,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10]。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其本质是人的生产实践和实践能力的协调[11]。因此国家在对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的实践上,必须要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与利用、人口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可以看出,其对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空间分布具有重要影响,选择各民族地区的传承人,能够实现文化互补和共同发展,以实现各民族和各地区之间共生互补、和谐均衡的良好局面。
3 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3.1 法律保障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四级非遗传承人体系,尤其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录中,每个批次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数量都呈上升趋势。但在喜人成绩的背后,却存在着“重申报,轻保护”的实际情况。在加强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上,国家在政策和经费上会给予特殊的支持,某些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利用此中便利,积极申报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使本地区既赢得最高级别的传承人荣誉,又获得了资金支持。但在后续的传承保护工作中缺乏规范,没有将专项用款落到实处,而是投入到其他方面使用。更有甚者,有些人本不是该项目真正的传承人,却为了名利弄虚作假申报传承人,以至于真正应当进入体系的传承人流失在外。许多由几个人或者一批人共同完成的非遗项目,根据现有的非物质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和认定程序,政府只申报一人作为代表性传承人。在这种情况下,非遗的责任与义务表面上都压在这一人头上,伴随的还有“非遗传承人”的光鲜的名头和相关利益的独占[12],无形中制造了传承人群体内部的管理混乱。这种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管理的混乱而造成的非遗界乱象,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3.2 保护结构两极化
目前,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上呈现出严重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是重视申报和保护知名度高、传播范围广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忽视那些鲜为人知的项目传承人。例如侗族大歌、蒙古族长调民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等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的项目,其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人数均位列前茅,而布鲁、安昭、廓孜等大众闻所未闻的项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极其稀少。另一方面是重视人口较多民族的传承人的保护,缺少对人口较少民族的传承人的保护。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藏族人口占西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98.53%,从前文分析中已知,西藏96个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中藏族有95人。正是由于藏族人口在西藏地区庞大的人口规模,藏族文化生存环境较好,藏族文化物质基础坚实,国家也更倾向对藏族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和保护。又如在多民族聚居的云南地区,107个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中共有19个民族,其中彝族27人,彝族人口占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32.84%;独龙族1人,独龙族人口仅占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0.04%。还有基诺族、怒族等仅有1个传承人,这些民族位于云南山区地带,文化活动空间小,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能力十分脆弱。因此入选传承人名录的仅有1—2人,甚至有部分民族尚未有传承人,非遗传承保护情况不容乐观。
3.3 文化生态脆弱
目前,对于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仍是单一的、孤立的,缺乏整体性保护,这一问题体现在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之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协调机制缺失。一是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冲击,原生态的生活环境遭到破坏,文化传承失去生存土壤。二是汉文化扩散传播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使得本民族文化内涵加速弱化,甚至被汉化。三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在各地区之间缺乏联动性。例如同种项目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分布十分分散,4名侗戏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分布在广西、贵州、湖南三地;格萨尔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分布在青海、四川、西藏、新疆、甘肃、云南、内蒙古多地。再例如,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分布也相当不均,回族非遗传承人在宁夏有12人,河南7人,江苏和北京4人,新疆、天津和河北3人、青海和山东2人,浙江、云南、四川、上海、陕西、甘肃、福建等地只有1人,由于空间分布范围较大,省际之间协调联动性不足,影响同项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或同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在区域之间的交流和联系,造成片面式、孤立式的保护,不利于民族文化生态形成有机的、富有活力的文化整体。
4 思考与展望
根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中反映出的不足之处,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加强政策性保护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方面充分发挥扶持、组织、执行、监督的功能,全面完善民族非遗法律体系,探索建立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长效评估、监督和退出机制,提高传承人专项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科学量化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数量,优先考虑人口数量少、非遗类型稀缺的项目传承人,构建数量可观、结构合理的非遗传承人队伍。首先提高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比例,国家应积极培养传承人备选团队,把握好传承人队伍与传承人的关系,并且更多地开展传承人技能培训和考核机制培训,明确传承人传承义务与权利。其次积极做好少数民族非遗普查工作,挖掘非遗传承队伍,充分尊重和积极认定他们的传承人身份。同时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知识产权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处理好原生与变革、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以老带新,以高荐低,使得传承链焕发持续的生命力。
4.2 做好结构性保护
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等项目需要靠口口相传才能得以传承,所以对由于传承人的离世造成传承危机的项目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加快对濒危项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寻找的步伐,动员广大社会力量一同加入调查研究行列。利用现代化技术尽快收集相关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建立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数据库,对它们进行精心保存和深入分析研究。同时对濒危项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有所倾斜,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知名度较低的项目,应当利用其中的文化故事进行宣传,扩大知名度。以独特人物和故事作为宣传的核心价值,通过个性化的展现,扩大其在社会的影响力。对于人口较少、传承困难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群体,应当有针对性地开展“研修计划”“人才培养计划”,提供更多培训机会。整合地方高校、科研学者等资源,帮助这一传承人群体夯实基础,拓展眼界,提升文化自信和可持续创造能力。
4.3 强化整体性保护
在文化交流方面,通过联合举办文化交流会、研讨会、文化艺术节等形式加强省际之间的联系,跨省域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保护共同的民族文化的土壤和环境。在信息资源方面,将各地同民族、同类型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档案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互补、信息共享。加强省级之间的有效互动,加深社会对该类非遗项目的认识和了解,扩大传承人的影响力,全面落实区域间文化协调发展战略,形成区域间的整体性保护,重构传承生态。在文化空间方面,不能孤立地静态地将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放到人造的环境中。在传统的原生态的特定的空间里进行的非遗创作,才能保留少数民族最根本的特色。以民族非遗文化内涵为立足点,十大非遗项目内容为依据,由政府与旅游、文化、民委等部门牵头,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搞好非物质文化资源的调研,进行科学性和可行性的规划论证,建立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缓冲隔离外来文化的消极影响,维护非遗的多样性和生存环境的生态性,以实现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中华大地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财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凝集着各民族的民族意志、民族审美以及民族记忆,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在民族非遗的认同、保护、传承当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的探讨,有利于清醒地认识到传承人群体的处境和出路,通过深挖其中的价值和内涵,增强传承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