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然
2020-02-10李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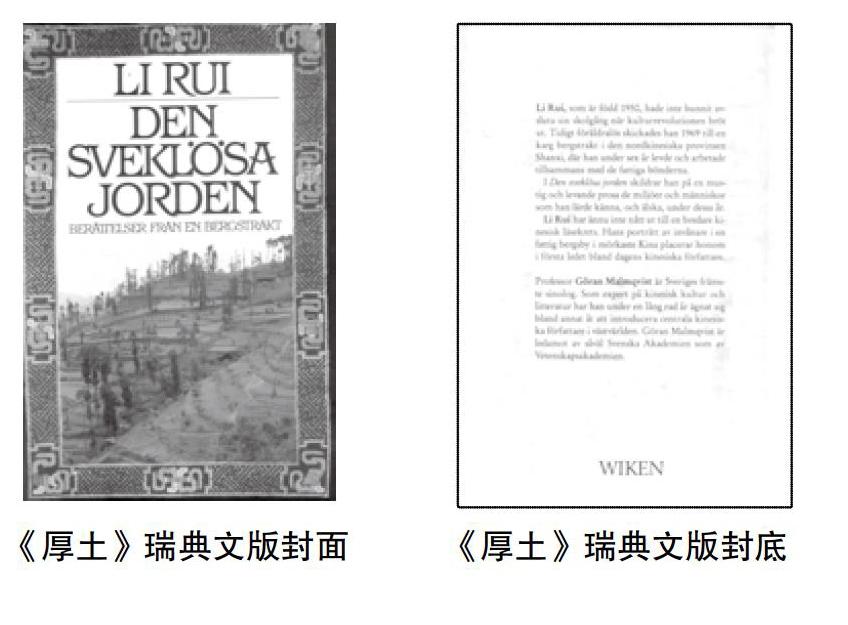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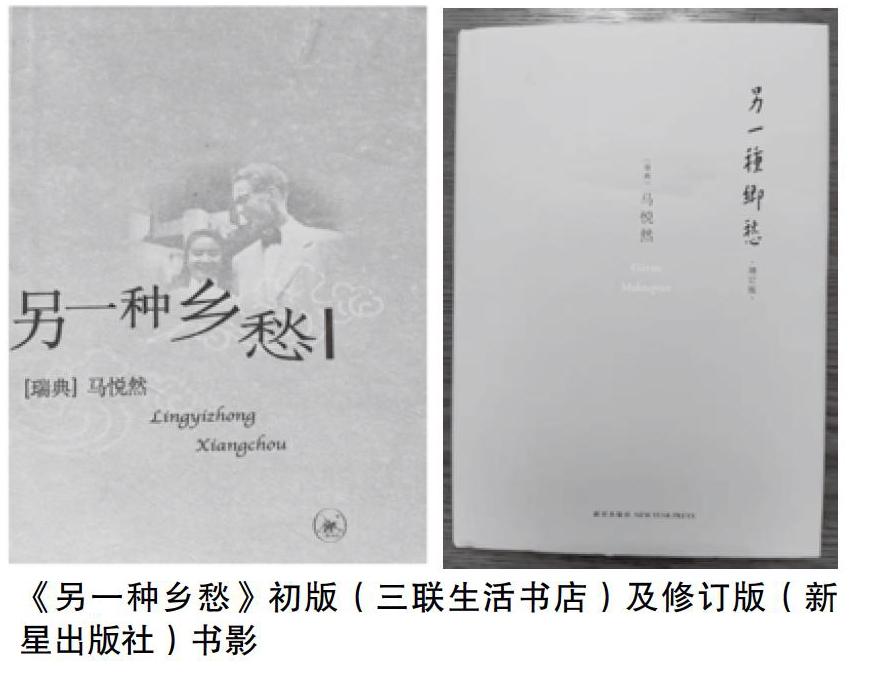

心上的秋天
马悦然,1924年出生于瑞典南方。1946年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先生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1948年大学毕业,到中国四川做方言调查。1950年和陈宁祖女士结婚,当年秋天返回瑞典。1952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6年至1958年任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秘书。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中文系、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1990年退休。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院士,1987年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至1982年,1986年至1988年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
1965年以来,马悦然把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他的母语——瑞典文。他的译作包括:《诗经》(一部分),《楚辞》(一部分),大量的汉代诗歌,唐诗,宋诗,宋词,元曲,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等人的作品,以及朦胧诗人北岛等人的诗歌。此外,他还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以及沈从文、李锐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
五十多年前,一个瑞典小伙子因为读了林语堂先生英文版的《生活的艺术》,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好像一个远游的人被一条大河所吸引,不由得想沿河而上去看个究竟,看看这条大河到底是从哪儿发源的,看看河上到底还有些什么奇特的风光。于是,他从一本叫做《道德经》的古书开始。于是,他找到一位叫高本汉的老师作向导。或许连这个年轻人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条大河,他花了自己一生的时间在这条大河上寻觅,考证,阅读,翻译,思索,徘徊……从上古到中古,从中古到近代,从近代到当代。那双原本年轻火热的眼睛,从新奇,而渐渐平静,从平静,而渐渐深沉。终于有一天,当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家,当他把自己心爱的中国妻子安葬在墓地里的时候,看着墓碑旁边那棵秋叶落尽躬身伏地的白桦树,望着不远处广漠无语的大海,他忽然意识到原来已经消逝了很多很多的时光……自己在大河中,大河在时光中,滔滔不息,一去不返……一位中国的智者曾经感叹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
五十多年前的那个年轻人终于皓首穷经,著作等身,成为世界知名的汉学家。他把西汉典籍 《春秋繁露》翻译成英文。他让同胞们和他一起分享 《詩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美妙篇章。他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一版再版,到处流传。他的翻译和介绍让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现代、当代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引起世界的注意。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外国人像他这样无怨无悔,不辞劳苦,到处传播中国文化,到处传播中国的语言和声音。当马悦然先生回首一生,追忆往事的时候,他用中文写下了这本书,书名叫做《另一种乡愁》。在我看来,皓首穷经,著作等身,只能算是一个学者,只能是学术的证明。而一颗被乡愁缠绕的心所流露的却是情意满怀的人。一个人如果不是把自己的生命和中国连在一起,一个人如果不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文化的学习和传播,一个人如果没有深深的眷恋和寄托,他是不会把中国认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的,更不可能体会到中国人悠悠千载的乡愁。
1950年夏天,经过十几天的颠沛周折,悦然终于坐汽车从成都到重庆,又坐轮船从重庆到武汉,再坐火车从武汉到广州,等到箱子和人都过了罗湖桥来到九龙的时候,他满心惆怅地问自己:“可是我的心呢?我的心在哪儿?”那时候,还有一个障碍隔在命运中间。等到那个障碍终于消失了,悦然立即拍了一封电报到成都,向他的房东陈行可教授的女儿陈宁祖求婚。那故事浪漫得像一部电影。
2000年春天,我从巴黎来到斯德哥尔摩。悦然带我到一家鲜花店买了两盆花,然后带我来到宁祖的墓前。圆圆的一块石头,静静地掩埋在草地里,在1931――1996这两个年岁之间镌刻着宁祖的名字。十年前,我第一次到瑞典,就是宁祖和悦然一起冒雨到机场去接的我。到瑞典的第一顿饭,就是宁祖亲手做的热汤面。那天晚上,悦然的茅台酒,宁祖的热汤面,和她爽朗的笑声,让我如归故地,一下子回到了家里。可现在,这一切都静静地埋在那块石头下面。石头上,把一个人六十五年的生命,缩写成那简单的一行字。悦然把墓碑前枯萎了的花挪开,用手铲把新买来的花轻轻埋在土里。然后把旧花放进附近的垃圾箱,把墓碑旁飘落的枯叶拣拾干净,这一切他做得熟练而又细致。等到都做好了,悦然指着那棵躬身伏地的老白桦说,这棵树真好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白桦。悦然告诉我,为了能靠宁祖近一点,他特意退了城里原来的大房子,搬到这里来住。他每天都坚持散步,每天散步都要从宁祖的墓前经过,每天都要和宁祖待一会儿。
我曾经在不同的季节三次到过斯德哥尔摩。也许是因为高纬度的原因吧,我在斯德哥尔摩看到的总是如水的斜阳,明澈宁静的斜阳,悠远而又慈祥,总给人说不出的慰藉和伤感,总让人觉得那是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总是让人深深地想起秋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记下了这个无以名状的感触:“在中国,秋天是怀念和伤感的季节,一颗‘心上放了一个‘秋字,就是愁。就是中国诗人不绝如缕咏叹了千百年的情怀。”
现在,悦然要我为他的书写一个序言,一篇篇地翻过悦然的短文,我看见又有一个人加入到这千年的咏叹当中来。
西元2002年8月11日傍晚写,
14日晨改定于太原家中。
(本文为作者给马悦然《另一种乡愁》所作序言)
却望吕梁是故乡
(近日收到《明报月刊》的约稿信,要为祝贺悦然的九十大寿做一个专辑,约我写一篇文章。下面这篇短文写于八年前,虽然是旧作,可却有许多难得的记忆弥足珍贵,权且当作是以叙旧为老朋友贺寿。)
我是1969年1月12号离开北京来到吕梁山区的,在一个叫做邸家河的小山村里当了六年插队知识青年。插队的时候没有想到日后会当作家,更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竟然会把一个叫马悦然的瑞典人带到邸家河来做客。
1986年我开始了系列小说《厚土》的创作,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副标题“吕梁山印象”。小说陆续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一些反响。1988年的6月10号我接到一封来自瑞典的信,写信人是陈宁祖女士,她自我介绍她的丈夫马悦然是瑞典汉学家,正在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在不同的刊物上看到《厚土》,说是“很想翻译”。我当时根本不认识马悦然何许人也,当然也更不知道他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教授、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主席等等这一系列头衔。只是觉得有人“很想翻译”自己的作品,这让我很高兴。于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情。先是笔墨的,后是感情的,现在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从《厚土》开始,接下来是《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在前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悦然一本一本地翻译了我大部分的小说。1988年《厚土》的瑞典文译稿完成,交给布拉别克(BRA BOCKER )出版社出版。1989年初,悦然告诉我,他和宁祖很想到吕梁山来看看,并且他已经和七八位诺贝尔奖评审院士说好要一起到中国来,到吕梁山来看看我插队的村子。1990年他们邀请我第一次去瑞典访问,其中有四五天的时间住在瑞典南方他们的别墅旁边,那几天,宁祖天天在家里给我做中餐。1993年他們夫妇两人一同来中国到云南、四川游访,在北京见面时我们还在讨论什么时候能一起去吕梁山。
1996年,宁祖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三个人的约定从此永缺一人。
1999年,悦然再次提起要来吕梁山的动议。为此我已经打听预定了上山要用的越野车。悦然决定和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多弼教授同来,并且要带他的小儿子陪他一起来。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又因为入境签证出了问题被迫取消了行程。这之后,我又去过两次瑞典。2001年的诺贝尔奖百年庆典,我受到特别邀请再赴斯德哥尔摩。但悦然已经不再提起来山西的话题。吕梁山就在眼前,每天我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只要抬起眼睛就能看见它,真的是近在咫尺,也真的是遥不可及。所谓物是人非,所谓世事难料,没有想到,我和悦然的约定,竟是如此的曲折艰难。
2004年春天,我插队时的房东闰月子,带孙女来太原看病。闰月子告诉我,邸家河附近的山上现在发现了一个大煤矿,已经有公司花了上亿的投资,钻探、开发、修建厂房,邸家河说不定很快也会搬迁了。我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悦然,我说,悦然你能不能去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要很快回去看看邸家河的。悦然立刻从网上回信,有几分悲壮地宣布说:在死之前,我一定要去邸家河看看!
于是,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吕梁山之行的准备。
2004年8月底我和悦然终于在北京汇合,陪他去了东四史家胡同,看他当年住过的老宅。随后,又和台北来的陈文芬女士汇合。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曲折和等待之后8月28日下午,夕阳斜照的时分,满车泥浆的我们终于走进邸家河,终于在村口看见了那棵被我说过无数次,也写过无数次的老神树。十五年前的那个约定,终于在这一刻梦想成真。这棵被老君坪的山泉滋养的老杨树,得天独厚,长了足有半间屋子那么粗,四五层楼房那么高,枝繁叶茂,浓荫匝地,苍老的树皮一道一道翻裂开来,像是被犁铧翻耕过的土地,不知把多少岁月沉淀在它苍老的皱纹里,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活了几百几千年。
闰月子早已经为我们专门打扫了一孔窑洞,准备了干净被褥,还特意用蓝色的花格塑料布围出一道漂亮的墙裙。我跟乡亲们开玩笑说,咱们邸家河三千年,除了见过日本鬼子之外,这是第一次看见一个洋人。其实,除了老神树而外,小小的一个山村,没有任何可供旅游者“奇观”的风景。空间被村东村西两只石头狮子把守,时间只剩下一块记录重修庙宇的石碑,当年的知青宿舍已经废弃,门窗都是暗影憧憧的黑洞,院子里、屋顶上蒿草横生……
在来之前,悦然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由他来做东,请邸家河全村的男女老少打牙祭。这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悦然从刚刚得到的《另一种乡愁》的版税里拿出三千块,交给闰月子、平安父子俩去操办。买酒,买肉,买菜,炸鱼,炖鸡,蒸馍。从饭店里租来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闰月子依照老规矩,前一晚挨家挨户去问请。村里的女人男人纷纷来帮忙。平安还专门租来一套音响,大唱梆子戏。请来神锁当大厨,开出菜谱,八个凉盘,十个热菜,一道汤。8月30号,农历七月十五那一天中午,艳阳高照,邸家河全村男女老少,加上南耀村闻讯赶来的乡亲,总共一百来口人,在平安家的小院里办起一场地道的乡村筵席。最后,连霉霉那个又傻又哑的媳妇也正正经经坐到席面上来。满院子的欢声笑语,满院子的举杯相庆。如今邸家河的生活比我们插队的时候强似百倍,通了电,有了电话、电视,甚至每家的院子里还装上了自来水。可是,新的困难也来了,随着煤矿公司的大举推进,他们和一些掌权的干部互相勾结,巧取豪夺,强占土地,黑了心的坑害农民,已经引发了农民集体上访。压迫和剥夺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没顶而来。寂静的山林早已填满了欲望和恐怖。乡亲们世世代代地渴望着改变自己贫困的命运,可改变所带来的这一切却又让他们始料不及。看着这满院子熟悉的笑脸,不由人感慨万端:所谓黄了谷子,红了高粱,转眼就是几十年,“历史”这两个大字,常常是和这些普通人无关的。如果不是和这些窑洞里的劳动者生死与共、相濡以沫,你永远也体会不出在那些憨厚笑脸背后的生命深度。
那天夜里格外晴朗,稀疏的云团之间是柔和明朗的月亮,整个山谷一片迷蒙的银光。睡到凌晨四点的时候起来去厕所,推开窑门来到院子里的一瞬间,我还是被眼前看过了无数遍的景色惊呆了:银盆似的大月亮静静地沉落在西山凹里,天上只剩下几颗疏朗的星星,东边的启明星像一滴闪光的冷泪幽幽地挂在墨黑如渊的天幕上。四野无声,只有我自己轻轻的喘息。
8月31号的早晨下了几滴湿地皮的小雨。为了保险起见,早饭之后,闰月子和平安还是开着他们的三轮农用车,带上铁锨,为我们护航送行。一直到翻过豹梁,看见山谷下面河底镇那边的焦炭厂了,闰月子他们才和我们告别。站在半山坡上,地老天荒之中悦然说,来,再抽最后一支烟。很快,烟抽完了。大家拍拍肩膀,各自上车。闰月子和平安一直站在路旁等着我们先走。一转身,眼前只剩下一弯又一弯的山路
三天很短,一闪而过。
六年很短,一闪而过。
十五年的时间也很短,也一闪而过。
从我插队第一天来到吕梁山至今已经三十五年,还是很短,还是一闪而过。年过半百,才懂得人生苦短。在这一闪而过的时间和人生里,吕梁山却成为永世难忘的记忆。先是我的记忆。后来又成为瑞典人马悦然的记忆。
西元2004年12月11日午夜写,
2005年3月30日改于太原,
2013年4月27日修订于北京
走廊里的肖像
经过多年的写作和翻译,马悦然教授的《我的老师高本汉》的中文版终于出版了,译者是著名的翻译家李之义先生。看完这部三百多页的传记,我不由得想起另外一本书。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大摊减价处理的书堆里翻出一本叫做《庚子西狩丛谈》的旧书,繁体字,竖排版,记忆中毛笔手写的馆阁体书名,和那个又黄又黑的旧封面很相衬。书是口述记录,口述者叫吴永,曾任直隶省延庆州怀来县知县,是当年打败太平军救了大清朝的功臣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讲述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反洋扶清”失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的亲身经历。当年救了满清朝廷,一心盼着大清朝中兴的曾国藩绝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孙女婿有幸面见龙颜的时候,当今皇上和太后竟然是一副村夫村妇的装束,为了讨一碗粥吃而哭得泪水涟涟。吴永因为迎驾服侍有功,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和信任,从怀来县一路随扈西行,这本书记录的就是他西行路上的种种亲历亲见。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在被人可耻地打败逃跑的时候,还可以更可耻地把逃跑叫做“西狩”。
“西狩”的大清朝廷一直向西,“狩”到了西安,才心惊肉跳地定住神喘过一口气来。此后,打了败仗的大清国,只好在列强的枪口之下,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才算把“庚子之乱”摆平。痛定思痛,垂帘听政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终于明白,祖宗的旧制、旧法是救不了命的,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也是救不了命的。尽管十分的不情愿,尽管此前她囚禁了力图变法的光绪皇帝,杀了戊戌变法的六君子,到头来,慈禧太后被逼无奈还是只好走上革新变法的路。于是才有了兴新学、废科举、办实业、修铁路、开银行,讨论君主立宪,等等一系列变革举措。于是,才有了山西大学堂,才有了一个二十二岁的瑞典人跨洋越海万里迢迢来到山西,开始了对中国北方方言的调查,并从此走向了他学术生涯的里程碑――《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国有句古训:造化弄人。历史的原因和结果常常会南辕北辙,出人意料得让你目瞪口呆。
在山西大学文学院主楼的走廊里挂着一排大幅的肖像照片,照片上的人都是自山西大学创建以来,在中文系曾经任教的著名学者,都是些高山仰止的人物:张籁,郭象如,黄侃,李亮工,常赞春……因为时间久远,许多照片边际模糊,黑白两色也早已褪变成陈旧的灰黄。在这一排中国宿儒的肖像里,有一个洋人分外显眼,照片下边有一句简洁的注语:
高本汉(1889-1978),瑞典人,国际著名汉学家,曾任山西大学堂中斋语言学教习,著有《中国音韵学研究》等专著十余种。
在这不到五十个字的注解里面,“山西大学堂中斋语言学教习”这句话,如果不作一点解释,现在的人看了会不大明白。山西大学创建于1902年,创建之初叫做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一起成为中国三所最早创建的公立现代大学。山西大学堂创建之初,分中学专斋,西学专斋,简称中斋、西斋。西斋的办学经费是庚子事变后,山西省应当付给耶稣教会山西教民的赔款,总计白银五十万两。(另外付给天主教会的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不在此列。)当时的山西巡抚岑春煊邀请上海广学会总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山西,帮助处理这笔教案赔款。李提摩太提出建议,这五十万两银子分十年付清,交由他来全权掌管,不用做赔款,而是全部用来创办一所大学,并同时创办一所译书院。后来经过岑春煊的代理人和李提摩太反复艰难的谈判协商,最终决定,李提摩太提议建立的“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西斋,西斋的教材、教学、学制、管理、教员聘用、财务开支等等一切事物均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并由他本人担任西斋总理。十年之后,西斋的校舍、器材、书籍、用具全部无偿转交山西地方当局。而当时大学堂的教师无论中斋、西斋,都称做“教习”,并无教授、讲师、助教的区分。至今太原师范学院侯家巷校区内还保留了山西大学堂的主楼,楼内的墙壁上还嵌有“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教职员题名碑”,在这面宣统三年凿刻的石碑上,李提摩太的全称是“英国道学博士文学翰林西斋总理李提摩太”,而在正式公文中,他的全称是“钦赐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三代正一品封典英国道学博士文学翰林西斋总理李提摩太”。
在经过艰苦反复的谈判之后,《山西大学堂创办西斋合同二十三条》 终于正式签约。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下午(西元1902年6月9日),岑春煊在巡抚衙门设宴庆贺,并为李提摩太饯行。根据记载,那天宴会的菜单如下:一品燕菜,青豆油鸡,五香炸鸽子,鸡粥扒鱼翅,洋磨广肚,烧烤鸭子,白枝竹笋,炸熘板鱼,洋鲜蜜桃,茄梨笋汤,洋鲍鱼汤,烧烤方肉。如此丰盛的宴会,岑春煊和地方官员们却不吃菜肴只吃水果,因为其时山西大旱,巡抚衙门颁布告示要民众节制饮食以度灾荒,为此官员们要与民同苦以身作则。时间久远,邈不可见,我们已经无从看到席间的彬彬揖让,也无从闻到珍馐佳肴的香味了。可百年之前的当事者们所开创的事业至今犹在眼前。
回身思量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高本汉当年能够来到山西大学堂担任教习的機会,就是从那次宴会之后开始的。
马悦然教授在传记中记述,高本汉1910年底到达太原,1911年1月9日正式和山西大学堂签订合同,“每周上22小时法文、德文和英文课,一个月工资170两白银。”十个月后,高本汉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离开山西,转道北京,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返回瑞典。
高本汉在这一时期写给家人和老师的信里,说得最多的就是他怎样不辞艰险骑着骡子到处去作方言的调查研究,他来中国不是为了当个教书匠,而是要雄心勃勃地开展他的语言学研究。说白了,他是要借庙成佛。四年后他提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音韵学研究》。正如他的老师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教授所说的,“当这部作品问世时,高本汉将在汉学研究领域里占有一个极为荣耀的地位。”1940年三位最负盛名的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翻译出版了《中国音韵学》。罗常培先生评价说,“这部书不但在外国人研究中国音韵学的论著里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就是在我们自己所做的音韵学通论中也算是一部空前的伟著……”
1978年高本汉教授以89岁高龄辞世。这位誉满天下的学者可能并不知道,在遥远的中国,在他曾经执教过的山西大学,人们把他的肖像高高地挂在教学大楼的走廊里,莘莘学子以他的身影为标志,激励自己在苦学的道路上一代又一代地跋涉攀登。
应当感谢马悦然教授为他的老师写了这本翔实的传记,因此让我们可以在那一句简洁的注语后面,不止看到一位杰出的学者,也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2009年5月9日,于太原,草莽屋
九月寻踪
一块简陋的路牌孤零零地举着胳膊站在岔道口上,一眨眼,就从平坦的柏油路挤上了坑坑洼洼的土路。宽阔辽远的群山之间,这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一路向上渐行渐远,细如游丝,终于挣断了线,好像它不是淹没在荒远的山顶上,而是淹没在幽深冷寂的蓝天里。游客如织、寺院林立的台怀镇转眼落在了身后,热闹和喧嚣也像是被突然浇灭的篝火。群山无语,只有漫山遍野的松树,和它们重叠的塔形树冠,静穆地站在透彻的阳光里。我们要去的吉祥寺就在土路的尽头,那个地方叫清凉桥。清凉桥地处五台山偏僻的台中,离台怀镇二十多公里,因为路远,来五台山游访的客人很少有人能去清凉桥的。我们不辞劳顿赶去清凉桥是为了拜访一位僧人,准确地说是要去拜访一位僧人的灵塔,这位僧人的法号叫能海。能海法师是悦然的忘年交。
1990年秋天第一次和悦然见面,就听他说起过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高本汉,一个就是能海。高本汉教授是悦然的汉学导师,而放下军刀立地成佛的能海法师是悦然的忘年之交。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人居然都和山西有着极深的渊源。高本汉教授1910年底来到当时的山西大学堂任西斋语言学教习,直到辛亥革命爆发离开中国,取道西伯利亚大铁路回到瑞典。正是在山西教学期间,高本汉教授骑着毛驴深入实地做艰苦细致的方言调查,随后写出了奠定他学术地位也极负盛名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至今,在山西大学文学院主楼的走廊里还悬挂着高本汉教授的大幅照片。写出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的高本汉是和张籁、郭象如、黄侃、李亮工、常赞春这样一些高山仰止的宿儒一起比肩而立的。2006年暑假期间,悦然为他自己撰写的《我的老师高本汉》的中文版翻译工作来到北京,和翻译者李之义教授一起校对译文,到9月工作告一段落,悦然和文芬一起来到太原在我家里小驻,休息数日。临来之前,悦然在电话里特别说明他们自己承担这次的费用,并且再三强调一不要见官员尤其是作协的官员,二不要见记者,不要有任何采访,只想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天。我问悦然,那你们在山西想看看什么呢?悦然说,想看看他的老师高本汉工作过的地方,再有,就是想去五台山,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能海法师的踪迹。于是,我们先去山西大学文学院主楼拜见了高本汉教授的照片;随后又去了蒋韵的母校――太原师范学院侯家巷校区,1902年创办的山西大学堂就在侯家巷,一些残存的中西合璧的砖构建筑历经百年依然如故,楼内的墙壁上还嵌有宣統三年凿刻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教职员题名碑”。可惜,能供勘察的实在有限,只用一个上午就看完了所有的内容。悦然意犹未尽,他还带来一幅当年高本汉教授拍摄的老照片,是一座古建筑的侧影,飞檐翘壁,廊柱依稀。我们查遍资料,到处打听,可还是无法找到它的任何线索。所有曾经巍峨矗立过的真实,最终,都在时间的河水里浸泡成了边际模糊的老照片,变成了无法还原的寻找。
带着这样的遗憾我们来到五台山,希望能和悦然一起寻找到能海法师的踪迹。悦然说他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认识能海法师的,能海在出家之前是四川军阀部队里的团长,后来以在家居士身份来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时决意出家,回川后他脱下军装,遣散家人,放弃一切财产、名分,两度进藏求师修行,抗战期间曾在成都近慈寺创建金刚道场,弘法利生,一时轰动西南。到了1953年,能海法师又返回五台山,专心选择了偏远荒芜的清凉桥吉祥寺做根本道场,率领众僧翻修屋舍,开荒种地,设坛开讲《四分律根本含》。最终,能海法师在“文革”劫难中坐化而去远离苦海。
在此之前悦然已经知道能海法师早已辞世。我岳父有一帧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五台山广济茅棚和能海法师的珍贵合影,据说这张照片成为能海法师在世期间所能找到的最后影像。五台山的僧人为了给能海法师塑像,还曾专门派人来借去照片当作参照的摹本。这次我们为了方便寻访,又拜托岳父专门从太原崇善寺住持的手上拿到一封介绍信说明原委,希望能得到五台山寺院僧人的帮助。在五台山的寺院里,能海法师的名字如雷贯耳,他被僧人们尊称为老上师。几经交涉,我们被领进能海法师的事迹陈列室,陈列室里除了能海法师的金身塑像而外,只有很少的几张照片,和附在照片下面的简短的说明文字,除此而外,再无一件实物,再无其它记录。在此岸的苦海里真实地度过传奇一生的能海法师,悦然曾经的忘年之交,也正眼睁睁地在我们的面前变成一种难以还原的寻找。可能是看出了我们难掩的不够满足和遗憾,讲解的僧人说,老上师的新灵塔建成不久,就设在清凉桥吉祥寺院内,灵塔上还有赵朴初居士题写的铭文。
于是,为了还原一个曾经的真实,为了印证一段刻骨的情谊,我们再次上路,直奔清凉桥吉祥寺。当我们站在能海法师白色的灵塔面前时,碧蓝的天空纤尘不染,九月的斜阳慈祥地铺满了院落,浩荡的山风把塔身上的经幡刮得翻飞不止,寺院外面的山坡上站满了松林,重重叠叠的塔形树冠肃穆地矗立在透澈的阳光里,就像是沉在水底的倒影……亦真亦幻。
忽然,有啄木鸟“得得”的敲打声从那片深沉的倒影里传出来……
2013年5月3日,
为悦然九十岁寿辰 记于北京
天上一颗星
——怀念悦然
十月十八号早上起床后,习惯性地打开手机,猛然看到文芬发来的微信:悦然十七号下午三点半钟,坐在家里餐桌旁的椅子上安然去世了。一时间,难以置信的冲动让脑子里一片空白……下意识地,为了证明自己的难以置信,我马上翻看之前的微信记录:九月二十一号文芬来信,讲述他们一年之内的四次病危又转危为安的经历,还在讲悦然难以愈合的脚伤一只已经好转。随后还有悦然坐在轮椅上的照片,人瘦了很多,脸上还是那个熟悉的笑容。文芬说,只要身体允许,悦然就会坐在电脑前工作,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回答说,相信他能给我们一个奇迹。为了给他们鼓劲,我还专门找出2006年6月我和蒋韵陪他们两人同上五台山,寻访能海法师的几张照片。静穆的寺庙背后,远山、森林、蓝天、白云,一派澄澈,浩荡的山风吹乱了我们的头发和衣角。一切恍如昨日。
为什么不呢?既然九十三岁的悦然还能完成《庄子》的翻译,为什么九十五岁就不能继续下去呢?
可是,不能。真的不能了。永远不能了。
文芬说,悦然吃了两口麦片加牛奶,说了一句不舒服,十秒钟之内就坐在椅子上升天了……
从1986年6月悦然宁祖给我第一次写信,商讨翻译《厚土》,到2019年10月17日,足足三十三年的友情,悦然撒手而去。
不知为什么,眼前忽然闪现出悦然在邸家河捧起冰凉的泉水赤膊盥洗的豪爽场面。那是一个经历了十五年等待和挫折的约定。从1989年初一直等到2004年8月28日下午,悦然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来到吕梁山当年我插队六年的邸家河村。第二天一早,从闰月子家的窑洞里醒来,悦然舀了半盆大缸里的泉水,就在窑洞前的台阶上脱光了上衣赤膊而浴,哗啦哗啦撩起的冷水在晨光里晶莹璀璨地飞溅,顺着他健壮的胳膊又哗啦哗啦地流回到盆里,闰月子和家人站在一边喊,嗨呀,水太凉!不敢着了凉!不敢洗啦!嗨呀,看这老汉硬么!这哪像个八十的?比个十八的后生还莽撞!文芬站在一旁笑而不语。闰月子和他的家人不知道也不打算知道,这个八十岁的老汉是个汉学家,还是个院士和教授。他们只是惊讶这个从外国来的洋人,比中国人还会说中国话。居然还和闰月子是本家,都姓马。闰月子本名马振声。
在邸家河住了三天,悦然还出钱请全村老少打牙祭,办了一场地道的乡村酒席。總算圆了他的一大心愿。总算圆了他的一个梦。一个瑞典人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而走进了中国,因为翻译一本小说,而记住了吕梁山,记住了千万里外那些原本和他毫无关联的山民们。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像悦然这样坐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的亲人身边离开世界,是寿终正寝。和那些浑身被插满各种管子,在冷冰冰的重症监护室去世的人相比,九十五岁能在自己家里寿终正寝,应当说是一种福气。理性告诉我,这是活着的人面对无可抗拒的死亡最终也最无奈的自我安慰。这也是每一个人最终无可逃脱的面对。
面对永远的诀别,面对永逝无回,面对永无回答,面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面对永远无法填满的黑暗,所有的安慰就像是撒进大海的沙子。可是,你必须接受大海,必须接受沙子,你还必须接受自己给黑暗的无用的解释。
一直呆举着的手机瞬间黑屏了,就像世界突然在眼前中断。耳朵里忽然听到外孙女无比兴奋的尖叫声:星星!星星!爷爷――爷爷!快来看看星星呀!
我朝着孩子叫喊的房间走进去,原来她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用手电筒照亮了她自己做的星光桶,手电的光芒从桶壁的星形空当里折射到黑暗的墙壁上,于是,黑暗中就亮起无数灿烂的星光。面对这么多自己造出来的星星,让这个五岁的小女孩惊喜、兴奋,几近发狂。
心里顿时想起那个代代相传的民谣: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接着,又想起,以后如果想悦然了,如果再想看看他,再想和老朋友聊聊天,就可以抬起头来看看满天星斗,在天上,在广阔无垠的黑夜里,一定会有一颗星星是他,是悦然。
外孙女还在不停地尖叫,孩子停不下她的惊喜和兴奋。她没有看见,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身后那个满头苍苍的人忽然湿润了眼睛。
2019年10月19日于北京
12月2日改定
附录:李锐、蒋韵悼念马悦然所撰挽
联及马悦然夫人陈文芬致李锐信
李锐记:无法去参加悦然的葬礼了。只能用这副挽联表达我们无以言表的遗憾和悲伤。海天万里,渺不可见。在北极附近寒冷黑暗的漫漫长夜之间,此时此刻,遵照悦然生前的意愿,他的葬礼正在社区附近的小教堂举行,他的棺木将在亲友的陪伴下,从小教堂走向墓地;从最后的可见一面走向永无可见的诀别。祷告声起……心痛如割……
2019年11月16日拟联于北京郊外家中。
2019年11月21日 ,斯德哥尔摩时间上午11点,北京时间18点,悦然葬礼之时发表于网上。
(我们拟定挽联后,邀请画家朋友怀一先生执墨书写,并拼图排版,特此致谢。)
亲爱的李锐:
我的丈夫马悦然已于十月十七日下午三点半整在家仙逝,享年九十五。
悦然自从三年前害病,很少跟朋友联络,他珍惜最后在书桌前奋斗的时光,努力读书,翻译 《庄子》 。他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活著死”的生存状态,在家里圆寂而去,我们的大孙子、曾孙女得以搭乘当天的夜车从南方到首都,在第二天早晨到我的公寓全家人喝了咖啡,送悦然离家时,太阳出来。我们遵从中国的古礼,请四十岁的大孙子打了一把黑伞护送爷爷的远行。
他生前的愿望是在我们家族常去的地区小教堂,已故亡妻宁祖的葬礼举行的相同的场地,只有六十席的小教堂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但两个儿子(老三已于三年前过世)愿意更多的朋友前来送别,刊登了广告,葬礼在星期四,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最后登记有一百三十人。
我们家庭五世同堂包括姻亲约有五十人。登记参加的朋友多为悦然的老学生、学院同事以及在地的中国友人。牧师魏安妮女士,是悦然的学生,曾经在瑞典驻北京大使馆担任文化秘书,她是我们家庭珍贵的友人。
悦然三年前订立遗嘱为自己写下讣闻铭句,这句话非常不好翻译:“恩赐干活,日燃光芒。”我只能勉强这么翻。我犹记得他当年写这句话,跟我分享时开心自得的样子。
悦然最敬爱他的老师高本汉。
悦然过世,我的悲伤与痛苦难以言喻。他以一生用功读书的方式来怀念老师,也为我的余生的前途指出了方向。
谨此。祈安
文芬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