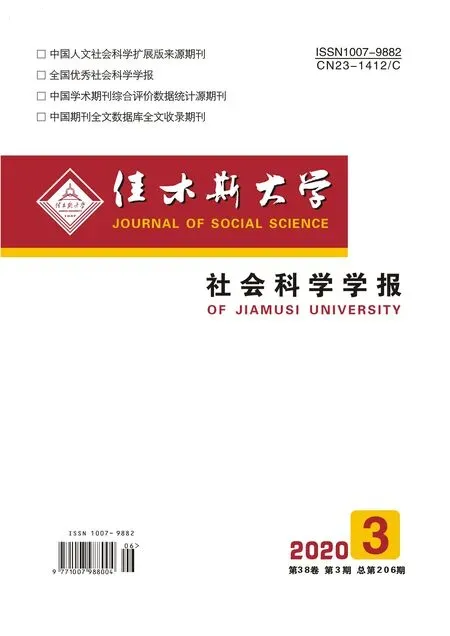《谕中原檄》的文体意识*
2020-02-10任竞泽
陈 墉,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作为一种官方文书,檄文凭借其独有的文体特色,在两军交战前夕,对震慑敌方军队、提升我军士气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檄之文章,早已有之。但真正将其作为一种特定的文本,则要追溯到战国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暨乎战国,始称为檄。”[1]188吴讷也在《文章辨体序说》中谈到:“春秋时, 祭公谋父称文告之辞,即檄之本始。至战国张仪为檄告楚相,其名始著。”[2]40纵观檄文发展脉络,我们不难看出,檄文于魏晋南北朝时发展至巅峰,自此之后,便成衰落之势。《谕中原檄》是明代一篇重要的檄文作品,相传由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为吴王朱元璋所作。相比于明代其他檄文作品,诸如朱元璋的《讨张士诚檄文》、《谕温台庆元人民人檄》,张苍水的《海师恢复镇江一路檄》等,《谕中原檄》格局更为宽广,内容更加充实,文学性也相对出彩。全文近千字,洋洋洒洒,颇具魏晋檄文之风。本文以《文心雕龙·檄移》篇为楷模,对《谕中原檄》进行文体意义上的探究,以求窥见檄文文体意识的继承与超越。
一、“恭行天罚”与“叙彼苛虐”
“夫兵以定乱,莫敢自专,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1]190意为军队是用来平定祸乱的,没有哪个人能够独自专断。天子亲临战场,即为“恭行天罚”,也就是十分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恭行天罚”肇自《尚书·甘誓》,亦为执行天命之意。《檄移》篇对于“恭行天罚”的强调,也体现出古代战争中双方对于交战理由是否名正言顺的重视。檄文所面向的群体无论是敌是友,归根到底都是士兵民众。而对于自身出战的具有合理性的暗示,则能最大限度地唤醒人们对于正义之师的渴望。隗嚣在《移檄告郡国》中细数王莽逆天、地、人三等大罪,激起人神共愤,故“上帝哀矜,降罚于莽”[3]518,以证己方出兵为正。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中,先数曹操祖父曹腾及父亲曹嵩之恶行,继而以袁绍为正,清点曹操“败法乱纪”、“行桀虏之态”、“贪残酷烈”等罪状,鼓励众将“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4]2584。钟会于《移蜀将吏士民檄》中言太祖曹操“拨乱反正”,斥益州刘备“中更背违”,以正统姿态广布“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窥祸于未萌”之论,迫使民众“详择利害,自求多福”[5]788-789。骆宾王在《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指责武则天“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所以“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6]484。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谕中原檄》是为吴王朱元璋在应天府出兵北伐时所颁,其目的不外乎叙述元朝统治之无理,取得人民的认同。文中对于“恭行天罚”的表述也是十分明晰的:开篇即言:“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7]87看似并不像其他檄文那样直截了当进行抨击,但却是悄然留下伏笔。接着论述元朝皇帝与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之事,指出这样败坏纲常的行径“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7]87。最后引出结论:“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7]88虽然造成元朝失去民心、天天百姓纷纷起兵造反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元朝当朝官员的 “失道”造成的,但为强调己方出兵的正义性所在,仍旧将局势的关捩指向了“天弃之”。其次,在文章第二段中,作者言“天运循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强调百姓是如何战战兢兢,对目前将要讨伐的对象则以摧枯拉朽之势沉痛批评,指出他们是“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7]88。实际上,在强调敌方是“生民之巨害”的同时,已经奠定了自己是“华夏之主”的地位。在下一段中,作者更近一步,直言“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7]88,意即我恭敬地顺承天命,不敢独自过安定的生活,现在决定要发兵北伐驱逐元朝朝廷,于生灵涂炭中拯救中原万千百姓,从而恢复汉官的威严,重整河山。在此,作者已经接过“恭行天罚”这把尚方宝剑,真正表明了自己是“替天行道”,“行非常之事”。最后,在谈到蒙古、色目等其他少数民族时,说道:“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7]88可以看出,从最初的以旁观者的身份来控诉元朝统治是“失天命”,到借“天命”之名来“恭行天罚”,到最后完全入主“天命”的角色,作者不断移行换位,最终完成了角色的转换,显示了自己北伐的正义性。
此外,在《檄移》篇中,刘勰对檄文的文体特点表述了自己的态度:“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角权势。”[1]191-192檄文的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即要么讲述我方的美好昌明,要么指责敌方的暴政苛虐,用以明确天意,审视人事,比较强弱,衡量权势。这便是用对比的手法来凸显交战双方的或正或邪,并放大来看,以此呈现出我方军队行使“天罚”的合理性和决绝性。而刘勰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总结,与各檄文名篇不无关系:《移檄告郡国》中怒斥王莽的“悖道逆理”;陈琳《为袁绍檄豫州》述曹操“豺狼野心”;钟会《移蜀将吏士民檄》更是一一训斥刘备、诸葛孔明、姜伯等,以朝廷之德对比百姓之失,如云:“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兴兵朔野。困踬冀徐之郊,制命绍布之手。太祖拯而济之,兴隆大好,中更背违,弃同即异。诸葛孔明仍规秦川,姜伯约屡出陇右,劳动我边境,侵扰我氐羌。”[5]788-789可见,“叙彼苛虐”是檄文写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谕中原檄》中对元朝统治者的指责是甚为显著的。首先,是对元朝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的批评。有“大德废长立幼”,有“泰定以臣弑君”,有“天历以弟酖兄”,而“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是“上下相习”所致,“恬不为怪”。这还未完,他们的后代沉沦荒废,“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7]88,宰相专权,御史台等监察部门专做挟私报复之事,官吏刻毒暴虐,终于“人心叛离,天下兵起”[7]88。孔子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是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纲常不备,则朝政废乱。这是从上层的朝政君臣的角度来说的。其次,是对“胡虏禽兽之名”为美称的“雄”,也就是驻守边疆的将士们的指责。其一是“河洛之徒”王保保,他“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7]88,假借元朝廷的名义,满足自己割据一方的私心,拥兵自重,要挟皇帝。“凭陵跋扈,遥制朝权”,凭借着自己占据的大量土地而飞扬跋扈,甚是嚣张,远远地控制了元朝廷。其二是“关陕之人”李思齐、张思道、孔兴和脱列伯,他们虽然“众少力微”,但却“阻兵据险,贿诱名爵”,把仅有的军队驻扎在险要的关隘,对朝廷威逼利诱,贿赂官员,其目的不外“志在养力,以俟衅隙”,积蓄自己的力量,待时机成熟时向中原进发,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两类人“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也就是朝廷所派去剿灭反叛军的。等到清剿完成,“兵权已得,志骄气盈”,便再也没有尊重朝廷、效命皇帝、保护臣民的意愿了,反而互相吞噬,成为“生民之巨害”。这是从下层的军队将士的层面来说的。一上一下,标明元朝这棵参天大树从内到外尽然腐烂。虽无平民百姓之描绘,但一切皆在不言中。
二、“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与晓谕臣民
《檄移》篇云:“植义扬辞,务在刚健。”[1]192是言檄文在安排行文写作时确立意义,发扬文辞务必要刚强劲健,直击心灵。郭英德先生云:“不同的文本语境要求选择和运用不同的语词、语法、语调,形成自身适用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由此而构成一种文体特定的语体。”[8]9檄文具有实用性与文学性的特点,而其文学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语言方面的特色。如同纵横家恣肆夸张的言论一般,檄文的语言运用也要达到一种震慑人心、壮我军威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运用不同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檄文也能起到晓谕臣民,平定民心的效果。这在历来的檄文篇章之中都有涉及,《谕中原檄》也不例外。
《檄移》篇讲:“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1]192意为用诡诈的话来宣传自己的意图,用光彩的言语来宣扬自己的说法。刘勰此言确有可资借鉴之处。人们常说,兵不厌诈。作为开拔前的军事文书,檄文就如同外交辞令般,厉则有威震全军之势,弱则长他人之气。适当的夸张能够极大地提升将士的自信心,而音调的铿锵和谐,也能令这一语言艺术最大限度地发挥价值。在谈及自身处境时,作者先言本是淮西贫苦百姓出身,因为天下大乱,所以被众人推选出来,率大军渡江,占领金陵城,得长江天险之庇护,至今已十三年。继而顺承:“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7]88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如作者所言,向西至四川,东至海边,南抵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北延淮南淮北,直至整个江苏都纳入了朱元璋的版图之中。所以作者放话,“奄及南方,尽为我有”。然而根据考证,事实并非如此。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平定陈友定,占据福建。洪武四年(1371年)明升投降,朱元璋封其为归义侯,始收重庆。从时间线来说,《谕中原檄》的创作时间为吴元年(1367年),此时明军尚未占据整个南方。作者这样写,实为夸大之举。究其目的,在于展现明军的实力强大,俨然成破军之势,虽未奄及整个南方,但言下之意,“尽为我有”之势指日可待。于无形中将明军表现得势如破竹,大有一举攻克全国之势。可以说,这是“谲诡以驰旨”的重要体现。
此外,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也毫不吝啬地展示了“炜晔以腾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檄文中,已经出现了檄文语言由散体向骈体转化的趋向。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骈散结合,显示出明显的骈化倾向。至两晋南北朝时,骈化色彩已经相当浓厚。不可否认,檄文骈化的形式让本身作为军事文书的檄文有了一定的文学色彩,但随着时代和文学自身的共同进步,到了《谕中原檄》,已经逐渐摆脱了骈文的模式。虽不如骈文工整,却也有其独特的韵致。作者于文中大量使用排比,使得文章气势雄健,洒脱豪迈。在论述正统道义时,云:“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7]88站在暴政的对立面,更能强化正义的角色。在谈到控制区的情况时,言:“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7]88百姓生活渐渐安定,粮草渐渐充足,军队渐渐精锐,将士们手握弓箭,注视中原的万千百姓,为长久以来没有一个皇帝和朝廷愿意真正担负起管理保护中原的职责而深感愧疚。一连三个“稍”,看似平平描述政权之初生,其实意下透露出收复中原的急切心情。三个“稍”连用,百姓生活之希望,国家统一之渴望,全都表露出来,可谓一字顶千钧。
至于晓谕臣民这一功用,在历代檄文名篇中都有涉及。《檄移》篇云:“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1]192《文心雕龙》将“檄”与“移”共称,可见在刘勰的视野下,作为晓谕臣民的“移”也是檄文篇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行文逻辑来讲,在发布讨敌檄文之后,对平常百姓加以晓谕也是情理之中。隗嚣在《移檄告郡国》后强调“有不从命,武军平之”,气势凌人,大有横扫六合之势。陈琳在《檄吴将校部曲》中为了让檄文达到孤立孙权的效果,宣扬己方“开弘旷荡,重惜民命”,而后“诛在一人,与众无忌”。钟会在《檄蜀文》中为百姓描绘美好愿景来达到“谕”的效果:“百姓士民,安堵乐业,农不易亩,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求安之计,岂不美与?”[5]788-789如果说之前的檄文中,晓谕臣民的说法只是为了锦上添花,增强气势,那么到了《谕中原檄》,晓谕已经成为作者叙述的重要环节了:“虑民人未知,反为我雠,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7]88作者已经明确强调,为了防止百姓混乱之中“反为我雠”,所以要事先讲清楚。而一句“归我者永安与中华”,恰恰成为百姓心意转换的关键点,不仅能体现出己方军队的圣明正义,也在无形之中潜入百姓心中,给犹豫之人以方向,给坚定之人以信心。更为可贵的是,《谕中原檄》还注意到了团结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民。在最后一段,檄文曰:“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7]88作者是相当聪明的,此文一出,即表明蒙古、色目等“非华夏族类”的少数民族同中夏之人一样,都可成为我朝臣民,为那些“身在元朝心在明”的少数民族打开了一条道路,为明军出兵北伐减少了阻力。同时,这也可看出作者涉及到的“华夷之辨”的思想,这也是本篇檄文深厚内蕴的体现。
三、“华夷之辨”及其影响
如果说“恭行天罚”、“叙彼苛虐”、“植义扬辞,务在刚健”和晓谕臣民是对《文心雕龙·檄移》篇的继承,那么“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所体现出的华夷之辨,则是《谕中原檄》对檄文原有特点的超越。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天下之大防二,华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未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9]373关于华夷之辨的论述,古已有之,兹不具论。而在檄文中提到华夷之辨思想的,《谕中原檄》当为第一篇。《谕中原檄》曰:“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7]88国学大师钱穆言:“于易代之际,而正式提出中国夷狄之大辨者,今可考见,惟此一文。”[10]99在檄文中体现华夷之辨的现象并不常见,其原因在于,首先檄文的发展并不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朝代的更替而逐渐繁荣的,檄文自魏晋南北朝繁荣之后,便陷入了低潮期。这导致以宣战为主要方式的檄文并不能被广泛的运用并加以记录。其次便是国家政权的归属者问题。在最开始的檄文中,对于“夷”的指向性大多趋向于少数民族。而细数历朝历代,汉族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主要元素。这时的“华夷之辨”,便只针对中原以外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例如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中所用“蛮夷自擅”、“今奉币役至南夷”[11]3045都是指南方的诸民族。自元代蒙古族人占据中原以后,用“夷”来指代少数民族政权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对于华夷之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到了《谕中原檄》,文章便站在“驱逐胡虏”的立场,对于元朝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猛烈抨击。全篇充斥着“夷狄”、“北狄”、“胡虏”等词,又用“中国”、“中原”、“华夏”、“中华”、“中夏”等词划清与元朝旧党的界限,清清楚楚地展现“华”与“夷”的对立。
在同时期及以后的诸多檄文中,也有着许多同《谕中原檄》相似的“华夷之辨”。例如在明末张苍水的《海师恢复湛江一路檄》中,作者直言“天经地义,华夷之辨甚明”[12]245。作者在檄文中使用“东虏”一词指代满族入侵者。而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诸多檄文。由于这场政治运动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即清朝满族统治者,故而在檄文篇章中有大量的具有蔑视性、贬义性的词汇指代满族人。杨秀清在《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中有“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12]273-274之言,洪仁玕在《劝谕弃暗投明檄》中将杨秀清的说法拓展为“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12]297,另有“鞑妖之流毒我中华者如此”、“歼此丑夷”之言,其在《拟出师北伐檄文》中,亦有“尔等凡属华裔,悉是夏宗,皆系天堂子女,无非一脉弟昆”[12]314之言。悉数举例,皆为相似。而除了具有指代少数民族之外,“夷”在明代之后的檄文中,又增加了指代外国入侵者的含义。如清朝林则徐在《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中用“夷人”代表英国人,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窃外夷之绪”[13]191,此处之“夷”亦指向外国人。刘永福的《谕黑旗将士檄》用“法夷”来指代法国人。诸如此类,标明在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基础上,“夷”的意义外延有了新的扩张。即便如此,《谕中原檄》中发出的口号也成为了一个起点,以至于清末孙中山先生所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都可看作是《谕中原檄》的延伸。在孙中山先生提出口号后不久,龚春台还在《萍浏醴起义檄文》中再言“誓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以雪灭国之耻”[12]339。学者萧公权评价《谕中原檄》说:“此檄词旨激扬,实为二千年中创见之民族革命宣言,而亦中国最先表现之民族国家观念。”[14]499《谕中原檄》不仅在用词上大量使用“中国”、“中原”、“华夏”、“中华”、“中夏”等表示民族国家观念的词语,而且在思想上继承传统“华夷之辨”思想,为后代檄文乃至革命战争提供了新的方向指引。
然而,不论是宋濂还是王夫之,抑或是钱穆等,他们对于“华夷之辨”的强调都有着特定的时代环境。宋濂强调“华夷之辨”,是元明易代之际的时代需要;王夫之肯定“华夷之辨”,是以明清易代为前提;钱穆肯定“华夷之辨”,是以近代革命为背景。今天,我们身处和平的年代,生活于各民族统一团结的环境之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定位,我们应当领会的是“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7]88所体现出的各民族平等和睦的思想,充分发挥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而不是一昧地强调“华夷之辨”。
综上所述,《谕中原檄》作为明代为数不多的檄文,其行文构思仍旧保持了檄文一以贯之的文体特色。“恭行天罚”、“叙彼苛虐”、“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晓谕臣民等仍旧是其作为檄文不可或缺的要素体现。另一方面,正如王若虚所言:“定体则无,大体须有。”[15]427一种文体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历史环境的变迁及文体发展的,檄文本身也需要新鲜血液的输入,其对中华民族国家概念的强调、对“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内容的传承以及所体现出的民族团结和睦便成为了《谕中原檄》独具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