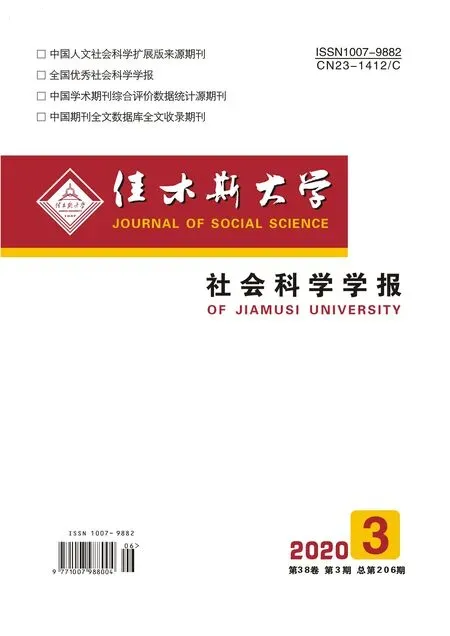经世致用、德主刑辅:左宗棠法律思想探寻*
2020-02-10谢时研
谢时研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号朴存、湘上农人,出生于湘阴县东乡左家塅(今金龙镇金龙村)。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职,封恪靖侯。左宗棠因平定太平天国运动、镇压陕甘回乱、收复新疆、洋务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而名垂青史,成为“同治中兴”的三大名臣之一,被梁启超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却又极富法治智慧,他将“经世致用”“德主刑辅”等法治理念融入军事、吏治和洋务运动,既实现了“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又稳定了当时统治秩序。然而,究竟左宗棠法律思想具有何种渊源,又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知识谱系?仍然值得我们今天予以探寻。
一、“经世致用”与“德主刑辅”的法治理念
学界专门研究左宗棠法律思想的成果非常少,目前仅有徐明的《论左宗棠的法律思想与实践》、华友根的《左宗棠的法律思想以及与曾、李比较研究》等少数几篇论文进行了研究。不过从现有文献来看,可用于左宗棠法律思想研究的素材还是非常之多,比如,《左文襄公全集》《左文襄公年谱》《清史稿》等文献资料。另外,还有一些传纪类著作,比如,戴慕贞的《左宗棠评传》、张振佩的《左宗棠传》、左景伊的《左宗棠传》等,也有部分内容涉及了左宗棠的法律思想。其中,从罗正钧的《左文襄公年谱》卷一,我们可以初略地了解其早期所受的教育情况。左宗棠五岁就熟读儒家经典,基本上是一个中国传统型的儒生。从十九岁起,受业于贺长龄之弟贺熙龄,贺熙龄“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1]8由此观之,左宗棠年轻时期所受儒学熏陶,无疑对其“德主刑辅”的法治理念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同时,他与陶澍、魏源、林则徐等一批“经世致用”学派的学者有着密切交往,并在当时掀起一股新的社会思潮。尽管受宋学的影响较深,但他并不满足于宋学的空疏,这种“经世致用”可以从左宗棠的笔端得以体现。1833年,左宗棠在第一次会试的答卷中写道:“夫穷经将以致用也,而或泥于章句训诂之学,捃摭遗义,苏索经馀,前人所弃,后复拾之,纵华辨之有馀,究身心之何补?或好为诡异凿空之论,影借旧闻,创为新学,古人所无,今故矫之,既隐怪之可伤,复源流之不辨。若是者博士赏之,纯儒羞之,曲学主之,至人辟之,职是之由也。”[2]406-407该文表明了他主张要以经术为治术,把为学与致治联系起来,讲求“实学”的价值取向。
然而,要想真正把握左宗棠在军事、吏治和洋务运动等领域的法律思想,必须把握贯穿其中的法治理念,这些理念涉及到一些本源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思考,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翻阅、吃透原始文献,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去体验,到去实地考察一番。或许左宗棠故居一些文化遗迹可以激起我们的灵感,把我们带入特定的历史时空,让我们有如同拨开历史的云雾之感。如此,我们才能感悟左宗棠法律思想生成背景,进而增进认识。
2018年寒冬的一天,我们驱车来到湘阴县樟树镇巡山村,即左宗棠的旧居“柳庄”所在地。据文献记载,1843年,左宗棠将在安化县执教陶澍之子陶桄所得积蓄约900两白银,在此购地70亩,建造了一座占地4亩多,有48间房屋的砖木住室。41岁之前的左宗棠在此隐居期间,长期泳于书籍之中,过着耕读的生活。
进入“柳庄”院内,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门联、字画,无论是“典藏阁”,还是庭院,我们注意到“天地正气”格外引人注目,尽管一时还没有过多思考其中缘由。后来,在左宗棠卧室里,我们在一块黄色的水牌上又看到了“天地正气”几个字。通过上面的文字介绍,才得知“天地正气”竟是左宗棠的座右铭。然而,为什么左宗棠对“天地正气”如此情有独钟,“天地正气”又表达了什么样的理想信念?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此处所说的浩然之气是由正义在内心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不是通过偶然的正义行为来获取它的。后来到了南宋时期,文天祥的《正气歌》拓展了正气的内涵,将天地之气赋予了高尚品德、坚贞气节,嫉恶如仇、维护正义和为民效力等人格化内涵。从此之后,天地正气作为一种在外的无形品德,体现了天地视万物平等一致的法则。天地正气作为一种“形而上”,以“民本”为旨归,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把经世致用、德主刑辅统合起来。左宗棠对于“天地正气”的信仰,难道是他崇尚文天祥的英雄气节?抑或他把文天祥视为自己的精神偶像。这些猜测虽然有点“八卦”,但左宗棠早期的志趣与信仰,无疑对后面的军事、吏治、洋务运动等方面法治实践产生重大作用。
二、“以法治军”与“抚剿结合”的军事战略
在左宗棠故居的堂屋右侧,我们发现墙壁上有几幅老照片,通过底下的文字介绍,才得知左宗棠同胡林翼、陶澍、林则徐、曾国藩等人之间有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说,胡林翼五次推荐左宗棠;他同陶澍是亲家关系;他与林则徐泛舟湘江,宴谈达曙。受这些人物“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左宗棠利用蛰居柳庄的十多年,潜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学识自有一番精进。左宗棠的读书境界,可从其一封家书得以窥见:“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2]9
左宗棠在柳庄,除了钻研地学、农学之外,还广泛涉猎军事、水利、荒政、田赋、盐政等领域。他体察人情,通晓治道,通观国事,关注边陲,形成了“置省开屯”、“万里输官稻”的筹边韬略。他后来的军事法治成就,与这段时期的“经世致用”理念密切相关。此外,深受“德刑”说的影响,左宗棠将“德主刑辅”理念应用到军事实践,将“德”阐释为“抚”,把“刑”与“剿”对应,运用“抚剿”的军事策略镇压农民起义,从而确立了“抚剿结合”的军事策略。在农民起义严重危及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时,他灵活运用剿抚策略,以“剿主抚辅”镇压太平军起义,以“剿抚兼施”镇压捻军起义,以“抚主剿辅”镇压回民起义,创造了军事史上奇迹。
左宗棠不仅善于运筹帷幄,而且十分擅长以法治军。1860年,左宗棠创立楚军时,就十分注重整肃楚军营纪。左宗棠说:“用兵之道,纪律为先;驭将之方,赏罚为要。”[3]542他制定了《楚军营制》,其中,“行军必禁”条规定:“凡是有犯奸抢烧杀的人,查明后立即斩首示众,决不宽恕。就是打牌、聚众赌博、吸鸦片、酗酒、行凶、嫖妓、私出兵营、拉帮结派、捏造谣言四处张贴之类的,以及敲诈勒索老百姓钱财、强抢老百姓船只、强买百姓财物的行为,都应当严格禁止。全军士兵,长夫的衣服,只准穿青、蓝两种颜色,不允许结拜哥老会、天地会等会,并且不准辫搭红线。凡是有违反此规定的,在查明真相后分别严惩。”“体恤勇夫”条规定:“凡是统领、营官、哨官,都要体恤士兵和长夫,如同家人。如果士兵、长夫有受伤、患病,营官、哨官、什长均应该照护,不得命令立即出营。如果因病重、伤重严重而危及生命,不得不出营救治,也应该派人服侍汤药。营官也应当斟酌犒赏,务必使生病、受伤的人不受亏苦。”“体恤百姓”条规定:“我军务必要体恤百姓,决不准搬百姓家门板子,不准拿老百姓家里桌子椅子、衣服、小菜、碗桶等东西。如军中有人不遵守规定的,由营官随时予以查办。”“买卖务宜公平”条规定:“营中购买的食物等所有物品,必须依照市场价公平购买。卖的人当然不能抬高时价,买的人也不得低钱强买。如果各勇士、买办有低价强买的行为,故意扰乱市场而滋生事端,经查明真相后,根据情节的虚实轻重分别予以惩处。”①此外,左宗棠还制定了《行军五禁》《车队事宜》《马队事宜》等制度,这些楚军军事制度都融入了“德主刑辅”的理念。
在评价左宗棠军事法治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左宗棠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时杀人不少,以及勾结外国势力,把它归结为一种“德主刑辅”有些不妥。对此,我们认为,历史事实需要辩证地看待,不可一叶障目。左宗棠在平定回变时,收编降众成为招抚回民的一种手段,其“抚剿结合”法律思想充分体现了“德主刑辅”的理念。1868年,左宗棠就如何安置回民降众问题提出:“安抚投降的人,应分三种情况区别对待。对于健壮的人,可以留下杀贼,让其建功赎罪;对于患有重病的人,应安置到老营,待战争结束后,分别资遣回家,发免死护照。如有愿意随军西征的,经挑选后可酌留,充任军中士兵、长夫。对于被抢的孩童,均应资遣回家,提供路费,决不允许各营隐藏,致使骨肉分离,这类孩童应尽早资遣回家。”②此外,为了训导回民降众,他发布的《谕降众示》指出:“现在你们已经诚心归顺,本大臣也诚心抚你。你们充当士兵之后,就视为本营士兵,从编队之日起,按照本军马步军营制发放口粮马干,一视同仁。决不准本营士兵抢劫你们财物,不准军中官员苛索无度,以示皇恩浩荡。你们如果有冤屈事情,允许你们请求统领、营官秉公处理,你们不必妄生疑虑恐惧。只是本大臣军律一向严厉,曾制定了《行军五禁》,士兵如有违犯,决不宽容。你们既然已经当了士兵,就应该遵守营规,如有违犯,将按照兵勇加等惩处。兵勇原本是平民投军,你们之前未立寸功,还是带罪之人,本来就不一样。你们现在应该反思,如何激发良心,更加和驯谨慎,以报再生之恩。”③可见,左宗棠大部分军事制度还是体现了“德主刑辅”理念,尤其从回民投楚制度来看,确实显得非常人性化。
三、“察吏”与“亲吏”统筹兼顾的吏治策略
在“柳庄”的短暂探寻,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一些文房四宝、农具、生活用品之类,从中很难发现法治元素的痕迹,毕竟此处是左宗棠前半生的主要活动场所。带着沉重的心情,在快要离开之时,柳庄售票处的那块寿匾再次映入眼帘。那是左宗棠七十岁寿庆收到其部将王德榜的一份特别礼物,寿匾上刻有“克家不私”几个字,也许这是对他其一生为官之道的最好诠释。虽然已经驱车远去,但左宗棠故居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沉思与遐想。为了获取更多有价值信息,当天下午我们又紧接着赶往湘阴县左宗棠文化园,期待在那里对“吏治”会有新的发现。
据了解,左宗棠文化园是为纪念左宗棠诞辰200周年而兴建的一座仿晚清园林式文化园林,包括左宗棠纪念馆、天地正气广场、左宗棠雕像、功德石柱、烽火台、年谱大道、诗联碑廊、场景人物浮雕等景点,配套建设了八甲古街、文星塔广场、南岳行宫、仰高书院等仿古建筑。在左宗棠纪念馆,我们得知65岁高龄的左宗棠主动请缨督师西征,一举歼灭阿古柏匪帮,逼迫沙俄交还伊犁,促成新疆建省。左宗棠时任封疆大臣和枢府大臣的20年,在整饬吏治方面所实施的“察吏”与“亲吏”策略,同样融入了“经世致用”“德主刑辅”的法治理念,主要体现在一些法治事件和某些文字(包括奏折、咨札、批札、书腆等)当中。总体而言,左宗棠在治理西部实践过程所蕴含的以法吏治思想,主要体现在整饬吏务和提高官吏素养两个方面。
这些展板信息让我们知道,左宗棠对于当时社会的弊病秉持着尖锐批判的态度。比如,他多次上书贺熙龄说:“天下人心大率一利字尽之,且咀吮于秽浊之中,游泳于戈矛之内,风俗安得不下,气运安得不衰也?思之概然!”为什么左宗棠认为“察吏必先惩贪”,要坚决清除官场毒瘤?对于了解左宗棠治国理念和为官之道的人而言,或许这不难理解。左宗棠二十三岁时曾撰一联曰:“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4]此联充分表达了他急公忘私的博大胸怀和追求真理的崇高气魄。同时,也源于他历经贫困之后的对社会的认识。在《二十九岁自题画像》诗的第四首写道:“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飱。五鼎纵能隆墓祭,只鸡终不逮亲存。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2]458这幅饥荒的生活图景就是对其二十一岁之前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过惯了贫困生活的左宗棠,虽然后来飞黄腾达了,但生活依然很俭约。事实也表明,左宗棠实乃廉洁自律典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对各种陋规大加禁革,自己于廉俸之外分文不取,并通饬属吏:“凡遇庆贺礼节,概应删除……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禁例。”左宗棠主政西北的吏治实践,表明了其矢志不移的反腐决心。1881年,左宗棠进京就任军机大臣,在离开哈密时,陕西布政使王思沂打算向他送一笔“别敬”,他复函说:“仆早岁甘于农圃,不乐仕进,所求易足,无营于外,心亦安焉。入世卅年,渐违素愿,而无负于官私,始终犹可覆按也。……近时于别敬,概不敢受。至好新契之例赠者,亦概谢之。”[5]左宗棠除了不接受名目繁多的好处,也从来不为这些“付费”。光绪七年正月,左宗棠自兰州抵北京,宦官向他索要门费四万两银子,左宗棠答曰:“彼系奉皇帝命来京,何以付费?不给一个铜板。”[6]67左宗棠在被拒不得入城数日之后,最终免缴门费,可见他傲骨铮铮、两袖清风。
尽管左宗棠也清醒意识到晚清的吏治昏暗已无力回天,但他并没有惧怕与退缩,而是积极投身于吏治实践。当人民被贪官污吏逼入了绝境之时,左宗棠迫切希望满清统治者实行廉政,主张以“儒术策治安”。他的吏治实践,同样也融入了“德主刑辅”法治理念。一方面,提出要严惩贪官。他为国为民严厉制裁贪污,果断地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比如,甘肃总兵周东兴、徽县县令杨国光等案。另一方面,主张裁汰庸吏。左宗棠在主政闽浙、陕甘等地之时,积极主张倡廉擢才,为官僚队伍注入新的血液,企图刹住、扭转地方的颓败风气。他认为,“今欲修明政事,则必先求治事之才。”因而,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展厅的一些图片看到,一批“操守廉洁而才有专长”的士大夫曾被左宗棠提拔并予以重用,比如,他将“出使俄英大臣”曾纪泽举荐于上。左宗棠此举,足见其惜才之心。在其所主政的大多数地方,通过惩处地方贪官、大修吏治,吏务实现了有效整饬。
左宗棠在“察吏”方法上,坚持直接与间接方式相结合,针对如何考察地处远边的官员,提出了“或因公接见,询以吏治得失;或接受禀详,考其政绩设施”。除了主张“察吏”,他还强调“亲吏”。他认为,“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他在“亲吏”上强调“教育训导官吏”和“体贴亲恤官吏”。而“教育训导官吏”方面,尤其注重以书育吏,以端仕风。1872年,左宗棠于在兰州编写了《学治要言》一书,作为地方官员廉洁尽职的标准。该书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为官必须爱民。强调“官必爱民,乃为尽职”,“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二是为官必须清廉。当官“必自守严正安重,无偏好,无轻言妄动,使人得而玩之。”。三是做官要勤于治事。“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尝与同官论三事次第,皆曰以清为本,余则谓非勤不能。”四是为官要慎于用人。强调要“宽以待百姓,严以取吏役,治体之大凡也。”五是官吏必须熟悉国家法令、法律。《大清律例》一书,乃国家之大经大法,合行通饬所属各厅州县,嗣后于办公之暇,将《大清律例》及《洗冤录》二书,各自反复批阅,深思熟读。④
我们从该展厅的图片信息了解到,左宗棠反复告诫属吏,为官应以民为本,爱民恤民,真心以待。他在陕西临潼知县伊允祯的到任禀贴上写了一段很长的批示,大概意思就是:“做官不仅要认真、谨小慎微和耐得住性子,更要体察民情,一心为百姓着想,就如慈母抚养年幼的儿子,时刻关心他们的冷暖饥饱。能够做到这点,可以称得上勤政为民的好官!有些人,他们平日为人甚好,心地善良,可一旦为官就变了。非常信任他的官亲、幕友、门丁、差投,不只是别人说他不好,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做得不够好。旁边的人说他没有才华,上司也可惜他没有才能。其实那不是无才,而是不认真。如果真心诚意地为老百姓服务,那么必将获得天下人百姓的称颂。今日百姓的事,交给官亲、幕友、门丁、差役,如果这些人本不是官,他们又怎么会诚心?《诗经》上说:‘如果做不到亲力亲为,就不会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应当牢记于心。’”⑤可见,左宗棠十分强调地方官员的责任担当,特别注重为官之道。左宗棠经常关心自己的属吏,督促他们为老百姓多做实事、善事。除此之外,他还想方设法为下属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常常书面开导他们,致力于物质与精神方面够解决实际问题,促使其下属专心治事,能成就一番事业。总之,从左宗棠吏治实践来看,始终贯穿着儒法思想,体现着“民本”理念。
四、“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与“道本艺末”的洋务运动方略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提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寻求民族自救之路。左宗棠作为“洋务先驱”,作为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在洋务运动中提出了“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道本艺末”等主张,其法理逻辑仍然是“经世致用”“德主刑辅”。左宗棠文化馆的“洋务运动”展厅,以专题的形式介绍了左宗棠与洋务运动有关的事迹。展厅通过对历史碎片的重新粘连、组合,既保持了历史事件的原真性,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复活了当年的生动形象,让我们可以一窥全貌。19世纪中叶,清朝政权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西方列强又怀觊觎之心,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面对装备精良的西方强敌,左宗棠看到了中西方之间艺事的差距,明确提出了“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从而为兴办洋务确立了基本原则。
左宗棠一贯坚持加强国防,抵御外国军事侵略。为了师远人之长,他创办洋务工业,造船成为其向西方学习迈出的第一步。可以说,他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洋务活动是建立造船工业。1865年,左宗棠制定并公布了一个商人购买轮船章程,规定商人购买轮船,经向清政府登记后即为合法。[7]不过,在左宗棠看来,购买轮船不如自造。同年,他在《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书》中写道:“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1866年6月,左宗棠向清政府的奏折中提出:“自从海上用兵作战以来,西方各国的军舰可以直接到达天津,篱笆难以发挥作用。因为行船速度非常快,以致于无法阻挡。自从允许洋船装载北方商品到各港口销售,北方商品价格飞涨。与洋船相比较,以海船为业的江、浙大商人到北方进货的成本越来越高,毕竟海船费用高且行船太慢,不具有竞争优势,如此下去会导致企业严重亏损,甚至关门歇业。滨海区的四类人当中,商人占据百分之六七十,市场萧条必然引起财税锐减。富商变成穷人,最后只能帮人当差。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海船搁浅后腐烂,目前江浙海运就担心没有船只,而水运粮食也就更加难以应对。因此,现在已经是非设船政紧急造轮船不可。”⑥可见,左宗棠此时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设厂造船的必要性、重要性,认为“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
1866年12月11日,左宗棠上奏清廷的《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提出了:“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8]27左宗棠拟定了《艺局章程》,对学制、管理体制、规章制度、培养目标和待遇等做了详细规定,并获朝廷的批准。1866年,左宗棠开创“西艺”教育之先河,创办了“求是堂艺局”,后改名为“船政学堂”。由此可见,为了抵制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与经济侵略,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坚持“经世致用”“德主刑辅”的法治理念,将“治夷”的层面由军事拓及经济,创办了一大批洋务企业。他在办洋务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着“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的原则,为治夷提供了实现的途径,以求国家独立富强,充分展现了其爱国主义情操。
五、余论
今天,留存下来的左宗棠祠堂共有两处。据了解,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抗法前线因病逝世,湖南巡抚吴大溦奉旨在长沙和湘阴营建祠堂,以此纪念这位爱国英雄。从左宗棠纪念馆出来,我们又寻访了旁边的左文襄公祠。一周后,我们又去了位于长沙北正街北端的左宗棠祠。左宗棠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他的法治文化遗迹,还有待我们继续考察。虽然本次寻踪的行程不远,但已经收获很多,至少我们有了现场的亲身感受。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左宗棠的法律思想无不体现湖南人生存方式的历经变异,以及湖南人的精神与性格。张明园先生曾分析湖南人的性格时说:“湖南人表现健壮性、激动性,表露自己,支配、改变、攻击、竞争,在一般中国人(侧重静)少有的性格。”[9]钱基博先生也曾说:“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艰苦,故强。”而陈独秀也曾对湖南人的精神有过一段从满激情的描述和赞叹:“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底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10]139左宗棠的法治实践,体现了典型的湖南人性格,其一身的事业,贯注了刚直的个性和救国的使命。这种坚忍不磨的精神,在左宗棠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左宗棠法治实践所贯通的“经世致用”“德主刑辅”理念,也使得近代湖湘法治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当然,对于左宗棠的法律思想,我们的认识也不能过于简单化。虽然他的法律思想深受宋学的影响,但是其军事实践也表现出严刑峻法的一面。原因在于,他的军事法治强调法术势相结合,也就是说他的法律思想吸收了晋秦法家的成分。此外,在洋务运动法律思想方面,他坚信中国与西方不同,绝不能以西法治中国,其整个思想并没有跨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边界。实际上,左宗棠所主张的西学为用,其开明之见还不如李鸿章、张之洞,甚至也不如冯桂芬、魏源,他的法律思想是比较保守的。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最辉煌的是收复了六分之一的国土,从而挽救了晚清政权。与其说破碎的山河成就了左宗棠的功名,不如说左宗棠用法治开创了历史的壮丽篇章。他的军事、治吏和洋务实践所蕴含的法律思想,铸就了湖湘法治文化之魂。
[注 释]
①参见徐明.论左宗棠的法律思想与实践[D].华东政法学院2004年硕士论文.
②参见左宗棠著,刘涣涣等点校.左宗棠全集(札件)[M].长沙:岳麓书社,2009:126.
③参见左宗棠著,刘涣涣等点校.左宗棠全集(札件)[M].长沙:岳麓书社,2009:574-575.
④参见张耀中.左宗棠整伤吏治[J].唐都学刊,1995(1)29-51.
⑤参见张耀中.略谈左宗棠整伤吏治[J].史学集刊,1994(1)28-31.
⑥参见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4册),奏稿卷18,《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M].上海:上海书店,1986:2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