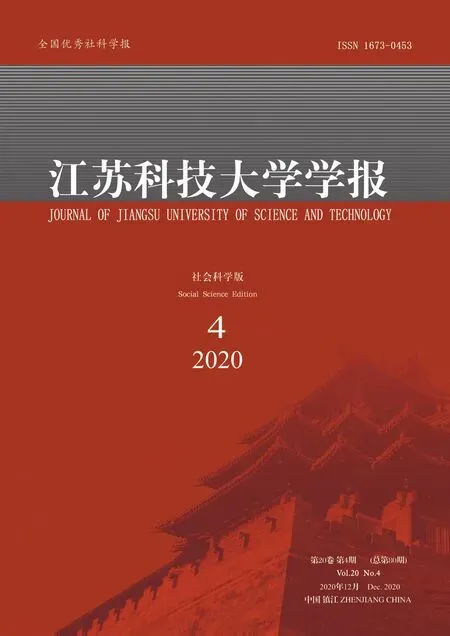论《祝福》与《母亲》文学形象生成的同形异构
2020-02-10张媛
张 媛
(1.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100;2.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鲁迅与赛珍珠都为文学史奉献了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劳动女性形象,这与新文化运动之前上层女性形象绝对占据文学创作半壁江山的文学景观相较,可谓是一种颠覆与创新。
《祝福》(1924)与《母亲》(1934)分别是鲁迅与赛珍珠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传世名篇,付梓出版以来就聚讼纷纭。两部作品的叙事都集中于言说世界及人类的生存困境。两部作品都是先由杂志刊载,后成书出版。1924年3月25日,东方杂志半月刊第21卷第6号刊载《祝福》,后作为首篇被收入小说集《彷徨》,被列为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之一,于1926年8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母亲》先由《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连载,1934年1月底由约翰·戴出版公司出版。无独有偶,鲁迅与赛珍珠在这两部作品的创作中为“母亲”这一文学母题增添了集慈母与苦难母亲于一身的女性形象,补充并丰富了母亲叙事传统。有学者对此展开比较研究,探讨了中国劳动女性形象的塑造问题[1],也有研究从称谓角度分析了人物身份[2],这实际上也是两部作品最为显性的文学表征部分。这种基于社会学理论的身份研究是必要且有效的,但鲁迅与赛珍珠对中国农村女性形象的书写具有更为丰富与深刻的思想内涵,因而有必要对这两部代表性作品进行超越社会学批评理论的去身份化研究。笔者认为,除“称谓”选用与“身份”定位方面的文化契合外,两部经典作品在艺术表现、思想内容上都存在显著差异,显示出鲁迅与赛珍珠这两位同时代作家在艺术表现方式、文化立场、价值取向与审美旨趣方面的迥异。因此,藉由《祝福》与《母亲》文学形象生成的同形异构,对鲁迅与赛珍珠在中国农村女性形象书写方面的开拓性努力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厘清两位作家从不同角度为构建中国现代文学谱系所作出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还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景观,再现其文学场域的多样性与整体性。
一、 同形:《祝福》与《母亲》的表面形似
同形主要指具有共性特征的表面上的形似。鲁迅在《祝福》中营造了一个虚实相间的故乡鲁镇,祥林嫂是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赛珍珠在《母亲》中为母亲设定了一个空中楼阁般的虚拟乡村,主人公“母亲”却实有原型。1917-1919年赛珍珠定居宿州时,“镇上有一家姓李的”[3],女仆李嫂成为其创作中国农村女性形象时以资借鉴的人物原型。两部小说中的人物都依存于作家营造的亦虚亦实的社会场域。《祝福》与《母亲》的表面形似主要表现于主人公的人物设定,其生存状态可细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主人公称谓的随意与附属特征相似。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一般而言都拥有独有的特定称谓,即便是以男性群像为中心的《水浒传》中的次要人物,也是各自有其具体姓名,如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等作为配角出现的女性。《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母亲》中的母亲,都是既没有独属于自己的闺名或学名,更未曾获得创作者给予的任何表字冠姓。祥林嫂处于无名状态,而母亲身处共名状态。1934年2月,多萝西·坎菲尔德(Dorothy Canfield Fisher)在《亚洲》杂志“亚洲书架”栏目发表对《母亲》的无标题评论,认为赛珍珠是为了使故事具有普遍意义而不给母亲及其他人物冠名的,这个女性人物是“所有的母亲”,因为“她的本性就是做母亲,别无其他”,小说就是一种对母亲身份的研究[4]。两部小说主要人物的无名和共名状态,反映出鲁迅和赛珍珠对旧中国农村传统女性角色认知上的共识。她们都没有专属于自己的姓名,她们只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妻子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她们的存在意义仅仅在于其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价值,她们的不幸源于承担妻职和母职的能力与权利的丧失[2]。鲁迅在《小杂感》中剖析:“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5]鲁迅关于祥林嫂的命名强调的正是其妻性,而赛珍珠对“母亲”的共名式命名强调的则是女性的天然母性。看似随意的主人公称谓选择实则蕴涵着两位作家的不同立意。
其次,主人公主体身份、地位的卑微相似。人的称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在社会范畴中的身份与地位[2]。《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得名于她的第一任丈夫,《母亲》中的“母亲”则处于共名状态,她们都是在他者的定义中获得自我的身份与地位的。一方面,独立身份的缺失,依靠他者命名,预示她们身份、地位的低下;另一方面,父权制下女性他者的从属身份又使其被视作社会的他者,从而在社会生活中饱受歧视与漠视。
再次,主人公个人秉性的纯良相似。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弱势女性,受制于诸多因素,因而女性主体意识淡薄。作为下层劳动妇女,勤劳质朴是她们的本色,祥林嫂干活“抵得过一个男子”,为东家“彻夜的煮福礼”,“竟没有添短工”[6]8;母亲同样勤于操持,整日在家里、田地里劳动。她们都不具备现代科学意识,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祥林嫂将解脱的希望寄托于“捐门槛”以救赎自己的罪孽;母亲则总是提心吊胆,害怕直视土地公公的眼睛。
最后,主人公人生境遇相似。“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7]5祥林嫂与母亲都是生活在20世纪中国封闭的乡土社会中的女性,“礼俗社会”“有机团结”的乡土性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两位女性共同的不幸遭遇。她们都曾经遭遇家庭生活的不幸而成为寡妇:祥林嫂的第一任丈夫比她小十岁,以打柴为生,在春天去世,由此成为寡妇;母亲的丈夫则是自己离家出走不知所终,母亲因此成为事实上的寡妇。她们都遭遇了第二个男人,从某种程度而言颠覆了以往的传统女性形象。祥林嫂的第二个丈夫因患伤寒去世,而母亲则遭遇管事的始乱终弃。她们都遭受了丧子之痛,祥林嫂的儿子阿毛意外地被狼叼走,而母亲的女儿外嫁被折磨致死,最疼爱的小儿子则因为造反和革命被杀。“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7]8祥林嫂与母亲均受囿于这种封闭性乡土社会在地理与心理双重层面所带来的世俗、人言、鬼神的限制与戕害,其悲凄命运与此种社会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
从主人公的称谓、身份地位、秉性、人生际遇等几个维度看,《祝福》与《母亲》具有惊人的相似点和相同点。这种人物生存背景表面上的形似,构成了两部小说的外部同形。
二、 异构:《祝福》与《母亲》的内在差异
对于作品的比较分析,共同之处是比较的基础,而差异则构成比较的核心。掩藏于《祝福》与《母亲》诸多表面形似背后的核心价值,是其在艺术表现方法、思想内容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一) 艺术表现方法差异
《祝福》与《母亲》在艺术表现方法上的差异,可以从叙述框架、叙述视角、人物形象塑造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首先,两部作品叙述框架的严谨度与宏阔性不同。作为短篇小说巨匠,鲁迅追求结构艺术的严谨。《祝福》采用典型的框架式结构,故事的叙述时间被严格限制在一天之内:小说的开头,“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6]1;小说的结尾,“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6]20。鲁迅化用非线性叙事技巧,通过倒叙、插叙等手法,在一天之内的叙述框架内选择了几个片段,以展示祥林嫂命运多舛的悲剧一生。鲁迅的这种结构技巧带有明显的西化影响。赛珍珠作为喜爱并推崇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作家,重点考量的是作品的宏阔空间。1934年1月《母亲》正式出版之际,《纽约时报书评》在头版刊发J.唐纳德·亚当斯的评论文章,他称赞《母亲》“结构上的建筑统一性具有打动人心的质朴与力量”[8]。赛珍珠采用说书人讲故事的方式,《母亲》从再有一两个月就要生产小儿子的母亲在厨房劳作的生活片段开始[9]1-7,到母亲在坟地哭悼小儿子时得知孙儿诞生结束[9]219,时间跨度达21年。这种线性叙事类型与流水账似的小说结构相较于《祝福》而言,其叙事节奏明显更为散漫而拖沓。在叙述框架上,鲁迅明显接受了西方现代小说的结构艺术,赛珍珠则更倾向于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结构手法。
其次,两部作品叙述视角的选择不同。叙事者/人物与小说事件相对应的位置/状态构成叙述视角,这是叙事者/人物观察故事的特定角度[10]。《祝福》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这是中国传统短篇小说罕有而现代短篇小说常用的一种写作手法。叙述者既是作品中的人物,又充当见证人,实际上是线索人物。其优点在于:一是真实性,以事件亲历者、见证者与参与者的身份讲述故事,既能赋予故事以客观特征,又可辅之以叙事主体的主观感受,保证了叙事主体及其叙事的客观性、可靠性与有效性,其优势在于整合故事的写实与虚构元素,能够全方位、多层次地刻画人物形象,展现主客观有机统一的小说艺术的本质特征;二是叙事者在叙事过程中能够自由变换叙事主体,根据叙事需求选择和切换他人的视点和观点,从而打破叙事者在资讯见闻方面的认知局限。鲁迅在《祝福》不足万字的篇幅中精心撷取了祥林嫂生活的三个片段:二十六七岁正值韶华初到鲁镇时的祥林嫂,“得到祥林嫂好运的消息之后的又过了两个新年”[6]12,“我”回到故乡鲁镇除夕前日见到的祥林嫂。“叙述者可能与被叙事件、与所表现的人物和/或其受述者之间保持或大或小的距离。”[11]三个场景或者是叙述者“我”本人亲见,或者是倾听别人的转述,作者灵活地改变叙事角度,连贯、完整地呈现了祥林嫂悲剧性的一生。因应于特定情境的叙述视角切换与精心严格的素材选取,使第一人称视角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此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名篇。
赛珍珠在《母亲》中采用第三人称并以全知视角塑造了一位贤淑善良、勇敢独立、极富生活气息的平凡但绝不普通的母亲形象。这样一种无限制的全方位的视角选取与作品采用长篇小说这种体裁类型密切相关,也与赛珍珠的小说观契合。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下的叙事朴实清晰,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方式,可以收到良好的阅读效果。这种传统的叙述视角具有多重选择性,作者的全方位介入导致了叙事的“全知性”,决定了故事叙事者对故事进程进行观察和讲述的“全知全能”角度,其优势在于能够自然展现宏阔的时空视野与繁复的情节架构。全知视角并无固定视角,切换时空场域时基本不受物质世界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伴随视角转换而来的是叙事的客观性、真实性存疑。
“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都要受观察点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支配。”[12]从叙述视角选择看,《祝福》具有现代性,它以其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小说文本在思想内涵、现实呈现、美学品格等维度的深广,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奠定了审美现代性的一些核心要素。《母亲》则具有更多的传统性,“全知”叙事形态相对封闭,结构单一刻板,基本是遵照自然时序组织时空转换,进而导致留白与想象空间受限。
最后,两部作品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的功力不同。人物形象是小说的灵魂,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小说成为经典的标志。
虽然《祝福》中的女主人公祥林嫂这一称谓属于无名状态,但祥林嫂形象却进入了文学经典之列。这主要得益于鲁迅高超的对比描写手法,例如对祥林嫂的三次肖像描写。
最初见到的祥林嫂:
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6]7
回到鲁镇的祥林嫂:
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6]12
最后一次见到的祥林嫂: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6] 2-3
作者采用白描、细节描写手法“画眼睛”,透过人物外貌的细微变化,用极为俭省的笔法勾勒出祥林嫂遭逢家变前后的巨大变化。
其他如语言描写,祥林嫂口诉阿毛的故事,“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6] 13在惜墨如金的鲁迅笔下,祥林嫂不厌其详反复重复这一故事,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祥林嫂精神上遭受的沉重打击,另一方面是为了再现周围看客的冷漠疏离。
此外,典型环境的渲染与营造更加凸显了悲剧性。年关祝福“送灶的爆竹声连绵不断”,这不但烘托出祥林嫂在普天同庆的祝福声中孤身一人去世的悲惨,而且深刻揭露出鲁四老爷等人的伪善冷漠。
鲁迅通过肖像描写、语言描写和环境描写,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留下了永恒的经典。
赛珍珠在《母亲》中也采用了肖像描写、语言描写和环境描写等手法勾勒人物各个侧面以充实人物性格、扩大小说容量。如正面与侧面肖像描写:
火光照在她那宽圆而健康的脸上,丰满的嘴唇,透着被风吹日晒成的暗紫色,她一双乌黑的眼睛,映着闪耀的火光,显得明亮又安详地平躺在眉睫下边。她的面孔并不好看,但是充满着热情和慈爱。[9]2-3
看她那水汪汪的眼睛,欢笑的声音和喜乐的态度,怎么今天她脸上烧得这么红![9]106
《母亲》的语言描写也颇具特色。母亲待人善良温和,常怀感恩之心,日常话语常使人如沐春风。如,“姐姐,你真是好心肠”[9]22“你好好休息吧”[9]30“噢!我说你一定还要活很久呢!老妈妈,我从没有看见过像你这样年纪的老太太还能有你这样好的身子”[9]57“是呀!你真好。我回来了,我真是累极啦”[9]93“你等着,老妈妈,隔一两天我就做好了”[9]102“孩子,妈这些日子心里不舒服,明天清早,我要去买些眼药来医你的眼睛,我早就说过了”“儿子,明天我替你洗洗衣裳,我没有见过你这样脏破的衣裳,你是个很俊的孩子,知道吗?被我糟蹋成这样”[9]118等。
《母亲》是一曲自然与生命力的颂歌,通篇充溢着对四季更替、春生夏长的自然环境的描写:
转眼又到稻子收割的时候了,稻穗变得金黄,沉重地挂在田里等待着收割。[9]52
月亮伴着才落下去的太阳慢慢升了起来,又大又圆,寒亮而且灿烂地照耀着大地。[9]92
这整个月来,寒风从北方荒郊里就没有停息地吹着,带来了寒意,树叶在树上皱卷起来,路旁的野花也干枯凋残了,所有地上的生物都无精打采,显出即将灭亡的现象。[9]127
母亲坐在那里,望着四围的山头,想这夏天怎么这样的热,每座山边都满是绿油油的,田间的稻子也已长得很高了。[9]170
小说接近尾声时,最疼爱的小儿子惨死在屠刀之下,母亲的悲恸到达顶点,这时只有化育万物的天地成为唯一接纳、包容母亲的自然环境:
母亲坐在那里,望着寂静的、才渐渐开始发亮的天空,鲜红的太阳慢慢爬升起来了,金黄色的阳光普照着大地……田里的稻子又到成熟的时期,稻穗都很饱满,稻叶染成了金黄色。旭日的光芒照亮着田野。[9]217
但客观而论,由于赛珍珠在叙事上强化小说的故事性及情节,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相对薄弱,未能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现历经人世沧桑的母亲应有的复杂性与立体感。就其人物的典型性看,母亲在小说末尾延续了其在小说初的性格特征,显然不如祥林嫂形象变化那样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母亲的个性特征不够显著,形象过于大众化而显得模糊、苍白,极易湮灭于古往今来虚构与现实中出现过的众多勤劳坚韧的中国女性群像中。古往今来,母亲这一称谓及其所代表的形象在世界各地都备受歌颂,这既是在文辞与社会学意义上的专有敬称,又在文化上归属于既不提名也不道姓的共名状态。不仅主人公母亲的形象缺乏变化,缺乏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独有特征,所有次要角色皆无姓名,仅存男人、大儿子、小儿子、婆婆、瞎眼女儿、堂兄、堂嫂等基于家族辈分排序且依据与母亲的亲缘关系所作的身份性命名,或是管事、长舌寡妇等职务及绰号性称谓。客观上的非典型“共名”情状,标示了作者对各类角色的隐形化需求及普适化设置[13]。始终笼罩在虚无迷雾里的母亲形象由于缺乏真实可感的细节刻画,因而缺乏成为经典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必要条件。
(二) 思想内容呈现的差异
《祝福》与《母亲》在思想内容上的差异,可以从文本所表现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对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上展开分析。
《祝福》深刻揭露了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对于下层劳动妇女的戕害。祥林嫂的第二次改嫁实质上是其婆婆操控的一桩交易:“将她嫁到山里去……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6]11族权、夫权悄无声息地剥夺了祥林嫂的自主权与选择权,将其物化为一宗财产,成为宗族借以牟取最大利益的商品,从而完全丧失了人权以及作为人的尊严。更为重要的是,《祝福》揭露了神权对下层妇女的思想禁锢,“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柳妈都充当了促使祥林嫂精神彻底垮掉的直接推手。鲁四老爷厌憎祥林嫂的寡妇身份,认为其“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6] 14。柳妈则借闲聊之机、假关怀之名向祥林嫂灌输“烈女不嫁二夫”男权思想:“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6]17祥林嫂为此前往“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6]18,但鲁四老爷仍旧严禁她触碰祭祀物品。这彻底摧毁了祥林嫂的精神世界:“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6]19
相较于《祝福》,《母亲》也描写了封建政权(管事)、神权(土地公公/菩萨像的眼睛)对于下层劳动妇女的欺压、欺骗与精神束缚。
管事的形象类似于传统小说、戏曲中始乱终弃的恶棍形象。当他接近母亲时,“睁大眼睛,凝视着母亲,目光像带有一种权威似的”[9]97,“一双眼睛在黑暗里向外看着,像极了夜里野兽的眼睛一样晶亮”[9]99;翻脸无情时,“这回可是板着脸,斤斤计较地同对待别人一样收了母亲的地租”[9]105;在母亲找到管事告知自己已经寡居时,管事甩脱她的手,高声说“那与我有什么相干……他又粗鲁地说:‘我没有亏负你呀……我已经赏你不少的啦’”[9]111;母亲因私自打胎而九死一生之后,“管事故意装作不经意地看着母亲”,向大儿子透露自己再也不“到这村里来了”[9]117-119。
以土地公公/菩萨像为象征的神权始终禁锢并主宰着母亲的思想。土地公公“凝视的眼睛”是小说中不断出现的重要意象:“中间的一位是个端严的土地公公,瞪眼直向前面看着”[9]99,“怕是太侮辱了被她蒙了脸的土地公公”[9]114。作为淳朴农村女性代表的母亲终其一生都受制于神权的压迫,“母亲有时也会抱怨着有这种权力摧残凡胎的神明菩萨们”[9]200,“又好像觉得菩萨像已经知道似的向下看着她,凝视着这有罪还未偿债的女人”[9]128。
但无论是对政权(管事)还是对神权(土地公公/菩萨像的眼睛)的描述,其批判力量显然与《祝福》不可同日而语。《母亲》是以女仆李嫂子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其中也夹杂赛珍珠本人的内心独白,隐藏着赛珍珠心底的秘密——性爱与残障女儿卡罗尔给她带来的心灵创伤。佩尔·哈尔斯特龙(Per Hallstrom)在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曾对《母亲》作过高度评价:
她的整个命运都体现在“母亲”这个词中……丈夫不久就弃家出走了,但是她为孩子努力撑持着这个家。整个故事以悲伤结束,但不是失败。[14]
《祝福》以其彻底的、震撼人心的悲剧结局,表现了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性以及批判性;《母亲》则是以近乎大团圆的结局写母亲终于得到了孙子、人生有了继续下去的理由。两部小说均聚焦于人类生存的本体域,以迥异的艺术手法呈现了不同结局,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阅读体验与效果。这种处理手段的高下实际上是由两位作者的文化立场、艺术取向、价值取向等因素决定的。
三、 同形异构表象后的创作动因及书写策略
“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主导思想,每一社会都有自己的官方哲学,否则便是一个没有历史个性的时代和社会。按照机械反映论的理解,文学就应该描绘现行的思想体系。”[15]鲁迅与赛珍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祝福》与《母亲》无疑是时代的反映与存照,但其在对中国农村女性这一文学对象的描摹上却存在诸多差异,因而塑造出同人不同命的主角形象并构成风格迥异的文学文本。因此,有必要对形成这种文学差异的深层原因展开进一步探析。鲁迅与赛珍珠的文学创作动机由不同的外在机缘触发,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其关注焦点与创作意图大相径庭。《祝福》与《母亲》文学形象同形异构的深层原因与两位作家的文化立场、艺术取向、价值取向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 文化立场差异:反传统与对传统的肯定
作为现代中国的启蒙先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鲁迅所秉持的“反传统”新文化立场事实上得益于两种因素:一是内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于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对中国民众生理、心理束缚的准确把握,对于国民性的深刻了解,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元素深恶痛绝;二是外因,从晚清开始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环境与时代氛围决定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新文化立场,反封建、西方理性主义、西化、启蒙一直是时代的主流。《祝福》无情揭露愚昧残酷的封建礼教等反传统特征在同时期小说中表现较为显著。在这篇以冰冷尖锐的笔触撰写的短小精悍的小说中,鲁迅的悲悯与愤怒通过充满激愤的反传统书写表露无遗。时代因素的影响,鲁迅本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决绝态度,深邃而广阔的文化视野,这些因素共同使得《祝福》所具有的批判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
赛珍珠的多元文化立场,使她徘徊、摇摆于东西方文化之间: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母亲》在孝亲、勤劳、母教等方面肯定了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受西方女权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及本能理论的影响,再加上她本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以及女儿卡罗尔的先天残疾,这些都影响了赛珍珠在《母亲》创作过程中的素材选取与尺度权衡。因其作品中的母亲形象不够纯粹,显示出新旧并呈、中西杂糅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个性解放的色彩,因而作品本身也成为赛珍珠将艺术与人生相结合的典型范本,缺乏一以贯之的写作方式与统一风格。
作者文化立场的这种差异,从创作源头上影响并决定了“祥林嫂”与“母亲”这两个具有诸多共同点的文学形象呈现出诸多差异。
(二) 艺术取向差异:向西方学习与向东方汲取养料
在艺术取向上,整个“五四”一代学人,当然包括知识精英的代表鲁迅,主要是向西方学习,“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16]。对于西方艺术的汲取,可以在《祝福》文本中觅到诸多痕迹,如采用框架式结构、第一人称手法、白描手法、注重细节真实、营造典型环境等,这些都与同时代的西方艺术手法同步。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赛珍珠则是向东方学习,对于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艺术手法情有独钟并汲取其养分应用于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这些在《母亲》中同样留下诸多印痕,如采用说书人讲故事的流水账似结构、全知视角、第三人称手法、细节的失实、非典型环境描写等。这些与东方传统艺术手法异曲同工。
作者艺术取向上的这种差异,在创作手法上决定了作品文学性与审美化层面的差异。虽然小说主人公在诸多层面上相似,但两部作品却在美学风格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学景观。
(三) 价值取向差异:批判与颂扬
在价值取向上,作为“五四”一代文人的先驱和代表人物,反对传统封建文化,学习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是鲁迅的基本价值取向。鲁迅秉持启蒙立场,始终关注国民麻木的精神,批判与唤醒麻木的国民灵魂是鲁迅的奋斗目标与基本价值取向。因此,在《祝福》中,鲁迅对主人公祥林嫂虽然抱以深切的同情,但对其精神的麻木、迷信的可悲、仅寄希望于鲁镇一干众人的同情与理解的消极被动和蒙昧无知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撞香炉拒绝改嫁只是一心要做节妇;捐门槛亦只是为了在阳世做一个稳妥的奴隶,在阴间做一个完整的鬼魂。“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鲁迅对以祥林嫂为代表的普通中国民众失望至极,对于直接导致祥林嫂悲剧命运的鲁四老爷、柳妈,鲁迅难掩讽刺、批判的锋芒,即便对于鲁镇其他人物,如四婶、卫老婆子、听悲惨故事的男人、女人,鲁迅都难掩其悲愤交加的极端情绪。祥林嫂心底最痛的伤疤莫过于儿子阿毛被狼叼走吃掉一事,可偏偏鲁镇的无聊闲人专以揭人伤疤为其隐秘的乐趣,最初是有些老女人特意寻来要求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待祥林嫂反复诉说后,祥林嫂丧子的不幸便传扬开去并成为众人厌烦进而取笑的话题。以柳妈为代表的鲁镇人未曾真心体恤、怜悯祥林嫂,却不失时机、不无恶意地以其额角上的伤痕为题去探秘其再嫁的内幕。祥林嫂“自从和柳妈谈了天, 似乎又即传扬开去,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来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6]18。充当看客、消费他人痛苦以为娱乐从而凸显自身优越感的鲁镇民众,于闲言碎语的交互传递之际暴露出人性暗藏的阴暗冷漠之一隅。民众幸灾乐祸的麻木心理代表性地映射出国民性中阴暗隐晦的劣根品性,小说设置的环境鲁镇就此成为笼罩在晦暗之中的人性荒原。
由于文化背景、个人身份的不同,赛珍珠与鲁迅在价值取向、人生态度上无疑存在巨大差异。鲁迅揭示国人的精神麻木及病态人格的社会性忧虑与赛珍珠状写并还原历经世态沧桑的生命形态内蕴力量的乐观立场与姿态无疑是明显不同的。如果说鲁迅在《祝福》中主要展示的是中国国民性的消极面并对此进行了震撼人心的批判,那么赛珍珠在《母亲》中秉持的则是对中国底层人民特别是底层劳动妇女颂扬的立场。无论是母亲的勤劳、孝顺、母爱,还是母亲出轨管事,因丈夫出走而欺瞒乡里,均展现出下层人物灭而不绝的顽强生命力,即便是周围的邻居、堂兄、堂嫂等次要人物身上也散发出充满人性温暖的光辉。母亲多灾多难的人生映射出时代的没落、衰败,人类命运被厄运笼罩,灰暗色调的行文至结尾处峰回路转,突现光明,母亲八年来一直执念的孙子在小儿子被杀之际突然降临,旧生命的逝去暗含新生命的创生,象征人类在被动接受命运的痛苦过程中对新生命的孕育,螺旋式前进的人类历史总在与挫折交织中进步,无望与希望相辅相成。这是赛珍珠关于人之生存现实与人类命运走向创作的共同母题。
赛珍珠满怀“对人及其成长的无限兴趣”[17]235,坚信“即便因环境因素而被邪恶所制,人也绝不会变得完全邪恶。人将仍旧保留隐藏于心的善念,随时可能弃恶从善”[17]235。赛珍珠一贯持有的这种对人的坚定信念在《母亲》中通过对母亲形象的刻画而完美演绎出来。“蓬勃向上的生长力是天生固有的,唯有死亡才能使之终结。”[17]235诚如其在《必须赶紧推开石头》(RollAwaytheStone)中所言,“我对人类的心灵与其向光生长的力量有着如此深刻的信仰,我在这里找到了足够的理性和理由,使我对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17]237。
综上所述,《祝福》与《母亲》的小说类型、女性题材、中国语境和叙事要素类似,其文学形象生成的同形异构促发迥异的内在视景与审美体验,展现出作者同中有异的批判立场、文化反思与美学品格。“小说是对同胞的生存做出的肯定。小说强大有力,经由想象创造出比现实更为清晰的一种生活,小说选择性地采集与生活相似的某些片段,这种选择足以媲美历史记录。”[18]从文化史视角而论,“小说比历史更真实”,因为“小说是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小说又不止是历史,它源于由语言形式组成的现实以及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这种牢固的根基”[19]。鲁迅与赛珍珠这两位几乎在同一时期享誉文坛的作家,尽管都聚焦于20世纪初期新旧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农村,但迥异的个人经验与文学创作品格使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泾渭分明的立场、艺术与价值,由此形成各自鲜明的文学与美学轨迹。鲁迅站在启蒙的立场,居高临下地鞭挞披着封建道德外衣的古旧思想对人的掠夺、异化以及对人性的漠视与摧残,挖掘腐朽文化与落后文化背后的社会原因,揭露并批判国民的劣根性。赛珍珠则一直钟情于母亲题材创作并有多部相关作品问世。1933年,《论语》第21、22、24、26期连载赛珍珠《老奶妈》(唐锡如译文);同年,《现代父母》第1卷第1-2期连载赛珍珠《老母亲》(冯雪冰译文),《民族文化》1945年第5卷第1-3期、1946年第5卷 第2-3期连载赛珍珠《老母亲》(姚启东译文);《太平洋月刊》(北平)1946年试刊第1卷刊载赛珍珠《母亲的故事》(逸安译文)。赛珍珠从民间立场与大众视野出发,以平等的眼光与姿态描摹悲凄中不乏温情的人世,凸显普通民众乐观丰沛的精神、坚毅刚强的品格与独立自持的力量,为饱受苦难的芸芸众生种下生之希望。在艺术方法上,鲁迅是东方的,向西方靠齐;赛珍珠是西方的,趋向东方,是从平民主义的艺术角度抒发其中国情怀。在价值取向上,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新旧时代之交的中国进行犀利而无情的批判;赛珍珠则是满怀热情地赞扬与讴歌中国及其大地上生活的朴素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