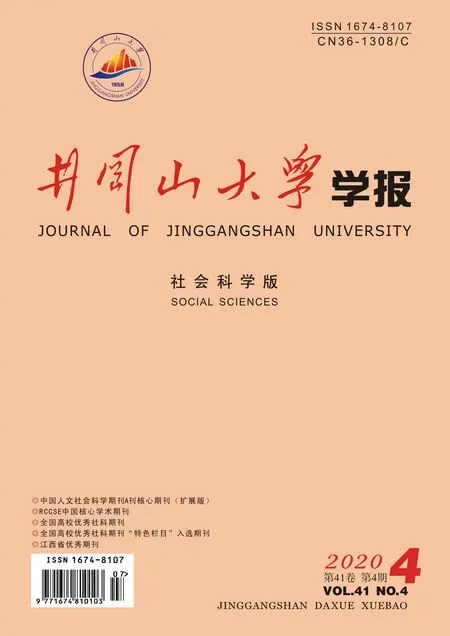试论当代俄罗斯自由派与爱国派文学批评之争
——以亚·普罗哈诺夫小说《黑炸药先生》为例
2020-02-10朱涛
朱 涛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黑炸药先生》由当代俄罗斯极右派作家、政论家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创作。该作于2002年出版,荣获当年的俄罗斯“年度最佳畅销书奖”,随后又在2003年荣获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评选的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熟悉当代俄罗斯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黑炸药先生》在当代俄罗斯文坛的地位不可谓不特殊,它恐怕是近些年来最受争议的作品之一,围绕该作,俄罗斯批评界各派势力悉数登场,进行了空前论战。诚如我国学者姚霞所指出的那样:“后苏联文学批评的现状——不同年代批评家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的纷争——在颇具轰动效应的2002年度‘民族畅销书奖’的评选中得到了生动的说明。《明日报》主编普罗哈诺夫因奖金出资单位的干预,使连载《明日报》的小说《黑炸药先生》获奖。此后评论界就作家作品以及评奖过程所展开的论辩较之评选结构揭晓前更为激烈。”[1](P101)可以说,《黑炸药先生》为我们近距离观察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的现状提供了宝贵契机。
一
《黑炸药先生》是普罗哈洛夫最新的一部作品,小说先在报上连载,后由莫斯科的“埃德·马尔吉涅姆”出版社推出。这部充满反犹太主义印记的小说讲的是1999年莫斯科居民楼的爆炸事件,这是一场由车臣恐怖分子发动的真实事件,而小说却别出心裁地将该事件的幕后主使设定为克格勃,认为其目的是为了配合普京政府渲染反车臣情绪。
小说的第一部“检察长行动”,描写试图调查克里姆林宫中腐败行为的检察长遭到陷害。一些前情报人员制定了旨在拯救俄罗斯的 “斯瓦希里计划”,暗中选定“代表”,并准备通过周密的计划最终将“代表”推上最高统治地位。为换取总统及其霸道女儿的信任,他们决定除掉正在追查克里姆林宫贪污受贿情况、让总统一家头痛不已的检察长。最终,中了美人计的检察长被革职,而“代表”则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局长。第二部“总理行动”,描写“代表”如何成功地取代了现任总理。设法让“代表”当上总理,是“斯瓦希里计划”的第二阶段。情报人员设下圈套,让现任总理在车臣问题上出了大丑,总统于是将“代表”任命为新总理。第三部“加缪行动”描写总统周围势力被削弱。为了巩固“代表”的地位,情报人员设法除掉了总统女儿周围的人,首先是两位犹太大亨。而在莫斯科市长为莫斯科河上的一座新桥举行的揭幕典礼上,“代表”的恩人、曾任彼得堡市长的老民主斗士“小留声机”在喝下一杯法国产的“加缪”牌白兰地酒后突然死去,两位犹太寡头也因有下毒的嫌疑同时被捕。“代表”以总理的身份来到桥上,总统女儿上前挽起了他“短小的胳膊”,后来,“代表”又含泪出席了恩人的葬礼。第四部“黑炸药行动”写的是发生在莫斯科的爆炸案,竭力扶持“代表”的情报部门事先就获得了车臣人要在莫斯科制造爆炸事件的情报,但他们并没有立即制止,反而加以利用,以便发起一场新的车臣战争,借此树立和巩固“代表”的威望。第五部“俄罗斯号飞机”,写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们应邀飞往索契出席一个会议,代表们分乘两架飞机,机身描有“俄罗斯号”几个大字的总统专机首先升空,其中坐的是还没有成为总统的“代表”,而另一架满载“斯瓦希里计划”骨干精英的飞机,却在起飞几秒钟后起火爆炸了。“尾声”写道,“代表”在飞机上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国家,稍后他走进驾驶舱要求独自驾驶飞机,机组人员半个小时候走进驾驶舱时却发现里边空无一人。[2](P4)
《黑炸药先生》一经推出,旋即引发了评论界的轩然大波,围绕这部作品所展开的讨论空前激烈。小说不乏支持者,如Д.奥尔尚斯基指出:“普罗哈诺夫庞大的、猛烈的激情对他的小说影响甚大,他在昏暗的文学生活中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最有意义的现象。”(《莫斯科新闻报》2002年4月5日)Л.皮罗戈夫指出:“喧闹的90年代对于俄罗斯文学而言是损失很大的年代,是自由派的布克奖之死气沉沉的时代……2002年最优秀的俄罗斯作家当属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独立报》2002年4月11日)。一直牢骚满腹的老作家邦达列夫竟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最新的长篇小说《黑炸药先生》,就像是我们当今文学灰暗背景中一枚腾空而起的火箭。”
反对者也不甘示弱。如涅姆泽尔认为“充斥着野蛮的反犹主义的《黑炸药先生》,除了政治(残酷和愚蠢的)只有病态的自爱、闲得无聊时可以技术的修辞错误——作家的反动思想与粗劣的写作技能一目了然,毋庸赘述。”传统派杂志《我们的同代人》编辑部不知为何认为小说具有“亲普京”的倾向而没有接受,使得它只好以两份报纸的特刊形式发表。多数老自由派不喜欢这部小说对现实的暴露以及对政界要人的批判,不喜欢它的 “反普京”倾向,因而对它持否定态度。这类人的代表、著名批评家阿尔汉格尔斯基连续发表文章,对这部小说得到公众承认和获奖表示愤慨和不可思议。邱普里宁则指出,小说并不构成对现实的批判,并非官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某种失误,“而我在所发生的一切之中所看到的并非宣传的失败,而恰恰相反,是当今政权蓄意谋得的一个特殊的胜利。”小说发表之后,“所有的人都赢了,不是吗?普罗哈诺夫赢了,他的出版者赢了,‘年度最佳畅销书奖’的策划者赢了,报刊杂志上那些自命为媒体高手的‘黄金青年们’赢了,国家也赢了,大家全都赢了,除了文学。 ”[3](P197)
从上述对作品的评论我们不难看出,支持这部作品的多为年长一辈的爱国派批评家和少数青年一辈的自由派批评家,而反对这部作品的多为年长一辈的自由派批评家。众所周知,爱国派(保守派)和自由派(民主派)之间的争斗一直是当代俄罗斯批评发展的主线,两派历来是水火不容、不共戴天。他们的争斗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截至90年代尘埃落定,最终以自由派的全面获胜而告终。自由派虽大获全胜,但两派之间的争斗其实从未停止,在新世纪仍不断重燃战火。并且获胜的自由派内部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年轻的自由派想要从老一辈处夺取话语权,这种分裂不断加剧,最终以《黑炸药先生》为导火索,双方爆发了一场全面论战。使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为何在面对《黑炸药先生》时,爱国派与自由派批评家之间的争吵会如此激烈呢?自由派内部为何会起内讧呢?作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何少数青年一辈的自由派批评家要站出来反对自己的阵营,去追捧一位资深的爱国派作家呢?
从两派的论战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很少言说《黑炸药先生》的审美性,而大谈其政治性,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两派论战的动机。资深批评家邱普里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何谈论 《黑炸药先生》的人中没有人,甚至不尝试用真正的批评工具去理解小说,首先解析出其中的意义、政论,并为读者解释小说值得读并不是作为胡闹的幻想小说,而是作为严酷的控诉,指向联邦安全委员会、政府、整个普京制度?仅仅是因为真实批评传统和将文学文本变成政治游戏的有效武器如今被忘却了吗?”“或者,我们冒险假设,订货一开始曾是另一回事:不是加剧而是相反掩饰、抹粉、抑制对小说的宣传,将它变成平淡的习以为常的后现代主义的与‘隐喻’和‘动力师’的游戏?要知道,应当认为做出屈服的,并不是想出来主义的新闻公司,而是А.普罗哈洛夫本人,和他不知疲倦的阐释者В.邦达连科,他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谨慎地绕过所有尖角和热点,主动谈及高超技艺、妓女们,总而言之,随心所欲,除了不谈作品真正的内容。 ”[3](P188)
二
众所周知,2000年代初俄罗斯自由派批评经历了后苏联时期最大规模的分裂。这场分裂的主要原因为如何看待文学和意识形态中的歧视和反西方运动问题,次要原因为如何看待90年代作为一个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时代及2000年代初审美上的创新。
第一场大争吵围绕文化领域中极右派作家、政论家А.普罗哈诺夫的合法化。在20世纪70—80年代,他曾在《新世界》《我们的同代人》上发表了一些小说,这些小说为克格勃在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秘密行动辩护。它们在风格上容易使人想起40年代的斯大林社会主义以及约翰·卡雷的英文间谍小说。1984年普罗哈罗夫出版了政论书籍《核盾》,该书论证了苏联强化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在这之后自由派作家给他起了个绰号——“总参谋部的夜莺”。90年代普罗哈诺夫担任《明日报》的主编,该报主要刊发俄罗斯民族主义作家的文章,他们宣称俄罗斯政府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把西方国家强加在俄罗斯之上。
普罗哈诺夫的小说充满了对克格勃的无所不能及对冷战的怀念。情况在2000年代初急剧变化,普罗哈诺夫成为电视脱口秀的常客,2002年他的小说《黑炸药先生》在“埃德·马尔吉涅姆”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以出版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译本(福柯、德里达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著称。《黑炸药先生》充满反犹太主义印记,讲的是1999年莫斯科房屋爆炸的事情,该事件由克格勃一手策划。该作荣获当年的“国家畅销书”奖。此后他的小说开始在一些知名出版社出版,发行量也逐渐增大。
围绕《黑炸药先生》出版的所有事件——从出版社与作家的预先签订协议,到在“埃德·马尔吉涅姆”的出版,再到获奖——都事无巨细地刊登在报纸《Ex Libris》上(属于《独立报》)。该报是当时俄罗斯青年批评家的主阵地。最初普罗哈诺夫和“埃德·马尔吉涅姆”高层会面的纪要,由这些青年批评家中的一位——Л.皮罗戈夫撰写,并且普罗哈诺夫的合法化在他的文章中是作为一个项目,一个对于整个俄罗斯文化具有意义的项目而呈现的。С.邱普里宁曾敏锐地指出,《黑炸药先生》的成功乃是《独立报》和青年批评家精心策划的一个文学项目:“所有参与者的角色一开始就恬不知耻地分配好了。起初,在当代海报或电视节目字幕中描绘出作者庞大的构想(我们假设这是Л.皮罗戈夫)和工程指挥(А.伊万诺夫),然后小一点的是总制片(И.佐托夫)和联合制片(В.邦达连科),最后是最小的表演者、小说的作者 (А.普罗哈诺夫)。 ”[3](P189)他还指出这部作品具有明显的“订制”倾向:“由于新闻机构(毫无疑问是《独立报》)的指挥,立刻可以推算出订货人——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别列佐夫斯基。”[3](P189)批评家 Д.奥利尚斯基的文章《我如何成为一名黑帮分子》为这部作品大唱赞歌,他在文中放弃了自己“民主派的过去”,宣称自己是爱国派的一员,他高声宣布90年代的整个俄罗斯文学是 “自由派的布克奖的死气沉沉”,他在文末指出,“2002年最好的俄罗斯作家为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 ”[4](P205)
在《黑炸药先生》的观察者们看来,这些所谓的“宣传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某部小说的成功,也不是为这位受争议的作家打广告(在所有为普罗哈诺夫辩护的人中,真正对其个人感兴趣的似乎只有达尼尔金),而是重新划分整体的文化空间。奥利尚斯基直截了当地写道:“出现了一个赞扬狂暴的、不正确的、按民族方式思考的作家及作品的时代——读者因这些作品感到不寒而栗。真正的文学只讨论两个主题——死亡与政府。 ”[4](P206)
三
普罗哈诺夫的成功乃是2000年代俄罗斯社会一些倾向的鲜明反映:排外情绪的加剧、拒绝社会反映、对“伟大国度”的思乡病。这些复仇主义情绪与消费者对新实践的广阔兴趣相连,与对新的、西式的、现代的生活风格的追求相联。与此同时,在社会上弥漫着一些集体神经症和恐惧症,它们与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有关,与世界上的局部冲突的加剧有关,如南斯拉夫战争、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一些作者将民族主义、排外和孤立的言论、反对政权的情绪及对媒体和政治技术的无所不能结合在一起,结果他们比起以往的那些作家在俄罗斯文化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早在70年代,熟知普罗哈诺夫的一位半官方的苏联作家批评家,对他的小说受到如此之多的赞誉感到吃惊。最让人吃惊和害怕的是普罗哈诺夫的辩护者们,首先是Л.达尼尔金和В.邦达连科,宣称他不仅是一位民族思想型作家,同样也是一位先锋派和新派人物,这见证了俄罗斯文化中极右思想合法化的急剧转型。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俄罗斯民族派批评家的话语具有公开的反现代主义特征,他们诉诸于“根基”,痛斥先锋主义是一种异己的、资产阶级的和大众文化的现象。如今,普罗哈诺夫生搬硬造的、胡言乱语的表现主义风格被年轻一代批评家宣称为一种新型文学,甚至连资深批评家В.库里岑也认为普罗哈诺夫的小说很有才华。在为该小说开辟的网站上,库里岑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那些在伦理上无法接受但在审美上具有价值的作品。
自由派作家在评价《黑炸药先生》时产生了分歧:他们中的少部分人将所发生的争议视为年轻一代批评家大不敬的结果,如Б.肯热耶夫、А.聂姆泽尔、П.阿廖什科夫斯基,大部分人则认为是新闻媒体精心策划的一种阴谋的结果。许多自由派批评家认为普罗哈诺夫的合法化乃是后现代主义与其固有的拒斥审美标准及道德虚无主义的合理结果。著名文学评论家М.利波维茨基认为,撇开小说在后现代主义出版社“埃德·马尔吉涅姆”不谈,这一解释仍是某种视角的集体蒙骗。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М.雷克林和М.扬波利斯基在1992年成为“埃德·马尔吉涅姆”的创始人之后,曾公开论及普罗哈诺夫的风靡。年轻批评家И.卡斯佩和诗人C.利沃夫斯基则极力反对,甚至利用了“后现代主义者”之名,但年长一代的作者们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
利沃夫斯基在文章《这是动物学》中断言:“将技术至上的狂热与民族主义、排外相结合乃是法西斯主义常见的手段,我们尝试合法化的对象正是法西斯主义。 ”[5](P127)他将自己及自己的拥护者界定为左翼自由派,并郑重宣布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知识社会的计划。奥利尚斯基则撰文予以反驳,他痛斥自由主义是一种精神投降主义,并发誓,如果有朝一日在俄罗斯建立新制度的话,一定会射杀利沃夫斯基。利沃夫斯基在文章中列数了一些创新型作家,如 А.列夫金、М.希什金、А.戈尔德斯坦、Е.法娜衣诺娃等,在他看来,正是他们的作品确定了9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最终,这场争议完全不是关于普罗哈诺夫的,是关于民族主义亚文化的,也是关于俄罗斯文化在自由的90年代(在其发展的新阶段)所走过的道路的思考。
流露出感伤情绪的自由派批评家——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一辈(А.拉蒂宁娜、А.库兹涅佐娃等),都不认可这条道,认为这是文学的衰退和解体。在对待利沃夫斯基所列出的那些作者上,他们通常持仇视和警觉态度。普罗哈诺夫的合法化对于他们而言只是这种解体的一个见证。А.库兹涅佐娃这样谈及普罗哈诺夫的成功:那是“文学经理人们”活动的结果,如同“巴比伦塔”文学小组的实验诗人(利沃夫斯基也是该小组的一员)的诗集出版一样。М.利波维茨基认为在这场争议中,失望的自由派们分为对立的三组。
第一组以传统民族主义者为对手。他们在60—70年代开始发表文章,并决定随着普京的掌权发动为掌握文学的权力进行第二阶段斗争,这场斗争从此以后将按照他们习惯的苏联规则进行。
第二组是年轻的现代批评家——达尼尔金、皮罗戈夫、奥利尚斯基等,他们努力成为新阶段的思想主宰,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成为时尚的立法者。他们也认为自己的时代到了,这种感受是因为90年代文学场地不定型性和分散性,以及社会对待文学的态度。他们曾经思考“正常”文学复兴的特征。这些批评家的活动及民族浪漫主义作品的巩固,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俄罗斯200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的两个方面。该进程是20世纪新民族演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若不是因为新批评本质上是危险的,该进程会是非常自然的。达尼尔金在自己那些关于普罗哈诺夫的文章中,使用了由俄罗斯出版家А.伊万诺夫发明的表述“俄罗斯式愁苦”(русская хтонь), 该表述使人联想起“本质”和“土壤”这些爱国派的最高价值。由于讨论转向了“愁苦”,那些关注复杂的个人心理问题或传统家庭变化问题的作品受到了排挤。
第三组是失望的自由主义者们。如艾森贝格、利沃夫斯基、斯基丹、诗人兼批评家法娜衣诺娃。他们自认是20世纪俄罗斯非审查文学的继承者。跟第一组的自由派人士不同,他们否定地对待苏联文学经验,并未将在2000年代初出现的超级大国主义意识形态视为后现代主义的胜利,而是视作与苏联文化起源上相关的力量之复辟。诗人、批评家、新闻记者В.克里武林早在《黑炸药先生》出现前就最强硬地表达了那一立场:
曾是一个英雄时代,当时似乎真实的东西及存在主义式悲剧色彩的艺术有能力成功地对抗僵硬的、年老的制度,对抗完全的享乐主义及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冷淡,对抗“劳动知识阶层”的两面性,他们曾在司空见惯的对俄罗斯政治现实的恐惧中生活了数十年——他们希望事物已确立的秩序会自行改变:政府很快变得和善、人性、有文化,并且希望我们在一个“美好和狂暴的世界中”生活地轻松和幸福。
60—70年代末,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这一希望相违背。如今,正在进行一些将它忝列已倒台的苏联体系之中的尝试,并将其与该体系一起埋葬。何况扮演亚文化掘墓人角色的正是那些文学家或艺术家,他们过去最紧密和最令人脸红的方式与苏联官方相连……在改革时代,这些人肯定地说自己一直恨那些他们不得不为之而工作的主人们。他们害怕旧的文化特权阶层被新的从体制的审美对手中招募的人所取代。
他们保留了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新的文化浪潮没有赋予他们特权,新的文化特权阶层也没有形成。亚文化是平庸者们的组织,撇开其内部有才华的艺术家的人数与有才的传统者人数无法相比。如今,随着对过去的“秩序和昌盛”的相思病的加重,那些变老的“苏联意识形态的尉官们”指责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搞混艺术,消灭一体的俄罗斯文化。与此同时,真实的图景,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正在被歪曲,正在建立的一些前提正在歪曲将来的关于最新俄罗斯艺术史的理念。就是今天,恢复对事情的客观看法正变得困难。明天,我担忧就会太晚了。[6](P128)
四
综上所述,围绕《黑炸药先生》的种种争议,我们不难看出,当代俄罗斯自由派与爱国派批评之间围绕话语权所进行的斗争从未间断,在新形势下,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事实证明,两派之间的斗争不仅在苏联官方话语体系下才有意义,在解体后的苏联也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由派的胜利是得不偿失的,它不仅未能消灭自己的对手,而且也引发了自身的身份危机,在自由派话语内部期望一种更具社会、文化价值的立场。在这层意义上,自由派批评的危机再现了过去苏联知识阶层的后苏联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