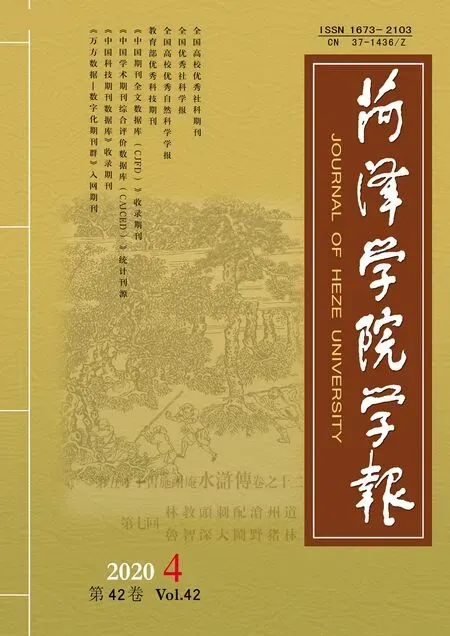论比较文学中的翻译文学
2020-01-19盛永宏
盛永宏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384)
至今为止,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较文学的内部研究也更丰富。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东方文学被纳入到比较文学的视域,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更加开阔,语言的问题也更为突出,于是,翻译的重要性引起人们的重视,翻译文学也随之受到更多的关注。
在个案的对比研究中,因为民族所具有的稳定性及其语言使用的独特性,所以民族文学被认为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所属的民族文学与异国的民族文学被放到一个平台或一个标准下进行比较研究,此时的异国文学需要被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即使研究者具备阅读甚至评论的能力,但在形成文字时仍然不可避免地需要将两种语言统一成一种语言来进行表述,于是翻译文学就更为重要。因为一个人无法熟练地掌握多种语言并进行阅读,所以对于大部分的读者而言,翻译是必备的。就如法国学者阿普特提出的:“把一种新的比较文学的前景置于翻译的问题中”[1],翻译成为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而翻译文学也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并给予它在学科中应有的位置。
一、存在论意义上的不可或缺性
翻译作为译介活动一直存在,从古至今翻译在民间的交流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但很多时候人们并未认识到这些,认为翻译仅是语言的转换,类似于工匠的手艺。“由于翻译受到轻视,作为翻译的一个类型的翻译文学自难幸免。”[2]翻译文学对促进民族间的交流、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但人们对于翻译文学的认知也仅限于此,没有做更深入地探究,在具体的操作中更多地表现在对翻译标准、方法和原则等的研究上,其成果可谓卷帙浩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比较文学进入自身发展的第三个阶段,面对理论大潮、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和文化研究的热潮三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比较文学迎来了新的生机和挑战。其中,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意味着比较文学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东方和西方处于两个文化圈,在价值观念、风俗信仰上异大于同,语言上的差异尤其突出,由此,翻译在这种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由于多元经济逐步替代寡头经济,殖民体系随之瓦解,现代社会的来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中心论”趋于解体,而之前处于文化边缘地位的东方文学开始挣脱过去的从属地位,“向中心移动,它们面临着借鉴当代意识,赋予传统以新意,使之发扬光大的使命。”[3]与此相应,西方的一些学者也察觉到过去比较文学自身发展的局限,认识到东方文学的价值,将东西方文学间的比较纳入到比较文学研究中,开拓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解决了之前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间的争论。于是,“在丰富而多元的当代翻译研究中,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范式。”[4]“它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它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5]它更加关注的是不同民族、文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进行的交流,不同的文化是如何沟通和交融的,及产生了哪些误读或歪曲的现象,最终对文学间的交流或影响产生怎样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翻译研究和文学翻译为比较文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翻译文学在传统的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中往往处于一种无所归属的处境,翻译研究一般注重的是语言间的转换、标准、效果等现象,并不关心它的文学地位;文学研究中往往只看到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的影响,而并不认同它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现象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张铁夫先生提出“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6]一说。
然而,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整体,它具有研究的价值:翻译文学与译语国的民族文学有怎样的关系?翻译文学可以等同外国文学吗?翻译文学在译语国的民族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的提出,涉及了翻译作品的价值,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再创造,延伸了作品的生命。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对此我国的前辈学者对此曾有过肯定,如矛盾先生和郭沫若先生等对于翻译的看法:“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7]而国际的学术界对此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将翻译文学视为民族文学(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过的两个版本的文学史,其中提到翻译的地方多达200多处,翻译者182人等。在我国一本作品有多种翻译版本,比较经典的就是《哈姆雷特》的翻译,各不相同,但又各有特色。这些都体现了翻译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对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而言,不仅开拓了研究领域,更是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存在的前提基础。
二、本体论意义上的创造性特质
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因为翻译者的个人风格、语言习惯等因素的不同,所翻译的作品也呈现不同的风格。另外,译著所处的时代和接受群体的不同也影响着作品的翻译。所以,作品在被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与原著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点出于不同的原因或隐或显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即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说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8]翻译文学因为这种创造性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创造性即是翻译文学的本质属性。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可分为有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和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两种。先看有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指翻译者在面对原著时,因为个人的翻译原则、特殊的追求目标及外在环境的影响因素等,采取了有意识的改变,如译著采用的文体、选取的篇章、是否属于转译等,这些方面都带有个人的喜好。以拜伦诗歌的翻译为例,马君武使用的是七言古诗体,苏曼殊使用的是五言古诗体,而胡适使用的是离骚体。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上,几位翻译者都使用了不同的形式,形成的效果也不同,甚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形成了差异,这其中的变化就在于翻译者的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另外,翻译者在选择原著进行翻译之前,也会根据接受环境和接受群体来选择译著所需要的词汇和风格。如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迄今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的最完整的、质量较好的译本。译本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为宗旨,译笔流畅、文辞华瞻。朱生豪先生的译著主要在20世纪的30、40年代集中完成,那时时局动荡,朱生豪先生不愿为敌伪效劳,仅靠微薄稿费维持极困难的生活,极尽忠实于原著,胜在“神韵”、文辞优美。当然这样的评价来源于与其它译本的比较。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人类文学的艺术史上达到了一个顶峰,其中包括他对戏剧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刻画及对人文精神的思考等,但在用词的选择、口语化的表达及民间手法的使用上都体现了迎合当时的市民需求的特点,并不完全高雅。但在朱生豪先生的译本中原有的粗俗化的言语都被摒弃,形成了有意识的叛逆。当然这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息息相关的,20世纪30、40年代,战火纷飞、国恨家仇、民不聊生,但在观念上整体比较传统保守,特别是在当时能够接受教育的人群基本来自于有产阶级,高雅、正统、风范等观念植根于这类人的骨子里,所以,朱生豪先生所采用的翻译原则使得他的译著广受欢迎,影响延续至今。这类主动型的创造型叛逆为作品赢得了生机,带有翻译者的个性。
在接受效果上,形成了归化和异化两者不同的效果:归化即译著在译语文化中被吞并的现象,如傅雷先生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除了人物的名字让人感觉生疏外,整部作品带有浓烈的本土气息。异化,即译语文化屈从原著文化的现象,如鲁迅先生主张的“硬译”就是典型的事例。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不能翻译的词汇等,就直接拿过来,慢慢地这种被拿过来的词汇也成为译语词汇文化的一部分了。最终,有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为文学自身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养分。
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是指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因为错误理解原文或是偶然漏掉了某些部分而造成的叛逆。这种叛逆往往来源于对原著所属的地域文化、风俗等不甚了解,按照字面的意思进行翻译,最终形成了“误读”现象。如生产生活中的一些意象被用来沟通交流时,东西方对它们的理解是不同的。以动物“狗”为例,虽然狗被认为是人类忠实的朋友,但在汉语的部分词汇中却表现出其他的意思,以带有“狗”字的成语、歇后语为例:“狼心狗肺”“狐朋狗友”“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狗血喷头”“狗眼看人低”“狗腿子”等,这表现出在汉语的语境中与“狗”相关的词的贬义性。在这样的语境中如果将“You are a luck dog”直接翻译“你是一条幸运狗”恐怕会引起祸端。类似的现象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很多,一些具有特定内涵文化意象的传递问题就更为复杂,所以这类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也会给文学间的交流提供素材。在这种意义上,“译本不仅是原作简单的生命延续和跨文化意义上的文学新生命,也是文学性和作品所隐含的文化意蕴的辐射和播散。”[9]
三、认识论意义上的民族文学养分源泉及组成部分
民族文学因其在形成的过程中依托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并受其民族自身社会、心理、语言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它往往反映的是本民族的审美心理和美学品格,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由此也成为比较文学研究展开的基点。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文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与外来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自身。特别是当民族文学所处的时代出现动荡,在民族文学急于改变的形势下,外来的文化往往就成民族文学汲取养分的源泉。
埃文-佐哈在《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中提到“翻译文学可以部分或全部填补这一空缺”[10],此处的“空缺”指向的是民族文学中“迫切需要的技巧储备”、新的文学样式、精神内质等。埃文-佐哈先生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不是固定的,根据不同的外在环境中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可区分为中心或边缘两种。其中处于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基本不被重视,一般是本民族文学发展的很快,远超于翻译文学,此时的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民族文学的影响不大。我们主要来看当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意味着它积极参与了多元系统核心的构建”[11]。因为此时的译入者并没有过多地考虑翻译文学与译入语民族文学间的差别,基本将二者视为一体,看重的是翻译文学中的一些全新的特征,如创造技巧、使用词汇等。由此可以看出,翻译文学为译入语文学提供了养分。但就此会有人说,这些养分的来源实质上是另一民族的文学,而非翻译文学,由此我们来分析一下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间的关系。
翻译文学的生成是由翻译者决定的,翻译者可以有两类人:第一类是译者将自身所属民族的文学译介给其他民族,此时译者对自己民族非常熟悉,但对其他民族的熟悉度要低很多,所以此时译者会选择自己民族最为优秀的作品进行译介,但译入语民族并不完全认同,由此导致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对译入语民族文学的影响小,成为译入语民族文学的点缀,仅为其民族文学增添一点异族文学的色彩而已,或可称其为不被直接需要的养料库。第二类是译者将自己熟悉的民族文学译介给自己的民族,此时因为译者非常熟悉自己的民族习性、风俗制度、接受习惯等,所以在选择原著时会考虑读者的接受习惯,或是会选择与本民族文学风格、美学追求等完全不同的原著,目的是借鉴学习,汲取其中能为自身所用的养分。又因为译者对本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极为熟悉,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将原著的内容本民族化,成为劳伦斯·韦努蒂在《翻译、共同体、乌托邦》中指出的:“通过翻译的任何交流都涉及某种本土残余物的释放,尤其是文学的翻译。”[12]由此读者看到的作品就很容易被吸引,此时的翻译文学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已经注入了译入语民族文学的色彩,在这种意义上翻译文学因为译者的因素,特别是上一部分中提到的创造性特征而使得翻译文学成为民族文学的一部分。
翻译文学与译入语民族文学往往处于边缘与中心,或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关系中,当外在的多元系统发生变化时,两者间的关系就会发生调转,这与翻译者的主观选择和个性特征相关,“最终促成(翻译)适当性的条件与对等现实高度重合的状态。”[13]译入语民族文学吸收的养分,加速发展,翻译文学因为浓烈的译入语民族气息而融入民族文学,成为其组成部分。
翻译文学因其自身的存在价值为民族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但在长期偏重于民族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使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变,翻译文学受到关注,但对它的性质、归属、走向仍然没有明确的界定。作为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基本要素,在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中,经常出现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的交叉处,容易引起混淆,无法分清作为研究对象的异民族文学是翻译文学或是外民族文学。由此,我们需要理清翻译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重新界定翻译文学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位置,给翻译文学以应有的学科地位,使其不再归属、依附于其他学科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