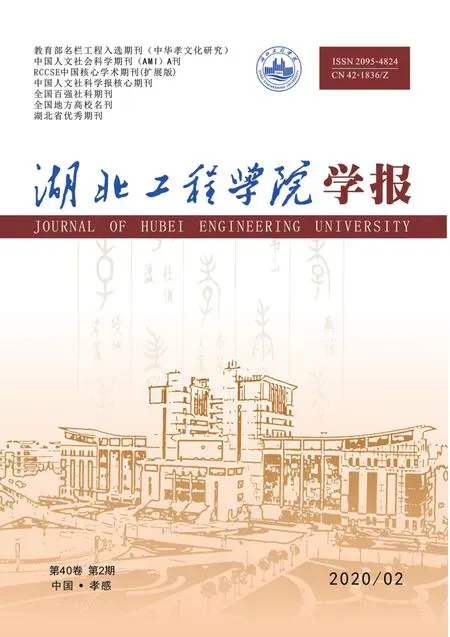布龙菲尔德之意义观刍议
2020-01-19王佳敏
王佳敏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1933年,列昂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语言论》出版,该书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之作。当前学界对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将布龙菲尔德语言观与索绪尔、萨丕尔、弗斯等学者的语言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如Koerner[1]、熊兵[2]等;二是整体评介布氏语法理论,如石安石[3]等;三是聚焦直接成分分析法,讨论其优劣及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如陆丙甫[4]等;四是探究“布龙菲尔德难题”,即向心结构短语与其中心语存在语法功能不一致的可能,如黄和斌[5]等;五是追溯行为主义心理学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如Sampson[6]、马庆林[7]等。
“语言研究必须从语音形式开始而非从意义开始。意义……只有无所不知的通才才能分析或加以系统梳理”[8]162,这类观点成为“意义不可知论”的直接导火索。对此,学界普遍认为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重形式、轻意义,后布龙菲尔德学派的一些学者,如哈里斯甚至在语言分析中完全排斥意义,只重形式[9],因而少有学者关注布氏意义观,系统考察布氏意义观的产生原因及其具体表现者更是少见。值得一提的是,黄倩认为布氏所主张的语言分析原则是立足于形式,兼顾意义,并使意义形式化。[10]296该观点虽对布氏意义观有了新的解读,但并未探讨其内在原因,也未深究其意义观的特征表现。深入研读《语言论》,我们发现,布氏虽然认为意义不易控制,语言分析须从形式着手,但文中多处提到“意义”一词,强调意义研究的必要性,如“本身微小而不重要的话语也是重要的,因为它具有意义”[8]27,甚至以“意义”单作一章,集中讨论。布氏认为语言学主要研究语音和语义,实用语音学和音位学都得以了解意义为前提,而语义学就是说明什么意义附着于不同的语音形式之上[8]137-138,由此可见布氏对意义研究必要性的重视。布氏坚持,根本没有人可以完全否认语义,语言研究需要考虑和运用意义。[11-12]一言以蔽之,布氏并非排斥意义,只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认为意义存在复杂性,主张语言分析先从形式入手,然而在理论层面,仍要顾及意义研究。基于此,本文拟从布氏意义观所产生的历史背景着手,探讨其基本特征,尤其是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多个层面的表现,以重新审视布氏意义观,旨在发现其内在本质。
一、布氏意义观的产生背景
为深入探究布氏意义观,我们认为有必要回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缘由,包括其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哲学和心理学基础。
第一,实践基础。美洲印第安人土著语濒临灭绝,由于种类较多,彼此差异较大,语言学家急需一套科学、完整的调查分析方法,以快速描写和记录这些语言。同时,二战爆发,为帮助军队迅速了解和学会南美、非洲等地的语言,语言学家需得掌握一套简单高效的语言描写分析技巧,加之传教的需要,这些现实因素驱动美国描写语言学迅速发展,从形式出发研究语言成为必然趋势。
第二,理论基础。在语言本质认识和语言分析方法上,布氏《语言论》受到了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影响。索绪尔注重抽象的语言体系,关注理论推衍,奠定了现代语言科学的基础,而布龙菲尔德关注实践性与易操作性,坚持理论与实践互为印证,使语言研究成为了一门科学。[13-14]虽然索绪尔基于社会心理学来研究语言,布氏基于机械主义和行为主义来分析语言,但在研究范围等多个方面,布氏延续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如索绪尔区分了共时与历时,提倡共时的语言描写,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则正是建立在对语言的共时描写基础之上。在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上,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a system of signs expressing ideas)”[15],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意义之间具有任意性。布氏基本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语言是一种“信号系统(a system of signal)”,从形式开始研究语言[8]162,由此奠定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第三,哲学和心理学基础。布氏深受机械唯物论范畴下的行为主义的影响,提倡用刺激-反应论来解释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把数理逻辑方法与传统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结合起来,主张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旨在取消“形而上学”,建立一种科学哲学。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只承认感性认识,排斥意识,将人类意识等价为刺激和反应,即将意识简化为感官、肌肉和腺体的运动过程[16],该主张实质上是从机械唯物主义的视角否认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否认意识的能动性。魏斯是第一位把行为主义心理学运用于语言研究的心理学家,直接影响布氏的思想,但魏斯本人实际又是受到华生行为主义的影响。Hymes & Fought指出:“布龙菲尔德从魏斯那里学到的是科学的理念,而非某种心理学”[17]。换言之,布氏实际上是继承和发展了机械主义和行为主义所蕴含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即摈弃内省,采用可观察、可验证的方法来对实验对象进行研究、归纳,主张实证论、决定论和机械论。
综上,快速记录和学习语言的客观需求,前人理论观点的熏陶,加之机械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濡染,在多重因素联合驱动下,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注重描写,多从形式出发,表现出三大特征:实用性、科学性和语言对比差异性[18],这也直接驱动布氏行为主义意义观的产生。
二、布氏意义观之特征表现
布氏将意义定义为说话人所处的情境和听话人的反应[8]139,认为语言中最重要的不是发音方式,而是说话人刺激和听话人反应两者联系所起的作用[8]128,这充分说明语言中意义的必要性。布氏意义观主要表现为三大特征:语境依赖性、形式制约性、所指多样性与模糊性。
1.意义理解依赖语境。言语交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呈现动态性,情境中的言语行为(如对话)和非言语行为(如手势)都有意义。布氏用杰克和吉尔的故事,说明语言是一种刺激-反应过程,并且强调言语行为的重要性。简单来讲,杰克和吉尔一起走路,吉尔饿了,看到树上的苹果,发出声音,杰克为她摘苹果。吉尔发出声音,其话语不一定是直接陈述她饿了这一事实,但杰克通过实际情况,立刻明白了吉尔的意思。语言的替代性反应和刺激(r…s)虽然本身没有价值,却使吉尔轻松得到苹果,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意义,使得听者能够通过语言刺激,产生实际行为反应,在这一过程中,语境发挥重要作用。语境对语义影响很大,同样的话,在不同语境中,可能会使听话人产生不同的刺激反应。如在四季分明的地区,一位母亲在冬天和夏天,对孩子说了同一句话:“你能穿多少就穿多少”。显然,如果该言语行为发生在冬天,意思是让孩子穿得越多越好,如果是夏天,则是让孩子尽量少穿,以免中暑。布氏认为,说者和听者的全部生活史决定言语行为的发生和行为发生前后的全部实际事项[8]23。语境的范围十分宽泛,不仅包括可观可感的外在环境,还包括说者和听者的文化、思想、情感、态度等诸多方面。如地铁里一个女孩给她男朋友打电话,她说:“我快到站了,你赶紧来地铁站接我。如果你到了,我还没到,你就等着吧。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你就等着吧”。同样是“你就等着吧”,但在两个不同的预设情景语境中,意思大不相同。第一句是让男生等着她,第二句则是叫男生走着瞧。当然,除了考虑语言的外部语境,有时还须回归词语本身,关注词与词的搭配等内部语境。如英语“dog days”本义指三伏天,而非狗一样的日子,又如汉语“文不加点”指文章一气写成,不用涂改,形容文思敏捷,下笔成章,而非写文章不加标点。在这类语言语境中,须避免望文生义,造成误解。
2.意义表征受限于形式。布氏认为“任何一种语言的意义只能附着于某些形式特征上”[8]168,对此,他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区分粘附形式(bound form)、自由形式(free form)、简单形式(simple form)、复合形式(complex form)、直接成分(immediate constituents)、最终成分(ultimate constituents)等。同时,布氏主张一种语言的语法由各种形式的有意义的配列构成[8]163,主要有四种配列方式:一是词序(order),组成成分出现的先后顺序影响意义,如“John hit Bill”和“Bill hit John”,两句中的施事与受事都正好相反。二是变调(modulation),次要音位运用不同影响意义,如“John!”和“John?”。三是变音(phonetic modification),主要音位发生变化影响意义,如“convict”,当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时,指“罪人”,在第二个音节上时,指“判罪”。四是形式选择(selection of forms),语法配列相同而成分不同,则意义不同,如带有感叹收尾音高的语素可能是呼唤或引人注意,也有可能是命令,分别如“Waiter!”和“Jump!”。又如“drink milk”和“fresh milk”,前者为动词词组,叙述动作,后者为名词词组,描述事物。
值得注意的是,意义对形式具有反作用。在直接成分分析中,最终语素成分的划分需以意义为准,换言之,层次切分需要考虑各个层次直接成分的意义[19],如“好天气”的直接成分为“好”和“天气”,而非“好天”和“气”,因为“好天”没有实际意义,又如“她们提醒队员穿好衣服,别感冒”中的“穿好衣服”分析为“穿好/衣服”而非“穿/好衣服”,因为其成分划分,受语境制约,需考虑更高层次的意义。
3.意义所指多样性与模糊性。布氏对意义的理解无处不在,涵盖范围很广,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语言论》中一系列概念都与其有关,包括词汇意义(lexical meaning)、语法意义(grammatical meaning)、内涵意义(denotative meaning)、转移意义(transferred meaning)等。意义与形式不可分割,但意义的理解受人类知识等多重因素限制,因此具有模糊性和多指性。总体而言,布氏“意义”包含语音意义、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语用意义和文化意义等,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语音意义。布氏认为语言研究主要有二:语音学和语义学,前者主要考察发音动作、声波、耳膜活动等语言事实,忽视意义,后者则需研究某种语音的发生情境,以及听话人的反应,了解发音、声波等语言要素与意义的关系。[8]74“在人类的语言里,不同的声音具有不同的意义。研究一定的声音和一定的意义如何配合,就是研究语言。”[8]27只有考虑话语的意义,才能确定不同声调的话语是否为同一个语言形式,如以不同声调连说“I’m hungry”,虽各语调存在差异,但其包含某些固定不变的声波特征,即属同一个语言形式。但汉语不同的声调可能表示不同的意义,如“调tiáo”和“跳tiào”,前者为升调,意指搭配均匀,后者为降调,意指两脚离地,全身向上或向前的动作。有时,同一声调可能表示不同的意义,如“跳tiào”和“眺tiào”,后者意指往远处看。“只有在我们知道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认识一段话语的区别性特征”[8]77,布氏认为只有与意义相关的语音特征,才是区别性特征,才是交际所必要的,这表明意义在判别话语的区别性特征上起到参照作用,同时说明意义在语用交际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词汇意义。《语言论》中的词典意义、中心意义 、转移意义、广义意义、狭义意义等都指词汇意义。另外,对语素和义素的定义也都涉及意义,即语素是最小的有意义单位,而义素是语素的意义。布氏认为词汇意义变化多端,主张将语言形式二分为常规意义(中心意义)和边缘意义(隐喻或转移意义)。人们通常基于中心意义去了解某一语言形式,除非实际环境迫使其选择转移意义,如“car”本指汽车,在“The dinner is the second car forward”中指火车车厢,这说明语境以及词汇意义本身对语言形式的理解起重要作用。有时,转移意义由形式结构决定,如“pussy(小猫)”和“willow(柳树)”复合成词时,“pussy-willow”转义为“絮柳”。“对于任何一个说话人,一种形式的意义只不过是他在某些环境里听到这一形式的结果”[8]151-152,如“give out”,在小句中作及物动词词组时,多指“分发”,作不及物动词词组时,常转义为“花光、耗尽”,这表明转移意义通常依赖于语言结构,即意义依赖于语境。布氏还提到九种语义变化的情况,即语义缩小、语义扩大、隐喻、转喻、提喻、弱化、强化、贬义化、褒义化等,并且认为词汇意义发生变化与外在环境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三,语法意义。布氏将语法定义为,一种语言中各种形式的有意义的配列[8]163,词序、变音、变调、形式选择等语法单位(即“法位”)都会对意义产生影响。每个法位就是一个结构形式,加上意义,就构成了语法元素(tagmemes),即语法形式的最小意义单位,而语法元素的意义就是语法元素意义(episememes)。“任何有意义的、重复出现的这些成套的语法单位就是句法结构”[8]184,如“John ran”,“John fell”,“Bill ran”,“Bill fell”这四个皆为施事-动作结构,包含选择法位和词序法位,在选择法位中,“John”和“Bill”为主格表达,“ran”和“fell”为定式动词表达,两者无法互换使用;在词序法位中,主格表达在定式动词表达之前。施事-动作结构的意义在于:任何体词就是一个施事者,执行定式动词词语的动作,前者处于施事位置,后者处于动作位置,两大成分无法互换。[8]185甚至一些非完整结构,如顿绝语(aposiopesis)、错格语(anacoluthon)、犹豫形式的插语中,说话人所说的话仍有意义。总之,任何一个语法单位如单独取出,就无任何意义,它们的结合却能构成一个语法元素,表达一定的意义。
第四,语用意义。布氏将意义直接定义为“说话人发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景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儿所引起的反应”[8]139,这反映了布氏行为主义思想,表明他注重语境。“言语行为的发生和行为发生前后的全部实际事项的过程,都取决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全部生活史”[8]23,在通过语言传递信息,表达意义时,需充分考虑当时、当地、当事人的具体语境。语用意义可以说是布氏行为主义意义观最直接的表现。
第五,文化意义。布氏在谈到内涵意义时,认为一些语言形式,如方言、外来语、俚语等,很难摆脱附带意义的影响[8]152-157,如数字13,在欧美国家里通常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此处的附带意义指的就是语言使用中的文化意义。又如某些不合时宜的语言形式,人们通常回避使用,如“die”和“death”等不吉利的话,或“hell”等宗教禁忌语,或“whore”等不得体的语言等。有些语言为表尊敬还会避开第二人称代词,如“your Honor”。
有时,布氏将几种意义混合来谈,最典型的就是将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结合,如“一个语音形式加上它的意义就构成一个语言形式,一个结构形式加上它的意义就构成一个语法形式”[8]166,第一个“意义”指词汇意义,第二个指语法意义。“语言信号中有意义的特征包含两种类型:由音位组成的词汇形式和由语法单位组成的语法形式”[8]264,词汇形式与语法形式联系紧密,一方面,词汇形式所表现的语法结构有一定意义,另一方面,任何一段实际话语中的词汇形式都有一定的语法功能。词序、变音、变调、形式选择等法位不仅包含语法意义,还涉及词汇意义,甚至是语用意义和修辞意义,如“Away ran John”和“John ran away”,两者句义相同,但词序法位不同导致结构不同,前者为倒装句,后者为陈述句,并且前者更为生动。
三、布氏意义观的几点思考
布氏意义观的焦点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深受机械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影响,布氏意义观表现出两面性,辩证性与局限性共存。
1.形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形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布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形式与意义是否孤立的问题;二是形式与意义的地位从属问题。第一,语言研究中,形式与意义具有不可分割性。“具有意义的语音形式就是语言形式,包括句子、短语、词、具有意义的音节等”[8]138,“一个形式往往把它说成是表达意义的”[8]141。《语言论》中,形式与意义的结合随处可见,如语素和语法元素等概念的确定、区别性特征的确定、直接成分分析法的运用等等,都需要意义的参与,这表明语言形式与意义难以分割,不可孤立看待。第二,从形式出发,兼顾意义。布氏主张基于形式分析语言,以归纳语法形式,区别语法意义。布氏在分析语言形式时,将语法形式和意义有机结合,因为在同一个语言社团里,某些话语在语音和意义上是相似的或者部分地相似,而相似话语的共同部分都有一个稳定的语音形式,一个语音形式加上意义构成语言形式;结构形式加上意义构成语法形式。不可否认,布氏深受机械行为主义的影响,对意义的理解表现出消极的一面,但这并不能说明布氏完全忽视或排斥意义,而是对意义研究设定了高标准,不仅要有精确的知识和科学的分类,还要考虑环境、肢体语言等多重因素。布氏意义观中意义所指的多样性和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布氏已经认识到意义研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并试图对其进行层次划分,他提出一系列概念来描述语言形式,如自由形式、粘附形式、语素等,并把一种语言的语法形式归纳为句型、结构和替代三类,这些内容为普通语言学中形态学和句法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语言研究从形式出发,兼顾意义,这是语言研究方法的一种选择。黄倩认为,布氏从形式入手研究语言,通过实际观察和描写,使语言学走上科学之路。[10]295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史看,从形式描写入手研究语言,有力推动了英语等印欧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语法形式的类别划分问题上,布氏批评传统语法“以类义定形类”,过于依靠意义,指出一切形类都不能根据意义来加以规定,而因根据语言的词汇或语法特征,即其功能,加以判断。[8]264-269布氏反对完全根据意义来识别和规定词类的做法,对词类划分意义重大,不仅在当时是一大进步,而且对现在的语言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2.布氏意义观的两面性。第一,布氏意义观的辩证性。一方面,布氏主张将语言稳固的、可确定的意义作为研究前提,提出语言学的基本假设:“在特定的言语社团中,某些话语在形式和意义上是相似的”[8]144,这意味着每一个语言形式都有一个固定的、具体的意义。另一方面,布氏强调语言形式的意义依赖于语境,呈现动态性,即同一语言形式可能因语境不同,而意义发生改变。这说明意义具有双重属性:相对静止性和绝对变化性,前者实质指语言的基本概念或中心意义,后者则指其扩展概念或特定语境下的边缘意义。另外,在形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上,也体现出辩证色彩。一方面,布氏主张形式决定意义,相同形式的不同配列方式或不同形式的相同配列方式都会对意义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意义对形式具有反作用。在直接成分分析中,最终语素成分的划分需以意义为准。第二,刺激-反应论对意义解释的局限性。布氏深受机械唯物论范畴下的行为主义的影响,把语言视为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一系列的刺激和反应过程,把言语刺激看作是客观实际刺激的等价物,这一想法实质上是忽视了语言的社会本质,疏忽了语言的概括性与抽象性。[20]实际刺激是具体可感的,通过事物本身的物理特性进行,是第一信号,而言语刺激是通过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引起反应,是信号的信号。将言语刺激等同于实际刺激,认为意义只能用第一信号来表示,是抽象意义无法得到解释的重要原因。行为主义意义观借助指示法、婉转法、翻译法等去解释那些具体可感的语言表达,如表示事物动作、性质、状态的词语,但是对于很多抽象词汇却无能为力,如“爱”“恨”“和蔼”等,而这些难以确定意义的词在词汇里占了绝大多数。[8]139
正因行为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对意义研究的高标准,《语言论》中多处有关意义的表达都带有消极色彩:“为了科学、准确地定义每个语言形式的意义,我们必须对说话人世界里的万事万物都有科学、精确的认识。人类的实际知识跟这种要求比起来,着实有限。”[8]139“对于语言中绝大部分的意义,我们甚至还找不到一种求助于外部标准的方法。同社会行为有关的一些名词,只有当人种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今天所梦想不到的完善、精确的地步,才能定义。那些只有本人才感觉得到的人体状态名词,只有当我们有了关于活的人体内部活动的详尽知识,才能确定。”[8]280布氏认为,很多心理活动在机械主义者看来,只是人体各种活动的一般通行术语。如果这一活动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们就无法做出反应,只能通过话语或其他可观可感的动作去了解他人的内心活动,即通过说者的实际环境和听者的反应来确定意义。[8]142-144布氏之所以认为抽象词汇难以定义,是因为他混淆了词义与客观所指,忽视了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将产生语言和理解语言的过程做了简单化处理,以维护其行为主义语言学思想的自洽性。
四、结 语
深入学习《语言论》,我们发现,布氏意义观的产生是多重因素联合驱动的产物,主要缘于客观实践需求、前人理论奠基、经验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濡染。语境依赖性、形式制约性、所指多样性与模糊性是布氏意义观的三大典型特征。布氏意义观主张语言研究从形式出发,兼顾意义,形式与意义不可分割,体现出辩证性与局限性。本文重新解读布龙菲尔德意义观,旨在澄清有关布氏“只重形式、轻忽意义”的模糊认识,并为形式与语义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