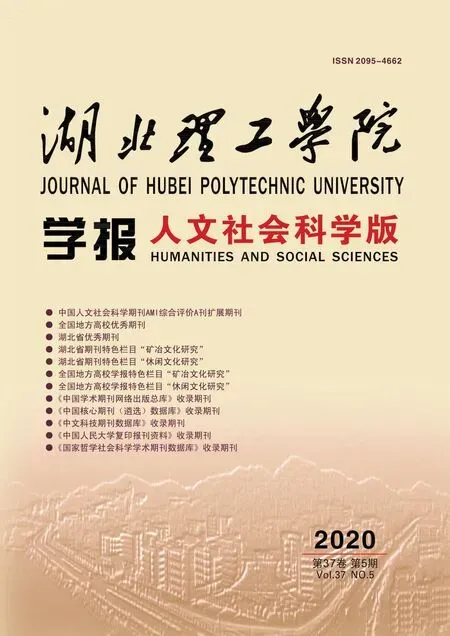论慧能禅身心合一的休闲智慧*
2020-01-19孙敏明
孙敏明
(浙江万里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随着西方“身体美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和中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的加速,身体美学的倡导者舒斯特曼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他说:“虽然我的身体美学思想源自于实用主义,但是古代中国哲学在身体美学思想的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身体美学思想强调和考察了身体,即活着的、感性的、有目的的身体,将其视为所有感知活动不可或缺的媒介。”舒斯特曼在他的著作和论文中多次说明“身体美学”是个很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它绝不仅仅是关注身体外在形态的美或规范,同样“关注身体自身之知觉和意识的内在能力”,“它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由我们的行为举止所导致的我们的行动和周围环境的含义、理解、成效和美感,以及从这些行动和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行为举止所得出的精神和意义”[1]41-47。本文即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反观中国禅宗思想中的禅修和禅悟,做一些思考和探究,应该是有意义的。
禅宗思想是佛教思想的中国化,慧能可谓是中国禅宗思想的确立者,他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经过神会等弟子的大力倡导,从声势和影响上压倒了神秀,成为禅宗的正统。由弟子法海根据慧能在韶州大梵寺说法而记录下来的《坛经》①是唯一一本由中国僧侣所著且被称为“经”的著作,也被当作南宗禅甚至是禅宗的“宗经”。本文主要以慧能禅及其流派为研究对象,从身心的感受、体悟和实践等角度来考察其身心合一的禅修和禅悟。
一、禅修的理论革新及方式
(一)理论革新:“由定发慧”到“定慧一体”
关于禅的本义,宗密说:“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中华翻为思惟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称为禅那。”[2]422可见禅的本义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定,也就是安定身心;其二由定发慧。前者重在身体行动,后者重在思维活动。这种坐禅的工夫从禅宗初祖达摩开始,如达摩以“壁观”法门为中心,“以壁观教人安心,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2]433又如四祖道信有“闭门坐”,五祖弘忍常常是“萧然端坐”,到南能北秀的北宗神秀,其方法宗密说是“息妄看净,时时拂拭,凝心住心,专注一境,及跏趺调身调息等也”[2]433。可见禅定的修习方法源远流长,早就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程式。
但慧能对此种禅修方式做了极大改革,认为定慧不应是禅修的两个阶段而是一体的,“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一三)。“定慧一体”的提出打破了原来的坐禅程式或规范,不再教人坐禅入定,而是偏重于对自我心性的修炼,将外在的实践活动和内在的主体意识相结合,从内心的觉悟上来用功,即修“般若行”,成就“般若智慧”。
慧能对“禅定”重新加以解说:“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禅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名禅定。”(一九)取消静坐不动息想摄心的禅定,而重在内心的觉悟,于是禅修不再是形式上的枯坐,而与日常生活的种种生命活动相融通,“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三六)。禅师和普通人的差别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出家,比如持戒、坐禅等外在程式和规范,而在于能否明心见性,顿悟自我佛性之完满。
(二)禅修方式
1.耕种劳作
慧能禅摒弃持戒、坐禅等修持工夫,主张任运自然的生活,饥来吃饭困来眠。从表面来看,禅师们的日常生活与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差异,而禅修就体现在担水、劈柴、饮茶、种地这些日常活动中。
将禅修融入到耕种劳作,可以追溯到四祖道信时期。起初达摩禅在传法方式上是“游化”形式,禅师来去无定,随缘而住;后来四祖道信定居双峰山,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僧众团体,为保障生活道信开创了农禅并重的禅风。五祖弘忍在道信门下,“常勤作役”,早上待人差遣,晚上坐禅;神秀见弘忍后,“决心苦节以樵(打柴)汲(打水),自役而求其道”;慧能初到弘忍处也是在椿米房做活。可见,从事劳作是禅修的一贯传统,之后作为慧能禅重要继承者和发扬者的怀海禅师,为禅宗制定了丛林清规即“百丈清规”,其中有一条为“普请法”。在《敕修百丈清规》中记载:“普请之法,盖上下力均也。凡安众处,有合资众力而办者,……除守寮直堂老病外,并宜齐赴。当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3]可见寺中一切人,除了值守和老弱病者,不分职务高下,一视同仁,人人出坡劳作。在《五灯会元》里就有记录弟子因不忍怀海禅师辛勤劳作悄悄藏了工具,而怀海禅师严格遵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故事。
沩山灵佑继承了百丈怀海的衣钵,与其弟子仰山慧寂开创了沩仰宗,他们重视耕种劳作。师徒间有一段小故事:“师夏末问讯沩山次,沩曰:‘子一夏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所务?’师(慧寂)曰:‘某甲在下面,锄得一片畲,下得一箩种。’沩曰:‘子今夏不虚过。’”[4]530灵佑禅师对慧寂禅师一个夏天的劳作做出充分肯定,认为这样才是不虚度时日。
2.茶禅
《晋书·艺术传》里有关于坐禅饮茶的记载:“僧人单道开坐禅,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饮荼苏一二升而已。”单道开开启了茶(荼苏)和禅相融合的大门。后来僧侣们种茶、制茶、饮茶,以茶待客,以茶助修,以茶供佛,到唐代僧侣已将茶事看作参禅悟道之物,在《敕修百丈清规》中完备地记录了禅茶礼的内容、特征、仪式等。
茶禅是通过对茶的体认和感悟而进行禅修禅悟的一种方式。茶对人的作用,从生理上讲可以解渴祛乏保健养生;从心理上讲可以调和情绪,平复心态;茶的自然清新淡雅使人心旷神怡,安宁恬淡,从而提升精神境界。赵州从谂禅师(慧能的第四代传人)“吃茶去”的公案,是一则禅宗史上的佳话。“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4]204再度前来的僧人应该有不少疑惑想向大师求教,新到的僧人头一次见大师,觉得应该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院主听到大师用同一话语告诉不同情况的两个僧人,总觉得有什么深奥的道理隐含在其中,而从谂禅师让他们统统都“吃茶去”。茶清香甘甜,略带苦涩,只有在平心静气时,才能充分品味茶的妙处,也正是在品味自然清雅的茶味中,人生的种种杂念妄想慢慢消歇,这也正是禅的“平常心是道”。
3.亲近自然
禅师们的生活是清贫辛劳的,但他们却有着从容豁达、自然率真的性情和气度,这也得益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游历山水、欣赏自然风光是禅修禅悟的重要方式之一。正如《五灯会元》的《云门文偃禅师》篇所言:“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游山玩水。’”[4]929
宋代无门慧开禅师做过一首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说的便是在自然界的水流花开、四季流转中保持恬淡的心情,便处处皆宜,回归生命的质朴和单纯。在大自然中悟道的例子很多,我们仅看两例。临济宗云峰文悦禅师写过一首《原居》:“挂锡西原上,玄徒苦问津。千峰消积雪,万木自回春。谷暖泉声远,林幽鸟语新。翻思遗只履,深笑洛阳人。”[5]60初春时节,文悦禅师挂锡西原,本图闲散无事,但参禅的弟子们却不停地前来探问修成正果的门径,该如何回答他们呢,任何禅理的解说都是多余的,甚至是缘木求鱼,还不如来一起欣赏眼前的景象:群峰积雪消融,万木回春,一片翠色;深谷回暖,泉流丰沛,水声传向远方;深幽的山林中百鸟欢鸣,声音显得特别的清脆。目之所及,耳之所闻,身之所触,处处是大自然焕发的蓬勃生机,哪里还需要去苦苦寻求什么“祖师西来意”,只有将禅的名相彻底剔除,即物而真,感悟到生命的澄明宁静,这便是禅。又如汾阳善昭禅师《示众》云:“春雨与春云,资生万物新。青苍山点点,碧绿草匀匀。雨霁长空静,云收一色真。报言修道者,何物更堪陈。”[5]61这是一幅清新淡雅的春日烟雨图,对于习禅者而言,这便是最好的感悟:春日云行雨施,万物新绿,远看重峦叠翠,近看碧草如梳,雨后初霁,天宇澄明。个体沉浸在大自然中,消融了所有外在的干扰,获得直观感受,这也正是禅所谓的“现量”——“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发,不加思索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6]360通过这两首临济宗的禅诗,我们可以了解禅者如何在自然图景中获得即色即真的禅意感悟。
二、顿悟的机缘和法门
佛教的目的是教人解脱,即成佛涅槃。在慧能看来,每个人心性本自清净具足,成佛不向外求,而是向内了见自我自足的心性。
一般都说南能北秀、南顿北渐,似宗派分明,而慧能说:“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渐顿?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渐顿。”(三九)可见所谓的南宗北宗的区别,首先是地域上的分别,第二是学人悟性的差异。明心见性的成佛目的是一样的,神秀“时时勤拂拭,勿使有尘埃”,要人做渐修的功夫,主要适用于钝根人。慧能的工夫则从根本上来做,不讲渐修的工夫,适用于利根人。顿悟可以是每个人当下的每一个念头,但顿悟是极其讲究机缘的,如沩仰宗的香严智闲禅师写过一首《独脚颂》:“子啐母啄,子觉母壳。子母俱亡,应缘不错。同道唱和,妙云独脚。”[5]98用“子啐母啄”来类比禅师指导弟子开悟。蛋孵熟了,鸡子在里面啐,母鸡在外面啄,必须同步。如果时候未到,鸡子未啐,母鸡先啄,则鸡子死,亦或母鸡不啄,仅鸡子在里面啐,力量不够,鸡子死。
在慧能禅后来分化的不同宗派中顿悟的理论是一贯的,但触发方式有所不同。顿悟法门常见的有与物相接“触类见道”,机锋相交顿现真如,而顿悟又是极具个性化的“独知”体验。
(一)触类见道
身心无时无刻不与万事万物相接触,在行住坐卧、语默动静中都潜藏着悟道的机缘。南宗禅师们单刀直入,触类见道的顿悟例子有许多。如“磨砖作镜”的故事是大家熟知的,怀让禅师通过磨砖的行为启迪马祖道一,既然磨砖不能成镜,那坐禅亦不能成佛,由此打破了马祖道一一直以来枯坐不悟的状态,幡然醒悟心外无佛,成佛只在自悟本性。
我们再来看一首曹洞宗开创者洞山良价禅师的开悟诗:“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5]130这是洞山良价参见云岩昙晟问“无情说法”后返回,涉水过河,看到河中的影子忽然得到了悟。河水倒映出自己的影子,那影子正是我或说我的显现,影子处处跟随着我,完全依附我的存在而存在,但影子终究是虚幻的,不具有我的真实性,虽然不能说影子不是我,但我却不是影子。这就是“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南怀瑾先生说:“佛性虽然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但是并没有一个能够被直观地认识和把捉的实体,因此我们必须借助于心、相之用,从心与相的关系和作用上,才能意会(悟)到它的存在……若无性体即无以成其心、相,若无心、相,亦无以显出性体。”[7]89洞山良价禅师正是从河水的影子里领悟到了心相和心性的关系,开悟到了“真实的自我”。
触类见道中的一种常见方式,就是在自然景致中悟道,这在上文已有所涉及,这里再举一例。据说是唐代无尽藏比丘尼写的开悟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寻春的过程即为访道的过程,开始时不辞辛劳地向外找寻,走过山山水水,但“春”似乎无从可得。失望疲惫地归来,无意间摘下一朵梅花,放在鼻下嗅着它的香气,这才忽然醒悟,一树盛开的梅花,不就是自己找寻的“春”吗。当抛开一些汲汲追索的东西,而以舒缓平和的心态来对待事物时,自我的本真和澄明正可以映照出物的本来面目。慧能禅的心性论,正是强调了心性清净和个人真切的领悟体验。
(二)机锋棒喝
能否开悟,关键在于迷悟的主体,悟的机缘也常常依靠言语机锋的相互磨砺,甚至在当头棒喝的情急之下,身心大受激荡,闪现思想的火花,从而顿悟自我之佛性。
如临济宗开导弟子禅风凌冽,手段辛辣。《临济录》载:“有定上座到参,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下绳床,擒住,与一掌,便托开。定伫立,旁僧云:‘定上座何不礼拜?’定方礼拜,忽然大悟。”[5]54定上座来问佛法大意,禅师跳下禅床,一把将其擒拿住,飞掌而击,又推开。旁边的僧人提醒他礼拜,礼拜之时突然开悟。这便是超越了言语的特定情境中的领悟。又如“师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什么?’师曰:‘野鸭子。’祖曰:‘甚处去也?’师曰:‘飞过去也。’祖遂把师鼻扭,负痛失声。祖曰:‘又道飞过去也。’师于言下有省。”[4]131百丈怀海也正是在马祖道一禅师的扭鼻子、当头棒喝得“三日耳聋”等种种机缘中悟道而成为一代大宗师的。
顿悟是某种特定情境中身心合一的体悟,具有亲证性、独特性和个性化的特点。如宋代临济宗杨岐派著名禅师圆悟克勤在听了师父例举的两句艳诗“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后有所悟,遂作诗一首:“金鸭香炉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4]1254这是一首小艳诗,少年和佳人之间的温柔甜蜜只有当事人自己知晓,不是语言所能表达,也不是他人所能体味的。这也正寓意着禅悟是一种佛法大意与自我的心心相印式的自悟自得。
三、顿悟后的禅境
禅师们在顿悟之后,依然是平常的生活,但境界迥异。
(一)无念、无相、无住
悟的境界在心理上达到的是“无念、无相、无住”的“三无”之境。
慧能说:“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自清净。”(三一)“无念”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是对外在事物的无知无觉,而是不以任何一种偏见或执念去看待事物。关于“无相”,慧能说:“何名无相?无相者,于相而离相。”“但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一七)可谓是以纯然超越功利的态度对对象作纯表象直观。“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系缚也。”(宗宝本《坛经》)[2]44简而言之,“三无”是一种对万事万物去除了世俗利害关系的考量,是一种不离万物又超然于万物的心理状态。
这样的境界也可以称之为“无心”的状态,呈现为“空静”的特点,空不是空无所有,而是涵容了万物。慧能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二四)正如苏轼在《送参寥师》一诗中如此形容参廖禅师,“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也正是禅者排除了外在的种种干扰而直达其清净的自性。徐复观先生曾指出:“‘性之德’为静,人必须把生命在陶熔中向性德上升,即是向纯净而无丝毫人欲烦扰夹杂的人生境界上升起。”[8]27这便是自性与佛性合一、小我与大我合一的大境界。
禅者“随缘应用”,无心于万物,一派天机自然,便成为了一个悠游自在的闲人,如《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载:“问:如何得不落阶级?师云:终日吃饭,未尝咬着一粒米;终日行,未尝踏着一片地;与么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2]236
(二)“禅者,活泼泼也”
禅境的特点是恬静、单纯、朴素的,却也是活泼而生动的。赵州从谂禅师曾说:“禅者,活泼泼也,非枯木死灰。”比如云门宗的禅诗里就有通过牧童形象来表达禅的这种活泼和快乐:“雨后鸠鸣,山前麦熟。何处牧童儿,骑牛笑相逐。莫把短笛横吹,风前一曲两曲。”“寒气将残春日到,无索泥牛皆勃跳。筑着昆仑鼻孔头,触倒须弥成粪扫。牧童儿,鞭弃了,懒吹无孔笛,拍手呵呵笑。归去来兮归去来,烟霞深处和衣倒。”[5]178前一首写麦子成熟的秋天,后一首写天气渐暖的春天;不管在新雨鸠鸣的雨天,还是烟霞正浓的晴天,牧童们倒骑牛背,或风中吹笛或嬉笑追逐,不识佛祖,无妄无真,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乐趣。
(三)气象雄浑
禅者的境界除了任运自然,还有气象雄浑的一面。从慧能禅明确提出佛性就在自性,成佛是向内修心,明心见性,于是极大地提高了自我的主体性地位,从“小我”而进入“大我”,“大我”即是佛性之我,与山河天地融为一体,表现出打破一切外在权威的自信与豪情。如百丈怀海禅师在回答僧人“如何是奇特事”的时候形容自己:“独坐大雄峰。”据《江西通志·山川略》记载:“百丈山在奉新县西一百四十里,冯水倒出,飞下千尺,西北势出群山,又名大雄山。”而且“大雄”又是释迦摩尼佛的尊称之一。独坐大雄峰的修行似乎很平常,但又似乎很不平常,禅者独坐于大雄峰上,俯瞰滚滚红尘,熙来攘往,有着阔大的胸襟,宏伟的气象和沉静的态度。又如李翱在《赠药山高僧惟俨》诗中是这样形容惟俨禅师的,“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高僧直登孤峰高顶,当云散月出之时,他洪亮的笑声在山谷间回荡,这想来也是豪情万丈的情态。在《临济义玄禅师》中,义玄和凤林禅师机锋相对时有一句对自我的形容:“孤蟾独耀江山静,长啸一声天地秋。”[4]648是说一轮孤月,无限江山,禅者惊破夜空的长啸,让天地都为之动容。
(四)保任的工夫
禅者在明心见性之后,从悟境中转身而出,度化众生。证悟是不可言说的内证境界,而如果存有了了悟的观念或沾沾自喜于了悟,也就不是真正的悟了。因此临济宗讲究“无垢人”还需精神的洗浴,“一物不将来”时还要“放下”,悟后要继续保任的工夫。
如何“保任”“自肯”,可以看曹山本寂禅师的回答,“问:‘学人十二时中,如何保任?’师曰:‘如经蛊毒之乡,水也不得沾着一滴。’”[4]791禅者在“一念顿悟自理”之后,“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2]437。宗密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两种清净,分别是本性清净、离垢清净,在本性清净的基础上往往还需要渐修达到离垢清净的状态;也有两种解脱,分别是性自解脱、离垢解脱,在前者的基础上还需要渐修来达到离垢解脱的状态。两种清净、两种解脱相结合才是完满的。
综上所述,从禅修的方式、顿悟的法门和顿悟后的境界来看,慧能禅在理论上虽然具有本体性的“心性”要远远高于“眼耳鼻舌身意”的身体感官感受,但其实都强调了身心合一的体悟或实践,也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特点。对于西方哲学中占主要地位的主客二元论而言,舒斯特曼对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眺望是确有道理的。慧能禅身心合一的禅修和禅悟,对于今天如何安放身心的休闲理论也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注 释
① 《坛经》全名《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除法海本外,还有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等。《坛经校释》由慧能著,郭朋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全本分57节,下文所引原文如没有特别说明,均出自该书,仅注明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