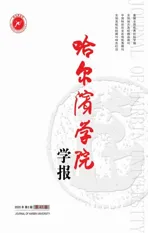试析“宝玉摔玉”的思想意蕴及艺术特色
2020-01-19王丽频
王丽频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 阳泉 045200)
《红楼梦》是一部有着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著作。在这部作品中,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经典片段,如第三回“宝玉摔玉”,不仅意蕴丰厚,平常琐碎中蕴含着无限的烟波,而且在整本书的布局结构中,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从人物出场上来看,中心人物贾宝玉在前两回的层层铺垫中,第一次正式登台亮相,贾宝玉和林黛玉第一次相遇相识;从内容情节上,“宝玉摔玉”是“石头”(贾宝玉)下凡历劫的前奏,也是宝黛爱情即将开启的序幕。可见,“宝玉摔玉”作为小说正式的开场锣鼓,写什么?怎样写?无疑对后文的人物性格、情节发展发挥着定调定性的关键作用。因此,探寻“宝玉摔玉”的意蕴及艺术价值,对深入理解作品至关重要。
一、“宝玉摔玉”的深层意蕴
(一)宝玉思想性格的凸显
第三回中,宝黛初次相遇,本来是亲人团聚其乐融融的场面,可是因为林黛玉没有玉的一句如实回答,致使贾宝玉顿时发起痴狂病来,将脖子上佩戴的晶莹美玉狠命地朝地上摔去。这块玉并非普通佩物,而是贾宝玉出生时口中衔着的那块“通灵宝玉”。尽管它是“石头”的幻象,但是在不知真相的世人心中却无比神奇珍贵:贾母视它为宝玉的“命根子”,黛玉认为它是世间“罕物”,北静王则称赞果真“如宝似玉”。贾宝玉作为贾府寄予厚望的接班人,“玉”不仅关系其自身的祸福安危,而且还关系到家族的兴衰荣辱。在世人眼中,“玉”是贾宝玉不同凡俗、地位尊贵的标志。可见,与生俱来的 “通灵宝玉”对贾宝玉意义非凡。从常理上讲,贾宝玉应该视玉如己,加倍珍惜。但他却一反常态,不仅不珍视,反而要狠命地摔玉。
为何要“摔玉”?宝玉以为,家中的姐姐妹妹都没有,唯独他有,如今来了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见玉不是什么好东西。从宝玉的话语来分析,“摔玉”的原因有三个:一是“通灵宝玉”不通灵。宝玉惊世骇俗的名言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1](P28)在他心中,女儿是真善美的化身,她们与世俗社会浊臭逼人的男子有着天壤之别。正是这份深厚的女儿情怀,被众人称为“活龙”“凤凰”的贾宝玉时常感到自惭形秽,多次以“浊物”“浊玉”自称。在他看来,“通灵宝玉”既然是世人眼中美好吉祥之物,他如果有玉,那么家里的姐姐妹妹也应该有,“神仙似的妹妹”更应该有,但她们偏偏都没有,可见“通灵宝玉”并不通灵,只是徒有虚名罢了。二是“玉”制造了他与众姐妹的差别。在珠环翠绕的“女儿国”中,贾宝玉是“怡红公子”,是闺阁中的良友,而不是高高在上“主子”“二爷”。既然姐姐妹妹们都没有,唯独自己有,他便觉得毫无趣味。三是发泄内心长期对生存处境的不满。贾宝玉虽然生在锦衣玉食的贵族之家,“万般宠爱集一身”。但他种种不合时宜的言行却并不被世人理解,他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他的行动处处受到限制。因此,贾宝玉的心灵需求与现实境遇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他不满,所以借此发泄。综上可知,宝玉“摔玉”的举动,看似不可解,实则事出有因。
贾宝玉对玉的态度与家长、世人是截然不同的,他在乎的不是“玉”的表象及世俗的附加意义,而是“玉”是否名实相符,是否能够给他带来内心真正的快乐。世人奉若神灵尊贵无比的“玉”,在宝玉看来,只不过是伪饰不灵、制造差距、辖制自由的赘物罢了。“摔玉”这一举动就是要极力挣脱,求得自由,求得平等。因此,“摔玉”表象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贾宝玉一颗无比真诚善良的赤子之心,一颗渴望自由、追求平等的高贵心灵,一颗长期积怨于胸的痛苦灵魂。这恰恰凸显了贾宝玉核心的思想性格。纵观全书,在人际交往中,他无视“宝二爷”的贵族地位,喜出望外为平儿打理妆容、善解人意地为香菱替换石榴裙;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他对科举功名深恶痛绝,拒绝走家长安排的“仕途经济”之路;在爱情婚姻上,他放弃“德言容功”样样俱佳的薛宝钗,选择志同道合、心灵相通的林黛玉。以上种种无不体现了贾宝玉追求自由、平等的核心思想性格。贾宝玉作为文学作品中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他的这种思想性格,体现了18世纪民主、进步的思想光辉。
(二)宝黛爱情的预演
宝黛爱情是文学作品中最真挚缠绵也是最令人黯然神伤的爱情。《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从第三回宝黛初会到三十四回宝玉赠帕、黛玉题诗,再到九十八回黛玉魂归离恨天,最后一百二十回贾宝玉出家,曹雪芹饱含深情地描写了宝黛爱情从萌芽、生长、成熟到夭折的过程。对于宝黛爱情的整体宏观把握,在宝黛初会之际,“宝玉摔玉”便已经做了小规模的预演,这条主线的发展走向都可以从这个细小的片段中发现端倪。
1.痴情的表现
贾宝玉是情痴情种,他对大多女孩儿都有着怜香惜玉温柔体贴之心,而他对黛玉的感情却与众不同,这在他们初次见面时就显示了出来。脂砚斋在评点“宝玉摔玉”时写到:“奇极!怪极!痴极!愚极!”[2]纵观全书,这份奇、怪、痴、愚的举动仅仅是对黛玉,而非其他女子。此回之后,在贾宝玉所有接触过的女子面前,他再也没有出现一见面就摔玉的疯狂行为。我们知道,宝黛爱情的“前生”是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之间的灌溉报恩情缘,即“木石前盟”。因此,前世的情缘注定了宝玉非“摔玉”不可,没有“摔玉”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就无法显现宝玉初见林黛玉时那种异样的情感,无法显现“木石前盟”情感的力量与威力。宝黛相遇之初,如果说贾宝玉对林黛玉一见如故、久别重逢的感觉是他神奇的心理反应,那么,“摔玉”就是他本能原始的情感反应。当代作家王蒙独创性地用“天情”一词描述了宝玉“摔玉”的情感特征:内心与生俱来的,像天一样弥漫于宇宙空间的情感。“摔玉”就是在“天情”的强烈支配下,为了和对方取得一致而产生的极度情绪化的表现。有了宝玉“摔玉”的痴情,在宝黛爱情发展过程中,宝玉对黛玉的一切如痴如狂的言语行动才显得合情合理,有根有据。如五十七回,贾宝玉一听紫鹃说黛玉要回苏州,立刻眼睛变直手脚冰凉,人死了大半个,等等。“摔玉”是了解宝玉内心情感的一扇窗户,在宝黛初次相遇时,他对黛玉的那份“痴情”便已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2.矛盾的伏笔
《红楼梦》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无处不在,作为小说主线的宝黛爱情也不例外,它分为宝黛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共同面对的来自家长的外部矛盾。从宝黛内部冲突来说,寄人篱下的林黛玉除了有对贾宝玉的满腔痴情外,几乎一无所有。自卑和“不放心”使黛玉成为宝黛爱情矛盾冲突的主要制造者。在宝黛心灵互通之前,黛玉对宝玉极度不放心,所以她一次次的用“金玉”刺激、试探贾宝玉。而贾宝玉为了表忠心,让林妹妹放心,就一次次狠命的摔玉、砸玉。第三回,宝玉因林妹妹无玉而摔玉;第二十九回,因林妹妹放心不下,“金玉良缘“成了心病,宝玉再次狠命摔玉;第二十九回则是第三回的放大升级。可见,宝黛二人的矛盾始终躲不开这块“玉”。随着宝黛二人心灵的彼此互通,内部矛盾才最终烟消云散。但接着,他们却不得不面对共同的外部矛盾,那就是代表强大世俗力量的“金玉良缘”对他们爱情的威胁。“金玉良缘”成了宝黛二人挥之不去的心病:林黛玉心底有“既有金玉之论,亦该你我有之”[1](P446)的不平之叹;贾宝玉梦中有“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前盟”[1](P492)的激愤之语。总之,宝黛爱情的矛盾冲突,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归结为二人有玉和无玉的差别。而林黛玉无玉和贾宝玉有玉的差别,最终转化成林黛玉“无”和薛宝钗“有”的差别。林黛玉进贾府时,便是孤身一人,一无所有。而薛宝钗则不然,一来脖子上就戴着与玉成双成对、象征金玉良缘的金锁。当然,薛宝钗和林黛玉的差别远远不止这一点,除了有目共睹的有形差别之外,还有许多无形的差别,如为人处世、思想性格,等等。随着贾府经济的每况愈下,薛林之间“有”和“无”的差别更是日渐加剧强化。最终,家长在家族利益权衡之下,选择了“金玉良缘”而舍弃了“木石姻缘”。最终有金锁的薛宝钗战胜了一无所有的林黛玉。第三回,贾宝玉因林妹妹无玉而摔玉,不得不说,他们之间一开始便存在着“有”和“无”的巨大鸿沟。通读全书之后发现,第三回“宝玉摔玉”早已为宝黛爱情矛盾冲突的发展留下了伏笔。
3.悲剧的预示
宝黛爱情是人世间理想爱情的化身,但这棵爱情之树最终还是凋零了:林黛玉香消玉殒;贾宝玉悬崖撒手。爱情毁灭的直接原因是“金玉良缘”战胜“木石前盟”,深层原因是代表封建家长的家族利益战胜了代表青年男女的自由意志。正如恩格斯所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3]
这种悲剧的结局不是突发性的,而在宝黛初会时就已有了预示。宝玉狠命摔玉,可摔来摔去,只不过是对不说话的哑巴出出气而已,并不能改变什么,“玉”依旧坚硬如初。“玉”成了贾宝玉心头的“紧箍咒”,成了不可抗逆的家长意志,成了不可抗拒的宿命定论。所以,宝黛初次会面之际便充满眼泪、不满、怨恨、抗争、无奈、悲哀。宝黛爱情还没有正式开始,“宝玉摔玉”就已经让读者感受到了笼罩在宝黛心头的愁云惨雾。
二、“宝玉摔玉”的艺术特色
“宝玉摔玉”不仅思想意蕴丰厚,而且也表现出很高的艺术价值。在这短短的情节片段中,无论是塑造人物的手法和还是小说的整体结构布局,都体现了曹雪芹高妙的艺术匠心。
1.人物出场定型的“点睛”之笔
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轴心人物,在他没有正式出场前,曹雪芹就通过众人之口对他从侧面进行了介绍,冷子兴演说中的“新奇异事”,王夫人口中“孽根祸胎”,林黛玉听到的“顽劣异常”。世人两首《西江月》更是极尽嘲讽之能事,对贾宝玉不合时宜的思想性格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冷嘲热讽。当贾宝玉“千呼万唤始出来”时,通过“摔玉”这一点睛之笔,其独特另类的个性跃然纸上,也为前两回众人的评说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证据。随着情节发展,这种思想性格不断地被放大强化,如第十六回中众人都在为贾元春晋封之事洋洋得意时,唯独贾宝玉“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1](P211)再如第四十三回,合家上下为王熙凤庆祝生日时,贾宝玉偏偏一大早跑到郊外去祭悼死去的金钏。可见,“宝玉摔玉”情节,让宝玉一出场就展现出性格中的核心因素,既为他出场前世人的评说作了交待,又为后文展现性格的丰富性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在中国传统的古典小说中,“出场定型”这种塑造人物的手法,早已有之,《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诸葛亮、曹操、张飞等采用的都是“出场定型”的手法。对这种传统的手法运用,曹雪芹没有简单的拿来,而是推陈出新把它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首先,“定型”的人物不是扁平单一的性格,而是层次丰富的立体圆形人物;其次,“定型”不仅仅停留在相貌、道德、才能等方面,而是深入到人物的思想、意志、情感等心理层面,而这些内容显然是人物性格中更深幽隐蔽、更具个性化的东西;最后,“定型”人物的思想性格,在不同的观察者眼中,存在着好坏褒贬截然相反的评价,读者需独具慧眼才能发现真相。因此,“宝玉摔玉”虽然是对宝玉的“出场定型”,但在整部作品中,贾宝玉的思想性格仍然是开放流动、鲜活饱满的。在《红楼梦》栩栩如生的人物艺术长廊中,“宝玉摔玉”同黛玉葬花、晴雯撕扇一样,成为展现人物不可或缺的“特写镜头”、经典画面。
2.“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端始
著名红学家蒋和森先生说:“在《红楼梦》中,许多故事和事件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组成部分而互相交错、此起彼伏的存在着。”[4]“宝玉摔玉”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谐有机、天衣无缝的融合在曹雪芹的整个艺术构思和布局中。为了实现结构布局的完整统一,曹雪芹在构思上多处采用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结构技巧。“宝玉摔玉”便是其中的一处,它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起端。在第二十九回宝黛发生口角,宝玉听到林黛玉“好姻缘”曲解了自己的意思,赌气从颈上摘下玉来,再次狠命摔玉。第三十回,通过紫鹃的补述我们知道,宝黛二人因为玉闹腾过不止一遭两遭了。从三回到三十回,曹雪芹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手法将二十多回文字前后勾连起来,小小的“摔玉”情节如蛇行于草、灰露于地一样,断断续续,时隐时现,看似微不足道却最终引起轩然大波。曹雪芹正是通过“宝玉摔玉”这一情节,把宝黛爱情发生、发展的线索巧妙而又不动声色的贯穿了起来。
总之,第三回“宝玉摔玉”摔出了主人公贾宝玉的真性真情,摔出了宝黛爱情中的痴情悲情,也摔出了作家高妙的艺术才华。它与全篇气脉贯通,展现了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