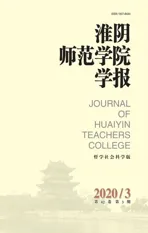抗战时期旧体诗词复兴因素论析
2020-01-19杜运威
杜运威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抗战诗词价值的发现经历了从漠视到局部个人关注,再至整体“复兴”[1],并以专章格局进入文学史[2]的基本过程。改革开放之前,除了因政治影响而被格外关注的部分官员外,很少有人触及现代文学背景下的古典诗词。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个案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惊奇地发现那些在五四至抗战前视旧文学为粪土的新文学家们,于抗战期间都不约而同地创作起旧体诗词,如郁达夫、郭沫若、田汉、王统照、邵洵美、叶圣陶、俞平伯、闻一多、沈尹默等。如果这些新文学家自始至终都在创作诗词,人们会认为是传统教育惯性所及,或许并不会引起多大反响。值得玩味的是本来鼓吹创作新诗的他们,在抗战时期,都或多或少地放弃初衷,而选择“勒马回缰作旧诗”。这一变化的原因与旧诗复兴有密切联系。对此,刘纳《旧形式的诱惑——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和胡迎建《论抗战时期旧体诗歌的复兴》(《晋阳学刊》2000年第4期)已经有所关注,但对彼时文艺思想、政治动机、生存现实等外部环境考察还存在不足,且未能从诗词艺术范式和社会功能等内部特质出发,透析全面复兴的主要动因。另外,对复兴主力军的定位也存在偏颇之处。
一、旧瓶装新酒:抗战时期诗词合法地位的理论重建
“合法性论证是社会秩序的建立者与社会成员之间双方博弈的一个场域。”[3]欲真正洞悉彼时创作语境及实际情况,必须回到1937至1945年历史建构的现场。由于建立文艺统一战线的现实需要,人们对是否利用“旧形式”来宣传抗战展开激烈争论。所谓的“旧形式”,包括“民间形式和传统文人的旧文体”[4],“旧文体”主要指古典诗文词。
争论前期聚焦于“有无必要利用旧诗词”。随着话语权的丢失,诗词逐步沦入弹词、戏曲、民歌民谣、评书等一类的“旧形式”中。旧形式受到攻伐,诗词当然难逃诘难。有作家指出:“旧体诗受格调的限制,早已变成僵尸了,无论有什么新的意义,一受了‘平平仄仄平平仄’的限制,绝不会新鲜活泼,把维他命注射进僵尸体内,僵尸还是僵尸,它永远不会复活的。……这些作品(旧体诗)根本和当前的文艺工作没有关系……”[5]甚至将古典诗词贬为“‘言之无物’的绣花枕头”[6],“早已僵化了的死文学”[7]。此时距五四新旧文学之争已过去近20年,但贬斥之语似有增无减。检点相关著作,发现有不少新文学家仍然在创作旧诗,但其创作动机已大不相同,余慕陶曾言:“我们有时倒无妨以游戏的态度作之,可是,当我们来努力去写作时,那我们确是复古了。”创作词的人更是“因为时代的没有出路,都来陶醉在恋爱方面,或追回过去的梦影”[8]。
当然也有新文学作家提出反驳意见。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中除了风花雪月、男女恋爱,“正有不少充满着热烈的爱国情绪的作品,像文天祥……岳飞……陆游……”[9]在民族存亡面前,连大鼓、快板、相声、双簧等都能被拿来改造内容,唤醒民众,深具千年道统的诗词更应该更被推上“前线”。有的学者在“批评当下新诗创作良莠不齐、混乱不堪的局面下,提出应向旧诗中汲取营养,尤其学习旧诗的文字技巧,艺术方法”,并且客观地提出“旧诗未尝不能够用新名词与新事物,我们不应用诗的体式新旧来判诗的好坏,而应当看诗的内容”[10]。影响力较大的郭沫若和张恨水都强调诗歌成就高低不在形式,而在能不能感动人。(1)参见王训昭编《郭沫若研究资料·“民族形式”商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上册,第305页;张恨水《新文艺家写旧诗》,重庆《新民报》,1942年11月23日。正如王有兰诗云:“旧瓶盛新酒,瓶旧酒味新。新瓶盛旧酒,瓶新酒味陈,新陈各异味,欣赏存其人。文艺真善美,不重式与形。……”[11]至此,以形式作为判断文学优劣标准的言论逐渐消失,“诗歌是否动人”成为未来文学发展努力的方向。
争论也由此转为“如何科学利用与改造旧诗词”。雷石榆在《从旧诗词中学取什么东西?》中充分肯定诗词的情感表现力和艺术技巧的成熟,呼吁作家“要坚执着新的创作方法的武器,从遗产中摄取技术的补助,创作有血,有肉,有壮旺的生命力的民族形式的东西,不要变成遗产的蛆虫,化身于复古的骷髅……”[12]面对抗战题材,传统文人比新文学家更加从容老练,南北宋、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积淀告诉他们,外敌入侵、国家存亡之时,必须放下风花雪月和流派之争,而将“前后方可歌可泣的故事,缀为长歌”[13],发扬“诗史”“词史”的传统精神。
争论焦点的转移,标志着自五四以来被新文学家们蔑视、排斥、打倒的旧诗词在文艺界——至少是理论层面——重新获得存在的合法性。至此,人们不再一味地否定旧体诗词,而是汲取其字句、韵律、章法、语言、叙述方式等精华,以便滋养创造更适合抗战背景下的民族文艺形式。以上文艺态度的转变奠定了旧体诗词复兴的理论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伴随以上争论过程的深入,新文学暴露出自身的诸多问题。正因为新形式在宣传抗战上遇到了障碍,才去寻找其他途径和方法加以弥补。换言之,辨析新形式的局限性有利于认清旧形式的根本特质。其局限性有二:第一,影响范围的局限。新文学的口号是推倒贵族山林文学,建立平民文学,其出发点是要与底层民众紧密联系,而实际“新文学作品所可宣传的对象只是一般知识分子,广大的知识落后的同胞无法被我们的作品所宣传”[14]。对复杂口味的民众来说,旧形式如弹词、评书、戏曲、小调、章回小说,乃至旧体诗词依然广受青睐。仅北平每年通俗刊物销售就达180万部[15],其消费群体多为普通民众[16]。第二,抒写方式的稚嫩。新文学抒写方式多源自西方,或写实,或浪漫,或魔幻,或精神分析等,而由于引入的模式化和自身吸收转化的不完整,在表现抗战这一新题材时,无论是创作方法还是词汇的使用都显得捉襟见肘。正如艾思奇总结的,“一方面有现实主义和平民化的要求,另一方面生活在广大的民众之外的作者和外来的写实形式不能达到真正的现实主义和平民化的目的”,即“形式的写实手法不能充分地反映抗战的现实,表面上是现实的,实际上却是对于现实有限制的”[17]。此两点局限性足以使新文学在宣传与反映抗战上力不从心,而这恰恰是透视旧体诗词复兴的重要突破口。
二、勒马回缰作旧诗:旧诗词的独特魅力
向来鼓吹创作新诗的文学家们居然或多或少地放弃初衷,开始“改行”创作旧诗。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抗战时期的旧诗词可以自由、大胆地寄托作者的情感,而不必顾虑政治宣传问题。正如新文学家自己交代:“小说是写给别人看的,诗是为自己写的。”[18]“给别人看的”这一前提,导致此期的新文学都不同程度地被戴上了“镣铐”。有学者指出,郭沫若之所以在抗战时期转行作旧诗,主要在于新诗所表达的是“当时形势下他需要表达的、符合他‘文化界旗帜’身份的思想感情”,而旧体诗则用于“更真实地传达他的人生慨叹和人生体悟”[4]。这正说明新诗在抗战时期,虽在形式上自由,但情感内容上并不自由,因为它必须承担着与作者身份相对应的政治立场。相反,旧体诗词因为其传统性和保守性,可更直接地抒发新诗中不能言说的仇恨苦闷、彷徨不安、慨叹体悟、交游酬唱,乃至偶尔的消遣娱乐。那些勇往直前的文人固然值得钦佩,但并非所有作家都直接参与战争。回顾历史,彼时文人多生活于大后方,面对战乱,人们的心情十分复杂,或恐惧、矛盾,或仇恨、愤慨,或自信、期待,或者只想平静生活,构成战争背景下值得关注的生活百态。基于这点,已经发展千余年的旧体诗词在面对不同心理状态的群众时,其可操控的情感空间比新诗要大得多。
第一,旧体诗词是文人排解苦闷、刻录心迹的主要依托。面对日军侵略本质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很多文人难以理解而又无可奈何,只能借诗词纾解不平,如刘冰研在其《貂裘换酒》小序云:“东三省之亡,不亡于异族专政,不亡于洪宪称帝,尤不亡于北府专横,而乃亡于素以党治号召天下者。……暴日兽军寇我辽阳,破坏国际公法,背叛非战公约,世界震惊,人天同愤。以我国竭人民数干百万之脂膏,养此数百万之健儿。三月以来,不能竭全力与日一战,收复寸地,仍仰鼻于不生不死,国联之下,宁不可异。……吾作此愤言,不过以歌当哭,唤醒沉酣。代全国人民一洒伤心之泪。嗟嗟美人芳草不无寄托之词,商女庭花惟以悲哀为主,知我罪我,听之可也。”[19]类似借词题小序增强叙事性的作品在《剪淞梦雨词》中还有很多。从此可以管窥,作词是刘冰研一类文人的主要情感倾诉渠道。甚至有的文人将此视为托命之举,如沈祖棻《上汪方湖、汪寄庵两先生书》云:“受业向爱文学,甚于生命。曩在界石避警,每挟词稿与俱。一日,偶自问,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而二处必有一处遭劫,则宁愿人亡乎?词亡乎?初犹不能决,继则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20]随着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相继沦陷,为躲避纷乱,中国掀起迁徙西部的难民大潮,史书对迁徙过程有相关记载,但对当时人们的真实心态及旅途过程中的切身体验几无介绍。受战争影响,彼时很多依托传媒界的新文学也十分冷落,与之相比,旧文学却显得更加活跃。传统文人不只是记录每日辗转之地和所见所闻,而且抓住行程的各个瞬间,以诗家之眼,凝练出羁旅逃亡中的艰辛、忧虑、彷徨和无奈。如沈祖棻《鹧鸪天·寄千帆嘉州,时闻拟买舟东下》:“多病年来废酒钟,春愁离恨自重重。门前芳草连天碧,枕上花枝间泪红。 从别后,忆行踪,孤帆潮落暮江空。梦魂欲化行云去,知泊巫山第几峰?”[21]又如杨苍白《铁骑》云:“铁骑纵横遍两京,每闻寇陷辄心惊。红颜狼藉年前死,赤子漂流劫后生。破屋荒城余鬼哭,残阳古道少人行。由来夷祸今为烈,更道宁亡不与盟。”[22]字数虽少,而情感却错综复杂。同样于颠沛行程中爆发前所未有创作力的还有唐圭璋,其“词章所写家国存亡之痛及个人身世之感,都是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颇能动人心魄”[23]。其中《虞美人·丁丑避地真州》《行香子·匡山旅舍》《清平乐·宿白鹿洞贯道溪畔》《踏莎行·德安重九》《兰陵王·成都遭敌机空袭》[24]等数篇,将作者避乱中“忍抛稚子”的无奈,“无限离愁却比一江多”的苦闷,“不知身在何州”的漂泊不定,“十四年来重到梦魂惊”的恐惧表露无遗。尽管逃亡的路途艰险,但在诗人眼中除了目睹一路上流民失所、妻离子散、盗贼横行的乱象外,始终有一股豪气横亘胸中,这种豪气和信心一旦时机适合就会喷薄而出,如卢前自南京一路西迁,历经甘苦,至避开危险后望赣江波涛汹涌而作:“举手终教能杀敌,矢心自勉共成仁。多艰岂已似南宋,步武文山必有人。”[25]类似呼声在西迁文人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马一浮《避寇集》、杨沧白《天隐阁集》中俯拾皆是,感人肺腑。
第二,丰富的叙述策略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首先,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员,鼓吹宣传抗战自是不可推卸的责任。翻看那一时期文人的诗词集,首先扑入眼帘的就是为前线战士的热情歌颂和呐喊助威,如邓拓《狼牙山五壮士》:“北岳狼牙耸,边疆血火红。捐躯全大节,断后竞奇功。畴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五人三烈士,战史壮高风。”[26]类似作品还有姚伯麟《台儿庄大捷歌》、黄炎培《送从军青年》、何香凝《大刀赞》《颂五百大刀歌》、宋哲元《杀敌救国歌》、马叙伦《遥吊佟麟阁赵登禹两上将》、刘永济《入春五日,又闻湘捷,再用坚字韵赋喜》,不必举具体诗句,从题目就能看出作者的主要目的。鼓吹抗战的诗词《民族诗坛》收录犹多,宏观场面从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事变至南京大屠杀,细微处如前线战士的穿戴呼吸,一次有效的抵抗,成功的杀敌,都成为诗人笔下素材。可以说几乎前线所有大小战事、英雄事迹皆有诗词在场。这也是自五四以来,不断被新文学压迫的旧诗词再次焕发光彩的一幕。其次,通俗语言与白描手法满足了教育民众的技术要求。新旧形式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利用旧形式来扩大宣传,旧体诗词显然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可以调动,如唐代元白诗派之白居易、清代性灵派之袁枚等。传统文人对此也有思考,据李木庵记载:“林老说:怀安诗社作者不宜长时停滞在旧诗形式内,应求作品通俗化,以起到现实的战斗作用。……希各人放宽尺度,不拘格式,每人先写出几首,交换观摩,培养兴趣,转移风气。……现在语体新诗也确有叫人难懂、不知所云的,都应鉴戒。”[27]基于此现实需求,文人作了两个方面的探究:一是新体诗歌的探索,即将音乐与文学再度结合,给改编后的诗词谱曲,便于传唱。如1938年龙榆生词、谭小麟曲《悼黄自先生调寄采桑子》,以“人在心弦,一曲悲歌万口传”[28]的形式响彻大江南北。二是白话诗词的兴起。如李木庵《无定河》:“无定河,无定河,大盗窃国动干戈。为反独裁争民主,大众翻身理不讹。”又钱来苏《陕北杂咏》:“民主政权初展开,穷根拔去富根来。自由平等从何得,保卫田财反独裁。”[29]51相近文人还有冯玉祥、聂绀弩等。第三,沦陷区文人借深奥典故寄托反抗本质。留守北京、上海、南京的沦陷区文人,因为生存语境的特殊,他们不可能像国统区、根据地那样直接鼓吹抗战或批判讽刺。只能用深藏不露的“隐微修辞”[30]传达对日伪政府的不满和无奈合作的懊悔。郭则沄为首的蛰园律社和延秋词社就曾以“五色鹦鹉”典故寄托深层故国情思。如《龙顾山房诗赘集》卷一《正月十三日过苍虬阁久谈》:“末劫何繇著两翁,强偷视息入顽癃。槁灰不死天尤酷,行住俱殚世坐穷。可语待君箝口久,无成胜我负恩终。仁先近有句云‘无成甘以诗人见’长春节亦随人改,心系寒晖肯向东。”[29]42又《夜坐述感》云:“秋人自厌是秋声,聒耳阶蛩底善鸣。奇服甘焚宁有避,隘喉触鲠故难平。独醒此夜支残漏,自诡余年暱短檠。唤彻荒鸡天不省,一星高处少微明。”[31]郭则沄一方面数次拒绝出任伪职,另一方面又多次在日伪主办的《雅言》上发表诗词,前后行为的矛盾恐怕只有身处危难间的这群文人才能体会。因为既要保持民族气节,又要在沦陷区有尊严地活着,在日伪报刊上发表诗词应该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但看上文收于其遗稿中的诗歌,那种“槁灰不死”“心系寒晖肯向东”的倔强,“隘喉触鲠故难平”的压抑,是“隐微修辞”无法掩藏的。在郭则沄等留守文人群体身上,旧体诗词既被用作粉饰太平、雅集娱乐的工具,又是掩藏心机、不平则鸣的发泄渠道,旧体诗词功能强大至此恐非新诗可比。
旧体诗词的魅力还有很多,比如钱钟书《槐聚诗存》中批判讽刺功能的拓展;再如柳亚子诗中对“大同进化之论”[32]新思想的阐释与推广……总而言之,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词与晚清以前截然不同,后者往往慑于“文字狱”的政治高压或群体流派的审美局限,而导致畏手畏尾,甚至作茧自缚;而前者则处于推翻封建后的新时期,且有先进的理念支撑和丰富的历史积淀,几乎可以满足各类人的审美需求和现实需要,这是旧体诗词真正魅力所在。
三、不薄新诗爱旧诗:传统文人是诗词复兴的主力军
上文所谈抗战时期旧文学复兴问题,无论是“如何利用旧形式”的激烈争论,还是“勒马回缰作旧诗”的创作现象,不难发现讨论的对象仍然是新文学家。这种先入为主的本位观念严重削弱了传统文人(2)传统文人与新文学家的区别主要看其一生的创作及活动,若以古典诗文为主,则为传统文人。在诗词复兴中的重要作用。换言之,当下学界不少人将抗战时期诗词复兴的功劳归于少数的新文学家和党政官员,这是以偏概全且十分危险的论断。如果我们转换新旧文学本位视角,会发现新文学家一方面是发现了旧体诗词在抒写抗战题材上的优势,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当时传统文人的影响,最终选择接纳并“改行”作旧诗,使得旧体诗词一度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文学样式,继而呈现与新诗并驾齐驱之势。所以,在考察诗词成就时,当以传统文人及其作品为中心,新文学家、党政官员为羽翼,以“不薄新诗爱旧诗”的态度,方能准确判定其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第一,传统文人与抗战诗史。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战争的残酷成为诗家创作的动力源泉,而诗词固有的短小体式非常适合短时间的构思和抒情,能够快速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争态势。内外因素的结合使得旧体诗词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尤以姚伯麟《抗战诗史》最为典型,从“九一八”“一二八”到“七七”“八一三”等系列事变,再至“太平洋战争”及最后胜利皆有吟咏,该别集成为诗词始终在场的一个缩影。再如创作于1943年反扫荡时期董鲁安的《游击草》,作者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因愤于日寇暴行而参加革命。他用177首旧体诗歌记录了三个月的反扫荡经历。据作者《岳南日记》载:“曾过四县(阜平、涞源、灵丘、繁峙),二百余村;曾住四十六村,曾行八百八十六里。大山突围二次,狼山突围一次,罗家湾突围一次。遇警数次,挨饿数次……”[33]《游击草》中的细节描写可补党史之缺,是名副其实的诗史之作。
除了诗史的记录,忧国忧民、感时伤乱的悲悯情怀是传统文人一直坚守的道统。如陈寅恪《七月七日蒙自作》:“地变天荒意已多,去年今日更如何?迷离回首桃花面,寂寞魂销麦秀歌。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总蹉跎。南朝一段兴亡影,江汉流哀永不磨。”[34]诗中没有叫嚣鼓吹,没有歌功颂德,却于看似冷静的叙述中蕴藏更大的苦痛,这不是一个人的呻吟,而是固有的士大夫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以坚强不倒的姿态勇敢面对现实苦难,不作苟且偷安的文化汉奸,不为无法奔赴西南无奈选择留守而百般辩解,更不甘仅仅作鼓吹抗战的传声筒,他们赋予诗词更大的内涵和吟咏的空间。类似作品很多,如马一浮《旧历丁丑腊月避兵开化,除夕书怀,呈叶君左文》:“微显在一心,时论犹冰炭。味此治忽本,坐令安危判。疲氓忍兵役,练卒夸劲悍。致戎夫谁尤,树栗无往谏。……于野验同人,见睍识冰泮。密行大化中,巧历焉能算……”詹安泰《月夜独行忽忽若有所悟因作》:“蓬累今生且放颠,旧家消息故难传。地高野翠能留月,世乱同情不值钱。纵被黄蜂伤毒螫,胜如曲巷听哀鹃。丘山华屋非真感,题句还当着意妍。”用旧体诗文践行冷静客观的审视与批判是传统文人守正开新的价值所在。
第二,传统文人与诗词社团的兴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生活趋于稳定。诗词的创作形态由个人的羁旅行驿转向群体的结社唱和。人们内心不安,急需寻找一群同道者,一方面嬉戏娱乐,诗词会友;另一方面互相倾诉,彼此安慰。1939年后,各地诗词社团如雨后春笋,蔚然壮观,如:四川的雍园词社、藕波词社,贵州的湄江吟社,云南的椒花诗社,湖南的山中诗社、五溪诗社,重庆的饮河诗社、民族诗坛协会组织、中兴诗社、潜社渝集,福建的南社闽集、寿香词社,兰州的千龄诗社,上海的午社、蚕社等。令人惊奇的是沦陷区诗词活动也异常活跃,如京津地区余园诗社、蛰园律社、稊园诗社、玉澜词社、瓶花簃词社、延秋词社、梦碧词社,南京同声月刊社等。结社唱和将诗词创作推向新的高峰。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大部分社团皆由传统文人发起组织和运行,这是本文立足传统文学本位的重要依据。当然此期新文学家、党政官员也积极加入创作队伍,尤其是郁达夫、俞平伯、茅盾、老舍、阿垅、于右任、陈毅、朱德、郭沫若等重量级人物的参与,更壮大了诗词创作的局面。
对此,需特别关注抗日根据地的“三大诗社”[35],分别是陕甘宁边区的怀安诗社,江苏盐阜一带的湖海艺文社,晋察冀边区的燕赵诗社。1942年前后产生三大诗社并非偶然,人们往往将其作为党史掌故和根据地文化建设来考察,却忽视他们在团结旧式文人方面的重要作用,也低估了三大诗社作为文学社团的理论贡献和创作成就。首先,传统文人是三大诗社主要成员。诗社的成立得益于“三三制”政策的建立和地方参议会的筹备。如燕赵诗社缘起云:“边区民主,谠议宏开,定反攻之大计,期必胜于来朝。……以燕赵之诗歌,作三军之鼓角,为此倡议立社,邀集联吟,所望缙绅耆老,硕彦鸿儒,踊跃参加,共襄斯举。”[36]238又怀安诗社:“9月5日,林伯渠、谢觉哉、高自立等同志,于交际处宴请延安民间诗人墨客,到会者多为寿高六十岁或七十岁以上之老人,……因当场多诗词之士,乃由林老发起组织一诗社,本‘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旨,定名怀安诗社……”[37]正因“硕彦鸿儒”“诗人墨客”的积极参与,三大诗社发展十分迅速,成员规模达一百余人。其次,沟通新旧,创作通俗易懂的作品是诗社的指导思想。谢觉哉《致钱来苏》信中云:“曾和一秧歌剧作者谈,我说剧作得好,只是唱词有些不好念。平仄阴阳不谐。……做新诗的人少研究过旧诗,不是从旧诗中扬弃出来的。因此,象你这样旧诗作者来革新诗运,是份所应当罢。”[38]谢觉哉发现部分新诗或歌剧不好传诵的根本原因在于平仄不谐,这是所有新诗作者的痛点。而旧诗的音韵体系能够轻易做到朗朗上口,便于传播。燕赵诗社成员皓青《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志盛七律四章并序》又云:“窃维此社宗旨,欲沟通新旧,文言白话,均属诗材,不拘体格。”[36]240该理念得到根据地诗社成员的普遍认同,如陈毅《湖海诗社开征引》云“不为古人奴,浩哥聊自试。师今亦好古,玩古生新意”。又朱婴《纪事诗》云:“怀安不为古人婢,愿为古人添新装。怀安不为今人笑,愿与今人共平章。”最后,三大诗社的诗歌是对根据地人民生态的多维透视。既有《怀安诗选》中所呈现的“南泥湾”前后变化的专题描写,也有钱来苏《陕北行》中所说“此地昔贫瘠,兵旱灾相连。土地多荒芜,黎民无吃穿”[29]45的艰难处境;更有宋泽夫《呆子吟》中所讽刺的“看风下棹迟,随风转舵快。惆怅三歧路,徬徨十字街”的两面派。总之,根据地三大诗社绝不是几位党政官员的业余性诗社,而是众多传统文人参与的,秉承沟通新旧、不拘体格的先进创作理念,在根据地产生重要影响的专业性文学社团。
第三,传统文人与诗词刊刻、发表及传播。抗战诗词文献是一个亟待整理开发的学术富矿。目前主要有线装、平装和报刊三大传播介质。其中不仅有数量极其庞大的个人别集,还有选集、总集、合集、社集等。上文所及各大社团大多有单行本刊行,如《雍园词钞》《寿香社词钞》《蛰园律集》《午社词》等等。别集方面以卢前《中兴鼓吹》最为典型。此集一出,反复刊刻,分别有:1939、1942独立出版社本及增订本;1942贵阳文通书局;1943福建建国出版社,还有成都茹古书局、桂林汉民中学、南京所等各版本。甚至还有音乐版歌谱、行书范本字帖、英译本、袖珍线装本等各种形式流传。这部词集在当时能获得如此巨大的传播效应,堪称奇迹。这固然与卢前词本身内容的巨大鼓动性有关,但也可以说是旧体诗词全面复兴的证据之一。1938年1月,教育短波出版社出版《抗战诗选》,辑有新旧体诗56首,它是新旧形式之争背景下,两大文人群体握手言和的重要标志。这种现象在五四至抗战前夕是不可想象的,也足以说明旧体诗词的地位得到重新确认。
此期以旧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报刊成为诗词传播的主流。影响较大的是重庆的《民族诗坛》,它“以韵体文字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之情绪”为办刊宗旨,是抗战时期引领中国诗坛的专业刊物,也是旧体诗词承担时代使命的主阵地。另外,从传播角度看,南京汪伪政府的办刊举动也值得肯定,先后创办《同声月刊》《学海月刊》《中国诗刊》《国艺》《民意》等,皆辟有诗、词专栏。尤其《同声月刊》,在龙榆生主持下,逐渐淡化政治色彩,以追求诗词艺术性和学术性为目的,赢得不少读者青睐,其撰稿群由初创期的龙榆生、陈曾寿、夏敬观等数人,扩至几十人,当时诗词坛的重要名人多有投稿。彼时不少杂志都单独开设诗词专栏,如《新知识》设《湖海诗文选》栏目;《斯文》《大千》《中国文学》有“词录”;《群雅》《雅言》《古今》《制言》等刊物皆有诗词发表。报纸中诗词出现的频率也在扩大,如《解放日报》开辟《怀安诗选》专栏;《盐阜报》《拂晓报》开辟《弦歌脞录》专栏;其他如《晋察冀日报》《救亡日报》《广西日报》《民国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时事新报》等报纸也不定期有诗词发表。如此众多报刊出现诗词身影,逐渐在整个诗坛形成创作旧文学的新风尚,其影响堪与新诗分庭抗礼。
综上所述,在历史契机和自身特质的共同推动下,旧体诗词展现出全面复兴的态势。历史契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现实需要,接纳并改造“旧形式”成为文学界的共识。这标志着旧体诗词重新获得正统文学的合法地位。二是抗战期间,新文学与政治宣传过于亲密,使其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政治传声筒的角色,这无疑束缚了新文学的自由。而旧体诗词恰因为边缘化的处境,没有特殊的负担,得以轻松自由的发展。该特质最大限度地适应了战乱环境中不同群体的心理诉求。自身特质表现为范式众多和功能丰富。前者之优势在于面对不易言说的处境时,它就用经史典故加以掩饰,以微言大义的形式顽强生存;面对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时,它又以朴素平实、晓畅通达的语言灵活呈现。后者之优势在于它既可以承担抗战鼓吹的政治使命,又具备抒发一己悲欢离合,乃至雅集唱和、嬉戏娱乐等多种功能,既传承了诗词固有的文体特征,又随着时代因地制宜和人们的需要而变化。除了以上因素外,还需明确诗词复兴的真正主力军是传统文人。在国破家亡的压力下,他们秉持士大夫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通过诗词艺术呈现出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态。不仅使旧体诗词再次焕发活力,还取得了堪与新诗并驾齐驱的创作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