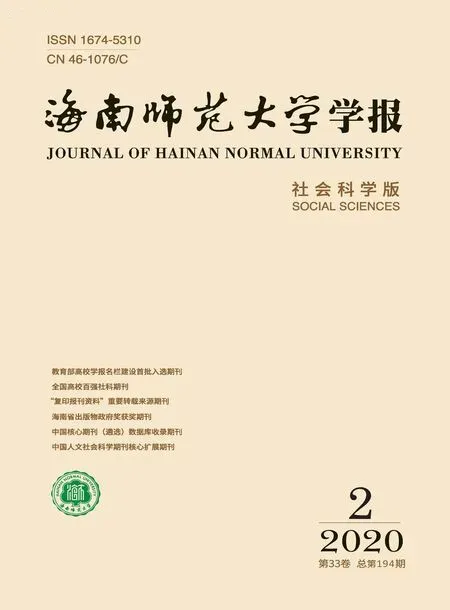黄东平《侨歌》三部曲中的闽南侨商形象
2020-01-19向忆秋
向忆秋
(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 漳州 363000)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关涉印尼著名作家黄东平的学术论文,迄今在中国大陆学术刊物上也发表了十余篇。但是从闽南侨商的视角去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目前还尚无踪迹。东南亚作为闽南移民的集结地,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闽南侨商。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也塑造了数量众多的闽南侨商形象。因此本文拟以作家黄东平《侨歌》三部曲为中心,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中的闽南侨商形象进行研究,这将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领域非常有意义的“开荒”工作。1923年,黄东平生于印尼加里曼丹外围一个叫柯达峇鲁的小岛,幼年曾回中国生活。黄东平成年后回到印尼继承父亲“衣钵”,长年累月在华商处担任记账员并以此谋生。因其家族三代侨居印尼,黄东平对成千上万漂洋过海的华侨华人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的命运发展和人生轨迹颇为熟悉。又由于黄东平具有强烈的为华侨华人“请命”的责任感,有决心为华侨华人“画像”“立传”的创作意志,使其终成东南亚华人作家中的卓越代表。黄东平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是被誉为“华侨史诗”(1)许经汉:《黄东平简历》,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一卷,雅加达:印尼椰嘉达金门互助基金会文化部,2003年,第11页。的《侨歌》三部曲——《七洲洋外》《赤道线上》《烈日底下》。《侨歌》三部曲叙述了20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荷属东印度坷埠华侨社会中华人的生存和生活历史画卷,以及在艰难困苦中侨民与当地土著携手合作、艰苦奋斗,共同对抗殖民者的壮阔图景。《侨歌》三部曲的背景是荷兰属地“东印度”的大岛海岸边一个被华侨简称为“坷埠”的市镇。在这个市区只有几平方公里,四乡只有几万人的市镇,却有华侨、华裔一万多人,还有坷埠“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三保公庙”等,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华侨社会。生活在其中的华侨华人从“头家”到伙计、学生,大多是闽南人。在此,我们以主要人物“福昌”头家李熙昌为论述中心,探析《侨歌》三部曲中的闽南侨商形象。
一
在历史上,由于贸易、天灾等各种原因,“下南洋”是中国东南沿海居民传统的人生选择。“福建和广东是东南亚华人的主要移出地……闽南是福建最主要的侨乡,东南亚的‘福建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就是‘闽南人’的代称。”(2)陈衍德,卞凤奎:《闽南海外移民与华侨华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早期闽南人“下南洋”也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殖民者的海外军事、政治、经济活动有关。尤其是西方各国殖民者争相盘踞、开发东南亚,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工,于是“过番”的闽南人中有许多成为帮助殖民者开发东南亚的华工。由于闽南人善于经商,从唐、宋、元以来就与海外有商贸往来记载,林銮和涂文轩是唐代“中国民间到勃泥,亦即到马来西亚、文莱等地经商贸易的第一批有名有姓的商人。”(3)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过程中也有大量闽南人参与海外贸易。总之,中国古代有大量“下南洋”的闽南人去东南亚经商谋生,闽南海商集团更是数个世纪纵横外贸领域。据《菲律宾华人通史》介绍,“闽南海商集团崛起于13世纪,主导中国海外华商网络到19世纪中期。如同荷兰人被称为欧洲的‘海上马车夫’一样,较早进入远东贸易网络的荷兰人也誉称闽南人为中国的‘海上马车夫’、是17世纪中国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4)庄国土,陈华岳等:《菲律宾华人通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在闽南海商群体中,部分海商常居东南亚,或往返于东南亚与闽南之间,再加上部分华工在略有积蓄后也开始经商,所以侨商成为东南亚华人中最常见的一类人。也可以说,侨商、华工的身上凝聚着闽南的人文历史元素是闽南与海外(包括东南亚)的文化、经济交往的“媒介”。
《侨歌》三部曲中的“福昌”头家李熙昌就是作家黄东平为闽南侨商“画像”“立传”的突出艺术形象。李熙昌是厦门人,早年到南洋经商谋生。厦门早在明末清初就成为闽南乃至中国的重要对外贸易港口。“清初开放的四个口岸中,厦门即榜上有名,但四个口岸各有侧重:清政府给广州的政策是允许欧洲船只来华贸易;给厦门的政策是允许本地商人出海贸易。”(5)洪卜仁,周子峰:《闽商发展史·厦门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1页。这使闽南人出洋经商变得更为便利,侨商成为许多侨居东南亚的闽南人的身份标记,而“福昌”头家李熙昌则是代表闽南侨商的经典文学形象。李熙昌身上具有商人的典型性格:精明算计、务实逐利,善于与外人周旋,为此“脸谱”随时转换;他又紧紧护住自己商业“小王国”的利益,不惜苛待亲人和伙计,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唯我独尊。
身为务实逐利的商人,李熙昌遇事总要权衡利弊得失。比如他在走出福昌杂货店参加社会活动后,变成“身兼数职的社要”。这是李熙昌“兀自在心头打了一通算盘之后”,觉得“可以增加自己的身价”,也不至于太损及私利,才乐此不疲。商人大多具圆滑的共性,李熙昌特别善于与外人周旋,善于表演“变脸艺术”。南洋复杂的生存环境也是促使李熙昌养成见风使舵的多重性格的重要原因。“当他正在疯狂地斥骂伙计或家人时,一旦有商人进来,他会突然转化为满脸笑容,立即纵声大笑,聊起天来……”(6)[印尼]黄东平:《七洲洋外》,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一卷,雅加达:印尼椰嘉达金门互助基金会文化部,2003年,第140页。像李熙昌这样老于世故的商人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人,自然会具有不同的态度和反应。东南亚华人侨商生活于西方殖民者、当地土著和华人混杂共处的社会网络中,尤其练就出灵活多变的多重脸谱。他们忍受殖民者的压榨盘剥,在殖民者面前心存畏惧;他们在当地穷苦的土著面前,又显露出奸商的面目,要伙计在秤货时耍花样,在交易中弄虚作假,损害穷苦劳工的利益,甚至欺骗那些“一天只有两仙半工钱”的当地劳苦土著;在同道商人面前,他们时而谈笑自若,时而彼此恶语相向,为利益而相互倾轧。
比如在《侨歌》三部曲中,对伙计、家人“生硬可畏的态度”,以及转过头来就对外人“满脸笑呵呵”的态度,自然而然结合在头家李熙昌身上,“这不能不使不熟悉他的人感到诧异,但熙昌本身却好像没有自觉似的。”(7)[印尼]黄东平:《七洲洋外》,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一卷,第82页。李熙昌本人的“不自觉”,正是作家对长年累月在商场打滚的商人习性的深度刻画。又如《赤道线上》中,李熙昌面对殖民者势力时那种刻骨的畏惧心态有细微入神的精彩描写。李熙昌一生用心经营的福昌,可谓一个公众场合,各色人等往来于此,长年累月聚集着一些人喝茶、聊天。荷兰殖民者加强了对坷埠华侨的迫害,人人陷入危惧中。福昌店前聚集的何培基、黄坤山,甚至侨生林添禄,都认为发生暴动“不能免”。大家正沉入恐怖中,突然有黑影闯进来。
“哎呀!给荷兰鬼暗牌听到了!”李熙昌一震,话几乎脱口而出,身子也随之“自动化”地想站起来,可下肢一软,反教他挫倒在椅子上去了。于是他只好一再眨巴着眼睛定神惊望,才看清来人是张亚枚,而且“看见”他动作神色慌张。
“哎呀!快关店门!”熙昌的潜意识又电光般一闪,头立即旋向吴阿贵,但命令在他舌尖上滚了几滚,却又缩回去了。因为别人已先他开口:
“亚枚,外面有甚么消息吗?”
“没有呀……”张亚枚回答着,他知道大家在担心,又舒畅地笑了。
黄坤山、李熙昌们深深嘘出一口气,安安稳稳地瘫坐在椅子上了。(8)[印尼]黄东平:《赤道线上》,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二卷,雅加达:印尼椰嘉达金门互助基金会文化部,2003年,第372页。
以上对李熙昌行动的描述精细入微地刻画出他对殖民者惧怕到骨子里的心理。即使不是直接面对荷兰殖民者,而仅仅是“荷兰鬼暗牌”(这个“荷兰鬼暗牌”还仅仅是他的臆想),李熙昌已经不由自主地“‘自动化’地想站起来”,下肢发软而“挫倒在椅子上”。待到清楚来人是搬运工张亚枚,而且“荷兰鬼”方面没有消息,他才深嘘一口气,“安安稳稳地瘫坐在椅子上了。”对“荷兰鬼暗牌”的惧怕心理更能反映出以李熙昌为代表的侨商对西方殖民者深入骨髓的畏惧。李熙昌们之所以如此惧怕殖民者是侨商们险恶的生存处境所致。在中国在世界秩序中处于劣势地位时,华侨犹如巨石重压下的“野草”曲折艰难地生存着,没有强大的祖国可以依靠,只能任由殖民者盘剥、压迫。虽然比较成熟的华侨社会已经有了中华会馆等机构与殖民者交涉,可以代表侨民发声,但在华侨华人还没有足够团结并凝聚成强大的力量时,他们与殖民者的较量几乎都是以卵击石。
身为经商盈利的商人,李熙昌紧紧护住自己商业“小王国”的利益,不惜苛待亲人和伙计,特别是在伙计面前,李熙昌冷酷无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唯我独尊。伙计吴阿贵曾将李熙昌看作帮自己交纳“按地金”、领上岸的恩人,对熙昌头家满怀感激,带着子侄辈的感情为他效劳。但吴阿贵慢慢发现头家李熙昌在福昌就是高高在上的“主人”,君临福昌这个小“天下”,其余人都是“伙计”——长子捷华是要继承大统的“伙计”,熙昌婶是不受薪的“伙计”。李熙昌对待家人自然也有感情,对待店里真正的伙计,“都带着一种对待外人的察看、冷漠,甚至对立的情绪。”(9)[印尼]黄东平:《七洲洋外》,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一卷,第138页。对伙计而言,李熙昌是位极其严苛的东家。阿贵在福昌做了几年伙计,没有分文报酬。在福昌做牛做马若干年的长庚,老年罹患重病,李熙昌连探望都没有,只在需要长庚做事时问一声。病危之际,李熙昌提出送长庚去“老君厝”,即荷兰区的西人医院。那时埠里华侨常将失救的人送去给西医。“他这时的提出‘老君厝’所考虑的只是免得长庚死在店里,教福昌沾上不吉利,则长庚死在‘老君厝’,他又可以免得代收埋,花钱又费手脚而已。”(10)[印尼]黄东平:《赤道线上》,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二卷,第566页。面对伙计如此无情无义,可见商人李熙昌冷酷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
可以说,李熙昌在面对西方殖民者、同道商人、当地穷苦土著、伙计等不同对象时变化无常的多重脸谱,充分反映了一位华人侨商的心态和精神面貌,这个形象同时也反映了绝大部分侨商的共性。因为侨商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中,他们之上有西方殖民者,他们之下有伙计、华工和当地穷苦土著。这种“中间”状态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行为、心态和精神面貌,使他们具有共性。《侨歌》三部曲通过对李熙昌的形象刻画表现了这种东南亚华人侨商的共性。
二
由于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西方殖民者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等国家纷纷入侵东南亚,在殖民地对当地土著进行大肆的经济掠夺和政治迫害。对于早先抵达的华人(包括为数众多的闽南人),殖民者一方面利用,另一方面歧视和迫害。漂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内聚力更强,这是东南亚华侨社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学者高伟浓指出清代的东南亚华侨“聚落”居住形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农村社区;二是矿区;三是港口城市……‘华侨农业区’、‘华侨矿业区’,属于前两种类型;居住在港口城市的华侨,则主要是商人。”(11)高伟浓:《清代华侨在东南亚:跨国迁移、经济开发、社团沿衍与文化传承新探》,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高伟浓所概括的三种华人聚落形态到了20世纪依然存在,并在黄东平的《侨歌》三部曲中都有所呈现,而其中所描写的坷埠华侨社会就是由这三种形态的华人聚落所构成,对坷埠“中国人大街”、卡汶加烈橡胶园和斯达干煤矿的描述就是对上述三种形态华人聚落的典型表现。
在《侨歌》三部曲中,坷埠华侨社会(港口市镇及农业区、矿业区)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在中华会馆的领导下,以及中华学校教师徐群的推动下,侨领、侨商、侨众携手一致应对困局,并在困难和共同协作中激发出空前的团结、热情和大爱精神,推动华侨社会不断发展。在时局、事实和时势的推动下,侨商李熙昌的认识(见识)和行动不断变化,性格和精神面貌也有所变化。东南亚华侨社会中的资金相对厚实或贡献比较突出的侨商往往也兼具侨领角色,侨商李熙昌就是如此,在时局变动中他的精神境界在不断提升,体现出身为华人侨领应有的精神格局,为华侨社会及故国家园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后殖民理论认为身份是被建构的,人的身份意识受到社会、文化、权力的深刻影响。坷埠华侨社会经历了多番激情澎湃的募捐活动和互助活动,侨领、侨商和普通侨众在参与重要社会事件的过程中激发出他们不同以往的认识和身份意识。李熙昌也是如此。李熙昌虽然是个颇精明、有心计的侨商,遇事总要谋算、权衡一番,不做吃亏事,但他到底属于华侨社会的“好人”,又因为是福昌头家、侨领,各类募捐总比一般侨众表现更积极些。在为中华学校募捐时,李熙昌慷慨捐出一千盾,支持华侨教育事业。1928年年底,美国华尔街发生金融风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恐慌发生。殖民统治者决定“提高税则和加强税收”,从“支那”商人那里拧出钱来。侨商生存变得艰辛,普通侨众更是艰难困苦。“‘我想了好几晚,再这样屈辱、忍受下去,将会得到怎样的结局?看来不做些什么给荷兰鬼看看是不行的啦!’……怕事的李熙昌,今天也作出这‘激越’的主张,这样可以代表那些一向只知采用圆滑手段应付恶劣环境的华商的新见解了。”(12)[印尼]黄东平:《七洲洋外》,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一卷,第470页。中华会馆及下属各团体关于组织华侨、共度时艰的具体办法出来了。李熙昌捐出白米二十五大包,并表示福昌店里可以安插两三个人“弄帮”(也即义务地给生活无着的侨众提供食宿)。从总是在肚子里打算盘的头家到“激越”主张给“荷兰鬼”颜色看,再到实实在在帮助普通侨众解决困境,李熙昌确实在改变着。华侨社会互助互济、共度时艰,坚持一年多。侨商黄坤山是被李熙昌带动的,感叹要支持到什么时候?李熙昌心头“立即引起一阵共鸣的颤抖”,但作为 “积极分子”,这又激起了李熙昌的“抵触情绪”。“再久,再苦,——也得支持下去!这事关系到咱们全埠华侨的前途!哪能让许多贫苦的侨胞沦为乞丐?哪能让华侨的团结和组织垮了下去?哪能让荷兰鬼耻笑咱们唐人?”(13)[印尼]黄东平:《赤道线上》,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二卷,第14页。他把从中华会馆听来的大道理一股脑儿地抛向黄坤山。这些大道理虽然不是李熙昌个人的深层认知,但他脱口而出的劝导,也表明其对这些大道理的认同。惟其如此,他才能忍着痛苦,苦苦支持坷埠华侨社会的公益行动。
支持斯达干煤矿罢工和尽力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是坷埠华侨社会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斯达干煤矿罢工斗争根源在于殖民者的压迫加剧。“殖民”是南洋群岛各民族人民被迫害的主要根源。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强国凭借着军事、科技的强势,踏上南洋群岛,但他们吃惊地看到已经有不少中国人在开拓南洋。勤劳、善良、忍让、没有祖国“撑腰”的华人移民与群岛上的土著一样,成为西方殖民者的压迫对象。侨商们议论“红毛鬼(指英殖民者)是钻,荷兰鬼是铇!”“熙昌笑着代说明:‘统治马来亚、缅甸等地的红毛鬼,专找有钱的下手,有如钻,一钻到底,但有重点;荷兰鬼则不分贫富,一视同仁地压下去,鉋得又光又干净!’”(14)[印尼]黄东平:《七洲洋外》,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一卷,第174页。不仅坷埠港口市镇的侨商侨众深受荷兰殖民者之害,而且斯达干煤矿的华工和当地穷苦劳工在殖民者的控制和压榨下,同样深受其害。两族工人终于秘密携手合作,开始了反抗殖民者的斗争历程。“大狗”(华侨用来指荷兰或英国警长)及其他殖民统治者极力破坏两族矿工的团结罢工。坷埠市区支援罢工早已酝酿开了,徐群指导的青年学生鼓动其事,中华会馆的进步侨领相应其事。侨商李熙昌们对华工的慷慨支持是殖民地特殊社会关系所促成的。“法侬认为,在殖民地,最根本的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种族对立,而不是阶级对立。”(15)赵稀方:《后殖民理论与台湾文学》,台北:人间出版社,2009年,第17页。黄东平的《侨歌》三部曲充分印证了法侬的理论。“作为小有产者的侨商,对于支持工人罢工,对抗雇主,确乎不会感兴趣,但华侨社会却是例外。在当日的华侨中,同受殖民者压迫,同是唐人,这两个共同点就具备着潜在的巨大鼓动和号召力。”(16)[印尼]黄东平:《赤道线上》,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二卷,第298页。坷埠华侨社会不分阶级、不分行业能够团结一致对抗殖民者的压迫,与李熙昌等侨商、侨领的带头作用分不开。李熙昌被荷兰军警逮捕,他一腔愤慨、满心沉重。在坷埠华侨社会热情支援斯达干煤矿工人罢工斗争中,李熙昌顺应时势变化,并为此做出牺牲,李熙昌的心已经与全体被殖民者压榨的侨众的心连为一体。
到了《侨歌》三部曲第三部《烈日底下》,坷埠华侨社会支援祖国抗战,抵抗日寇侵略,成为头等大事。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李熙昌认识到时局大势不可违,慢慢在各种事实的教育下,成为了做出更大贡献的侨领。李熙昌向学生们宣传日寇侵华,介绍祖国近况;当他看到小儿子敏华在街头宣传,心情复杂:他为敏华“干的是为国为民的大事”而“感到无比骄傲”;又担心“他骂起南京政府”而遭到坷埠国民党党部的报复,“但终于骄傲占了上风,熙昌认为青年学生们是对的,又得到侨众的支持,党部可能不敢下手;他深感自己今后责无旁贷,应该为爱国事业尽最大的力量。”(17)[印尼]黄东平:《烈日底下》,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三卷,雅加达:印尼椰嘉达金门互助基金会文化部,2003年,第26页。在大时代的推动下,李熙昌虽然一直不脱商人精于算计、权衡利弊得失的秉性,但终于跟上了时势并超越普通侨商,具有了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感和责无旁贷、救国救民的担当意识。“坷达班岱中华会馆筹款救国委员会”成立了。徐群建议不用捐册,只备一个大捐筒,由侨众自愿筹捐。捐款进行了一个多月,最后汇总时传出惊人的消息,中华会馆收到的全部捐款达到七万八千多盾。在轰轰烈烈的义捐活动中,李熙昌的见识和胸襟变得更加宽广。“‘我国受辱到这地步,何能再屈膝求生?’李熙昌激昂地说,‘只要能起来抗战,中国就决不会亡!我中国要扬眉吐气,就在这个时候,何必怕一时受苦。苦尽甘来,中国必然强盛!’”(18)[印尼]黄东平:《烈日底下》,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三卷,第432页。身为侨领,李熙昌终于站到了坷埠华侨社会的“制高点”,引领华侨社会的动向和发展趋势,并且深刻认识到祖国的灾难深重与其在国际关系中倍受伤害的深层联系。这时李熙昌的“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分外突出。在为祖国义捐的行动上,更是令人震惊地慷慨捐出一万盾。虽然这毁家纾难的捐款大行动也是他“早已排比盘算了好些日子”,但李熙昌到底是行动派,也是爱国者,在时局的推动下,李熙昌已经突破了一家之私和个人利益的局限,发挥出侨领的重要带头作用,成为引领坷埠华侨社会风潮的重要人物。
可以说,作为侨商,李熙昌确实有着务实逐利、精明算计的商人本性,虽然侨商是华人群体中处于上层地位的华人移民,但处身于漂离母国的异国环境中,与其他华侨华人存在着血脉相连的文化亲情;又因为侨商与普通侨众共同处于西方殖民者压迫盘剥之下,是同属于被压迫的弱势种族群体和利益共同体,所以能够团结一致对抗殖民者,彼此守望互助而共度时艰。血脉相连的文化亲情与在异国环境中作为弱势种族被迫害的深切感受、深刻认知,唤起侨商和其他华侨华人强烈民族(身份)意识、爱国情怀的巨大力量。他们在祖国的抗日战争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历史上海外华侨华人爱国爱乡的艺术写照。
三
南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使闽南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心,这也成为促成闽南人大量“下南洋”的动因之一。闽南人大概是最早移民东南亚的华人群体。“福建人是马新最早的华族移民。早在15世纪初马六甲王国建立后,华人陆续在马六甲定居。”“马六甲早期著名华人甲必丹郑芳扬和李为经都是闽南人的事实见证了福建人在当地占多数和支配的地位。”(19)颜清湟:《福建人在马新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林忠强等:《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早期东南亚的“福建人”实际上就是“闽南人”。在马来西亚槟城,早期五大姓氏谢、邱、杨、林和陈都来自漳州。在近现代,在海外经商、创业打拼的闽南人比比皆是,在东南亚的闽南人尤其如此。许多闽南移民白手起家、艰苦奋斗、成功创业,成为著名侨商、实业家,如祖籍安溪的林梧桐、祖籍惠安的骆文秀、祖籍永春的陈志远等。黄东平《侨歌》三部曲以李熙昌(侨商/侨领代表)、吴阿贵(伙计/华工代表)、徐群(知识分子代表)等三位重要人物为支撑,勾勒了波澜壮阔的南洋华侨社会历史画卷,其中李熙昌、吴阿贵都属于闽南移民,代表了闽南族群中的侨商/侨领和伙计/华工,可谓真真切切把握了南洋华侨社会的人文历史。
身为“下南洋”的闽南移民,李熙昌身上自然而然蕴含着闽南人的精神气质。这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强烈的家国观念和家族意识。在历史上,闽南人多数属于中原移民的后裔,从中原南迁,接着东渡台湾,或播散海外。闽南人具有极强的宗族观念和家族意识,慎终追远不忘故国家园,这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自古以来,因各种原因“下南洋”的闽南人努力打拼的一个现实目的就是为了让故乡亲人过上像样的日子。“番邦钱,唐山福”这样的闽南俗语反映了闽南移民思慕家乡、顾念故乡亲人的家乡情怀。李熙昌与他们一样,不断汇款奉养故乡老母和其他亲人,对于过继兄弟也有一份顾念之情。他将侄儿少华接到南洋学做生意,主要原因乃是身为闽南人的家族意识。这种对家乡亲人的顾念之情升华为对祖国家园的慷慨支持,在坷埠华侨社会以募捐形式进行抗日救国的运动中,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个人所能做到的最大贡献。李熙昌这种护家爱国的精神及实践行动也是现实中许多爱国华侨的艺术投影。其二,强烈的海洋文化色彩。陈支平说:“闽南人最显著的人文特点是具有比较浓郁的海洋文化色彩,比较注重财富的追求,勇于冒险。自唐宋以来,闽南人以其面临大海的自然优势,甘冒风涛之险,向海洋发展,进行国际贸易。”(20)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4页。这也可视为是不同于内陆文化的闽南文化特点、闽南人文历史和人文环境,它造就了闽南人向海洋发展、冒险求进的人文精神,也体现为闽南人“爱拼”“会赢”的人文性格。李熙昌沿着闽南先民的脚步“下南洋”,在异国打拼出福昌这片商业小天地,“决不肯在商场上败下来,”以至于不自觉地成为“华侨商业连锁网里的樁眼”,“即使钱赚多了,他也非照样干下去不可,死而后已。”(21)[印尼]黄东平:《赤道线上》,许经汉:《黄东平文集》第二卷,第499页。李熙昌由此成为闽南人“下南洋”进行商贸活动的人文历史“样板”,具有深沉的闽南侨商精神气质。
四、结语
作家黄东平一生依靠为商人记账谋生,因此对商人群体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和判断。《侨歌》三部曲为我们呈现了众多的商人(侨商)形象,其中福昌土产店头家李熙昌是最为典型、个性最为鲜明丰富的闽南侨商形象,是体现了闽南人“下南洋”、谋生存、求发展的人文历史传统的艺术形象。李熙昌身上既具有商人务实逐利、精明算计的典型性格,也具有作为华人侨领为侨众做实事、为国家无私奉献的大精神格局。李熙昌远在南洋却时刻顾念唐山亲人,体现出闽南人比较强烈的家族意识;在南洋打拼经营生意,多数时候稳扎稳打,但也有冒险求财的投机心理和行为,具有闽南人“爱拼”、冒险求进的人文性格。李熙昌身上有着闽南文化的精神胎记,是闽南文化孕育而出的艺术形象。黄东平耗费数十年呕心沥血刻画的具有多重身份和多面性格的李熙昌这一文学形象,既集中书写了殖民地时代华侨华人在缝隙中求生存的群体特征,又体现了其作为闽南移民所携带的闽南族群文化基因,值得我们一再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