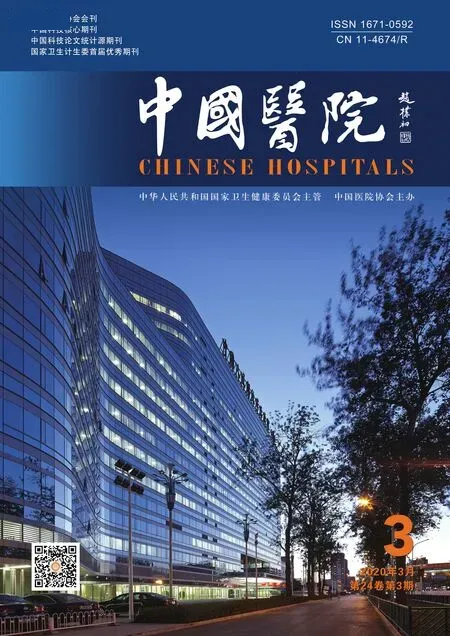“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国际经验及借鉴
2020-01-19寸待丽崔文彬于广军
■ 寸待丽 崔文彬 于广军
近几年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并不仅仅是受到健康经济因素的驱动,更主要是因为飞速发展的计算机科学和互联网信息技术。“互联网+”医疗服务作为科技变革进程中重要的一环,已经成为当今医疗服务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互联网+”医疗服务通过减少疾病负担、并发症发生率、住院率、疾病复发率和过早死亡的风险来降低医疗成本,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在心血管等慢性病的预防和长期照护上具有特殊的巨大潜力[1]。我国医疗信息化起步较晚,但“互联网+”医疗服务已然走在了世界前列,不过仍然存在着政策法规不健全、标准规范不统一、数据共享困难、数据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作者通过查阅文献和访问相关网站,梳理国际上“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发展历程、先进理念和实践经验,为我国“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1 “互联网+”医疗服务概念内涵和历史进程
1.1 概念内涵
“互联网+”医疗服务这一概念源于e-Health。e-Health是一项基于现代化的电子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医疗健康服务实践,至少可以追溯到1999年。这一专业术语概念各不相同,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它至少有51种不同的定义。在这51种定义中,引用最多的是:“e-Health是医学信息、公共卫生和商业交叉领域的一个新兴领域,指的是通过互联网和相关技术提供或增强卫生服务和信息[2]。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个术语不仅代表技术发展,还代表一种思想状态、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态度和一种承诺,即通过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通过网络和全球思维来改进本地、区域和全世界的医疗保健。”
总之,e-Health这个术语包含电子健康档案(electronic health record)、计算机化医嘱录入(computerized physician order entry)、电子处方(ePrescribing)、临床决策系统(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远程医疗(telemedicine)、远程康复(telerehabilitation)、远程手术(telesurgery)、远程口腔(teledentistry)、消费者健康信息学(consumer health informatics)、健康知识管理(health knowledge management)、虚拟医疗团队(virtual healthcare teams)、移动医疗(mHealth /m-Health)、网络医学研究(medical research using grids)、卫生信息系统(health informatics /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s)等处于医学/医疗保健和信息技术边缘的服务或系统。而“互联网+”医疗则是“e-Health”的中国表述,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最先引入“‘互联网+’医疗”这一概念[3],其内涵与e-Health类似。
1.2 历史进程
e-Health最先出现在美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心电图(ECG)的发明者威廉·埃因霍芬(Willem Einthoven)率先将医疗信息通过电信号将心电信号从医院传送到1.5公里外的实验室。1949年香农(Claude Shannon)和罗伯特·法诺(Robert Fano)开发了第一个数据传输压缩算法——二进制。1966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了ATS-1卫星用于远程医疗,这是未来数十年众多用于远程医疗卫星中的第一个。1967年麻省总医院(MGH)远程医疗计划建立,医生每天24h使用双向微波音频/视频为机场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1968年杜克大学创建的电子病历系统(TMR)成为美国最早的电子病历系统之一,也是目前通用电子病历系统(EMR)的原型。1969年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ARPANET)接通,ARPANET是世界上第一个可操作的分组交换网络,也是组成全球互联网的核心网络。1971年实现了计算机化的医生指令输入系统(CPOE),1972年由医生设计的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信息系统Regenstrief医疗记录系统(RMRS)出现。1977年加拿大的远程医疗服务开启,同时“互联网+”医疗服务实现移动设备端到端的无缝传输,产生了第一个商业网络ARCNET以及出现了电子处方自动书写系统。1980年MGH开发了一个基于计算机的医学教育、参考和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DXplain。1984年澳大利亚的西北远程医疗项目建立。1989年美国医学信息协会(AMIA)成立,国际协作形式的连接亚美尼亚和乌法的美苏远程医疗咨询太空桥出现。随着1991年互联网的第一个web服务器斯坦福线性加速器(SLAC)创建和1992年互联网站的大量注册,奠定了“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基础。1993年美国远程医疗协会成立,1995年负责维护医疗保健应用中的隐私和安全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成立,1999年创建有关健康和保健信息的互联网站点WebMD,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WHA58.28号决议世卫组织认识到互联网的日益重要性及其通过广告和促销医疗产品影响健康的潜力[4]。进入21世纪以后,web2.0和web3.0为“互联网+”医疗服务创造了条件,3G/4G以及5G技术的兴起更是将互联网医疗服务引入无限可能,全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各国家和地区都开始建立、完善和创新自己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体系。
2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国际经验
2.1 美国经验
美国很早就创建了区域卫生信息组织(RHIOs),发布了医学研究院(IOM)患者安全数据标准,成立了国家卫生信息技术协调员办公室(ONC)、卫生信息共同体(AHIC)、卫生信息技术标准委员会(HITSP)。而美国1996年通过的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PA)则引领美国走在了世界健康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先列。该法案对多种医疗健康产业都具有规范作用,包括交易规则、医疗服务机构的识别、从业人员的识别、医疗信息安全、医疗隐私、健康计划识别、第一伤病报告、病人识别等。在病人隐私保护上,HIPPA要求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机构制定保障政策和安全措施来保护患者医疗信息,无论这些信息存储在纸上、计算机上还是云中。患者有权查看自己的医疗记录和决定谁可以使用自己的医疗数据。在医疗数据安全上,HIPAA会对数据泄露的医疗机构进行高额罚款的同时协同专业IT机构给出了医疗机构数据保护措施的建议:数据加密、控制存取、用户认证(密码和生物信息识别)、使用虚拟专用网或VPN提供安全的远程访问和基于角色的访问规则等[5]。
2.2 英国经验
英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国民拥有良好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制度。英国互联网医疗服务系统主要分为以下3类:(1)基于国家层面来促进整个国家互联网医疗服务生态系统的中央服务系统NHC,无论患者处于何地接受何种医疗服务,该系统都可以通过特定的身份识别来获得患者的就医记录,同时监控医疗服务质量以及根据患者的需求调整医疗服务计划。(2)基于地区的互联网医疗初级医疗保健服务的地方服务系统Albasoft,英国各地区系统之间相互连接并且借助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和医疗服务规划来提供更高效便捷的互联网医疗服务。(3)基于日益增长的自我健康管理和护理需求的互联网个人护理解决方案服务系统NHC Choices、Grey Matters、Cellnovo、Handle my Health等。通过远程移动监测、症状识别自查和危险值警示等来提高病人自我监控、诊断和治疗的能力。此外,英国于2018年5月推出的《国家数据选择退出》(National data opt-out)使患者能够根据《国家数据选择退出》的建议和指导,自主选择决定自己的医疗数据是否可用于研究或其他目的,病人能够查看自己医疗数据的用途并且随时可以更改自己的选择[6]。
2.3 丹麦经验
在欧盟国家中,丹麦的公众对医疗体系的满意度最高。在于“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推进方面,丹麦也被视为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榜样。丹麦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成功可以归功于精湛的计算机信息技术、政府对医疗健康服务的重视和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从而创建了两个比较成熟和便捷的中央医疗保健数据网络系统Sundhed.dk和MedCom。丹麦人可以使用数字签名登录Sundhed.dk来预约医生、订购药物和更新处方、查看药物记录和健康数据,并与医疗卫生当局沟通,卫生人员须利用安全证书才能登录该门户网站访问医院的记录摘要和其他医疗信息,用于患者治疗目的之外的其他任何患者医疗健康数据使用均需征得患者同意。MedCom通过开发、测试、分散风险来确保卫生部门电子通信和信息的质量安全,实现了丹麦5 000多所医疗机构和50个不同的技术供应商都使用同一个电子表格系统来为患者提供初级保健服务。医疗责任方面,丹麦政府协助澄清病人积极参与的跨部门合作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的过错方,并且努力杜绝互联医疗服务的“灰色地带”[7]。
2.4 加拿大经验
加拿大与其他拥有全民健康保障体系的国家相比,加拿大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稍显逊色。加拿大互联网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安大略电子健康系统(eHealth Ontario),eHealth Ontario的药物档案审查系统可以显示250万安大略省药物福利计划和Trillium药物计划参与者的处方药物信息。eHealth Ontario的电子处方试点项目让医疗机构的医生通过电子方式将处方发送到相应的当地药店从而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目前仍在使用[8]。 由于加拿大的医疗信息系统是以省为单位创建,全国没有统一的运行系统和标准,加拿大民众所体验到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参差不齐,尤其在线上预约、检测结果查询和线上咨询问诊等方面。出于隐私安全考虑,加拿大的医疗健康数据被分散保存在不同的地方,只对特定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开放,全国没有联通的医疗数据共享系统,患者的医疗数据常常需要重复输入。另外,加拿大也没有全国统一的官方医学信息网站,人们获取医疗知识的途径是通过互联网,而互联网缺乏监管,医学信息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无法得到保障。
3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中国借鉴
中国互联网医疗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漫长的探索期,2011年开始步入了市场启动期并于2016年迎来了高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12-2016年,我国互联网医疗保持38.7%的年复合增长率,2016年已经达到109亿人民币的市场规模。根据预测,2016-2026年我国互联网医疗的年复合增长率将维持在33.6%的水平,并于2026年达到近2 000亿人民币的市场规模。
互联网医疗与互联网的发展密切相关。总体而言,我国互联网医疗可以划分为PC互联网阶段的1.0阶段,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2.0阶段,目前处于2.0阶段向3.0阶段的过渡期,3.0阶段意味着向互联网医院方向完全转型。这一过渡期的主要特征是实现诊疗线上化,最终3.0阶段将实现全面的互联网医院,囊括诊断、远程治疗、处方药开具等服务内容。目前我国互联网医疗产业已经整合了移动医疗服务商、医疗设备制造商、IT巨头、风险资本、移动运营商、应用开发商、数据公司和保险企业等众多参与者,形成了以在线医疗和可穿戴设备为主的产业格局。
针对我国互联网医疗服务目前存在的政策法规不健全、标准规范不统一、数据共享困难、数据安全隐患、专业人才匮乏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不仅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还要吸取国外经验教训来规避风险和解决互联网医疗中的实际问题。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健全的政策法规和规范指南来规范和监督互联网医疗服务、保护数据安全和患者隐私,可以借鉴英国畅通的国家级、地方级服务平台的构建来打通数据共享通路,借鉴丹麦政府对人才的重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来吸纳专业人才提高医疗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民众对互联网医疗的参与度。至于医疗责任追责问题,发达国家医生大多以个人名义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责任方与医疗机构无关[9]。我国可以借鉴丹麦政府部门参与积极澄清病人与医疗机构的过错方,由过错方承担医疗责任并且减少互联网医疗服务“灰色地带”的做法。
4 小结
总之,我国e-Health的起步虽然较晚,但是在“互联网+”医疗服务方面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其高效和便捷有目共睹。目前世界都在积极建设和完善自己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体系,但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发展或多或少还存在一些阻碍和壁垒。我国要在借鉴国际上先进理念技术和吸取国外经验教训的同时结合国内形势积极探索出属于自己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体系和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