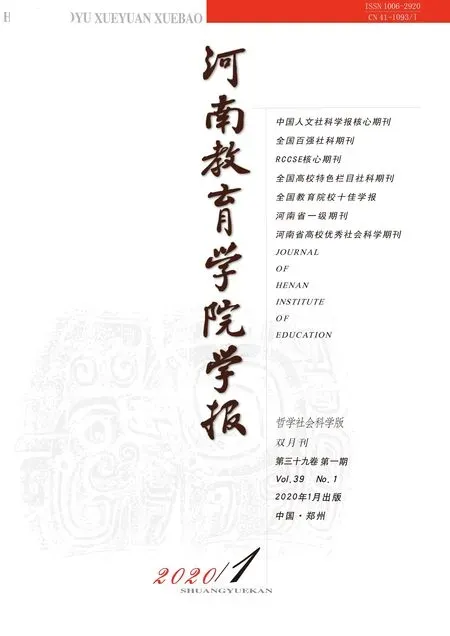中国式家庭性别关系幽灵的显影、破解与缝合
——关于小说及热播剧《都挺好》性别表达的思考
2020-01-19马为华
马为华
由阿耐的小说《都挺好》改编而成的电视剧《都挺好》一路走红,豆瓣评分开播就是8.5分,这在国产电视剧里是很不寻常的分数。与阿耐小说原作比,电视剧将一些冲突戏剧化了。但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剧,都抓住了转型期中国原生家庭的痛点,对中国式家庭性别关系及其想象有着精准独到的呈现与表达。
一、父母皆“祸害”?
通常意义上当我们谈起家庭的性别关系时,都会有一些诸如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被家庭这个父权制最集中的化身所剥夺压榨等刻板印象。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其实往往并不是这么一律,否则也不会有“妻管严”这一类的称呼。通常表现家庭关系矛盾都会集中笔力写婆媳矛盾,或者是改头换面的后妈和女儿之间的矛盾争斗,这是男权制家庭中两个外来女性通过争夺男性来争夺权力的斗争。《都挺好》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于这些既定关系模式的突破:纵观整部小说,那个没出场就死去的母亲才是所有矛盾的根源所在。她剥夺了明玉上好大学的资格,剥夺了她在家里放一张床的资格,让明玉十八岁就要独立养活自己;她强势压迫自己的丈夫,让他唯唯诺诺,十几年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她把二儿子宠成了无用且自私暴力的“啃老族”。她是儿子们的天使,同时又是女儿和丈夫的魔鬼。小说一开场她就死了,她的影响力却虽死不灭,幽灵般地持续影响着还活着的苏家人的生活。
天使和魔鬼这样两极对立的女性形象是男权文化里常见的女性形象。天使代表着希望与恐惧,魔鬼代表着规训与惩罚。我们耳熟能详的白雪公主童话故事里,完全没有自己欲望的甚至可以给七个丑陋的小矮人服务的公主是天使,那个想要掌控白雪公主人生的继母是恶魔。就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而言,我们的文学作品里有很多伟大的母亲形象,但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反而应该是恶魔般的母亲形象,其中最为著名的恐怕要数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和铁凝《玫瑰门》里的司猗文这两个形象。这两个形象的共同点都是恶得令人毛骨悚然而又无比真实,而且曹七巧和司猗文都是那种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欲望而会扼杀下一代——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的生活的恶母形象,这样的形象刻画自然有其深刻价值,但是却似乎有些过于戏剧化和文学化,更接近于西方文学传统里那个疯狂的美狄亚形象。阿耐的《都挺好》里展现出的母亲形象更接近中国社会生活里的具有日常性和普泛性的母亲形象。这个重男轻女到极致的母亲是一个集恶魔与天使于一身的复杂形象,这恰是对中国式男权制度下的性别特质最到位的表达。任何一种权力制度的特点都是高度关注权力,更关注这种制度下每个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只有各就其位的角色才能保证制度的稳定与“光滑运作”。因而,任何一种性别,只要能保证权力等级制度的顺利运转,无论男女都可以成为权力结构里的掌权者。中国历史上位高权重的太监就是中国式男权制度下的特殊产物,《红楼梦》里有话语权的是贾母,掌管整个家庭运作的是王熙凤。阿耐的《都挺好》里的母亲则是个永远在场的权威,她在小说里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却是不可言说的威力无比的威权本身。
小说除了将中国家庭里非常具有特色的强势母亲显影出来,将和这种母亲形象相对称的父亲苏大强也塑造得格外生动,以至于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热播之后,各路媒体广告都衍生出了不同版本的苏大强表情包。苏大强是妻子强势的牺牲品,一生唯唯诺诺,但是在妻子死后,仅仅因为他是个父亲,又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是个被折磨过的丈夫,他以父亲的名义同时又以被折磨过的委屈姿态不断盘剥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一种剥夺方式让子女很难反抗,因为是可怜的、受过苦的父亲,所以在中国这个特殊的文化语境里多少子女都在咬着牙忍受这种盘剥。这种父母形象的出现,呼应了现实生活中处于家庭秩序转型期下的中国儿女们独具一格的疼痛,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阎云翔是持续关注中国家庭与个体生活变化的学者,从他早期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观察到的子女日益离开父母,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到最近他所提出的“新家庭主义的观点”都显示了学者特有的敏感。他指出新家庭主义的特点是,“新家庭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家庭主义,它赞扬个人的价值,同时强调家庭利益的优先地位。它将家庭生活的重心从祖辈转移到孙辈身上,从而重新定义了家庭生活的意义”[1]。充满洞见的他看见了家庭生活对于中国人而言的那种意义,无论时代怎么变迁,从聚族而居到核心家庭出现,中国人都还是具有非常强的家庭观念的人。但阎云翔所不能明了的是,他把这种新家庭观念仅仅归结为利益驱动,不过是基于功能主义工具主义思维对鲜活事实的偏离。新家庭观念中,并不仅有利益,也还有斩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结。否则豆瓣上不会出现一个很热门的“父母皆祸害”的讨论小组。那么多人聚集在那里痛诉自己从父母那里受到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多半是情感和心理上的伤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正是因为中国人从来都对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有着很深的期待,也才会导致更多的失落与被害感,所谓爱之深责之切。阿耐的小说《都挺好》对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家庭关系做了很好的呈现。
二、发现女性形象与创造女性形象
《都挺好》不仅显影了中国式家庭性别关系,更重要的是成功刻画了一个可亲、可敬、可信的女主人公形象苏明玉。明玉刚出场的时候就明确地表示过“法律上她承认有父母、二哥,道义上她承担相应责任与义务,但感情欠奉”[2]13。随着小说的展开,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在被自己强势的母亲压制嫌弃甚至不无虐待中长大的女性,她和自己的父母几乎势不两立,恨不得如同“哪吒般剔骨还身”[3]212,永远脱离和苏家的关系。她又对自己的身世充满了好奇:“她但凡是妈在外面偷情的产物也罢了,起码还是爱情结晶,可偏偏看来她应该是个权色交易的产物,她的产生,是为了拉那个至今不成器的舅舅进城。她是工具,而不是结晶”,“她的孕育是如此无耻丑陋”,“她是个生来就被诅咒的。她不知道自己需要多少自信自强才能正视自己的出生”[3]125。一边是对自己身世的探索,一边是明玉父亲反复强调明玉是最像她母亲的人,“那眼神和说话方式让苏大强万分害怕,不敢直视”[3]128。
在探询的过程中她发现了那个施虐者母亲原来同时是个受虐者的事实,而且指认了一种恶毒可以代际传递的中国式女性命运:“她的外婆,她的妈,还有她,是不是也一脉相承?”“三个女人的恶毒秉性一脉相承?三个女人都咬牙切齿地为别人活着”[3]136,中国女性从小到大在父权文化家庭中长期受虐,等到年纪渐长拥有一定权力的时候,往往会心安理得地变为施虐者,以“补偿”当年自己受过的苦,正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近年热播的很多“大女主”电视剧,如《甄嬛传》《芈月传》,似乎演到最后都在比狠斗恶,支撑这种人物形象的文化心理逻辑也当在此。阿耐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她必须停止如此变态的代代相传,不为别人,只为她自己正常的、不阴暗的生活。”“所有的阴暗都必须停止,即使她还有很多仇恨没有清算,还是得停止,否则她的一辈子都得搭进去。”“忘记过去的最佳办法,不是将过去的每件事做个了结,那将没完没了。而是,潇洒或不潇洒地硬说一声再见,一刀切。”“她像个阴气极重的女鬼急需阳气拉扯一把,否则无以回到人间。”[3]137-138明玉在发现了母亲命运真相的同时,也在另起炉灶、创造自己的形象:她不再重复母亲的命运,不再成为彻头彻尾的牺牲品和阴鸷的施虐者,而是和家人保持疏离的关系。苏明玉一边划清界限,一边力所能及地去帮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她可以因为死亡而宽宥她的母亲,但是她不会爱她的母亲,也不打算让人错会她会爱她的母亲。”[2]29“她一个受伤者被压迫一辈子了,难道还得去照顾既得利益者的小心灵?公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有能力,她自己会创造。”[3]129
除此之外,《都挺好》里明玉人物设定并不符合一般大女主戏的标配:“除了与女主角最终修成正果的男主角之外,每部剧至少还有两个男性角色对女主有着爱慕之情,并对其成长成功助力颇多。这些男性角色无一不是兼具容貌与才华,并对女主角一片深情。……而这类电视剧中的女性配角,除了极个别是为男女主人公的感情起推动作用之外,大多数都被设定为嫉妒乃至憎恨女主的才华和美貌、处处为女主的成长之路设置陷阱的反面角色。”[4]明玉身边有父亲般的蒙总,柳青性情气质与明玉最相合,也都是工作上叱咤风云、配合很好的好伙伴,但明玉最终却选择了会疼她、对她充满了保护欲的石天冬。明玉和自己的嫂子之间也似乎有更多的默契与相通,而不是互相“嫉妒与憎恨的关系”。
三、缝合式的职场女性生活想象及其限度
摆脱了原生家庭束缚的明玉,最终赢得了石天冬的爱情,似乎是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生赢家,但明玉形象在这当中经历的变化是很耐人寻味的。从一出场似乎可以掌控一切,但几乎没有性别魅力,也不会照顾自己饮食起居的花木兰式“大女主”,转变为被爱人呵护、怜惜的小女生,这几乎是明玉人生历程的概括,借由此种方式明玉逃避了她所恐惧的“阴盛阳衰”的家庭模式。起初她觉得,“她接触的年龄适合的人里面,除了柳青,别人似乎都可以让她阴盛。不,她不愿意,她宁可不结婚也不重复父母的生活,那等于自杀”[3]30,但矛盾的是她最后选择的人生伴侣不是不会让她阴盛的、职场上默契度非常高的柳青,而是看起来平凡普通的石天冬。经由石天冬,苏明玉才知道自己也是需要疼爱、怜惜的“女性”,这是变形的现代中国版灰姑娘童话:只有男性的爱,才能恢复女性的生命活力,即便是事业有成的职场女性,没有男性爱情的加持,便不能算是人生赢家。电视剧播出后,很多人都觉得整天捣鼓吃的、没什么事业心的石天冬配不上明玉,电视剧最后把原小说中出身平凡的石天冬改成了富二代以增添人物光环,仍避免不了“配不上”的评论。女强人明玉对这种“阴盛”的不无矛盾、违和之感的逃避,很有点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的味道,而大众文化叙事中矛盾绽出而又最后光滑解决的情节,才是现实生存困境的症候式表达。矛盾“冲突并不是文本的缺陷;它揭示了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他者’,而文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与自身的边缘和自身之外的世界维持着关联。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就是要揭示其非独立性,并时刻牢记在文本的物质实在中包含着某种确定的缺席的痕迹;这种缺席同样是文本自身不可或缺的特性之一”[5]92。就明玉这一形象而言,缺席的是职场女性的现实处境,专门有词来指认这种处境:“剩女”白骨精。剩女,这个词别具匠心而又不无嫌弃和恶意;所谓的白领、骨干、精英,却没有婚姻、伴侣,是被剩下来的女性。她弃柳青而选择石天冬,恰恰是中国女性已经独立强大,而这种强大却既不能被社会接受,也不愿被自己接受的胶着生存状态的呈现。
“文本是围绕着不可言传的缺席之物建立起来的,某些为文本所压抑的词句时刻威胁着文本,试图‘卷土重来’。因此,这本书并不是某一种意义的延伸,而是包含了若干种意义的矛盾体;而正是通过这种剑拔弩张且连绵不断的矛盾冲突,本书将自己与现实牢牢绑在了一起。”[5]140《都挺好》引起热议的原因也在于它是和中国转型期极具矛盾乃至痛感的各种伦理关系变化绑在一起的,能干的职场女性明玉经由平凡而又包容的石天冬回归“安全”的性别秩序。这是现代化转型中,对中国当下职场女性理想生存方式的一种缝合式的表达和想象:社会身份地位是独立的、现代的,情感需求是古典的、传统的,这种想象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神话式表达。神话从来都是人类建构意义的一种方式,“其作用在于提供一个合理的模型,消弭社会中的矛盾”[5]149。《都挺好》从小说到电视剧最大的变动就是对于原小说中复杂的家庭性别权力关系的简化和浅化,明玉妈妈在电视剧中变成了十足的恶人,苏大强变成了十足的“作精”,苏明玉变成了拯救一切的圣母型人物,原小说中纠葛的性别权力关系变成了善与恶的交锋。也许是非分明,却又无关痛痒。“神话从不否认事物的存在,恰恰相反,其功能就在于谈论事物、‘净化’事物,将事物装扮成无辜的样子,使事物具有永恒的先天性与合法性——神话从不对事物进行解释,而是直接将事物陈述为事实……它使世界变得毫无深度,进而也就消弭了冲突,它让整个世界显得开放而明晰,并通过此种方式营造出一种确切无误的幸福之感。”[5]149原小说里的“都挺好”其实是明玉对家人不无疏离的情感态度的一种略带反讽的表达,这种反讽确立了她个人生活和所谓的道德楷模的界限,而到了电视剧中却完全失掉了那一点点反讽的意味,变成了煽情而又俗套的道德故事。电视剧结尾,得了老年痴呆症的苏大强惦记的是去买当年小明玉念念不忘的练习本,明玉和观众一起无比感动,明玉重回老家,依稀回忆起童年受委屈时,母亲曾经抱着她哄的经历,所有的伤痛都一笔勾销,化为感动的泪水。但是,感动之余很多观众并不买账,认为这种强行洗白的操作并不会在生活中发生,从而感慨“生活是生活,电视剧是电视剧”,不满之情溢于言表。电视剧改编通常会考虑观众的口碑和收视率,独立女性苏明玉变成了圣母型人物刘慧芳,但是从观众反应来看,老旧的让女性充当拯救者的性别秩序想象并不能弥合现实生活的伤痛。或许这也是近几年女性题材国产电视剧虽多,但是精品稀缺的深层次原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人际关系、情感关系变化在女性题材的电视剧中最易于得到呈现,这是火爆的原因,但是过去那种凭借煽情而胜出的逻辑慢慢失效。观众不满的评论表达了对如何使人更像一个人的深层次诉求,这种诉求不是凭借旧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就可以满足的。这应该是女性小说创作和电视剧改编应该仔细思考和具体回应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