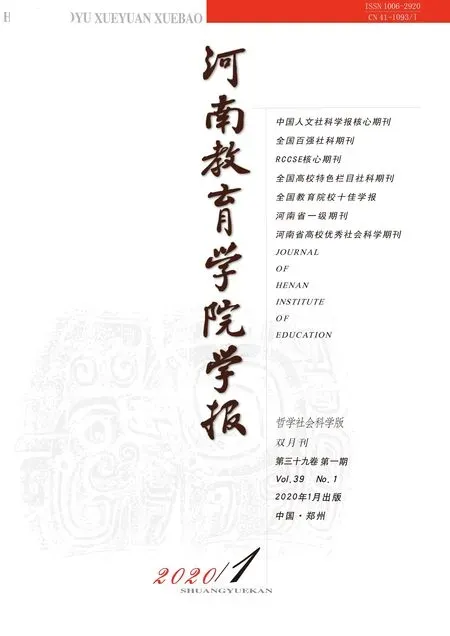传统村落的遗产价值与遗产特性研究
2020-01-19常玉荣严淑华
常玉荣 严淑华
古村落是保存传统文化存留物的最后的自然空间,但是它在现代化进程中正在遭遇被淘汰的危机。村落惊人的消失速度,使普通人都感觉到了家园丧失后的无根感。保护的迫切性让传统村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2年,国家正式启动对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并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2年、2013年、2014年、2016年和2019年,我国先后五批认定了6 799个传统村落,目前基本完成了调查建档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分类中并没有“传统村落”一类,它是我国自己确立的一个类别。冯骥才说,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国家搞举国体制的村落保护工作,我们的思想理论全部要创造。[1]他首次提出将传统村落看作第三种遗产的观点。所谓第三种遗产,是相对于已经建立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而言的。在这两大保护体系的基础上,我国又建立了传统村落遗产保护体系,形成了三大遗产保护体系。[2]
将传统村落看作第三种遗产,相关理论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什么样的村落可以称为传统村落?传统村落具备何种价值使其可以成为遗产?其遗产特性是什么?这是进行传统村落遗产保护工作的最基本的问题。上述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传统村落保护对象、保护价值、保护理念和保护方式等一系列保护工作的方向和具体措施。
一、传统村落遗产的概念及其内涵要素分析
传统村落这一概念是在名录建立之后形成的概念,之前被称为“古村落”。2012年9月,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以突出其文明价值及传承意义。因此,传统村落是一个将古村落视作遗产进行保护的过程中提出的概念,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村落概念。住建部等四部委《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指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3]
历史形成较早,村庄传统文化资源丰富,至今保存较好或基本完整的村落,从时间、资源、价值和空间四个方面界定了传统村落的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这样的村落已经很少,而且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如今,已纳入城区的城中村落所存无几,城郊地段村落的消亡速度也在加快,在传统农业区域和山区丘陵地带,以及交通不甚发达地区,传统村落也有强烈的消亡或变异趋势。
时间上要求“形成较早”又保留至今,这就强调了村落必须具备较长的历史存在时段。但是这一概念并未限定确切的时间。笔者认为,传统村落承载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文化信息,将其时间下限定为清代以前较为适宜。
“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是从文化资源上的界定。具体而言,文件提到了传统建筑风貌完整、选址和格局的传统特色和非遗的活态传承三个方面。传统建筑风貌完整,需要“集中连片分布或总量超过村庄建筑总量的1/3,较完整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3]。这一规定缺乏具体内容指向,仅仅强调了空间分布和数量的多少,而对建筑的类型、时代跨度以及空间分布的形态、传统风貌的内涵以及历史断面或节点的衔接等,没有具体要求。具体到传统村落的建筑,传统民居、院落、寺庙、祠堂、寨墙关塞、街道、广场等公共建筑和空间是必备要素,山水环境、寨墙关塞等也往往与风貌有关,它们构成了中国传统村落的基本架构,也是其文化理念的基本表现。
“选址和格局的传统特色”,文件规定“村落选址具有传统特色和地方代表性,利用自然环境条件,与维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反映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村落格局鲜明体现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鲜明体现有代表性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且村落整体格局保存良好”[3]。村落选址涉及山脉河流、交通地理、田地农园等自然空间的风貌完整性。
遗产价值方面,非物质文化资源种类繁多,单国家规定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包括6个方面。具体到每个传统村落,6个方面的价值会有所侧重,但要兼顾村落的综合价值。空间上,定义村落遗产空间和身份属性的,是村落而不是城镇,也不是历史街区。
在这一概念中,传统村落最难界定的恐怕要数传统资源。有人认为,传统村落保护更加强调历史和文化两方面。传统村落也被称为历史文化村落,具体包括古建筑村落、自然生态村落和民俗风情村落三类。[4]上述所列的各类传统资源概括起来就是传统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简单,简单的划分并不能涵盖村落丰富的文化资源。村落作为人居环境,其传统资源是由人来创造和传承的,村落居民所创造出的村落遗产不仅仅是上述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简单相加,其本身的内容要丰富得多。例如,由家族和村民群体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秩序、伦理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家族承续、名人名事等同样是看不见的文化遗产。门前的老树、街口聊天吃饭常坐的石头,虽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却具有家园情感价值,也是村落遗产的组成部分。因此,传统村落具备非常丰富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之外的文化资源。对于这一部分内容,应该对其丰富完善,而不是将其看作无足轻重的东西。
二、传统村落的价值如何被凸显
村落的价值是在文物建筑和非物质文化保护过程中逐渐凸显的。换言之,村落是因其环境和生存空间而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的。
人类对于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保护经历了一个由物质到非物质,由单体、个体到整体保护的认识过程。西方社会对于遗产保护,最先关注的也是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保护体系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建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提出,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近年,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又专门制定和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发展变化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中国文物(泛指意义上的文物,等同于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发展变化时所指出:“中国文物保护在2000年之后的这种变化,是一种从思想到实践,从观念到操作的跨越式发展,是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是从关注作为历史见证而存在的个体文物,向作为整体的文化和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传承、弘扬的转变。”[5]
《文物保护暂行条例》(1962)强调古迹遗址和文物建筑本身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2003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3、2016、2017年曾进行修订)中规定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是指对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对古迹遗址和文物建筑周边环境的保护的强调,是基于对物质遗产单体保护的需要,对周边环境的要求,严格来说并不能称之为整体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等概念的提出,则是对建筑古迹遗址整体风貌保存的尝试。在名城、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概念所划定的空间范围内,真实地反映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建筑风貌及其相关的非物质文化,是中国基于自身建筑文化特性逐渐建立起的整体保护观。但是建立在文物保护基础上的整体保护,还停留在较为浅层次和机械理解的层面上,这是因为所谓的“整体”首先看重的是空间的整体,强调的是受保护文化建筑与周边环境的统一。其次,在文化观上,所谓的整体是建立在物质与非物质的两分基础上的,并且试图将两者统一起来,但是这种统一是机械的,在真正的保护中很难实现。这并不仅仅因为两者的保护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更重要的是没有找到将两者统一到一起的空间和媒介。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涉及另一个十分流行的词,即活态保护。何为活态保护?这一问题的提出源于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发现,不论是物质遗产,还是非物质遗产,如果离开生活,脱离产生、滋养它的环境和人,就会成为“死的遗产”。人们逐渐认识到,非物质遗产离开生活,离开人,进入博物馆,将会成为死的历史存留物。如果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功能,文化所应具有的功能也会丧失,文化也最终失去存在的意义。
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工作中,人们渐渐认识到整体保护和活态保护是实现保护初衷,传承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创新民族文化的重要的价值原则。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统村落走进人们的视野。或者说,在遗产保护发展的十几年中,村落在实现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整体和活态保护中的价值和功用越来越重要。村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国家从2006年开始审批“非遗”,到现在已经审批了三批,国家一级项目共1 291项,它们绝大部分都保留在村落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要求,非遗必须“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传统村落作为孕育农业文明,产生、存留文化遗产的自然空间的价值被凸显。如果还把村落看成物质的(尤其是建筑的)和非物质的简单集合,看成对各类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进行整体和活态保护的自然和人文空间,显然不能很好地保护这种珍贵的遗产。如果是这样的话,村落充其量不过是某种遗产存在的必要条件,并不能成为独立的,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的第三种遗产形式。村落遗产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只有将其看作第三种遗产,研究其遗产价值和遗产特性,才能真正将这种遗产保护好。不应将村落遗产简单看作乡土建筑群及其附属建筑的非物质文化,又照搬之前的文物的,尤其是单纯的建筑保护的理念和方法。
三、传统村落的遗产价值
传统村落作为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价值,概括地说,有历史价值,它是传统社会较长历史发展的物质见证;有科学和艺术价值,传统村落所保存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体现了传统社会的技艺、工艺和艺术水平等多方面的智慧。区别于狭义的文物,传统村落遗产的价值不仅仅是上述价值。作为文化遗产,传统村落具有更多的遗产价值,即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从某种意义上看,传统村落遗产最珍贵和独特的是它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单就建筑物而言,传统村落所保有的乡土建筑,其历史或者科学艺术价值并不是非常重要。当然,某地区典型民居代表村落另当别论,如福建永定初溪土楼古村落、徽州地区宏村等传统村落。对于大多数传统村落而言,乡土建筑,庭园、庙宇、祠堂等更为重要的是其文化和社会价值。基于这样的价值认识,我们就会发现传统村落的不可替代性,发现其作为第三种遗产的必要性。
(一)传统村落本身就是农业文明和文化的产物
“村落是由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在族群部落的基础模式上,进而因‘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需求而建造的、具有相当规模、相对稳定的基本社会单元。”[6]在这样一个聚族而居的、由人构成的社会单元中,必然会产生基于农业文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各类文化,包括建筑的、民俗的、物质的、精神信仰的、社会组织结构的、伦理价值的、家族的、家国民族的等不同维度的文化产物。如果说哪种方式能够生动具象保留和体现中国百姓千百年来的日常生活及其文化内涵特征,那就是村落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基于各种科学技术和哲学艺术精神建造的物质环境——村落格局、民居、祠堂、书院、庙宇、小桥、水井;也可以看到村民处理人和自然或人与人关系的各种行为准则、节日庆典、祭祀礼仪;还可以感受到依然流淌在乡风民俗中的仁义忠孝。
河北涉县国家级传统村落王金庄拥有的旱作梯田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文化遗产,早在1990年就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专家称为“世界一大奇迹”“中国第二长城”,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体现了农民对土地执着的追求和在大自然面前不屈不挠的精神。涉县由此产生了诸多相关的乡村礼仪、风俗习惯、民间文艺及饮食文化等。比如每年数九给辛苦一年的驴过生日,谚语“打一千,骂一万,数九叫驴吃碗面”(驴是当地重要的农业生产畜力来源)就是最好的证明。
涉县国家级传统村落原曲村,保有宋代建立的涉县洙泗书院。元至正十七年(1357),书院重建正屋三间,由乡贤李世能提供土地,进士牛田、举人牛嘉协助兴建。明永乐年间始,进士牛秦、周晟,举人姚福、姚俊英;解元周冕;监生李时、姚洪等数十人曾在该书院就读。明弘治二年(1489),该院重修。明嘉靖元年(1522),书院殿屋顶俱坠,只留屋基,乡贤秦坤遂建屋五间,后历经多次修葺。至明嘉靖八年(1529)夏秋,因大雨,书院倒塌。嘉靖四十二年(1563),知县李嘉臣重建屋殿,并遴选教谕教授生员。书院修建和不断重修的历史正是民间儒家教化的历史,从中可以感受到千百年来儒家兴教育人、伦理教化的传统。村中秦氏祠堂门前有副对联:“岂徒拜跪趋跄体先志守先规方是敬宗尊祖,不在富贵贫贱做好人行好事乃为孝子贤孙”。河南安阳的马氏庄园,亦有类似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静以修身俭以养性,入则笃行出则友贤”。
传统村落中,传统文化的生活化、具象化的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传统村落的文化功能是单一建筑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保护无法承担的。
(二)传统村落是自足性生命体,具有强大的文化孕育力量
这里所说的村落并非自然空间意义上的村落。村落是自足性生命体,是人的生活空间。群居的人类在建设家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时的思想精神、价值原则、组织结构、具体活动都在这一空间产生并发展。村落一旦形成,就会在全体村民的共同活动中不断产生新的文化。所以,众多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均是在村落中产生并生存的。离开了村落,离开了生活,离开了乡民,任何遗产都将成为死的遗留物。这种强大的文化孕育力量是任何单一遗产都不具备的。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小传统,即是在这样的空间中生成和发展的。大传统的思想和伦理价值在这一空间内寄居并与小传统文化相融合。前者,即各类民间文化。后者如前文提及的乡土建筑的对联。河北武安冶陶镇固义村拥有中国最古老傩戏“捉黄鬼”,每年的正月十五前后,全体村民都要参加傩戏组织和演出。它反映的是村民对于驱邪逐疫、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还有娱乐狂欢的意味以及道德教化的功能。类似这样的民间文化在各个村落中还有很多,是村落百姓基于传统社会日常生活需求而逐渐形成的文化传统。
(三)乡土之情、家园之思
村落中,有价值的不仅是那些承载了较多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本体资源,还有许多上述价值不太明显,但是却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内涵的要素。村落是人居环境,是祖祖辈辈生活的空间,承载了儿时的记忆,年轻时的梦想,家族的荣光,家庭的幸福,奋斗时的昂扬,过日子的安稳等。村落的文化和社会价值由此而凸显。村落是百姓日常生活空间,是家园,是乡土。自家院子里吃饭用的石头桌凳,妈妈做的粗茶淡饭,还有那只一到吃饭就围绕人转的老母鸡,点点滴滴,都是家园记忆,都是生活的记忆,都是思绪依恋和情感偎依,都是时光荏苒和命运感慨。这些事象虽然不具备什么重大的历史或艺术价值,但具有乡土意义和情感价值。这是其他任何一种遗产形式都不能比拟的。目前,村落遗产保护观念虽然已经关注到了遗产所具有的上述文化和社会价值方面,但是在具体操作中仍然认为这些日常生活记忆的承载物不是保护的重点,更多关注的还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存留物。在村落调研中,当地人谈及以前村子生活的情境记忆,都充满了自豪和欢愉。在对涉县固新镇原曲村的调研中,正好遇到涉县妇联主席。她就是本村人,她说,正月元宵节的时候,原曲村要“过十五”,村里会选小孩坐在高高的杆头上表演。小时候,她就非常羡慕坐在上面的小孩,心想自己啥时候能坐上去。村主任回忆小时候村子里还有耍猴的、说书的。时隔几十年,岁月的流逝并未让记忆褪色,反而更加醇厚。人们对于乡土的眷恋岂不是村落遗产在当代最重要、最实用的价值?
四、传统村落的遗产特性
村落遗产,既不同于文物,也与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运河等新类型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区别。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下,村落是作为名镇名村进行保护的。但是名镇名村意义上的村落还是和“传统村落”有所不同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重点保护乡土建筑,兼顾其他,确切地说是保护 “乡土建筑群”,村落的田园农园、河流山脉等资源要素并不在保护之列。所以,名镇名村意义上的村落保护实质是保护村落中的文化遗产,而不是保护村落遗产。现有的文化保护准则也不能完全适用于村落遗产保护。因此,明确传统村落遗产的特性,是进行有效保护的前提。
(一)传统村落遗产是综合性、系统性遗产
传统村落遗产的综合性是指村落遗产中的各类资源类型多样,数量丰富,建筑与环境、人文与自然、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物质与非物质等共生共存。稀缺性、重要性资源与普通资源,名人与普通村民,重大历史事件与日常柴米油盐,后者并非因平凡普通而没有存在意义。村落遗产的系统性是指上述二元对立形式区分的诸多的资源类型形成一个互相交融、依偎的系统,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这里笔者并没有用目前使用较多的“整体性”来说明村落遗产的特性。目前的“整体性”是以建筑为核心的,强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强调村落建筑格局风貌的整体风格的统一,这是建筑学意义上的统一。这种从某一学科角度出发强调的统一必然是单向度的,仅仅看到了村落中的乡土建筑遗产。仅仅把握建筑学意义上的村落显然是不够的,即便是加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过是机械组合,现实层面更不具备将两者统一的可操作性。将村落看作一个整体,不能从某一单一的学科出发,而要从村落和村民发展的角度看村落,此种意义上的村落资源是综合的,存在是系统的,村落是一个有机体。实质上,村落就是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从研究的层面看,如果立足学科立场,社会学、民俗学等人文和社会学科也应参与其中,并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与建筑学一起对村落遗产进行多学科合作保护。
(二)传统村落遗产是“活的遗产”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实施活态保护已经形成基本共识,非遗项目不是死的遗产,而是存在于百姓生活中的活的遗产,即见人见事见生活。非遗离不开的活的源头,就是其产生和赖以生存的村落。回到村落遗产上来,村落遗产本身就是活的遗产。村庄是人的生产生活空间,是由人创造和建立的,其中一切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均是人的创造和传承的结果。一个没有人的村落,必然是一个失去生机活力、最终要衰亡的村落。露天博物馆只不过是针对建筑的单体集群保护,哪里还有村落的影子?村落遗产既是物的遗产,也是人的遗产。村落遗产保护和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的村落空间上。在现阶段最初的保护和关注点可能更多地聚焦于此,但是村落遗产保护和研究更需关注人的方面。村落遗产是以人为中心的遗产,要研究保护村落中的人群及其社会结构、组织、秩序。例如,涉县娲皇宫是全国重要女娲祭祀之地,其存在意义已经超越了村落本身,但是其存在还得依托于区域内村落百姓的信仰。每年民间朝顶祭拜仪式是村民信仰的重要形式,仪式的组织者、参与者就是村中百姓。他们是根据什么样的关系组成仪式队伍,因此而组建的民间机构“社”又在发挥什么作用?村民在祭神过程中形成了什么样的社会交往关系和规则,产生了什么样的民俗?这样的联系下,村落中又产生和形成什么文化存留物?正如前文所提及,村落遗产的各要素,以人为中心形成密切相关的有机体。村落遗产这一活的特性是它所具有的孕育力量的源泉。村落遗产的保护研究应是以人为中心的保护研究。
(三)传统村落遗产具有日常审美性和情感特质
传统村落遗产作为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因其具有的历史性、科学或者艺术特性受到重视,具有与众不同的遗产特性。与重要的历史古迹和文化遗址相比,村落很少承载和见证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更多承载传统农业文明下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读书、种田、娶妻、生子。当然也会与名人和大事发生点关联,例如,村里出个举人就了不得,有个大官就更得纪念一番。这里充满了人间烟火。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百姓而言,这是一个须臾不可离开的空间;即使离开,也是心心念念,最终要叶落归根。所以,村落遗产作为承载了成百上千年生活流的空间,是积淀了一代代一辈辈日常生活记忆的所在。活着的人在这里找到了根,而死去的人在这里获得了归属;老去的人在这里找到了生命的记忆,小孩子在这里发现人生的梦想,享受人生的幸福。在美学意义上,这些本来平淡无奇,甚至有些平庸的日常生活具有了日常的审美性和情感特质。
(四)传统村落遗产是发展中的遗产
谈及村落遗产未来的命运,保守主义者认为随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消失,村落不可避免地也要消失。仅仅把传统村落看成传统文明的遗留物,因为这些遗留物渐渐失去其实用功能退出时代,就由此断定传统村落也必然要消失是片面的。这是静止地看待村落遗产。造成传统村落消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城镇化,城市生活的优越,都导致村落的消亡。但我们不能把拥有深厚文化遗存和记忆的家园彻底抛弃。很多村民并不知道自己村庄的珍贵,不知道其建筑的独特。当他们离开村庄时,村庄的传统也就瓦解了。我们并不否认在诸多因素下造成的目前村落迅速消失的局面,但是不能因此断定所有的村落都会如此。
尽管某些古村落会消失,但是总有古村落要继续存在下去,并且要遵循历史规律,向前发展。村落要在现代社会,带着它积累千百年的传统完成其更新和转型,完成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文化的更新、传统的复兴以及在现代文明中的蜕变,实现传统与现代的逐渐融合。正如之前的村落体现了一代文明的记忆一样,村落也必然要在新的时代完成其蜕变。村里的庙会依然存在,神灵信仰依然存在,但是人们拜神的目的,许下的愿望不一样了。庙会仍然在发挥它的信仰、商贸、社会交往的功能。除此之外,庙会还成为百姓确认自身文化的视角,外来的游客、学者、专家把庙会当作一种有价值的文化进行记录和研究,百姓也从“外人”的眼光中确认自己文化身份和个性。在走访的诸多村落中,庙会、正月社火绝大多数仍在继续。每年正月,村里还是要闹社火,虽然规模不如从前,但人们渴望狂欢、释放激情的需求没有变。传统在保持着并悄悄改变着,有活力地存在着。
传统村落遗产既然是发展的遗产,就意味着村落必须在农业生产方式上完成转型,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村落中的村民唯有继续以农业为谋生手段,方可以真正留在村落中生活,由此继续保持与之相应的更多的传统生活方式,并经过现代文明的改造。有了稳定的农业谋生方式,满足了其追求现代生活的需求,村落才能继续存在下去,村落遗产才能因人的存在而得以保留和传承。质言之,传统村落遗产不能仅作为历史某一时段的凝固物,而是要寻找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发展下去。当然,也有人主张利用村落的文化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可以旅游开发,尤其是那些不太具备发展现代农业条件的村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文化资源促进村落发展,但是村落发展的内生性动力必须源于农业生产方式。如果没有它,田园风光、古朴雅韵、乡规民俗等将不复存在。村落文化不一定非要以能赚钱的实用价值而存在。包罗万象的文化资源,其中有的本身就是生产性的,比如河北邯郸磁州窑技艺、河北蔚县剪纸等,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充分发挥其艺术和经济价值。但很多村落文化资源其产生之初也并非主要用来赚钱,经济价值并不是其主要的或者重要的功能,它们就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实现传统村落发展的正途仍然是寻找村落在现代化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以及更新,使具有悠久历史的村落不断延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