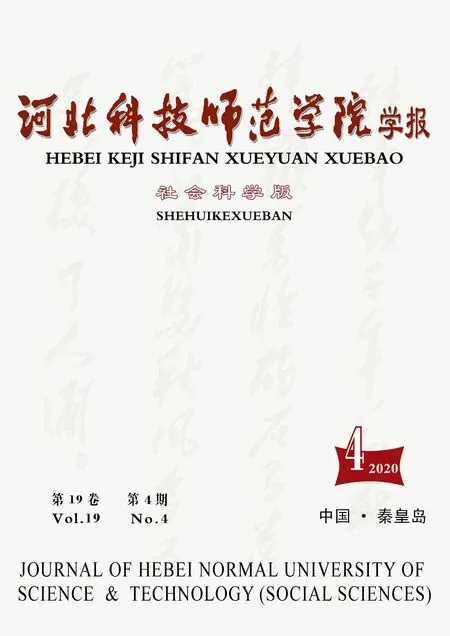王夫之《庄子解》语法观研究*
2020-01-17彭再新
彭再新,周 霞
(1.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2.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说文广义》是王夫之阐释文字的著作,其中有不少关于虚词的表述[1],而王夫之的注疏类著作在考证名物的同时,涉及大量的词法和句法现象,集中体现了王夫之的语法观。《庄子解》是王夫之解庄之作,学界集中研究其哲学与政治思想,无人研究其语法观,故笔者以王夫之《庄子解》为对象,以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中《庄子解》为底本[2],分析其中大量注释,探讨王夫之的语言观。
一、《庄子解》的词类观念
《庄子解》中体现的词类观念的注释主要涉及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语气词等类别。表达观念的方式主要有同训法、义界法、义训下位词、补充说明等多种。
(一)名词观念
《庄子解》中共采用了四种方式表现他的名词观念。
1.同训
同训就是用被训词的同义词去解释这个词,或同义词相释,或今语释古语,或通语解释方言。如:
(1)《徐无鬼》:药也,其实堇也,桔梗也,鸡廱也,豕零也。
《庄子解》:堇,乌头也。鸡廱,芡也。豕零,猪苓也。
(2)《秋水》: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
《庄子解》:练实,竹实也。
按:以上两例皆属于对植物名词的解释,第一例采用同一种药物的另一学名解释词语,表明该词的名词性质,以中药名“乌头”“芡”“猪苓”分别解释“堇”“鸡廱”“豕零”;第二例则采用通语“竹实”即竹子的果实解释“练实”,从而确定“练实”一词的名词性质。
(3)《齐物论》:见卵而求时夜。
《庄子解》:时夜,司夜鸡也。
(4)《齐物论》:螂且甘带。
《庄子解》:螂且,蜈公;带,蛇也。
(5)《庚桑楚》:奔蜂不能化藿蠋。
《庄子解》:奔蜂,小蜂也。藿烛,豆间大青虫也。果赢化螟蛉,化小虫耳,大遂不能化。
(6)《山木》:鸟莫知于鷾鸸。
《庄子解》:鷾鸸,燕子也。
按:以上诸例均属于对动物名词的解释,大都采用“某,某也”的形式,前者为被释词,后者是释词,都为同义词相释,《庄子解》以这种方式将《庄子》中一般人不认识的动物名称解释为人所熟知动物名称,如将“时夜”“螂且”“鷾鸸”分别解释为“司夜鸡”“蜈公”“燕子”,从而确定其名词性质,尤其是例(5)将“奔蜂”解释为“小蜂”,“藿烛”解释为“豆间大青虫”,不仅说明了其名词性质,而且借此解释了“小不可化大”的句意。
再如《庄子解》用“子游名” 释“偃”人名,用 “即蝄蜽”释“罔象”鬼名,用“竹口帚也”释“篲”工具名,用“太公兵法” 释“六弢”书名,用“今谓之响箭”释“嚆”武器名,用“旁门也”释“阿门”建筑物,都是以同义词解释词义,体现名词观念。
2.义界法
义界,即采用下定义的方式来解说词义,用一句话或者几句话来阐明词义的界限。
表植物名词的例子如:
(1)《外物》: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庄子解》:槐者,东方之木,老而生火,谓自生而自贼也。
(2)《人间世》:以为门户则液樠。
《庄子解》:松心木为樠,音瞒。膏液如樠粘人也。
(3)《则阳》:为性萑苇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寻擢吾性。
《庄子解》:蒹葭卽萑苇也。情之始萌,取声色臭味以扶形,而内已拔去性根矣。
(4)《知北游》:果蓏有理,人伦虽难,所以相齿。
《庄子解》:木实曰果,草实日蓏。
按:以上诸例采用义界中的定义法,对该词做出简明扼要的界定。如例(1)确定“槐”为“木类”中“东方之木”,从而判定“槐”为名词,并对其“自生自灭”的特质加以说明。例(2)确定“樠”为“木类”中的松心木,从而判定“樠”为名词,并解释其膏液粘人的特点。例(3)则用同训和义界结合的方式解释“蒹葭”为“萑苇”,并以其“中空外形”的植物特质暗喻“情”,表明其名词性质。例(4)则采用义界法中的比较式,将“果”和“蓏”相近的果实的定义作对比,以确定其名词性质,借此显示两词为“木”“草”的果实的区别。
表动物名词的例子如:
(1)《逍遥游》:蜩舆鷽鸠笑之。
《庄子解》:鷽鸠,小鸟。鷽音学。长尾曰鷽,短尾曰鸠。
(2)《齐物论》:猵狚以为雌。
《庄子解》:猵狚音篇达,似猿而狗头,一名獦牂。
按:例(1)采用义界法中的比较式,先定义鷽、鸠为一种小鸟,确定其名词属性,然后以长尾、短尾表明其概念上的区别,例(2)采用义界法中的比喻式,选用“猿”的形象来代替“猵狚”的形象,既描述了“猵狚”与“猿”的外貌,也揭示了两者同为动物的名词属性,又以“狗头”与“猿”加以区别,从而使“猵狚”作为动物的外貌特点更加突出。
表天象名词的例子如:
(1)《庚桑楚》:我其杓之人邪?
《庄子解》:杓,音标,斗柄第一星,遍指十二方以为标准。
(2)《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庄子解》:野马,天地间气也。尘埃,气也。尘埃,气蓊鬱似尘埃扬也。
(3)《逍遥游》: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
《庄子解》:羊角,风曲上行如羊角然,俗谓之旋涡风。
按:例(1)将“杓”定义为“斗柄第一星”,从而确定其作为星象的名词性质。例(2)则将“野马”定义为“天地间气”,将“尘埃”定义为“蓊鬱之气”,从而确定其气象名词的属性。例(3)则采用同训法和定义式结合的方式,以俗语“旋涡风”释“羊角”,确定其作为风类名词的性质的同时,以定义法描述风似羊角的形状。
表饰物名词的例子如:
(1)《说剑》:曼胡之缨,短后之衣。
《庄子解》:曼胡,粗缨无文理也。
(2)《应帝王》: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
《庄子解》:月题,马辔饰。旧注“马额上当颅如月形,乃的卢也”,非是。
按:例(1)采用义界法中的嵌入式,首先以“曼胡之缨”中的“缨”嵌入义界占据主训词的位置,肯定了“曼胡之缨”作为“缨”这类饰物的名词性质,然后以“无文理”来显示该词的词义特点。例(2)则采用义界法中的排除式,表明了其作为马的配饰的名词属性的同时,又肯定了此配饰为马颈上的器具而非马额头上如月形的配饰。
表音乐名词的例子如:
(1)《达生》:梓庆削木为鐻。
《庄子解》:鐻,音据,乐器。或曰钟鼓之柎也。
(2)《则阳》:以十仞之台,县众间者也?
《庄子解》:间,簨簴也。其乐如登高台奏大乐。
按:例(1)采用定义法,或直接指出“鐻”作为乐器的名词性质,或者以“钟鼓之柎”这种定中短语表明其名词属性。例(2)则采用特指法,将“间”释为“簨簴”,“其乐”更是表明了它是属于具备发音的事物的名词属性,以“如登高台奏大乐”这种特点区别于他物。
以上诸词均采用义界法中定义式、比较式、特指式、比喻式、嵌入式等方式,既解释了被释词的名词属性,又突出了被释词的主要特点。
3.义训下位词
《庄子解》中常通过某些形式标志或其他手段揭示义训词的事物性、行为性、性质状态性、指代性等小类,从而确定其名词性质。如用“属”表示被训释词与训释词代表的事物同类。
(1)《齐物论》:狙公赋茅。
《庄子解》:狙,子余反,又七虑反,猿属。
(2)《胠箧》:惴耎之虫,肖翘之物。
《庄子解》:肖翘,翾飞之属。
按:以上两例均以“属”字表示被释词和释词代表的事物同类,由此便可确定“狙”作为“猿猴”这类动物的名词属性以及“肖翘”作为会飞的昆虫的名词性质。
有用“者”组成“某者”的格式。如:
(1)《庚桑楚》:圣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庄子解》:言仁义礼智信者,圣人也。
(2)《齐物论》: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
《庄子解》:昭氏名文,古善琴者。
(3)《骈拇》: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
《庄子解》:俞儿,古之知味者。
(4)《则阳》:至齐,见辜人焉。
《庄子解》:辜人,有罪而被斩者。
(5)《山木》: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
《庄子解》:林回,即假人之亡者也。
按:以上诸例均采用特殊指示代词“者”组成“某者”的格式来表示人或物,揭示其名词性质,如对“圣人”“昭氏”“俞儿”“辜人”“林回”的解释皆可翻译为“言仁义礼智信”“古善琴”“古之知味”“假人之亡”,加“……的人”的形式,从而判定其名词属性。
采用“名”用以指明被释词的名词性质。如:
(1)《知北游》:大马之捶钩者。
《庄子解》:江东三魏之间,谓锻为锤钩。旧注:剑名。
(2)《逍遥游》:谐之言曰。
《庄子解》:齐谐,书名。
(3)《秋水》:商蚷驰河也。
《庄子解》:蚷音渠商蚷,虫名。
(4)《至乐》:羊奚比乎不箰。
《庄子解》:羊奚,草名,根如芜菁。
按:以上诸例均采用“名”用以指明被释词之类,从而判定其名词性质,如释“捶钩”为“剑名”,并采用同训法指出“江东三魏之间,谓锻为锤钩”,分别释“齐谐”“商蚷”“羊奚”为“书名”“虫名”“草名”。
4.标句读
以此种方式体现的名词观念,如:
《齐物论》: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庄子解》:枢,句。合于道枢,则得环中。
按:此句 “枢”字断句,且随文释义“枢”为“道枢”,可见“枢”为名词。
5.词类比较
主要是对“古今字”“假借字”“通用字”进行比较,并通过分析对比,体现词与词之间的相关词性,并以此方式体现名词观念。如:
(1)《德充符》:四者,天鬻也。
《庄子解》:鬻,古“粥”字。
(2)《人间世》:兽死不择音。
《庄子解》:“音”与“荫”通,林木之荫也。
(3)《秋水》: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
《庄子解》:“虚”同“墟”。
(4)《达生》: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
《庄子解》:“齐”“ 脐”通,水之旋涡如脐也。
按:以上诸例,王夫之分别对“古今字”(鬻和粥、虚和墟)、“假借字”(音和荫、齐和脐)一一对应分析,通过古今字和假借字之间均有意义上的关联,从而从意义的角度说明“鬻和粥”“音和荫”“虚和墟”“齐和脐”均为名词词性。
6.校误文
通过对句中错误的校订,体现词语的名词观念。如:
《天地》:若夫子之言,于帝王之德,犹螳螂之怒臂以当车轶。
《庄子解》:轶一本作辙。
按:用 “一本作”表示“字之误”,指出“轶”为“辙”之误,“轶”处之字应当与“车”构成名词词组,意为“车辙”,从而表明其名词属性。
7.语音分析
语音的变化有时候反映了词性的变化,《庄子解》通过描述语音的变化来体现名词观念。如:
(1)《缮性》: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
《庄子解》:分,去声,得失之数曰分。
(2)《缮性》:是故大知观于远近。
《庄子解》:大知之知,去声。
按:上述两例子,《庄子解》有意运用破读之法区别词义,例(1)用读去声作名词的“分”区别读平声作动词的“分”,故后面用“得失之数曰分”补充说明其名词词性。例(2)则用读 “去声”作名词的“知(智)”区别读平声作动词的“知”。
(二) 动词观念
《庄子解》中涉及动词观念之例,按其表现方式分为以下几类。
1.同训法
第一,采用“某,某也”的形式。如:
(1)《齐物论》: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
《庄子解》:缄,封也。
(2)《齐物论》:麋鹿见之决骤。
《庄子解》:决骤,奔归也。
(3)《人间世》: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
《庄子解》:挤,子礼切,排也,陷也。
(4)《德充符》:且子见执政而不违。
《庄子解》违,避也。
按:例(1)至(4)皆采用“某,某也”的形式,来表现前者释词和后者被释词的同义关系,从而判定“缄”“决骤”“挤”“违”与“封”“决骤”“排”“避”共同具备动词性质。
第二,采用术语“犹”。如:
(1)《人间世》:回之未始得使。
《庄子解》:使犹教也。
(2)《马蹄》:齕草饮水,翘足而陆。
《庄子解》:陆犹陆梁之陆,跳也。
按:二例皆运用术语“犹”表示释词和被释词的同义或近义关系,体现“使”“陆” 的动词性质。
第三,运用术语“曰”。如:
《胠箧》:赢粮而趋之。
《庄子解》:赢音盈,担负曰赢。
《汉志》:“赢三日粮。”
按:运用术语“曰”,并引用《汉志》,说明“赢”表“担负”义的动词性质。
2.功能分析
通过分析动宾或主谓结构来确定词语的动词属性。如:
(1)《齐物论》: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
《庄子解》:枝,柱也。策,杖也。瞽者柱杖,举而击节赏音。
按:王夫之释“枝策”为“柱杖”,“枝”所支配的对象为“杖”,说明他意识到此处为动宾结构,“柱”当为动词。
3.代换法
通过对动宾短语中宾语的替换从而表明动宾结构中的动词性质,如:
(1)《天地》:离坚白,若县寓。
《庄子解》:离,剖析之也。
(2)《胠箧》: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
《庄子解》:攦,折之也。
按:以上两例均用代词“之”去代替“离”“攦”的支配对象“坚白”“工倕之指”,并分别解释为“剖析”“折”,确定“离”“攦”的动词性质。
4.义界法
以下定义的方式来判定某个词的动词属性,如:
《齐物论》:大仁不仁,大廉不嗛。
《庄子解》:嗛音谦,喉含物也,当吞而不吞。
按:将“嗛”描述“喉含物也,当吞而不吞”的动作,意为“含而不吞”的这个动作,从而确定其动词属性。
5.词类比较
主要是通过通假字判定词语的动词性质。如:
(1)《齐物论》:鸱鸦耆鼠。
《庄子解》:耆,嗜同。
(2)《人间世》:隐将芘其所藾。
《庄子解》:芘、庇通。藾,荫也。郭象曰:“其枝所荫,可以隐芘千乘。”
按:以上二例均采用通假字判定词语词性,表明“耆”“芘”与“嗜”“庇”同为动词,例(2)引郭象言“隐芘千乘”进一步通过支配对象的补充来确定其动词词性。
6.语音分析
《庄子解》以此种方式表示动词观念,如:
(1)《德充符》: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庄子解》:“中地”“不中之“中”,去声。
(2)《德充符》:子产蹵然改容更貌。
《庄子解》:更,平声。
(3)《天地》:非王德者邪?
《庄子解》:王,去声。
(4)《山木》: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
《庄子解》:王,去声。长,上声。王长犹言为王为伯。
按:以上诸例均依据破读原理,有意标明“中”字是读去声的动词,而非平声的名词, 标明“更”字为平声的动词,而非读去声的副词,标明“王”为去声的动词,而非平声的名词。
7.校误文
此类例子如下:
(1)《应帝王》: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
《庄子解》:跬当作毁。
(2)《山木》:舜之将死,眞冷禹曰。
《庄子解》:眞泠字讹。旧说:乃命二字之误。杨慎曰:“眞泠即丁宁。”
按:以上二例采用“当作”“字讹”“某字之误”的校订词语错误的术语,例(1)认为名词“跬”当为动词“毁”,例(2)指出“眞泠”为“乃命二字之误”,再引杨慎之言“眞泠即丁宁”,确定作为动词的性质。
8.标句读
以此种方式体现动词观念,如:
《达生》: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沉有履,灶有髻。”
《庄子解》:有,句。
按:王夫之注释“有”字句读,是为了表明此处“有”为对“有无鬼”的回答,故王夫之此处确定“有”作为表存在义的动词。
(三)形容词观念
1.同训法
《庄子解》中主要采用“某,某也”“某,某意”的训诂方式,通过同义词来解释词语的形容词性质。如:
(1)《知北游》:彷徨乎冯闳。
《庄子解》:冯音凭,盛也。闳,大也。
(2)《天地》:聪明睿知,给数以敏。
《庄子解》:敏,捷也。
按:以上二例均采用同义训释,均借“也”字术语释词,从而证明“冯”“闳”“敏”具有其释词“盛”“大”“捷”相同的形容词词性质。
2.词性揭示
主要用术语“某,某貌”体现形容词观念。如:
(1)《逍遥游》: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庄子解》:绰约,轻秀貌。
(2)《天地》:子贡瞒然慙,俯而不对。
《庄子解》:瞒然,目失神貌。
(3)《齐物论》:为其脗合,置其滑愍。
《庄子解》:滑愍,未定貌。
(4)《应帝王》: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
《庄子解》:徐徐,安舒貌。于于,无知貌。
按:各例均直接运用术语“貌”,表明了王夫之对于“绰约”(轻秀貌)、“瞒然”( 目失神貌)、“滑愍”( 未定貌)、“ 徐徐”(安舒貌)、“于于”(无知貌)形容词性质的认识。
3.词类比较
主要是通过通假字判定词语的动词性质。如:
(1)《达生》: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
《庄子解》:殙与惛同。
(2)《天地》:葂也汒若于夫子之所言矣。
《庄子解》汒同茫。
按:此二例释“殙”与“惛”同,“汒”与“茫”同,说明王夫之意识到了“殙”“殙”二字的形容词属性。
4.语音分析
(1)《大宗师》:与乎其觚而不坚也。
《庄子解》:与,平声,和适貌。
(2)《说剑》:瞋目而语难,王乃说。
《庄子解》:说,音悦。
按:例(1)注“与”为“平声”,意在说明此为形容词,而非读成上声的连词和读成去声的动词。例(2)意在说明“说”是读成“悦”表示“高兴”的形容词。
(四)代词观念
代词是具有指代作用的一类词,在《庄子解》中涉及代词观念的例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词性揭示
主要通过其功能意义的揭示体现其词性。如:
(1)《齐物论》: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庄子解》:天谓之彼。
(2)《山木》: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尽矣,而汝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
《庄子解》:“彼”字,指“吾所以著”者而言。
(3)《缮性》: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
《庄子解》:彼谓轩冕,此谓穷约。
按:例(1)采用“谓之”的术语释“彼”指代“天”为,例(2)用“指……而言” 释“彼”指代“吾所以著”,例(3)用术语“谓”释“彼”谓“轩冕”、“此”为“穷约”,以此表明“彼”“此”的代词属性。
2.词义训释
训释方式多为同义训释,如:
(1)《齐物论》:既使我与若辩矣。
《庄子解》:若,汝也。
(2)《齐物论》: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
《庄子解》:而亦汝也。
(3)《应帝王》: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而固得道欤?
《庄子解》:而,尔也。
按:上述例子释“若”为“汝”、“而”为“汝”、“而”为“尔”,说明王夫之有严格意义的代词观念。
(五)语气词观念
《庄子解》中涉及语气词观念的实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术语运用
《庄子解》常运用“疑词”“助语词”“语词”等传统术语来注释语气词。如:
(1)《天运》:天其运乎?地其处乎?
《庄子解》:乎,疑词。
(2)《大宗师》:而我犹为人猗!
《庄子解》:猗,助语词。
(3)《德充符》:而奚来为轵?
《庄子解》:轵,语词,“只”通。
按:例(1)王夫之直接指出“乎”用作疑词,说明他意识到“乎”位于句末表示疑问语气。例(2)王夫之指出“猗”为助语词,说明王夫之知道“猗”表感叹语气。例(3)王夫之指出“轵”为“语词”,与“只”通,说明王夫之知道此处的“轵”与“只”一样位于句尾,表示疑问语气。
2.校异文
异文指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书记载同一事物而字句互异的现象。这些异文有些是古今字、通假字的关系,但是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由于抄写者和出版者认为词性、意义、作用皆同的字可以互换,所以有些异文的词性和作用是相同的。如:
(1)《骈拇》:天下惑也!
《庄子解》:也,一本作矣。
(2)《天运》: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庄子解》:已,一本作夫。
按:上述二例用异文表明了“也”和“矣”、“已”和“夫”都是语气词。
3.代换法
用词性用法相同的语气词代换表明词性。如:
《齐物论》:果有言耶?
《庄子解》:果有所见而立言乎?
按:上例《齐物论》中的“耶”,《庄子解》用“乎”代替,可见王夫之知道二者皆可以在疑问句里表示疑问语气。
(六)词类活用观念
《庄子解》所关注的词类活用范围主要在于名词和形容词两种。
1.名词活用
《庄子解》主要有名词活用作一般动词、名词活用作状语两种。如:
(1)《刻意》:熊经鸟申。
《庄子解》:熊经如熊攀树,鸟申如鸟之申颈。
(2)《逍遥游》: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
《庄子解》:宿舂粮,谓隔宿舂粮。
(3)《齐物论》:道之人,何由兴乎世?
《庄子解》:道之人,有道之人。
(4)《天运》:孰网维是。
《庄子解》:为网以维系。
按:《庄子解》例(1)以“如熊攀树”“如鸟之申颈”释“熊经”“鸟申”。例(2)“宿”对应“隔宿”,修饰“舂粮”这个动宾短语,可见王夫之意识到了“熊”和“鸟”是名词作状语。例(3)释“道”为“有道”。例(4)释“网”为“为网”, 可见王夫之意识到“道”和“网”为名词活用作一般动词。
2.形容词活用
《庄子解》中的形容词活用主要有意动用法、使动用法,具体实例如下。
(1)《人间世》: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
《庄子解》:平之,抑之使平。
(2)《徐无鬼》:法律之士广治,礼乐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际。
《庄子解》:贵际,以与物交际为贵。
(3)《胠箧》:非所以明天下也。
《庄子解》:明谓明示人。
按:例(1)用“抑之使平”释“平”, 例(2)训“贵”为“以……为贵”, 例(3)训“明”为“明示”,可知王夫之意识到形容词“平”用为使动,“贵”为意动用法,“明”为形容词作一般动词用法。
3.代词作动词
如《天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庄子解》:“谁,知辨谁何。”王夫之在这里把疑问代词“谁”当成了动词注释。
(七)联绵词
郭在贻在《训诂五讲》中说:“所谓连语(又写作謰语,又叫联绵词),是指用两个音节来表示一个整体意义的双音词,换句话说,它是单纯性的双音词。”[3]徐振邦认为:“联绵词是双音节的单纯词,义寄于声,构成联绵词的两个字只用以表音,词义与词形并无关系,因而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用哪两个字来记录同一联绵词往往不同,于是同一联绵词出现了几种形体。”[4]149他还指出了了联绵词具有 “反转组合”[4]142的灵活性以及声韵同一性的特点[4]175。
(1)《应帝王》:七日浑沌死。
《庄子解》:方以智曰“浑沌”一作“混沌”,一作“倱伅”。按:“昆仑”即“浑沦”也,“浑沦”即“浑沌”也。太岁在子曰“困敦”,《淮南子》曰“坤屯”“犐 ”,皆“浑沌”之声义。
(2)《齐物论》:厉与西施,恢恑憰怪。
《庄子解》:恑音诡,憰音谲,与诡谲通,皆变异意。
(3)《庚桑楚》:与物委蛇而同其彼。
《庄子解》:委蛇音逶迤。
(4)《齐物论》:山林之畏隹。
《庄子解》:畏,平声。隹,音崔。与崔嵬通,倒用之。
按:王夫之注意到了例(1)的“浑沌”还可以写成“混沌”“倱伅”“浑沦”即“浑沌”“困敦”“坤屯”“犐 ”。例(2)“恑憰”还可写成“诡谲”。例(3)“委蛇”还可以写成“逶迤”,说明他意识到了联绵词字体多样性的特点。例(4)则注解“畏隹”为“崔嵬”的“倒用”,说明他注意到了联绵词 “反转组合”的灵活性。徐振邦认为:“从王念孙发现联绵词可以倒言,至今学界都将这一现象看作联绵词灵活使用的一个特点。”[4]142其实,这一特点王夫之《庄子解》早就提及。
二、《庄子解》的词组观念
王夫之主要对词组的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动补结构、数量结构、状中结构有所涉及,具体如下。
(一)主谓结构
赵元任指出,“在主谓结构中,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可以是动作者和动作的关系。”[5]45《庄子解》的主谓结构观念主要是从加字分析、语义关系分析以及标句读三个方面体现的。
1.加字分析
在主谓结构的主语和谓语中间加字,以确定其主谓结构性质。如《缮性》:“彼正而蒙己德。”《庄子解》:“彼自正也,而使之蒙己以为德。”王夫之在“彼”和“正”之间加了反身代词“自”,使“彼正”的主谓结构更为清晰。
2.语义关系分析
通过分析词语间的语义关系来判定主谓结构,如:
(1)《齐物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庄子解》:两行,两端皆可行也。
(2)《齐物论》:厉风济,则众窍为虚。
《庄子解》:厉风,猛风也。济,风过也。
按:例(1)王夫之分析“两行”为“两端皆可行也”,说明他认识到“两”为“行”的施事者,“两行”是“施事者与施行动作”的关系。同理,例(2) “厉风济”亦为施事者和施事动作的主谓结构。
(二)动宾结构
《庄子解》中涉及的动宾结构主要为词义诠释,如:
(1)《马蹄》:烧之,剔之。
《庄子解》:烧其毛,如今火印,剔其蹄。
(2)《至乐》:攓蓬而指之曰。
《庄子解》:攓同搴,音牵,取也。取蓬枝而指之。
(3)《田子方》:今也又蕲见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庄子解》:振、拯通,谦言救己之失。
(4)《徐无鬼》:兵革之士乐战,枯槁之士宿名。
《庄子解》:宿,迟留也。不汲汲于时,留身后名。
(5)《人间世》: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与其心。
《庄子解》:容与,徐动之也。言我因察人之情以求动其心。
(6)《人间世》:无迁令,无劝成。
《庄子解》:迁改其辞令,劝人成事。
(7)《骈拇》: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
《庄子解》:窜句游心,点窜文句,游治其心。
(8)《齐物论》: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
《庄子解》:枝,柱也。策,杖也。瞽者柱杖,举而击节。
按:例(1)重点训释动词所支配的对象“之”分别为“毛”“蹄”,意为“之”分别受“烧”和“剔”支配,可见王夫之认识到“烧之”即“烧其毛”,“剔之”即“剔其蹄”,均为“动词+名词”的动宾结构。例(2)至(5)均重点诠释动词,可见王夫之意识到“取”“拯”“宿(迟留)”均为动词,“取”与“蓬”、“拯”与“我”、“ 宿”与“名”分别构成动宾结构关系,皆是“动词+名词”的动宾结构。例(6)至(8)兼释动词和动词所支配的对象,据其分析“令”“句”“心”“策”分别受“迁”“窜”“游”“枝”支配,“迁令”“窜句”“游心”“枝策”皆为“动词+名词”的动宾结构。
(三)动补结构
《庄子解》中涉及的动补结构主要通过加字分析来体现。如:
(1)《达生》: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达生》
《庄子解》:有德于生。
(2)《达生》:使之钩百而反。
《庄子解》:百、陌通。《左传》“曲踊三百。”钩陌者,钩旋于陌上也。
(3)《徐无鬼》:礼乐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祭。
《庄子解》:饰敬于容。
按:以上诸例,“德生”释“有德于生”,“ 钩百”释“钩旋于陌上也”,“敬容”释“饰敬于容”,说明王夫之认识到“生”“陌”“容”分别作“有德”“钩旋”“饰敬”的补充成分,并还意识到此成分是“于”所引出,说明王夫之较为了解动补结构的特点。
(四)数量结构
《庄子解》涉及的王夫之的数量结构观念,如:
(1)《逍遥游》:之二虫又何知?
《庄子解》:二虫谓鹏、蜩也。
(2)《天运》:天有六极、五常。
《庄子解》:天、地、日、月、风、云,各尽其极。
(3)《骈拇》: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
《庄子解》:肝神仁,肺神义,心神礼,肾神智,脾神信。
按:例(1)释“二虫”为“鹏、蜩”,直接点名二虫的内容,例(2)释“六极”为“天、地、日、月、风、云”,例(3)释“五藏”为“肝、肺、心、肾、脾”,可知王夫之意识到“二虫”“六极”“五藏”为“数词+名词”式的数量短语。
三、《庄子解》的句法观
《庄子解》中体现王夫之句法观的主要有被动句、判断句、疑问句三种特殊类型。
(一)被动句
《庄子解》所涉及的被动句在注文中主要通过“为N所V”的形式体现,例如:
(1)《天道》:夫至人有世。
《庄子解》: 世为其所有。
(2)《天地》:方且为绪使。
《庄子解》:为事之所役。
(3)《天地》:方且为物絯。
《庄子解》:絯,公才切,絯束也,为物之所缚。
(4)《达生》:故其灵台一而不桎。
《庄子解》:桎犹牿也。不为物所牿。
按:例(1)“人有世”一句,《庄子解》注为“世为其所有”,“人”为主动者,“世”为被动者做主语,说明王夫之已有被动句观念。例(2)的“为绪使”、例(3)的“为物絯”,《庄子解》注为“为事之所役”“为物之所缚”,说明王夫之注意到了被动句式的标志“为N所V”的形式。例(4)“不桎”注为“不为物所牿”,说明王夫之注意到了无标志的意念被动句。
(二)判断句
《庄子解》中所涉及的判断句观念主要通过解释句意以及类比句式体现。如:
(1)《缮性》:夫德,和也;道,理也。
《庄子解》:和乃德也,理乃道也。
(2)《徐无鬼》:凡成美,恶器也。
《庄子解》:成美者,成事之美,犹工之成物,必资利器,刀斧椎凿,皆恶器也。
(3)《齐物论》: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
《庄子解》:三子之知,句。
按:例(1)“德,和也;道,理也”,“和”是“德”的谓语,“理”是“道”的谓语,而《庄子解》注为“和乃德也,理乃道也”,“德”变成“和”的谓语,“道”变成“理”的谓语,说明王夫之知道它们是判断关系,故加副词“乃”强调。例(2)王夫之于“成美”后加“者”,说明他已认识到“成美”应当作为整体语义的判断对象,“恶器也”,便是其陈述语。例(3)王夫之于“三子之知”后断句,可知他已经意识到该处“三子之知”与“几乎皆其盛者也”之间是表判断的陈述关系。
(三)疑问句
《庄子解》中涉及王夫之疑问句观念主要以“术语运用”和“语音分析”的表现方式来体现。如:
(1)《齐物论》: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
《庄子解》:三句皆诘词。谁亲耶?皆悦耶?有私耶?自问则曰吾,问人则曰汝。
(2)《齐物论》: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庄子解》:四句皆疑词。疑其有真君,非果有也。
(3)《天道》:莫为盗? 莫为杀人?
《庄子解》:莫为,诘而问之词。
(4)《养生主》:天与?其人与?
《庄子解》:二与字平声。
(5)《人间世》:恶用而求有以异?
《庄子解》:恶用之恶,平声。悦贤恶不肖,仁义绳墨之言也。恶用此以求异为耶?
按:以上诸例,例(1)(2)(3),用“诘词”“疑词”“诘而问之词”等术语去解释,说明王夫之疑问句有明确的认识。例(4)对“与”标明语音“平声”,可见他意识到“与”字念平声当通“欤”,“欤”位于句末表示疑问语气,从而判定此句为疑问句。同理,例(5)借读“恶”平声表示“如何、怎么”之意,而且释“恶用而求有以异”为“恶用此以求异为耶”,加了表示疑问语气的“耶”字,从而确定该句为疑问句。
四、《庄子解》《说文广义》与王夫之语言观
王夫之的《说文广义》对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有不少详细而准确的阐释。如《齐物论》:“果有言耶?”《庄子解》释:“果有所见而立言乎?”[6]101用“乎”训释“耶”。《说文广义》则详解为:“邪,从邑。琅邪,地名。借为语词,与‘乎’相近,而缓于‘乎’,盖亦古人方言,借音不借义也。自汉以下,北人俗谚称父为邪,又解散字画,从耳、从邑、造为‘耶’字,流俗更复加父作‘爺’,形声乖陋,上下施行之,乃六书之大蠹,莫可如何者也。”[7]398《说文广义》不仅阐释了“邪”和“耶”的正俗关系,“邪”表示语气词是“借为语词”,还说明了“邪(耶)”和“乎”作用类似而又不全同,所谓“与‘乎’相近,而缓于‘乎’”。再如上文论述代词的时候,《庄子解》释“若,汝也”“而亦汝也”“而,尔也”,简单地说明了“若、汝、而、尔”的意义相当,而《说文广义》在阐释“爾”字时则详解为:“若‘尔汝’之‘尔’,自当作尔,作爾者讹。尔,词之必然也,指其人而定呼之,故称卑贱者曰尔。若云尔、但尔、徒尔、偶尔之类,则‘而已’二字合呼。尔、爾、耳,皆而已切,可以通用。”[7]166不仅说明了“尔、爾、耳”三字“可以通用”,还说明了“尔”字指代的独特性:“指其人而定呼之,故称卑贱者曰尔”,还说明了“尔”作为合音词的用法“若云尔、但尔、徒尔、偶尔之类,则‘而已’二字合呼。”《说文广义》阐释“汝”:“汝,本河南水名,以其流经女儿山,故从女。或借为‘尔汝’字,于义无取。古人‘尔女’但作‘女’,不从水,是也。‘尔女’犹言男女,卑者之通称,音与尔相近,而字借用‘女’。‘女’犹子也,尊之则称子,卑之则称女,不应从水。”[7]186详细地阐述了“汝”和“女”表示第二人称的区别。《说文广义》阐释“而”:“其用为‘尔’‘汝’之称者,则音与‘尔’‘汝’相近,方言清浊不同故随借一字行之。”[7]70此处则阐述了“而、尔、汝”三字用法相同的原因为“方言清浊不同故随借一字行之”。如果说《说文广义》是抽象阐释了一部分语法观,那么《庄子解》的注解就是《说文广义》语法观的具体实践,只不过是《庄子解》中所包含的语法观比《说文广义》更广,当然这是二书性质不同的缘故。但是《说文广义》在阐释“若”字时并没有提到其代词的用法,所以要探究并且全面总结王夫之的语言观,最好的方法是结合《说文广义》和王夫之注疏类著作研究,这样才能有更好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