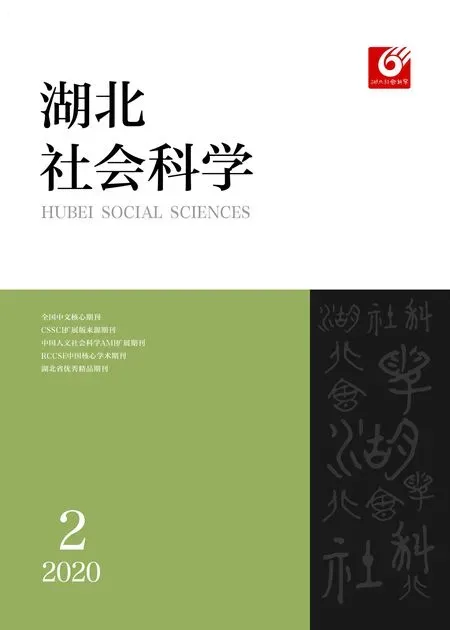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述评
2020-01-16王哲
王 哲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所谓形态,从字面含义来理解即“形式、样态”,是主体对对象存在状态的认知与把握。从认识论角度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通常遵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进路,从对象的直观表象出发,逐渐深入到内核与本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形态研究广泛应用于自然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当然,不同学科中形态研究的基本要求和具体内涵有所差异,但共性之处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外在样态、内部结构及发展规律。也就是说,研究对象的“形态”,既要描述其“看起来像什么”,更要揭示其“究竟是什么”,而对后者的把握就必须揭示对象的系统结构和演变规律。在这方面,通过借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可以为研究提供基本范式与遵循。因此,形态研究实质在于揭示现象和本质间的内在关联,并从根本上阐明对象的存在状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历史中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有其存在的整体面貌和基本规定,然而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形态问题已经进入学者们的视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目前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尚未形成共识,多数是基于现象层面的直观描述,亟待进行由表及里的纵深研究并规范澄清基本概念与内涵。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既要取“他山之石”、借鉴相对较为成熟的教育形态及德育形态相关成果,又要攻“自身之玉”、从描绘外在表象深入到解析内部结构之中。遵循这一思路,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概括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
一、借鉴:教育形态和德育形态研究成果
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教育学特别是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尤为密切。较之于后者,目前学界对教育形态和德育形态的研究相对更为全面和系统,加以借鉴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育形态研究概述。
第一,关于教育形态的含义及理解。大体上有三类,一是将形态理解为由各种教育要素所构成的教育整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表现形式,如褚宏启认为“教育形态是指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存在状态和变化形式”,[1](p5)持同类观点的学者还有罗明东、胡弼成等;二是将形态理解为教育的类型、途径或方式,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多数并未对教育形态概念进行细致考察,通常阐发或列举教育的某一或某些形态;三是借用了形态概念对教育领域个别问题的研究,这类研究中对形态的理解大体与第二类接近,如董云川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不同形态及特点,[2](p74-77)龙宝新介绍了教师教育形态的当代转型路径等。[3](p43-48)第二,教育形态的划分标准。概括而言,多数学者认可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三条:一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是人类的认识能力;三是教育自身的发展,其中每一条又可进一步划分出更为细致的标准,学者们在研究时往往基于这三条主要标准中的一条,区分不同的教育形态。对此有学者认为,单一的划分标准具有较大的片面性,难以深入本质,同时“缺乏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完整形态上来把握教育的发展阶段”,[4](p2-3)因而主张以不同尺度相互交织融合为标准划分教育形态。第三,教育形态的主要分类。大体上有两类,一是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在逻辑上分别从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人与人的关系及社会意识特点、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式等方面展开论述,如罗明东提出的群体社会教育、物化社会教育、自主社会教育,[4](p4-8)胡弼成提出的农牧时代信仰教育、工业时代知识教育、信息时代思维教育等;[5](p15)二是按照教育的不同类型与实现方式,如结构性教育与功能性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等。此外,也有学者将这两类结合起来,提出了横纵交织的立体教育形态:个人—非制度化形态、个人—制度化形态、社会—非制度化形态、社会—制度化形态。[6](p24)第四,关于教育形态研究的独特视角。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傅松涛的形态学视角与比较教育学视角,区分了形态与类型的关系,指出了形态研究的超越性整合特征与基本要求,认为教育形态研究是比较教育学的基本范式,并阐述了该范式的确立依据、历史发展和基本精神(科学化分类、解剖性分析、归纳性概括、类比性迁移)。[7](p62)此外还有褚宏启的现代化视角,论述了教育形态与教育现代化内在关系。[1](p4-10)
(二)德育形态研究概述。
第一,关于德育形态的含义及理解。刘巍在其博士论文中明确对“德育形态”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所谓德育形态,是指在某一特定的人类共同体中的德育现象的存在和表现形式”,[8](p6)包括静态的现实要素和动态的机制运行,以及二者间的内在联系。而多数学者则直接使用这一概念,并未做系统考证,但其理解是不完全相同的,主要有三类:一是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不同时期的德育形态;二是从横向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比了不同国别地区的德育形态;三是动态的实现形式与运行方式的角度,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德育形态。第二,德育形态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三个维度,一是德育自身的发展演进,如檀传宝认为德育在历史上大体经历了习俗性德育、古代学校德育和现代学校德育三种形态。[9](p25)二是基于一定的理论框架,以人的历史发展为标准进行划分,如杨现勇根据人的整体性、个体性、共生性三种存在形态,区分了德育整体主体性、个体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三种形态;[10](p37)而王晓丽则根据历史上经历的依附人格、单主体和生成主体三种人格形态,区分了奴化德育、物本德育、生活德育三种形态。[11](p41)三是基于德育的类型、模式、运行及实现方式的差异进行区分,如檀传宝提出的直接德育、间接德育、隐形课程意义上的德育三种德育现实形态;[12](p4)刘巍在博士论文中详细介绍的中国古代、中国当代、美国当代三种德育形态。[8](p13-93)第三,德育形态的论述角度。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学者们对某一或者某些德育形态的介绍主要从相应的社会历史环境、目标、特征及主要内容、方式方法、运行机制、优缺点评价等方面来进行。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大体上涵盖了德育学原理的主要方面,如果只是从一般意义上泛泛而谈的话,便会显得相对空洞。第四,当代德育发展的一些新兴形态。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德育必然会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新兴形态。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张洪春基于生态伦理学的“本体论承诺”,提出了生态德育形态的概念,并介绍了生态德育的实践视域和价值追求;[13](p28)再如骆郁廷提出的形象德育形态,即“一种依托和运用生动具体的形象开展思想道德教育,从而培育、塑造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社会实践活动”,[14](p20)并指出这一形态的实质在于以形象启迪思想。
综合目前教育学与德育学在形态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第一,研究内容较为接近,主要有对形态含义的理解、形态划分的标准、形态的主要类型等。第二,对形态内涵的认识大体有两个角度,一是历史发展的视角,认为形态是作为整体的教育或德育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呈现或表现;二是分类比较的视角,认为形态是在某一时期教育或德育的不同类型、方式及模式。第三,可以看出,对形态内涵的理解学界目前是存在分歧的,而内涵的界定却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规定着研究方向的确立与研究内容、方法的选取。因此,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且亟待澄清,应当成为今后研究的关键所在。
二、整合:基于字面含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成果
近年来,形态问题已经进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学者的视野中,题目或关键词中出现“形态”的文章不断涌现。然而通过斟酌辩驳可以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数是取其字面含义将“形态”作为一个现成的概念拿来使用,来描绘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要素的种种样态,而缺少对“形态”概念本身的反思和界定。从形态学视角来看,这应当说是必要的,但不够充分并有待深化。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含义。前文已述,总体看学者们多数是在字面含义上直接使用形态一词,即“形式、样态”之意,但各自的角度又有所不同:一种理解认为是思想政治教育或其某一要素的类型、类别及构成。如石书臣、樊浩、刘梅等学者论述的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15](p1)道德教育的精神形态、[16](p44)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形态、[17](p10)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等形态;[18](p53)再如王颖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矛盾形态、[19](p109)熊建生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形态、[20](p58)李锦红等提出了高校隐形思想政治教育的三种形态、[21](p121)石书臣阐述的“双主体—客体”的主客体关系新形态等。[22](p4)第二种理解是从动态的角度认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方式或实现路径。如周琪提出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三种形态:主导式、交往式及网络形态;[23](p233)再如郑富兴阐述了三种道德教育的历史形态:传统社会的社会化—生活化形态、现代社会的国家化—学校化形态、当代社会的媒体化—生活化形态。[24](p4)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许慎认为“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是一种分析视角;[25](p42)樊浩认为道德教育形态是“其存在的现象学表现”。[16](p46)较之于字面含义,这种认识显然更具有理论性。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要素的形态名称及类别。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种种形态。基于对形态概念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划分标准,学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如前文提到的互联网+形态、主导形态、交往形态、社会教育形态、精神形态等等,其中每一种形态又可进一步划为多种形态。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某一要素或方面的种种形态。较之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形态,这一类属于“亚形态”范畴,因而标准更为多元、划分更加繁杂,见仁见智。如熊建生将政治、思想、道德、法治、心理视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五种形态,并论述了彼此间的相互关系;[20](p58)李锦红等区分了高校隐形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制度、精神三种形态;[21](p121)石书臣系统论证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形态等等。[22](p4)最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理解形态。这一类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研究范畴,总体看数量不多,但理论色彩浓厚。如钟启东阐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逻辑。[26](p56)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要素形态的分类标准与论述视角。学者们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相关问题时,不仅提出了各种形态的名称及其划分标准,还会对某一形态或某类形态展开具体的阐述,这样就涉及了论述角度的问题。概括起来,学者们主要从生成基础、背景条件、内涵本质、基本架构、运行特征、建构原则及策略等角度展开论述。如周琪就从这些视角出发,阐述了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形态发展的多重理解;[23](p233-236)刘梅则主要从机制和路径两个角度谈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教育形态的建构策略;[17](p12-13)杨晓慧则借鉴孙绵涛的观点,在区分了学科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活动、组织三形态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这些形态的内涵、地位、特征,结合当下现实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路径;[27](p15-16)石书臣在介绍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时,首先提出了这一形态的概念、内涵,论述了其确立的依据,阐发了这一形态的基本原则即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并从教育功能、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要求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15](p1-5)
第四,名称中含有“形态”的理论或事物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不少文章在题目或关键词中出现了“形态”字眼,虽然这些“形态”的主体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但却与其关系密切。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文章阐述的是一些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等理论。还有一部分学者则关注到了一些事物或现象,其名称中含有形态,且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较为密切。如有学者借鉴传媒学理论,论述了“短形态”这一当下流行的信息资讯表现形式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的策略;也有学者以教师为研究中心,论述了教师在不同道德教育形态中的地位及作用;还有学者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整合问题时,谈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形态的整合问题。[28](p39)
通过梳理这部分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认识:首先,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学者们对“形态”概念的理解繁复多样,缺乏统一共识,对其内涵认识不一,大体上包括要素结构与类型、运行模式及方式两大类。其次,之所以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认识,源于对“形态”概念的理解停留在字面的“现象、表象”,而未能进一步探究“形”和“态”的深层含义。这样,任何可以被人们感知的事物或存在都有其直观的表象,因而“形态”便可以是诸如内容、方法、类别等等的直观反映。最后,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这般现状,反映出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学界目前对于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客观现象本身”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尚未进行明确的区分,以致将以作为人类社会一般现象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元理论湮没在了旨在探究更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应用理论①从这个意义上看,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实际上是以我国当下实际为基本视域、具有很强现实导向性的理论,因而仍属于广义的应用理论的范畴。之中,因此,将包括形态问题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从应用理论中剥离出来,赋予其独立的地位,是十分重要而迫切的。
三、拓深:波及形态问题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成果
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他学科形态学理论中可以发现,对事物形态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描绘现象,更要深入到揭示内部结构及发展规律中。由此,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而言,可以找到一些具有重要意义却是潜在或是被遮蔽的问题域。
(一)思想政治教育起源、演进中的“形态”问题。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研究中的“形态”问题。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时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代表人物是张澍军,认为“原始社会已存有完整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29](p1)李俊奎、王升臻、杨威、孙佩锋、张苗苗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并支持该观点,赵继伟基于对原始社会思想依存和思想共生现象的研究,在区分了社会发生与个体发生的基础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0](p164)二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阶级社会,这种观点可以从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思想政治教育定义中得到依据,代表人物有张耀灿、何祥林、周军虎、余仰涛等,如何祥林明确指出“阶级意识形态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特有的产物”,[31](p6)此外,李合亮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探本——关于其起源及本质的研究》中也持此观点;三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起源于近现代的意识形态政治,代表人物金林南。[32](p29)其二,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根源、缘由。段建斌从人的政治社会化、人类规范性文化传承、人的生成与完善需要三个维度进行了论述;[33](p16)杨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为理论依据,指出劳动、分工、社会意识的产生及分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重要条件,[34](p19-20)李坤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个人与社会需要的张弛发展中。[35](p15)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地为思想政治教育原始发生论提供了依据。其三,思想政治教育起源问题的研究方法。在“原始发生论”与“阶级发生论”两派学者的争论中,也阐述了关于起源的研究方法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区分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事实)发生与逻辑发生、对广义狭义政治概念的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认识论与本体论维度、从后思索与倒叙反思的方法等等。应当说,这些成果对于界定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内涵、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思路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演进即历史分期研究中的“形态”问题。首先,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研究是最为成熟的。就学科归属而言,历史分期是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树荫概括道,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标准主要有三条,一是中共党史与新中国史、二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三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在考察各标准的优缺点基础上,他指出“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分为两大时期、三大阶段和若干小阶段”。[36](p9)与之相比较,中西方古代、近代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研究则相对较为薄弱,多散见于断代史、专题史或比较研究中,缺少宏观线索式的总体性研究。甚至还有部分学者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直接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史,对此有学者评论道(这种研究)“在视野上过于狭窄和封闭”“在内容上侧重于历史经验总结,而未能深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37](p195)其次,一些学者尝试基于更为宏大的历史视角,从总体性的角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及演进规律。如陈炳在其博士论文中以现代性为视域,指出现代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之间的契合性,进而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实践活动,自人类社会中的阶级和国家产生之日起就有了其客观的存在形态”。[38](pI)此外还有学者将视野进一步放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始终相伴随的现象”,[39](p96)并论述了其在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三种存在形态;类似观点还有“思想政治教育应起源于原始社会,经过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到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共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等。[40](p26)应当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层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课题,但目前学界的关注度与研究成果尚且薄弱,应当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重点。最后,还有学者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及分期的研究方法问题,如刘梅阐述的意识形态逻辑主线与“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综合分析框架的建构问题;[37](p193-195)张艳红提出“以意识形态性为其逻辑主线,以时间为纵轴、实践活动为横轴”[41](p173)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分析框架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划分的理论建构无疑提供了思路与启示。
(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范式中的“形态”问题。
就一般意义而言,模式是指“事物或活动中由若干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具有典型特征的简化模型或范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贯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态与实践的纽带与中介”。[42](p315)可以看出,模式与形态的共同点有二:一是体现了事物的内在结构,二是具有类的特征和属性;而二者的区别则在于模式更偏重于操作层面,是思政理论和实践的中介,而形态更偏重于对思政本身的描述,是其现象与本质的统一。由此,一些名称中包含“模式”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也多少涉及了“形态”的问题。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问题的研究,许瑞芳、高国希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指出目前在该领域国内研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主要包括古代儒家教化模式和近代革命时期共产党思政模式;二是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以国别划分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德育或公民教育模式,以类型划则有道德认知、社会学习、体谅、价值澄清等模式;三是当代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主要有主体性、主体间性模式,认识、情感、行为导向模式,网络思政模式等;四是不同模式间的比较研究。[43](p25-30)
而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则是指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或现象的认识、看法或理解,其核心为思维方式。较之于模式,范式与形态的关系相对更远一些,但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范式与形态一样同属于学科基础理论或元问题层面,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具有相似性;二是学界目前认可度较高的两种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社会哲学范式”与“人学范式”,既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又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问题,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都是形态研究所应当重点关注的。
可见,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起源、发展史及类型模式等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重要而潜在的问题域。一则这些领域的研究为形态问题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为进一步进行理论的抽象奠定了基础;二则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在元理论层面进行的,因而为思考形态问题提供了研究思路及方式的借鉴。另一方面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历史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范式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澄明,从而使边界勘定更加清晰明确、避免重复研究。
总结目前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相关成果,可以得到以下四点认识:第一,形态学在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和发展前景,对于推动学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这一领域研究较为薄弱,形态问题应当被加以重视和关注。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应以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为基本遵循和范式,借鉴其他学科形态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教育学和德育学相关成果,注重由表及里展现对象功能结构的纵深剖析以及演进发展中对象存在方式和状态的历史呈现,而不能停留于字面含义进行直观的现象描述;同时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身特点,从元理论的角度加以把握,与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区分开来。第三,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在于界定基本概念和内涵、明晰概念层次与划分标准,从而避免未经反思的泛化使用(取直观表象之意)、层次不明的混合使用(整体形态与要素形态)、以及标准不一的自说自话(历史形态、国别形态、运行形态)等问题,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第四,对于这样一个新课题新领域的研究应持开放态度,允许争议和“试错”,在交流碰撞中博采众长,在探索尝试中廓清方向,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新时代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