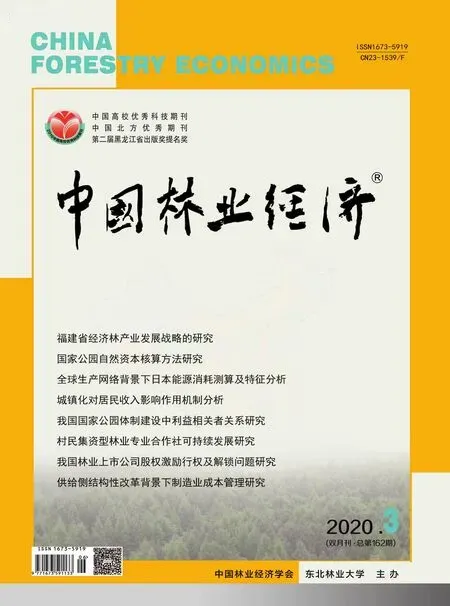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中的利益失衡与均衡
2020-01-14何昊琛李卓垚汪海燕
何昊琛,李卓垚,汪海燕
(1.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210037;2.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武汉430077)
1 问题的提出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是以保护森林生态系统为目的,将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和提供者之间通过费用的支付相连接的制度安排。由于森林生态效益具有效用的不可分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使得有效的市场需求难以形成,市场机制的作用有限,宜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外部经济性的内化,即由森林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向被视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支付合理价格,由政府作为补偿义务主体通过公共财政向森林生态服务的提供者进行补偿。
然而并非所有的林权主体在林业经营方面的投入都应得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当且仅当为公众提供森林生态服务的林权主体所投入的经营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无法通过市场获得有效弥补的场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才成为必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得农户对家庭承包林地拥有了用益物权,但是公益林区划则直接导致农户的产权缺损,将应由政府承担的公益林建设责任转嫁给了农户[1]。现有研究已构建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应遵循的制度路径,但还需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实施环节实现森林生态公益与私益的均衡。
2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逻辑基础:兼顾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
理论上,公益林区划应以保障生态利益为目标且应适用“征收”程序,在管护环节应降低农户经济利益损失,同时在补偿环节有效弥补农户损失[2]。
第一,公益林区划应以保障“生态利益”为首要标准,同时满足农户基本的生计需求。
公益林区划过程中首先应由国家和省级林业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区划界定标准和技术规程进行公益林范围的划定;其次由县级林业行政管理部门与区划范围内的农户充分协商,取得农户同意,按照行政征收程序将特定林地划为公益林,签订管护合同,并以此作为森林生态补偿资金分配的基础。对于“靠山吃山”的农户而言,林地承包经营权可能构成其唯一的财产和收入来源,必须保证其拥有可从事商品性经营的林地达到一定的面积,以满足其基本的生存需求。
第二,政府对公益林的管制措施应满足“最低限度损失”的要求,在确保公众生态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
林木采伐构成农户林业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林木采伐直接影响森林蓄积和森林覆盖率,因而采伐行为成为政府实施的公益林管制措施的核心。理论上,森林资源状况的评价包括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微生物资源和景观资源等多个方面,需要通过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森林灾害面积、树种结构、林分结构、林龄结构及所处区位等多项指标才能估算森林生态功能的可获得性及大小。采伐行为受限必然限制农户经济利益的实现,但并不必然有助于公众生态利益的实现,因此,对采伐行为的限制与禁止并非公益林管制的必要措施。
第三,对公众生态利益的保护与对农户经济利益的限制必须成比例,不能使其中任一方居于绝对的优先地位。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商品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和和林木所有权分到户,市场对林产品需求的增长使得林地价值不断上升,公益林与商品林的收益差距进一步拉大,公益林禁伐使林农承担提供公众所需的森林生态产品的成本,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当对林农进行营林成本、管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的补偿。
3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实施现状: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失衡
2004年财政部正式建立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并与原国家林业局联合出台《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正式将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改称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2007年两部委发布修改后的《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把公益林建设纳入公共财政的框架。
3.1 区划标准的界定与实施倾向于保护生态利益
《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第二条规定:公益林的认定以生态区位极为重要或生态状况极为脆弱为依据。第十四条规定:国家根据生态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科学确定国家级公益林的规模和布局。国家级公益林稳定在全国林地总面积的30~40%。由此可知,我国现行公益林区划标准仅考虑地理位置,不考虑树种、林分和林龄结构等因素,对林农经济利益施加限制的同时并不必然有助于保障森林生态功能。
《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区划界定国家级公益林应当兼顾生态保护需要和林权权利人的利益。但关于林权主体权益保护的具体规则在该办法的26 个条文中仅有两处提及:在区划界定过程中,对非国有林,地方政府应当征得林权权利人的同意,并与林权权利人签订管护协议;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保持集中连片的前提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已确权到户的国家级公益林,其林权权利人在与地方政府签订管护协议时可以调出国家级公益林。林权权利人不同意区划为公益林或者主张调出公益林时该如何提出诉求以及如何实现权利救济,缺乏相应法律规定。
3.2 管护措施单一,造成经济利益的不必要损失
目前生态公益林无经营类型的划分,仅划分生态公益林建设类型。《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管理办法》虽然将公益林分为三级,但并没有对不同等级的公益林分别确立有区别的经营管理制度,仅规定了有区别的保护管理制度:一级公益林实行全面禁伐;二级公益林只能进行抚育或更新性质采伐;三级公益林可进行抚育或更新采伐。本文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地方政府为降低公益林管理成本,公益林的管护措施仅限于禁伐和限伐,限伐所需满足的采伐类型要求和程序要求使得农户实际上无法从采伐中获益。
3.3 补偿标准偏低,未能实现对经济利益损失的有效弥补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主要考虑了我国财政的承担能力,仅实现了对公益林管护费的补助,没有对公益林林权所有者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3]。本文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以南方集体林区主要树种杉木的平均出材量和平均市场价格为例:1hm2林地一般出材杉木90m3,每年每亩林地进行商品性经营的收入可达1 680元。农户林地被区划为公益林后,每hm2林地每年仅能获得不足450元补偿,其经济利益损失达千余百元。
4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改进: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均衡
4.1 从公益林区划程序方面实现农户经济利益的保障
国家基于生态保护的目的将家庭承包林地划入公益林范围从而禁止经营性质的采伐,构成对农户的产权限制,应当遵循行政征收程序。按照行政征收程序将特定林权主体的林地划为公益林,签订管护合同[4]。公益林的比例不应超过林权主体所承包林地的一定比例,不能仅基于集中连片的需要而导致某户林地全部或大部分划为公益林,超过一定比例即允许林权主体部分退出或置换。农户之间代代传承的森林资源管护经验也应成为公益林区划的依据之一,保障农户在公益林区划阶段的参与决策权,以保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目的妥当性”的实现。
4.2 根据公益林的生态功能类别实行分级分类管理,降低农户的经济利益损失
生态公益林限制性利用除了生态采伐以外,还考虑适当地补植和套种。在实践中,不是所有的公益林均需采取禁伐措施,不同保护等级的公益林应采取不同类型的公益林管理方式,发挥不同生态功能的公益林应采取不同类型的经营方式,从而赋予农户相应的开展限制性经营活动的权利。对于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林地以及生态极其脆弱、采伐后难以更新的生态林区,实行全面封山,禁止一切性质的采伐[5];对于上述地区以外的公益林区,在确保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可实行限制性采伐,允许进行林下经营[6],提高林地利用率,减少因森林生态功能保护而导致的农户经济利益损失。
4.3 综合多方因素确定补偿标准,满足农户的基本生计需求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确定应综合考虑森林的生态区位、生态状况和质量,结合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兼顾与商品林经营收益的差额和物价指数的变化,形成具有激励功能的补偿标准[7]。
第一,应基于生态功能的判断确定补偿标准:对于实行全面封山,禁止一切性质采伐的公益林,补偿标准应以当地公益林的经营成本和商品林经营收入为依据进行充分补偿;对于上述地区以外的公益林区,允许进行林下经营且已利用森林资源获得经济收入的经营者,可少补偿或不补偿。第二,应根据地理位置、树种和质量的差异,区分公益林的经营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交通不便的山区,商品林经营成本较高,可采用较低的补偿标准;靠近人口密集区的人工生态林经营性利用的价值较大,管护成本较高,可采用较高的补偿标准。
5 政策建议
现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明显将公众的生态利益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农户的经济利益未得到相应的均衡保护,本文认为应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保障农户的经济利益,具体政策建议包括:
首先,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中确立农户的程序性权利。第一,参与决策权[8]。公益林区划过程中应当听取农户的意见,保障农户的林权主体地位并遵循农户的森林管护经验[9]。第二,置换权及退出权。对于因“生态区位极为重要”以及“生态状况极为脆弱”而导致大部分林地被区划为公益林的农户而言,应考虑通过“置换”方式保障农户的经济利益,满足此类农户基本的生存需求。对于一般类型的公益林,则应允许农户“退出”[10]。第三,获得救济权。农户的参与决策权、退出权、置换权、限制性经营权及受偿权受到侵犯时,有权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等方式进行救济。
其次,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中确立农户的实体性权利。第一,限制性经营权。根据公益林的生态功能类别确定农户限制性经营权的具体内容,保障农户获得与公益林类别相适应的经营权。第二,受偿权。在公共财政有限的条件下,应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提升至每年750元~1500元/hm2,以充分、合理的弥补农户的产权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