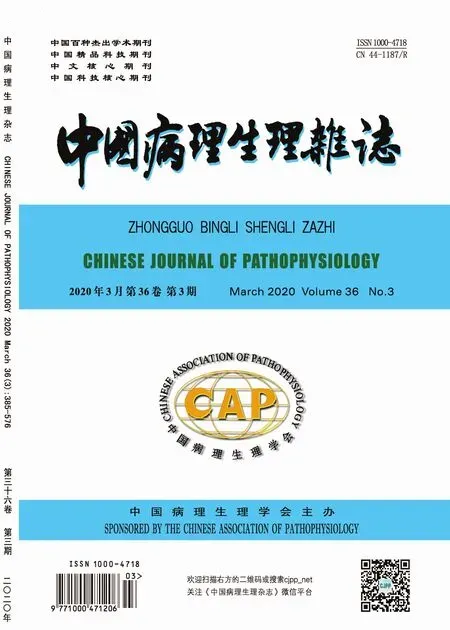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心肌损伤的病理生理机制探讨
2020-01-14陈韵岱李玉珍刘秀华
陈韵岱, 李玉珍, 刘秀华, 周 浩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 2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院研究生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北京 10085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自2019年12月爆发流行以来,截至2020年3月9日,已迅速蔓延至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99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确诊111 044例,累计死亡3 876例[1],成为了全球性的公众健康威胁。肺组织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攻击靶器官,常见的临床症状为发热、干咳、乏力;少数伴有鼻塞、流涕、咽痛等。近期研究发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患者中,16.7%的患者合并心律失常,7.2%的病人出现急性心肌损伤,而10.5%的患者最终死于心血管疾病[2]。因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的心肌损伤值得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明确指出心肌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侵犯的重要脏器,表现为心肌细胞变性、坏死,心肌间质可见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部分血管内皮脱落、内膜炎症及血栓形成[3]。由于本病为新发传染病,其诱发的心肌损伤尚缺乏深入的探讨和基础实验数据支持,本文拟通过分析讨论COVID-19相关心肌损伤的病理生理机制,为重症患者心肌保护治疗提供临床参考。考虑到细胞因子风暴和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表达失衡已经被众多学者报道和分析[4-5],本文主要从新近心肌组织病理结果中的血管炎和低氧血症2个方面进行探讨。
1 血管炎
心脏收缩的能量物质和氧气供应受到冠脉血流的调控。心肌是高耗氧器官,静息状态下冠脉血流中70%的氧气被心肌摄取。因此,在心脏负荷加重、心肌收缩活动增强时,提高单位血液中心肌摄氧能力的潜力较小。此时,更多依靠冠脉及心肌微循环通过舒张血管、增加单位面积下的血流量来满足心脏高负荷条件下对氧气的需求[6]。调节冠状动脉和心肌微循环舒张的主要方式为内皮依赖性的血管舒张活动:内皮通过自身特异性的一氧化氮合酶(nitric oxide synthase, NOS)将左旋精氨酸转化生成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也被称为内皮依赖性舒张因子)[7];随后被平滑肌摄取并作用于钾通道的开放,最终诱发血管平滑肌的舒张。不仅如此,单层内皮构成的心肌末梢微循环中,由于缺乏神经的分布,心肌组织代谢物质的交换更多依赖单个内皮细胞的舒张活动[8]。由此可知,内皮功能受损是冠脉血流储备能力下降和舒张功能失衡的重要标志,而功能失调的冠脉及微血管舒张活动,将会限制心肌在高负荷条件下的血供,引发心肌缺血[7]。同时内皮细胞是血管的第一道屏障,可以感知血液中的各种应激条件的变化(例如缺氧、炎症、高脂等),并通过自身旁分泌功能和形态学变化向心肌传递各种血液中的信息。例如受损的内皮可以通过表达细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1, ICAM1)来吸引炎症细胞[9]。同时,受损的内皮表现为细胞通透性及细胞间屏障结构的破坏,由此加速炎症细胞通过形变来穿透内皮层进入心肌组织中。因此,内皮功能异常可能是心肌炎症的始动信号。最后,内皮细胞是天然的抗凝屏障,其细胞膜上含有肝素、前列腺素等精细调节局部抗凝活动的物质[10]。内皮脱落诱发的内膜下胶原暴露,是局部血栓形成的关键因素。综上所述,冠脉及心肌微血管通过调节血流量来影响心肌能量供应,通过旁分泌和自身形变来扩大心肌炎症反应,通过自身天然抗凝作用决定局部血栓风险的高低。
血管炎是指血管壁及血管周围有炎症细胞浸润,并伴有纤维素沉积、胶原纤维变性、内皮细胞坏死等血管损伤。血管炎从广义上分为原发性血管炎和继发性血管炎。心脏几乎是所有原发性血管炎的靶器官[11]。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3],心脏的病理活检提示心肌血管表现为内皮脱落、内膜炎症和血栓形成,说明SARS-CoV-2感染可能诱发内皮细胞功能下降甚至内皮细胞死亡脱落,同时伴随着内皮及内皮下的炎症细胞浸润,以及机体较高的血栓风险。而上述变化,可以通过影响心肌的血液供应、诱导心肌炎症反应以及增加冠脉血流负荷,导致患者出现急性心肌损伤。在治疗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3]指出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疗需给予循环支持。心肌微血管是决定心肌组织血液灌注量以及血液和心肌组织进行物质交换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由于微血管损伤发生在全身循环衰竭的早期,而心肌微血管障碍会更加隐蔽和难以捕捉,因此早期针对冠脉和心肌微血管的保护可能是减轻心肌损伤的重要策略。
ACE2是SARS-CoV-2的细胞内受体,该受体是SARS-CoV-2感染、入侵机体的关键分子[12]。它在肺、心脏和肾脏中高度表达,主要定位在这些器官的大动脉、小动脉和小静脉内皮细胞上[13-14]。根据近期的尸检结果以及临床经验,我们发现SARS-CoV-2主要受累器官为肺、心脏和肾脏。这3种不同脏器有相似的血管炎病理变化:肺组织内表现为单核、淋巴细胞浸润以及血管内血栓形成;心肌血管表现为内皮脱落、内膜炎和血栓形成;肾脏表现为肾小球毛细血管网的蛋白质渗出和间质的微血栓形成。尽管目前血管中是否有SARS-CoV-2包涵体尚无确切报道,但是基于这3种器官都是血管丰富的组织且在内皮细胞均高度表达ACE2,我们推测SARS-CoV-2可能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诱发“泛血管炎”的病理生理变化。一方面,SARS-CoV-2通过攻击血管(主要是内皮),导致内皮层的脱落和继发血栓形成,破坏内皮依赖的组织血供,导致器官的能量代谢下降或中断,引起血管炎症从而扩大组织的炎症反应。另一方面,SARS-CoV-2刺激全身炎症因子风暴,炎症因子通过启动凋亡途径,诱导内皮细胞损伤、死亡和脱落;同时,炎症因子可以进一步激活内皮细胞,被激活的内皮细胞表达大量黏附分子,后者介导炎症细胞黏附和侵入血管壁或血管周围。上述泛血管炎的理论推测还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和动物及细胞实验中进一步证实和修正。
2 低氧血症诱导的心肌损伤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3]中病理改变显示:心肌细胞可见变性、坏死。SARS-CoV-2感染诱导的低氧血症是引起心肌细胞变性坏死的重要病理生理学基础。氧气作为心肌的能源物质,被用来生成ATP供给心肌细胞的电生理收缩和舒张活动。氧气含量的下降,首先表现为机体的ATP耗竭和能量物质的匮乏。心肌细胞为了满足细胞代谢的需求,通过诱发线粒体自身分裂而在短时间内提高线粒体的数量,从而保障心肌细胞的氧化磷酸化。但是这种异常的线粒体分裂,将会诱发线粒体结构和功能的失衡[15-16],表现为线粒体基因组的不稳定、线粒体膜电位的降低及线粒体依赖的细胞凋亡途径激活,从而导致心肌细胞死亡。不仅如此,难以纠正的低氧血症,将会造成心肌细胞的酸中毒和氧化应激。由于长期的氧含量下降,线粒体有氧糖代谢被阻碍而无氧糖酵解过程将会被加强[17],由此造成了葡萄糖不完全分解并产生大量的乳酸,诱发胞质酸化。同时,由于有氧糖酵解的失衡,还原氢等抗氧化物质无法得到及时的弥补和再循环,由此造成心肌的氧化应激损伤[18]。过度的氧化应激、胞内酸中毒,共同作用于细胞内源性凋亡通路,由此诱发心肌细胞死亡。同时,新型冠状病毒诱导的细胞因子风暴也可以通过提高肿瘤坏死因子α的含量,激活外源性凋亡通路,进一步加重心肌细胞的死亡。上述病理生理学过程可以解释COVID-19患者病理结果中心肌细胞变性坏死的改变。
在临床证据上,COVID-19患者中有16.7%出现心律失常[19],表现为早搏,提示SARS-CoV-2感染可提高心肌的自律性和兴奋性[20]。相较于其他非收缩细胞,心肌细胞膜可通过细胞膜的去极化而诱发细胞膜上离子通道通透性的改变,随后促进心肌细胞内外钙离子、钠离子的快速流动和交换,引发单个心肌细胞的收缩,并通过细胞间连接将这种兴奋收缩进行传导,最终诱发心肌的整体收缩。由于低氧造成的ATP不足,心肌细胞膜的钠钾泵无法正常工作,使得心肌膜电位轻度去极化,由此造成心肌细胞兴奋性的上升和自律性的提高,但传导性却相对下降,这种病理生理学变化将会提高心肌细胞电生理异常的风险。除此之外,心肌细胞收缩和舒张过程,本质上是肌浆网介导的胞浆钙离子振荡。尽管钙离子从肌浆网向胞质中释放是一个顺浓度梯度扩散过程,但舒张期钙离子的回收却是逆浓度梯度,极度依赖胞内ATP水平[21]。由此,低氧介导的能量匮乏,将会显著干扰心肌细胞的舒张功能,造成心肌顺应性的下降,影响静脉血的回流。最后,为了应对低氧血症,机体交感神经的异常兴奋将会提高心肌电生理紊乱的风险[22],交感递质的大量释放也会加重心肌的氧耗和负荷。综上所述,无法纠正的低氧血症,会通过一系列心肌细胞内病理生理学反应,导致交感兴奋介导的心肌氧耗和负荷加重、心肌收缩舒张功能失调、心肌电生理紊乱,以及部分心肌的坏死。
3 总结
尽管新型冠状病毒的靶器官是肺组织,但是急性心肌损伤以及心血管死亡率却是现阶段治疗中未解的难题。众多学者提出ACE2介导的病毒直接攻击心肌以及细胞因子风暴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多脏器损伤的潜在机制。本文依托近期的尸体解剖证据,从心脏冠脉血管炎及低氧血症诱导心肌损伤的角度剖析了临床上可能忽视的病理生理学改变,阐述了COVID-19相关的心肌损伤机制,希望为临床治疗提供潜在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