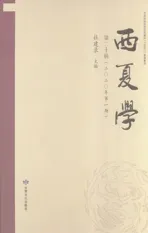合法性的接续:元代昔里钤部家族构建沙陀认同的地方因素
2020-01-14邓文韬刘志月
邓文韬 刘志月
1206—1227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六践夏土,摧毁了立国河西189年的西夏王国。在行将灭国之际,原驻守于沙州与肃州的西夏守将昔里钤部、昔里都水(一作“举立沙”)兄弟先后选择了背离故主,归降蒙古。战后,昔里都水之子阿沙因其父献城未遂惨遭杀害而被给予抚恤,受封肃州路世袭达鲁花赤。昔里钤部则随蒙古西征中亚,立下赫赫军功,又以断事官佐政燕京行台,最终在1251年受贵由汗派遣赴其封地大名路世袭达鲁花赤。诸路总管府达鲁花赤的起仕职级与怯薛世家的入流捷径,为昔里氏子弟的宦途铺平了道路。有元一代,至少22名昔里氏家族成员终仕至三品以上职官。其中,昔里钤部之子爱鲁仕至云南行省右丞,其孙教化甚至以拥立武宗之功升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几乎位极人臣。可见黄金家族之宠幸使昔里氏成为元朝中前期地位显赫的唐兀人家族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记载昔里氏肃州路支系事迹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以下简称《肃州碑》)在甘肃省酒泉市重见天日;1990年与2013年,该家族大名路支系的《李爱鲁墓志》和《小李钤部墓志》又在河北省大名县旧治乡先后出土。新史料的问世吸引了大批学者投身相关研究,使昔里氏家族史成为元代西夏遗裔研究的热点命题①史金波、白滨、汤开建、敖特根、王颋、张沛之、朱建路、邓如萍等专家学者均曾撰文就该家族的族源、世系、居地与家族成员的各种政治军事活动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分别见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汤开建:《〈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Herbert Franke(傅海波):Zur chinesisch-uigurischen Inschrift von 1361,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Vol. 153, No. 1 (2003)。敖特根:《西夏沙州守将昔里铃部》,《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1期;王颋:《元代大名路达鲁花赤唐兀人昔李氏世系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张沛之:《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第三章《元代唐兀昔里氏家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朱建路、刘佳:《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朱建路:《元代〈宣差大名路达鲁花赤小李钤部公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史金波:《河北邯郸大名出土小李钤部公墓志刍议》,《河北学刊》2014年第4期;邓如萍(Ruth. W. Dunnell):《昔里钤部及沙陀后裔的神话:宗谱的忧虑与元代家族史》,《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赵生泉:《〈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考释〉补正》,《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朱建路:《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释补》,《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就以上研究成果,张琰玲作出了全面的学术史梳理,总结了当前关于此命题的研究现状(见张琰玲:《昔李钤部家族研究述论》,《西夏研究》2016年第4期,第34—41页)。。
在国内绝大多数相关研究成果中,昔里氏家族的族属(或谓之“族源”)皆按照碑文的记载被考证为“沙陀贵种”之苗裔。然而,这一论断却存在些许疑点,值得进一步商榷,笔者拟从地方因素对家族集体记忆建构的角度出发,重新解释“沙陀贵种”出现在昔里钤部神道碑中的原因。
一、昔里氏源出“沙陀贵种”的疑点
就昔里氏家族之族属或族源而言,白滨、史金波二位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肃州碑》记载碑主系“唐兀氏”而将其判定为“党项家族”②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第69页。。但汤开建先生旋即撰文指出元代文献中的“唐兀”,并非指“党项”,而是包罗所有不同民族的西夏遗裔所构成的政治体,依据传世文献所收昔里钤部墓志,该家族应为沙陀人③汤开建:《〈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党项西夏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19—422页。。此后,研究者多循汤氏结论,谓“其族属,东迁至河东又回迁河西的沙陀”④王颋:《元代大名路达鲁花赤唐兀人昔李氏世系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5页。或“族源中含有沙陀突厥成分”⑤张沛之:《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第三章《元代唐兀昔里氏家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1页。。作为学术史的梳理者,张琰玲也再次重申了“昔李钤部家族为沙陀人”⑥张琰玲:《昔李钤部家族研究述论》,《西夏研究》2016年第4期,第40页。的结论。
然而,以上研究者所依据的关键史料——“其先系沙陀贵种”,却是仅见于《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铭并序(以下简称“昔里钤部神道碑”)》(成文于1280年⑦按碑文谓爱鲁“今进拜中奉大夫、参知政事、行云南等路中书省”;核查《元史·爱鲁传》,爱鲁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事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是可知碑文撰于此时前后。)与《李爱鲁墓志》(成文于1292年⑧按墓志谓墓主“以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有七日葬之大名县台头里之先茔”,鉴于墓志多随墓主下葬,可知此志文亦当撰于此时前后。)中的两例孤证。
为何称之为孤证?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理解:其一,就墓碑的载体类别而言,“其先系沙陀贵种”仅见于立于昔里钤部陵冢之侧,供世人所瞻仰的神道碑,而不见于随之入葬并深埋地下的墓志铭中。其二,就时代的早晚而言,出现于13世纪末昔里氏家族的两方碑铭中的“沙陀贵种”先世,在14世纪的文献记载中销声匿迹,无论1308年立石的《李爱鲁神道碑》或是程钜夫所撰的《魏国公先世述》,抑或是1347年成文的《野速普花(昔里钤部曾孙)墓志》,甚至是明初官修《元史》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汪古部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元史》本传中清晰的记载该家族“系出沙陀雁门之后”。,都未见类似记载。其三,就家族内的不同宗支而言,被称为“沙陀贵种”后裔的昔里钤部与爱鲁皆为昔里氏家族大名路宗支成员,而世袭肃州路的昔里都水宗支后裔在撰述《肃州碑》时却并未言及他们与沙陀人之间有何关系;与此同时,昔里钤部堂兄束南玉绀部后裔的墓志中也同样不见事关沙陀之叙述。

表1 不同文献中昔里氏家族的先世记载
上述迹象表明,昔里氏源出“沙陀贵种”的传说很有可能只是昔里氏大名路支系在13世纪末所公开声称的世系,而并未被接纳成为整个家族内部不同支系所共同认可的集体记忆。邓如萍(Ruth. W. Dunnell)更进一步将这个族源传说的始作俑者指名道姓的点出,谓沙陀后裔世系的出现和消失“表明那是教化首先做出的虚构。教化很可能是在13世纪70年代中期空想出了其家族与中国北方中亚统治者的联系,这可以美化他的世系,有助于重建其家族在充满权贵争斗的蒙古政治建构中的声誉”②邓如萍(Ruth. W. Dunnell):《昔里钤部及沙陀后裔的神话:宗谱的忧虑与元代家族史》,《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第35页。。
二、“小李”还是“昔里”
为了能使“沙陀贵种”的族源传说看起来更加具有可信度,教化还将家族的族姓也重新作出了解释。该家族之姓氏在元代文献中有“昔里”“昔李”“小李”等多种写法,似乎只是某一少数民族姓氏发音Sire的汉译。但姚燧却依据教化提供的行状和家乘,在爱鲁墓志中写道“康懿之先,七世相夏,同其王李姓,以小大称”①[元]姚燧著,查洪德编校:《牧庵集》卷一九《资德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右丞赠秉忠执德威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魏国公谥忠节李公神道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302页。。言外之意,由于西夏国主自拓跋思恭以后被赐姓为李氏,故同样被唐朝赐姓,但身为西夏臣民的教化先祖不得不将姓氏屈称为“小李”。
教化对族姓的解释,甚至迷惑了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学者,让钱大昕将“昔里氏”注为“小李,讹为昔里”②[清]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廿二史考异》卷九四《元史九》,凤凰出版社,第1546页。,今人更是根据墓志和神道碑中的蛛丝马迹,勾勒出该家族姓氏的来龙去脉:唐末,李国昌(朱邪赤心)部众受吐谷浑人赫连铎偷袭,“被打散而流落在陕陇间,那支‘河西贵种’却迁到了肃州地区……西夏占领河西以后,这支‘李氏’沙陀投降了西夏,并世代为西夏高官”,他们“并非姓‘小李’,而是对西夏王室的一种屈称”,昔里氏之来源乃“‘小李’之讹,‘小李’又源于沙陀李姓”③汤开建:《〈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补释》,《党项西夏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24—425页。。
然而,无论“康懿之先,七世相夏”的高门家世④“康懿”即昔里钤部之父,西夏“必吉”达加沙。据《元史》本传,昔里钤部生卒年为1190—1259,其父达加沙应生活于12世纪后半叶至13世纪前半叶,按20年一代计算,达加沙之七世祖的生活年代应为11世纪中期,约在元昊、谅祚、秉常及乾顺统治前期。然而,元昊以后西夏国相长期为没藏讹庞、梁乙埋、梁乞逋、任得敬等外戚所把持,昔里氏先祖并无染指国相之可能,故所谓“七世相夏”显然是溢美之词。,还是昔里氏因西夏国主姓李而不得不屈称“小李”,都存在着明显的疑点。就后者而言,西夏国主以李姓冠之的记载几乎全部出自辽、宋、金方面,西夏国内文献则多用元昊所改之姓“嵬名”,极少见其自称李氏。又据《金史·交聘表》,西夏赴金使节中凡李姓者有李子美、李元吉、李元贞、李元膺、李公达等23人之多⑤[元]脱脱:《金史》卷六〇、卷六一、卷六二《交聘表》(上、中、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5—1490页。,而未见有屈称姓氏为“小李”者。可见,唐朝所赐之李姓,在西夏国内本就无须避讳,无论昔里氏家族还是其他西夏李姓官宦世家,都没有屈称“小李”的必要。“同其王李姓,以小大称”更像是一种从辽、宋、金的汉文史料出发,根据字面意思对“小李”所进行的解读。更何况出身于这个家族的孛兰奚和野速普花,直到元末至正间也依旧在使用“昔李”作为姓氏,并未改称“李氏”;就连教化自己,在至顺年间成书的《镇江志》中也被纂修者称为“昔里教化的”⑥[元]俞希鲁编纂,杨积庆等点校:《至顺镇江志》卷一九《人才·寓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71、774页。。明朝初年官修《元史·昔里钤部传》中,也称其系“昔里氏”⑦[明]宋濂:《元史》卷一二二《昔里钤部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011页。。由此可见,教化试图将族姓Sire释为“小李”的努力,并未被包括全体家族成员在内的元人所完全接受。
相较于与沙陀贵种的传说,笔者怀疑“昔里”更有可能是某个西夏党项族姓的同音译写。北宋时期,就被有称之为“息利族”①[元]脱脱:《宋史》卷五《太宗纪二》,中华书局,1977年,第76页。或“悉利族”②[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卷三三雍熙二年四月辛丑条,中华书局,2013年,第329页。[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七九《外制集》卷一《悉利族军主嗟移可都军主制》,中华书局,2001年,第1144页。的党项部落生活于陕北地区,其中居住于府州附近的一支宗族归附了当地豪族折氏,成为北宋所管辖的蕃户③汤开建:《五代辽宋时期党项部落的分布》,《党项西夏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7页。,而生活于银夏地区的息利族宗支则随着元昊的称邦建国成了西夏臣民,按照党项人以部族名为姓氏的惯例推测,他们也有可能是元代的昔里氏家族的真正先世。但这一推论是否准确,还有待更多史料的佐证。
从论证视角来看,无论是将昔里氏家族的族属判定为沙陀,还是将其姓氏确认为“李氏”的观点,都倾向于将神道碑与墓志铭中的记载视为真实的史实予以考订④为此,邓如萍批评道:“宣扬杰出的先祖是常见的事情,尽管无法辨其真伪,而令人惊诧的是,学者对此竟一直未加校核,甚至还要设法证实它。”(邓如萍:《昔里钤部及沙陀后裔的神话:宗谱的忧虑与元代家族史》,《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第34页)。,而缺少对神道碑与墓志铭类史料的批判和反思⑤对于元代神道碑与墓志铭的史料价值,陈高华先生以谨慎的态度论述道:“神道碑作者既奉皇帝之命,又受人之币,所依据的是家属认可的行状,当然不免有许多讳饰不实夸大溢美之词。”“死者行状,其中必然充满溢美之词。据行状写成的墓志、墓志铭自然为死者歌功颂德,成为众所周知的惯例。”(参见陈高华:《元代墓碑简论》,《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16、225页),即“在利用它来进行相关研究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对它的编纂者、编纂目的、编纂过程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进行研究,否则我们就不具备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前提”⑥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4—155页。。相较之下,邓如萍是为数不多将昔里氏家族构建沙陀认同动机置于元初历史背景下予以考量的学者:“有些少数民族和汉族移民曾经参与过蒙古帝国的初创,其后代就不厌其烦地爬梳其家族事迹的史料,以求获得乃至扩展他们在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中享有的世袭特权。”⑦邓如萍:《昔里钤部及沙陀后裔的神话:宗谱的忧虑与元代家族史》,《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第30页。如邓氏所说,“维持家族地位”或“拓展世袭特权”固然可以作为昔里教化构建先世的动机,但其建构对象为何是“沙陀贵种”而非其他北方唐宋少数民族(如突厥、回鹘、吐蕃、契丹等)显贵?邓如萍并未给予充分的论述。要回应这一问题,我们更应从地方因素着眼,联系“沙陀贵种”在大名的历史地位予以进一步考察。
三、地方因素与昔里氏先世的构建
关于地方文化资源在宗族建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目前学界已有一定认识。正如刘志伟先生所说,明清族谱中以传记、行状、墓志铭或世系图表等方式出现的历代祖先事迹,“不能只以其所记述事实本身是否足信来评价,而应考虑到有关历代祖先故事的形成和流变过程所包含的历史背景,应该从分析宗族历史的叙述结构入手,把宗族历史的文本放到当地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解释”①刘志伟:《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基于这种研究态度,历史人类学者相继解构了南雄珠玑巷移民徙入珠三角,山西洪洞大槐树徙入北方诸省以及宁化石壁村为客家源流等移民传说,指出历史上各地土著将本地流传的移民传说编入先世叙述,进而实现身份合法化或凝聚宗族力量,最终获得政治经济利益的现象。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昔里钤部家族并非大名路土著,而是由河西迁入的少数民族移民,作为大名路的世袭达鲁花赤,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论证自己统治大名的合法性,得以使他们世代在此获取政治利益。而树立高大的碑石,无疑可以使他们向治下表达政治宣示②“碑与墓志不同,志长埋于地下,不能为时人所见,属于一种相对私密性的个人表述,而规模宏大的神道碑、德政碑则不同,其往往立碑于主墓前或通卫要道之间,为往来行人所目,是一种公开性的政治宣示,具有显著的景观效应……古人素有刊石勒铭、永志不朽的美好希冀,巨型石碑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景观与权力象征,其展示的永久性与纪念性,对于古人的生活世界而言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于无数普通的庶民而言,在其庸碌的一生中可能都从未有机会接触到上层政治,但巨碑作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象征,无疑是庶民了解政治变动的少数管道之一。即使对于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而言,一块巨碑所展示的政治意义都是不难理解的。”(仇鹿鸣:《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余欣主编《存思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论文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8—189页)。正因为墓志与神道碑有着社会功能的差异,教化并未在昔里钤部墓志中加入族出沙陀等先世书写,而仅仅只是在神道碑中进行宣示。。作为迁入大名的第一代,昔里钤部神道碑的碑文书写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个最为直观的例子是神道碑文对昔里钤部赴任大名的年代以及委派者的改写。按《元史·昔里钤部传》记载“丙午,定宗即位,(昔里钤部)进秩大名路达鲁花赤”,其史源当为《李爱鲁神道碑》中的“岁丙午,定宗即位,曰:‘是大名,昔朕分封,卿往为监’”,由是推测,昔里钤部是在“丙午年”,即1246年被贵由派遣到自己的封地大名路担任达鲁花赤的。然而,《昔里钤部神道碑》却记载道“宪宗皇帝奖其旧臣,处内地便之,命锡金虎符,充大名路都达鲁花赤”,将昔里钤部就任大名书写为受蒙哥派遣。显然,这种书写模式受到了蒙古汗权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的影响。在13世纪末元廷面临察合台系与窝阔台系西北诸王叛乱的历史背景下,碑文的书写者试图忘却贵由派遣昔里钤部统治大名的真实历史,而将其统治权力的来源解释为蒙哥的授予。
除了反复宣扬碑主追随黄金家族屡立战功,将统治权力来源解释为元朝皇室,尤其是拖雷系的给赐以外,立碑者教化还试图接续历史上沙陀贵族在大名的影响。按《昔里钤部神道碑》载:“钤部李公其人也。公讳益立山,其先系沙陁贵种,唐亡,子孙散落陕陇间。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复以世故,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河西人。”③[元]王恽著,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卷五一《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铭》,中华书局,2013年,第2377页。碑文中虽未明言先祖之名讳,但所谓李姓之“沙陀贵种”,极易让碑文的读者联想到因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而被“赐国姓并名”且“敕令编籍郑王房”①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一七《朱邪先代》,中华书局,2002年,第317页。的沙陀人李国昌(原名朱邪赤心)一族。
而李国昌后裔染指元代大名路故地,则始于裔孙李存勖夺取魏州(治今大名县东北)。915年,与河东处于敌对中的后梁政权趁原天雄军节度使(即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去世,将天雄军原辖的六州一分为二,“置昭德军于相州,割澶、卫二州”“仍分魏州将士府库之半于相州”;然而“魏兵皆父子相承数百年,族姻盘结,不愿分徙”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贞明元年三月丁卯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8787页。,遂发动兵变,胁迫后梁新任节度使贺德伦款投河东。两月后,李存勖自晋阳至魏州,受贺德伦所上印节,正式兼领天雄军节度使。魏博遂成为沙陀李氏继河东以后所获得的第二镇,也成了李存勖经营河北诸镇的大本营——“晋王为尚书令,置行台于魏州”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一后梁龙德元年正月甲辰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8861页。。
后梁灭亡前夕,李存勖在魏州开展了一系列塑造其正统地位的活动,将其在魏州统治的合法性彻底稳固。首先,编造传国玉玺现世并被沙陀李氏收纳的政治传言。按李存勖最初本欲“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却偶得“魏州开元寺僧传真献国宝,验其文即受命八宝也”。但此玺的来源,史籍只见“黄巢之破长安也,魏州僧传真之师得传国宝,藏之四十年”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一后梁龙德元年正月甲辰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8861页。等寥寥数语。值称帝前夕,失落四十年的玉玺竟现身于李存勖所在的魏州,未免太过于巧合,极可能是沙陀李氏政权自行炮制的,用于论证天命所在的一出戏。其次,将使君与僚属之关系改塑为皇帝与臣子之关系。因亲信宦官张承业的阻挠,李存勖称帝之议最初“诸将宾僚无敢赞成者”;此后,唐朝遗臣苏循被征至魏州,“入衙城见府廨即拜,谓之拜殿。时将吏未行蹈舞礼,及循朝谒,即呼万岁舞抃,泣而称臣”⑤[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六〇《苏楷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812页。,沙陀政权之君臣名分至此始定。再次,祭坛告天,大赦改元。自汉魏以来,禅代称帝者多先在都城南郊祭天而后称帝,沙陀李氏亦然:“晋王筑坛于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坛,祭吿上帝,遂即皇帝位。国号大唐,大赦,改元。”⑥[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同光元年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8881页。最后,建立宫室,定都更号。李存勖称帝后,“宰相豆卢革因进拟为兴圣宫”⑦[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唐同光元年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8883页。,改故魏州牙城为宫城。与此同时,魏州还被改为兴唐府,先后被称为东京、邺都。在后唐时人的奏议中,邺都通常与“三京、诸道州府”并称,足见其地位之特殊。
总而言之,李存勖称帝前后在魏州进行受玺、筑坛、祭天、称帝、建都等政治活动,大大提升了后唐政权在魏州的影响力,使沙陀李氏统治魏州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得到了合乎于传统儒家礼法的解释。
继庄宗即位的后唐明宗起家于魏博戍卒的哗变,自然也极为重视保全沙陀李氏政权在邺都的影响力,故以“邺都士庶驰诚,表章继至,思朕车御暂到”①[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一一四《帝王部·巡幸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246页。,“昨者以全魏名邦,兴唐霸国,当去弊除奸之后,是安民抚众之时”②[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一一四《帝王部·巡幸第三》,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246页。为由,计议亲往邺都巡行,只不过因“军士愁怨,大臣颇以为言”③[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四《郑钰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620页。而最终放弃。即便是后唐灭亡之际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末帝李从珂,亦不忘“朕且幸魏州,徐图兴复”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七九,后唐清泰元年三月甲子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9112页。,足见后唐皇族在魏州根基之深厚。而李从珂计划中东山再起的根基,则当是迁入魏州驻守和定居的大量沙陀士卒⑤李存勖在采取措施维持沙陀人在魏州影响力的同时,还将原在晋阳的沙陀劲旅也带入了魏州驻扎。史载917年8月李存勖“大阅于魏州”,参与阅兵的除幽、沧、刑、洺、易、定等州步骑和奚、契丹、室韦、吐谷浑部落兵外,还有“河东、魏博之兵”。梁将刘鄩围太原时,认为“晋兵尽在魏州”,可推测其调动规模之大。据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后唐与后晋时共17人曾任天雄军节度使,其中9人为沙陀人,3人虽族属不详但同样出身自河东集团 ,这些武将在魏州镇守时,帐下势必有为数不少的沙陀士兵,其余胤也有可能继续留居魏州。,他们的后裔历宋金统治二百余年而及于元。
因此,当元初昔里钤部家族再一次以外来少数民族身份监临魏州故地大名路时,出身西夏且使用“益立山”“玉里止吉住”“达加沙”等典型非汉语人名昔里氏家族无法将先世追认为某个在中国北方具有影响力的汉人世家,却幸而在大名路地方文化资源中找到了曾经在此完成了统治权力合法性建设的沙陀李氏家族。他们便将姓氏“昔里”改写为读音相近的“小李”,又通过神道碑文的叙述将自己描述成了李国昌流寓陕陇间的余胤,李存勖的亲族。于是乎,一个西夏遗裔家族的初来乍到就变成了二百余年前沙陀贵种的卷土重来,沙陀李氏对魏州和大名路的统治权力就这样被合法接续了起来。
可惜的是,教化费尽心机搭建起来的家族谱系并未上升为整个昔里氏家族的集体记忆,而是随着家族地位的逐渐稳固被遗忘。从现有史料来看,直迟于1308年⑥是年教化因拥立武宗而立下大功,“属当代邸之迎,功参平勃,继预汉廷之拜,位次萧曹”([元]程钜夫著,张文淑点校:《程钜夫集》卷二《特进平章政事教化特加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保太尉平章军国重事上柱国封魏国公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6页)而被加封为魏国公。,大名昔里氏家族已不再于各种文献中强调自己“沙陀贵种”的族源,而是更加重视祖先“河西著族”的籍贯和“七世相夏”的政治地位。至于昔里氏为何会出现选择性“失忆”的现象,其原因尚不得而知。
四、余论
虽然教化搭建的沙陀先世谱系最终没有被其后代传续下来,但却为我们理解元代西夏后裔的先世书写展现了一种新的角度。在蒙元大一统的时代格局下,无数唐兀人主动或被动的迁徙至全国各地定居。与文化同质性较高的汉族杂居的分布格局,以及当时民间争相构建远代世系的影响,使得元代唐兀人纷纷从定居地的地方文化资源中去寻找自己前西夏时期(即汉唐以来)的先祖,以获取某种政治经济利益,留下了许多有疑点甚至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先祖传说。①融入除汉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唐兀人,也大致有这样一个自我认同发生变迁的过程:《史集》载“正如现今,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厫部落。如札刺亦儿、塔塔儿、斡亦刺惕、汪古惕、客列亦惕、乃蛮、唐兀惕等,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字,这样一来,他们现今的后裔以为,他们自古以来就同蒙古的名字有关系并被称为蒙古。”([伊朗]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6页),久而久之,这些“自我吹嘘”为蒙古的唐兀人便融入了蒙古族。元代由自灵州迁至西宁的西夏遗裔(该是否为西夏皇族后裔存在争议,但西夏遗民的身份应无太大疑问)李南哥家族及其后裔,亦在明清两代先后构建了西夏皇族和李克用后裔的血缘认同,最终融入了土族。
譬如在西夏尚未灭亡前出使宋朝不返,最终定居无锡的倪氏家族,便将江南梅溪倪氏的先世插入到家族的谱系中,自称“姓倪氏,系出汉御史大夫宽”②[元]虞集著,王颋点校:《虞集全集·道园学古录》卷五〇《倪文光墓碑铭》,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80页。,“倪之先,汉御史宽之裔也”③[元]倪瓒:《清閟阁遗稿》卷十四《元处士云林倪先生墓志铭(周南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5),书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08页。,胡乱攀附的谱系引得后人“阅之喷饭”④“倪云林《清秘阁集》,以世系冠编首,其裔孙所为,阅之喷饭。一世为汉御史大夫宽;二世曰浩,官枢密院使郑国公,四世曰朋,官监察御史拜中书令,六世曰嗣祖,官四镇节度使;八世曰承赞,官参知政事。不知唐宋官名,何以两汉已有之?至二十四世曰思注,乾道进士,盖文节公也。按文节六子,祖义、祖常最贤,乃云二子讹,尤为不经。且文节系南宋人,而谱在三十二世,乃入宋;三十四世允清,庆历四年应举,官至枢密使。时代前后,舛谬颠倒,似一不识字人为之。异哉云林,二百年后,乃有此辱!”([清]独逸窝退士辑,武铭点校:《笑笑录》卷四《云林谱系》,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7页。);由灵州东迁的王翰家族,在离开故土的第四代尚能维持“灵武”的籍贯认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后人亦已改宗太原王氏,对祖先的记忆,也加入了来自南京乌衣巷等叙事⑤《沙堤乡王氏溯源》,王金城、王孝谦主编:《太原王氏沙堤乡志》,1992年,第173页。,与福建当地之“开闽王氏”的族源记忆逐渐趋同;湖北罗田的一支余阙后裔则在家谱中声称:“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封奉化公余天锡,弟兵部尚书天任,及元副使佥都元帅府事余阙皆同宗”⑥[清]管贻葵修,陈锦纂:《(光绪)罗田县志》卷八《杂志·后裔》,第28页。《中国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第2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所收《(光绪)罗田县志》仅七卷,第八卷内容见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数据库所收义川书院藏版《(光绪)罗田县志》,网址链接: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shuzifangzhi/medaDataObjectDisplay?metaData.id=822978&metaData.lId=827459&IdLib=40283415347ed8bd0134833ed5d60004(2017年3月21日查阅)。,并构建了余阙之祖先于宋金之交因兵乱而被掠入西夏的历史记忆,这显然也是为了攀附蕲春义川余氏而编纂出来的;元代晚期权臣伯颜之妻怯烈真氏在追述生母唐兀氏孛罗真的家世时,称其乃“唐贞观贤相之裔”⑦[清]沈涛撰:《常山贞石志》卷二四《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405页。;即便高贵如西夏皇族后裔的李世,也选择了铭记与祖先自称元魏后裔相矛盾的另一套说辞,“惟李氏家陇西成纪者,实秦将信诸孙。汉至六朝,门阀甚峻,惟与崔、卢、郑世姻,不连他族”⑧[元]姚燧著,查洪德编校:《牧庵集》卷一二《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公李公家庙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
无论倪宽、太原王氏、余天锡、“贞观贤相”还是秦将李信,大多都在当时被视为各地汉族土著大姓的先祖。从影响来看,各支内迁西夏遗裔在构建前西夏时期的世系时大量掺入了定居地的文化资源,这种血缘认同取代了元代唐兀人对河西故地的乡土认同,泯灭了他们区别于当地居民的自我意识,最终融入其他民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