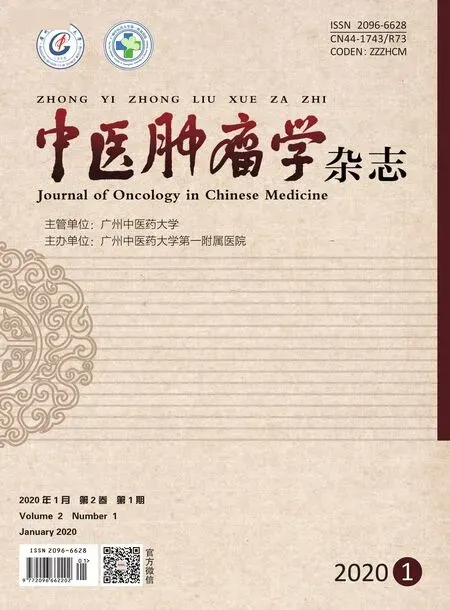浅议癌毒辨识及其论治思路
2020-01-11徐人杰孙大志修丽娟叶敏赵颖刘煊陆烨岳小强
徐人杰, 孙大志, 修丽娟, 叶敏, 赵颖, 刘煊, 陆烨, 岳小强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中医科,上海 200003
恶性肿瘤是严重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的慢性疾病,在世界范围内高发。中医药近些年在参与肿瘤的综合治疗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其理论和疗效优势也在实践中逐步彰显。“癌毒”理论是近年来中医学者基于肿瘤自身生物学特征所提出的重要学术观点[1-2],为指导肿瘤临床指明了方向。但癌毒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辨识它?又该如何论治?目前还鲜有较为系统的论述。笔者不揣鄙陋,略陈管见,望业内行家正之。
1 癌毒辨识
恶性肿瘤的临床特征为起病隐匿、进展快、预后差,虽然近年来其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但主要还是多见于中老年人或先天禀赋不足者(部分肿瘤与遗传等因素密切相关),且具有较明显的地域性和家族聚集倾向。临床除部分血液系统肿瘤外,多可通过切诊或现代影像学技术探及瘤块。肿瘤一般生长迅速,易于发生浸润、播散或转移,随疾病进展出现疼痛、出血、发热等症状,后期因肿瘤消耗更见消瘦、乏力、纳差等正气亏虚表现,甚至出现恶液质后在短期内死亡。正是基于以上临床特点,中医专家根据传统理论推断恶性肿瘤的病因当具有强烈的毒性,并形象地提出了“癌毒”这一针对恶性肿瘤发生学的新概念。更有学者借助现代医学理论将癌毒描述为“已经形成和不断新生的癌细胞或以癌细胞为主体形成的积块”[2],为肿瘤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提供了思路。
1.1 癌毒概念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会发现,癌毒之渐,多无形可循、无症可辨;待其已成,或累累高起如岩,或溃烂流溢脓水,甚或走窜流注如瘤,其形有兼痰、夹瘀、裹水、挟湿之分,其性有寒热之别,病程中各种病理又多相互裹挟,寒热属性也不断发生变化,症状上也是疼痛、发热、出血等随部位而各异,若仅按照中医传统四诊辨识,着实难以切中肯萦,明其因机。笔者认为,癌毒作为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创新概念,必须从中西医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并互参。
现代医学认为,恶性肿瘤(“癌”)本质上是一种基因疾病,其发生主要源于基因的突变,是机体内的基因错配与修复、癌细胞产生与免疫清除等自稳机制失衡的结果,借助中医理论来看,这类似于机体脏腑阴阳的失衡,本质为体内“气”(功能)的平衡失调。在祖国医学中,“毒”作为一种病因概念,尤其自明清学派兴起后广受重视,其本质上强调致病的峻烈性、特异性、复杂性、流窜性、难治性等特征[3],这与现代恶性肿瘤的致病特点高度吻合。两者互参,癌毒当为机体阴阳失衡所产生的一种“异气”[4],其类似于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所论的“杂气”,既“非风、非寒、非暑、非湿”,“无形、无象、无声、无臭”,发病隐匿,致病严重,又具有“一气一毒”,“一气自成一病”,传变转归不同等特点,故因“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5]。但是,吴又可所谓“杂气”,更多特指引发温病的外感性致病因素,从肿瘤发生学来看,癌毒更象一种内源性的致病因子,它是在机体内外致病因素的长期共同作用下,导致机体脏腑功能失衡的结果。其疾病初起发病隐匿,更像一种“伏邪”,却暗耗脏腑气血阴阳,临床只有通过少数特定而敏感的肿瘤标记物可以测知;待其势渐成,就会量增势张,变逆作乱,影响机体脏腑功能,导致气血津液等代谢失常,化生痰湿瘀血等病理产物,此时癌毒与其裹挟,胶结成块,便可有形可征,可手扪而得之,或通过现代影像学检查而见之。
1.2 识癌辨毒
随着“癌毒”概念的提出,我们认为当与时俱进,中西医结合,从识癌与辨毒两方面来认识它,以提高临床论治水平。
1.2.1 识癌
基本思路是借鉴西学,执西参中,包括认识病位、明确病理和了解癌基因表达情况等方面。①结合肿瘤所生部位以明其脏腑病位:原发于不同部位的肿瘤,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如肺癌易兼痰,肠癌易挟湿,肝癌多留瘀,即便是发生远处转移,在特征上也多具有原发部位的某些病理特点。在治疗上通过调整相应脏腑的功能,也有助于对肿瘤的控制;②结合肿瘤病理来分析其病性特点:如非小细胞肺癌从组织病理学分为腺癌和鳞癌两大类,一般而言,结合临床发病表现,鳞癌其性属阳多火(热),腺癌则性属寒多(痰)湿;③根据基因表达情况辨识其异质性与同质性:罹患同一肿瘤患者的基因表达谱差异是其肿瘤异质性的重要内在基础,而不同肿瘤相同癌/抑癌基因的表达异常又成为其同质性的证据。肿瘤分子靶向治疗近来发展迅速,其用药基础则是基于肿瘤的异常基因表达谱,这种针对某一特定基因或通路的靶向药选用策略,已成为中医“异病同治”的新注脚。当然,未来可否将某一或某些肿瘤相关信号通路的异常赋予相应的中医病因病机内涵,目前还任重而道远。
1.2.2 辨毒
基本思路是中西结合,西为中用,包括辨毒力大小、寒热属性和癌毒形质几个方面。①辨毒力大小:既可以借助中医“有诸内必形诸外”的传统理论,从肿瘤生长的速度、发生转移的快慢与多少等来间接判断癌毒毒力的大小,更可借鉴现代检验检测技术,通过肿瘤标记物的动态变化(超过正常值数十、数成百倍或短时间内迅速上升等均是癌毒炽盛的表现)、肿瘤的组织病理类型(如肺癌中小细胞肺癌相对而言毒力更强)及分化程度(未分化或低分化较高分化肿瘤毒力强)等来研判其毒力大小,据此决定选择攻毒药物的品种、剂量以及是否联合手术、放化疗等治疗手段;②辨毒性寒热:多数癌毒生长迅速,暴戾无制,当属实属热。但致病因子偏中人体,常因为治疗用药和患者体质等因素发生兼化,或从阳化热,或从阴化寒;或局部属热,整体属寒。因此临床治疗时,必须虑其寒热、顾其虚实而调之;③辨毒之形质:毒为异气,原本无形,待与痰湿瘀血相合,便有形可征。中医临床论治有形无形相合的兼夹邪气,尤重先祛除有形,则无形之邪无所依附可自解,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在肿瘤临床治疗中,必须重视痰、湿、瘀血等有形之邪的辨识与祛除,并针对性地辅以化痰解毒、利湿解毒、散瘀解毒之法。
2 论治思路
基于上述对“癌毒”理论的认识,其治当中西医有机结合,西学识癌,中医辨毒,中西医并举而论治之。而在中医的论治中,当重点在“毒”,又不离乎“癌”。
2.1 断其根
肿瘤作为一种“伏邪”,常隐匿深伏,根深蒂固,有时即便通过手术也难将其彻底根除。在临床实践中,许多患者更是丧失了手术的机会,难以获得根治,此时我们常遵循“坚者削之”、“留者攻之”的指导思想,用“以毒攻毒”之法治之,使用有毒药物如蟾皮、砒霜、雄黄、天龙、蜈蚣、斑蝥、全蝎等来攻逐癌毒,动摇其根本,促其消散。甚至可将现代医学之放疗、化疗等治癌手段归于“以毒攻毒”大法之中。还有部分患者,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但体内还有少量残存的癌毒(如术前异常的肿瘤标记物在术后仍然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术后病理发现切缘侵犯、脉管癌栓或伴神经侵犯等),可以在扶正祛邪、整体辨证的基础上伍用以毒攻毒药,以求铲灭其根本。
对于以毒攻毒药物的选择,临床可根据癌毒的程度、性质与表现而灵活选用。如根据癌毒轻重将其分为“瘤毒(无法切除的肿块)”、“余毒(肿瘤切除后机体内尚残存少量肿瘤细胞)”两个层次,前者用蟾皮、斑蝥、砒霜等大毒之药攻伐;后者使用小毒药物如生半夏、生南星、蜂房等搜剔清除,使祛邪而不致伤正。对质地坚硬、血供丰富、局部疼痛明显、舌紫脉弦者,选用斑蝥、蜣螂、蜈蚣等活血通络解毒之品;对质地较韧、边缘光滑、伴有肿大淋巴结、胸腹水、脉滑者,选用生半夏、泽漆、甘遂等化痰逐水解毒药物;对伴有脘痞呕恶、便粘尿浊、舌苔厚腻者,选用蟾皮、鸦胆子、拳参等利湿解毒药物;对局部灼热、红肿热痛、或糜烂出血者,选用蟾蜍、蟑螂、守宫等寒性解毒中药;对畏寒肢冷、疮口紫暗不愈、流败絮脓水者,则选用草乌、硵砂、升药等热性解毒之品。至于病邪兼夹,则发挥中医方药调剂之优势,灵活伍用。
同时,根据祖国医学“邪正交争”的发病观,正气亏虚是恶性肿瘤发生的主要内在基础,而肿瘤的生长会进一步损耗正气,正不遏邪又反过来助长了肿瘤的发展,所以正虚邪实贯穿于整个肿瘤的疾病过程。反映在治疗上,中医还可从扶助正气的角度,选用黄芪、当归、女贞子、鹿角等扶正之品配合攻毒之药,以扶正托毒抗癌。
2.2 易其性
癌毒既成,便附着机体,害而为病。在此过程中,癌毒既会随患者机体的阴阳属性发生兼化,又可因临床寒温药物的使用而发生转化,表现出或寒或热,或寒热错杂的状态。
一般而言,处于进展期的恶性肿瘤,由于肿瘤细胞的对数增殖,常使患者呈现全身或局部热象;临床体质较壮的年轻患者,发病后邪气容易从阳化热;或体表、头颈部、食管等偏上、偏外的肿瘤,发病后容易化热,出现如低热、口干、舌红苔黄、尿赤便干等热毒内蕴之象。此类患者临床宜高度重视,因为肿瘤常进展较快,即便接受了手术等根治性治疗,术后也常需要辅以一段时间的中西医结合干预,以清除余毒,巩固疗效。对于此类患者,可使用清热解毒之法,伍以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石见穿、石打穿、蛇莓等药。同时,兼顾肿瘤部位的不同而选用相应药物,如甲状腺癌多用夏枯草、黄药子,鼻咽肿瘤用玄参、山豆根,肺部肿瘤用金荞麦、冬凌草,食管肿瘤用石见穿、八月札;胃癌用蒲公英、白花蛇舌草;肠癌用藤梨根、蛇莓等。
临床上早期肿瘤虽然属热属实者多见,但随着肿瘤进展,由于热毒耗阴伤气,阴损及阳,或患者叠经手术、放化疗等多种有创治疗,损阳耗阴,故肿瘤晚期阳虚或阴阳两虚的患者也不在少数,表现为畏寒肢冷、小便清长、舌淡而胖、脉沉而弱等,或者体表局部肿瘤破溃,疮口紫暗不愈、或流败絮脓水,此时可选用附子、半夏、南星、蜂房等温阳散寒解毒之品。同时兼顾病情虚实,对于偏实者,可用附子、半夏,偏虚者则石龙子、蜂房更宜。若寒热虚实错杂,则又当灵活而伍用之。
2.3 化其形
癌毒进展,必裹挟痰、湿、瘀血等有形之邪,方能结聚成块;而肿瘤形成后留滞局部,更会阻碍气血津液的正常运行,从而加重痰、湿、瘀血的留滞。肿瘤临床以瘀为主者局部常表现为肿块质地坚硬,形状不规则,血供较丰富,疼痛较明显,全身则有面色晦暗、爪甲青紫、舌下络脉怒张、舌紫或有瘀斑等,临床可选用三棱、莪术等以活血化瘀,消散癌毒。上述药物既可解毒攻癌,还能改善局部循环,逆转肿瘤所致的“高”、“粘”、“凝”、“聚”状态,改善肿瘤局部微环境。临床根据证情的不同,对血瘀伴有血虚者多用当归、丹参等养血活血,络滞疼痛较甚者用刺猬皮、九香虫以通络止痛,有出血倾向者用蚤休、三七等活血止血。
“湿”亦为肿瘤病人常见病理因素之一,尤其是消化系统肿瘤、盆腔妇科肿瘤、泌尿系肿瘤等,其肿瘤常多挟湿。盖脾胃为水谷之海,其病则运化失职,水湿内停;女性生殖系统隶属奇经,病后多伴带脉失约,故常下赤带血水;肾主水、膀胱贮存蒸化水液,其病则津化为湿。此类患者常有胸脘痞闷,纳少腹胀,尿少,大便不爽,口秽,苔腻等,此时可主以利湿解毒之法。湿在上则伍以芳化,用藿香、佩兰等辟秽解毒之品;湿滞于中则用苦参、鸦胆子等苦寒燥湿解毒;湿停下焦,则用马鞭草、猫人参等淡渗利湿解毒。
古人很早就提出“百病皆有痰作祟”、“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是痰”,许多表浅肿瘤可扪及肿大的韧性痞块,肺癌、消化道肿瘤、乳腺癌、甲状腺癌等常在疾病早期就会出现沿淋巴道的转移,类似于古代文献记载的“痰核”“瘰疬”。还有脑瘤、间质瘤等癌块形态多规则,质地较韧,或者肿瘤过程中并发胸腹水,这些均属痰饮为患。临床并可从胸脘痞闷、泛吐痰涎、苔腻、脉滑等征象中窥得端倪。对此当以化痰逐饮解毒之法治之,化痰药常用半夏、天南星、浙贝母、牡蛎、海藻、山慈菇、僵蚕等药,饮邪者伍以葶苈子、泽漆、牵牛子、商陆等,痞块明显者再伍以瓦楞子、鳖甲、龟板、牡蛎等化痰软坚散结。
总之,随着临床对肿瘤认识的不断深入,癌毒在恶性肿瘤病机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推动着中西医结合肿瘤防治工作向前发展[6]。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少临床医生简单地以某味中药是否具有抗癌作用的药理来选用药物,摒弃了四气五味、毒性归经等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在现实中影响了整体疗效的发挥,所以识癌与辨毒二者不可偏废。同时,由于肿瘤种类多样、病机复杂,上述针对癌毒的三个方面的治法并非完全独立,在临床上常须根据病机灵活联合使用,甚至配合发汗、通腑等方法驱邪外出,方能发挥出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