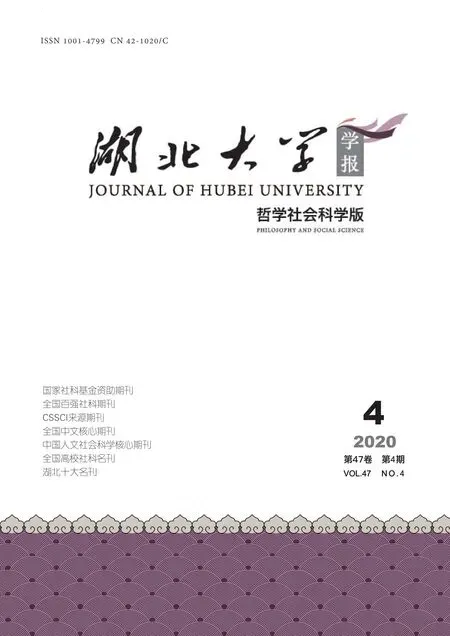风与俗:中国现代作家“地缘文化”表现形态论
2020-01-11陈方竞
赵 冰, 陈方竞
(1.湖北经济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2.汕头大学 文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程千帆先生在为刘师培著《南北文学不同论》所写“案语”中说:
文学中方舆色彩,细析之,犹有先天后天之异。所谓先天者,即班氏(按:班固)之所谓风,而原乎自然地理者也。所谓后天者,即班氏之所谓俗,而原乎人文地理者也。前者为其根本,后者尤多蕃变,盖虽山川风气为其大齐,而政教习俗时有薰染;山川终古若是,而政教与日俱新也。(1)程千帆:《文论十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
程千帆先生的高论深化了我们有关作家与故乡地缘文化关系的认识和思考。我们可以依此作出如下阐释,地缘文化之于作家存在着“先天”与“后天”两种形态:前者即自然地理,它是作家生活的自然环境,包括山川地貌、气候、水文、动植物等,这些都对作家的创作潜在地发生影响,它更具有客观性与稳定性;后者即人文地理,它是作家生活之地的文化形态,包括民风民俗、宗教信仰、语言习惯等等,相较而言,它具有主观性和变异性,是与时代和社会的变迁相联系的,其对创作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作家的自觉汲取与追寻,地缘文化的内涵更是作家通过人性的自我建构表现出来的——前者(“潜在”)与后者(“显在”)相交汇,形成奔突于作家创作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富有张力的文化场,故乡地缘文化因而获得更富有力度的表现。据此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群文学创作中的“地缘文化”,我们发现,周作人与鲁迅论及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缘文化积淀的自觉表现与“流寓”或“侨寓”之地生命体验的故乡地缘文化建构,是作家“地缘文化”表现的两种形态;分属两种不同形态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表现,共同呈现了“地缘文化”的丰富多彩,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别样的画卷。
一
对于故乡地缘文化之于作家的这两种表现形态,周作人与鲁迅曾各有侧重地做过说明。
周作人更多地谈到前者的地缘文化表现。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与此前的文学在整体上根本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地缘文化个性是难以真正发展起来的,这不仅缘于千年古国文化环境的封闭,更直接受制于直至清末的“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专制。对此,他曾说:“道学家与古文家的规律,能够造出一种普遍的思想与文章,但是在普遍之内更没有别的变化,所以便没有艺术的价值了。”(2)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许志英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10页。周作人的这番话,又是针对新文学提出的,即“因为传统的压力太重,以致有非连着小孩一起便不能把盆水倒掉的情形”(3)周作人:《〈旧梦〉》,许志英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第317页。,如“评论家”强调的“文艺的统一”,“凭了社会或人类之名,建立社会文学的正宗,无形中厉行一种统一”,但这是“不应有”的,也是“不可能”的(4)周作人:《文艺的统一》,《自己的园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相同。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要去强迫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实现了,这样文艺作品已经失了他惟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5)周作人:《文艺上的宽容》,《自己的园地》,第9页。,如果由此“因袭下去”,其结果只能是“成为新道学与新古文的流派,于是思想和文艺的停滞就将起头了”(6)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许志英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第310页。。他针对“因反抗国家主义遂并减少乡土色彩”的现象,说:“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讲地方主义,唯独在艺术上常感到这种区别”,“我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假文学,然而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因为“乡土色彩”和“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7)周作人:《〈旧梦〉》,许志英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第316-317页。。1923年他撰写的《地方与文艺》,对此有更进一步的论说:
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这本是不足为奇,而且也是很好的事。我们常说好的文学应是普遍的,但这普遍的只是一个最大的范围,正如算学上的最大公倍数,在这范围之内,尽能容极多的变化,决不是象那不可分的单独数似的不能通融的。这几年来中国新兴文艺渐见发达,各种创作也都有相当的成绩,但我们觉得还有一点不足。为什么呢?这便因为太抽象化了,执着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我们的希望即在于摆脱这些自加的锁枷,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8)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许志英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第308-309页。
作为中国最早提出“乡土文学”,并一生以“提倡乡土文艺为职志”(苏雪林语)的作家,周作人的这一段话中,把他提倡乡土文学的缘由讲得十分明白。在他看来,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强调学习西方的文化大背景下,暴露出了“太抽象化”、“写出预定的概念”、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等问题,而“从土里滋长出来的”有个性的乡土文学似乎正是克服这一“不足”的良方。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提出“地方”、“风土”、“个性”等概念,是建构他的乡土文学理论的关键词汇,而“风土”则又是其中核心的关键词,在其不少文章中被反复提及、强调。如上文中讲“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不同的风格”,强调“我们说到地方,并不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9)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许志英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第310页。。在《〈旧梦〉》中他说,“但觉得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知道的因风土以考察著作,不知道的就著作以推想风土”(10)周作人:《〈旧梦〉》,许志英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第316、317页。。就正是看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缘文化积淀对作家创作的巨大的影响力。这组关键词中,“地方”是源泉,“风土”是核心,“个性”是旨归,由“地方”——“风土”——“个性”,形成了周作人乡土文学的内在的理论逻辑。
所以,周作人认识中的五四文学变革意义,更在于实现了新文学之为“文学”的发展,而要求作家的地缘文化个性从“道学家与古文家”的钳制中解放出来,这是能够充分显现作家创作个性的,是对古代文学与地缘文化关系的一种真正发展,因此,他“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认为“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11)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许志英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第310页。,反映了他对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缘文化积淀的自觉表现的重视。
1923年后的“乡土小说”的出现,显然与周作人这一提倡是分不开的,由此也可见他直接影响的“浙东乡土小说作家群”出现的意义。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缘文化积淀的自觉表现,鲁迅无疑也是重视的,他曾说:“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12)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2页。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也曾讲:“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13)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页。鲁迅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创者,鲁迅之所谓“乡土文学”,又不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文化积淀的自觉表现,像他说过的法国19世纪流亡国外的贵族作家的怀乡之作,更是通过“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1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7页。。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中国作家“被故乡所放逐”,“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流寓”或“侨寓”成为他们更主要的生存方式,鲁迅同样重视这种“异地”社会人生体验和感受在“乡土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如他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也述及1923年后出现的“乡土小说”,说这些“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蹇先艾写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裴文中“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李健吾取材于故乡生活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的,“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同来自浙东又同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王鲁彦和许钦文,两个人的“乡愁”却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王鲁彦“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湘中作家黎锦明的作品“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而“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童了”(15)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5-249页。。显然,“流寓”或“侨寓”之地的生命体验和社会文化感受,是这些作家的“乡土小说”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形成的根源之一,而使他们的作品在“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的北京,呈现出非同一般的特色。
我们还注意到,序言中鲁迅提到了勃兰兑斯及其“侨民文学”(现通译为“流亡文学”),虽说只有一句话,说“乡土文学”与“侨民文学”并不一样,但鲁迅在这里肯定并非随意地荡上一笔。据朱寿桐《〈流亡文学〉与勃兰兑斯巨大世界性影响的形成》(16)朱寿桐:《〈流亡文学〉与勃兰兑斯巨大世界性影响的形成》,《江海学刊》2009年第6期。一文介绍,鲁迅1924年就读过德文版的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933年又购买过日本翻译出版的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2、4、6分册,认真阅读还经常向青年人推荐。显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尤其第一部《流亡文学》中勃兰兑斯对流亡作家的关注与同情,流亡地作家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对创作的影响,于被故乡“放逐”、“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鲁迅是心有戚戚的。勃兰兑斯是在流亡柏林过程中写成《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此前他因其强烈的批判锋芒而遭排挤,并被解除哥本哈根大学的教职,1877年移居柏林,1883年才回到祖国。正是这几年流亡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勃兰兑斯把《流亡文学》放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第一部,对流亡作家倾注了极大热情,并为全书奠定了情感基础。而鲁迅的文学创作(包括小说和杂文),特别是1926年和1936年两次集中性地向故乡地缘文化返归(这个问题后文将专门论述),“侨寓”之地的境遇、心态的影响同样是分明的。其实,周作人一生“侨寓”于北京,所写的大量回忆故乡生活、风物的散文,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鲁迅上世纪30年代论“京派”与“海派”,更为明确地提出“京海之争”并非主要源于作家的“本籍”,而更是他们的“流寓”或“侨寓”之地社会文化淫染的表现,即:“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17)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页。
二
前述周作人与鲁迅各自侧重的不同方面,是中国现代作家故乡“地缘文化”表现的主要方式,这在沈从文、老舍、巴金等作家的创作中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彼此之间的差异也更为明显。
在我们的一般理解中,沈从文的创作是接近于周作人所说的“乡土艺术”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和“湘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热爱故乡的“乡下人”(沈从文总是爱称自己是“乡下人”),沈从文在其小说和散文创作中为我们精心建构了一个美丽的“湘西世界”,美好的山水和美好的人们,诗意地描绘出一片“无可替代的乡土生活”。湘西地处偏僻、交通落后,但山川秀丽、河水清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虽然奉巫敬神、贫穷落后,却又民风淳朴、率性顽强、重情重义。山民憨厚勇猛,水手粗犷多情,土匪豪爽仗义,即使吊脚楼上的妓女也“温厚痴情”……各种生命形态丰富多彩、自由舒展,充满原始的顽强活力。而这美好的环境和这美好的人性又是那样和谐地呈现于沈从文的笔下,达到生命与自然、人性美与自然美的完美融合。沈从文自幼生活的湘西是南方楚文化的故乡,凌宇说:“沈从文与苗族的血缘联系,决定了他的创作在骨子里所烙上的中国南方楚文化的印记。”(18)凌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笔下的“湘西”又是通过他后来在北京、上海、青岛的都市生活体验建构起来的,所以他有关湘西的小说、散文创作又或隐或显地贯穿着“双重视角”,既是从“湘西”看“都市”,又是从“都市”看“湘西”。即如他的代表作《边城》,小说第二章写茶峒城的景致,插上了这样一句:“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可以发现,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地无一时不使人神往倾心。”(19)《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7页。点出作者是在以“都市人”的眼光看“湘西”。接着写这里的“风俗淳朴”:“大都市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寄食者,因为商人的需要,水手的需要,这小小边城的河街,也居然有那么一群人,聚集在一些有吊脚楼的人家”,“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20)《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69-71页。。这在提示,他的《边城》又是立足于“湘西”看“都市”,整个作品的立意更主要在此。特别是写天保、傩送兄弟俩都喜欢上了翠翠,那句“兄弟两人在这方面是不至于动刀的,但也不作兴有‘情人奉让’,如大都市懦怯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的可笑行为”(21)《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115页。,道出了他写《边城》这则爱情故事的动因。同样,沈从文写《八骏图》、《罗汉》这些城市题材的小说时,是从一个乡下人的角度,看出了腐烂的上海城市文明,产生一种生命的危机感。而在上海写作《丈夫》这类乡土题材的小说时,他又由这危机感、恐惧感而想到家乡的原始生命活力被现代文明逐步吞噬的危机的出现。所以钱理群说:“他(沈从文)在北京写了《边城》,在上海写了《丈夫》,这显然是和他在北京、上海的不同体验有关的。”(22)《钱理群:沈从文笔下的北京上海文化》,2004年5月11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32-2.html,2019年5月10日。可见,沈从文离开了“侨寓”之地的社会文化体验和认识,是不可能建构起他的“湘西世界”的。
较之沈从文,老舍执著于写他自幼生活的底层社会市井杂院下等贫民所固守的“老北京”传统,更接近于周作人说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缘文化积淀的自觉表现。如果说沈从文为我们诗意地构造了一个美丽的“湘西世界”,那么,老舍则用他特有的“北京味儿”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世俗的京城“市民世界”。具有老北京特别风味特别气度的人文景观——胡同、大小杂院、四合院里的各色风俗人生世相,街头巷尾的各种古城职业活动等,老舍作了几近百科全书式的描绘。据舒乙介绍,老舍作品中出现过240多个真实的北京地名,像骆驼祥子拉车的路线、地点都真实到可以验证(23)参见舒乙:《谈老舍著作与北京城》,《文史哲》1982年第4期。。而在人物的塑造上,“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不同,老舍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他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2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3页。。无论是早期的《二马》中得过且过的老马,《猫
城记》中保守愚昧的“猫民”,还是《离婚》中墨守成规的张大哥,《骆驼祥子》中几经努力终于失败而沉沦的祥子,《四世同堂》中怯弱保守又好面子的祁家老太爷,《月牙儿》中同为烟花女子的母亲和女儿等等,莫不显示出传统的北京文化对“老中国的儿女”的深刻影响。特别是老一辈的市民,老舍最为熟悉,因而下笔最多也写的最好。作为皇都北京文化的“官样”特征如体面、礼仪、等级、规矩等等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分明。《四世同堂》中祁家老太爷也就一普通市民、平头百姓而已,但尊卑贵贱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老祖宗留下的礼教。战争都打到门口了,还忘不了自己过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25)老舍:《四世同堂(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60页。。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老舍对北京的熟悉,根源于他的北平文化背景中的满族血统。作为旗人的后代,老舍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26)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2页。他特别强调,“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它的“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27)老舍:《想北平》,《宇宙风》1936年第19期。。对此,樊骏先生评价说,“一个特定的地域与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亲密无间到如他所说的这般地步”,“以致没有北京就没有了老舍与他的作品——在中外古今的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28)樊骏:《认识老舍(上)》,《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但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的地缘文化氛围,不仅与北京这座元、明、清三代皇都的帝王气象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且对“五四”转而成为新文化倡导中心的北京也多少有些隔膜,即使是他执教英伦增添的一些流寓之地的文化体验,似乎也要经过在他身上根深蒂固的地缘文化感受与体验的过滤,而且,这种“流寓”体验与他所擅长表现的“老北京”传统之间呈现的是融合而不是对抗关系,他几乎自然而然地抹平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差异,以保证不失“老北京”传统特有的味道。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他是最能够把地缘文化的“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的作家,但也显而易见,早年生活空间的逼仄也局限了他,他难以超越“有限的平凡的存在”而“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29)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自己的园地》,第15页。,这不能不限制他的地缘文化表现的广度与深度。
与老舍相反,巴金的创作不是从故乡地缘文化浸染中萌发出来的,而是被“五四”催生的,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十分典型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作家。1927年巴金流寓法国,受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感染开始写作,但他又没有实际参与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活动,切身体验之不足而靠着如火一般的青春激情创作的大量小说,其概念化、模式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缺乏地域指认性。处女作《幻灭》出版后大受欢迎,尤其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喜爱,但英雄的主人公却是由俄国民粹派英雄衍化而来的。如果说人们欣赏沈从文主要是看到了“不一样”的湘西,那么青年读者喜欢巴金则是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了共同的理想与激情。直至巴金回到自己早年熟悉的败落中的上层社会官僚家庭的生活题材写出《激流三部曲》,其中地缘性的“土气息泥滋味”之不足仍然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家》是巴金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文学史家认为“高公馆为人们认识封建家长制提供了完整而形象的模型”(30)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263页。。但这认识是建立在政治学而不是建立在文化学、民俗学上的,成都高公馆是整个中国封建家族的缩影,看不到它与巴蜀文化历史的联系。巴金自己就说,“我们在各地都可以找到和这相似的家庭来”(31)巴金:《〈家〉初版后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1)》,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8页。。《憩园》是巴金离开家乡18年后据1941年、1942年两次回故乡的体验而创作的。沈从文抗战后也曾两次回到故乡,写出了《湘行散记》和《湘西》两书,呈现的仍是他所热爱的湘西特有的风情和人物。《憩园》中则几乎没有“川味”的山水风物、世态人情,巴金的体验是“看到金钱的威风,和钱滚钱、利滚利、坐吃山‘不’空的大表演。成都正是寄生虫和剥削鬼的安乐窝,培养各式各样不劳而获者的温床”(32)巴金:《谈〈憩园〉》,《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266页。。巴金要表现的是中国“广大的世界”,作品中是难有巴蜀之地特有的区域文化观念和符号的表征的。巴金的这个创作倾向也是可以从与同样自幼生活在成都平原、同样曾经留学法国的李劼人创作的《死水微澜》的对比中看出来的。历史上的巴蜀之地由于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的阻隔,在语言、信仰、风俗、习性和心理特征等方面与内地明显不同。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写成都平原一带的社会人生形态,呈现的是与中国汉文化圈不完全相同的另一个文化圈里的人物及其生活故事,写出了这里的伦理道德观和人生价值标准与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的一些根本差异。1986年10月巴金曾在李劼人故居感叹,“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33)黄里:《重温李劼人: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四川日报》2011年9月30日,第13版。。对比可见,巴金小说几乎是没有“故乡”的,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最少“地缘文化”特征的作家之一,或者说,他的流寓生活“主观”情感体验的表现,自觉或不自觉地模糊甚至中断了他“客观”上所应该有的故乡之缘,即“天府之国”特征极其鲜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地理历史传统。所以严家炎说“要研究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选择巴金也不太合适”(34)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页。。也有研究者指出,“完整考察‘出生地——地域——地域文化——作家——作品’的过程,可以发现巴金文学创作的巴蜀文化特征没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巴金文学创作‘内返性’、‘超越性’、‘时间性’的特征对‘地域性’构成消解,表现出‘反地域文化’的特征”(35)童龙超:《论巴金文学创作的“反地域文化”特征——兼谈对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反思》,《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三
由上面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鲁迅与老舍、巴金是明显不同的:一方面,就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缘文化积淀的自觉表现而言,鲁迅并不逊于老舍的“客观”,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取材于故乡生活的小说中,包孕着深刻的否定性思想的是他与浙东民性深厚的亲和力,而要求浙东景观、风物以及故乡人物浮雕似的艺术再现的准确性,如他笔下灰白色沉重的晚云、黎明前的暗夜、遍身油腻的油灯、单调的纺车、丁字街头、酒店、茶馆等等,成为他笔下的“鲁镇”、“未庄”、“S城”等几乎难以更易的“标识”;又如他曾经因为人们对《阿Q正传》的种种误解,一再对作品主人公阿Q予以说明与解释:
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36)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50页。此外,鲁迅在《忽然想到·九》(《鲁迅全集》第3卷第63-64页)、《〈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78-379页)等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说明。
另一方面,鲁迅也一次次“被故乡所放逐”,他的生命历程也是在不断“流寓”中渡过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37)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5页。——这些言辞更是在“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38)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的异国、异地体验中蒸腾起来的,这使他将一己的经历与外在世界联系起来,透视覆盆桥周家台门内发生的种种变故——“明爷爷”(子京)在科场拼搏一生,最终“掘藏”疯颠而死(39)参见收入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呐喊〉衍义》里的“县考”、“掘藏”、“发狂”三节。鲁迅将“子京”这一“原型”写进小说《白光》中。;到老“连半个秀才的名分也未捞到”而穷困潦倒的“孟夫子”,因“窃书”遭打,且被台门内外之人当做“笑料”(40)参见收入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呐喊〉衍义》中的“孔乙己”一节。鲁迅将“孟夫子”这一“原型”写进小说《孔乙己》中。;败落大家的诸多落魄子弟如“桐生”的“末路”(41)参见收入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百草园》中“桐生”和“桐生二”两节。鲁迅将“桐生”这一“原型”写进小说《阿Q正传》中。;“衍太太”代表的族中势利长辈们的那一幅幅诡谲、阴毒的面孔(42)“衍太太”出自鲁迅的《朝花夕拾·琐记》,收入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呐喊〉衍义》“本家与亲戚”一节,说她就是周家诚房的子传太太。这个人物可代表鲁迅的祖父入狱、父亲病故后,欺负孤儿寡母的族中势力长辈。;还有父亲的病故(43)参见鲁迅在《呐喊·自序》和《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中所述。,祖母蒋氏的丧事(44)鲁迅的小说《孤独者》开端写魏连殳赶回寒石山为祖母送葬的情节,就是取自鲁迅自身的经历,即他在杭州教书时赶回绍兴为祖母蒋氏送葬。参见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二十五节“孤独者”。……在鲁迅的心目中,这些已经不再仅仅限于台门之内,为之或忧、或悲、或愤,而成为他“熟识的本阶级”的一砖、一木、一石,他从中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的根基松动,并转而成为他营造的文学大厦最为坚实的素材。显然,就异国、异地体验推出的故乡地缘文化建构而言,鲁迅比巴金更为“主观”,他作品中之作为故乡生活写照的“鲁镇”、“未庄”、“S城”等又是他认识中的“老中国”的缩影与象征,是他认识中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现实社会人生境遇的缩影与象征;他的可以追溯到早年地缘性“绍兴师爷笔法”濡染的杂文(45)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91-97页。,作为贯穿他一生的主要创作,这些杂文在整体上构成的竟然是一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一部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历史、道德、法律、文学艺术的“百科全书”,一部展示现代中国人的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活的“人史”(4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375页。。
鲁迅作品中故乡地缘文化的表现,似乎更接近沈从文,就主客观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一致地表现出的是一种主观化了的“客观”与客观化了的“主观”,或者说,“客观”是在“主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观”同样是在“客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地缘文化表现在主客观之间是高度统一的。但是,鲁迅与沈从文之间仍然是有根本差异的。沈从文的异地体验和认识,在他的小说中又程度不同地限制了他不能整体上感受和认识“湘西文化”,他关注的多是都市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的畸形现象,即所谓“阉寺性”(4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282页。又见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9页。,他将此归结为人性的缺失,为此要造一座“人性小庙”(48)沈从文曾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见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页。,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它存在于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中(49)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2、5页。,以重造民族灵魂,重建民族精神。他对湘西的表现也就主要聚焦于此,以此为轴心辐射开来。这样一种都市体验和认识,不能不使他曾经生活过的保留着原始蛮荒的湘西在他笔下有些“纯化”了,呈现的是一个带有他自身“文人化”特点的世界,而渐少了他当初作为一个“外乡人”来到都市尚存的精神与意志的东西。显而易见,对照孕育了远古楚文化的湘西,我们能从他的小说中看到《楚辞》所表现的未受“文明”污染的自然生态,特别是“天人合一”的人情人性之美和颇为浪漫的性自由,但却难以从他小说中感受和认识到《离骚》整体上呈现的屈原精神与意志的世界——就此而言,他建构的“湘西世界”仍然需要通过周作人推重的“培养个性的土之力”得到深化,当然,对都市社会文化整体感受与体验的强化与深化,对他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要求。
鲁迅则不是这样的,他在差异已不甚显著的“两浙”文化中提取浙东,向历史深处走去,在浙东文化中感悟、认同、追寻远古越文化,建构起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由此而形成随岁月的流逝和踪迹的迁徙也难以割断的“地”之“缘”(50)详参陈方竞:《鲁迅与浙东文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突出表现在他1926年和1936年两次集中性地向故乡地缘文化返归,形成主客体之间富有张力的文化场,这是需要我们特别给予分析与认识的。
鲁迅第一次向故乡地缘文化返归,是1926年他完成的《朝花夕拾》。如研究者所说,是“对于‘爱我者’的眷恋,对以往生活(包括童年)的‘反顾’,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含情脉脉的‘爱’与‘温情’,都表现着‘人’的返归历史(过去)的倾向”(51)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139页。,这些回忆性散文把地缘文化的“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切合周作人所说“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生活积淀的自觉表现(52)如鲁迅在1934年4月11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70页。,但这仅仅是《朝花夕拾》写作动因与内容的一个方面;还有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这个方面与鲁迅的现实境遇与冲突直接相关——1924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学潮,要驱逐校长杨荫榆,鲁迅于1925年5月,也就是等到校方要开除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时,才写了两篇文章《忽然想到》和《“碰壁”之后》表示对学生的理解与支持。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刚起草《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准备联合一些教授为学生说话时,北京大学现代评论派的一批教授出马了。在1925年9月12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西滢(陈源)发表《闲话》,批评学生“闹的太不像样了”,尤其指责“某籍某系的人”“暗中挑剔风潮”,“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鲁迅认为,既然你先用“秽物掷人”,“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53)鲁迅:《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9页。。于是,你来我往,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当时轰动一时、后来影响深远的论争就开始了。这场论争非本文论述的重点,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论战中鲁迅一再说到辛亥革命,怀念和追忆光复会中的人。如在《忽然想到》中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54)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6-17页。,感慨辛亥革命这么快就被“国民”遗忘了;在《杂忆》中亦有对辛亥革命中人、事的忆写和感叹;在《华盖集·补白》、《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中特别提到刺杀恩铭的徐锡麟和“以革命为事”的陶成章及“好发议论”的章太炎等革命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更是再次提起秋瑾和王金发的“死案”,说明打落水狗的必要。
看到这一点,就会明白鲁迅1926年11月写出《朝花夕拾》的结篇之作《范爱农》,是顺乎其然的,这又决定了该篇写辛亥革命与前此的小说所写会有所不同。
在鲁迅全部著作中,《呐喊》最多地写到辛亥革命,如《药》、《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等,从中可见他对这场革命的“失望”与“否定”。几乎唯有《范爱农》与此明显不同:“革命的前一年”,范爱农与“我”在故乡“熟人的客座上”邂逅相遇——“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绍兴“光复”后的范爱农,几乎变了一个人,“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说:“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继之,“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55)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3-314页。。这样温情的语句,在鲁迅写辛亥革命的作品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胡风曾当面问鲁迅:“《孤独者》里面的魏连殳,是不是有范爱农的影子?”鲁迅不假思索地说:“其实,那是写我自己……”停了一下又说:“当然,也有范爱农的影子……”(56)胡风:《鲁迅先生》,《胡风全集》第7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5页。周作人也说:“《孤独者》这篇小说……写魏连殳后半生的事情。这主人公的性格,多少也有点与范爱农相像,但事情并不是他的。”见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18页。说明魏连殳也可以用来解释《范爱农》。那么,这个《范爱农》,作者所要追寻的又是什么呢?或者说,鲁迅通过与现代评论派论战写出《范爱农》,从中提取的究竟是什么呢?
《范爱农》的开头,鲁迅写了在日本的留学青年的一个生活片段。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就擒被挖心和秋瑾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传来,大家很愤怒,“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但一个声音起来了,“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57)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10-311页。。这个人就是范爱农。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明地看出他和一般革命青年的不同,他“任个人而排众数”,不在意“照例”的形式,不注重形式上言行的激烈,而表现出一种实际的决绝的革命态度。有学者说,“在鲁迅笔下实有其人、能见越文化风骨的,是光复会中的反清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范爱农,而在鲁迅创作中得到集中表现的,则惟有范爱农”;范爱农的表现就正是越人风骨,即“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而与这片土地上世代相传的“以牙还牙”、“睚眦以报”的复仇反抗精神一脉相承,也正是鲁迅自身风骨的体现(58)如上阐释可参见陈方竞:《鲁迅与光复会——〈范爱农〉解读》,《名作欣赏》2010年第30期。。
1936年鲁迅逝世前,着手于类似《朝花夕拾》的回忆性散文集《夜记》的写作(59)据冯雪峰、巴金、许广平回忆,鲁迅1936年应文化生活出版社之约,准备写一本类似《朝花夕拾》的回忆性散文集《夜记》,逝世前已写出的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死》、《这也是生活……》等。,是再一次向故乡地缘文化返归,其中的《女吊》与《范爱农》相一致,由现实境遇与冲突而发,呈现出主客体之间富有张力的文化场,不过,《女吊》直接针对的是“上海的‘前进作家’”(60)鲁迅:《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第614页。,将“被压迫者”与所谓“‘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61)鲁迅:《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第617页相对立,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62)鲁迅:《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第619页。。这一越文化风骨的再现(63)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1936年一再提起这一话题:“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第614页);“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官,遂编《越风》,函约‘名人’撰稿,谈忠烈遗闻,名流轶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鲁迅全集》第8卷第404页);“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致黄苹荪》,《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6页);“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59页)。,不仅是鲁迅与左联“左”的势力冲突所致,更是挣脱自身“左”的思想束缚的表现,如研究者所说,是他逝世前“精神上新的升华”的表现:
王元化先生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里讲到鲁迅,“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思辨短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90页)指出《二心集》以来所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对于鲁迅来说是一种局限性,不抱成见的研究者都会承认此说是符合鲁迅的实际的。也许还可以说,他对“国防文学”口号的反感,也同这种精神状态有关。(64)朱正口述、朱晓整理:《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1-112页。
向故乡地缘文化返归折射出的鲁迅逝世前“精神上新的升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这期间,鲁迅“置病于不顾”,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65)相关的记载有:“病前开印《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到上月中旬才订成,自己一家人衬纸并检查缺页等,费力颇不少。但中国大约不大有人买,要买的无钱,有钱的不要。我愿意送您一本,附上一笺,请持此向书店去取”(《致曹白》,《鲁迅全集》第13卷第400页);“珂勒惠支的画集只印了一百本,病中装成,不久,便取尽,卖完了,所以目前无法寄奉。近日文化生活出版社方谋用铜版复制,年内当可出书,那时当寄上”(《致王冶秋》,《鲁迅全集》第13卷第427页);“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季市》,《鲁迅全集》第8卷第401页)。。实际上,鲁迅在停止了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翻译后,其域外视野转向了他留日以至“五四”这段时间关注过的几位国外哲人和作家(66)姚锡佩在《现代西方哲学在鲁迅藏书和创作中的反映》(见《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中说:“自1933年以后,他购读的文艺理论和哲学著作的重心,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说转向他早年重视的几位哲人身上。”这几位哲人是尼采、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文学上重点关注的作家是果戈理、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他自1935年2月始,带病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直至去世(67)1935年9月28日《死魂灵》第一部译讫,9月29日始译第一部附录,10月6日译讫。1936年2月25日始译《死魂灵》第二部,译至第三章未完病逝。。对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的超越,研究者张直心早在上世纪末即有深入的研究,他提出鲁迅晚年“与病魔的切身抗争、与死亡的近距离对视,……使鲁迅对生命存在的眷注、对人生意义的思索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透彻、都紧切”,鲁迅逝世前的创作,是对“不无偏狭”的“《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剥离,使自己本有的文体风格以“更深沉、更动人的力之美”再现出来(68)张直心认为,“《二心集》型批评文体”大致“涵盖了《三闲集》后期至《南腔北调集》这一阶段”。他说:这一文体“不见了前期的隐晦曲折,而代之以一种观点鲜明、逻辑严谨、明白晓畅的理论风格”;晚年“与病魔的切身抗争、与死亡的近距离对视,……使鲁迅对生命存在的眷注、对人生意义的思索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透彻、都紧切”,这“赋予鲁迅晚年话语形式一种有别于《二心集》文体的更深沉、更动人的力之美;……使鲁迅的文思突奔纠葛,终于冲决明快畅直却不无偏狭的《二心集》形式渠道”。见张直心:《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3期,后修订收入张直心文集《晚钟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4、156、157页)。。
有学者认为,“作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家乡或自己生活、工作地方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融入创作中,赋予作品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文化价值”(69)李莉:《地域风情之奇与文学作品之美——以恩施土家族作家为中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的确,缘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出现而引发的对故乡“地缘文化”的关注和重视,在鲁迅、周作人、沈从文、老舍、巴金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身上都有突出的表现。周作人与鲁迅论及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缘文化积淀的自觉表现与“流寓”或“侨寓”之地生命体验的故乡地缘文化建构,是作家“地缘文化”表现的两种基本形态。相较而言,周作人更多地谈到前者的地缘文化表现,作为中国最早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作家,因受法国学者泰纳关于文学的时代、环境、种族三成因学说的影响,他强调的是“地方”、“风土”,是“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创者,自然也不例外。就像他致陈烟桥的信中所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70)鲁迅:《致陈烟桥》,《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1页。。但除此以外,鲁迅他还重视“被故乡所放逐”、“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作家“流寓”或“侨寓”之地的生存方式,重视这种“异地”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在创作中的重要影响。从此出发,我们发现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具有浓郁“北京味儿”的“市民世界”,最为接近周作人所说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缘文化积淀的自觉表现。老舍熟悉北京,北京的文化已融入他的血液里,古城给了他的性格,所以他能对老北京的市民生活作百科全书式描写,使北京的地域文化与他和他的作品达到亲密无间的地步。当然,老舍早年生活空间的逼仄以及北平市民文化对他根深蒂固的影响又制约了他,限制了其地缘文化表现的深度和广度。而巴金则是典型的恰如鲁迅所说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作家。他留学法国,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他的创作出自他火一样的革命激情,要表现的是中国“广大的世界”,流寓生活“主观”情感体验的表现,自觉或不自觉地模糊甚至中断了他“客观”上所应该有的故乡之缘,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最少“地缘文化”特征的作家之一。他没能像李劼人那样使“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其作品缺少地域指认性,失去了民俗学、文化学的认识功能,表现出“反地域文化”的特性。巴金的这种创作特点,在中国现代作家创作中是非常分明而且少见的,几乎只有在同样具有火一样创作激情的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中才找到相似情形——“《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7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103页。。沈从文和他们不一样,他对独特的“湘西世界”的诗意抒写,看起来非常吻合周作人的“乡土文学”理论,但其作品中又或隐或显地贯穿着“双重视觉”,即既是从“湘西”看“都市”,又是从“都市”看“湘西”,这似乎又暗合了鲁迅的“流寓”或“侨寓”之地影响之说,其创作的地域文化表现形态与鲁迅相近。但是,沈从文与鲁迅也是有根本差异的。他没有鲁迅那样的对都市社会文化深刻的整体感受与体验,因而削弱了他对“湘西文化”的整体性认识。我们可以从其作品中看到《楚辞》所表现的自然生态之美、“天人合一”的人性之美,却难以感受到如《离骚》般呈现的屈原精神与意志。鲁迅则能从故乡提取浙东文化,并走向历史的深处,感悟、认同、追寻远古越文化。1926年和1936年的两次集中性的向故乡地缘文化的回归,是其相关理论在创作上的突出表现,推出的也正是鲁迅的越人风骨。需要说明的是,周作人与鲁迅论及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缘文化积淀的自觉表现与“流寓”或“侨寓”之地生命体验的故乡地缘文化建构这两种“地缘文化”表现的基本形态,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都有或明或隐、或深或浅、或有意或无意、或合二为一或各有侧重的表现,上述鲁迅、周作人、老舍、巴金、李劼人、沈从文等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而已。如茅盾,其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就既有赖故乡“吴越文化”的浸润、影响,又有侨寓之地“理论、生活、文学修养上的充分准备”(7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223页。。这些作家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论及。而在所有作家中,鲁迅因其对于故乡文化的深入而全面的认识,对于侨寓之地生活体验的独到和深刻,及其思想的博大和精深,其小说和杂文的创作成就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并为我们提供了“地域文化”表现形态的杰出而典型的范式,达到了至今无人企及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