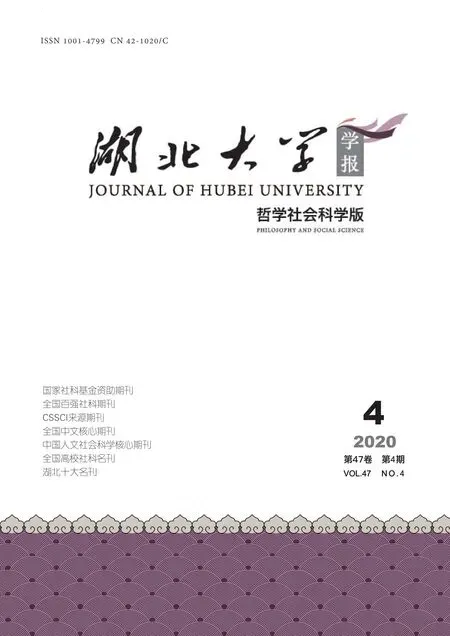辽金元科举制度的创新及其政治文化影响
2020-01-11李兵
李 兵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与唐宋的汉族科举相比,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辽金元科举无论是从实行科举的持续时间(1)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建立了以契丹贵族为核心的政权,国号契丹,建元“神册”;大同元年(947)改国号为辽,至圣宗统和六年(988)才正式在其全境实行科举,此时距辽朝1125年为金国所灭只有137年,辽朝开科仅50余次。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称帝,为金太祖,以会宁府为都城,建元收国;熙宗在天眷元年(1138)五月,将科举推广至其统治的全境,直至金朝灭亡,共计开科40余次。1260年,忽必烈建元中统,定都燕京;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大元,至仁宗皇庆二年(1313)才正式开科,实行科举的时间只有40余年,开科仅16次。,还是从录取进士的人数(2)对于辽朝科举录取的进士人数,学界仍有较大分歧,如朱子方认为辽朝开科53次,取进士2211人,详见朱子方:《辽代进士题名录》,《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 年第 4 期;李桂芝认为辽朝至少开科58次,取进士至少2432人,详见李桂芝:《辽金科举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因史料记载阙如,学界关于金朝进士数的统计亦有不同,如周腊生认为金朝开科43次,约取进士15000人,详见周腊生:《金代贡举考略》,《孝感教育学院学报》(综合版)1996年合刊;都兴智则认为金朝进士总数为6150人左右,详见都兴智:《辽金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94页。元朝进士数,尽管学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但开科16次,取中进士1139人是比较公认的结论,详见杨树藩:《元代科举制度》,《“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68年第17期;陈高华、宋德金、张希清主编:《中国考试通史》卷2“宋辽金元”,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1、368页。等方面而言,均有自身的不足。如果仅从进士在官僚阶层中所占的比重而言,科举对辽金元政治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对于辽朝进士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在《辽史》中有传或有附传的人,共计272人,其中出身于进士者仅22人,只占所统计总人数的百分之零点八,其比例确实很低。”(3)朱子方、黄凤岐:《辽代科举制度述略》,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9页。在金朝的授官制度中,进士排在“内属外戚,与国人有战伐之功、豫腹心之谋者”和“潢霫之人”(4)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16《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63页。之后,他们能成为宰相的极少。元朝进士任官的比例也极低,姚大力认为:“元朝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其数量或地位来说,在官僚构成中都居于绝对劣势。”(5)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年第6期。萧启庆也同意这一观点,认为“由于进士人数少,地位低,不足以构成一个具有自卫或扩张能力的群体”(萧启庆:《元代科举特色新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八十一本,第一分)。因此,辽金元科举的地位和影响容易被人忽视。然而,如果从中国科举的发展历程,以及科举对辽金元政治模式转变、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影响等角度来审视辽金元科举,我们对其历史地位与影响应该会有不同的认识。
一、辽金元科举实行范围的拓展和制度的创新
辽与五代、北宋并存,金与北宋、南宋并存,辽金科举制度仿效唐朝、五代和宋朝科举制度的色彩非常明显。元朝科举是在入主中原30多年后才被恢复的,基本继承了南宋科举制度。辽金元统治者以科举选拔文官,科举的使用范围得以向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拓展。从总体而言,科举的影响力明显得到提升。与此同时,因适应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需要和特殊性,辽金元科举制度得以不断创新,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辽朝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后,“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6)脱脱等:《辽史》卷45《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5页。。为了解决对汉族官员急剧增长的需求,也为了笼络燕云地区的汉族士子,辽朝于会同元年(938)决定效仿唐朝、五代,在燕云十六州率先实行科举取士,并于次年正式开科取士。辽太宗之后,世宗、穆宗两朝20年的动荡局势,尤其是穆宗的暴政使辽朝面临内忧外患。其后景宗时期执掌朝政的皇后萧绰唯才是举,在团结大批有才干的契丹贵族的同时,也大胆任用汉族官员,内安百姓,外御强敌,为政局的稳定奠定了良好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加强科举制度建设成为辽朝统治者的重要选择,以选拔更多有才华的汉人和渤海人。统和六年(988),辽圣宗将科举从燕云十六州推向辽朝全境;与之相适应,还将贡院从南京迁至上京临潢府,并将其管理范围扩大到了辽朝全境,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境性的科举管理机构。这是辽朝科举走向制度化、正规化的重要标志。至兴宗、道宗两朝,辽朝科举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无论是制度建设、录取人数,还是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已经达到了鼎盛的阶段。辽朝成为第一个在其统治全境实行科举制度的少数民族政权,开了少数民族政权通过科举取士的先例。
然而辽朝统治者因担心让契丹族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会影响契丹族历来强调的尚武骑射精神,从而削弱契丹族子弟的战斗力,故从设立科举之初就严格禁止契丹族士子以及辽朝北方的其他游牧民族士子参加科举考试(7)至辽末,这一政策似乎有所放松。据《辽史》卷30《天祚皇帝本纪四》记:“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孙也。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升承旨。”(脱脱等:《辽史》卷30《天祚皇帝本纪四》,第355页)这也就是说,宗室耶律大石于天祚帝五年(1105)进士及第。,只允许汉族以及汉化程度比较深的渤海族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因此,辽朝虽然拓展了使用科举取士的地域范围,但是科举并没有成为辽朝大多数少数民族士子入仕的途径。
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在与辽朝进行军事对抗期间,重视网罗被称为“异代进士”的辽宋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金朝政坛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让金朝统治者看到掌握儒家知识的士人对金朝建设的重要作用,而且使他们对科举制度有了真切的认识,因此金太祖收国年间即实行科举取士(8)对于金朝开科时间,学术界有争论,如赵冬晖认为始于天会元年(1123),详见赵冬晖:《金代科举年表考订》,《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周腊生认为是天会二年(1124),详见周腊生:《金代贡举考略》;李桂芝认为早于天会元年,详见李桂芝:《辽金科举研究》,第134页;笔者认为金朝开科应该在金太祖收国二年(1116)前后。。尽管金朝初开科只是临时之举,并没有严密的制度,但是仍然为金朝的扩张和稳固发挥了重大作用。金朝攻灭北宋以后,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实现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金太宗在授予儒士较高官职的同时,着手改革科举制度,吸引原北宋地区的士子应试,以补充官员空缺,这使金朝科举实施的地域范围远远超过辽朝,即不仅基本覆盖原辽朝统治地区,而且还将淮河以北的原北宋统治地区也囊括其中,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士子都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
由于原北宋和原辽朝管辖地区的士子在知识结构和文化水平方面都存在差异,天会五年(1127)八月,金太宗下诏,决定实行南北选。南选的对象为原北宋控制地区士人,北选的对象则是为原辽朝管辖地区士人。由于参加南选的士人原为北宋的北方人士,他们擅长经义,故而南选时,他们应试经义进士,兼应词赋进士;而参加北选者原为辽朝所属士人,他们擅长文学辞章,因而让他们应考词赋进士,兼考经义进士。随着金朝统治地区文化差异日渐缩小,海陵王即位以后,改南北选为南北通选,宣布取消经义科,仅留词赋一科,让原北宋和原辽朝管辖范围内的士子同场竞争。不仅如此,至世宗朝,越来越多的女真族人与汉族人杂居,他们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汉文化水平明显提高。大定十三年(1173),金朝统治者正式设立女真进士科,以选拔女真族子弟为官,“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真)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9)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30页。。女真进士科的考生只要考一场,考题是策问,而且可以免乡试、府试,直接参加会试和殿试。设立女真进士科是金朝科举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也是中国科举史上专门为少数民族士子设立科目的首创,这种专门为少数民族士子设立科目的做法,可以吸引更多的女真族士子读书应试。与辽朝相比,金朝科举不仅在使用的地域范围上得到进一步拓展,而且在对少数民族士子的影响程度上也有明显加强。
蒙古贵族窝阔台在征伐的过程中,希望解决儒士地位问题,以达到笼络儒士的目的。忽必烈当政期间,不仅大臣们之间有恢复科举的激烈讨论,而且蒙元最高统治者也多次谕令有关部门出台恢复科举的相关措施,但均无果而终。直至元仁宗即位之后,恢复科举再次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为达到通过科举选拔儒士、改变吏员成为选官的主要来源的目的,在翰林院承旨程钜夫、中书平章政事李孟、参知政事许师敬、翰林学士贯云石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十八日下诏“行科举”。此时距元太宗1238年举行戊戌选试已有75年,距元世祖1279年攻灭南宋统一中国亦有34年之久,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科举中断最长时间后的重建。延祐元年(1314)举行乡试(10)因皇庆三年正月即改元延祐。,次年举行会试、殿试,正式录取新科进士56名。由于元朝疆域广大,读书应试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所分布的地域范围不仅远远大于辽朝、金朝,而且也超过了唐朝、北宋、南宋。因此,如果从空间来看,科举的实施范围在元朝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
在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方面,尽管元朝并未像金朝一样设立专门录取少数民族士子的科目,但是元朝举行乡试、会试时,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的考试内容、场次和录取比例都有明显的区别。蒙古人、色目人仅考两场:第一场试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而汉人、南人则需要考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各治一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选择一道作答;第三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蒙古人、色目人的考试题目难度也大大低于汉人、南人。录取时,分右榜和左榜,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四种人各占录取名额的四分之一。无论是从人口的绝对数,还是从读书应试人数而言,蒙古人、色目人都远远少于汉人、南人,而其录取名额与汉人、南人完全相同,元朝统治者照顾蒙古人、色目人的意图非常明显。尽管这一政策清楚地表现出了元朝科举制度的民族歧视色彩,但是对于吸引蒙古人、色目人士子学习汉文化却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科举制度在辽金元的统治区域实行,是其影响力的外在表现的话,那么科举制度本身是否能结合少数民族政权的特点和统治的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则是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内在保障。与辽朝科举制度基本仿效唐朝、五代、北宋科举制度不同,金朝科举进一步完善了入场搜检制度。在泰和元年(1201)之前,金朝科举入场搜检时,曾经采用“解发袒衣,索及耳鼻”的手段。由于这一做法缺乏对应试者的尊重,引起了他们的反感,金朝廷不得不恢复大定二十九年(1189)的做法,即要求考生在入场前沐浴,更换上官方统一提供的衣服,这既能防止夹带,又尊重了应试士人的人格,达到了“既可防滥,且不亏礼”(11)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一》,第1147页。的良好效果。这种防止作弊的办法在中国科举史上是十分独特的,对明清乡试、会试的入场搜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重要借鉴意义。
尽管开科时间、次数远远不如辽金两朝,但是元朝却在诸多方面发展了科举制度。比如,在考试层级方面,元朝基本确立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制,而且乡试基本是以省为单位举行,改变了唐宋科举实行以府州为单位实行解试的做法。元朝乡试在全国设17处考场,其中设在行省的有11处,即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江浙、江西和湖广;设宣慰司2处,即河东和山东;设直隶省部路4处,即真定、东平、大都和上都(12)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21页。。各处考场或利用南宋原有的贡院,或新建贡院作为专用考场。会试在京城贡院举行。
在考试时间方面,元朝乡试为八月,会试为二月,殿试为三月,明清乡试、会试、殿试的月份基本与之相同。
在贡院规制方面,元朝乡试、会试时,考生除允许带《礼部韵略》入场之外,严令禁止怀挟文字,每名考生由一名士兵搜检。为防止考官徇私录取,元朝科举还制定了回避制度,即“举人与考试官有五服内亲者,自须迴避,仍令同试官考卷。若应避而不自陈者,殿一举”(13)《中书省奏准试科条目》,转引自陈高华:《元朝科举诏令文书考》,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1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7-158页。。
在试卷处理方面,元朝的规定较宋朝更加详细。乡试、会试考生答题完毕之后,至受卷所交卷。受卷官接收考生试卷,将其姓名登记下来,并给考生发放交卷凭证,考生以凭证出场。受卷所将试卷交给弥封所,弥封官“腰封用印,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并且给试卷编号,其编号的具体方式是“以三不成字撰号。每名累场同用一号,于卷上亲书,及于历内标附讫”(14)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24页。。然后,试卷送交誊录所,“牒送誊录官置历,分给吏人,并用朱书誊录正文,仍具元卷涂注乙及誊录涂注乙字数,卷末书誊录人姓名,誊录官具衔书押,用印铃缝,牒送对读所”(15)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24-2025页。。如誊录有错误,即重罚誊录者。尽管誊录是宋朝科举的延续,但是用朱笔誊录成朱卷却是从元朝开始的。之后,誊录的朱卷与考生作答的墨卷送交对读所。翰林院官员要清点试卷的总数,呈报给监察御史。对读所的官员详细核对考生墨卷与朱卷,确定没有任何差错后,签名确认,将朱卷呈交内帘,考生墨卷交还弥封所保管。受卷所、弥封所、对读所书写文字均用朱笔,以区别于考生墨卷所用的墨笔。考官评阅试卷时,用墨笔批点。
在录取程序方面,阅卷结束后,“收掌试卷官于号簿内标写分数,知贡举官、同试官、监察御史、弥封官,公同取上元卷对号开拆,知贡举于试卷家状上亲书省试第几名”(16)宋濂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25页。,录取工作就基本完成,只需要张榜公布了。
这些制度几乎为明朝科举所继承,并加以进一步完善,成为明朝洪武十八年(1384)所制定的科举“永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金元统治者在地域上极大扩展了科举的使用范围,同时在仿效、继承汉族科举的基础上,结合少数民族政权的特点和统治需要,在诸多方面进行了科举制度创新,使其在体现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向公正、公平选拔人才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二、辽金元科举推动少数民族政权政治模式的转变
科举作为一种选拔文官的考试制度,对辽金元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对政治的影响最为直接。从政治模式看,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其初期应该属于武人政治或军人政治,以及建立在武人政治或军人政治基础上的依靠世袭荫恩获取特权的少数民族贵族政治。辽金元统治者通过科举选拔读书人充任文官,让他们在官僚阶层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不仅是协助少数民族政权实现对汉族地区统治的重要力量,而且也取代了部分武人或军人、世袭贵族的职位,使辽金元政权的政治模式逐渐转向文官政治。
辽朝进士在官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金史》云:“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17)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一·序》,第1129页。进士出身者在辽朝官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是有客观原因的:其一,辽朝是在取得幽云十六州后,也就是会同元年(938)才开始在原汉族统治区域实行科举取士。在辽朝200余年的历史上,在其全境实行科举的时间大致只有60%左右。因此,从实行科举制度的延续时间来看,进士出身者不可能在辽朝官僚体系中占据太高的比例。其二,辽朝严禁契丹族子弟报考应试,而契丹贵族又是辽朝官员的重要来源,因此这一政策直接导致进士出身者在辽朝官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大大降低。
尽管如此,部分进士出身者仍然在辽朝官僚系统中有着比较高的地位。根据《辽史》等文献的记载,在辽朝进士中,官至宰执者至少有32人,如室昉、张俭、杜防、张宥、刘三嘏等。由进士出身者出任宰执,这是辽朝从武人政治向文官政治转变的直接表征。不仅如此,随着辽朝政局逐渐稳定,其与宋朝、西夏、高丽的战争逐渐减少,甚至领土纠纷都不是完全依靠武力,更多地是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而进士出身者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充当了出使宋朝、西夏、高丽的副使,以及接伴使和馆伴使的角色。在与宋朝的交往中,与契丹族官员相比,文化素养较高的辽朝进士对中原文化、宋朝大臣的处事态度和思维方式等有更多的了解,更容易掌握宋朝的意图,便于及时沟通和商量对策,有可能为辽朝争取到最大利益(18)对于宋辽的交聘制度,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曹显征:《辽宋交聘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24页。。比如,为向宋朝“索取十县”之地,太平十一年(1031)进士刘六符不仅两次作为副使出使宋朝,而且还以接伴使和馆伴使的身份接待宋朝使者富弼等人,多次与富弼等人交锋,迫使北宋朝廷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进士出身者的出使活动,加强了辽朝与宋朝、西夏和高丽的交往,让契丹贵族进一步了解了宋朝的政治制度,对于契丹贵族仿效宋朝的文官政治有推动作用,促进了辽朝这个崇尚武力的少数民族政权向文官政治转变的步伐,这是科举对辽朝政治影响的重要表现。
与辽朝类似,进士出身者在金朝官僚体系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并不高,但是他们对金朝从武人政治向文官政治转变有直接推动作用。金人李世弼在评价科举制度的功绩时云:“近披阅金国登科显官升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间见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赞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余载,朝野闲暇,时和岁丰,则辅相佐佑,所益居多,科举亦无负于国家矣。”(19)李世弼:《登科记序》,张金吾编纂:《金文最》卷45,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53页。金朝在建立之初,任命对宋辽制度比较熟悉的进士出身者为相关典章制度、重要礼仪的制定者。比如天会八年(1130)赐进士及第的张浩是金朝的重要礼仪制定者,“太宗将幸东京,浩提点缮修大内,超迁卫尉卿,权签宣徽院事,管勾御前文字,初定朝仪。……天眷二年,详定内外仪式”(20)脱脱等:《金史》卷83《张浩传》,第1862页。。天眷二年(1139)进士及第的石琚也是金朝典章制度的重要制定者,大定二年(1167)擢石琚为左谏议大夫,“奉命详定制度,琚上疏六事,大概言正纪纲,明赏罚,近忠直,远邪佞,省不急之务,罢无名之役”(21)脱脱等:《金史》卷88《石琚传》,第1959页。。张行简为大定十九年(1179)状元,为官30年,“凡朝廷有大制度、大典册、大号令,至于纪世宗、显宗、章宗三朝之宏休伟烈,未尝不经公之手”(22)赵秉文:《赠银紫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张文正公神道碑》,张金吾编纂:《金文最》卷88,第1287页。。此外,孙铎、张行简、阎公贞等进士出身者为金朝典章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3)李桂芝:《辽金科举研究》,第253页。。元人对进士出身者在金朝典章制度建设方面的贡献有较为公允的评价:“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岂非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24)脱脱等:《金史》卷51《选举志一》,第1130页。与辽朝进士在辽朝政治向文官政治的转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相比,金朝以进士为主体的官员仿效宋朝、辽朝建立起的典章制度、重要礼仪,不但有力地推动了金朝较快地从武人政治向文官政治的转变,而且还为金朝文官政治的运作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进士出身者出任金朝官员,不仅从整体上提高了官员队伍的素质,而且对澄清金朝的吏治,维持文官政治的运作有极大的帮助。不少进士出身者为官清廉正直,他们不仅不跟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甚至还敢于与权贵展开正面斗争。石琚进士及第后,初授官授邢台县令。然而,“邢守贪暴属县,掊取民财,以奉所欲,琚独一物无所与。既而守以赃败,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办,改秀容令”(25)脱脱等:《金史》卷88《石琚传》,第1959页。。有的进士还敢于与位高权重的女真贵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比如大定二十八年(1188)进士张行信认为完颜讹可遇兵辄溃,毫无斗志,其上书曰:“御兵之道,无过赏罚,使其临敌有所慕而乐于进,有所畏而不敢退,然后将士用命而功可成。若讹可败衄,宜明正其罪,朝廷宽容,一切不问,臣恐御兵之道未尽也。”(26)脱脱等:《金史》卷107《张行信传》,第2364页。兴定元年(1217)三月,术虎高琪为宰相,“专权用事,恶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动遭窘辱”(27)脱脱等:《金史》卷107《张行信传》,第2367页。。身为参知政事的张行信多次弹劾术虎高琪。时人对张行信不畏权贵,敢于尽忠直言赞誉有加,“发凶竖未形之谋,则先
识者以为明。犯强臣不测之威,则疾恶者以为刚”(28)元好问编:《中州集》卷9《张左丞行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3页。。
不仅汉进士如此,女真进士也坚决反对女真贵族擅权。大定二十八年(1188)女真进士及第的裴满亨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内侍梁道儿恃恩骄横,朝士侧目,亨劾奏其奸”;在担任大名知府时,“豪猾从衡,前政莫制”,裴满亨上任伊始不仅明确宣布条规,而且还严格执行,严厉打击违规者,使大名府“阖境帖然”;在担任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时,一些世袭贵族大肆侵夺民田,“亨检其实,悉还正之”(29)脱脱等:《金史》卷97《裴满亨传》,第2144页。。在辽朝,一方面,女真进士是文官政治的执行者,他们直接推动辽朝政治向文官政治转变;另一方面,他们的特殊身份,使其在反对女真贵族所希望保持的武人政治或者贵族政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往往会超过汉进士。
元朝建立后,虽然将文官政治模式已经相当成熟的南宋纳入版图之中,但是元朝依然保留了浓厚的少数民族贵族政治的特点,萧启庆则认为,“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表面上采用了中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但未扬弃蒙古传统的‘家产制’,实际上,蒙元政府是一种蒙汉混合的‘官僚家产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30)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第5页。。在元朝的政治运作中,蒙古、色目贵族是占主导地位的,然而蒙古族、色目族官员往往汉文化水平较差,有的甚至连基本的行政能力都不具备,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3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刻名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页。正因为这样,元朝统治者从各级政权的实际运作出发,需要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吏员来协助处理行政事务,即以吏入仕,这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改变元朝贵族政治的效果。与掌握一般知识的吏员相比,进士出身者的个人素质往往高于充任吏员的儒士,这对元朝文官政治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吴师道认为进士出身者由于受到儒家圣人之学的熏陶,是异乎常人的,他说:“由科目而仕者,要必以有异乎人。然异乎人者,岂有他哉?正身明教,守职奉法,一循圣人之道,而不戾明天子之意,则所谓异者,又不过即其常而已。”(32)吴师道:《吴师道集》卷14《序一·送浦江邑长元凯公序》,邱居里等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01页。
不仅如此,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作为主要考试内容,进士出身者深受程朱理学中重义、重节思想的熏陶,他们比非进士出身的官员和普通人更重民族大义和名节。元朝末年,面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全国呈现出一片衰败之气,官员之中望风而逃者有之,兵败投降者有之。而进士却成为官场的中坚力量,正如周霆震所言:“今世变滔滔,毅然左冲右溃而不可夺者,悉由进士中来。”(33)周霆震:《石初集》卷3《送吴县丞赴江西省掾并序》,胡思敬辑:《豫章丛书·四元人集》,南昌:南昌古籍书店,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在元朝危难之际,有的进士挺身而出,甚至能舍身成仁。杨维桢指出:“我朝科举得士之盛,实出培养之久,要非汉比也。至正初,盗作。元臣大将守封疆者,不以死殉而以死节闻者,大率科举之士也。”(34)杨维桢:《送王好问会试春官叙》,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2册卷133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519页。有的进士在危难关头能亮明自己的进士身份。比如,冯文举面对农民起义军明玉珍的进攻时,他对妻子马氏说:“我元进士,蒙恩厚,今天运至此,有死无二。汝光州马中丞孙女也,其从之乎?”马氏回答:“夫既义亡。妾生何益!”(35)柯劭忞:《新元史》卷232《冯文举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69-3370页。于是,他们夫妇俩在学宫自缢而亡。至正二十七年(1367),明军攻陷福州,获独步丁毫无惧色,他说:“吾兄弟三人,皆忝进士,受国恩四十年。今虽无官守,然大节所在,其可辱乎!”他最终“以石自系其腰”(36)宋濂等:《元史》卷196《忠义四》,第4434-4435页。,投井而死。实际上,进士们为元朝慷慨就义,基本上都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清人赵翼云:“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37)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0《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北京: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645-646页。赵翼根据《元史》的记载,列出了余阙、台哈布哈、李齐等16人死于节义。桂栖鹏考证出元末农民战争时期为元朝“死节”、“殉难”的进士为42名(38)桂栖鹏的《元代进士研究》中所统计的42人中,没有明确登科时间的是张恒、海鲁丁、穆鲁丁、王瑞、潘炎等5人,也就是说桂栖鹏统计的,有37人的登科时间是明确的,详见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7-83页。。而展龙在桂栖鹏统计的基础上,考证出元末农民战争期间死难进士为60人(39)展龙:《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2-255页。。虽然元朝死于节义的进士在千余名进士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但是进士死于节义却有着示范、榜样作用。进士死节应该是在文官政治模式之下,进士们面对武力侵害所做出的必然选择,是文官政治成熟以后,进士们面对国家、朝廷受到强烈侵害所采取的一种极端的对抗手段。
因此,尽管进士出身者在辽金元官僚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但他们确实是推动辽金元从武人政治、贵族政治向文官政治转变的最重要力量。由此可见辽金元科举在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三、辽金元科举促进“华夷同风”的实现
建立辽、金、元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人均为游牧民族,他们本身对于汉文化,尤其是经史、文学知识缺乏基本的了解。当他们将战争锋芒均直指中原,占领文化水平远远高于自身的汉族地区,学习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与汉文化融合是更好实现对这些地区统治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引导和促使包括少数民族士子在内的各族士子学习经史、文学知识的有效手段,儒家文化因此逐渐成为辽金元的主导思想,这是“华夷同风”在辽金元时期的最直接表现。
以科举取士既是辽朝重视儒家文化的重要表现,也是推动儒家文化在辽朝统治地区传播的重要手段。辽圣宗、兴宗、道宗等对儒家文化都有浓厚的兴趣。辽圣宗在辽朝统治域内遍设府州县学,在推广儒家文化教育的同时,又把科举由燕云十六州推向全境,进一步扩大了科举在辽朝的影响。兴宗、道宗对科举考试更加重视,甚至亲自出考试题目,这在少数民族政权中是极为少见的。重熙五年(1036)十月,兴宗“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40)脱脱等:《辽史》卷18《兴宗本纪一》,第217-218页。。这一方面表现出兴宗自身有比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另一方面体现出辽朝最高统治者对于科举的重视程度。
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重视,辽朝科举对推动儒学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辽朝科举制度仿效唐宋,有明经、词赋等科目,经史、文学是重要的考试内容,科举制度不但为辽朝士子学习汉文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能较为有效地引导北方游牧民族士子学习经史、文学知识。包括契丹族士子在内的辽朝各族士子对学习儒家文化都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其水平不断提高,有的甚至达到了可以与汉族士子同场竞争、博取科举功名的水平。耶律蒲鲁“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至重熙中叶,耶律蒲鲁不顾辽朝的禁令,参加科举考试,“举进士第”(41)脱脱等:《辽史》卷89《耶律蒲鲁传》,第1351页。。他因违反契丹族士子参加科举的禁令而遭到处罚,然而,辽兴宗处罚的对象并不是耶律蒲鲁本人,而是其父耶律庶箴。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辽兴宗不但没有惩罚耶律蒲鲁本人,也没有取消耶律蒲鲁的进士资格,甚至还任命他为牌印郎君。应该说,辽兴宗的这一做法是很耐人寻味的,说明他一方面需要严格执行禁止契丹族士子参加科举的规定,另一方面对像耶律蒲鲁这样热衷于学习儒家文化的契丹族士子又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至道宗以后,辽朝禁止契丹族以及与契丹族习俗相近的少数民族应试的禁令应该是逐步取消了。作为皇族子弟的耶律大石能顺利参加科举,并考中进士,说明辽朝后期已经不再禁止契丹族士子以及其他游牧民族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应该说,这是儒家文化向辽朝的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传播的结果,而少数民族士子积极应试,能在与汉族士子的同场竞技中脱颖而出,足以说明辽朝少数民族士子的儒家文化水平已经明显提升。
与辽朝禁止契丹族士子及与其习俗相近的北方游牧民族士子应试科举不同,金朝允许其管辖范围内符合报考条件的各族士子应试,各族士子在科举的推动下努力学习儒家文化,女真族尤为典型。金朝立国不久,女真学者完颜希尹仿汉人楷体和契丹文字,结合女真语,创制女真大字。熙宗年间又创制女真小字,颁行于金朝管辖地区。为提高女真人的文化水平,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颁行以女真大小字翻译的儒家经典,并设立女真族文学校,以便让女真族子弟能更好地学习女真文字和儒家经典,女真族知识分子队伍明显壮大,在府学就读的女真族子弟就多达3000余人。为使女真族士子有更好的入仕途径,金朝设
立女真进士科,专门用来录取女真族士子,使女真族士子学习儒家文化有了制度保障。李世弼在谈到科举对于儒家文化在金朝传播的贡献时说:“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弟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国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者,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其大乎。”(42)李世弼:《登科记序》,张金吾编纂:《金文最》卷45,第653页。应该说,辽朝禁止契丹族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应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学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而金朝允许管辖范围之内的所有士子应试,使其官学和私学教育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儒家文化在北方地区传播的成效更明显,使女真族人的文化水平整体上提升,一些女真族士子的文化水平甚至跟汉族士子相当。如女真进士裴满亨“敦敏习儒,大定间,收充奉职”。世宗对他说:“闻尔业进士举,其勿忘为学也。”大定二十八年(1188)裴满亨进士及第,世宗非常高兴,升其为奉御。有一天世宗问他“上古为治之道”时,裴满亨回答说:“陛下欲兴唐、虞之治,要在进贤,退不肖,信赏罚,薄征敛而已。”(43)脱脱等:《金史》卷97《裴满亨传》,第2143页。应该说,裴满亨的回答与精通儒家经典的汉族士子没有明显的差异。
可以说,正是为了应试的需要,大量的女真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子弟学习儒家文化,接受儒家文化,使得民族之间的鸿沟变浅、变窄,这有利于汉族和女真族文化上的相互认同,进而实现民族融合,“华夷同风”在金朝已经十分清楚地体现出来了。金朝涌现出了一批在教育、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颇有造诣的进士及第者,他们不仅是金朝文化的创作者和传播者,而且还是金朝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承者。兴定五年(1221)进士及第的元好问是金朝最有成就的史学家之一。他晚年以整理金朝史料为主要任务,他编撰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其文集成为元人修《金史》的重要依据,也是后人研究金史的主要史料。赵翼在《廿二史劄记》说:“《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他认为《金史》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其修撰者“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44)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7《金史》,第544页。。
与辽金在建元不久即开科取士不同,元朝建立之后长期未恢复科举。在停开科举期间,汉族大臣和一部分蒙古族官员多次呼吁恢复科举。大批精通程朱理学的儒臣在劝说元朝统治者实行科举过程中,极力陈说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对治国理政之利弊,让包括元朝最高统治者在内的蒙古、色目等贵族逐渐了解、认识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忽必烈在漠北潜邸时,金末状元王鹗被召至潜邸,忽必烈对他非常尊重。王鹗为忽必烈“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每夜分,乃罢”。忽必烈听完之后,对王鹗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45)宋濂等:《元史》卷160《王鹗传》,第3756页。尽管元朝并未能立即实行科举,但关于恢复科举的多次讨论,使元朝统治者基本认同了儒臣们所倡导的重经义、轻诗赋的观点,为此后元朝实行科举时确立以程朱理学为主要考试内容奠定了思想基础。
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十八日,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诏书中明确考试内容“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46)《元典章》卷31《礼部四·科举条制》,陈高华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95页。,强调科举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辞章为辅。与这份诏书同时颁行全国的,还有由中书省向仁宗上奏的《中书省奏准试科条目》(或称《科举程式条目》),此份公文由仁宗批准的时间是皇庆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这份文书对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有更加明确的阐述:“为这上头,翰林院、集贤院、礼部先拟德行为本,不用词赋来。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等都不用,止存留诏诰、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才去也。”(47)《中书省奏准试科条目》,转引自陈高华:《元朝科举诏令文书考》,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1辑,第155-156页。应该说,在理学家的推动下,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政策得以确立。
虽然元朝科举长时间的停罢,确实打击了部分士子读书应试的积极性,刘诜对此现象的描写是:“当时不知其乐,其后皆迁城,虽巷陌相望,然各缠家患世故,浮沉困耗,而少年英锐之气俱少衰矣。”但是,恢复
科举的消息公布后,“士气复振,咸奋淬以明经为先”(48)刘诜:《建昌经历彭进士琦初墓志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2册卷68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很快就掀起一股学习程朱理学的热潮。杨维桢说:“贡举法行,聘硕师教子,复出厚币为赏试,曰‘应奎文会’。”(49)杨维桢:《故义士吕公墓志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2册卷1317,第64页。江浙行省的慈溪、鄞县甚至出现了士子“于朱子之书,莫不家传人诵”(50)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7《送慈溪沈教谕诗序》,四部丛刊初编本。的景象。一些努力学习程朱理学的士子往往能比较迅速地考取进士,比如建德的刘环翁自幼从名师学程朱理学,精通《春秋》,后来乡贡取中,正好遇到科举停罢,但是他“执其业不少懈,若有待者。逮今天子更新庶政,科举复行,遂以至正四年再荐于乡,登五年进士第,授将仕郎、建德录事”(51)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7《建德录事刘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不仅汉族士子要学习程朱理学,蒙古人、色目人也不能例外,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时,第一场试经问五条,要求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52)脱脱等:《元史》卷81《选举志一》,第2019页。。正是在科举的指挥棒下,程朱理学成为包括蒙古人、色目人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学习的知识,官学、私学、书院也将程朱理学作为主要教学内容。
元朝最高官学国子监的中斋“据德”、“志道”专门录取蒙古人、色目人,上斋“时习”、“日新”录取汉人,其教学内容即是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虽然是为家塾制定的,但元朝国子监将其颁发给全国各地的郡县学校,因此家塾、郡县学校的教学内容可以在这份文献中得到反映。程端礼规定,士子年满十五岁即开始“大学”教育的学习,主要课程为朱熹的《四书集注》,学习顺序是“《大学章句》、《或问》毕,次读《论语集注》,次读《孟子集注》,次读《中庸章句》、《或问》,次钞读《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钞读《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读本经”(53)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1,姜汉椿校注,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41-42页。。他希望士子们通过三四年时间的潜心学习,掌握程朱理学,这是“终身之大本”,然后学习科举应试的作文之法。书院也不例外,其教学也是为科举服务。苏天爵在惠宗至正七年(1347)所作的《新乐县壁里书院记》中云:“方今朝廷开设贡举,三年大比,旁求硕彦,聿修治平。他时壁里之士,将有经明行修以应有司之选,则中国文明之盛,人材长育之多,而远近皆有所则效焉,非徒以称观美而已。”(54)苏天爵:《滋溪文稿》卷3《新乐县壁里书院记》,陈高华、孟繁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4页。
元朝统治者通过实行科举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后,各族士子对其的认同程度也明显提升,这无疑会对促进元朝的民族融合、实现“华夷同风”产生直接影响。
总之,无论是从对中国科举制度建设的贡献、对政治模式转变的推动,还是从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文化融合的作用来看,辽朝科举的影响力小于金朝科举,更远远小于元朝科举。元朝科举虽然实行时间短,但是其在制度创新和对后世的影响方面远远大于辽朝和金朝。而辽金元科举的地位虽然不如唐宋科举,更无法与被视为“抡才大典”的明清科举相提并论,但是从其制度创新和影响范围的角度而言,辽金元科举是中国科举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