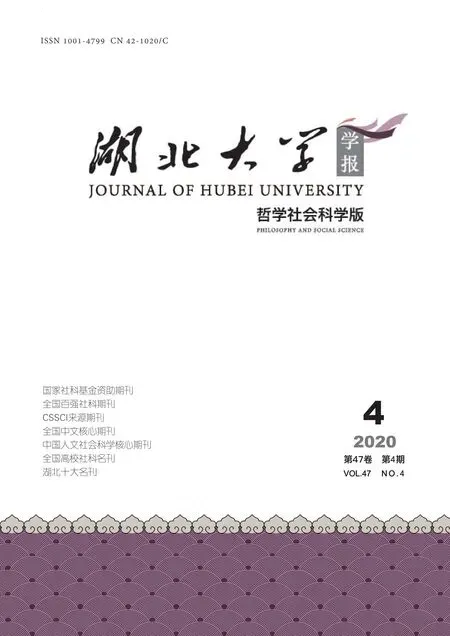论数码媒介技术的物质性
——以“数码人类学”为中心的考察
2020-01-11王眉钧
张 进, 王眉钧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在西方渐成热潮。1987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的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出版了其物质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MaterialCultureandMassConsumption),并担任了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物质文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持续致力于物质文化研究,并向现代生活的诸多方面拓展其研究触角,其研究成果产生了世界影响。2009年,他开创了“数码人类学”研究生必修课程。2013年,他和希瑟·霍斯特(Heather A.Horst)主编的《数码人类学》(DigitalAnthropology)一书在英国出版。研究者认为,“数码人类学”是物质文化研究的大树上长出的新芽,而这棵大树则深深扎根于英国人类学传统的土壤中。在研究对象方面,该著作从数码人类学与社会、政治和设计等大的面向上延伸出了诸多具体研究方向。在方法论层面,它所采用的仍然是马林诺夫斯基确立的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这意味着“人”才是数码人类学的最终指向,即“数码人类学”聚焦的是数码科技之下的人的文化交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数码人类学”的研究旨趣是数码时代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的社会交往,但是它依然在物质文化的论域当中,并且以后者作为方法和工具来研究社会和文化交往。数码技术的发展变革,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使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突出,由此孕育而生的媒介文化和社会关系逐渐变成当代人日常生活的景观,而数码科技作为一种“人造物”和中介,反过来塑造人。物质文化的研究方法决定了数码人类学的核心内容建立在物质性的基础上,即通过数码技术这一“人造物”来认知社会关系,进而认识处身其中的文化。数码人类学的这一特点无疑沿袭了米勒的物质文化研究传统。如同米勒在《数码人类学》中所言,“数码,和其他物质文化一样,不仅仅只是衬底,而是逐渐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组成部分”(1)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页。。数码技术变革中的人类学凸显了物质文化研究对社会实践中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关系的现实关怀,聚焦于当今数码时代物质世界的社会化进程中所显示出的物的秩序。因此,“物质性是数码科技的根基”(2)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第33页。。通过对物质性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数码媒介技术的本质特征。
一、从物质文化到数码媒介的物质性
米勒在一部研究物质性的著作中明确了物质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即理解世界如何造人以及人如何造物(3)Daniel Miller,Materiality,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p.2.。20世纪80年代米勒在剑桥大学考古系学习时,剑桥大学考古专业深受安东尼·吉登斯和布迪厄理论的影响,这也让米勒之后在伦敦大学学院任教后“采用了吉登斯的‘物品域’(object domains)和布尔迪厄的‘习性’的概念来分析文化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4)尹庆红:《英国的物质文化研究》,《思想战线》2016年第4期。。20世纪90年代,英国考古学和人类学在物的研究上分道扬镳,尽管两者都关注人工制品在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的历史和文化,但是考古学侧重史前史历史语境中的人工制品,而人类学则聚焦当代的、活着的历史语境中的人工制品及文化特点。
米勒在《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中指出,他试图打破人与物之间长久的二元对立,从人与物“之间”建立一个非二元的模型,这个关系的建立过程是动态的,通过“对象化”(objectification)进程来实现(5)丹尼尔·米勒:《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费文明、朱晓宁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7页。。在米勒看来,切入物质性的理论内涵有两种路径,“第一种仅仅是作为文物或者人工制品的庸俗理论;第二种是完全超越主体和客体二元论的理论”(6)Daniel Miller,Materiality,p.3.。米勒强烈反对把物质文化的研究范围框定在单纯研究文物或人工制品的范围内,他多次强调应该研究当下的、时代性的由物及人的物质文化的特点。米勒对物质性的定义远远突破了作为文物或人工制品的“代理人”角色,物质性还包含了我们多元的文化,是物质文化的整体性的维度。这是因为物质世界是文化造物的结果,我们所见的物质秩序的呈现并不简单,包括了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的所有关系共同的作用。
米勒提出数码人类学的六大基本原则:“数码对文化辩证属性的增强”、“数码科技没有抵消人性”、“整体性研究原则”、“文化相对主义”、“数码的变化性”、“数码的物质性原则”。从中显示了米勒对数码人类学关键问题的基本判断,其中最核心的原则是“数码的物质性”。
米勒的陈述不禁让人们产生疑问,为什么要将物质性问题作为数码人类学的关键来研究?其实米勒对物质性的强调贯穿了他的物质文化理论。数码科技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的产业,数码的发展为变革提供了契机,关注数码也是关注人类的生存现状。所以数码人类学只是与当今时代特征对接时的注脚。事实上米勒对物质性的关注远远早于数码这个起点。在人类历史进程当中,对佛教、印度教等宗教来说,神学一直集中地对物质性进行批判。他们都宣称精神层面的智慧是真实事物的基础,而物质世界是虚幻的,真理在人们的头脑当中,然而矛盾的是所有关于物质形式的丰富表达都是为了超越对物质生活本身的依恋。米勒认为,即使到了自觉的现代信仰体系中,物质性的问题依然是大多数人对世界立场的基础,因为“人性被视作把物质资料转变为生产过程后的产品,资本主义打破了人们通过创造物质产品从而创造自己理解的循环,相反,商品被拜物教化,反过来压迫制造商品的人”(7)Daniel Miller,Materiality,p.2.。物质性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人性的悲观态度,那就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商品,人性也随之慢慢丧失。而数码时代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似乎数码在人性面对本真和虚幻之间,又竖起了一道屏障。数码与人类现代生活如此交融,甚至很难批判性地思考数码带给人们的秩序感。米勒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秩序的形成,恰恰是理解物质文化中物质性的关键。对此,米勒认为是两个来源启发了物质文化理论的建构(8)Daniel Mliier,Materiality,pp.4-5.。
第一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的框架理论(9)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6,pp.21-40.。“框架”可以分为框架和条目,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证,其中框架是条目的组织类型,而条目是人们具体活动的顺序。戈夫曼认为人们的大部分行为是由期望构成,即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其对情景的定义。那么框架如何形成?在戈夫曼看来,框架一方面来源于个体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来源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和戈夫曼一样,米勒也认为人们的行为由其对语境的认知框架来决定,换言之,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使用特定的阐释框架来理解日常生活。为此,米勒举例说明人们不会去拯救一位舞台上正遭受“暴力”的女演员,因为事件的背景告知我们,那是表演而不是真正的暴力。人们正是通过对社会角色、社会情境的诠释,来调整在特定行动场景中自己应有的交往行为和表现,使日程生活井然有序。米勒试图说明框架理论基于象征互动视角,解释了人们如何在某个特定时间和社会背景下用特定期望去规范行为。
第二个来源是艺术史家贡布里希(Gombrich)关于秩序感的论述(10)E.H.贡布里希:《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范景中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17-18页。。贡布里希除了关注艺术品本身,他更关注艺术品的框架。贡布里希认为艺术品的框架的作用很重要,符合语境的框架可以框定一件艺术品,譬如面对一幅带框架的绘画作品,人们不会注意到框架本身,但是我们也能意识到,如果框架本身不符合语境或不合适,人们会立即注意到这是个框架。总而言之,框架不能独立地表征艺术品的任何特质,但是却能引起对艺术本身的特殊关注,框架赋予了人们识别和鉴赏艺术的秩序感。
米勒之所以特别强调戈夫曼和贡布里希的理论对物质文化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启发,是因为这两个理论让他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对物质性的阐释有了思想基础。为此米勒在其早期不止一部著作中对来源于戈夫曼和贡布里希的理论进行了创新拓展,并结合其人类学田野调查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理解物质性的重要理论——“物的谦逊”(the humility of things)。
何谓“物的谦逊”?简单来说,当物越日常性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参与我们的生活实践,我们就越无法觉察出其作为物质与运行机制的过程,也即人们常说的“熟视无睹”状态。米勒用大量的研究实例来说明“物的谦逊”不但出现在如同“牛仔裤”这种普通物的研究中,同时也出现在数码科技领域。当数码科技越高效,人们越觉得稀松平常,“只有在这个机制无法正常运作,或无法满足需要的时候,人类才惊觉它的存在”(11)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第34页。。这表明,理解数码媒介的物质性需要厘清物质文化与数码科技之间的关系,“物的谦逊”理论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数码科技被掩盖住了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往往是像数码科技这种积极参与了人类生活并与人进行互动的物,才是我们研究的聚焦点。数码媒介因人而起,又作用于人,所以数码媒介对人的社会身份的构建、维持和转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也充分说明物质性使物质文化和数码科技之间建立了联系。
二、数码媒介物质性与数码科技的关联向度
如上所述,尽管物质性是连接数码媒介和物质文化的关键点,也是数码科技的根基,但是如何理解数码媒介的物质性,却面临着跨学科研究的障碍以及对“物”的界定问题。米勒在研究物质文化时,具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那就是把物的研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拜物教等问题的批判性辩论中解救出来。他指出,对物质文化的研究的恐慌来自于对物质性毫无根据的负面渲染,他说:“目前,对于物质文化的兴趣更多地是在一种恐慌的语境中形成的,这是一种对物正在替代人的位置的恐慌。”(12)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01页。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伴随着数码媒介技术发展,物质性的讨论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具有无法回避的重要性。对数码媒介物质性的批评和攻击,很大程度源于人们粗暴地认定数码媒介物质性过于抽象和不可捉摸,不仅会把人引向更加隐蔽的异化之路,而且依然没有解决心灵与物质对立的局面。对此,米勒坚信数码媒介技术的特点之一就是融合原生语境和再生语境,换言之,数码媒介不会让“虚拟”的数码世界与现实世界分道扬镳,相反,线上和线下的人生都具有本真性(authenticity),数码媒介各个面向的物质性都具有明显的实践倾向。
首先,数码媒介具有秩序层面的物质性。数码媒介物质性的关键点之一是数码媒介呈现出的物质秩序。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宇宙和万物都按照分类体系建立了其运行秩序,因此他主张:“物应当置于系统性的文化规则和文化密码所运行的特定环境中去理解,这样才能传递出物在具体语境下的意义。因而,物具有适宜的文化位置。”(13)伊恩·伍德沃德:《理解物质文化》,张进、张同德译,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75页。米勒对物质秩序的理解与布迪厄、拉图尔等学者的观点一脉相承,即物质世界就是人工制品的聚合,人工制品在本质上是文化造物,所以物质世界包孕了所有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所依赖的物质性规则秩序,人性正是通过物质世界社会化的过程得到彰显。
然而,我们要注意到,当数码媒介的物质性始于0和1的二元交替和二进制代码的新技术时,就表明数码媒介本身是一种物质存在。福柯对秩序的讨论或许能为我们理解数码媒介的物质性秩序提供启发。在福柯看来,秩序的确立无需参照外部单元,人们无法认识“处于单独本性中的”物之序,但是通过发现最基本、最简单的事物,并由这些事物传递再发现,人们便能做到由简到繁、由浅到深地认知事物。对此,他解释道:“凭着秩序作的比较是一个简单的活动,这个活动借助于一种‘完全连续不断的’运动,使我们从一个词项过渡到另一个词项……第一个词项是一个性质(une nature),人们就能拥有该性质对其他所有词项的直观;在这些系列中,其他词项依据那些不断增长的差异性而被确立起来。”(14)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56页。如果“虚拟的”线上世界是福柯所谓的“词”,对立于线下真实场景的“物”,那么词与物显然不能直接相互还原。事物被镶嵌进入了时间的流动中,根据进化系列中授予的位置而区分开来,数码媒介的秩序正是基于二进制编码这种新的知识体系的最基础的性质,凭借二进制编码的差异性结果,在数码媒介技术领域的不同方面快速增长,如互联网、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数码媒介的秩序凸显了它自身的优点,特别是数码产品容易再现和共享。这赋予了数码媒介特殊功能,即能够凭借其秩序实现线下静态物所不能呈现的线上虚拟物的动态性。
其次,数码媒介具有内容层面的物质性。不同的数码媒体平台影响着受众不同的使用习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理解数码媒体,必须从数码媒介传播的内容出发。在数码媒介出现之前,媒介的传播形态主要分两种:一是大众传播,如广播、电视、报刊等以“广告天下”的覆盖方式实现传播;二是以二元传播的P2P的形式实现沟通,如电话。数码媒介融合了这两种传播方式,并呈现出新的特点。米勒从社交网站以及艺术理论的研究实践中发现,网站有着自己的隐性受众群体,“正如同好像艺术品,是专门为某一些浏览者所量身定制的诱惑圈套,而对那些非目标族群,这样的圈套则显得索然无味”(15)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第35页。。这并不奇怪,在日常浏览网站的过程中,网站会根据浏览者的偏好而推送相关内容,这表明,数码世界在拓展虚拟世界的同时也拓宽了物质文化的研究范围,让具有身体感的数码媒介物质属性介入每时每刻的日常生活当中。
受到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吉尔的艺术与能动性(agency)理论的启发,能动性的探讨也被纳入物质性研究的范畴。米勒认为数码媒介的网络正如同吉尔所谈及的艺术品。吉尔认为艺术品在生产、流通和接受过程中都充分表征其自身的能动性特点,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艺术品不是孤立的人工制品,而是人类文化情境中的能动者。他反对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研究物质文化,原因是艺术品的审美特征和意义阐释不能脱离其语境而存在,所以“艺术品的本质就是嵌入社会情境中的一种功能”(16)尹庆红:《艺术人类学:从符号交流到物质文化研究》,《民族艺术》2017年第2期。,具有介入参与者的精神活动并协调社会关系的能动性作用。吉尔的艺术与能动性理论充分说明,主体和客体关系是双向辩证的,同时具有“人的造物”和“物的造人”特点。在这一点上,米勒与吉尔的观点如出一辙,米勒认为数码媒介在内容层面的物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消费者的网络浏览者在消费和获得信息的同时,也积极地参与了数码媒介内容的分配过程;二是网络浏览者或消费者利用视觉的物质性(visual materiality)处理数码媒介内容时,不仅表征了自我构建和认同的过程,也构建了对他者的理解。数码媒介内容的物质性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建构中被表征出来。
最后,数码媒介具有语境的物质性。语境一直是物质文化研究对于物质性争论不休的议题。物质文化理论有这样的主张,就是让物为自己言说,但是对于人类学家而言,物的意义是通过社会语境赋予的。所以物是在去语境化还是在语境内解释,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阿多诺在《棱镜》中这样叙述“去语境化”的物:“德语中的‘博物馆’一词有令人不快的含义。它描述了观察者不再与物有互动联系,这些物正在死亡的过程中。物的存在价值仅仅是处于对历史的尊重而非基于现实的需要,博物馆和坟墓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语音相似,博物馆就像是艺术品的祖坟。”(17)Theodor W.Adorno,“Valéry Proust Museum”,in Prisms,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Cambrige:The MIT Press,1981,p.173.阿多诺对去语境化的物显然非常不满,他尖锐地指出了死气沉沉的物带给人的不适感。这种不适感源于物与人及语境生硬的割裂。如果这昭示了物与人和环境关系的一种极端联系方式,那么另一种极端方式就是人被物牢牢牵引和束缚住,也就是从马克思到后来法兰克福学派不遗余力所批判的“拜物教”。
为了避免两种极端情况,人与物或心灵与物质的关系似乎需要遵循一个微妙的度。人类学家提姆·英格尔德(Tim Ingold)认为物本身就有自主性,物质文化研究的核心不应该是对物的物质性和具体语境的关注,而是对物从制造到存在的整个“史”的意义上的关注。米勒认为英格尔德忽视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人工制品时代,而非自然化的时代,语境的研究重心就是揭示物、人、环境三者之间交错的社会关系。不论以何种视角看待物的语境,都对数码媒介在语境面向的物质性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对于数码媒介科技辐射广度和深度的过分夸大和吹捧,让数码媒介的语境呈现出了更加复杂的特点。本文立论的前提是,数码媒介的确具有去空间性的特征,但是结合社会实践生活来看,数码媒介的语境具有高度的物质性。
数码媒介语境的物质性体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在空间(space)层面,数码媒介通过物的网络联结了物理空间,而且高度灵活的移动性特点也让它确立了主体间性的接触方式。数码媒介与空间结合的技术颇具代表性的是全球定位系统(GPS),GPS是典型的“时空物”(spime)(18)“时空物”(spime)一词是科幻小说家、设计理论家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在《塑造》(Shaping Things)一书中创造的新词。在《数码人类学》第四章《地理媒介:数码文化中的空间新主张》一文中,作者莱恩·德尼克拉(Lane DeNicola)认为,时空物可以理解为依托时间和空间的抽象人造物,其生产、交换及消费过程都历时地镶嵌于具体时空结构中,旨在说明人与物在语境关系上的革新。,GPS技术实现的同时也展示了一个庞大的视觉数据库,其技术研究者和技术使用者凭借技术本身与物理世界建立了亲密联系,所以类似于GPS这样的“时空物”“不仅意味着人对空间的意识,同时还意味着‘物’对空间的意识”(19)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第36页。,实现了物、人、环境的错综复杂的对话,数码媒介不仅没有使物质实体的真实空间消亡,相反却使空间烙印更加深刻。
在时间(time)层面,数码媒介通过人们在数码领域的实践活动,叠合了时间的概念。正如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所言,较空间而言,社会理论对时间更加偏爱,数码媒介让象征时间和自然时间的边界更加模糊,因为数码媒介时间“同时既是地球时间、生物时间、钟点和年历的时间,又是自然的和社会的时间”(20)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6页。,数码世界的各种角色扮演游戏使人穿梭于现实与游戏当中,这引发了不少批评。对此,米勒研究指出,网站的功能不能局限于社交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在其中安家。这些角色扮演游戏就像米勒研究的日常生活中的物一样,它们的指向不是虚拟而是现实,角色扮演游戏在时间的层面,依托数码技术让反馈变得更加快速(21)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第36-37页。。贝纳尔·斯蒂格勒则用“事件化”过程来进一步阐释模拟与数字技术凭借其筛选功能,叠合了真实与虚拟,他认为,“模拟与数字技术把输入的(在场的)真实效果与实时或直播合并,开启了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对时间的全新体验……那么这种对时间的全新体验也许就是历史时期的出口”(22)贝纳尔·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 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不难看出,除了在空间与时间面向所表征出的数码物质性之外,在具体微观语境层面也广泛地存在表现数码物质性的丰富多样的物质实践活动。
数码媒介的物质性生动、活跃地体现在快速高效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中,这不禁引发了人们对数码惊人速度的惶恐不安,因此数码媒介在平衡具体与抽象事物的同时也遭到了误读和批评。最典型的刻板印象是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数码传播的是一种非物质,换言之,数码形式是一种非物质性的(immaterial),这一认定引发了广泛的问题。然而数码人类学作为物质文化研究中延伸出的方法,其关注点在于物而却不囿于物,人如何造物以及物如何造人的文化过程才是物质文化研究的重心所在。数码媒介能让我们更加切身地感受到速度、动态的世界以及文化的活力和多样性,途径之一便是通过我们的消费与文化领域相关的爆炸式增长的物质产品。这些物质产品包括以数字形式展现的、在线的产品,它们是文化的表现,而“文化也不是一个存在于个体之外的静止的客体,而是一个建构性的主体‘对象化’的实践过程,从而实现社会的自我再生产”(23)尹庆红:《艺术人类学:从符号交流到物质文化研究》。,这表明数码媒介在秩序层面的物质性让线上和线下的世界获得动态的互通,事实上线上和线下无法被清晰地分开,所以数码媒介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称为“非物质”。
三、数码媒介物质中介功能的矛盾性
物质性和人性之间的辨析是物质文化研究长期聚集的重点所在。“媒介之网紧紧包裹着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所感知的全部世界都由媒介提供的信息所打造,人成了悬挂在媒介之网上的动物”(24)张进:《活态文化与物性的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当今学界充斥着对数码的批评,认为数码让人类的本真性慢慢丧失,人性减少或降低,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数码作为一种“中介”的负面效应。《数码人类学》开篇就反对这些判断:“在数码的世界里,不仅人还是人,而且,数码为人类学提供了新途径来理解人何以为人。”(25)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第5页。米勒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数码媒介这种新兴技术,但是他从未停止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事实上,对数码媒介技术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一种“预设的恐慌”——冰冷的、无感情的、充斥着各种不平等权利结构的数码媒介会通过其“中介”性质去吞噬人性。换言之,人们对新兴技术的惶恐不安都源于对技术与人性关系的悲观态度。
其实这种悲观论调由来已久,技术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会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成为谈论的焦点。本雅明曾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阐述对技术的看法,那就是通过大量的复制,传统艺术逐渐式微,这集中表现为“光韵”的丧失。何谓“光韵”?概括地说,“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26)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87页。,换言之,“光韵”是一种包孕于艺术品的意境和弥漫在艺术品上的韵味。本雅明认为“光韵”是神秘的、模糊的但又能直击心灵的一种吸引力。他举例说明电影成了机械复制时代的代言者,电影在快速传递信息的同时,“光韵”也随之消亡。“光韵”充分表现在艺术品的本真性上。追求本真性是本雅明艺术批评的最高标准。遗憾的是本雅明并没有看到现代的科技已经让机械复制发展成为数码复制,尽管“本雅明对技术带来的新形势与新媒介持欢欣鼓舞的态度”(27)张进、姚富瑞:《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物质媒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然而不变的则是人们对本真性从始至终的追寻以及对丧失本真性的担忧。马歇尔·麦克卢汉也同样哀叹:“这是忧虑的时代,因为电力技术的内爆迫使人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它完全不顾及个人的任何‘观点’。”(28)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6页。
一方面,面对数码媒介,人们对人性麻木、减弱、丧失的担忧源于人们对本真性的追寻。本真性要求如实、客观地反映物及其社会关系原貌,暧昧不清、混淆认知是追逐本真性的绊脚石。当数码媒介作为一种介质、中介起沟通作用的时候,追逐本真性的路径上介入了数码技术这个威胁人性的异质物,数码媒介既抽象又快速增生,人和物似乎变得不真实了,人很难及时跟进数码媒介技术的发展,这反过来也导致人性异化,从而引发了人们无尽的担忧。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其《赛博格宣言》(ACyborgManifesto)中传递出人与机器、人与自然的界限日益模糊的信息(29)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in Joel Weiss,Jason Nolan,et al.,eds.,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Heidelberg:Springer Netherlands,2006,pp.117-158.。布鲁诺·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里明确指出,与技术联袂而行的现代性制造了一种双重分裂:“一方面是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分裂,另一方面是天堂与尘世之间的分裂”(30)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页。。然而,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称哈拉维和拉图尔的观点实际上让这种“技术威胁论”从“敌托邦式”的修辞走到“敌托邦”对立面的表现。他没有为“人性被技术吞噬”这一论调辩护,因为“我们与技术的牵连成了我们的存在无法超越的地平线。我们以某种几近无差别的‘赛博格’本身的形式与技术结合了起来,再也没有反对技术的可能。终止顽固抵抗并彻底拥护技术的时刻已经到来,应该给予技术以进一步良性发展的时刻也已经到来”(31)安德鲁·芬伯格:《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高海青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62页。。米勒认同芬伯格对技术的态度,他补充说明,没有理由认为人们坐在一起的沟通交流就是原汁原味、直达本真性,而通过媒介交流就不是纯粹直接的了,因为在人类学中没有纯粹的直接性,即便是两个人面对面的语言交流,在文化层面都是曲折的(32)Daniel Miller,Tales from Facebook,Cambridge:Polity Press,2011,pp.23-26.。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持技术恐惧症论调的人,预设了新技术意味着离自然越来越远,人性会越来越异化,但是在现实中,他们却需要革新旧技术而成为真实的自己。
另一方面,数码鸿沟动摇了不同地域、国家的人平等地享有数码媒介科技带来的发展权,尽管“数码鸿沟”“这一概念已经逐渐被‘数码不平等(digital inequality)’与‘数码共融’(digital inclusion)的概念所取代”(33)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第256页。,但是它强化了人们对数码科技带来的一定是优越的、不可替代的武断认定。这并不奇怪,数码鸿沟不仅反映在技术方面,更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牵制能力,因此各国都在抢占数码技术的最先发展权,数码技术已经带来了人们在生活工具和生活形态的双重变化。柏拉图在《理想国》的洞穴故事里提出的哲学思辨模式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对知识的划分,那就是抽象的知识优于具体的知识,沉思式的真善美的知识优于与身体、物质相关的知识。而数码技术显然被划分进了抽象知识领域,因此被赋予了优先地位。值得思考是,这种划分其实依然反映了“身—心”、“精神—物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米勒认为这种论调毫无新意且相当乏味,颇有“矫枉过正”之嫌。因为每当有新技术崭露头角的时候,人就不可避免地沉浸在怀旧的伤感中,沉浸在失去的哀叹与伤感中,而这种怀旧的伤感很可能对过去进行了夸大的浪漫化描绘,其中的逻辑是过去的技术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与此相对,现存的技术则是通过削弱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覆盖和否定过去的技术而出现。米勒不主张一味地回头看,同时认为这种悲悯和担忧站不住脚,因为只要是人类能力之所及的技术都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不管是过去的(如农耕技术)、现在的(如社交媒体)还是未来的(如虚拟现实)技术时代。他提出“获得理论”(the theory of attainment)(34)米勒和Jolynna Sinanan为2012年10月9日至23日召开、由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EASA)主办的第41届电子研讨会撰写了会议论文“Webcam and the Theory of Attainment”,专门探讨“获得理论”(the theory of attainment),www.media-anthropology.net。来诠释人性的概念,大意是人总会接受新技术,尽管需要时间,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人不会被技术异化。所以问题并不是出在新兴技术上,而是在我们对人性(humanity)这个词的界定上,以及出现在我们用来探讨这些技术的哲学上。
当然,米勒的判断不无道理,如果否定目前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特性,那么好像过去的人性就是人的天性,可是过去的人性依然要面对过去的技术。米勒质疑后人类和赛博格的可能性,他主张我们要革新关于人性的哲学思辨。在这一点上,拉图尔和米勒都试图弥合主客二分,把研究视角拉回到物与物的联系上,把重心放到物自身的能动性,使物被提升至与人一样的高度来研究。如果说拉图尔是以打破二元对立的现代性为起点,在主体和客体、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寻找一个接触带(contact zone),在这个接触带上主体与客体、人类与非人类构成杂合体,同时具有主体和客体的性;那么,米勒比拉图尔更进了一步,他认为从人类学的视角而言,这种忧虑与其说是对技术和数码媒介研究对传统人类学民族志的挑战,不如说是一种馈赠,原因在于数码媒介的优点之一就是置身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相互交流,不会因为被研究而显得不同,反映的是本真的生活状态。人们在网络上的社会联系容易被记录,这也给田野调查带来了便利。媒介不会中介人性的原因是数码媒介使用者能够任意切换平台,即,是数码媒介传播的内容而非平台这种形式起决定作用。显然,米勒的论述实际上站在了数码媒介良性发展的思考维度。
余论:数码媒介物质性的流动性
长期以来,媒介研究透出一种深层潜在的研究权重,那就是数码媒介技术不过是人的附属和“延伸”,真正的研究重心还是人。这种习以为常的媒介研究权重实际上发出了非常封闭的讯号——弥漫着人与物(技术物)、技术与文化二元对立的观念。毋庸置疑,这对于数码人类学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与此同时,数码媒介技术作为一种技术物,很难让人们像抽丝剥茧那样与实实在在的物形成联系,因此数码媒介技术的物质性似乎是个过于抽象和暧昧的概念,与其所置身其中的文化形成了一种难以透彻洞悉的关系。数码人类学作为物质文化研究的分支,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去调整和打破人与物的二元对立关系。然而,现实世界中的人又总是被数码的世界所覆盖,数码设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技术伴侣,人在很大程度上被技术物“撩拨”、控制甚至形塑,这类媒介技术物质性所引发的思考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回响。
一方面,数码媒介技术不仅是技术的拼合,而且是混融的“复媒介”(poly media)(35)“复媒介”是Madianou和米勒提出的概念,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媒介的选择是一种复合的选择,会参考其他媒介以及当地地方性文化等因素,媒介不仅仅是沟通工具,媒介的选择还关涉了道德和情感责任以及社会性和家庭性因素,对媒介的选择使用严格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参见M.Madianou,D.Miller,Migration and New Media: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Polymedia,London:Routledge,2012.。因此,不同的数码媒介技术,其物质性是通过复合叠加并且综合文化、社会、道德及情感等因素而发生作用。技术物如此快速地融入人类日常生活,这不仅仅受到文化规范和个体性的双重影响,也取决于技术物本身的物质性。尽管文化规范在整体层面上发挥着监督和道德约束作用,然而技术物的物质性却让“普通”乃至“稀松平常”成为数码人类学的文化解释模型,从而实现了平等的比较和研究。数码物质性不会单独出场,它总是被赋予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多重媒介技术物质性构成的复媒介生态环境,给予使用不同媒介的人多元化的身份,人们使用不同的媒介,意味着扮演不同的身份。这种多元身份显然不能单纯剥离为“线上”和“线下”(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更无法通过物质文化理论所倡导的突破“线上”“线下”的界限就能够解释和还原。从这个角度出发,“复媒介”的物质性所携带的技术要素、社会要素和情感要素就被选择性地逐出数码人类学的解释模型。举例来说,当人们习惯性地在数码媒介设备上搜索信息时,由大数据计算推送来的信息无形中就构成了一种不露声色的控制和操纵。人们在数码媒介设备上玩一次付费游戏,之后会有大量相似的游戏推送接踵而至。大量生活实践表明,数码物质性发挥的作用非常复杂,根本不能简单还原为物质文化研究所主张的“普通”的文化解释模式。数码媒介技术与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数码媒介物质性研究需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张力,才能够揭开那些被遮蔽的内容。
另一方面,伴随着数码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学术界对于未来人工智能的各种声音,如何判定和解释数码媒介技术物质性与人性之间关系的问题,一直是数码人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而且也是贯通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常新的学术话题。物质文化研究有从传统哲学中汲取理论资源的偏好。作为其重要理论资源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给物质文化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启示——主体和客体在发展中所经历的分离过程原本蕴含着的积极的主客互动。然而,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却剔除了主客交融的“积极关系”。因此,面对以物质性为武器去批判人性的批评传统,数码人类学始终坚持物质文化研究所主张的物质性与人性的“不相关关系”,竭力反对以物质性为承受人性评判的道德砝码。然而,数码媒介技术并不能被视为一个纯粹的技术维度,原因在于技术物与人的分离感越来越难以保持一个适当的尺度,人甚至难以摆脱数码媒介技术的物质性去实现自我认同。马克思主义学派及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曾把商品与人性尖锐对立起来。进入web2.0时代,媒介技术让电子货币渗透到各个文化领域,对商品的消费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灵活、自由与快速。数码媒介在公共化和私人化的两条路径上联袂前进,并行不悖。物质性和人性的探讨已远远不能涵盖“复媒介生态”的重要议题,后者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媒介技术物质性与情感体验、娱乐等内容深度结合,自媒体的盛行为感性的宣泄提供了一个便捷快速的出口,个体的差异性的表达先行于文化的差异性的表现。数码人类学遵循文化相对主义而强调地方性和本土性的概念,突出了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而数码媒介技术无疑是对地方性和本土性经验的一种解构甚至重组,原因在于媒介物质性不再沿着理性的切线谨慎前行,感性化、娱乐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让媒介物质性总是处于“流动”和“摇摆”之中。
总之,从人类学研究辩证立场来看,数码媒介如同硬币的两面,利弊共存,需要谨慎辨析。马克思主义批评视域中,数码技术发展与物质生产水平息息相关,先进的数码技术无疑能够给人类生活带来福音。然而,人们对于技术的焦虑也从未消除过,数码技术物依旧以“幽灵般的”性质更加隐蔽地遮蔽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拜物教导致的阶级差异并未消除,甚至会用具有迷惑性的面具维持社会结构,麻痹人们的批判意识。米勒深谙马克思主义“商品拜物教”理论,面对传统批判路径,他致力于把数码技术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解救出来——数码媒介不仅仅是一串数字,而更多地是作为日常生活的沉淀,他为人们反躬自省数码技术提供了别样的思考路径。其数码人类学解释模型从规范性缩减到普通性,意味着人乃至人性并不是一个恒常的普世判断,而是需要伴随着文化的记忆被重新评判。若如米勒所言,数码技术的内容在重要性和影响力上是超过其形式的,那么如何对待基于数码媒介技术诸多的反面现象,如暗网、网络黑客、数码鸿沟等?显然,物质性的数码媒介对人性的影响并没有米勒设想的那么乐观,相反,数码媒介作为技术将会越来越深地以“普通”的形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人性面临着各种考验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