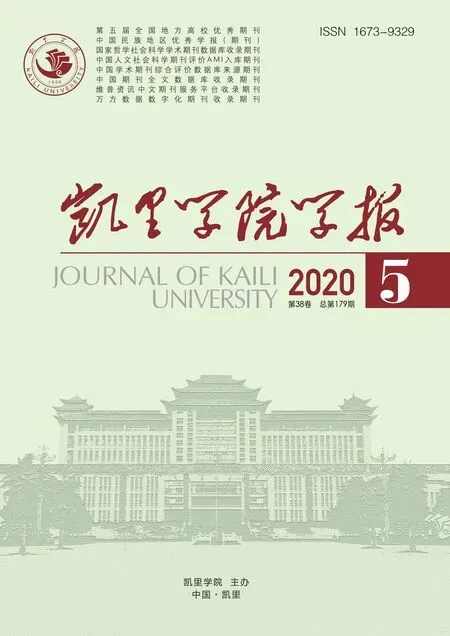欲望狂欢与党派脱冕
——论《都市女继承者》中的狂欢化世界感受
2020-01-09方冶文
郑 伟,方冶文
(1.凯里学院,贵州凯里 556011;2.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1681-1682 年是阿芙拉·贝恩创作的高产期,在这三年她一共有三部戏剧上演,分别是《圆颅党人》(The Roundheads,1680)、《漫游者·第二部》(The Rover,Part II,1681)以及《都市女继承者》(The City Heiress,1682)。以上三部戏剧都和当时的政治有紧密的关系,在贝恩的作品中可以归类为政治喜剧。我们可以把《都市女继承者》的故事分成两部分来看,一部分讲述的是爱情纠葛,另一部分是与爱情争夺纠结在一起的政治纷争。读者在阅读该剧剧本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阿芙拉·贝恩在表现主人公爱情的时候掏心费力,但是在表达政治态度的时候敷衍了事,仿佛是在例行公事完成政治任务。由此甚至造成了中心人物威尔第的顽劣品行与其莫名其妙的情场得意之间的矛盾,不由得让读者不解贝恩之意:要说她支持托利党,为何将威尔第描写成阴郁奸邪之徒?要说她反对托利党,为何又让威尔第一再取得都市女继承者们的爱情垂青?
阿芙拉·贝恩从未把写作剧本仅仅当做谋生之道,她认为剧场在公共空间可以发挥移风易俗甚至影响政治走向的重要作用。她在《都市女继承者》的开场白中不留情面地批评剧场观众: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重振朝纲,对于戏剧家来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你们对诗人们在舞台上针砭时弊的教诲置若罔闻,一如你们在教堂里无视牧师的劝诫。在这魑魅魍魉统治的时代,谁又能秉笔直书对之挞伐。在教堂的座位上你们鼾声如雷,在剧院里你们喝得烂醉跑来大声喧哗。一听说去教堂就眉头紧锁,来到剧院忙不迭眉来眼去,看能不能勾引上水性杨花的便宜货色。[1]9
从贝恩的描述看,复辟时期的公共剧场更接近于斗鸡赛犬等娱乐场所,甚至有许多观众将剧场当作了调情说爱的地方,难怪《都市女继承者》中出现了女主人公佳丽亚德宽衣解带与威尔第共进卧室的香艳场景。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的暧昧气氛形成共振,共同构成了17 世纪80 年代光怪陆离的伦敦剧场文化。罗伯特·马考莱提出了贝恩抵制反女权主义流俗,却在复辟时期的剧场取得了商业成功这一矛盾现象:“作为女性写作的先驱,贝恩在剧中歪曲女人合意的行为,嘲笑男性权威人物,揭穿浪漫的爱情。这些喜剧中充满怨恨的现实主义表明,贝恩和她的听众非常清楚地认识到17 世纪末社会对妇女的束缚。”[2]141他试图用该剧中嘲弄一切秩序的原初女性主义观点迎合了观众的粗俗喜好来解释贝恩的《都市女继承者》在商业上获得的成功。阿芙拉·贝恩在这个戏中将贞洁和自律这些在莎士比亚喜剧中对女性的要求完全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对于爱情和婚姻的讽刺和嘲弄。罗伯特·马考莱虽然在文章中对于贝恩在17 世纪晚期戏剧舞台上的成功给予了经济收入上的细致考察以及合理的解释,但是没有结合贝恩戏剧美学上一以贯之的狂欢化世界感受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着力论述之处。
本文结合17 世纪英国社会史、妇女史以及政治史分析《都市女继承者》中贝恩在性别身份以及政治立场上犬牙交错的错位态度,试图在运用新历史主义方法细描历史细部的基础之上解释男性中心主义在该剧中若隐若离的缺席与在场。经历了克伦威尔共和国以及查理二世复辟之后的伦敦大众已经对于莎士比亚戏剧中构建的秩序——无论是政治体制上的君臣、还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抑或家庭之内的婚姻失去了坚定的信仰,因而不会在剧场中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观众一样有耐心地接受正统的说教。在王纲解纽、政事混乱这一大背景下,该剧时而美化、时而丑化被视为托利党人的花花公子威尔第,增强他的政治参与者身份,在政治立场上给予劣迹斑斑的男主人公情场得意以合理的解释,在女性主义思想上反思浪荡子这一复辟时期广泛存在的男性人物形象。下文将主要从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对此进行分析。第一,剧本对于男性的斥责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社会何以成为可能;第二,父权制的衰落在剧本中的表现;第三,剧本试图探讨将女性欲望同自由恋爱结合以情感自由主义对抗辉格党政治狂热以及托利党马基雅维利主义。进入复辟时期,英国社会经历了动荡的政治环境以及王权的衰落。共和国时期严肃的日常生活与复辟时期自上而下恣意放荡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性禁忌逐渐在公共生活中消弭,加之剧场观众对于近乎粗俗的荤段子的娱乐需求,上述因素均给予女作家阿芙拉·贝恩在她的剧作中使用“物质——肉体”等手法表现狂欢化世界感受以必需的社会空间。
一、欲望狂欢与狂欢化性别表演
在英国的复辟时期,私生活放荡的查理二世周围聚集着一群同样眠花宿柳的廷臣。查理二世不仅公开拥有情人,其私生子蒙茅斯公爵甚至一度为了继承王位,发动了举国皆知的叛乱。可见,复辟时期的两性行为并不遵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克伦威尔时期严谨的私德。浮浪的社会风气给阿芙拉·贝恩在喜剧中言说欲望提供了机会。欲望是人类由于想占有某种事物所产生的某种心理活动。《都市女继承者》中的男女主人公均表达了自己的身体性欲望与物质性欲望。
威尔第自称利用诡计实现对女性的占有。他对佳丽亚德夫人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故意以蔑视的态度冷落对方。他对于佳丽亚德夫人的追求源于对其身体的占有,因此才直言不讳地言说自己的欲望:“佳丽亚德夫人的美貌怎能掩盖不彰,尤其是她还遇到了一位像我这样可爱的爱情伪君子。沐浴之后,她的皮肤如百合花一样白皙,如水流一样顺滑,又如葡萄一样松软。她的表情傲慢,眼神里都是蔑视,却别有一番魅惑的可爱。这样的女人一旦热恋起来,那是何其温柔、睿智、淫荡,让人不由得神往。不管什么时候,斩获她的芳心都能带给我莫大的荣誉。说这些该死的废话没有任何用处,她整个人都是我的。”[1]14从威尔第的这段台词可见,他将佳丽亚德夫人当作自己欲望的他者对象,从而揭穿了男性话语中高贵爱情的真相。他使用了一系列的比喻形容女性的皮肤,充满了对于肉体的直观感受,这种大胆直露的物质—肉体描写在莎士比亚时期的剧本中是从未出现过的。巴赫金认为:“物质—肉体生活形象的第二和第一这两个方面,交织为一个复杂矛盾的统一体。这些形象紧张矛盾的双重生活,也就是它们的力量所在,是它们的高度历史现实主义所在。”[3]28尽管威尔第的粗俗语言对女人充满了不敬,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解构了文艺复兴以降崇高的爱情,这也是阿芙拉·贝恩在《都市女继承者》中以物质—肉体描写进行欲望狂欢书写的表现。
在莎士比亚的喜剧《爱的徒劳》以及《仲夏夜之梦》中,尽管爱情一开始不被男女主人公信任,但是历经波折,他们最终在神圣的爱情中得到了幸福。但是,阿芙拉·贝恩在《都市女继承者》中将爱情彻底解构,尤其是在以威尔第为代表的男性看来,女性不过是满足自己性欲以及实现财富自由的工具。浪荡子非但不掩饰自己的欲望,反而将其袒露无遗。威尔第与查尔斯的如下对话即反映了男性血脉偾张的欲望:
威尔第:我已经因为这个女人欲罢不能。这么一位风姿绰约的小东西堕入我这样的男人的情网是多妙的一件事啊。更重要的是她还这么有钱,查尔斯,我一定要占有她。
查尔斯:你怎能同时爱上两个女人?我和你一样的炽烈、奢侈、年轻、有钱,但我不能和你一样下流。敞开心扉地说,时间可以让人分开,但是爱一定要全心全意。[1]14
威尔第将佳丽亚德视为可以占有的物体,原因在于一方面她拥有美丽的外貌,另一方面她还有巨额财产。阿芙拉·贝恩在《都市女继承》中颠覆了以往戏剧中男女的经济地位。尽管最终威尔第赢得了富有女性的爱情,也如愿以偿继承了叔叔的财产,但是他没有自己赚取财富的能力。这个剧中以佳丽亚德夫人和夏洛特·盖特奥为代表的女性都有独立的财产。她们都属于脱离了父权制管辖的新式女性。如威尔第一样风度翩翩的男性也需要依靠自己的英俊外表以及所谓的机智才能博取女性的欢欣,这不啻翻转了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
阿芙拉·贝恩在重构男女两性权力地位的过程中使用了狂欢化美学中的诙谐形式以淡化自己揶揄甚至讽刺处于弱势地位的男性所引发的男性观众的拒斥情绪。巴赫金指出:“所有这些以诙谐因素组成的仪式演出形式,与严肃的官方的(教会和封建国家的)祭祀形式和庆典有着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原则上的区别。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3]6阿芙拉·贝恩在《都市女继承者》中表现的是迥异于莎士比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盛赞的崇高爱情。她在剧中不仅将男性的欲望暴露无疑,而且女性也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欲望。青年男女两情相悦的动力从爱情变成了赤裸的欲望。佳丽亚德夫人对于威尔第顽劣的浪荡子本性自始至终都有着深刻的认识,但是她还是身不由己地与其共度春宵,对这一情节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女性屈从了欲望的召唤。巴赫金认为:“他们决定了当代资产阶级文化人的面貌——斯泰纳主义者、伯格森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及其笃信和朝拜的三个神坛:幻术、本能和性欲。”[4]62威尔第的所谓爱情即是出于本能和性欲,而他用来控制女性的办法即是语言的幻术。佳丽亚德与威尔第相处一直存在激烈的思想斗争,最为典型的是下面的对话:
佳丽亚德:这是怎么回事?爱神指引着我让我靠近他。
威尔第:夫人,你要和我说什么,赶紧说,我还忙着呢。
佳丽亚德:那我在谈情说爱时也不必过于低调。你每天都过得逍遥自在,主要的工作就是拈花惹草。你成天什么都不想,除了勾引女人没什么事情可做,好像只有情爱事业才能让你获得永久的快乐,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威尔第:变的人是你,不是我。我犯了多么愚蠢的错误,竟然认为你也同样爱我。但是当我向你乞求行极乐之事,只要互相真心相爱的人都不会拒绝。你却拿荣誉将我拒绝。那些郁郁寡欢的老女人都不会受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更何况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激情四射足以点燃火焰,他们又怎能拒绝爱神的召唤?
佳丽亚德:你哪来的底气敢和我说这一套歪理邪说?你难道忘记了我财产丰裕,年轻貌美?我可是品行端正的良家妇女。
威尔第:上帝啊,求你不要和说这些了。你越这样说越是煽动爱的火焰。
佳丽亚德:这些话也许激起了你的欲火。我有点不明白,你哪来的胆子竟敢用那套不名誉的求爱邪说接近我。
威尔第:夫人,当然是因为受到了你的鼓励。
佳丽亚德:老天,我什么时候鼓励你了?对我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耻辱。[1]17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在面对压制性的男权话语的境遇下,佳丽亚德夫人的财产给予其反击的底气。她指责对方竟敢将自己置于情人的地位,从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男女两性的欲望在此意义上得到了平等的表达,从而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性别平等。
阿芙拉·贝恩在《都市女继承者》中以狂欢化的手法表现男女两性的欲望实现了性别的表演。女性主义者认为造成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并非男女之间身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后天因素对于性别的塑造。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妇女从属于男人是个普遍的习惯,任何背离这种习惯就自然地显得不自然。然而,即使在这个事实上,这种情感是由习惯来决定,它整个地还是由丰富的经验表现出来的。”[5]266贝恩在《月球皇帝》以及《兰特寡妇》等多部戏剧中通过女主人公之口明确表示女性之所以不能像男性一样自由地恋爱是因为习俗(custom)使然。《都市女继承者》中的女性尽管受到欲望的辖制,但是在财富以及婚姻上皆实现了自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父权的控制。《都市女继承者》中的女性人物对比威尔第不仅在经济上处于绝对优势,而且以夏洛特为代表的女性在智慧上丝毫不输于男子。从两人的对话可以看出,夏洛特并不是对于威尔第没有任何要求,她在经济上持续对他施压:
威尔第:你对我这么好,如果明天我还拿不出来你想要的东西,我宁愿死在你的手里。我知道叔叔的遗嘱还有其它文书放在哪里。通过这些我就有办法让他把所有遗产让我继承。我的计策一定要成功,绝不能失败。她对我的爱让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心上人。
克莱克特夫人:假如她遇到什么情况不能遵守诺言怎么办?
夏洛特:你怎么知道他不能遵守诺言。即便如此,我也决定嫁给他了。我们两个每年有三千磅的收入,足够使我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了。我之所以要求他,是要看看他和叔叔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此外,我还要给另外一个寡妇,也就是佳丽亚德,一点颜色看看。[1]25
由此可见,夏洛特相对于威尔第处于优越的地位,她不仅在经济上远远超越对方,而且有信心实现对于对方的控制。莎士比亚在追求一种秩序。阿芙拉·贝恩笔下的男性在欲望的驱动之下不惜坑蒙拐骗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莎士比亚喜剧中虽然也有性格阴郁的男性,但是他们多数受到极大的外部势力制约。朱迪斯·巴特勒认为:“如同伊里格瑞所指出的,这个阳具逻格斯中心经济主要倚赖一种延异经济,它从不公然展现,但它一直是一方面作为预设、一方面又受到否认。事实上,父系宗族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同性社群(homosocial)欲望的基础上;它是一种被压抑、因而也是被鄙视的情欲;它是男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关于男人之间的结盟,然而这却是通过异性恋态度对女人的交换和分配进行的。”[6]55-56夏洛特以及佳丽亚德夫人都拥有巨大的财产,所以她们打破了阳具逻格斯中心经济的基础。查尔斯·麦瑞维尔及其叔叔安东尼爵士在追求佳丽亚德夫人的过程中显然组成了男性之间的同盟。查尔斯与威尔第虽然互为情敌,但是他们也是通过交换和分配女人实现了男性权力的彰显。《都市女继承者》中在经济上有实力的女性享有了部分的男性权力。她们不仅在狂欢化美学的掩饰之下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欲望,而且进行了狂欢化的性别表演。正如德雷克·休斯所说:“从其他视点观之(尤其从《都市女继承者》中的三位女主人公的命运),该剧的思想更加含混。这个剧中的托利党分子是一群三教九流之徒。他们横行霸道、粗俗不堪、善于控制别人。”[7]147可见,贝恩在《都市女继承者》中的政治观点与性别态度处于分裂状态。特别是在欲望领域,她充分利用喜剧的狂欢化美学实现了新的性别表演。该剧中的佳丽亚德夫人以及夏洛特显然偏离了英国传统文化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但是由于该剧的结局仍然是男性获得了财产以及女人,因此并没有导致当时男性观众不可忍受的不适。
二、党派脱冕:《都市女继承者》中的政治狂欢化
《都市女继承者》所涉及的复辟时期政治题材围绕着充满政治煽动性的辉格党老爵士提摩太·崔特奥及其托利党侄子汤姆·威尔第竞相赢得伦敦城里声名远扬的女继承人夏洛特的青睐展开。该剧符合复辟时期风俗喜剧的程式,将政治派别与爱情战场上的胜负结合起来。支持国王的托利党不管品行如何恶劣,最终都像该剧中的威尔第一样获得众多女性的爱情,以至于女人和金钱一样成为犒赏男性的战利品。阿芙拉·贝恩在这个剧中表达自己的狂欢化世界感受的另一个途径是对于辉格党与托利党党派成员的脱冕。脱冕是巴赫金在探讨狂欢节在中世纪民间文化中的历史进步意义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重要仪式现象。他在《诗学与访谈》中指出:“脱冕的礼仪与加冕仪式恰好相反,要扒下脱冕者身上的帝王服装,摘下冠冕,夺走其他的权力象征物,还要讥笑他,殴打他。脱冕这一仪式中所有的象征因素,全部获得了第二层意义——积极的意义。”[8]164阿芙拉·贝恩在《都市女继承者》中不仅让女性批判托利党人威尔第的种种劣行,而且借助于威尔第攻击辉格党人提摩太爵士性无能,从而以狂欢化世界感受完成了对于两个党派中代表人物的脱冕。
《都市女继承者》是阿芙拉·贝恩显豁地表达自己支持保皇主义观点的剧作。在贝恩所处的17 世纪末期,剧场是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设若贝恩如同辉格党剧作家莎德威尔一样反对宫廷,她势必会受到来自政治和男性同侪的双重压力,因此贝恩选择在政治上支持保皇党至少在经济收入上较之支持辉格党更有保证。资产阶级取得光荣革命的胜利之后,以辉格党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贝恩的政治观点无异于保守,但是如能依着这位传奇女作家的心性实现自己在文学公共空间成为女英雄的志向,那么在政治上选择依从实力更强大的托利党也是可以理解的行为。尽管阿芙拉·贝恩在《都市女继承者》的献辞中不仅以“臣民挚爱的国君们”[1]6表达自己对于斯图亚特王朝的无限忠诚,而且不吝笔墨盛赞阿伦德尔伯爵“在纷扰蜂起的多事之秋,在谎言、告密、咒骂横行的时代,阁下秉承了高贵的审慎,坚定的意志。并且以忠诚引领自己脱离了陷阱。”[1]6在这篇献辞中,贝恩对于托利党人阿伦德尔伯爵近乎称颂的溢美之词随处可见,她对于国王的歌颂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毕竟在政治局势紧张的英国17 世纪80 年代,宣称自己支持国王不啻为一种明哲保身之举。德雷克·休斯也认为:“阿芙拉·贝恩在《都市女继承者》中声称‘这是一部十足的托利党戏剧。在这个剧中,除了那个无赖之外,全都是忠于国王的人’。”[7]147但是,仅仅凭借这些程式化的应景言辞,我们可否判定贝恩是坚定的保王党人呢?我们从政治归属的角度审视阿芙拉·贝恩在《都市女继承者》中的态度找不到女作家对于托利党的异议,否则她也无法通过当时剧场的审查。贝恩在《都市女继承者》中设置了英俊潇洒的托利党花花公子,与其做对的是年迈、性无能而且贪婪成性的辉格党徒提摩太。提摩太的底气来自于每年6 000磅的收入。他甚至批评安东尼爵士的侄子查尔斯交友不慎,和恶毒的托利党浪荡子在一起鬼混:“谢天谢地,查尔斯爵士。你如此下流无耻,却能够拥有庞大的产业。你嫖妓、酗酒、游戏、玩得昏天黑地。你的叔叔安东尼·梅瑞维尔却要让你继承所有财产。即便如此,伦敦城里的浪荡子依旧到处招摇过市。试问你们这些人有何脸面,拍着自己的胸脯扪心自问,哪一个宗教允许你们如此放荡?”[1]11提摩太对于托利党浪荡子的批评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不仅指出了复辟时期托利党分子的寄生本质,而且揭露了这一群体败坏的私德。阿芙拉·贝恩成功地将托利党浪荡子进行了脱冕,因此实现了文化更新。
在《都市女继承者》上演的时期,辉格党与托利党开始了激烈的斗争。英国政治史上最早的两个党派皆产生于复辟时期。1679 年,围绕具有天主教信仰背景的约克公爵詹姆斯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争论。其中有一批议员反对詹姆斯公爵继承王位,他们中多数是资产阶级新贵,被政敌以诨号辉格讥讽。“辉格”(Whigs)的名称可能是“Whiggamores”(意为“好斗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一词的缩语。“托利”(Tory)一词起源于爱尔兰语,意为不法之徒。在讨论詹姆斯公爵是否有权继承王位时,赞成的人则被政敌讥讽为“托利”。托利党人是指那些支持世袭王权、不愿去除国王的人,这一党派的成员多数为土地贵族,也包括一批落魄贵族,他们借助于投机保王捞取政治利益。《都市女继承》中的威尔第即属于依附于托利党羽翼党同伐异,进而攫取财富、欺骗女性的浪荡子。
从数量上来看,《都市女继承者》中的托利党人占多数。除了提摩太之外,剧中的主要男性人物都属于托利党。阿芙拉·贝恩在掌控父权的男性群体中设置了安东尼与提摩太这两位对比鲜明的长辈形象。安东尼认为作为臣民必须服从国王和上级,并且禁止攻击政府,而以提摩太为代表的辉格党人只会利用宗教教义蛊惑民众发动叛乱。两位都是侄子的监护人,但是在对待晚辈的态度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两人在剧中有如下一番言辞激烈的对话:
提摩太:天哪!令侄安东尼嫖娼酗酒成性,你真应该把他带到教堂来接受教育。他急需到教堂里系统的学习经文。
安东尼:老天啊!你自己遵守那些古板教条吧。做自己的祭祀王约翰去吧,没人愿意和你说话,打起我侄子的主意来了。
提摩太:好家伙,安东尼爵士。你不要摆出一副清高无暇的样子。我关注的是整个城市的舆情。你要侄子过奢侈的生活,会给伦敦城里的年轻继承人做了坏榜样。
安东尼:别提伦敦了,它不过是一座充满牢骚、谎言和腹诽的城市。但凡智慧的、诚实的人们都听不懂这座城里的人说话的意思。是你还是伦敦城的别个人给我侄子的代理人或者裁缝支付过账单?他花的是我的钱,爱怎么花都行。你这个傻瓜无赖,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吧。
提摩太:我说的都是聪明人才说的话。
安东尼:你是什么聪明人!我看是聪明的乌龟吧!他们游说我把侄子教育成前程似锦的年轻人,还不是让他捧着经商的书阅读,要么就是把他送到大学死啃逻辑学,最后变成一个心旌摇荡、看似博学实则愚蠢的呆驴。他们时而矜持安静,时而扭捏作态地笑,为了赢得情人发一些卑微的誓言。我要砍伐别人的森林,就得支付租金。如果我要说服侄子做什么事情,就得为他好。要我强迫他和克伦普夫人结婚。她实际上只是令人崇敬的大人物的乏味女儿而已,这些都是该死的类似于《保卫者》这个戏中的人物做出的事。[1]16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安东尼不赞成提摩太的教育理念。他认为提摩太遵守的是不允许喝酒的清教徒的严肃戒律,并且为了利益不惜包办婚姻。安东尼认为辉格党人掌控的伦敦不过是一座充满牢骚、诽谤和谎言的城市。提摩太则批评安东尼纵容侄子查尔斯酗酒享乐,给城里的年轻人做了坏榜样。两个人互相攻击实则完成了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彼此的脱冕。
威尔第是托利党浪荡子中的典型代表。阿芙拉·贝恩没有因为其政治上支持国王而放弃对该人物的脱冕。他在政治上战胜其叔叔居然是打算采用给其戴上绿帽子的粗俗方式,足见该人物除了善于使用阴谋诡计,实则别无所长。我们从克莱克特、福平顿以及夏洛特三人的对话中发现阿芙拉·贝恩首先从经济上对威尔第进行了脱冕:
克莱克特:是的,他还是一个穷光蛋异教徒。你要嫁一个连买裤子的钱都没有的男人?还是和一个诚实正直、宗教感强烈、心有良知、以理性爱上女人的男人结合?福平顿先生怎么在这儿。你瞧他这身条儿,还有这英俊的脸、和箭一样挺直的腰背。我保证他就是现成的美男子。
夏洛特:怎么回事?还要给他买裤子?难道威尔第没有财产吗?
福平顿:是这么回事,命运的骰子又转了起来。他让那个乡绅光火,经过一些明争暗斗,威尔第也变成了需要自食其力的人了。
夏洛特:怎么?难道他的叔叔就这样让他没有财产独立谋生吗?
福平顿:是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夫人,我觉得你应该擦亮眼睛,看一看这个人与真心仰慕的人之间有什么不同。
威尔第之前属于辉格党,后来才转投托利党阵营。他的叔叔也因此剥夺了其财产继承权。毫无经济实力的浪荡子被无情地脱冕。表面上衣着光鲜、情场得意的花花公子实则困窘得连裤子都买不起。威尔第在生活上挥霍无度,在感情上朝三暮四,既不擅长经商,也毫无其他谋生能力。他值得称道的优点正如克莱克特所说的是一位美男子。此人冷酷无情,善于控制女性,以达到享有对方财富的目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威尔第的地位类同于出卖色相的妓女。威尔第最终取得了对于辉格党人的胜利也是采用假扮成抢劫犯的计策才得到了叔叔涉嫌反叛的秘密文件。他在与同党福平顿的对话中将自己巧取豪夺叔叔财产的计划公之于众:
威尔第:弗兰克,说到结婚,真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我的那位老迈的叔叔也会寿终正寝,和家族的祖先一起长眠。到时候,我每年就有6000 磅的收入了。有妻子要受到太多限制,只能给我寻欢作乐带来障碍。要我说,钱财最重要。
福平顿:怎么才能弄到钱呢?
威尔第:当然是从我叔叔那里搞钱了,尽管他宣布剥夺了我的继承权,让我以后靠自己的智慧和毅力自食其力。
福平顿:我只想知道具体的计划。
威尔第:我知道最近你手头也有点紧。你只需要在幕后或者观众席,其它在明处的事情由我操办,比如我会去咖啡馆搜集证据。那里穿着马裤的绅士把我的财产都一笔笔记录好了,他们的计谋比剧作家李利作品中的阴谋还要多。[1]26-27
威尔第大言不惭地承认婚姻对自己不过是一种束缚。他直言追求女性是为了寻欢作乐。阿芙拉·贝恩让浪荡子承认自己唯利是图的本性,从而实现了在政治上对于托利党的脱冕。威尔第不务正业,一心觊觎叔叔的财产。他对于辉格党活动的公共空间非常熟悉,所以才准备去咖啡馆搜集他们反叛的证据。
在17 世纪80 年代以后的英国剧坛,有两个因素造成了这一时期的戏剧与性以及政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第一个因素是戏剧中毫不避讳的性展示在此时期与浮浪的社会风气相得益彰;第二个因素是褫夺危机之后的英国各种政治运动和阴谋此起彼伏,连带着这一时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政治剧。性与政治的结合在复辟时期浪荡子题材中得到了统一,具体表现为剧作家安排风度翩翩的托利党浪荡子战胜老迈好色的辉格党人。阿芙拉·贝恩在《都市女继承者》中也运用了复辟时期戏剧的性政治套路让威尔第在财产所有权以及婚姻战场上战胜其叔叔提摩太。凯特·米丽特认为:“当我们希望从根本上讨论两性关系时,我们就引入政治这一术语,因为在概括两性历史的和现存的相对状况的本质时,它特别有用。在传统的、规范化的政治概念以外,我们有可能(甚至必须)建立一种有关权力关系的更加切合实际的心理学和哲学。”[9]37由此可见,政治与性均是人类权力关系的表现,都是一个集团实现对另一个集团统治所进行的文化规训。在英国文学史上,复辟时期戏剧中的性政治主题表现得最为突出。阿芙拉·贝恩也利用两性行为实现对于辉格党人提摩太的脱冕以及托利党人威尔第的加冕。威尔第在与佳丽亚德夫人唇枪舌剑的交锋中展现了复辟时期性与政治之间的象征性关系:
威尔第:是的,这两种优点你都不具备。要不然你怎么厚颜无耻地愿意嫁给那个老乌龟。他顶多能给你当一个衣服架子。到了他这个年纪,一看就知道确定无疑是个性无能。
佳丽亚德:你说的是你的叔叔吗?
威尔第:我说的就是他。三十年间他都没有过男欢女爱,你的脑袋不知道哪根神经出了问题,居然要和他结婚。天哪,想一想你们洞房花烛夜的幸福吧!
佳丽亚德:尽管你善于用辞令攻讦别人,你也没有能力阻止我的选择。
威尔第:你执意要嫁给我那个煽动叛乱的叔叔,我也爱莫能助了。你注定要成为好色之徒的受害者。一旦有朝一日我的叔叔被戴上了绿帽子,大家都会明白你的美貌不过是可资买卖的商品。恐怕到时候我们这些认为你是个诚实的妇人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犯了巨大的错误。
佳丽亚德:我并不缺少诚实。至于我的智慧接下来就足够你领教了。
威尔第:那就让世人评价你的这桩婚姻吧。你和那个老家伙结婚不仅会毁了你的名声,而且也没有婚姻的乐趣。因为他有钱,你就愿意嫁给那个又老又傻的东西,其实有很多英俊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喜欢你。[1]44-45
在这几段对话中,威尔第不遗余力地对辉格党徒提摩太进行性能力以及政治上的脱冕。他一开始攻击叔叔老迈力绵,接着又攻讦其煽动叛乱。威尔第使用了诸如老乌龟、衣服架子、绿帽子等露骨下作的语言。巴赫金认为:“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及其特有的诸范畴,狂欢节上的笑,狂欢节加冕脱冕演出的象征意义,易位和换装的象征意义,狂欢式的两重性质,还有狂欢式自由不拘的语言(亲昵的、露骨下作的、插科打诨的、夸奖责骂的等语言)的种种色彩——所有这一切深深渗透到几乎所有文学体裁中。”[10]168威尔第在剧中的语言具有粗鄙下作的典型特征,这也是阿芙拉·贝恩狂欢式世界感受的具体表现。阿芙拉·贝恩巧妙地运用复辟时期的党派纷争,对于辉格党与托利党进行了脱冕,实际上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秩序,体现了“交替与变更的精神。”[10]160
阿芙拉·贝恩在《都市女继承者》中让女性大胆地将自己的欲望以狂欢式的手法表现出来,目的在于进行新的性别表演。她在剧中利用了当时党派之争的情势,对于分属两党的男性都进行了脱冕,从而完成了政治狂欢化书写。像阿芙拉·贝恩这样具有狂欢化世界感受的思想者和在伦敦剧坛取得商业成功的职业女性作家,怎样看待性别与政治秩序?她是原初的女性主义者抑或坚定的保王主义者?对以上问题,很多既往的研究者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是令他们为难的是阿芙拉·贝恩剧作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总是虎头蛇尾,即如《都市女继承者》中的夏洛特以及佳丽亚德夫人先后委身于劣迹斑斑的花花公子。更令他们为难的是假定贝恩是坚定的保王主义者,缘何又将此类人物写得一无是处,而之所以会得出暧昧难决的结论,则大约是因为,阿芙拉·贝恩在性别思想上属于早期的女性主义,而在创作与政治上贴近保王主义。毋庸置疑,阿芙拉·贝恩对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必然是质疑与批判的,特别是对那些将女性视为欲望对象的封建糟粕思想。
但是作为17世纪80年代伦敦剧坛仅存的一个女性剧作家,一个心中燃烧着以笔成为女英雄的理想主义者,阿芙拉·贝恩更难表达的是如何面对现代之前的强势的男权文化传统。她显然意识到无法直接对抗英国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因为她清楚首先得把自己的女性声音在公共空间传播出去。《都市女继承者》中的欲望狂欢与党派脱冕既满足了当时观众对于性消费的遐想以及政治上的要求,又得以让阿芙拉·贝恩运用狂欢化世界感受在其中夹带女性主义思想私货,从而让表面情节之下隐藏的反传统女性思想得以在剧场中的女性观众头脑中留下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