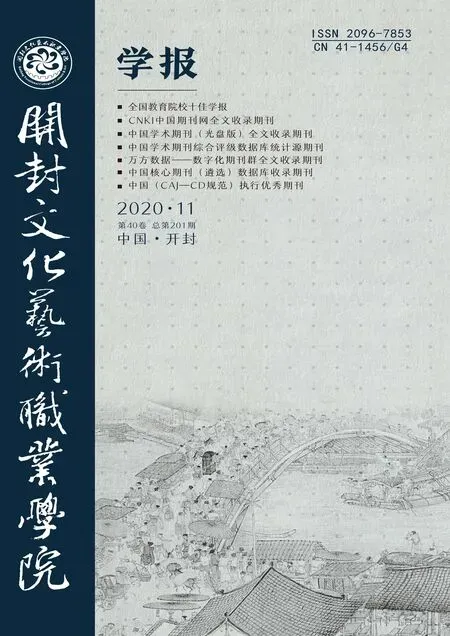《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内涵解读
2020-01-09谢静漪
谢静漪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2019 年12 月《 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以下简称 “《指导标准》”)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华传统文化课程有了统一的、具体可行的操作标准。《指导标准》充分考虑了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和实施路径,并与现代教育、现代中小学生年龄特点融合,为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成体系的、建设性的方案。此外,《指导标准》对于厘清中华传统文化课程的本质属性、指导教师进行中华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等具有重大启发意义,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的解读。
一、《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的出台背景
文化是国家的灵魂,是民族的血脉。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被提升到国家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战略高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2014 年3 月,教育部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对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出了总体要求。2017年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应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等各环节。而后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意见都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与实践。而2019年12 月发布的《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更是吸纳了先前优秀成果作为理论基点。它作为引领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实施建议的纲领性文件,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具体的内容指导。同时,针对中小学传统教育中出现的教学内容碎片化、教学形式仪式化、教学评价应试化等问题,《指导标准》也都给予了相应建议。它的出台对于增强传统文化教育与普通教育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顺应国家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趋势,构建实施中小学阶段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具有重大 意义。
二、《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的体系建构
(一)《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的体系结构
《指导标准》分为4 个部分:前言、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施建议。前言包括课程性质、课程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明确了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定位以及课程设计的重要理念和总体设计思路。课程目标从形成文化记忆、增进文化理解、提升文化自信3 个维度提出了对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学习的内在要求。课程内容是《指导标准》的主体部分,包括经典文本(以下简称 “经典”)、文化常识(以下简称“常识”)、游艺游戏和技能技艺(以下简称 “技艺”)3 方面的总体说明、学习目标、学习内容。通过对学习目标、学习内容进行分学段阐述,形成了一个横向互补、纵向递进的中华传统文化课程体系。最后的实施建议则从教学建议、评价建议、教材编写建议、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4 个角度提出课程实施的策略、方法和原则,同时为具体实践留有选择开发的空间。
(二)《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的内容设计
《指导标准》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基本理念展开设计,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课程属性、目标内容、实践评价进行了详细阐述。在课程性质方面,提出中小学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具有综合性、人文性、实践性的特点。同时,在课程设计与开发中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指导;以培养中小学生的文化素养为宗旨;注重知识逻辑、生活逻辑与认知规律统一的课程理念。此外,在课程目标上,着眼于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通过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帮助中小学生形成文化记忆、增进文化理解、提升文化自信。
而在课程内容方面,《指导标准》设计了一个由经典、常识、技艺3 方面构成的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内容体系。通过对经典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了解不同时代丰富的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精神状态,体会作品中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感受卓尔不凡的艺术魅力。通过对常识的了解,使学生在礼仪文化、器物文化、社会生活文化、思想文化中体悟传统文化的绵延流长。透过传统游戏、传统手艺、传统工艺乃至民间艺术等,引导学生窥斑知豹,了解极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技艺。
实施建议部分,《指导标准》从教学与评价到教材编写再到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都详细说明。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如何教学、教学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如何选择以及通过哪些方式方法进行教学评价等都给出了明确的标准和指导。
三、《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的特点
《指导标准》的出台,标志着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由实验探索阶段进入推进实施阶段。因此,把握其特点,对于指导中华传统文化课程教学实践有着重要价值。《指导标准》主要呈现出以下3 个特色:
(一)课程性质的综合性
在课程性质方面,《指导标准》提道:“中小学中华传统文化课程是由一门独立设置的课程以及在其他学科和活动中的渗透性内容组成的综合性课程。”[1]3而后的课程设计思路中对其综合性的课程性质作了详细阐述:“中小学中华传统文化课程是一种特殊的课程形态,它包括一门独立设置的课程,以及在其他学科课程及课外、校外教育活动中渗透、融入的一系列内容,可以表述为‘1+X’模式。”[1]6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课程作为一门课程,它是独立设置的。但究其内容来看,它又是综合的。其综合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表现在学科课程中的综合。在学校教育中,语文、历史、思想政治、地理、音乐、美术等学科课程中都包含着传统文化的内容。如在语文学科中,可从文言文、古诗词、传统戏曲、古代小说等传统文学作品入手,体会蕴含在文学经典中的精神内涵;在历史学科中,可从灿烂的青铜文明、昌盛的秦汉文化、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等历史常识出发,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通过不同学科的渗透学习,加强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从中获得必备的文化素养。
另一方面,表现在教育活动中的综合。在猜灯谜、下围棋、练太极等常见活动中都蕴含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因而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和地方资源,将传统文化学习与综合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民俗馆,采访手工艺人、曲艺传人等活动,深化学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切身体验。
中华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的特征,因而在教学实践中,只有通过多学科教学与综合实践活动相结合,才能确保学生接受较为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二)课程内容的具体化
课程内容是《指导标准》的主体部分,由经典、常识、技艺3 部分构成。而每一方面又从总体说明、学习目标、学习内容的角度进行详细阐述,且在学习目标中将 “总目标” 与 “学段目标” 相结合,呈现出总任务与各学段分任务的形式,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同时,学习内容的设定也进一步系统有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学段目标的有序化
学段目标对总目标进行了连续性划分,突出总目标中的核心思想。如在经典的总目标中提出要“诵读、精读、研读经典,能背诵一些优秀的格言警句、段落和篇章,逐步培育对经典的亲切感、感受力、理解力和理性认识”[1]14。在各个学段目标中,从通过诵读经典推动学生对蒙书内容有真情实感的体验,到精读经典体会蕴含其中的哲理美德,再到研读经典探究辨析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一系列过程有序推进,不断提高学段目标要求。
2. 学习内容的细致化
《指导标准》详细罗列了经典、常识、技艺3方面的学段学习内容。以常识为例,4~6 年级时要求学生能在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中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在与之对应的学习内容中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常识、交通文化、日用器物中应掌握的常识作了具体列举。从女子额间的抹额到祭祀时所穿的吉服,从亭台楼阁等景观园林建筑到以紫禁城为代表的宫廷建筑,从南起余杭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到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从商周的青铜到明清的青花瓷,等等,在列举中做到了 “点中有面,面中现点”。
3. 课程内容的体系化
传统文化教育要达到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就必须贯彻落实科学性与系统性的特征,零散碎片化的教育会使传统文化教育大打折扣。因而,在课程内容中通过经典、常识、技艺3 方面的巧妙设计,形成了一个横向互补、纵向递进的中华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使其具有严谨的内在逻辑和丰富的内容意义。其中,纵向的递进主要表现在随着学段目标的提高,学习内容也逐渐深奥。横向的互补则更多体现在经典、常识、技艺的学习内容中。如知道“姓、名、字、号的含义,会使用简单的尊称或敬称、谦称,知道避讳及其方法等”[1]19常识,能在阅读经典时避免误读等错误。再如,只有 “了解中国古代舟、船、车、轿等交通工具,简单了解其基本构造及制作流程,了解中国传统的交通及通讯方式”[1]27等,才能真正体会到杜甫笔下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的迫切与期待。经典、常识、技艺3 个模块虽承担着不同的目标任务,但相互协调、彼此推进,共同促进课程内容的体系化建设。
(三)实施建议的针对性
实施建议由教学建议、评价建议、教材编写建议、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4 部分构成,每一部分建议《指导标准》都给出了具体的实践操作性指导。
在教学建议中,《指导标准》针对我国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目前还是以重知识传授为主而轻情感培养的现状,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中明确提出 “注重知识学习与情感培养的结合,引导学生在诵读经典、习得常识、学习技艺的过程中提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1]33。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教授,而且是对青年一代文化价值观的培养。通过知识学习与情感培养并举,帮助学生在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中,习与智长,化与心成。
在评价建议中,《指导标准》提出重参与、重过程、重体验、重发展的整体评价观。这是对过去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重接受轻参与、重结果轻过程、重认识轻体验评价方式的否定与扬弃。传统文化教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沉淀。故而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从评价回馈中反思,不断改进教学策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在教材编写建议中,《指导标准》为如何构建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提供了可行的操作方案和实施路径。中华传统文化教材作为教师教学内容、学生学习内容的主要媒介,也作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内容上需体现传统文化自身的特征,在结构上符合传统文化的逻辑体系,从而更好地展现中国元素,讲好中国故事。
在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中,《指导标准》从学校、家庭、社会、现代媒体角度提供了获取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途径与方式。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大教育系统和现代媒体的作用,构成传统文化立体环状教育网络,形成各系统间的协同效应。
四、《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的实施意义
《指导标准》的出台,是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基础教育的重要基点,也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关键环节。它作为当前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在基础教育层面上的体现,为新时代开展学生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非凡意义。
(一)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教材体系的设计与开发
《指导标准》明确了中华传统文化教材的特色与价值导向,也为其编写提供了基本理念和内容体系。如在经典部分的7~9 年级中提出 “重点精读‘四书’,即节选学习《论语》《孟子》,全文学习《大学》《中庸》”[1]16,编者可根据该要求设计不同的学习内容。如针对性地选取《论语》《孟子》中关于 “仁”“义” 等主题的内容,辅之以相应主题的诗词散文,通过主题学习及群文阅读的方式让学生对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中的核心要素有所了解。除此之外,还可设置《大学》《中庸》等作品的整本书阅读任务,引导学生体会经典中的全息性与生命整体感,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2]4
(二)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课程体系的建设与推广
《指导标准》的出台,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一个牢固的基点,而相应教材的问世也为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教什么”的选择。那么,“怎样教” 就成为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早已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本身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诵读研修、实践训练等教学方式对于今天的教育依然适用,但仍需改变。因为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知识风暴与文化冲击。故而在传统文化教学过程中,应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主研究,用思辨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使学生对传统文化形成客观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待传统文化的合理情感与态度。
(三)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基础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作为一个 “多面手”,其内容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历史、思想政治、美术等课程中都有涉及,故而也增加了其独立设置的难度。但作为一门培养学生文化素养、提升学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课程,它的独立设置必然会成为一种趋势。故而,有条件的学校可利用校本课程的形式组织传统文化教学,如开展诵读经典活动,让学生在诵读的过程中 “沉潜讽咏,玩味义理,咀嚼滋味”,在聆听历史的声音中感受传统文化经典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