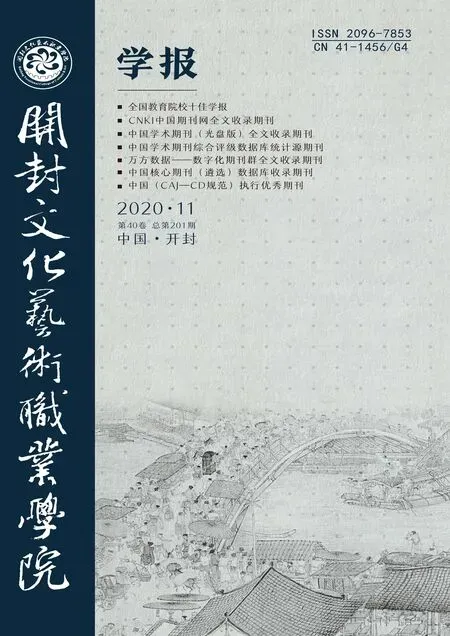龙榆生与夏承焘交游考
2020-01-09汪海洋
汪海洋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龙榆生是 “民国四大词人”[1]173之一。关于龙榆生与夏承焘的交游研究,李剑亮的《夏承焘词学与〈词学季刊〉》[2]从夏承焘与《词学季刊》这一方面进行了论述;萧莎的《夏承焘交游词研究》[3]从夏承焘与龙榆生的交游词方面进行了论证。这些论文为研究龙榆生词学交游提供了依据与基础。然而,相关论述均有待进一步深入,如1949 年前后龙榆生与夏承焘关系的变化。龙榆生生平交游是其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龙榆生与夏承焘在词学道路上相互帮助,相互影响,使得二人的词学观点互为补充。二人的交游既帮助了夏承焘,又对龙榆生的词学观产生了影响。本文将以龙榆生就职于汪伪政府为分界点,对龙榆生与夏承焘的交游进行研究,以此对龙榆生的词学活动进行梳理,为深入理解龙榆生的词学观提供参考。
一、 1940 年前龙榆生与夏承焘的交游
龙榆生与夏承焘相识于1929 年,他们的相识得益于李雁晴。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记录道:“得李雁晴厦门大学五月三十日函,谓暨南大学教授龙君榆生,名沐勋,江西人,黄侃弟子,近专治宋词,有所论述。雁晴嘱与通函讨论。”[4]99夏承焘从李雁晴处得知龙榆生专于治词,主动寻求龙榆生的帮助。这时,龙榆生已经是大学老师了,其在词学上的影响力要高于夏承焘。夏承焘此时正在编撰《唐宋词人年谱》,编纂年谱是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需要逐一考证词人生平。然而,当时的夏承焘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他既“无师友之助”又“闻见不广”,因此,急需他人在词学研究上给予帮助,而龙榆生正是这个能给予其帮助的人。于是,夏承焘开始主动给龙榆生写信,刚开始在信中以学生自居。夏承焘这个时候住在严州,因为严州的 “学问空气太稀薄”[3],而龙榆生住在上海,在暨南大学任教,兼之周围有许多师友,所以夏承焘渴望得到龙榆生的帮助,正如信中所言 “如得先生上下其议论,共学之乐,乃无艺矣”[3]。龙榆生是怎么回答的呢?他当即回信愿意与夏承焘结交,并进一步提出与夏承焘合编词人年谱,“与予缔交,问《词有衬字考》。又谓有意为词人年谱,欲与予分工合作”[3]。夏承焘则非常高兴,随即 “灯下作一书复之”[3]。
此后,二人交往日益密切,夏承焘常将著作寄给龙榆生指正。夏承焘要写《张子野年谱》,就委托龙榆生 “查子野入蜀年代”,在龙榆生的帮助下,夏承焘完成了《张子野年谱》,并刊登在龙榆生创办的《词学季刊》上。同时,夏承焘也在龙榆生治词的道路上给予了其帮助。龙榆生治词标举苏、辛,在一次写信中,他告诉夏承焘,“《稼轩年谱》已成,发愿为苏、辛词合笺”[3]。龙榆生想要为苏轼和辛弃疾著合笺,夏承焘长于词人的考证,“瞿禅专为词人做年谱,翻检群书,校核事迹,积岁月而成《唐宋词人年谱》十种十二家,开创词人年谱之先例”[5]。于是,夏承焘在给龙榆生的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苏、辛词使事较多,尊著于冷僻者一一注出,亦极便读者。”[3]夏承焘认为,苏轼和辛弃疾的词作多运用典故,对于简单的典故不必一一标出,龙榆生在做笺注时只需把其中生僻的、不常见的典故标注出来。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完成以后,夏承焘“为榆生阅东坡词笺”,并“删其繁处”,帮龙榆生校正《东坡乐府笺》,而且告诉龙榆生 “东坡词宋人有顾禧景繁补注,见《西塘集耆旧续闻》,共四、五事”[6]。夏承焘看了龙榆生的“补订辛梅臣辛稼轩年谱” 后,评价甚高,说其作 “甚详赡翔实”[3]。龙榆生写完《清季四大词家》以后,夏承焘指出《清季四大词家》中的4 点错误,龙榆生虚心接受并改正,最后刊登在《暨南大学学报》上。
夏承焘治白石词,二人在通信中多次交流观点。夏承焘写有《与龙榆生论陈译白石〈 暗香谱〉 书》《与龙榆生论白石词谱非琴曲书》《再与榆生论白石词谱书》等文章,后来都被刊登在《词学季刊》上。在《与龙榆生论陈译白石〈 暗香谱〉 书》一文中,夏承焘说其曾见陈东塾译白石《暗香》一书,认为 “其用《通考》旧法,而不免疏牾”,龙榆生看后 “定白石词谱为琴声”。夏承焘对于此说 “不敢尽信”,于是,又写了《与龙榆生论白石词谱非琴曲书》,“于旁谱辨中举数证献疑”。龙榆生回复:“茍宋词亦一字数音,可以由乐工自由增减,何以《渔歌子》曲度不传。苏黄以《浣溪沙》《鹧鸪天》歌之,必依谱改定其句度。” 夏承焘又写了《再与榆生论白石词谱书》,解释道:“虽一字一律,而缠声赴拍,并非毫无缓急。”[7]1107这些观点的交流加深了二人对于白石词的理解,并为以后夏承焘研究白石词打下了基础。
不仅如此,在二人的交往过程中,龙榆生还不断为夏承焘提供相关的书籍。龙榆生曾把 “蜕庵先生赓言” 的《蜕庵诗集》送给夏承焘。夏承焘研究姜夔词,龙榆生尽可能把自己所藏的相关书籍借给夏承焘。因为龙榆生受学于朱祖谋与黄侃,二人都曾点评过《梦窗词》,当夏承焘写《梦窗词集后笺》时,龙榆生就把朱祖谋与黄侃点评的《梦窗词》借给夏承焘,并且帮夏承焘把《梦窗词集后笺》发表在《词学季刊》上。因为夏承焘要编撰词人年谱,龙榆生就送给夏承焘 “《词莂》《菌阁琐谈》及陈慈首《稼轩年谱》”;因为夏承焘研究辛弃疾缺少书籍,龙榆生就帮夏承焘买《词话丛抄》;因为夏承焘研究姜夔,龙榆生就帮夏承焘 “向上海各词人问白石事”。二人还经常讨论《姜考》的体制。夏承焘研究宋元词,龙榆生就送给夏承焘《宋元三十一家词》《散原精舍诗别集》。另外,夏承焘还从龙榆生处见到了许多珍贵的书籍,如“大鹤山人诗稿、张尔田《词莂》未刊本”[5]。这些书籍均有益于夏承焘日后从事词人年谱研究。
龙榆生不仅为夏承焘提供书籍,还把周围的师友介绍给夏承焘。龙榆生是朱祖谋与黄侃的学生,而且交友广泛。夏承焘对龙榆生直言“足下见闻较广,当有以教我”,并希望龙榆生把自己引荐给朱祖谋,于是,龙榆生就充当了朱祖谋与夏承焘之间交流的桥梁。夏承焘认为朱祖谋所考吴文英的生年有误,与自己所考相差三十多年,遂请龙榆生把这一发现告知朱祖谋。龙榆生在信中说道,朱祖谋 “自承梦窗生卒为未定之说”,并且 “盼予速寄示”,随后夏承焘就通过龙榆生把《梦窗生卒考》寄给朱祖谋,朱祖谋看后评价道 “梦窗系属八百年未发之疑,自我兄而昭析”。在龙榆生的帮助下,夏承焘与朱祖谋开始有书信上的往来,并经常谈论词学。此后,二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龙榆生邀请夏承焘共同编纂《清词钞》,并且答应与其 “共访彊村”[3]。因为龙榆生的缘故,夏承焘于1930 年与仰慕已久的朱祖谋见面,“四月,赴沪,初与龙榆生把晤,初谒朱彊村”“七月,返温度暑假,经沪,第二次晤榆生,第二次诣彊村”“九月,经沪,访榆生、诣彊村”[8]226。
龙榆生于1933 年创办了《词学季刊》,期间共发表了夏承焘11 篇论文:《张子野年谱》、《梦窗词集后笺》、《贺方回年谱》、《韦端己年谱》、《晏同叔年谱》(上)、《晏同叔年谱》(下)、《冯正中年谱》、《南唐二主年谱》(一)、《南唐二主年谱》(二)、《南唐二主年谱》(三)、《南唐二主年谱》(四)。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夏承焘在词学上的影响力。这些论文几乎全为词人年谱,夏承焘长于考证的特点也在此时显露出来。对于龙榆生和夏承焘在词学上的成就,夏承焘曾评价道:“榆生长于推论,予则用力于考证。”[5]这个评价非常中肯。
这些举措无疑扩大了夏承焘的交往面。因此,龙榆生对夏承焘的词学研究给予了很大帮助,后来夏承焘回忆道:“阅严州日记,念僻居山邑,如不交榆生,学问恐不致有今日。”[3]
二、1940 年后龙榆生与夏承焘的交游
1940 年,龙榆生投靠汪精卫并在汪伪政府任职,二人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夏承焘在日记中写道:“闻口口将离沪,为之大讶,为家累过重耶,抑羡高爵耶。枕上不得安睡。他日相见,不知何以劝慰也。”[3]此后,龙榆生为士人所不齿,夏承焘遂用“口口”代指龙榆生。夏承焘经常写信劝诫他,“三月一日,夏承焘发先生函:‘劝榆生及时蓄积为退步计’”[4]125。
作为朋友,夏承焘还经常写词劝龙榆生回头,“夏承焘感先生事,为赋《水龙吟》‘皂泡’、《木兰花慢》‘题嫁杏图’、《虞美人》‘感事’、《鹧鸪天》‘万事兵戈有是非’、《临江仙》‘古津席上,名山翁示诗云:明岁春风二三月,吾曹犹及看花否?作此为报’、《虞美人》‘自杭州避寇过钓台’等词”[4]124。虽然此时夏承焘与龙榆生仍有往来,但夏承焘立场坚定,汪伪政府为龙榆生创办了《同声月刊》,夏承焘没有在上面发表过一篇论文。
此后,汪伪政府倒台,1945 年11 月8 日,“国民党教育部以了解学潮为由请走龙榆生,囚禁于老虎桥监狱”。夏承焘 “以万元托仲连买蔬肴馈之”[4]124,并且委托其在法院工作的学生琦君帮助龙榆生,1945 年12 月9 日:“发希真苏州高等法院一函,由心叔转,恳其相机照料榆生。”12月16日:“得希真复,谓榆生保释事,俟郑院长回苏时即可设法,似不甚难。”龙榆生在狱中时还经常与夏承焘通信,1945年7 月12 日:“得榆生苏州函,嘱画扇面,并嘱时时通书,以慰寂寞。”[4]124龙榆生得以提前出狱,夏承焘功不可没。龙榆生出狱以后与夏承焘继续通信并谈论词艺,《天风阁学词日记》1948 年12 月20日云:“昨榆生寄来新《忍寒词》一册,灯下阅数首,予曩劝其应删各篇己尽删矣。”[4]137-138
1949 年以后,龙榆生因为历史旧嫌,生活艰苦。1951 年,龙榆生经历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3年,夏承焘拜访龙榆生,二人曾有过唱和,“晨九时与朱、沈二君冒雨往上海博物馆访榆生,一别十馀年,已两鬓繁霜如老翁矣。谓蕙风先生为刘翰怡所抄之《词林考鉴》,积稿可三四尺。刘尚健在,此稿不知何在。(榆生所钞仅七八本耳。)又谓《彊村丛书》版已无可踪迹,《彊村遗书》稿则已捐与博物馆或文史馆。榆生导观博物馆,匆匆行十馀室,多见所未见”。龙榆生诗曰:“最难风雨故人来,佳节匆匆罢举杯。九死艰虞留我在,十年怀抱为君开。照人肝胆情如昨,顾影芳华去不迴。今夕霸王台下过,倘从云外一低徊。” 龙榆生在诗的自注中表达了对夏承焘的感谢:“予曩岁陷虏中,数来往彭城、燕京、金陵间,欲效辛幼安之所为。奇谋未就,终遭缧绁。微瞿禅及女弟子龚家珠后先营救,几早瘐死狱中矣。”[4]133
1954 年,为解决龙榆生生活上的困难,友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刘大杰等主持为上海公营新文艺出版社编印古典文学丛刊,约顾颉刚、容庚、詹安泰、朱东润、游国恩、王季思等分任编纂。其中词选一种,特请先生与夏承焘合作,藉让先生获薄酬开销”[4]133。龙榆生与夏承焘受邀合作编选《词选》,夏承焘刚开始答应与龙榆生合作,但1954 年8 月,夏承焘给龙榆生写信道,“备课忙,无暇及《词选》”,退出了词选的编撰工作。关于夏承焘为什么退出编纂工作,《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曾有记载,1954 年8 月11 日云:“微昭(陆维钊)来,谓上海友人颇以予与榆生合编词选为言,榆生历史旧嫌,至今不恕于人口。” 8 月18 日:“夕心叔(任铭善)、天五(吴鹭山)来,谈与榆生编词选事。心叔恐予过忙,谓可让榆生一手为之。” 19 日:“发榆生函,寄还唐五代北宋选目,并告事忙课忙,选词事不能兼顾,请榆生一手了之。”[4]139
龙榆生于 “1958 年5 月被划为右派”,1961 年才得以“脱帽”[9]907,此时龙榆生已经60岁。脱帽后,龙榆生与夏承焘仍有往来,并经常与其谈论这段经历:“午后榆生来,数年不见,发白八九分矣。谈此次脱帽经过,谓以八字自勉:戒骄戒躁,又红又专。又谈徐州事,予多不解。劝予早晨散步,最能安泰心身,谈两三小时云。”[4]351
1965 年,龙榆生64 岁,仍经常与夏承焘写信论词调词乐:“谈词学革命化研究计划,谓此一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之伟业,盼以热情毅力不断努力,促其实现。”[4]189可见,龙榆生在晚年仍然为推进词学事业的发展作贡献,这种精神让人敬佩。1966年,龙榆生卒于上海,至此,二人的交往告一段落。
结语
龙榆生与夏承焘相识于1929 年,他们的友谊持续了30 多年,30 多年来,二人在词学的道路上互帮互助,砥砺前行。在二人初识之时,龙榆生用自己在词学上的影响力积极地帮助夏承焘,为夏承焘介绍师友,提供词学书籍,拓宽其治学的道路;在后来龙榆生被人们非议的时候,夏承焘并没有因为龙榆生一时的错误而与其断绝往来,仍然不遗余力地帮助龙榆生。这30 多年,二人书信往来,谈论词学,交流词学观点,共同推进了现代词学的进步,而他们的友谊也成为词坛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