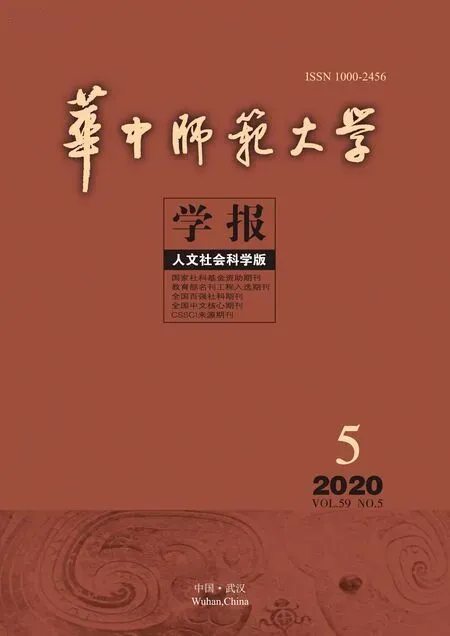老舍访日与20世纪60年代的中日文学交流
2020-01-09余迅
余 迅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0世纪60年代,受《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订的影响,“美帝国主义”成为了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在此背景下两国作家互访频繁,1965年由老舍任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对于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访日经历,老舍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本应该发表的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也“石沉大海,杳无音信”①。关于老舍访日的研究成果,多为基本情况的介绍②,鲜见对于访日背景、中日作家交流、访日意义等问题的探讨。本文通过梳理老舍相关文献,日本作家和新闻界的记述文字,回到历史现场,尝试窥视晚年老舍的心境,考察20世纪60年代中日文学交流所呈现出的历史特征。
一、老舍访日的背景和概况
1965年3月24日至4月28日,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日本。此代表团由老舍任团长、刘白羽任副团长,成员还有张光年、杜宣、茹志鹃等。
在众多老舍传记中,这次出访被描述为“极为愉快的一次国外旅行,完全生活在友好的情谊之中”③,一次“能暂时避开政治阴霾的外事活动”④。这类说法基本与《人民日报》《朝日新闻》的宣传保持一致。代表团到达日本时,《人民日报》的报道为:“代表团受到日本文化界和其他各界知名人士、东京华侨总会代表共一百多人的欢迎”⑤。《朝日新闻》更是在代表团访日前两周开始预热:“他们是受亚非作家会议日本协会(负责人堀田善卫)的邀请,计划在日本停留1个月”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之间于去年10月在北京签订了1965年度日中两国文化交流计划,本次就是按此计划实施的交流活动”⑦。
但是,这种友善平和的外表显然隐藏了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冷战”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为了追随美国,一直为中日文化交流设置种种障碍。直到1955年,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才实现了两国学术界的首次互访。但因“长崎国旗事件”和“新日美安全条约签订”的影响,中日文化交流举步维艰。1960年以后,随着中日政治关系的缓和,新中国作家才真正意义上踏上日本的国土⑧。在老舍访日之前,中国作家代表团曾两次访日。1961年3月,巴金率领代表团参加了“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自1958年参加在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以来,中国作家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就成为国家外交工作的一部分,通过在文学领域与新兴的亚洲独立国家展开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在美苏两大阵营之外,寻找到新的发展空间⑨。因此,亚非作家会议为中日作家的交流提供了亲密接触的机会。而此后1963年巴金和冰心的访日,1965年老舍访日也被纳入国家的外交轨道。
此次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构成颇有“新意”。团长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在日本也颇具声望。日本战后曾出现过“老舍热”,《四世同堂》被翻译到日本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骆驼祥子》在日本也读者众多,先后出现过七个日文译本⑩。因此,《朝日新闻》为了引起日本读者的关注,报道中大多以“老舍”为标题。其次,副团长刘白羽,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8年开始参与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工作,1961年就曾访问过日本,对日本文学界非常熟悉。而团员张光年不仅是评论家代表,而且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能够很好地把握访日的政治方向。另一团员杜宣则早年留学日本,1960年代之后,一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派驻亚非作家会议常驻代表,与很多日本作家交往颇深。年龄最小的茹志鹃是代表团中的“青年骨干”,这次与前辈作家出访也表明获得了某种“承认”,她的加入不仅展现了当时中国女作家的精神面貌,也有利于在与日本女作家交流时更好地开展工作。
在一个月零四天的行程中,老舍一行参观了东京、大阪、奈良、京都、箱根、镰仓、仙台、日光等地名胜,拜访了近30位日本知名作家、评论家的私邸,参与了亚非作家会议日本协议会、京都大学中国文学会的活动,与日本脚本作家、京都业余女性文学爱好者等群体进行了交流。这次被日本学者称为“超人”行程的日本之旅,对于已经66岁高龄,腿脚不便,因为高血压经常无法写作的老舍来说,显然颇为“辛苦”。在日本作家回忆中,访日时期的老舍“清瘦矮小”“显得特别老”,“象个终身终世埋头于某项手艺的工匠”。
从一些细节还是能够察觉到这次访日之行的“危险”。因为中日当时并未建交,只能从香港中转。“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之后,出访时的航班安全成为了敏感话题。在香港等待赴日的老舍,经常无法入眠。另外,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旁常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游行示威,杂以怪叫”。
老舍的访日之行并没有后来叙述中那么“愉快”,夹杂其中是严肃的外交任务,繁重的日常行程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但为了打破中日交流之间的壁垒,年迈的老舍愿意克服困难,承担起那份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在“疲惫”背后,始终给周围人一种“硬硬朗朗”的感觉。
二、对日印象:源自日记与旧体诗
收录于《老舍全集》的1965年日记,只有3月20日至4月29日赴日期间的记载。其中对于去过的地方,遇到的人,甚至吃过饭的菜单,事无巨细,依次罗列。但这些文字多为碎片式,表达也缺乏逻辑,看上去像老舍为创作长文准备的素材。其次,日记中并没有过多表现初访东瀛的兴奋,只有“饮酒写诗,甚快”“路过芦湖,甚美”“极倦怠”等为数不多的情绪表达。
这种语言上的“谨慎”,并不是个性使然,对比老舍1961年夏天的内蒙古之旅,他不仅发表了三十余首旧体诗,还创作了新诗《扎兰屯的夏天》,散文《内蒙风光》《可爱的内蒙古》等,他动情地写到:“我是那么快活,我时时刻刻总想唱一支歌!”情感体验的“缺失”,也不完全是外事纪律的要求,因为其他作家留下了极具“感情色彩”的文字。刘白羽在《樱海情思》中深情描述了这次充满美好回忆了樱花之旅:“我在这大地上行走过,我不只留下脚印,我也留下我的一段生命。”而张光年则永远难忘好友龟井胜一郎在病重之际却坚持出席酒宴,“向中国作家告别,也是向他多年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告别”。
访日途中老舍的“沉默”,可以作为他晚年心境的一种写照。一方面,访日前的几年,老舍已经渐渐远离文坛的中心,创作数量也是逐年减少,面对各种批判活动,他大多采取了不表态的缄默态度。另一方面,在访日期间,他身处多种角色之中,当作为文化官员时,他时刻要维护国家的形象,发表符合国家意志的言论;但是作为作家,他又希望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可以没有“束缚”地进行精神交流。当老舍无法化解不同身份造成的重重矛盾时,他只能选择用一种“沉默”来隐藏真实的情绪,或者用较为含蓄、暧昧的话语来表达。
老舍访日期间共创作了34首旧体诗,其中多为应日本友人邀请写的赠答诗。这些诗主要写给一直投身于中日文化交流、曾访华过的日本学者文人。针对不同的对象,老舍在创作时有着各自的考量。如《赠白土吾夫》:“白花笑对紫花开,土暖风轻春雨来。吾辈生涯爱劳动,夫随妇唱菜亲栽。”就是一首藏头诗,对应了“白土吾夫”的名字。白土吾夫自1956年开始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工作,曾接待梅兰芳为团长的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演出,随后曾一百多次访问中国,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在老舍访日过程中,他几乎全程陪同,这首诗就表达了老舍对于老朋友的感谢。又如《赠土歧善麿》一诗:“白也诗无敌,情深万古心。愁吟启百代,硬语最惊人。”3月25日的《老舍日记》中,在“土歧善麿”名字的后面标注有“杜诗”的字样,可见老舍对于接触的日本友人有过详细的了解。土歧善麿是日本著名的歌人和国文学者,曾翻译杜甫诗歌,著有《新译杜甫诗选》。在诗中,老舍首句就摘用了杜甫《春日忆李白》中的“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中的句子,后面“愁吟”“硬语”也反映了杜甫诗歌的典型特征与风貌。老舍晚年的旧体诗呈现出“师唐倾向”,他对于杜甫诗歌的驾轻就熟,使得在同日本友人交流过程中,让对方很容易体会到来自中国的美好情谊。收到老舍赠诗的日本友人,也会用和歌的方式进行唱和,如日本诗人扇畑忠雄就写有:“孤芳自赏还自怜,老舍先生倚杖前。”
访日期间,老舍还创作了不少纪游诗。其中既有对京都美景的赞赏,也有对奈良历史古迹的感怀,还有给聂耳墓献花时对“谱歌人”的纪念,以及在仙台鲁迅碑前对先贤的敬仰。老舍的纪游诗同样充满着唐诗气质,诗歌中的意象、色彩、声音都映照着盛唐文化的图景。比如在游览奈良的时候,老舍写道:“阿倍当年思奈良,至今三笠草微黄。乡情莫问天边月,自有樱花胜洛阳。”第一句叙述了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来中国留学的历史,第二句古今对比,“三笠”一词则点出了阿倍仲麻吕《三笠词》中“春日三笠山,明月出山前”的典故。“明月”和“洛阳”都是唐诗中经常使用的意象,“微黄”“樱花粉”中明亮的色彩对比也辉映着盛唐景象。
老舍在回国之后,曾把在京都和奈良时写的不少纪游诗寄赠给郭沫若,请他“斧正”。郭沫若也曾创作过相似的旧体诗,1955年在访问奈良的唐招提寺时,他写下《拜鉴真上人像》:“弘法渡重洋,目盲心不盲。今来拜遗像,衷怀一瓣香。”这首诗表达了对鉴真这位中日友好先驱者的崇敬。同为致力于中日交流的著名作家,老舍和郭沫若在创作时,经常从历史中汲取中日文化之间的认同感,其中既有对中日文化使者的怀念,也有对于源自中国的日本文化中服饰、饮食、礼仪的青睐,而承载各种情绪的旧体诗则成为传递情感时中日文化人之间重要的纽带。
三、拜访作家:传递友善与期待
老舍在访日过程中,行程密集地前往了中岛健藏、龟井胜一郎、白石凡、芹泽光治良、木下顺二、阿部知二、志贺直哉、依田义贤、谷崎润一郎、大冈升平、丹羽文雄、水上勉、井上靖等人私邸,加上在欢迎会上的交流,可以说与当时的日本文坛有了一次深入的接触。
这些作家中,老舍最熟悉的就是一批投身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左翼作家和评论家。在访日之前,老舍就曾多次与来华访问的日本文艺界人士进行过交流。如木下顺二回忆,在1964年访华期间曾专门前往人艺看《茶馆》,在老舍家中与他愉快地谈论起“日本崇尚菊花”的话题。因此,日本作家期待通过老舍访日,在向中国作家介绍日本文坛现状的同时,让日本读者有机会和老舍见面,使得中日之间的交流更加的“有效”。
老舍一行到达日本之后与时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以及副会长龟井胜一郎有过多次的会面。特别是回国前的聚餐,刘白羽和张光年后来均回忆,这其实是病重的龟井胜一郎与中国友人间“最后的晚餐”。1949年以后,正是在这批日本左翼作家和评论家的努力下,中日文坛间才保持了持续的交流,正是中日作家朝着共同目标执着追求,才促成了此次老舍之行。
老舍访日期间接触最多的日本作家之一是井上靖。通过这次的交流,井上靖体会到了老舍作为团长角色的艰难,“老舍应对有方,机敏周到。看来他始终在努力不要让对方感到不满意”。日本作家对于老舍,不像郭沫若、巴金、冰心那样熟悉,因为他之前并没有留日经验。例如井上靖曾提到一个细节,老舍曾在宴会上讲了一个关于“壶”的故事。一位破落子弟藏有一只珍贵的瓷壶,因不愿意让觊觎的富豪家得逞,选择与壶一起同归于尽。日本老作家广津和郎听后“当场驳斥”,认为在日本面对如此珍贵的宝物,“决不会去摔破它们的”,场面一度比较尴尬与紧张。就如刘白羽后来所说,“其实老舍和广津各自讲出各自的道德典范:老舍说的是面对横梁,宁死不屈;广津说的是不顾自己,珍惜国宝”。但这体现出日本作家对于老舍的某种“隔膜”,他们并不了解老舍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既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助兴的笑话”,也不会体察到老舍当时的境遇与这个故事之间的内在联系。老舍去世后,当井上靖再次提起这个细节,日本作家开始反思,认为这个故事是老舍命运的写照,对于老舍的人格肃然起敬。老舍的形象在日本作家眼中,经历了一个从“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到“令人敬佩的作家”的转变。
老舍出访的重要任务是做“中间力量的工作”,与这类作家交流时显然更需要把握尺度与注意技巧。水上勉就是对象之一,他是当时日本炙手可热的作家,因发表《雾与影》《海的牙齿》《饥饿海峡》等作品广受好评,他的小说社会批判性强,常常以揭发社会黑幕为主题,被认为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代表。但在1965年之前,水上勉对于“中国的情况一无所知”,作家老舍更是“不大熟悉”。在《蟋蟀葫芦》一文中,他回忆了老舍造访的经历。老舍“质朴”的第一印象拉近了与贫苦出身的水上勉之间的距离。他们并没有讨论政治外交的话题,而是从“蟋蟀葫芦”这个小物件聊到了民间习俗,谈话在老舍邀请水上勉访华的美好期盼中结束。若干年后来看,这显然是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以老舍为代表的中国作家给水上勉留下了博学多闻、平易近人的印象。此后,水上勉曾多次访华,为了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老舍与日本青年作家的交流也值得注意。老舍曾创作过一首名为《赠有吉佐和子》的旧体诗,其中写到:“有吉女文豪,神清笔墨骄。惊心发硬语,放眼看明朝。”有吉佐和子是日本战后著名的女作家,作品擅于揭露社会问题,特别是长篇小说《非色》(1963)批判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以及“世界各国的不平等思想”。虽然除了那首旧体诗,老舍没有留下其他文字,但是从老舍去世后,有吉在中国访问期间,特意走访调查寻找老舍死因可以看出,两人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来自老舍的信任与友善,使得这位日本青年作家更加明确想要了解中国的愿望,日后完成了《有吉佐和子的中国报告》等作品。
在访日过程中,老舍虽然在情感上并没有过多的外露,但是在和日本作家交流的过程中,努力传达了来自中国作家的善意。对于老朋友一直以来的情谊,老舍格外地珍视;而对于日本青年作家的支持与鼓励,也显示出他对未来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某种期待与憧憬。
四、媒体访谈:为中国文化界发声
老舍在日本接受的媒体专访以及与日本作家的对谈,为考察本次访日之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在“安保运动”中明确的政治独立目标,也慢慢转化成了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在地方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城乡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得一部分日本知识分子站在了反商业主义和社会批判的立场,而面对着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近邻中国,他们急需从中国经验中寻找方法,破解自己的文化困境。因此,面对着老舍一行,日本文艺界最关注的问题可以用现在、传统、未来这三个关键词来概括。
1965年3月29日,《朝日新闻》就关心的“中国文学界的现状”等问题采访了老舍。老舍高度肯定了梁斌、杨沫等作家表现“无所畏惧的革命者的优秀作品”;对于“深入生活,描写人民”的创作方法,老舍表现出谦虚的态度,认为自己对“全新组织”了解得还不够透彻。当被提问到如何评价邵荃麟“中间人物”的观点时,他认为“‘中间人物’本身是并不坏”,但“邵荃麟只是一味强调这点是不对的”。
众所周知,1962年大连会议中邵荃麟提到的“中间人物论”的观点,在此后几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964年更是发展为震惊中国文坛的“中间人物”事件。日本学者一直持续关注此事进程,对于“中间人物论”的观点也进行过深入探讨。例如竹内实在《中间人物论》中认为,通过了解以“中间人物论”批判为代表近来中国文坛的动向,有利于加深对于中国的认识。他敏锐地指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日本读者与邵荃麟的意见一致,认为人物有过于简单化的倾向,但他们仅就基本的文学常识发表观点,并没有触及中国文学的根本问题,而“中间人物论”的提出及其批判问题远比观点本身更为重要。
而以上老舍的回答,显然看到了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的错位,较为暧昧地点明问题的本质。与之相对,张光年在向日本读者介绍“中间人物论”这一观点时,则直接表明了批判的立场,认为这是用修正主义的理论,用同情的态度描写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时一种苦难和痛苦的过程,这是违背现实的。
而在与武田泰淳的对谈中,老舍少了些拘谨,多了几分朋友间的“畅所欲言”。他们的对谈主要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主题,老舍以作家身份向好友介绍了最新的写作计划。他极为真诚地表达了内心的矛盾,一方面觉得应该通过体验生活,书写全新的中国大众的生活;但是一方面却“不知不觉中,也常带着从前的生活,从前的感情,不能把变化后的新生活写得详尽”。老舍吐露了“五四”新文学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创作转型之艰难,虽然已经在创作理念上彻底向工农兵文学看齐,但在创作的具体过程中,已经形成的创作风格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
中日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面对着现代化带来的冲击,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成为两国作家在交流过程中关注的话题。例如在一次访谈中,日本作家木下顺二向老舍询问关于“京剧现代化”的问题。老舍认为京剧作为中国数百种地方戏曲的代表,对其进行改革具有指导意义。他提出要在京剧中融入现代主题,用这种古老的形式为社会主义新社会服务,而对于老的剧目,也并不是完全放弃,只是目前以现代主题为主。而在仙台召开的交流会上,老舍同样指出,对于京剧的改革,就是要在京剧里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因此作为创作者要去体验工农兵的生活,写出以工农兵为主的作品。而面对相同的问题,刘白羽的回答则和当时中国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结合更加紧密。刘白羽指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的京剧改革问题,其中也包括“恶意”攻击,给这个古老艺术形式注入新的生命力是一项时代的任务,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对于“未来”的阐释则是老舍一行访日的主要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努力践行中国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希望通过影响日本在内的亚非拉国家的世界想象,建构第三世界的共同体。例如,老舍多次在访谈中提到了“亚洲文艺复兴”的想法:“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和非洲各国,自古以来就有灿烂优秀的文化,但是近代以来,由于受到外部的压迫,被推广的文化越来越少了。……如果他们携起手来,一定可以振兴新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与老舍的观点形成呼应,刘白羽在谈到重写世界文学史时指出:“过去的世界文学史,老实来讲总是以西方为中心来写的。奋斗多年已经觉醒的亚洲人民,面对当前亚洲的斗争现实,为什么不会出现好的文学作品呢?”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的背景下,中国领导层十分重视与亚非拉各国之间的关系,将其视为反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日本显然在这些国家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以老舍访日为代表的中日文艺界交流,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外交宣传,也为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在反思日本与亚洲关系,建构新的世界秩序时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
结语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虽然受到战争等政治因素的影响,时而顺畅亲密,时而困难重重,但并没有中断。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家出访成为重要的民间外交手段,承担着外交上的联络任务。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日作家的互访经验为两国间的文学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通过作品的翻译和介绍,直接面对面的亲密交流,逐渐加深彼此的理解,形成中日友好的社会风气,让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变成了可能,进而为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出访日本既是怀旧也是探索。1955年之后,郭沫若、巴金、冰心等一大批重要作家访日,他们中有的曾早年在日本求学和工作,访日之旅变成寻访旧时光、邂逅老友的契机。而同时,访日经验带给中国作家更重要的是对于战后日本的全新认识与重新理解。他们一方面感叹于日本日新月异的变化,资本带来的物质上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也对商业社会天生具有的拜金本质,资本主义对于社会的毒害充满着警惕。如茹志鹃面对着机场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为钢铁资本家开辟道路,这样钢铁就有了销路”。老舍在日本特地参观了农户家庭,他敏锐地发现了贫富的差距:政府大量扶植中农以上的农民,但贫农们面对着来自美国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日本变成了一个参照物,让中国作家对于自己祖国的社会现状和历史进程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和体悟。
出访日本时,中国作家都十分注意言行,尽量避免由于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争端与冲突。他们在与日本作家交流的过程中,在表达自身立场的同时,传递来自中国的善意,努力营造亚洲共同体的印象。回国之后,作家代表团还召开报告会,把访日期间的所见所思传达给其他文艺界人士,如文洁若就回忆,老舍曾在文联礼堂做过专题汇报,并评价从未听过“如此生动的报告”。这种信息的传递有利于改变二战以来中国对于日本的刻板印象,而加深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而从日本作家的角度来看,老舍一行访日,是“过去十年间日中文化交流的基础上结出的果实”。战后日本左翼作家一直对于中国百废待兴的革命事业非常关注,努力创造条件来华访问交流。特别是60年代以后,围绕着《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问题,日本国内兴起声势浩大的“反美”浪潮,中国对于日本民间组织反美立场给予高度评价并明确声援。而表现在文艺界,日本作家在亚非作家会议等国际舞台上不断发声,希望寻求盟友,打破冷战背景下的对立局面,因此他们格外重视与一衣带水的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作家通过各种机会访华,创作了大批和中国有关的文学作品与报告文学。
作家出访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种民间外交的形式,有利于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推动国家间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合作。老一代作家因为有着广泛的国际关注度,更利于扩大出访的影响力;而年轻作家更容易在出访中感受到异文化带来的冲击,进而影响之后的创作。另外在与东亚汉文化圈的文人交往时,从历史中寻找文化间的认同感,通过诸如旧体诗的酬唱等方式,更加能够传达情意,引起共鸣。
注释
①③舒乙:《我的父亲老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第144页。
②例如孟泽人在《印在日本的深深的足迹——老舍在日本的地位》(《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一文中,对老舍访日期间拜访过的日本作家、前往的地点、日方相关报道做过整理。
④克莹:《患难情缘:老舍与胡絜青》,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3页。
⑤《我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人民日报》1965年3月27日,第6版。
⑥「中国の作家代表団近く来日」,『朝日新聞』1965年3月8日,第12版。
⑦「老舎氏、日本へ中国作家代表団長で」,『朝日新聞』1965年3月10日,第14版。
⑧参见孙承:《近现代中日文化交流概说》,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5-171页。
⑨参见王中忱:《走读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
⑩参见布施直子:《老舍在日本被接纳之状况》,《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