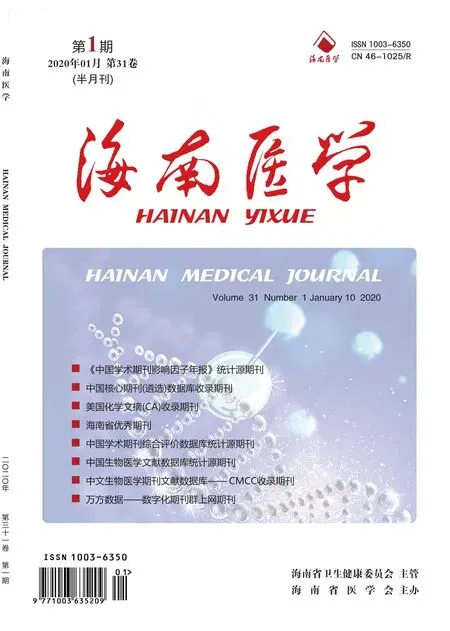促红细胞生成素在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的治疗作用
2020-01-09潘广艳王悦沣综述任光阳审校
潘广艳,王悦沣 综述 任光阳 审校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 遵义 563000
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pontaneous subarachnoid hemorrhage)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发病后当即死亡率占10%~15%。尽管治疗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然有25%的患者在发病后两周内死亡,且有20%~30%的幸存者伴有严重的终身残疾、行为和认知障碍,是一种严重致命的出血性脑卒中[1-4],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严重负担。迟发性脑缺血(delayed cerebral ischemia,DCI)是蛛网膜下腔出血严重的并发症,是SAH临床预后不良的决定性因素。其中脑血管痉挛是引起迟发性脑缺血的主要原因,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此外研究还表明微血管痉挛、微血栓、皮质扩散去极化和脑自动调节障碍也参与了DCI[5-9]。
众所周知,促红细胞生成素可促进红细胞的生成,随着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及其受体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发现以及其他研究表明,发现EPO对神经系统有着很大潜在神经保护作用。研究者通过大量的研究证实EPO具有抗细胞凋亡、抗炎、抗氧化应激、促进神经发生、促进血管生成、营养神经作用[11],还可以降低迟发性脑缺血发生率、预防脑血管痉挛、显著降低严重血管痉挛、预防再发脑梗塞以及降低自身调节受损的持续时间[10]。EPO是作为一种保护因素存在于脑组织中的。
1 蛛网膜下腔出血损伤机制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引发的脑损伤按照时间的不同分为早期脑损伤和迟发性脑损伤。
1.1 早期脑损伤 是指发生在72 h内的脑损伤。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发生后颅内压升高,导致脑血流不足、脑灌注压降低[11-12],进而引起脑局部缺血、缺氧,缺血缺氧引发脑毒性物质(如谷氨酸、红藻氨酸、血红素、氧自由基等)产生、释放及脑细胞毒性脑水肿,颅内压升高更进一步加重脑缺血、缺氧,从而造成神经元细胞及脑血管内皮细胞凋亡或坏死,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2 迟发性脑损伤 是指脑出血后第一次CT等检査未发现脑损伤,经过一段时间(数小时、数日或更久)后发现或在原无损伤的部位出现了新的脑损伤,如脑血管痉挛、再出血、脑积水等。其中脑血管痉挛是最常见的迟发性脑损伤,也是迟发性脑损伤最主要的原因。有研究表明,脑血管痉挛引起的变化与蛛网膜下腔血凝块的厚度有关,表明此过程开始于血液和血液分解产物释放到蛛网膜下腔[13]。SAH后血液进入到蛛网膜下腔,红细胞裂解释放出的血红蛋白(Hemo-globin,Hb)及其降解产物,可导致30%的患者脑血管狭窄和迟发性脑损伤[14]。SAH后Hb、氧合血红蛋白(Oxyhemoglobin,OxyHb)进入到蛛网膜下腔,OxyHb产生的活性氧(ROS)和血红蛋白可清除游离一氧化氮引起血管收缩[15]。OxyHb还会降低K+通道的活化,导致细胞内钙离子激增而引发血管收缩[15-16]。目前引起脑血管痉挛确切机制尚不明确统一,被认为是多种潜在机制共同作用,包括炎性因子、氧化应激、血管内皮细胞凋亡和坏死、一氧化氮产生减少、内皮素-1增加、钙离子及扩散皮质去极化等[17-22]。
2 促红细胞生成素在神经系统中的作用
胚胎直至妊娠晚期,EPO是由肝脏产生的;此后逐渐过渡到由肾脏产生,并在出生后完成。在成年人中,肾脏是EPO产生的主要器官,10%~15%是由肝脏和其他器官产生。继EPO及其受体在神经系统被发现后,其在神经系统中发挥的潜在保护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了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2.1 EPO的神经保护作用 研究发现EPO及其受体广泛存在于大脑中。大量体外及体内研究都表明EPO在神经保护方面发挥着多种保护作用,尤其在神经系统受损时。EPO可以发挥多种作用来保护神经系统的完整性,如通过抗细胞凋亡、坏死保持血管完整性,增加NO的产生及释放降低血管痉挛的发生等。EPO对各种脑损伤如局灶性脑缺血、新生儿缺氧缺血、短暂性脑缺血、创伤性脑损伤、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出血、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等模型中都有抗细胞凋亡、减小缺血半暗带、抗炎、抗氧化等作用[23]。
2.2 EPO的临床效用 鉴于大量实验基础研究以及EPO在不同形式脑损伤中表现出的保护作用,研究者开始将EPO应用到临床患者来观察EPO对人类的神经保护作用。在7例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挛患者中,连续3 d输注30 000 IU EPO,发现脑组织氧张力明显超过基线,数小时内就看到了明显效果,其恢复大脑的自动调节能力和抗炎作用效果被视为可能的潜在保护作用[24]。
3 促红细胞生成素在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的信号转导及保护作用机制
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引发脑内一系列神经保护通路激活。EPO分子与促红细胞生成素(EPOR)结合,激活EPOR同源二聚体,使酪氨酸激酶-2(janus tyrosine kinase-2,JAK-2)磷酸化后激活,JAK-2激活后引起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STAT)、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核因子(NF-κB)、核因子-红系2-(NF-E2-)相关因子2(Nrf2)等二级信号活化,即MAPK转导途径、PI3K转导途径、STAT转导途径、NF-κB转导途径、Nrf2通路的活化。
MAPK通路激活后可对抗谷氨酸盐的毒性,减轻脑细胞毒性水肿,保护神经元[25]。CHEN等[26]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兔模型中发现,rhEPO可激活基底动脉中JAK2和STAT-3通路,通过上调抗凋亡基因如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Bcl-2)、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xL(Bcl-xL)等的表达来减少脑血管内皮细胞凋亡,并提出了rhEPO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后脑血管痉挛的治疗作用与其抑制内皮细胞凋亡有关。另已有研究表明小胶质细胞在炎症相关的神经损伤中起作用,小胶质细胞分为两型:M1型小胶质细胞和M2型小胶质细胞。M1型小胶质细胞增加促炎介质的分泌,这会损害轴突再生[27];相反,M2型小胶质细胞可介导神经保护功能并促进神经发生[28-29]。WEI等[30]研究证明促红细胞生成素可通过EPOR/JAK2-STAT3途径调节M1型小胶质细胞向M2型小胶质细胞极化,减轻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炎症反应;此外他们在其研究中还发现EPO降低了促炎细胞因子(TNF-α和IL-1β)基因表达,并增加了体内或体外抗炎细胞因子(IL-4和IL-10)基因表达,增加了抗炎性细胞因子达到抗炎目的。EPO是一种多效细胞因子,它可以预防许多脑血管疾病中的神经细胞凋亡[31-32]。SAH后PI3K磷酸化后,可激活下游Akt,Akt-1激活后通过稳定线粒体膜电位以及阻止线粒体中细胞色素C释放到细胞质,抑制了半胱氨酸蛋白激酶(Caspases)家族激活,从而阻止了神经元细胞凋亡,提高了神经元的存活率[33]。SAH后血管痉挛是常见的并发症,并且是延迟性脑损伤的主要原因。NO是体内调节血管舒张的重要体液因子,可缓解脑血管痉挛,其合成受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的调节。EPO可以通过调节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的表达来调节NO的产生,进而改善脑血管痉挛。尽管EPO和NO之间的确定性相互作用关系尚未被完全认识,但目前认为EPO通过激活蛋白激酶B(Akt)致内皮细胞中eNOS的磷酸化使NO生成增加可能是EPO潜在治疗SAH后脑血管痉挛的重要机制[34]。研究还表明在内皮祖细胞(EPCs)中,EPO通过eNOS的Akt依赖性激活可促进大脑新血管形成[35]。蛛网膜下腔出血后,NF-κB可在基底动脉中表达增加,增加炎症因子的释放,EPO可以使其表达降低来减少促炎细胞因子(TNF-α和IL-1β)基因表达,从而降低炎症反应。以上这些转导途径及机制在蛛网膜下腔出血后并非分开单独起作用,而是几种途径及机制同时进行来维持神经系统的完整性。此外,有研究表明Nrf2在中枢神经系统(CNS)中表达,并且在炎症和脑损伤的反应中上调[36],但Nrf2蛋白的上调通过激活Nrf2-ARE途径支持作用机制,从而减少氧化应激[37]。SAH的基础性研究表明EPO可通过调节Nrf2/ARE途径,调节细胞凋亡和氧化应激反应机制。
综上所述,SAH后EPO的神经保护多而复杂,EPO在SAH中对神经的保护作用机制如下:对抗细胞毒性、抑制神经细胞凋亡、调节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进而调节NO的产生、抗炎作用、抗氧化作用、促进神经发生及血管生成等。促红细胞生成素在蛛网膜下腔出血中通过多种作用机制交互作用共同保护中枢神经系统的完整性。此外还可能包括一些其他的潜在的保护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4 促红细胞生成素在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的应用
BUEMI等[38]首次发布了EPO在SAH兔模型中的作用,他们发现腹腔注射EPO后可提高兔运动功能和存活率。之后研究发现全身大剂量应用EPO能够显著缓解大脑基底动脉血管收缩,改善临床神经功能结果,减少神经元坏死及凋亡,并能够降低S-100蛋白(脑脊液中脑损伤的标记物)水平。基于大量实验研究已证明的EPO神经保护作用和SAH脑损伤机制,研究者将EPO应用到SAH患者中。
2007年Springborg及其合作者首次报道了关于SAH后患者应用rHuEPO的双盲临床试验[39],73例诊断为SAH的患者被随机分配到EPO治疗组[500 IU/(kg·d),连续3 d]和对照组。6个月后进行格拉斯哥预后评分,评估了继发性缺血的替代指标,即经颅多普勒(TCD)流速、症状性血管痉挛、脑代谢、颈静脉血氧饱和度、脑损伤生化标志物和血脑屏障完整性。但作者发现除了EPO治疗组的脑脊液(CSF)中EPO浓度增加外,两组间在统计学上并无显著的组间差异,也因此未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作者针对此将其归因于样本量有限,部分原因归结为患者依从性差。虽然这次临床实验未能得出想要的结果,但并不能否定EPO对SAH患者潜在的神经保护作用。
后来TSENG等[40]进行了第二个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评估了静脉应用EPO对aSAH的患者的潜在作用。80例aSAH患者在48 h内随机接受安慰剂和90 000 U EPO治疗;应用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评估血管痉挛的发生率、持续时间、严重程度以及血管自动调节损害的持续时间,还记录了出院时和6个月时的DIND及相关结果;他们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EPO将严重血管痉挛的发生率从27.5%降低到7.5%,延迟性缺血性的发生率从40.0%降低到7.5%,通过观察到的EPO可降低血管痉挛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以及缩短脑自动调节受损的时间这些临床结果,做出了EPO可以减轻继发于SAH后的脑缺血损害的发生这一结论假设。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病例数量少、促红细胞生成素剂量应用单一、单个中心、缺乏预定的CT扫描检查,但本研究在人类中证实了促红细胞生成素在动脉瘤性SAH后限制脑血管痉挛和缺血的潜在有益作用[41],这和在动物基础研究中观察到的结果是一致的。该研究为EPO未来应用治疗SAH患者潜在的脑保护作用提供了新的依据和证据。
5 小结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一种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其发病急,致残率致死率高。对于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治疗根据患者病情可分为内科治疗和外科治疗,但内科治疗目前仍不乐观。大量的动物基础性研究及一些临床研究都表明了EPO对神经保护作用有很大潜能。SAH后早期应用EPO可能通过抗细胞凋亡、抗氧化应激、抗细胞兴奋性毒性、抗炎等机制来发挥神经保护作用。这些机制在SAH后迟发性脑损伤中也继续发挥着作用。EPO还可能通过调节脑血管的收缩程度来减轻脑血管痉挛严重情况,进而减轻继发于SAH后的脑缺血损害。此外,EPO还在非神经系统中也发挥着保护作用,SAH后除了神经系统并发症外,还有非神经系统并发症,以前的研究表明,SAH可引起明显的肺水肿和肺炎[42]。SAH后肺水肿和肺炎的发展是SAH患者死亡率增加和神经功能不良的独立预测因素;ZHOU等[43]首次证明了EPO可以通过减轻肺部炎症和体内不稳定锌的积累,在SAH诱导的肺损伤中发挥肺保护作用。由此可以看出EPO在蛛网膜下腔出血诱导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和非神经系统并发症中都有保护作用,但具体机制仍不清楚,还需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
关于EPO在蛛网膜下腔出血中的作用,大部分研究者都围绕EPO的保护作用来进行设计研究,至于EPO在蛛网膜下腔出血中潜在的副作用等还未可知。这也给EPO在临床中应用带来了警惕。在以往的SAH研究中,对于EPO的剂量的应用都较为单一,最大耐受剂量或最佳应用剂量尚未确定。SAH发病急,诱导的并发症重,由并发症所致的残疾和死亡率较高。EPO虽然可以通过多种现已知的可能机制来发挥保护作用,但SAH后多久应用EPO或者说在什么时间段应用EPO可以更好更佳地发挥EPO的潜在保护作用也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至今在研究中关于EPO给药途径无非静脉给药或皮下注射,哪种给药方式较佳,是否还存在其他给药途径,这也是需要研究的方面。而且无论在SAH动物模型中还是SAH临床研究中研究者都是单一应用EPO,与其他药物联合应用,是否可以更大发挥EPO的潜在保护作用或降低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也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
目前尚缺乏EPO治疗SAH的远期疗效观察,这为EPO未来治疗SAH留下了许多的不确定。但是已有研究证明EPO可降低血管痉挛的频率、严重程度以及缩短脑自动调节受损的时间,而且EPO在SAH中现阶段所发挥的神经保护作用和非神经保护作用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未来可以在应用EPO安全前提下,对EPO最佳耐受剂量、治疗时间窗、治疗持续时间、给药途径、联合用药、EPO衍生物等方面进行更深的研究。此外,目前关于EPO应用于SAH的多数研究主要基于小规模研究,未来基础研究或临床研究还需要增加研究对象,来获得更有说服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