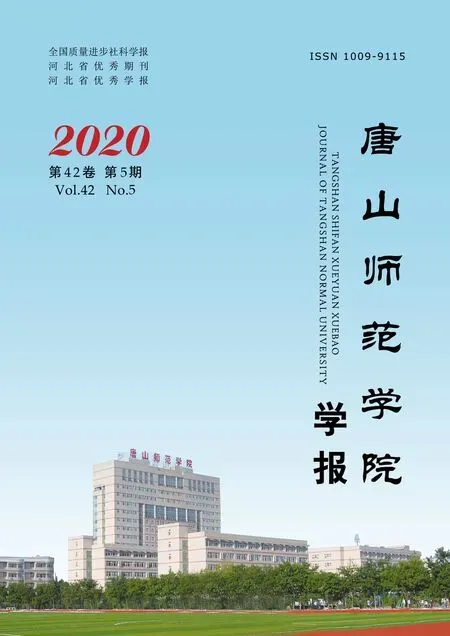论清朝社会结构与太平天国初期社会结构之异同
2020-01-09刘佐民
刘佐民
论清朝社会结构与太平天国初期社会结构之异同
刘佐民
(中共唐山市路北区委员会 巡察组,河北 唐山 063000)
在社会地位结构、生存活动结构、社会整合结构等领域,将清朝与太平天国初期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得出太平天国初期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于清朝社会等认识。
清朝;太平天国;社会结构;分化程度
清朝社会结构与太平天国初期的社会结构既有区别也有相同、相似之处。本文试图用社会学的方法在社会地位结构、生存活动结构、社会整合结构等领域,将清朝与太平天国初期社会进行比较,进而得出太平天国初期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于清朝社会等结论。
所谓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具有复杂性、整体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等特点。具体而言,社会结构包含着各种重要的子结构,除了作为基础要素的人口结构外,还有体现社会整合方式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体现空间分布形式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体现生存活动方式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体现社会地位格局的社会阶层结构等。在这些子结构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直接或间接体现社会子结构各方面的状况,各子结构间的变化存在互动关系,某一子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其他子结构的变化[1]。
一、在地位结构和生存活动结构方面
地位结构主要指社会阶层结构和阶级结构;生存活动结构主要包括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与消费结构,体现资源、机会的分配与配置过程。
清王朝的法典,对社会各种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均以不同形式分别有所规定。职业性质决定人的身份,身份依职业性质大致可分为三大基本等级:一是以皇权为中心的皇族、贵族及官僚集团,其职业属于管理性质,是特权等级的管理者;二是生产性质职业构成的平民等级,他们是社会的主体;三是从事服务性工作的职业,与主人有一定的隶属关系,由贱民等级和半贱民等级构成[2]。
第一个基本等级。皇帝,秦汉至明清时期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所谓“乾纲独断”。贵族,贵族由宗室贵族和衍圣公孔府贵族组成。宗室贵族,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受封爵,有参政权,爵位按一定制度世袭;有庄田,免田赋[3],还要领取俸禄和养瞻银。孔府贵族,孔子的后人被封为“衍圣公”,公爵世袭,拥有司法特权;拥有大量祭田,不纳赋税、例免差徭。官僚缙绅,科举出身的人成为官僚的主要来源,在司法上有特权,高级官僚有恩荫特权;领取俸禄和养廉银,有一定优免赋役、人丁的特权[4,p5072]。绅衿,是指有功名(学衔)而未仕的人物,在司法上有一定特权,经济上优免本身丁银。雍正四年再次明确:“绅衿祗许优免本身一丁”[4,p5073]。
第二个基本等级,平民。清制军、民、商、灶“四民为良”,即平民,在法律上称为“凡人”[5]。平民成分复杂,变化较多,经济来源不同。包括:庶民地主、自耕农、平民佃农、商人和手工业者、灶户、平民佣工、店伙、城镇居民、兵丁、民壮、乞丐,以及僧尼等在内。这个阶层没有特权,也是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等级。
第三个基本等级,半贱民、贱民。半贱民包括佃仆、雇工人。佃仆没有迁徙自由,财产权受到种种限制。雇工人称雇主为家长,具有主仆名分。清朝法学家沈之奇写道:“雇工人但受雇价为人庸工,工满即同凡人,与终身为奴婢者不同”[6]。奴婢是贱民中最主要的部分,男为奴,女为婢,奴婢与家长具有严格的主仆名分。这个等级的人在法律上受到压抑,规定不得与良民通婚,不得参加科举,也不得充任保甲长等。
清王朝等级结构是在皇权(王权)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满族入关之前就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并效仿明朝中央设立六部。著名学者经君健先生认为“清王朝整个国家机构都作为皇帝一人的办事机构而存在”[7]。当清兵逼近北京时对明朝官员宣称:“官来归者,复其官”,于是大批明朝官僚投降清方;明末官员通过归顺成为清朝皇权的工具,也再次成为特权阶层。清初还颁布了“投充人”法,为了增加奴仆数量逼迫一些汉族民众投充旗下世代为奴。可见,上述阶层的形成都离不开专制皇权的作用。各阶层的权利、财富依照其社会地位不同而不同。
关于秦汉至明清帝制王朝,刘泽华先生认为政治统治权和对土地与人民的最高占有、支配权是混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这样说,对土地和人身都是混合性的多级所有,王(皇帝——引者注)则居于所有权之巅[8,p31]。史实也的确如此,秦汉至明清王权专制国家的政治权力可以任意干预和改变土地占有形式和控制着广大生产者人身。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了中央集权时代以后,仍然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致,无不臣者”[9],与周天子口号完全一致;秦朝初年的“使黔首自实田”政策无非是承认原土地使用者拥有使用权乃至部分所有权。秦朝短暂,“汉承秦制”,汉武帝于元朔二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10],并在以后将迁徙豪强还形成一种制度。清朝颁布的“圈地令”,也是专制皇权掠夺土地的一种方式,给被圈地区的土地所有者带来灾难。
太平天国初期社会也是等级结构。等级身份依职业性质大致可分为三个基本等级: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贵族及官僚集团,其职业属于管理性质,是特权等级的管理者。有学者将太平天国统治集团分为“四等十九级”。第一等级为王:一级是天王,二级是东王,三级是西王、南王,四级是北王,五级是翼王,六级是燕王、豫王。第二等级为侯、丞相、检点、指挥、侍卫。第三等级为将军、总制、监军。第四等级为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11]。二是生产性质职业构成的“民”以及太平军士兵这个等级,按照《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兵、农是合一的。太平军初占武昌时设进贡公所与圣库,令居民进贡,“进贡与拜上异,拜上则为兵,进贡者依然为民也”[12,p594]。这说明原来清朝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只要归顺太平军,一般都转变为“民”这个阶层。依据《天朝田亩制度》及其实践,“民”这个阶层还应当包括:从事农业、公营手工业的“农”“工”“匠”以及从事公营商业等领域的劳动者。士兵的称谓有“兵”“伍卒”“牌面”等。太平天国初期社会中“民”应当是社会的主体。但是后期的“民”与前期的“民”是有一些区别的,如1860年洪秀全《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这里的“四民”含义与清朝就没有多大区别,应当包括庶民地主、手工业作坊主等。三是处于被惩处、被强迫地位的“奴”这个等级。至少包含三类人,太平天国官僚系统人员因罪被黜为“奴”[12,p639]的人。有学者认为当时“金陵”城内一些妇女处于“国家奴隶”地位,而另一些处于“家内奴隶”地位[13]。与此相关,太平天国后期允许其控制区域内存在“奴婢”现象。
太平天国等级结构也是在王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清王朝没有质的区别。太平天国仍然是君主制政体[14],1850年4月洪秀全在拜上帝教各位骨干力量的支持下“登极”“穿起黄袍”[15]。1851年在永安,洪秀全封东王杨秀清为九千岁、西王萧朝贵为八千岁、南王冯云山为七千岁、北王韦昌辉为六千岁、翼王石达开为五千岁[16,p102]。1851年洪秀全以天王名义在永安发布诏令称:“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以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17]。1851年太平天国还颁布了“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太平礼制》,其目的是通过礼制上的规定,进一步强化等级制和世袭制。虽然《天朝田亩制度》对土地所有权讲的并不具体,多年来学术界对此看法很多,但是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类观点:王田制[18,p60]、公有制[19]、小农土地所有制[20]。本文同意“王田制”观点。按照太平天国的理想,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完全是由王权为中心的官僚系统支配的,在民间不存在土地使用权的交易等问题,这与清王朝皇权、地主以及自耕农对土地混合性的多级所有还有一定距离。
清王朝等级结构与太平天国初期等级结构也有区别。首先,太平天国贵族官僚阶层经济特权少有明文规定,这与清朝不同,入关之前满族就已经是阶级社会。起义之初,太平天国阵营在“天下总一家,人间皆兄弟”这种宗教宣传氛围,主张“人无私财”、实行以“圣库制度”为基础的配给制、“别男行女行”禁欲主义等政策,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太平天国初期社会的君主制、等级制、世袭制开始逐渐地形成。在起义初期,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大体过着与太平军将士一样的生活。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继续推行一切财物尽归圣库公有政策,军政人员和百姓生活实行配给制。曾经每25人每7日给米200斤、油盐各7斤[16,p277]。在“礼拜之辰”,每名卒长领取“礼拜钱”70文,每名两司马35文,每名牌面兄弟21文。与此同时贪腐现象迅速滋长,形成了“莫不私藏秘积,足以自俸”[16,p277],依据爵位、官阶大小所占财富不等的事实。就是到后期其贵族官僚阶层经济特权也是少有明文规定的。其次,按照太平天国规定,其贵族官僚阶层世袭制的范围远远大于清朝社会,规定军帅就世袭,清朝仅仅是贵族世袭制。太平天国“民”这一等级,其中包含的职业种类大大少于清朝。这都是导致太平天国社会组织结构更具刚性结构特征的原因之一。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在太平天国初期社会,以家庭背景因素为主的“先赋性”社会因素对个人向较高的社会地位流动的影响超过清朝社会;换言之,在清朝社会以后天的学校教育及自身的努力为主的“后致性”社会因素对个人向较高的社会地位流动的影响超过太平天国初期社会。
二、在社会整合结构方面
社会整合结构体现社会整合方式,包括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组织是为实现对社会权力、权利、资源的配置而构建的体系。一个社会中,组织又分为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社会整合,是指不同社会要素以某种方式结合为一个整体。社会整合使社会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是社会生存和进化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中,政治与社会分离(马克思曾称之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在这里政治仍起很大的整合作用,但最基本、最常见的整合力量却来自政治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市场[21,p173-174]。
清朝政治组织体现为皇权(王权)——官僚系统。清朝地方官制实行省、道、府、县的四级行政制。尽管其官僚系统也是皇权的工具,但是其各级各类机构分工是很具体的。清朝县以下组织的设置并不统一,各地的名称和层级也不完全相同。可以称为县以下乡里基层组织,其职能包括:作为服役征收的机构,以维护地方治安,作为劝农的组织,根据乡约法以宣传教化等。对乡里组织负责人所扮演的角色,存在大致两种认识。其一认为传统的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乡里组织负责人扮演的是国家的代理人;其二认为“国权不下县”,基层社会有一定的自主性,国家权力对这种自治化倾向采取妥协屈就的态度,形成了“乡绅自治”。但这两种观点对于乡村精英(包括乡里组织负责人)与普通乡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却有一致的看法,即把农民视为被动、消极的对象,他们不仅在专制主义国家政权面前软弱无力,任人宰割,而且面对乡村精英的统治也无所作为[22]。
清朝社会中的经济组织,虽然都是在皇权的监控之下,仍然可以按照不同性质进行分类。如,从经营者身份可分为官营经济组织、民营经济组织;从生产目的可分为自给性经济组织、商品性经济组织;从营销范围可以分为经营国内贸易的经济组织、对外贸易的经济组织等。雍乾时期,手工业生产与明代比较,无论官营、民营都有很大发展,其中重要的纺织、陶瓷、矿冶、制盐等业发展迅速。尽管小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像汪洋大海一样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制糖业、陶瓷业、制茶业、制盐业、造纸业等也都出现了脱离农业而独立存在的工场手工业。雍乾时期,商品交换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拥有资本较多的有盐商、米商、丝茶商、典当商、木材商和公行商等,也出现了与小商品生产者相连接的包买商。农业领域,有设立庄头进行管理的皇庄、王庄、八旗庄田,以及国家直接管理的民屯、军屯;庶族地主和自耕农成为主要的赋税承担者。雍乾时期,较多地出现了经营地主、佃富农这些活跃的经济组织。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雍乾时期,经济作物种类很多,花生、水果、玉米、番薯、药材、麻、竹、茶叶、香草种类众多。如:福建是种烟最早的省份之一,时人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疏》介绍:“今则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所获利数倍于稼穑[23]。鸦片战争前,国内市场主要商品粮食和棉布主要是农户家庭生产的。
明清时期社会组织是广泛存在的,比如半官方的里甲、乡约、社学、社仓、义仓等,血缘性的宗族义庄、地缘性的善堂善会,兼具地缘和血缘的会馆、公所等组织的民间属性更为明显,商业会馆和商帮也都是典型的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的社会组织都在皇权专制的监督之下运行。如:乾隆三十五年北京的河东烟行会馆规定:“凡五路烟包进京,皆按斤数交纳税银,每百斤过税银肆钱陆分。□□轻重,各循规格,不可额外多加斤两。苟不确尊,即系犯法”[24]。这与唐宋以来的行会一样,仍旧替官府对工商业者的统治和征敛服务;不过,它作为会员利益维护者的作用日益明显。清代社会组织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其社会服务功能。
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纽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清代的家庭分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联合家庭、家族家庭等,以核心家庭、直系家庭这两类占家庭的大多数,各种家庭不断互相转化。父家长制形成家庭的等级结构和男尊女卑的社会,清代父家长对家庭财产、妻子命运,以及家庭对外联系等领域有极大处置权,是家庭的主宰。这种家庭等级制是整个社会等级制的缩影,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从家庭到家族到社会都有着等级制。清代大多数家庭从事农业经营,它的主要功能包括组织农业生产,以及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
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已经民众化,不同的家族形成了以祠堂、族谱、族田、族学以及族长家法为特征的制度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族权。乾隆朝协办大学士陈宏谋说:“闽中、江西、湖南皆聚众而居,族皆有祠。”[25]清朝允许民间建祠堂祭祀祖先,是要民人“移孝作忠”,做君主的顺民。而祠堂则把忠君的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明清政权希望宗族用传统的儒家伦理‘齐家’,成为政权的基层组织,以维持地方秩序。”[26]政府对宗族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原则,政府有足够的力量令宗族沿着它的政令走,而宗族只能服从,无力抗拒,只能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清朝君主是绝对的权威,宗族是它的附属物。
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分为省、郡、县三级。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先后颁布了《百姓条例》和《天朝田亩制度》,这两个文献精神上是一致的[18,p62]。《天朝田亩制度》作为一套完整的方案,有些内容实行过,如圣库制度、兵农合一制度以及乡官制度等。该文献对太平天国基层组织形式即乡官做出具体规定:“凡设军,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设一军帅,次设军帅所统五师帅,次设师帅所统五旅帅,共二十五旅帅;次设二十五旅帅各所统五卒长,共一百二十五卒长;次设一百二十五卒长各所统四两司马,共五百两司马;次设五百两司马各所统五伍长,共二千五百伍长;次设二千五百伍长各所统四伍卒,共一万伍卒。”[27,p325]还规定每家皆“出一人为兵”[27,p326]。《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分配原则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把土地按每年每亩产量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27,p321]。有学者认为是由于战争和可操作性差等原因,这种具体规定未能实现。更早颁布的《百姓条例》规定:“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取,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12,p750]。
《天朝田亩制度》中关于农民生活的若干规定:第一,“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第二,“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但两司马存其钱谷数于薄,上其数于典钱谷及点出入”;第三,“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第四,“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27,p322]第五,“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27,p326]。太平军占领武昌、南京等城市后,把城市人分男行女行,按太平军编制“以二十五人为一馆”群居一所[12,p593],称为男馆、女馆以及老人馆、能人馆等,各家居民原有房屋被统一分配、统一使用,“逐日发米谷”[12,p621]。当时南京城内妇女和老人从事粮食、蔬菜生产以及打扫卫生等工作。还规定“凡年过六十及十五岁以内,或有残疾者,皆免打仗”[12,p621]。这说明男子多数要参加打仗。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当时南京仿佛是一座大兵营。太平天国初期,尤其是县以下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和文化教育组织是高度合一的。
可见,清朝社会整合方式与太平天国初期社会整合方式的相同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清朝与太平天国都不是近代化的社会。“传统社会是政治化的社会,在这里政治(基于道德或宗教等原因)是社会中的主要整合力量。”[21,p173]清朝社会与太平天国初期社会在资源和机会的配置上都是由政治组织——皇权(王权)为中心的官僚系统掌控。这一结构处于高度社会整合状态,在这种结构状态下的组织系统中,官僚系统是唯一自主的要素,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是其附属物,官僚系统对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是一种命令服从关系。
清朝社会整合方式与太平天国初期社会整合方式的区别则有:首先,与太平天国初期社会相比,清王朝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系统组织的功能以及相应的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从社会学角度,“社会分化是指社会要素的数量增生和/或功能特化。正像生物细胞的分化之于生物进化一样,社会要素的分化是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21,p173]。清朝社会这种分化表现在,官僚系统将部分行业管理的职能转移给一些社会组织,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的领域多于太平天国初期社会[28],因此清王朝社会生活领域的自主性相对要强一些。太平天国初期社会没有社会组织、民营经济组织,取消了家庭、宗族,作为宗族标志的族谱、祠堂以及祭祀活动成为太平军打击、损毁的对象。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清朝社会分化程度高于太平天国初期社会。其次,太平天国初期社会经济更具“自然经济”特征。明清时期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商品流通大大加强了,正是由于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才使得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分工互补,并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通过上文介绍,《天朝田亩制度》对于种植农作物、家畜养殖、陶冶木石等手工业都有规定,而且要求“通天下皆一式”,这里没有提到商业,它取消了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要求生产者自己留下生活的必需产品,多余的上交国库,由太平天国政权系统统一调配;若真的实施起来可是不顾各地具体自然环境和经济文化传统的。经君健先生认为自然经济单位的特征是:内部有自然的和专业的劳动分工,产品能够自足并以实物形态在内部直接消费和储备,成员之间有直接的劳动交换和实物交换,对内对外货币均不通行[29]。由此看来,太平天国在武昌、南京等城市政策以及《天朝田亩制度》蓝图,与清朝社会相比更具有“自然经济”特征。
总之,从古代政治思想史角度,刘泽华先生提出了“王权支配社会”观点。王权又称君权、皇权,秦汉至明清王朝,“王权——贵族、官僚系统既是政治系统,又是一种社会结构系统、社会利益系统,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这个系统及其成员主要通过权力或强力控制、占有支配大部分土地、人民和社会财富。土地集中的方式,主要不是‘地租地产化’,而是‘权力地产化’。这个系统在社会整个结构系统中居于主要地位,其他系统都受它的支配和制约”[8,p31]。不仅明清王朝如此,太平天国也是“王权支配社会”。本文认为,如果认为秦汉至明清王朝为王权支配社会的一般形式,那么太平天国政权为王权支配社会的特殊形式。有学者认为,以太平天国1854年决定施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为标志,其政权在经济、政治上逐步走向“封建化”,太平天国的统治集团也与他们原先所属的阶级——农民逐步脱离[30]。这也说明,太平天国初期社会作为王权支配社会的特殊形式逐渐向王权支配社会的一般形式转变。从社会学的角度,这种转变也是其社会结构的演变。
①文中太平天国初期指的是洪秀全等宣传“拜上帝教”,推行《百姓条例》《天朝田亩制度》等政策时期,以1854年实行“照旧交粮纳税”、1855年准许南京城内恢复家庭生活等政策为标志进入后期。“清朝”社会结构重点指1840年以前。
[1]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及其影响[J].中国经贸导刊,2010,27(7): 9-11.
[2] 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632.
[3] 昆冈,等.户部田赋[M]//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五十九,光绪二十五年.
[4] 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第18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4:85.
[6]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51.
[7] 经君健.论清代社会的等级结构[M]//经君健.清朝社会等级制度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1-127.
[8] 刘泽华.王权主义概论[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23(3): 30-32.
[9] 司马迁.史记: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533.
[10] 班固.汉书: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9:121.
[11] 吴雁南.太平天国前期的等级制度与政体[M].贵阳: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1981:1-17.
[12] 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4册[M]//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3] 廖胜,王晓楠.太平天国的婢女问题[J].史林,2008,23(5): 111-119.
[14] 戎笙.如何看待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J].历史研究,1981, 28(3):77-90.
[15] 梁义群.太平天国政权建设[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43-44.
[16] 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3册[M]//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7]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35.
[18] 戚其璋.《天朝田亩制度》新探[J].东岳论丛,1993,14(6): 57-64.
[19] 冀满红,燕红忠.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与中西文化[J].史学月刊,2005,55(7):56-63.
[20] 范文澜.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零五周年[M]//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史论文选.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1:7-10.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管理世界,1991,7(1):173-183.
[22] 申立增.清代乡里制度研究综述[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4(增刊):141-148.
[23]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第15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4: 107.
[24]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50-51.
[25]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第16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65.
[26] 常建华.有关明清家族制的是是非非[J].人民论坛,2018, 27(2):142-144.
[27] 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1册[M]//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8] 经君健.清代关于民间经济的立法[J].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4,9(1):42-55.
[29] 经君健.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论纲[J].广东社会科学, 1988,5(2):82-83.
[30] 王天奖.太平天国政权与地主阶级——兼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J].中州学刊,1981,3(1):122-135.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Soci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LIU Zuo-min
(Inspection Group, Tangshan Lubei District Party Committee, Tangshan 063000, China)
It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status structure, survival activity structur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structur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degree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early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Qing Dynasty; the early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social structure; the degree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K254.2
A
1009-9115(2020)05-0076-06
10.3969/j.issn.1009-9115.2020.05.015
2020-07-02
2020-07-30
刘佐民(1967-),男,河北唐山人,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