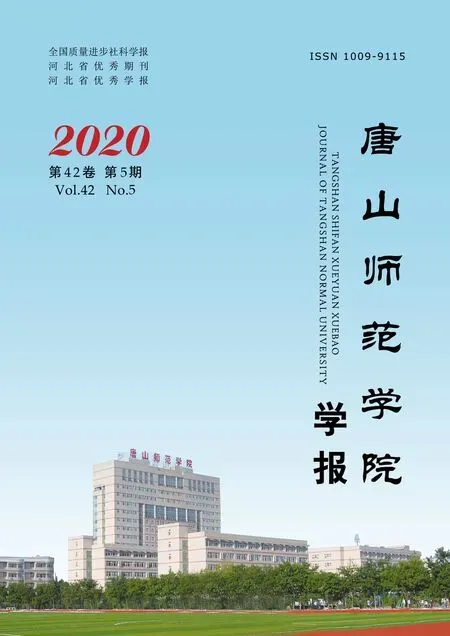“始于史料归于文学”——论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本事研究
2020-01-09陈婉琴
陈婉琴
“始于史料归于文学”——论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本事研究
陈婉琴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张均的本事研究主要以“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小说为研究对象,融合了“再解读”和“史实化”方法,利用丰富的史料探究本事与故事之间的“缝隙”,借助后现代理论揭示小说从本事到故事的生产过程和叙事实践,连通文本内外。张均的本事研究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博弈本事研究、人物本事研究和主题(问题)本事研究,具体操作分为三个步骤:梳理本事脉络——分析小说改写方式——探究叙事实践,这分别需要扎实的史料爬梳能力、细致的文本分析技术和广博的理论素养。
本事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践叙事学;张均
本事批评是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最早用于诗歌批评,后来相继应用于文言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文学批评中。本事,是作品创作所依据的素材,通常被认为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本事批评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还原和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方法,通过还原作家创作的历史现场或考证文学作品中人物、情节、环境的原型,解读历史意识形态和作家加工素材的方式、寄寓的思想情感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本事研究的运用不乏先例,但目前相关成果还不多,理论阐释不成系统、未形成一定共识,各家对本事研究的理解也各有差异。近年来,主要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张均凭借在制度研究和报刊研究中积累的史料爬梳能力,用史料研究文本,勾连文本内外,主动搭建自己的本事研究方法论,突破过往知人论世的研究框架,引起学界关注。
张均的本事研究主要以“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小说为研究对象,据笔者统计,张均早在2012年就以《召唤“隐藏的历史”——<暴风骤雨>动员叙述研究》为起点实践本事研究,至今已对《暴风骤雨》《保卫延安》《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董存瑞》《创业史》七个文本进行过本事研究。并且,在研究中,张均提出了自己对本事研究的理解:“依我之见,不但‘作家主体的心态’可以引入为史学化研究的问题,其实文本叙事实践也可引入为史料考订的最终‘落脚点’。……本事史料的存在,却可以使史学化研究突破古代文学本事研究‘知世论人’传统而深入到叙事领域。”[1,p14]在笔者看来,张均本事研究的叙事实践关注“十七年”小说家如何根据自身的在场体验和活动记忆或在场收集的素材讲述当代中国的革命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叙事法则和作家个人的叙述姿态如何影响文本的生成。本文主要解读张均本事研究的方法理论、研究内容和技术操作,探究本事研究作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
一、“再解读”与“史实化”的融合
本事批评对于所要研究的文本本身以及相关的史料状况是有一定要求的。面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激烈转型,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少作品记录了社会变动的现实状况,尤其是“十七年”小说,大多取材于1940-1950年代的革命战争生活,文本内容有较为密集的现实依托,是本事批评得以展开的基础。而近三十年来,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失却轰动效应”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入“文学史研究一统江山”的境遇,许多重要作家作品的史料得到有意识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张均的本事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这一转向密不可分。
“在‘再解读’与‘史实化’之间则另有方法互补。‘再解读’倘能以细密的文本‘周边史料’为基础,‘史实化’倘能以‘反现代的现代’等理论框架为自己插上思想的翅膀,无疑都会获得学术品质的提升。我自己近年试做的‘中国当代文学本事研究(1949-1976)’,就略有融‘再解读’与‘史实化’于一体的一点私意。”[2]这是张均有关其本事研究的方法主张,这句自我表述为探明其本事研究的形成背景和理论方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实际上,张均的本事研究是一种“史实化”的“再解读”,在吸收“再解读”研究方式的基础上,注入了更为详实的史料,“考”“释”并举,通过史料与文本的叙述对照,展现不同话语在意识形态场域中博弈的动态过程。
首先,张均的本事研究有意识比较同一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本事加工、结构方式、文类流变的差异。张均[3]对“歌剧《董存瑞》——长篇小说《董存瑞的故事》——电影《董存瑞》”的“层累”文学叙事进行探讨:在人物本事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艺术作品如何加工素材、塑造人物形象。歌剧《董存瑞》聚焦董存瑞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主要通过火中抢救玉兰子、侦察地形并掩护战友、舍身炸碉堡这三个具有一定现实依据、体现舍己为人精神的情节,将董存瑞塑造成“在历史中成长”的“新人”。然而,这种把个人的成长汇入阶级认同的叙事方式,使英雄的人物形象显得概念化。小说《董存瑞的故事》通过实地调查董存瑞的家乡、战场,访问其家人、战友,广泛收集其本事材料,在适当虚构和嫁接的素材加工中,呈现董存瑞“‘孩子王’——‘见习八路’——新兵——英雄”的成长经历,延续了董存瑞“在历史中成长”的“新人”形象,还将其表现得有血有肉、更加感性。电影《董存瑞》通过“嘎孩子”形象的创造,为董存瑞的“成长”注入了个人的欲望、情感等“主体的利益”,使人物形象呈现出可亲可感的革命美学。
其次,张均十分关注文本内外话语修辞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以及话语功能的动态博弈过程。在《召唤“隐藏的历史”——<暴风骤雨>动员叙述研究》[4]中,张均通过当事人记录土改动员过程的史料,从萧队长“改朝换代”“坐天下”的动员话语中分析出其“隐藏的历史”:乡间报仇雪恨、“夺袍上位”的权力斗争意图。而周立波向农民讲解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农民的大道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的话语传递的是“大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合理性。“隐藏的历史”和“大历史”话语在现实土改动员中互相缠绕,但当本事走向故事,坚持启蒙立场的周立波遵循“弱者的反抗”的叙事逻辑,把乡村“隐藏的历史”引导到阶级斗争正义的“大历史”中。
另外,张均借鉴文化研究的“历史化”方法,通过不同的历史文本分析不同权力或文化力量相互交织的关系。在《革命、叙事与当代文艺的内在问题》[5]中,张均发现:小说讲述的地主大多财力雄厚,拥有众多的土地,但品质败坏,弑杀、强奸、剥削、欺凌等无恶不作,而贫雇农大多品质高尚;电影讲述的地主家境与穷人没有多大差别,品质良善,通过自身勤俭积累财产,而农民残忍、贪婪,借助土改活动迫害地主。这体现了作家周立波和导演蒋樾、段锦川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立场:前者基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视点塑造“地主作恶/农民被压迫”的“刻板形象”,以此确证土改的合理性和解放的正义,并最终揭示农民参与“弱者的反抗”的历史必要性;而后者基于新自由主义的视点,颠覆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叙述的政治主张,将土地改革运动“下降为无意义的权力之争”和“非理性的暴力”。
二、本事与故事间的“缝隙”
张均的本事研究中的“本事”是与“故事”相对的。“本事”,即真人真事,是故事的原型、底本;而故事,是文学作品的内容,也即文本。张均的本事研究着眼于本事与故事的“缝隙”,通过各种史料的互证,辨析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的“多声部”,分析文本内外不同话语组成、文化因素和权力/阶层力量博弈的动态过程,并在分析正/反面人物现实经历和故事叙述的错位中,揭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事实践。笔者将张均的本事研究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博弈本事研究、人物本事研究和主题(问题)本事研究。
博弈本事研究通过分析不同的话语组成、文化力量、阶层/阶级等元素在文本内外互相缠绕、博弈的动态过程,揭示不同叙事因素在文本中共存的调节方式。博弈过程的双方通常处于主流/被边缘(隐性)的地位,在进行本事研究前,一些被边缘的力量在封闭的文本研究中消隐在历史的景深中。张均通过爬梳地方史料,进入小说的历史现场,在“倒置”的历史装置发现了“革命中国”主流力量以外的非主流因素,例如由宗族、邻里、宗派、宗族等因素组成的乡村社会组织、由游民文化主导的江湖世界等,从而在本事与故事的“缝隙”中揭示不同力量各自承担的叙事功能。在《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小说<红岩>史实研究》[6]中,张均从有关四川帮会势力的口述材料、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报告、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等史料中发现,当时1940年代的重庆鱼龙混杂、社会关系复杂,革命力量之外存在袍哥、军阀、地方帮会等犬牙交错的“江湖”势力。而小说把革命以外的江湖力量剔除干净,江湖转换成叙事元素嫁接进小说当中,例如小说在狱外斗争中大幅“升级”地下斗争的惊险系数,运用“秘密”、卧底设置陷阱;在狱内斗争中把有关“钉竹签”“夹手指”“老虎凳”等极端酷刑日常化等。由此,革命与江湖两种力量在动态的博弈纠缠中合力承担小说的叙事功能:革命形态的突显确认了英雄“力学的崇高”,而在“安全”边界使人心惊肉跳的江湖写法满足了“一体化”时代读者对于刺激、风险的想象。
人物本事研究以革命中国“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为研究对象,探究人物在现实原型和小说形象之间存在怎样的“缝隙”,小说人物在原型本事的基础上经历了怎样的叙事塑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人物的塑造起到怎样的建构作用。通过大量个案人物的研究,张均总结了“十七年”小说不同类型的人物所遵循的不同叙事法则,如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新人”梁生宝遵循“新人叙事学”法则、革命运动中的特务徐鹏飞遵循“特务叙事学”法则、《红岩》中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和《保卫延安》中英勇的解放军遵循“英雄叙事”法则等。在《<创业史>“新人”梁生宝考论》[7]中,张均指出:梁生宝取材于农村干部王家斌,王家斌本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农民,却被柳青选中为小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历史主体,这说明他自带“新人”特质或具有较强的“新人”可塑性。“新人叙事学”要求“体制选民”“根正苗红”,这使得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王家斌比在旧社会出入于赌场的蒲忠智更具“新人”资格。王家斌曾动买地的想法以发家致富,这一行为大悖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原则。柳青在小说创作中剥除了人物的经济和权力诉求,强化人物利他主义的善行,把梁生宝塑造成不沾权钱的“新式好人”形象。通过柳青传记和有关皇甫村的史料记载,王家斌带领村民走合作化道路,最终获得丰收,实际上得到了购买化肥和进口种子的政策扶助以及对不配合合作化的村民进行权力压制的思想教育。但小说舍弃了这两层重要因素,改写成梁生宝带领农民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丰收,使经济优先成为“新人叙事学”的重要原则。
再如《徐鹏飞本事研究》[8]探讨小说《红岩》如何塑造徐鹏飞的特务形象,使“特务”这一本来中性的词语受到读者的排斥。根据徐远举的交代材料、知情人的回忆录、公安部档案馆公开出版的《血手染红岩》等材料的梳理,张均发现小说大体实录了徐远举破坏《挺进报》、狱中迫害和屠杀难友这三件心狠手辣的事件。然而他光辉和悲悯的人性面遭到彻底删除,例如,他出身殷实之家,受过良好的知识教育,少有大志,年少从军得到重视的“前史”;忠义的人格信仰和帮助共产党人脱难的复杂经历。最终被剥夺“内心生活”的徐鹏飞在“特务叙事”的运作下被塑造成阴险凶残的形象。
张均挖掘人物本事,浮现了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交织着人性的善与恶、情欲与信仰的多面个体。好人不会好到底,坏人身上也有善良的人性。然而,“十七年”小说通常把人物区分出正面/反面,通过辩证的区分参与民族文化与情感认同的建构。正面人物以工农兵等绝大数基层民众为代表,是革命叙述所肯定的“历史主体”,他们承担“弱者的反抗”的历史任务,在历史斗争中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尊严,他们的斗争过程随之被“‘织入’苦难——反抗——解放的‘成长’序列”[9]。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本质主义的阶级和传统的儒家道德修辞生产“正面假象”。而反面人物以土匪、叛徒、特务等反革命势力为代表,是革命叙述所否定、批判的对象。他们作为战败者往往无法在历史中发声,失去讲述自我故事的机会,被动地接受正面人物的叙述,成为正面人物的“他者”,遭到“倒置”的叙事处理。他们在“妖魔化——野兽化”的处理中,被生产出愚蠢、残忍、狡猾的“刻板印象”。
主题(问题)本事研究以主题/问题探讨为导向,探究小说与本事所形成的某种悖论或张力,比如,混乱而又危险的西北解放战场经过怎样的叙事处理使小说《保卫延安》成为战争“史诗”,现实中普通的死难烈士进入小说《红岩》后何以成为崇高的英雄,革命小说《林海雪原》如何激活传统中国叙事学,从而融合革命与通俗两种叙事元素等。在本事与小说的矛盾张力的探讨中,张均发现作家在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法时,难免会暴露其知识结构、文学趣味、价值判断和人生信仰。而作家的写作姿态对小说的风格形成具有无法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新的“史诗”的诞生——小说<保卫延安>史诗考释》中,张均根据相关史料浮现西北解放战场的历史环境:由于部队伤亡惨重,不少战士产生畏惧心理,叛变、逃跑、自残现象频发,西北战场残酷而混乱。然而,杜鹏程出身穷苦,只接受“穷苦人民”的真理,抗拒国民党、地主、知识分子等非正义阶级的人生“道理”。加之,杜鹏程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对贪生怕死、自私好色的士兵极为鄙视,无意把他们以及革命之外的“异质”事件写进小说当中。正因为单方面呈现军兵忠贞的革命信仰、英勇的战斗意志和清教徒式的道德高标,小说“具有英雄史诗的精神”[10]。
当然,这三种本事研究类型的划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相融合,比如《<铁道游击队>的“徐广田难题”》[11]就融合了上述三种类型。“徐广田难题”作为一个问题以“文学塑造的英雄形象何以在现实生活中叛变”为研究导向。张均根据相关史料梳理徐广田的人物本事,指出徐广田忽然不干革命是因为与刘金山闹人事矛盾有关,加之家庭生计出现问题。在个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博弈中,徐广田为获取报酬的革命动机和将革命看作改变自身处境的活动逻辑与“人在历史中成长”的“新人叙事学”发生反向运作的龃龉,暴露出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叙事学”遮蔽人物“主体利益”的尴尬,最终现实中的徐广田脱轨英雄形象。
三、技术操作:史料爬梳、文本分析、理论素养
张均的本事研究可操作性强,研究思路有章可循,无论取法上述哪一种类型,都遵循三个操作步骤:梳理本事脉络——分析小说改写方式——探究叙事实践,这分别需要扎实的史料爬梳能力、细致的文本分析技术和广博的理论素养。
在梳理本事脉络的过程中,张均采用多种史料进行互证,包括口述文献、当事人日记、回忆录、历史档案、内部发行材料、口述纪录片等,力求在丰富的史料中通过“多声叙述”提供多面的历史真相。以《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12]为例,张均在考证《暴风骤雨》郭全海的原型郭长兴时,首先根据当地尚志市元宝镇主编的《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内部发行),梳理郭全海家人因地主韩老六的剥削和与蔡排长的冲突而失散、相继死亡的家庭状况,以及郭全海在土改中因表现出色而当上农会主任的经历。继而,张均在另一史料《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中找到了郭长兴的自述材料,确证了郭家家破人亡的经历。小说的反面人物韩凤岐主要取材当地地主韩向阳,而韩向阳在土改前夕就已经外逃,无法发声对证。张均通过当地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口述材料进行互证:当年的区委书记韩惠和有能力记录当时土改运动的元宝镇村民李万生都在《从光腚屯到亿元村》中回忆到韩向阳对农民欺压勒索的暴行,这些暴行与小说讲述的韩老六实际高度吻合;而元宝镇当年的许多农民在拍摄纪录片《暴风骤雨》(2005年摄制)中接受采访时,也多把小说的“韩老六”与现实的韩向阳混为一谈。小说还塑造了一批介于农民、地主之间的“坏根”,他们并无直接的人物原型。张均从《中共松江省委关于全省群众运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找到当时一些干部脱离群众的贪污腐化的具体表现,从而佐证了小说讲述“坏根”追逐权钱色的情节实际是当时腐化干部行状的现实投射。
另外,张均注重通过地方史料挖掘人物的前史,颠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阶级论,辅以其他历史研究成果,从现实生存逻辑和人性的复杂纠结中理解人物的真实行迹,具有现实穿透力。例如,在《悲剧如何被“颠倒”为喜剧——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土匪史实考释》[13]中,张均通过一位记者到“座山雕”(原型:崔明远)家乡山东新泰市龙廷镇采访其孙辈和当地知情人的材料,梳理崔明远入赘张家并继承岳父家产的发迹过程、劫富济贫的事迹和打击日本侵华力量的经历。张均还在地方史料的挖掘中找到了关于谢文东组建“抗日民众救国军”及其与日本激烈战斗的记录。他们的爱国情怀打破了过往对土匪集残暴、淫荡、狡诈于一身的认识。然而,曾经作为抗日英雄的他们在内战中成为共产党的敌对势力,与共产党发生正面冲突。张均通过有关土匪的历史研究,如英国贝思飞的《民国时期的土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田志和与高乐才的《关东马贼》,理解他们作为匪首的生存逻辑:他们作为“乡村豪杰”,并不如革命志士一样把民族与阶级视为最高信仰,而是基于自身地位和荣誉的考量,投靠有利可图的政党阵营,获得权力晋升的人生通道。
从本事到故事,张均以实录、改写、删除和虚构这四种方式探究作家对本事素材的加工方式。实录,即忠实记录现实生活。众所周知,“十七年文学”的作家大多是历史的在场者和亲历者,他们在参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意识收集在场素材,如《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兼任元宝区区委副书记,走访时“手不离笔,兜不离本”;《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系记者出身,长期随二纵四旅行军,在战争中写下了近二百万字的日记。进行小说创作时,这些作家首先面临筛选素材的问题,在架构故事的骨骼中,往往能够与当时的社会作出同步的历史价值判断,挑选事件的核心事件,并出于对故事人物的熟稔记录他们的性格特征和活动细节。这些实录的内容为本事研究提供“诗史互证”的重要依据。当然,受文艺意识形态和创作个性的影响,作家会对原型素材进行改写。分析改写内容能够在本事与故事的“缝隙”中窥探作家创作时所遵循的叙事原则和价值取向。比如受“人在历史中成长”的“新人叙事学”的影响,《铁道游击队》中的徐广田以维持生计为革命目的,却被改写成受党员思想教育影响而忠于革命;周立波的知识分子立场使得他将工作队/农民的关系改写成启蒙/被启蒙的关系,把颇为机智的农民写得幼稚而麻木。
“在左翼的文学批评中,仅仅关注作品中写到什么是不够的,还要关注它没有写到什么。这是左翼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尺度。”[14,p182]尽管作家不可能百科全书式地记录战争的全貌,但一些决定个人命运走向的事件和反映战争常态的细节会由于作家的顾忌而遭到删除,而这些顾忌大多构成了“十七年”小说“不可叙述”的禁忌。对这些“不可叙述之事”的挖掘,可窥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事成规。铁道队中的李正、东北剿匪小分队中的杨子荣作为抗日战士,在现实作战过程中延续了过往吃、喝、赌等游民生活方式,但这些情节在小说中遭到删除。小说还把杨子荣轻松对答座山雕黑话归结为杨子荣临时“练习”的结果。这表明,回避抗日或剿匪战士的不良生活作风、道德污点或“否定美质”是“英雄叙事学”的成规。虚构即无中生有,服务于作品的意义生产。有意思的是曲波对杨子荣“前史”的虚构。创作《林海雪原》时,曲波对杨宗贵(杨子荣原型)过去的人生经历一无所知,但仍然在小说中交代了杨子荣的“前史”,称他是雇工出身,父亲、母亲和小妹妹遭到地主的迫害,自己差点儿也被加害而死。这种虚构的经历接近“男版”《白毛女》,分享了相同的革命意义:雇工身份符合革命英雄的阶级属性,他的过去成为阶级压迫的历史见证,而反抗压迫成为他革命的动力。
张均的本事研究以实践叙事学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历史叙事学等理论。所谓“实践叙事学”:“即是摆脱与‘纯文学’概念紧密关联的形式主义叙事学(亦称‘经典叙事学’),将以讲述故事为主要特征的文学行为看成一种参与社会历史变迁的话语实践活动。”[15,p28]张均主张用文学社会学的眼光研究文学,勾连文学与历史、社会、文化、政治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实践叙事学”主要探讨四个层面的内容:叙述动力、故事策略、叙事机制和阅读效应。
张均的本事研究认为“弱者的反抗”构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动力。在《怎样“塑造人民”》[16]一文中,张均引用后殖民理论阐释“弱者的反抗”——革命求助讲述“工农子弟”(弱者)参与革命获得民族解放和个人尊严的文学,获得民族建构的自信以及加固“工农子弟”的历史地位。《保卫延安》塑造英雄的“正面假象”,把他们视为历史主体放置在成长“启示录”式的历史主义框架中,通过他们言说艰苦卓绝的革命过程和民族解放、复兴的历史成果,最终达到“弱者的反抗”的叙事目的。
叙事策略关乎“作者之眼光”和“关联语境的‘选择’”,主要探讨“可以叙述之事”“不可叙述之事”和叙述中的“看”“说”问题[15,p28]。在《红岩》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小说叙述中的“宰制话语”,革命信仰成为叛徒“不可叙述之事”,像李文祥、冉益智叛变后,内心惭愧,仍为同志、家人着想,但这些柔肠百转的内心世界无法在小说中诉说。而甫志高计较个人得失的“个人主义”和知识分子软弱的负面性格成为“可以叙述之事”。张均多次引用E H卡尔、理查德·艾文思、海登·怀特等人的历史叙事理论,分析负面人物在历史和文学中失去自我言说的地位,他们只能通过胜利者的眼光被言说,成为正面人物的他者,承担“负面的假象”。
“事出有因”,叙事机制是编织“可以叙述之事”时所采取的因果机制。比如,在人物塑造上,“十七年文学”中的工农兵作为历史主体被放置在“人在历史中成长”的因果序列,随着革命的进行与深入,逐渐摆脱初期幼稚、不成熟的状态,获得历史本质的清醒认识,自动承担解放民族、争取民族自由和发展的历史任务。而负面人物大多接受“倒置”的叙述机制,在被“妖魔化——野兽化”的“同质化的处理”中,“掉进了预定的排斥程序”[8,p81-82]。再如,《暴风骤雨》以“弱者的反抗”为文学诉求,在土改前以“地主施害/农民受害”的因果关系呈现农村旧有的权力结构,随着土改的深入,小说反映“地主压迫/农民反抗”的斗争过程。
阅读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给读者创造“真实世界”的经验,二是重构读者的伦理观念。前者的“真实世界”是对现实的创造性重构。在《红岩》中,江湖因素“不可叙述”,而艰苦的革命斗争得到突显,从而构造了“力学的崇高”的经验世界。后者是小说意识形态输出的现实功能。《红岩》展现共产党人忍受酷刑时的惊人意志和忠诚不贰的革命信仰,这种“力学的崇高”重塑了读者对共产党和革命信仰的情感认同。
[1] 张均.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之我见[J].文艺争鸣, 2019,34(9):10-15.
[2] 张均.我所接触的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J].当代作家评论,2018,35(5):68-73.
[3] 张均.董存瑞形象演变研究[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4):77-85.
[4] 张均.召唤“隐藏的历史”——《暴风骤雨》动员叙述研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34(6):10-23.
[5] 张均.革命,叙事与当代文艺的内在问题——小说《暴风骤雨》和记录电影《暴风骤雨》对读札记[J].学术研究, 2012,55(6):126-133.
[6] 张均.革命与江湖的辩证法——小说《红岩》史实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7(2):166-172.
[7] 张均.《创业史》“新人”梁生宝考论[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72(1):48-57.
[8] 张均.徐鹏飞本事研究[J].当代作家评论,2017,34(4):77-86.
[9] 张均.发现“人的文学”[N].社会科学报,2019-10-10(5).
[10] 张均.新的“史诗”的诞生——小说《保卫延安》史诗考释[J].扬子江评论,2014,9(4):26-33.
[11] 张均.《铁道游击队》的“徐广田难题”[J].文艺争鸣,2017, 32(11):46-52.
[12] 张均.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2,12(5):139-146.
[13] 张均.悲剧如何被“颠倒”为喜剧——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土匪史实考释[J].文艺争鸣,2016,31(2):83-91.
[14]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82.
[15] 张均.实践叙事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J].文艺争鸣, 2016,31(12):28-36.
[16] 张均.怎样“塑造人民”——小说《保卫延安》人物本事研究[J].文艺争鸣,2014,29(5):54-61.
“Starting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vestigating in Literature” : On Zhang Jun’s Study of Original Stor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HEN Wan-q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Zhang Jun’s study on original story is mainly based on the red classic novels of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which combines the methods of “reinterpretation”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 used 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explore the “gap” between the original story and the fiction. He revealed the novel’s production process and narrative practice by utilizing postmodern theory, connecting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tex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Zhang Jun’s study on original story: game original story study, character original story study and subject (question) original story study. The specific oper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eps: sorting out the context of the original story—analyzing the way of rewriting novels—exploring narrative practice. This requires solid historical data combing ability, meticulous text analysis technology and extensive theoretical literacy.
study on original story; socialist realism; practical narratology; Zhang Jun
I206.7
A
1009-9115(2020)05-0046-06
10.3969/j.issn.1009-9115.2020.05.010
2020-02-03
2020-05-27
陈婉琴(1996-),女,广东佛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