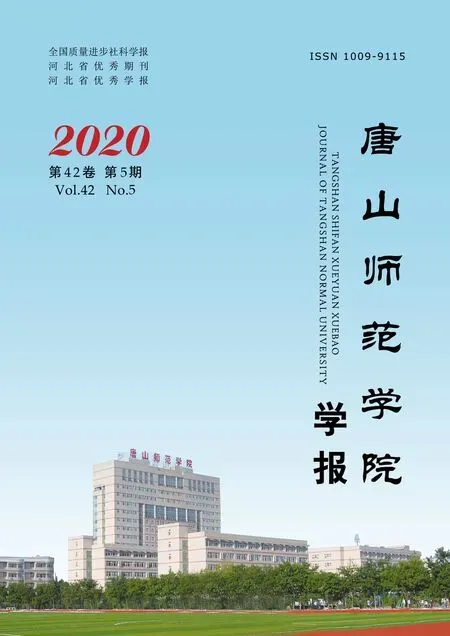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曹妃甸文学论
2020-01-09孙溢,杨扬
孙 溢,杨 扬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曹妃甸文学论
孙 溢1,杨 扬2
(1. 唐山师范学院 办公室,河北 唐山 063000;2. 唐山师范学院 外语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曹妃甸文学是曹妃甸发展建设的文化呈现,讴歌了曹妃甸建设者的科学决策和无私奉献精神,描绘了曹妃甸发展建设的进程,彰显了“锲而不舍、艰苦奋斗”的“曹妃甸建设精神”,形成了浑厚而秀美的文学风格,并表现出历史与现实紧密衔接、家国情怀与故乡情愫融为一体、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和谐一致、古典和现代的双重运用的写作特点。
曹妃甸文学;创业精神;文学风格;写作特点
曹妃甸是一片神奇土地。英雄的曹妃甸人在广袤的滩涂上创造了奇迹,现代版的“精卫填海”,广袤滩涂和海中孤岛变成了一个现代化世界大港和现代化滨海新城[1]。如今,曹妃甸已成为环渤海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
曹妃甸是一部英雄传奇,这里曾是斥卤不毛的盐碱荒滩和遗弃在茫茫渤海中的带状孤岛。在进入20世纪中叶后,这里却创造了令世人赞羡、世界称奇的历史。这里的海滩早在我国“一五计划”时期,就被国家列入153个重点开发项目之一。无数创业者筚路蓝缕、开拓进取,在茫茫的滩涂上建造了国营河北省柏各庄农场。经过几代农垦人的艰苦创业、不懈奋斗,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不毛之地建成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成为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国营农场,创造了独特的“农垦文化”。著名作家浩然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盛赞,誉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的美好图式。1982年柏各庄农场在农垦体制基础上建立唐海县,2012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曹妃甸区,到今天已经形成“一港双城”的宏大图景。因此可以看出,曹妃甸精神的内核就是创业精神,即开拓进取、勇往直前,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在这方热土上充满了现代化大工业、大农业的时代元素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丰富表情,所以我们可以将曹妃甸文学称为创业文学。
曹妃甸是充满丰富历史内蕴和现代化元素的城区。她原本是茫茫渤海中的一个充满诗意的孤岛,尽管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和浪漫的传说,但在大海上不知漂泊了多少个年代。岁岁年年,涛声依旧,孤立无助地在茫茫的渤海中守望唐山,渴望与陆地的连接。是新的世纪、伟大的时代把她与魅力新唐山、与现代化中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成为新世纪中国建设的新范本。今天在这里,从一块发热的滩涂到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从一座古老灯塔到世界级的港口,到处可见科学的含量,历史的容量和人文质量。这样,就使得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有了这样一个历程:30年前看广东(深圳),20年前看浦东,今天看冀东(曹妃甸)。如今曹妃甸这个“钻石级大港的巨大引擎”正在拉动唐山、拉动河北,将来也必将拉动整个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曹妃甸正在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高度和谐、环境最适宜人类居住的美丽的滨海城市。如今她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是河北沿海重要增长极,也是北京产业输出最大的承载地;是唐山市“一港双城”战略的主战场,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努力建成”的排头兵。在这里,有世界级大港、世界级钢铁基地、世界级石化基地,亚洲最大的盐场、河北最大的国营农场。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重要的经济地位,形成了曹妃甸独特的地域文化。自古以来,曹妃甸就融汇了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妈祖文化、海洋文化、东北文化、京津文化、老呔文化、中州文化,是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荟萃之地。因此,她也创造了大工业与大农业完美契合,农场文化与海洋文化有机融合的曹妃甸文化。
曹妃甸“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巨大变化鼓舞和感染了大批作家,他们尽情抒怀,写就了一部部(篇)力作。如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就曾在曹妃甸(原唐海县)挂职副县长,就以这里的“立体农业”“水上农业”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红月亮照常升起》。“雪莲湾”(南堡开发区)曾是关仁山的创作基地,他在这里开创了“雪莲湾系列”。他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奠基作《苦雪》,继而又创作了长篇小说《白纸门》,中短篇小说《蓝脉》《躁潮》《太极地》《醉鼓》《红旱船》《风潮如诉》等,从而享誉文坛,走向全国。曹妃甸文化也成就了著名报告文学家王立新,“海湾三部曲”(《曹妃甸》《首钢大搬迁》《大海上的钢城》)生动体现了“锲而不舍、艰苦奋斗”的“曹妃甸建设精神”,描绘了曹妃甸创业发展的恢宏进程,尽情讴歌建设者的科学决策和无私奉献精神,作品表现出了宏大气势。它“之所以表现出大气势、大气派,就是因为它拥抱了当下变革的生活,曹妃甸的建设和发展,就是当下变革的社会的缩影。作品除了正面描写建设中的曹妃甸,同时还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所以,它是立体的、厚重的。”[2]
曹妃甸的过去也不是文学的荒漠,有着较为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传承。从传承看,曹妃甸东半部分属于滦县,西半部分属于丰润,都是历史比较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老县区。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曹娴就是本地的渔家女儿,与李世民共同演绎了一段凄美的爱情传奇。这个传说由来已久、世代相传。作家刘兰朝、孙梦成根据曹妃的传说写出了《大唐曹妃》,朱永远和刘玉相也创作了《曹妃甸长歌》。作为曹妃甸的子孙,他们试图通过曹妃甸的历史传说来探寻曹妃甸的千年历史,并以此表现民族精神、弘扬传统美德。可以说,这两部作品为曹妃甸的开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人文依据,也为曹妃甸这个千年古岛增添了更加迷人的色彩。当然,曹妃甸文化的发展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58年到1961年这个时期,人民日报社、中国文联等中央单位的陈企霞、萧乾、钟惦棐、唐因、唐达成等108名右派在这里劳动改造。他们的到来“给海滩上这片文化荒漠带来些许亮色”,对传承地方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萧乾先生和季音先生曾多次撰文,回忆在柏各庄农场那段不平常的岁月”(张秀成《文化荒漠上落魄的书生们》)。如著名红学家蓝翎回忆录《龙卷风》第三章《从渤海湾到黄河滩》中,“有万余字记述了他在柏各庄农场改造的苦难历程。文中,有对自己在那场政治龙卷风中坎坷遭遇的感慨;有对萧乾、钟惦棐、陈企霞等老一辈文化人蒙冤受屈的同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柏各庄农场这片土地的眷恋;行文所至则充满了对曾在困境中给予他们同情和关爱的农工和干部的感激之情”(张秀成《走近蓝翎》)。改革开放之后,曹妃甸成为文学创作的热土,文学创作日益繁荣,如孙武勋创作的诗歌集《海韵诗稿》《海韵歌吟》,散文集《心路》和《山雨》;孙梦成创作的散文集《水乡清韵》《双龙河畔》,诗集《左古典右现代》,长篇小说《大唐曹妃》(与刘兰朝合著);杨海光的报告文学《渤海儿女》《大海娇子》;李庆玺的散文集《乡韵诗情》《史话曹妃故里》;郑春雷的诗文集《爱上曹妃甸》;付秀宏的散文集《行游曹妃甸》等。随着曹妃甸的建设发展,曹妃甸文学的发展前景也会像渤海东升的旭日,一片灿烂辉煌。
曹妃甸文学具有自身特有的发展历史和文学风格,结合其历史和文化背景,形成了浓郁的地缘特色,特点鲜明。
一、历史和现实结合紧密
曹妃甸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而今曹妃甸的后人们则试图通过曹妃故事来探寻曹妃甸的千年历史,还历史以真实面目。有两部作品在反映曹妃的文学作品中反响较大。一部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唐曹妃》,由刘兰朝与孙梦成二人合著,一部是长篇历史小说《曹妃甸长歌》,由朱永远与刘玉相合著。两部作品将史料与传说有效集合,历史与现实巧妙呈现,从人生和形象不同层面对曹妃进行了塑造,并充分展现了其承载的深刻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对于“彰显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传统,促进当前乃至以后地域文化建设,无疑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1]。
《大唐曹妃》的成功之处在于精心塑造了曹妃这个具有大爱之心、大义之举、大仁之德、大侠之气的民间奇女。她因与唐皇奇遇而走入皇宫,但她不安于在皇宫锦衣玉食的生活,而是积极参与唐皇治国济世救民的活动,并与唐皇一起东征。她在征途中冲锋陷阵,为受伤的将士施方疗伤。在返程探亲的海上,她不顾安危而抢救遇险的船只和船员,最后因积劳成疾而香消玉殒于故乡的海岛上,成为了故乡人民历代传颂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在曹妃身上集萃着中华女性的美德,她的外柔内刚、忍辱负重、惩恶扬善、扶危济贫、舍己为人等美质成为了曹妃甸精神的源头[3]。同时作品还把她独特的命运变化置于唐初这个特定的百废待兴、治国安民的大背景中,折射出了唐初的时代变迁,增加了作品的历史深度和生活厚度,从而给曹妃的生命历程增添了浓重的历史色彩,让她的人生经历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曹妃甸长歌》则把曹妃甸的历史人物与曹妃甸的千年历史熔铸为一体,体现出曹妃甸精神的源远流长、深邃厚重。在这部跨越千年的小说中,既有唐王东征、妃子曹娴为国为民献身香殒古岛的婉丽凄美的故事,有宋建炎年间曹妃后裔曹勋兵出曹妃甸、夜袭马城金节度使国尔嘎的征战,也有民国初年孙中山为中华民族的富强而在《建国方略》中要把曹妃甸建成深水良港的宏伟志愿,以及在21世纪初的今天,英雄的曹妃甸人无私奉献、勇于开拓,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区的创业精神……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衔接,使得这部长篇小说既有了丰富的历史底蕴,也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这对我们认知历史、洞察现今有着不可多得的审美教育作用。可以说,这两部历史小说是曹妃甸的恢宏历史,也是曹妃甸精神的赞歌,从中既可以看到曹妃甸千年的历史变化,也可以了解到曹妃甸人为了国家、民族和百姓利益而不怕牺牲、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
值得称道的是王立新的“海湾三部曲”(《曹妃甸》《首钢大搬迁》《大海上的钢城》),可称得上充满时代精神的英雄史诗。长篇报告文学《曹妃甸》全景式地展现了革命先驱、仁人志士、国家各级领导人为建造北方大港所做出的远大规划和科学决策,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描写了决策者、开拓者和创业者的精神境界,真实地再现了曹妃甸建设者所体现的锲而不舍、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英雄壮举。《曹妃甸》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她不仅是一部充满时代精神的作品,也是一部充满历史容量的文本。从孙中山的建造北方之不冻大港到现代化港口的建成整整一个世纪,作品记录了这个海中孤悬之岛的巨变的历史过程,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而《大海上的钢城》则全景式地展现了首钢大搬迁的艰难历程以及北京与河北携手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化钢城、积极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壮举,生动地描写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首钢人创造生产奇迹的历程,弘扬了首钢人攻坚克难、不屈不挠、勇创佳绩的精神,同时作品也见证了曹妃甸开发建设的奋进之路[4]。
二、家国情怀与故乡情愫融为一体
曹妃甸的作家是以家乡为精神的家园、创作的母体,以浩瀚的大海、无边的滩涂、翻滚的稻菽为创作背景,表现了“记得住乡愁”和对家乡的眷恋。如孙梦成的散文集《双龙河畔》就是思乡、恋乡、怀乡情绪的真挚表达。这部散文集布满了故乡元素和家族脉络,显示了家园之恋和亲情之美。正是因为作者的恋乡情绪的真挚表达,具有地理指向和心灵层面,才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作品“接乡愁、恋故园”的柔软质地,还有作者“何以回家”那切入肌肤的痛感。李庆玺的散文集《乡韵诗情》同样表达了“对家乡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幽幽深情”,寄寓了他对家乡人的无限热爱之情。他充满激情地歌颂了家乡人朴实憨厚、心地良善的传统品德,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美好天性[1],使我们可以真切感受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曹妃甸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痕迹。
曹妃甸作家有着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创作中,他们把爱国家与爱家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即把家国情怀与故乡情愫融为一体。如孙武勋的诗歌就表现出了热爱家乡、歌颂祖国美好情怀。他用诗美化家乡、诗化祖国。通过他的诗篇,我们看到了曹妃甸“但见粼光浅水,更有夹岸垂柳,绿叶映衬芦花羞,无垠稻田黄透”(《秋色赋》),感受到了他“扶嫩芽,著风雨,铸灵魂,担道义”(《园丁礼赞》)的使命意识,领略到了他“立命为官德在先,克己修身莫忘严,政声总在人去后,闾巷口碑最值钱”(《全县党风廉政建设大会感言》)的人格力量。
作为曹妃甸子孙的孙武勋、孙梦成、郑录礼、刘兰朝、郑春雷、李克东、李连君等人的作品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书写,为即将湮灭的历史留真,生动记录了曹妃甸的变迁,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生动感人的曹妃甸“史记”。
三、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和谐一致
文学作品应具有深刻的历史理性,又应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导精神,也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内核和精髓。这种精神的强大底蕴和生命力就在于作家对国计民生的挚爱和关注,对国家和社会所担承的责任和使命。它不仅要求作品真实地再现现实,而且要求“以热情为元素”,把对生活的愿望和理想展现出来[5]。曹妃甸作家的作品表现出了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契合,诗性和人性的统一,因而有了较高的质量和品位。如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纸门》,描写了在物欲进化和精神退化、物质进步和道德退步的激烈冲突和碰撞中凸显出的复杂的社会景象。为了保持“雪莲湾”圣洁的尊严,七奶奶、疙瘩爷、黄木匠等老一代雪莲湾人恪守传统文明,不与世俗妥协,甚至以身去殉自己所信奉的理想;麦兰子、麦翎子、大雄等新一代雪莲湾人有强烈的进取心和开拓意识,为渔村的进步和渔民的富庶舍弃个人利益而努力地工作着、奋斗着。正是这些小人物的奋斗牺牲和与世俗的不懈斗争,才实现了雪莲湾社会主义新渔村的和谐进步。
杨海光创作的大型评剧《三进门》则是一部反映城镇建设中拆迁工作的好戏。这部戏虽然写的是拆迁工程,但深刻地揭示了在和平年代如何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个重大课题。从平民化的视角入手,细节真实感人,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反映拆迁工作的“样板戏”“教科书”。
郑录礼的小说用欧·亨利小说的笔法,小中见大、纸短情长,表现出深刻理性和丰富的人性。如《褐色的牙齿》以暗喻的手法写一个村子的人都是褐色的牙齿(因饮用那井水所致,暗指一种文化积淀的负效应),他们却视为正常,不以为怪,“怡然自乐”。“我”因母亲去世,后被寄养在姥姥家,未被井水污染而有一口“洁白”的牙齿,但见到这种褐色牙齿感到“背冒凉气”,后因拒绝与有褐色牙齿的表妹成婚而惹怒了全村老少。“我”无力对抗这种“集体无意识”,而与表妹成婚。后来“我”也有了一口褐色的牙齿,而对这种褐色的微笑熟视无睹,并在与表妹褐色的长吻中感到了“温馨安逸”。
四、古典和现代的协调统一
曹妃甸作家擅长从古典诗词和民歌中汲取有价值的成分,使得作品呈现出历久弥新的魅力。孙梦成的诗集《左古典右现代》使用了古典和现代多种写作技法,在作品中也显露出壮美和优美两种美学风格。他的古典诗有大场面的意象,有家国和民族的忧思与豪情,有人世间所有的悲欢”,呈现出了豪放博大之美。他善于从历代古典诗歌中汲取精髓,领悟真谛,所以他的古典诗既有盛唐诗歌“笔力雄壮,气象浑厚”的雄浑博大的气势,又有魏晋诗歌“慷慨悲凉,简练刚健,明白晓畅”的风韵。如《七律·黄河壶口瀑布》《七律·登华山感怀》都写得气势豪迈、昂扬奔放、刚健有力。不仅如此,作者也善用现代技法写诗。如《写给母亲的歌》就用现代诗的句式表现了诗人对母亲的大孝之心、大爱之情,催人泪下,动人心魄。当然这部诗集不仅是诗学技法的运用,也是作者家国情怀的表达。在诗集里有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思与豪情,有对个人和家庭的亲情与和美,有对社会和人生的认知与感悟,有游历和观赏的感怀和寄托。可以说,他把对生命的思考、对人生的体验、对理想的追求、对诗歌的理解都凝聚和投放在诗集中,因而有着多重的生命意蕴和诗学意味。同样,关仁山在小说创作中也充分运用了传统和现代手法。他的“雪莲湾系列”颇有些古代传奇小说的色彩,如《蓝脉》中的蟹乱,《苦雪》中的人与海狗的搏斗,《秋殇》中的海骡子在海里与凶狠的魟鱼死命厮杀等,但他在小说创作中更多的是使用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技法,如黑色幽默、象征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等。郑录礼的小说也同样运用了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派小说手法。他在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写法的同时,还运用了黑色幽默、象征和隐喻等现代派手法,使得小说意蕴深厚、意味深长。
新时代,新征程,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如今曹妃甸的作家们凝心聚力,接续前行,奋力描绘新时代的家乡面貌,努力创作具有历史内涵和时代特征的佳作,以此回报家乡人民的重托,为曹妃甸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为唐山“三个努力建成”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1] 杨立元.雄浑厚重明丽秀美——曹妃甸文学论[EB/OL]. (2018-10-18)[2019-12-01].https://www.sohu.com/a/260219258_100279781.
[2] 武翩翩.长篇报告文学《曹妃甸》作品研讨会发言摘登[EB/OL](2007-03-29)[2019-12-01].http://www.chinawr iter. com.cn/bk/2007-03-29/27889.html.
[3] 星雨如歌的博客.莫大的鼓励与鞭策——杨立元教授为《大唐曹妃》写的文艺评论[EB/OL].(2011-08-03)[2019- 12-01].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6ec1ef0100wq27.html.
[4] 中国新闻网.长篇报告文学《大海上的钢城》首发,展现首钢人新生活[EB/OL].(2016-01-16)[2019-12-01].http:// www.chinanews.com/cul/2016/01-16/7718830.shtml.
[5] 王海英,杨立元.新现实主义小说现实品格论——兼论新现实主义小说与改革文学、新写实、先锋文学之不同[J].唐山学院学报,2003,16(1):80-85.
Facing the Ocean with Spring Flowers Blossoming:On Caofeidian’s Literature
SUN Yi1, YANG Yang2
(1.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e,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2.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Caofeidian literature is a cultural presentation of Caofeidian’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t vividly shows the magnificent process of Caofeidian’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t enthusiastically sang the spirit of Caofeidian builders’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and selfless dedication, forming a vigorous and beautiful literary style. It shows the writing technique of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integration of homeland and hometown feelings, the harmony of historical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spirit and the dual applications of classical and modern writing styles.
Caofeidian literatur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ry style; writing features
I04
A
1009-9115(2020)05-0036-05
10.3969/j.issn.1009-9115.2020.05.008
2019-12-26
2020-08-15
孙溢(1989-),男,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新闻业务。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